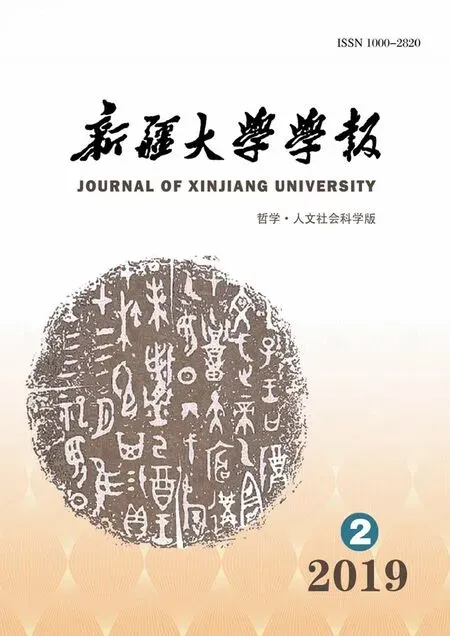论实验使用例外与创新的关系及对中国的启示*
马忠法,马明远
(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200082)
一、引言:实验使用例外——公共领域的一种形式
人类史上知识产权制度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于“羊吃人圈地”运动的“圈地”运动,即将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在性质上属于公有领域的人类知识或智力成果化为私人权利的领域,也就是让智力成果等知识的贡献者在特定时间内享有一定的专有权;虽然它遵守“公共领域是原则,知识产权是例外”[1]1-3之信条,但毕竟将可能最有价值的部分归属私人领域,影响社会大众的使用;而不当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有可能影响人类的整体创新活动。“随着共享经济的到来及共创、共有、共享和共赢等创新模式的形成,知识产权的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问题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18
何为“知识产权公共领域”?根据《韦伯斯特英语大词典》的解释,公共领域是指“包含属于公众范围之内、不受版权或专利保护并可以被任何人使用的财产权之领域(realm)”[3];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公共领域指发明或作品等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普遍状态,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无偿使用”[4];而有些学者将其界定为“特定的状态,即专利、版权、商标、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因过了保护期或被泄露等原因不再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的状况”[1]1-3。因此,可以说,公共领域不一定就是指“区域、空间”等,还可以指“状态”,甚至一种制度等;简言之,对它的了解,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因此,公共领域有很多种,例如权利保护期到期自动进入的公共领域、因客体界定而被划分进的公共领域①例如著作权法中的思想/表达二分法将“思想”归入公共领域,专利法中的发明/发现二分法将“发现”归入公共领域。、因某种具体事由而暂时不保护权利人而产生的公共领域等。
实验使用例外(Experimental Use Exception)就是产生上述所列现象中的最后一种公共领域的豁免②本文所称的实验使用例外(Exception)与实验使用豁免(Exemption)具有相同含义。“例外”侧重于方式,“豁免”侧重于结果,但实质上都是创造了知识产权的公共领域。,其含义是第三人对于受保护专利有限地、不妨碍正常利用、不损害合法利益地实验性使用不应构成侵权①有限性、不妨碍正常利用、不损害合法利益三个标准源自于WTO专家组对TRIPS协定例外条款的分析,会在下文详述。。其目的在于豁免专利的实验性使用,以保护并促进科技创新。这与公共领域“创造的前提、知识产权制度正常运转的工具”[2]22的价值是完全一致的。这一制度在美国自从产生已有超过百年时间的发展②美国的实验使用豁免是Story法官于1883年在Whittemore v.Cutter中首次创造。,其基本趋势是不断地缩小该例外的适用范围;目前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在世界范围内适用条件最为严格的实验使用例外。而欧盟、日本、印度等在各自专利法律体系中也有实验使用例外的规定。当一个社会的科技进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旧有的专利很容易对继续进步产生阻碍。美国科学进步协会(AAAS)的一项调查显示:“40%被访者认为研究中遇到确保专利的问题;58%被访者认为研究因此被迟延;另28%被访者因为专利方面的问题被迫放弃研究。”[5]846
本文将在探讨实验使用例外对创新影响的基础上,分析实验使用例外制度的国际规范及主要国家对其的规定并进行比较,进而分析我国的实验使用例外制度并论证其完善的建议。本文第一部分简要分析实验使用例外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为后文研究其对创新的影响、具体制度的分析等提供基础。第二部分将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角度,讨论实验使用例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本文第三部分将结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分析和论证强调将知识产权作为私权保护的该协定给各成员方的实验使用例外留下制定适应本国经济发展水平所需要的法律制度的灵活空间。第四部分将梳理各国实验使用例外制度及其区别,以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本文第五部分将分析我国实验使用例外制度的现状及其不足并提出完善的建议。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各部分内在的逻辑关系是:首先是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宏观数据)的角度探究实验使用例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这是本文观点的基础;其次基于如果为了创新而需要扩张实验使用例外的范围、限制专利权人的权利等容易违反成员方在TRIPS协定下保护专利权义务之可能性,讨论、分析TRIPS协定中的例外条款给各国留下的灵活应用实验使用例外条款的空间,这是本文结论的前提;再次,我们对各国实验使用例外制度进行了梳理、对比和分析,以给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最后本文在前面讨论、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实验使用例外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二、实验使用例外对创新影响的研究
关于实验使用例外对创新的影响,可以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索。下文将分别就此展开分析和论证。
(一)实验使用例外对创新影响的理论研究
一般而言,解释专利合法垄断性的理论主要有两种,即激励理论与披露理论。激励理论,如林肯所言,是“为天才的创造之火加上利益的柴薪”。该理论认为,通过授予发明人特定时间内的合法垄断权,使其获得经济利益(即回收研发投入的成本并获得预期的利益),可以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发明创造行业,从而从整体上改进一国的创新水平。但是这一理论受到非常多的争议。不同学者对于专利到底是否鼓励了创新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有学者认为现有的专利可能会阻碍后来的技术改进和相关的技术创新③参考Heller,Michael A:Can patents deter innovation?The Anticommons in Biomedical Research,上传日期1998年5月1日,访问日期2018年5月10日,网址:http://science.sciencemag.org/.。另一种理论是披露理论,该理论将专利授权看作是一种国家代表公众与发明人所签订的社会契约。在该契约中,国家许诺给予发明人一定期限的垄断权保护,其对价就是发明人承诺披露自己的发明及在保护期满后让发明技术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因为如果国家不许诺以专利的形式保护发明人的权益,那么发明人就可能会隐藏自己的发明,而社会就得不到相关的知识。为了得到国家授予的垄断权,发明人必须要全面的披露自己的发明。这在英国称为充分披露规则(doctrine of sufficient disclosure),在美国称为书面描述与能够实现要求(written description and enablement requirement)。由于专业水平上的限制,专利审查人员也不可能完全保证授予的专利一定是有用的、根据权利要求说明书能够完全地实现这一专利。有些专利申请人往往会巧妙地书写其权利要求说明书,达到隐藏更多、披露更少的目的。例如,信息技术行业获得的专利中,有很多对其发明的性质说明很少,无法给公众增加多少知识财富。针对这种情况,实验使用例外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豁免为了验证专利实用性而实施专利的行为,可以让公众也参与到对已授予专利的检查监督中。如果将测试某专利实用性的行为也认定为侵权的话,就会给专利权人过大的权利。一个被扭曲的披露要求会造成过度的保护,自然也不利于创新。
实验使用例外与创新更加直接的联系是它可能会促进一些被专利制度的垄断性所阻碍的对原专利技术的改进。严格地保护专利权人的权利、禁止一切形式的未经许可的使用可能会阻止由第三方进行的、可能会对原有专利做出改进的研究。因此在一定情况下限制专利权人的专有权是有必要的。
举例而言,美国在实验使用例外方面采取严格态度。在基因技术领域中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案件,即Myriad案。被告Myriad公司发现BRCA1/2基因突变与卵巢癌和乳腺癌的发病有密切联系,并对该基因申请专利保护,以将其应用在自己公司开发的疾病诊疗服务中。美国分子病理学会(AMP)起诉美国商标专利局(USPTO)与Myriad公司,认为“对基因授予专利权是一种过度的垄断。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专利权人的权利”①参见653 F.3d 1329(Fed.Cir.2011).。该案讨论的焦点是基因的可专利性问题。尽管法院最终肯定了专利权人的主张,但是它也给基因的可专利性附加了一定的条件,即即使基因是可以受专利法保护的客体,而在实验使用中给予一定豁免也是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在Myriad 公司之后,一家法国研究机构——居里研究所——利用自己的精梳DNA 彩色条形码(combed DNA color bar coding)技术,从Myriad公司检测为阴性(也就是没有突变)的患者身上检测出了BRCA1 基因突变。而且Myriad 公司的技术“只能检测基因小规模的缺失和重组”②参见Williams-Jones,Bryn."History of a gene patent:tracing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ommercial BRCA testing."Health LJ 10(2002):123.。这说明Myriad 公司的技术并不完美,是有待改进的。而Myriad公司的专利却可能阻止这种改进。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员Arupa Ganguly 就因为Myriad公司的压力被迫停止临床性和研究性地对专利基因的测试③参见Morowitz,Rachel."Overcoming Barriers Created by the Patent System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and Timely Response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Fed.Cir.BJ 25(2015):621.。这些现象可能会成为促使发达国家将研发外包到印度等对实验例外采取较宽态度国家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国与国之间专利法上的实验使用例外的宽窄之分会对研发投资产生流动压力,促使资金从较窄的国家流向较宽的国家,从而规避可能的法律风险。这种现象会在下文有详细的分析。
Iles提到过一种假设性的情形,更加进一步地印证了狭窄的实验使用例外对本国的创新相对于其他国家会造成比较性的劣势。假设R国的专利法中实验使用例外较为狭窄,R 国的技术改进者在技术改进过程中就更容易遇到专利侵权诉讼。由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基本上是由该国自行决定的,R 国的发明人对同一专利在不同国家获得的专利保护程度也是不同的。如果另一国家允许更加广泛的实验使用例外,那么第三方在该国就对R 国人在该国持有的专利产品有更大空间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创新,而由于R国本身的实验使用例外较为狭窄,R国人对外国人在本国持有的专利的研究和创新反而处处受限。这显然会使R国的创新事业相比他国处于一种劣势之中。”[6]61现实中,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日本专利法“并不阻止那些受美国法保护的专利在日本处于实验目的被使用”[7],从而为日本的技术创新解脱了束缚、提供了活力;不难理解,为何日本在二战以后其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与其专利法制度有一定的关联,而其中较宽的实验使用例外无疑是有利于其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实验使用例外对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进行实证研究,首先要从实证的意义上选择评估创新的视角。一项创新在创新前需要投资,所以研究和开发(R&D)的投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对象;创新时需要研究人员,而研究人员的性质,即属于公司、学术机构还是科研所等,也值得关注;创新后可能申请专利,因此与专利相关的数据也是评估创新的一个角度。
美国是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其技术研发之中的专利之争往往发生于其内部,因此可以以其为例,探究实验使用例外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许多学者批评“美国缺少像日本一样的、统一的实验使用例外条款,因此对大学的基础研究有消极影响”[8]。也有评论指出,“许可费和很高的交易费用威胁减缓大学进行的基础研究”[9]。但是,一项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显示,1979年至2000年间大学所有的专利所占所有实用专利的比例在稳步上升,学术性专利占新专利比例从二十年前的0.5%上升到5%。此外,获得专利的学术机构从20世纪70年代的300家上升到1998年的3153家。同一研究还显示:“自1953年,学术研究与发展的年平均增长要强于其他任何部门的研究与发展。”[10]523学术机构进行了43%的基础研究,是全美最大的基础研究者。“基于这些数据,很难认为美国较为狭窄的实验使用例外阻碍了美国的大学进行研究。”[10]524
就专利数相关的数据而言,拥有较为宽松的实验使用例外的日本却在专利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日本制药业的R&D 落后于欧洲与美国。“1995年与1998年间,日本的新进入市场的药品数量是下降的,新批准的药品数量降至十年最低。在1996年,日本市场批准销售的新药品中超过一半有外国专利权人,这段时间新授予的药品专利也在下降。”[11]44“自1997年开始,日本每单位产业投资的R&D费用的产出开始显著上升,而美国和德国都出现了下降。英国从1997年至1999年保持稳定,之后也有下降。”[6]812000年的总体专利数据中,“美国居民在美、日、欧三个专利局中拥有略少于35%的专利,之后是日本略多于25%,德国为13%,英国为4%。”[6]80在PCT申请数量上,“美国居民占38%,日本占13%,德国占13%,英国占5%。”[6]81“四国在产业提供的R&D 费用方面的排序也是同样的。”[6]24这说明在四国中,“日本相比其他国家每单位的R&D 投入能得到更多的创新产出”[6]81。日本也有希望“在每百万居民的创新数上击败美国”[10]531-532。日本较为宽松的实验使用例外制度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在R&D 投资方面,印度则吸引了大量投资。印度在2007年有超过150家外国科研机构在印度进行R&D。“在1998年到2003年间,这些公司在印度的R&D投资超过11亿,包括微软、英特尔、思科、IBM、阿尔卡特、爱立信、EMC、伟创力、诺基亚、三星、西门子、通用、特斯拉等等。”[12]这些R&D一般以三种形式进行:内部R&D、与其他公司合作、与私有实体、公共部门的实验室、大学的合同研究。外包工作的范围包括软件研发、计算机芯片设计、临床测试、药物研发等等。“在2008年至少有737项临床试验在印度进行。”①参见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Pharma Outsourcing in Asia: Are You Readjusting Your Sights?,上传日期2008年8月10日,访问日期2018年5月10日,网址:https://www.pwc.com/.印度专利法有着较为宽泛的实验使用例外,而印度相对而言又不是研发出的产品的主要销售地。因此,将研发外包到印度很明显可以节约研发费用,且研发中更少遇到专利侵权问题。研发出的成果可以在知识产权保护更加严格的发达国家寻求专利保护,而这些国家往往才是产品的主要销售地,也是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此外,印度较为严格的商业秘密保护也可能是配合其实验使用例外、促成研发外包的因素之一。在一个研究机构进行研究的工作人员跳槽到另一个研究机构,可能将其在之前研究机构学到的信息带给下一个研究机构,给予后者更多的优势。因为印度以普通法形式保护商业秘密,禁止任何商业秘密的泄露,所以这些研发机构能够得到更多的保护。②参考Reddy S, Sandhu G S:Report on Steps to be taken by Government of India in the Context of Data Protection Provisions of Article 39.3 of TRIPS Agreement,上传日期2007年5月,访问日期2018年5月10日,网址:http://chemicals.nic.in/.
总而言之,由于美国本身就是发达国家、技术上的净出口国,它与中国在鼓励创新方面遇到的不是同样的问题。中国面对的问题更多是如何从整体上提升本国的创新能力,而不是讨论创新、研发工作是由大学等科研机构进行还是由私人企业等进行。而相比之下,日本与印度的例子可能对中国更有可参考性。无论是从专利相关数据还是从吸引发达国家的研发外包上看,更加宽松的实验使用例外都是更好的政策选择。
三、实验使用例外与TRIPS协定义务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是一个强调保护的知识产权国际协定,在序言部分就将知识产权定义为一种私权利。为限制知识产权留下空间的代表性的条款是TRIPS 协定的第30 条和第31条;前者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般例外,而后者是不经专利权人同意而采取强制许可的一些情形。因此,与实验使用例外相关的条款就是TRIPS 第30条。鉴于中国是WTO 成员、TRIPS 协定的缔约方,无论是收缩还是扩张专利法中的实验使用例外,讨论和分析TRIPS 协定给成员方在实验使用例外立法方面留下的弹性空间都是很有必要的。
TRIPS 协定第30 条“授予权利的例外”规定:“成员方可以对专利所授予的排他权利提供有限的例外,只要此类例外在考虑到第三方的合法利益时,没有与专利的正常利用不合理的冲突,没有不合理地损害专利所有人的合法利益。”将该条与实验使用例外联系起来的是“加拿大:药品专利保护”案。该案中欧盟起诉加拿大专利法的第55.2节违反了加拿大在TRIPS协定下保护专利人权利的义务。被诉的加拿大专利法条文其实都与审批例外有关,该方面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豁免第三方为与任何产品的行政审批有关的对专利发明的使用,又称为准备工作例外;第二部分豁免为了在专利到期后及时上市而提前生产储存专利产品的行为,又称为储存例外①参考1985年加拿大专利法第55.2节。。欧盟认为该条所豁免的范围太大,不属于TRIPS 协定第30 条所要求的“专利权授予的排他权的有限的例外”。最终专家组在专家组报告中认为加拿大专利法Section 55.2 的前一部分,即准备工作例外是符合TRIPS 协定第30 条所允许的例外的,没有违反加拿大的TRIPS协定项下义务。针对准备工作例外,专家组认为这一例外是“有限的”,而且该例外也没有损害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因为“由于新产品上市所需要的冗长的行政审批程序所带来的专利期间在事实上的延长本来就不是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此外,这项例外还能“加速新药上市、降低成本,对改善公共健康问题有着很大的好处”。但是,对于后一部分,即储存例外,专家组却做出了不利于加拿大的认定,认为“该例外不属于TRIPS协定第30 条所允许的例外,因而违反了加拿大在TRIPS 下保护专利的义务”。专家组的理由是“在专利到期前生产并储存某专利产品是一种竞争性的商业行为,即使商业获利被延迟也不能改变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从生产到销售有一段时间差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专利期间不能生产专利产品的限制给专利权人带来短期的专利期间的续展是无法避免的事,也应属于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加拿大专利法Section 55.2 的第一部分,即准备工作例外,其实就相当于是经过Hatch-Waxman 法案②《Hatch—Waxman法案》又叫作《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补偿法》(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Restoration Act),由美国的众议员Hatch和参议员Waxman于1984年联合提出,因此常常以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法案。该法案被誉为当今美国仿制药、即非专利药工业的催化剂,对美国乃至世界制药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修正的美国专利法中的Bolar例外③Bolar例外(Bolar Exception)又称为Bolar豁免(Bolar Exemption),是指在专利法中对药品专利到期前他人未经专利权人的同意而进口、制造、使用专利药品进行试验,以获取药品管理部门所要求的数据等信息的行为视为不侵犯专利权的例外规定。参见35 U.S.C.§271(e)(1)(2000)。,区别是美国的Bolar例外仅限于药品,而加拿大的准备工作例外可以适用于任何需要行政审批才能上市的产品,比美国的Bolar例外豁免的范围更宽。
本案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本案专家组深入分析了TRIPS 协定第30 条的适用条件,为更加广泛的实验使用例外是否违反TRIPS协定义务提供了判断标准。专家组认为TRIPS协定第30条包含三个条件:“(1)有限的例外;(2)不得不合理地与专利的正常利用相冲突;(3)不得不合理地损害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三个条件之间应该是相互独立、逐渐递进的关系,即“满足前一个条件仍然有可能违反后一个”。
关于什么是“有限的例外”,专家组首先认为“‘有限’应当采用一种更狭窄的解释,因为‘例外’一词的含义本身就代表某种有限的缩减,而‘有限的例外’显然要求限制更多。”衡量有限的方式是“评估专利权所有人排他权被限制的程度”,而不是“简单地计算被限制的权利的数量”,也不是“只要不影响销售给最终消费者就是有限的例外”。“为行政审批进行的专利实施在数量和范围上都是有限的,因此准备工作例外符合‘有限’的标准”,而在专利到期前进行的储存性生产没有受到限制,完全剥夺了专利权人在专利期内限制他人未经许可生产专利产品的权利,“因此违反了‘有限例外’的要求。”④以上援引的专家组报告内容请参见:世界贸易组织:Canada-Patent Protection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s-Complaint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ir Member States-Report of the Panel,上传日期2000年3月17日,访问日期2018年5月10日,网址:https://docs.wto.org/.从中可以看出,行政审批例外(即加拿大的准备工作例外、美国的Bolar例外)符合TRIPS协定第30条中“有限例外”条件的原因是它所豁免的实施行为因其本身的特点是有限的,与是否是药品没有关系。该案中专家组明确了这种更加宽泛的、全行业的行政审批例外是符合TRIPS协定第30条而不违反TRIPS义务的。
根据专家组在“加拿大:药品专利保护”案中对TRIPS 协定第30 条义务的分析,仅仅为了满足好奇、求知性地或者为了验证专利实用性而实施专利显然在数量和范围上都是有限的,也不侵害专利权人的“正常利用”和“合法利益”。根据同样的标准,为了改进或者继续发明而对某专利进行的实验也应该是符合TRIPS 协定第30 条例外的。因为发明或者改进都非易事,显然在范围和数量上都是有限的,不会造成大规模地、不受限制地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被豁免。阻碍改进人改进某一专利技术很难说是专利权人的“正常利用”和“合法利益”。
TRIPS 协定第7 条中规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行应当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的转让与扩散。采用更加宽泛的实验使用例外可以间接地起到促进技术转让和扩散的作用,一方面更小的侵权诉讼风险会促进改进人对技术进行改进,自然带来了技术的扩散;另一方面,更宽泛的实验使用例外也会提高改进人在技术转让谈判中的地位。既然TRIPS没有可操作的条文义务去体现其第7条规定的目标,那么就更不应该剥夺宽泛的实验使用例外促进这一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四、主要国家实验使用例外制度及其比较
(一)主要国家的实验使用例外制度
1.美国
美国的实验使用例外有着非常长的发展历史。最早在1813年Joseph Story法官创造在Whittemore v.Cutter案中提出了实验使用例外,认为法律不应惩罚对专利物品进行“求知性的实验”的人①参见Whittemore v.Cutter,29 F.Cas.1120(C.C.D.MASS.1883).。Story法官在随后的Sawin v.Guild案中进一步明确专利权人没有受损时应允许侵权人援引实验使用例外,决定专利权人是否受损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侵权人是否从中获利。②参见Sawin v.Guild,21 F.Cas.554(C.C.D.Mass.1813).Patteson法官在Jones v.Pearce案中认为为消遣娱乐实施专利不构成侵权。③参见Jones v.Pearce,Webster's Patent Cass 122(K.B.1832).Ruth v.Stearns-Roger Manufacturing Co.案则表明教育研究可以被免除侵权责任,因为没有产生实际的好处和利益④参见13 F.Supp.697(D.Colo.1935).。Pitcairn v.U.S 案提出了正当事业(legitimate business)标准,即只要侵权人是在追求自己的正当事业的过程中侵犯了专利,就不得援引实验使用例”⑤参见547 F.2d 1106.。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庭(CAFC)对此例外采用了非常严格的态度。Embrex 案中,法院认为实验使用例外不能适用于有商业动机的实验中⑥参见216 F.3d 1349.。Madey 案中被告杜克大学抗辩自己作为学术机构,其研究是非商业性的,对专利的使用应该得到豁免。但是法院仍然认为,被告通过这一行为,可以提高自己的学术声誉,属于大学的正当事业,也不得援引实验使用例外。⑦参见307 F.3d 1362.除了判例法中的实验使用例外的抗辩之外,美国Hatch-Waxman Act给“为行政审批提供实验数据的药品专利实施”提供了条文法的例外⑧参见35 U.S.C.§271(e)(1)(2000).。这一例外一般与仿制药行业关系密切,仿制药制造商为了尽早完成冗长的药物上市行政审批手续,通常会在原药专利到期前就开始实验,“这明显是有商业目的的,但是仍然可以援引实验使用例外,这一例外包括所有FDA 管理的产品”⑨参见496 U.S.665.。在Integra Lifesciences I,Ltd.v.Merck KGaA一案中,法官讨论了这一条文,并同样收窄了该抗辩的适用范围,认为该抗辩只可适用于“已经上市的药物的临床试验”⑩参见Integra Lifesciences 1, ltd.V.Merck Kgaa, 331 F.3d 860, 866-68 (Fed.Cir.2003), vacated, Merck Kgaa v.Integra Lifesciences I,LTD.,545 U.S.193,545 U.S.193(2005).。总之,从一系列案件来看,实验使用例外在美国可以适用在专利权人无经济损失、侵权人无经济收益、小范围非商业性实验造成的侵权中。
2.日本
日本专利法将实验使用例外规定在其专利法第69条第1款:“专利权的效力不应延伸至出于供试验或研究之目的而使用专利权的场合。”①参见日本2015年《专利法》。该条规定的理由是促进科技进步。在早期,“商业目的行为、为行政审批进行的实验都不包含在此例外中”[11]25-26。1996年的五个判决都认为:“在原药专利有效期间内为仿制药上市的行政审批进行的实验不属于实验使用例外的情形。”[11]26-27在此之后东京地方法院判决的两个案件翻转了这一解释②参见Wellcome Foundation Ltd v.Sawai Pharmaceutica案与Daiichi Pharmaceutical Co.,Ltd v.Shiono Chemical KK案.。这两个案件中的被告都是“为仿制药行政审批进行的专利实施,而且都没有获得利润,也不与原专利相竞争”[11]17。法院认为“如果要求仿制药制造商等到原药专利过期后再进行实验、申请行政审批,实际上是不当地续展了原药的专利期”[11]16,这是“违背专利法目的的”[11]31,因此认为此行为属于实验使用例外。与之略有不同的是名古屋地方法院在Ono Pharmaceutical v.Malco Pharmaceutical KK 案中虽然认为:“为行政审批而进行的实验也是侵权行为,但是拒绝适用禁令,而是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1]20-21东京地方法院在Wellcome案与Daiichi案中的做法得到了日本最高法院的支持③参见Derzko,Natalie M."A Lo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Use Exception-Is Harmonization Appropriate."IDEA 44(2003):63.。
3.英国
英国将实验使用例外规定在其专利法案的第60.5 节:“某构成侵犯发明专利之行为,除本分章节规定之外,若符合以下条件则不构成侵权:(a)此行为是私下进行,且只为非商业之目的;(b)此行为是为与发明标的有关的实验目的。”在Monsanto Co.v Stauffer Chemical Co.的上诉案中,法院认为:“公司的所有活动都有商业目的,这本身不会使实验使用例外无效。”例如,“一个限于为了确定制造某产品的能力而根据其权利要求说明书进行的实验是属于实验使用例外之中的”。该法院将“实验”定义为“为发现未知事物或测试某一假说而进行的尝试”,这种实验包括测试在某一条件下可行的事物能否在另一条件下可行。而为了收集信息或者展示某一产品或过程如其所述的可行不属于这种“实验”④参见Monsanto Co.v.Stauffer Chemical Co.&Another.[1985]R.P.C.。法院也认识到某一测试的目的可能很难确定或者有着混合的目的,并认为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确定行为的目的是法院的责任。一般而言,“如果测试的目的是混合的(半研究半商业),英国法更倾向于将其认定为侵权”⑤参见SK&F v.Evans[1989]F.S.R.513,and McDonald v.Graham[1994]R.P.C.515.。
4.德国
德国将实验使用例外规定在其专利法中作出如下规定:“专利的效力不应延及为实验目的而实施专利发明内容的行为。”⑥参见2016年德国《专利法》。条文未经解释不得使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Klinische Versuche I案中认为:“实验使用例外的范围和含义应当依据欧共体专利公约解释。”在欧共体专利公约的语境下,该条款所讨论的是行为的目的而非行为的种类。德国最高院认为任何获得信息的行为,无论其使用该信息的目的是什么,只要实验与发明的标的有关,就可以适用实验使用例外。这是一种非常宽泛的解释。根据这一解释,“任何为了对发明标的进行科学研究而获取信息的实验都可以作为实验使用被豁免”⑦参见Klinische Versuche.[1997]R.P.C.。进一步说,因为德国专利法中的实验使用例外条款对实验既没有数量限制、也没有质量限制,法院还认为实验是仅仅为了证实专利声明中的陈述还是为了获取进一步的未知信息并不重要,实验是否包含商业目的也不重要。一旦满足实验目的这一初始要求,无论如何使用实验结果,都可以使用实验使用豁免。在Klinische Versuche II案中,因为欧洲共同市场专利公约中并不限制有商业目的的实验,法院认为商业目的并不从一开始就使得商业活动成为不被允许的专利侵权。而且法院还承认,因为极高的R&D费用,制药业的临床研究不可能没有商业目的。允许商业目的存在的同时,该案中法院还进一步明确了“实验”的含义:实验必须与技术理论相关;不应不成比例以至于失去了研究提供的正当性;以永久性地扰乱或阻碍发明人对其产品的分销为目的的实验是不允许的。总而言之,德国专利法是从促进技术进步的角度理解实验使用例外,因此“实验的目的必须是技术改进而非进行竞争”①参见Klinische Versuche(Clinical Trials)Ii.[1998]R.P.C.。
5.印度
印度的实验使用例外规定在其1970年专利法案中作出如下规定:
“依据本法授予专利需满足以下条件:
……
(3)仅为实验或研究之目的,包括向学生传授,任何既授专利或以既授专利的过程制造的机械、部件或其他物品可被任何人制造或使用,任何既授专利的过程可被任何人使用。”②参见印度1970年《专利法》(2005年修订)。
这是当时全世界范围内最早以条文形式规定实验使用例外的国家。印度1970年专利法案取代了其1911年专利与设计法案,“其主要内容是基于N.Rajagopala Ayyangar法官的研究。”[13]他认为“印度1911年专利法案过于偏袒外国专利权人,他们只是在印度拿到专利去确保垄断以及向印度进口他们的专利物品”[14]478。大多数专利权人并不在印度使用专利,而进口货物的价格,特别是药品往往让印度消费者无法承担。Ayyangar法官改革印度1911年专利法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扭转这一趋势,其措施之一就是“在印度1970年专利法案中加入了实验使用例外条款”[14]488。根据其报告,加入该条款的原意是“要区分商业目的的实验和非商业目的的实验”[14]492。但是印度立法机构在将其写入印度专利法时忽视了该例外对商业目的实验的适用限制,从而使得该条款的适用范围比Ayyangar 法官建议的更加广泛。印度法院适用实验使用例外时,是否有商业目的并不是考虑的重点,关键的限制在于“某一使用必须是实验,而不是一种专利产品仅仅就其功能被使用、没有任何对其背后技术的研究的纯消费型的使用”[5]852。此外,与英国法不同的是,“印度还允许实验使用例外包括为教育目的的使用”[5]855。
(二)各国主要规定的比较
通过对各个国家实验使用例外大致的分析,可以看出:从宽严上看,美国的实验使用例外最为狭窄,适用最严格;英国、日本略宽于美国,其次是德国,最宽松的是印度。导致美国严格限制实验使用例外的原因是美国在此问题上坚持商业性/非商业性二分法。美国是唯一一个将商业性与非商业之分作为可否适用实验使用例外标准的国家。这被很多学者批评为完全不切实际,因为“现在的现实是纯粹研究和实用研究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③参见Integra Lifesciences I,Ltd.v.Merck KGaA.,331 F.3d 860,872-78.。例如,在英国法院就承认商业性并不会当然使实验使用例外无效。而德国的做法则是首先对“实验使用”做出宽泛的界定,而不论其是否有商业性,然后再否定性地列举几种不能援用实验使用例外的情形(数量上不能不成比例、不能有与原专利人竞争的目的等)。德国实际上是采用了“负面清单”的方式来规范实验使用例外的适用,给这一例外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印度的实验使用例外则是最为宽泛的,因为印度对实验使用例外的适用逻辑正好与美国相反。美国是考察某一被诉侵权行为是否含有商业性,只要有一点商业性,即使是Madey 案中那样遥远间接的商业性也不得援用实验使用例外(除了行政审批例外之外)。而印度则是考察某一被诉侵权行为是否属于实验,只要属于实验而非专利实施行为就可以援用实验使用例外。这使得印度成为对专利的实验使用最为宽容的国家。
此外,英国和德国的实验使用例外有一个别国没有的特点:都要求实验与发明的标的有关,有关的属于“对专利实验”(Experiment on),可以豁免;无关的属于“用专利实验”(Experiment with),不可豁免。后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被专利保护的研究工具”[15]。美国没有这一区分,因为如上文所述,美国对实验使用例外采用非常严格的解释方式,很多“对专利实验”因含有商业性都无法援用实验使用例外,更不用说“用专利实验”的情形。印度的实验使用例外排除了“专利仅就其功能被使用”的情形,可以认为包含了排除“用专利实验”的含义,但是没有直接的规定。
五、对我国实验使用例外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中国《专利法》的规定及其实施
1.中国的立法内容
中国现行专利法对实验例外也进行了规定。相关规定如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四)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五)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制造、使用、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以及专门为其制造、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①参见2018年《专利法》第69条。也就是说,在中国因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相关专利的,不视为侵权。
值得交代的是:以上(四)、(五)两项被合称为实验使用例外。在前引的各国文献中,一般都将二者合在一起讨论。第(五)项所称的“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实际上指的是“相关药品的实验数据”。因为“法律对仿制药和医疗器械的上市有严格限制,须经一系列的实验,并向主管部门提供实验数据,待主管部门批准才可上市”[16]。因此,该项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实验使用。
此外,有学者认为这里的“‘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情形主要指‘与该专利本身’相关的技术改进,而不是指用该专利技术作为手段进行与其无关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如果是这种情况也难逃侵权的嫌疑”[17]。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显然这一项规定主要意在促进技术改进式的创新,即基于已有专利技术基础上的改进是允许的,否则人类的技术进步将会非常缓慢(只有到进入公有领域后他人才可以模仿创新是不理性的)。但是,它并不以此为唯一目的;如果他人以专利技术作为手段进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研究和实验,也应该是允许的;否则,在2008年专利法修改时,立法方面应该进行相应的完善,而事实上,修改后的专利法只是在第69 条(2001年专利法第63条)中增加了第五项,将原来的第二款变为单独的一条,而对其他方面的内容未作实质性修改。
2.司法实践
中国的实验使用例外的司法实践非常简单。检索北大法宝,无论是修订前还是修订后的《专利法》,涉及实验使用例外的案例都非常少,仅有两个:一是2006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三共株式会社等诉北京万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专利侵权案;第二是陆正明诉上海工程成套总公司、无锡市环境卫生工程实验厂专利侵权案。
前一案件涉及到为获得行政审批数据的药品实验例外。该案发生争议原因是2006年时的中国《专利法》尚无行政审批例外。该案中法官认定被告实施专利的行为不构成侵权,理由是为行政审批进行的实施行为不符合当时《专利法》(2000年)第十一条规定的“生产经营目的”②参见2018年《专利法》第70条。。实际上法官的这一理由明显受到了实验使用例外学说的影响,但是因为当时中国《专利法》中没有行政审批例外这一条,因此通过对第十一条的解释适用了该例外。2008年《专利法》修订之后就增加了行政审批例外条款,因此该案也没有继续讨论的意义了。
后一案件中的原告陆正明是上海市环卫废弃物处置管理处的一名工程师,他在工作过程中发明了“熟化垃圾组织筛碎机”并取得了实用新型专利权。在无锡市环境卫生工程实验厂委托之下,上海工程成套总公司对该专利进行了研究和改进,并将成果交付前者使用。一审法院认定,虽然本案标的确实与原告的专利构成等同,但是其中包含研究和改进,这属于实验使用例外的情形,因而被该例外所豁免。二审上海高院则推翻了一审法院的判决,认为:“(被告行为)属于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使用行为,亦不符合‘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使用有关专利’的条件。”③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陆正明诉上海工程成套总公司、无锡市环境卫生工程实验厂专利侵权上诉案,上传日期1993年4月,访问日期2018年5月10日,网址:http://www.pkulaw.com/.这里二审法院的做法是正确的,这种明显妨害专利人的合理使用、损害其合法利益的行为应该受到限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实验使用例外的范围作了界定,将其限定为“演示性的利用、或考察经济技术效果”,这样限制又显得过于狭窄。对于合理的界定,下文会有详述。
(二)中国实验使用例外制度的完善
1.司法方面的完善
中国《专利法》第69条中第4项仅对实验使用例外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第5项将行政审批例外的范围限于药品和医疗器械。如上文所述,扩大实验使用例外,扩张公共领域的范围,对促进中国的创新与发展是有帮助的。由于《专利法》第69条第4项仅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对该条款的正确解释就非常重要。该条款中的“专为”二字,很容易让法官在适用该条时联想到美国的商业性与非商业性之分,将“专为”理解为没有商业目的的纯研究性实验,从而像美国那样极为狭窄的理解实验使用例外。也有学者“从商业性与非商业性之分的角度提出对该条的解释建议”[18]。实际上,美国这种商业与非商业性之分由于无视现在实用研究与学术研究之间界限日渐模糊的现实而招致了很多批评。在加拿大,药品专利保护案中的专家组在对TRIPS 协定第30 条的分析提出的有限性、不妨碍正常利用、不损害合法利益三个累积性的标准在判断是否适用实验使用例外时其实是一个非常完善、值得参考的标准。与之相比,美国的商业性与非商业性之分显得颇为原始,不够深刻。第三方商业性的利用专利往往数量十分巨大、会妨碍到专利权人的正常利用和合法利益(往往就是商业利用和商业利益),当然不能落入实验使用例外豁免的范围。但是,例如行政审批例外,虽然明显是商业性的行为,但是数量和范围因其本身的性质也是有限的,符合TRIPS协定第30条的规定,而美国的商业性与非商业性理论就无法解释这一点,必须通过单独立法来解决,在逻辑上显得不够统一。运用有限性、不妨碍正常利用、不损害合法利益三个标准来解释《专利法》第69条第4项也是可行的,因为“专为”二字所针对的未必就是商业性与非商业性之分,还可能是有限制的例外与无限制的例外之分、妨碍专利权人正常利用与不妨碍正常利用之分、损害专利权人合法利益与不损害合法利益之分等。总之,“专为”只是一种对例外范围的限制,而限制的标准可以是多样的,在司法中应该用比较完善的标准来代替更原始的标准。
具体而言,结合上文的分析,符合有限性、不妨碍正常利用、不损害合法利益三个标准的实验使用例外至少包括:(1)为了满足好奇心、求知性的实施专利;(2)为了验证专利实用性而实施专利;(3)为行政审批需要的信息而实施的任何专利;(4)为非竞争性目的的改进而实施专利,可能包括“为发现制造或使用专利的新式方法和新的替代品或改进品”[19];(5)其它符合三个标准的实施行为。其中,(1)(2)(4)(5)能够通过对《专利法》第69 条第4 项“专为”一词在司法中的解释而得到适用。
2.立法方面的完善
前文提到的符合有限性、不妨碍正常利用、不损害合法利益三个标准的实验使用例外的五种情形中的第三种“为行政审批需要的信息而实施的任何专利”情形,难以在现行中国法律框架下通过解释被涵盖进实验使用例外的范围,因为《专利法》第69 条第5 项明文将其限制于药品与医疗器械当中。实际上,为行政审批而进行的实施行为应当都是符合有限性、不妨碍正常利用、不损害合法利益三个标准的,不因为是否是药品或医疗器械而不同。因此,在修改《专利法》时应当明确放松这一限制。《专利法》第69 条第5 项应当将药品和医疗器械改为专利产品,其条文应改为: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制造、使用、进口专利产品的,以及专门为其制造、进口专利产品的。
六、结 论
实验使用例外是实验引发侵权最直接的抗辩武器,因此与创新有着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该条款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也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实验使用例外的宽窄是否促进了本国的创新是一个比较模糊的问题,因为它们面对的是如何“更进一步”的问题。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曾经的技术落后国家而言,例如印度、过去的日本,采用更加宽泛的实验使用例外能够提升本国在创新上的竞争优势、减少现有权利的包袱(因为这些权利的所有者更多是外国人),促进这些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从理论上看,专利的社会契约性要求公众有权检查专利权人所披露的技术,豁免改进型的侵权也有利于提升一国的创新能力。从国际法的角度而言,因为TRIPS协定强调保护,所以其第30条给实验使用例外留下的空间一定要善加利用。TRIPS协定第30条的相关案例中专家组提出的有限性、不妨碍正常利用、不损害合法利益三个标准对于完善中国的实验使用例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实现路径是结合这三个标准来解释中国《专利法》第69条第4项,而行政审批例外只能通过修改法律来扩张其适用范围。本文分析从实证和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实验使用例外对一国创新能力的影响,讨论了TRIPS协定给该例外留下的空间,并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通过扩张公共领域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