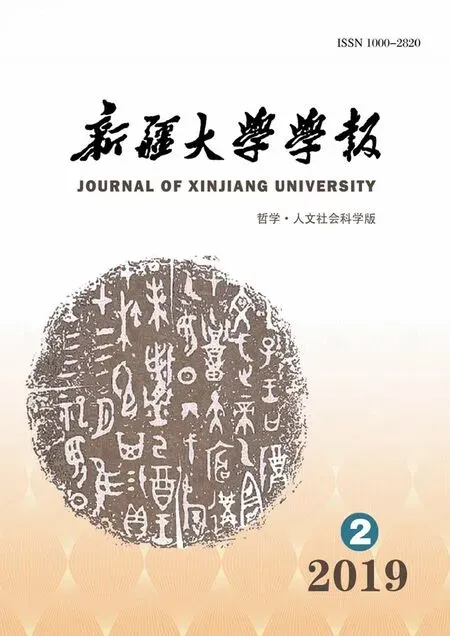义理不纯与文辞华妙
——论朱熹对苏轼著述的批判及其原因*
杨 曦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苏轼著述的批判始终是学者关注的焦点①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综合研究,如合山究《朱熹の蘇学批判——序説》(《中国文学论集》[3],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1972年,第25-36页)、涂美云《朱熹论三苏之学》(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后者最为全面,但深度略显不足。(2)从文道关系角度着眼者,如Peter K.Bol.“Chu Hsi’s Redefinition of Literati Learning”,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Years,ed.Wm.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Chaffee, 151-8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包弼德《朱熹对于士学的再界说》,《形成时期,新儒家教育》,狄百瑞、査菲主编,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谢桃坊《关于苏学之辩——回顾朱熹对苏轼的批评》(《孔孟月刊》第三十六卷第二期,收入氏著《国学论集》,第232-246页)、沈松勤《“新道统”理念下的偏见——朱熹讨伐“苏学”的文化诉求》(《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等。他们认为朱熹对苏轼的批评,反映出新儒家对古文家的批判,这一批判是为了重新建构符合他们需要的“道统”而服务的。(3)专论经解者,如林丽真《<东坡易传>之思想及朱熹之评议》(收入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主编《宋代文学与思想》,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第627-668页)、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100页)。(4)专论文章者,如吴长庚《朱熹文学思想论》第三章第三节《朱熹论苏轼》(黄山:黄山书社,1994年,第132-180页)、莫砺锋师《朱熹文学研究》第四章《朱熹的文学批评》(第134-208页)、张进《论朱熹对苏轼的批评与接受》(《唐都学刊》,2008年第2期)、韩立平《从心性论看朱熹文学思想——兼论朱熹对苏文的批评》(收入王水照、朱刚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3-305页)等。。但是回顾以往的研究,仍然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在材料使用上,学者多据《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等其他文献发掘不足。其次,即便利用文献较为充分,学者们也往往没有注意到朱熹的观点会因体裁、针对的对象以及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对记文、书信、题跋、语录等不同性质的材料必须有所区分,而不宜等同视之。黄震即将朱熹的言论分成三类。他说:“读先生之书者,其别有三:如《语类》,则门人之所记也;如书翰,则一时之所发也;如论著,则平生之所审定也。《语类》之所记,或遗其本旨,则有书翰之详说在;书翰之所说,或异于平日,则有著述之定说在。然议论固至著述而定。”换言之,论著、书信、语类的可信度依次递减,著述堪称定论,其次则为书信,再次则为语类。这一认识是否妥当,尚可斟酌,如钱穆即认为“读朱子书,据《文集》有时转不如据《语类》”,但在考察朱熹言论时确实有必要注意区分材料的性质。最后,朱熹自有一套评价人物的标准。他说:“品藻人物,须先看他大规模,然后看他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不好处多与少。又看某长某短,某有某无,所长所有底是紧要与不紧要,所短所无底是紧要不紧要。如此互将来品藻,方定得他分数优劣。”换言之,他在评价时,一般先观察其人总体的才具气概,再具体评判每一方面的得失优劣,最后再加以汇总。只有认清朱熹的评价是针对哪一方面而发,这一方面在其评价体系中权重如何,才能得出比较妥当的认识。但学者往往没有充分理解朱熹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与方法,最后,由于没有充分理解朱熹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与方法,学者一旦遇到前后矛盾的观点,经常各执一端,争论不已。因此,这一问题仍有重检的必要。本文拟以朱熹的学术思想为背景,从义理、文辞两个层面探讨朱熹对苏轼著述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批判的原因,以期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朱熹的观点及其意义。
一、义理不纯:合佛老、仪秦于一人
所谓“义理”,是指作者在经解、古文乃至诗词歌赋等著述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宋代以来,对于性命道德、仁义礼智等内容的阐发逐渐成为义理学说的核心,而这部分的内容主要都反映在经解之中。下面以苏轼的经解著作为中心,考察朱熹对其义理学说的看法。
(一)言性命流入佛老
在朱熹对苏轼思想的评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对苏轼人性论的批判。在性命道德之学方面,朱熹主要继承的是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他认为人性是宇宙中的天理落在人间的产物,由于天理至善,而人性是人所秉受的天理,因此人性也必然是至善的。此即所谓“天命之性”。因为性命道德之学在朱熹的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苏轼经解中有关性命道德的观点自然而然地成为朱熹重点关注的对象。
苏轼说:“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恶为哉!”[1]111换言之,他认为性本身并不具备善恶的属性,善恶是人本于性、以不同的方式驾驭七情而产生的结果。“苟性而有善恶也,则夫所谓情者,乃吾所谓性也。”性不过是一种可能性,性近于好恶这种情感本身,本身不具备好善而恶恶的规定性。它在不同境况之中,或显现为善,或显现为恶。如此一来,善恶只是性的显现,而非性的本体,善恶之分也就完全成为后天的、人为的。这一观点相当于告子“性无善无不善”说的翻版,自然与朱熹的性善论不能相容。
在《杂学辨》中,朱熹对苏轼在《东坡易传》中所阐述的人性论作了集中批判。下面选择其中最为关键的一节加以说明。苏轼说:
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逃焉,是则性之所在也……性之所在,庶几知之,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2]142
朱熹对其观点作了详尽的剖析,他说:
苏氏此言,最近于理。前章所谓性之所似,殆谓是邪?夫谓“不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则疑若谓夫本然之至善矣。谓“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则疑若谓夫良心之萌櫱矣。以是为性之所在,则似矣。而苏氏初不知性之所自来,善之所从立,则其意似不谓是也,特假于浮屠“非幻不灭,得无所还”者而为是说,以幸其万一之或中耳。是将不察乎继善成性之所由,梏亡反覆之所害,而谓人与犬羊之性无以异也,而可乎?夫其所以重叹性之不可言,盖未尝见所谓性者,是以不得而言之也。[3]3462-3463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对“不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的诠释。这句话一般会被理解为是在说“有不可消之恶”,但朱熹却说这似乎是在说“本然之至善”。朱熹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解读呢?细察文义可以发现,这句话语意的重点,可以不落在“有不可消之恶”上,而落在它的反面——“有不可增之善”上。君子日修其善,善与日俱增,最终达到了连圣人也无法再增加的程度,那么此时的善也就近于至善了。如此一来,苏轼的人性论的确与性善论相差无几。朱熹敏锐地捕捉到如此解释的可能,因此说它“最为近理”。
但实际上苏轼并没有对性的道德属性作出规定,他的表述也没有鲜明地呈现出性善论的色彩。参照苏轼的其他论述,这段话更近于性无善无恶论,当然,将之理解为性恶论或性有善有恶论,也都无不可。朱熹显然意识到性善论只是他一厢情愿的解读,并非苏轼的本意。只不过苏轼的观点并不清晰,包含了多种可能,朱熹难以直接驳斥,对此他大概颇有些恼火,因此才会说苏轼畏惧攻击、有意恍惚其词了。
那么,苏轼的人性论为什么会有如此似是而非的问题呢?朱熹认为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苏轼没有真正领会儒家学说的精义,“不知天命人心为义理本原之正”[3]3500,反而沉溺于佛老学说,“欲以虚无寂灭之学,揣摩言之”[3]3463。苏轼说:“古之君子,患性之难见也,故以可见者言性。以可见者言性,皆性之似也。”[2]142其意似指可见的善恶都是性的表现,而非性的本体,在可见的善恶之外,还另有一种超越善恶的本然之性,这种本然之性难以窥见、也难以言说。朱熹认为此处“性别有一物”的观念,与佛教“未有天地,已有此性”的认识无别。由于这种本然之性不具备善、恶的属性,因此本质上也就是所谓知觉运动。而佛教中也有“作用是性”之说,同样是将知觉运动作为“性”的本质。苏轼还认为如果能够把握住这一本性,便足以“原始反终”,对生死“了然而不骇”[2]349。朱熹认为,这也“溺于坐亡立化、去来自在之说”,与佛教中性死而不亡的观念一脉相承。要言之,在佛教的观念中,性别有一物,而且无去无来、不生不灭,其本质是知觉运动。由于知觉运动“既不辨善恶,亦不论趋向”[5]27,只是虚空,因此这一观念也被称为“空性观”。在朱熹看来,苏轼的人性论在性是否别有一物、性的本质如何、性是否有生灭等问题上的认识,都与佛教的空性观毫无二致,所谓“特假于浮屠‘非幻不灭,得无所还’者而为是说”。苏轼虽然没有直接引用佛教的术语,但其思考人性问题的方式及其得出的观点都与佛教无异,从根本上说背离了儒家之学。
如果我们针对苏轼的观点发问的话,既然善、恶之分是后天的、人为的,那么善从何而来呢?人又为什么一定要向善而不趋恶呢?对于这些问题,苏轼并没有能够给出一个圆满的答复。这些理论上的漏洞的确可能使善的成立失去根据。朱熹也正抓住了要害之处展开批判,自有合理成分。不过对于朱熹批评苏轼人性论流入佛老这一问题,还需辩证看待。陈植锷指出,宋学中关于性命道德的内容,本身就是在佛老之学的刺激下才产生的。二程以及朱熹本人之说也同样深受佛老影响,不仅苏轼一家之说如此。只不过与苏轼袭用佛老观点的形式不同,程、朱一系的道学家更多的是借鉴佛老性命学说的思维方式,建构出一套形式出于佛老但内容又属于儒家的性命道德理论。这套理论既汲取了佛老之说的精华,又能够不失儒家的立场,譬如蠹生于木,还食其木,因此最终在宋学性命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相对而言,苏轼人性论的核心内容既与佛教的空性观相混,理论体系也不够圆融精密,的确略逊一筹。当然,朱熹的批判也有可以商榷之处。因为如果将这一问题放在历史的脉络中来看,其实苏轼的人性论可以视为北宋中期以来性命之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在宋人建构性命道德理论的过程中,任何一种阐释的方向都可能产生,也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朱熹批判苏轼有意恍惚其词、眩惑他人,是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自然现象,因此并不妥当。朱熹之所以有此一偏之论,是因为他始终坚持性善论的立场,而完全否定其他任何有关人性的解释。但是,人性本无一定之论,不同的观点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只有在实际的历史环境中,其观点的价值与意义才能够具体展现出来。如果不顾时空变化,不论偏执于哪一种观点,都可能带来无穷的祸患。这是我们今天在探讨人性问题时所必须警惕的一点。
(二)论义利沦为纵横
朱熹除了认为苏轼言性命流入佛老外,还指责其思想中杂有纵横之学的成分。所谓纵横家,大都兼擅权术与词命,既通晓机变、长于权谋策略,又辩辞利口、擅长陈说利害。纵横家与儒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讲求权谋、强调实用,可谓以利为心,而后者则恰恰相反,行事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可谓以义为心。这就牵涉到中国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辨”这样一个重要命题。朱熹批评苏轼的思想杂有纵横之说,正可以从这一角度来认识。
《周易·乾卦·文言传》云:“利者,义之和也。”苏轼在《东坡易传》中解释说:“义非利,则惨冽而不和。”此意本于其父苏洵之《利者义之和论》,其文云:“义无利则不和,故必以利济义,然后合于人情。”[6]277换言之,在苏氏父子看来,义、利两者交相为用,唯有以利济义、调和义利,才能够达到义之和的境界。朱熹完全无法认同这一解读。他说:“苏氏说‘利者义之和’,却说义惨杀而不和,不可徒义,须着些利则和。如此,则义是一物,利又是一物;义是苦物,恐人嫌,须着些利令甜,此不知义之言也。义中自有利,使人而皆义,则不遗其亲,不后其君,自无不利,非和而何?”[4]1709他认为“义”偏于割制裁断,疑若不和,但实际上只有“义”才能辨明是非,使事物各正其分、各得其理,最终无往不“利”。“利者义之和”这句话的关键在于,利不是刻意追求所得,而是处置得宜后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利”“义”并不是两个截然分开的概念,“利”生于“义”而不外于“义”。但苏氏父子显然将“义”“利”一分为二了,而且在他们看来,义是惨杀之物,利是甘甜之物。他们强调以利济义才能达到和谐,其实也就是认为行义需要有利的诱导。而在朱熹看来,即便行义之前对利益心存期待都已经违背了道学的准则,更不必说是因为有利可图才去行义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了。如果遵从苏氏父子的观点,以利为言,也许一开始人们还会兼顾义、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会越来越重视利,而将义抛在脑后。如果把这一趋势推到极端,最终大概会形成一个只知利而不知义的世界。而这种世界,正是纵横家追求利益最大化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当然,苏轼的思想并没有纵横家如此极端,但是推到极致也没有区别,这也可以就是朱熹批评苏氏之学“为术要未忘功利而诡秘过之”[3]1301的原因所在。
在今天看来,这些苛酷的批评是朱熹站在严别义利的立场上作出的判断,虽然逻辑自洽,但是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人心是否能够达到朱熹所说的不存私意、尽忘功利的境界,还存在疑问。即便这一境界可以达到,那么是否可以用它作为标准要求所有人,也不宜妄断。在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朱熹就以这一不近人情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并不妥当。更重要的是,义利问题终究不是一个理解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实践中无法回避利害问题,趋利避害也是人之常情。朱熹强调不能以利为言、只能以义为言,可是他没有意识到以义为言也同样可能产生流弊。因为假使完全撇开行动、一味作诛心之论的话,那么,以义为言最终也只不过是说空话、唱高调而已,不仅于事无补,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判断其人究竟是喻于义还是喻于利,不能只论动机、不管行为,而必须综观心、迹,始能得之。结合苏轼的行为看,他绝不是一味追求利益的纵横家之流。王水照、朱刚便反驳说:“凡‘投机’,总是向矛盾的偏于能获利的一方‘投’去,而苏轼却每一次都‘投’到了相反的方向。”[7]336因此,朱熹给苏轼冠上诡谲欺诈的恶名,并不公允。
二、文辞华妙:浮靡新巧与伟丽雄健
当然,朱熹不是一位只知居敬穷理的道学家,他还具备很高的文学修养。他除了留意苏轼的义理学说之外,对其文辞写作也颇为关注,时有评说。下面即以朱熹对苏轼古文的评价为中心探讨这一问题。
初看朱熹对苏轼文辞的评论,似乎以贬抑为多。这与他个人的审美倾向有关。朱熹认为文章应当宁实勿华,他说:“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4]3320这一审美倾向在他比较曾、苏两家之文时表现得最为突出。朱熹偏好曾巩“词严而理正”[3]3918的文字,而对于“华艳”[4]3314的苏文时有指摘。他曾将曾、苏二人所作的同题材之文放在一起比较,他说:“南丰《范贯之奏议序》,气脉浑厚,说得仁宗好。东坡《赵清献神道碑》说仁宗处,其文气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丰不说。”[4]3314这两篇文字都涉及到仁宗朝的政治状况与当时言官的任职情形,而风格迥异。单看苏文,的确写得纵横驰骋、慷慨激昂,色彩鲜明。不过如果将它和曾文比较的话,那么不得不说,还是曾文更胜一筹。首先,曾文既称赞言官又不忘仁宗,能够两者兼顾,而苏文则只论言官、忽略仁宗,似乎不甚得体。其次,曾文颂美又不致于溢美,光华内敛,气象雍容,行文又曲折纡徐、不急不迫,苏文则锋芒外露、浮夸张扬,行文又劲疾飞动,未免有失浑厚。在具体的表述上,苏轼文中的“必取天下第一流”,也有意耸人耳目,不如曾巩的“如公皆一时之选”虽属平平道来,但却含蓄而又明白。总之,曾文几乎没有可被指摘的地方,而苏文则难免有可议之处。朱熹说苏文“气象不好”,虽然略嫌过度,但的确把握住了苏文浮夸张扬的弊病。此其一。不仅如此,朱熹认为将苏文放在历史脉络中观察,也可以看到其浮艳靡丽、刻意新巧所导致的流弊。他说:
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尝观嘉祐以前诰词等,言语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世有名之士。盖其文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浑厚。至欧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犹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气。到东坡文字便已驰骋,忒巧了。及宣、政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所以圣人取“先进于礼乐”,意思自是如此。[4]3307
在这段话中,朱熹借助历史叙述表达了自己的审美理想与社会理想。他认为北宋前期的制诰之文虽然质拙,但是遣词稳重谨慎,无意求工,自有浑成气象,这也是当时风俗浑厚的表现。但在欧、苏特别是苏文出现之后,文章便日趋驰骋工巧。至徽宗年间,更堕落为华丽浮靡,这意味着原有的和合之气已经消散殆尽,北宋的亡国之征已现。由此可见,朱熹将苏文视为文章败坏的一大枢纽,正是由于苏文过分求新出奇,才导致此后的文章日趋卑弱纤丽,不复有质实厚重之气。孔子在“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与“后进于礼乐”的君子之间,选择前者而非后者。朱熹也完全认同这一观点。因为华丽可能一变而为浮艳侈靡,新巧也可能一变而为驰骋好异,如此反而不如简朴质拙自有浑厚气象。朱熹的再传弟子李涂在《文章精义》中说:“文章不难于巧而难于拙,不难于曲而难于直,不难于细而难于粗,不难于华而难于实。”[8]63这段话可以移来作为朱熹观点的注脚。一言以蔽之,由于朱熹的审美观念是宁质勿文,而苏文恰好偏重文华、质实不足,而且可能带来浮靡新巧的流弊,因此他在将苏文与曾文以及北宋前期之文比较时,经常对苏文提出批评。
不过,严格说来,这两方面的贬抑并不属于同一层面。前者是由于朱熹坚持宁质勿文、宁实勿华的审美观念带来的,尚有一定合理性。而后者从根本上说是后学流弊,朱熹怪罪到苏轼头上,并不合适,一如莫砺锋师所说:“如果我们把衡文之言都从为后学指点学文之津梁这个角度来加以考察,也许可以对其散文批评增进理解。”[9]151
朱熹虽然不喜苏文,但他也并非完全只是从自己的审美倾向出发,而是力求客观公允,因此在他对苏文的评论也有不少称扬之语。如说苏轼早年所作的贤良进卷“壮伟发越”,《六一先生文集叙》“文章尽好”,《潮州韩文公庙碑》“初看甚好读”,《伏波庙碑》《峻灵王庙碑》两文“笔健”,闲戏文字如《潜真阁铭》之类“也好”[4]3311-3319等。对于苏文整体,他也曾给予“文字华妙”[4]3319的评价。甚至在比较曾、苏两家古文时,他也没有偏袒曾巩。尤为有趣的是一则假设曾、苏二人相见互评文章的语录,“或言:‘陈蕃叟武不喜坡文,戴肖望溪不喜南丰文。’先生曰:‘二家之文虽不同,使二公相见,曾公须道坡公底好,坡公须道曾公底是。’”[4]3316“好”与“是”分别代表了朱熹对两家文章的理解,这两个字也恰好对应着“辞”与“理”两个层面。换言之,就义理而言,朱熹认为苏文不及曾文,但是如果仅就文辞而论,他也承认苏文胜于曾文。可以说,朱熹高度肯定了苏文在文辞方面的成就。
那么,在朱熹看来,苏文的文辞华妙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综合《语类》各处的评价,大体有二。
其一是风格伟丽。朱熹说“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3]1864。“伟丽”可以视为他对苏文风格的总体把握。“伟”,即壮伟雄豪、波澜壮阔。苏文滔滔汩汩、随物赋形,行文跌宕起伏,富于气势。朱熹说苏轼“气豪善作文”[4]3320,说苏文“大势好”[4]3311,即着眼于此。“丽”则指华艳、美丽、富于文采。朱熹以“华艳”评价苏文,也是捕捉到了它绚丽多姿、神采飞扬的特点。
其二是笔力雄健。朱熹认为笔力原于姿性,换言之,作者的写作能力是由个人的秉赋才质决定的。在他看来,苏轼笔力过人,能够将感知到的情事几近完美地表达出来,但又毫不费力,堪称得之于天。这种雄健的笔力使得苏文呈现出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例如苏轼在《司马温公神道碑》中,先叙述天下治平之象,再阐论温公德行之美,这几大段文字读来令人兴起感动,志意发越,可谓笔力饱满,气势雄浑。朱熹赞叹道“说得来恰似山摧石裂”[4]3312,即着眼于此。另一方面,这种雄健的笔力还体现在论说的透彻上。朱熹说“东坡文字明快”“东坡文说得透”“如人会相论底,一齐指摘说尽了”“说利害处,东坡文字较明白”[4]3306-3312,也都是认为苏轼能够将事理阐发得清楚明白。
基于这一判断,朱熹对并不喜好的苏文也能给予比较恰当的历史定位。他说:“文章正统在唐及本朝各不过两三人,其余大率多不满人意,止可为知者道耳。”[3]3018钱穆以为“推朱子意,东坡文章,亦当在北宋两三人之列无疑”[5]186。其说甚是。朱熹在《楚辞后语》也曾提到:“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欧阳文忠公、南丰曾公巩与公(苏轼)三人,相继迭起,各以其文接名当世,然皆杰然自为一代之文。”[10]300类似的评价也见于《语类》之中:“文章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4]3309在朱熹的心目中,二程接续千载不传之学,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实为儒学史上一大转关所在,而将欧、曾、苏与二程相提并论,也足见三人在文章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朱熹说“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4]3316,而其正典地位又从根本上赋予了它作为范本的合法性。因此,朱熹认为“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3]1486。他在为指导士人学习写作开列的名单中,也一般会列上苏轼的名字。如说“韩、欧、曾、苏之文,滂沛明白者,拣数十篇,令写出,反复成诵,尤善”[3]1992,这是一种最常见的组合方式。又如说:“读得韩文热,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4]3309则去除了欧、曾,将韩、苏单独提出作为代表,此时苏文的典范意义就更为突出了。
朱熹赞誉苏文,除了苏文本身成就极高之外,也有着针砭时弊的考量。朱熹认为,时人作文完全沉溺在减字、换字等细枝末节的技巧当中,而舍弃了大道。相较而言,苏轼学有根基,其文章也平易明白、壮浪有气骨,“全不使一个难字,而文章如此好”[4]3322。因此,赞誉苏文也可以使后学知所趋向,而不致于误入歧途。朱熹对《战国策》系文章的评价也可以用来作为参照。他曾评价战国文字兼具豪杰、英伟之气,又说“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谊文亦然。老苏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4]3299。可见对这一系统的文辞都颇为欣赏。大概朱熹认为虽然战国文字立意不正,但是文辞超卓奇伟、恣肆辨丽,自有一股雄杰之气,其价值远在纤巧衰飒、萎靡不振的衰世文字之上。因此,在面对肤浅陈腐的时文时,对战国文字也不妨有所取材。苏文正与这一系统的文章一脉相承,而与时文有霄壤之别。朱熹之肯定苏文,应当也有类似考量。
三、分途异趋:朱熹批判苏轼著述的原因
以上从论道与衡文两个层面论述了朱熹分别对苏轼著述的评价。但是,文、道二者毕竟不可分离,一旦合而观之,苏轼的著述便相当于以华妙之文辞阐述不纯之义理了,其危害之大可想而知。因此,朱熹早年便曾发起“苏学之辩”对之大加挞伐,直至晚年讲学时也仍未停止攻击。罗大经说:“晦翁诋斥苏文,不遗余力。”[11]33最足以反映朱熹的激烈态度。那么,朱熹如此批判苏轼著述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下面试从现实原因与根本原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现实原因:圣贤之学与科举俗学之异
宋室南渡以后,苏轼的著述从禁毁中被解放出来。至南宋中期,孝宗更极力推崇苏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主政之人如汪应辰、尤袤等,在取士时也往往拔擢袭用苏轼观点的考卷。教学者如吕祖谦等也对三苏的文章进行编选、标注。此外,吕祖谦等人自己的文章,也都有苏文的影子。刘咸炘在《宋元文派略述》》中即指出:“吕祖谦、叶适、陈傅良皆以文名,皆苏氏之后昆也……适于前人多所排击,而颇称苏氏。”而他们的文字同样也是士子经常模拟的对象,因此士子在学习之时相当于间接地接受了苏轼的影响。这几方面或直接、或间接的力量汇集到一起,便最终形成了“淳熙中尚苏氏”的局面。朱熹对此均深致不满。他批评孝宗沉溺辞章华藻、又流入佛老,其实等于表达他对于崇苏无法认同。对于汪应辰,朱熹也说与他“多言而愈不合”。至于关系亲密的吕祖谦,朱熹更直言不讳批评他“留意科举文字之久,出入苏氏父子波澜,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坏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苏学为非,左遮右拦,阳挤阴助,此尤使人不满意”[3]1334。
朱熹在谈及他对于苏轼著述的批判时曾说:“非欲较(苏、程)两家已往之胜负,乃欲审学者趋向之邪正。”[3]1426这句话说明他之所以如此猛烈攻击苏文,很大程度上并在于客观地剖析学术的是非,而是针对士人的价值取向有的放矢,以期挽救时弊。朱熹认为苏轼精深华妙的文辞将其义理不纯的问题掩盖起来,使得异端思想能够暗暗地渗入士子心中而使人不自知,及至发觉,其病往往已经深入骨髓,而难以挽回了。因此,他说“其为学者心术之祸最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3]2136。换言之,文辞华妙不仅不足以补救其义理不纯的疏失,相反还会加重义理不纯造成的危害。朱熹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在书信中一再谈及:
苏氏之学,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倾危变幻之习,以故被其毒者,沦肌浃髓而不自知。今日正当拔本塞源,以一学者之听,庶乎其可以障狂澜而东之。[3]1624-1625
苏氏之学,上谈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学者始则以其文而悦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则渐涵入骨髓,不复能自解免,其坏人材,败风俗,盖不少矣。[3]1426
吾弟读之,爱其文词之工而不察其义理之悖,日往月来,遂与之化,如入鲍鱼之肆,久则不闻其臭矣。[3]1863
第一封信是写给国子祭酒芮晔的,朱熹希望他能够力挽狂澜,给予学者以正确的引导。这是对教育部门主管的请求。第二封信是给教学者吕祖谦的,朱熹建议他不以苏文教学。最后一封是写给内弟程洵的,朱熹在信中直接对学者提出了恳切的警告。虽然这三封信接收对象身份各不相同,但关注的重点全部都在“学者”这一主体身上,朱熹想要提醒所有阅读苏文的“学者”,不要被充满华藻的文章所迷惑、沉溺于功名利禄之途,而忘记了道德修养的功夫,相对前者而言,后者才是根本所在。罗大经说:“(朱)文公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11]33尤其强调学校应当禁止,正体现出朱熹批判苏轼著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对苏学借助学校、科举之势败坏士人心术的担忧。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科举俗学与圣贤之学的冲突被凸显出来。朱熹秉承孔子之教,将学者一分为二,即为己者与为人者。在他看来,为己者重在求道,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一系列方法,最终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为人者则趋向学文,他们所想得到的只是时文写作的技巧,以期通过科举考试,从而获得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朱熹认为为己者从事圣贤之学,最终既能成己又能成物,而为人者从事科举俗学,终将迷失方向、外骛忘返。对士人而言,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不受科举的拘束,能够集中精力从事道德修养。但是,就当时社会情况而言,大多数人还无法彻底抛弃功名、专心求道,甚至朱熹本人也不鼓励士人放弃科举。因此,在具体实践中,士人只能努力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
《语类》中有一段当时教学情况的实录:
先生问寿昌:“近日教浩读甚书?”寿昌对以方伯谟教他午前即理《论语》,仍听讲,晓些义理;午后即念些苏文之类,庶学作时文。先生笑曰:“早间一服术附汤,午后又一服清凉散。”①此条为吴寿昌所录,当系孝宗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以后所闻。“术附汤”以白术、附子为主,可以“治风虚头重眩苦极,不知食味,暖肌、补中、益精气”(《近效方》)。“清凉散”,由于医方所载往往不同,难以确指,但可以肯定是当时家庭中常备的普通药物,主要用于缓解“虚热上攻”(《孔氏谈苑》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页),或类似于今天黄连上清片之类的药物。复正色云:“只教读《诗》、《书》便好。”[4]2859
寿昌即吴寿昌,浩即吴寿昌之子吴浩,当时尚属童稚。方伯谟即方士繇。从这则记录看,方士繇在教导吴浩时,将课程平均地分成了两部分,上午诵习《论语》以通晓义理,下午阅读苏文以学作时文。前者是为了完善道德,后者是为了应付科举。古人云“书犹药也”,朱熹也以药物为喻,来分别形容《论语》与苏文的功用。《论语》好比术附汤,能够补中益气、治疗大病,而苏文则只不过如清凉散,最多只能去火消肿,解除些小病小痛,实属无关紧要。朱熹的一笑之中,既有幽默,但又透出一丝无奈与苦涩。而当他一旦清醒地意识苏文的危害,就立刻收起轻松的表情,板起面孔,一变而为严词厉色了。
只不过当时苏文流行势不可挡,朱熹的门下弟子尚且如此教学,当时社会上的情形更可想而知了。甚至朱熹本人也曾一度爱好苏文,所以他在感叹“今人又好看苏文”[4]3087时,应当是有着切身体会的。如此一来,不难想象朱熹在面对士人沉迷于苏文时痛心疾首的模样了。阅读苏文,使得士子们只知“缀缉言语、造作文辞”而忘记道德修养,可谓误人知见、坏人心术。他曾经感叹说:“都昌一二士人好资质,然亦无意于此(道学)。盖是萧果卿亲戚念得苏文熟了,坏了见识也。可惜可惜!”[3]4699直接将士人不志于道的原因归咎于苏文了。而这还必将导致政治风俗的败坏。孟子说:“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科举所选拔的人才最终是为了治理国家服务的,如果选出的人才存心不正,那么他们在行政之时也必然不能遵循义理行事,引发连锁反应。由此可见,朱熹言辞激烈地批判苏轼的著述,实有突出的现实原因。
(二)根本原因:儒者与文人之异
当然,朱熹批判苏轼著述的原因是否仅只于此呢?其实不然。即便抛开了现实层面的考量,朱熹依然丝毫不假以辞色,他对于苏轼著述的态度也没有根本性转变。因此,还有必要从更深层面进行探究。
当时士大夫如汪应辰、吕祖谦、刘清之等人大多认为士子学习苏文,主要都是学习其文辞言语,他们并不通过文章寻求义理,所以苏文在义理的偏差其实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认为苏学“无大害,不必辟之”。但是文、道两者是否可以完全分离,人们是否可能只学习文辞,而不受其中思想的影响呢?朱熹认为这显然不可能。如果以简要的语言概括朱熹之文道观,那么我们可以说他认为:论本末,道本文末;论先后,道先文后;论分合,文道合一。如果持此标准审视苏轼的著述,可以说苏轼可谓因文求道,恰好本末倒置了。因文求道虽然未必不想重道,但其实际结果却必然是重文,最终导致文、道分裂。朱熹在与吕祖谦谈及《宋文鉴》的编纂条例时说:“一种文胜而义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为虚文而不说义理者,却不妨耳。”[3]1476即认为不涉及义理的空言虚文于道之害为小,不妨姑存,而文辞华妙、义理不纯之文于道之害为大,全不可取。朱熹之不取苏文便基于这一考虑。
朱熹在评价苏轼著述时,始终以义理为第一义,而以文辞为第二义。因为前者是大本,而后者只是枝节。他在论及苏轼的一则经解时说:“文义,东坡得之,然未见其于全体用功而有自得处也。”[3]2059虽然肯定苏轼于文义有得,但同时绝不忘批判其在义理上的错谬。因为能够正确认识义理才是根本所在,如果在这一方面存在问题,那么即便贯通文义,终究也还是无所依托。朱熹也曾叙写自己阅读苏文时微妙的感情变化:“平日每读之,虽未尝不喜,然既喜未尝不厌,往往不能终帙而罢,非故欲绝之。”[3]1864“未尝不喜”是初读之下领略到文辞之美的欣喜,“未尝不厌”是转入思考之后对义理不纯的抗拒。可见义理纯正是朱熹心心念念的目标,一旦遇到悖离这一目标的学说,他就必然与之划清界限,不使自己陷溺其中。这种标准的形成,从根本上说,缘于朱熹志于道、即以圣贤为目标的人生追求。
朱熹以“儒者”自居,而将苏轼等人视为“文人”。他自认为继承了二程等人一脉相传的心法,真正地理解了经典中有关宇宙人生的真理。在他看来,苏轼与苏门文人把最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作文章,说高妙”[4]1760上,连经解也只是“文人之经”而已。其高者尚能考究古今成败,而其下者则只是吟诗作乐、游戏文字而已。苏轼等将自己定位为“文人”,无疑没有能够实现自我的完成,辜负了上天所赋予人的使命。
进而言之,这种“儒者”与“文人”的不同追求,展现出善与美之间的矛盾。文辞华妙代表着文章之士对美的向往,而义理纯正则体现出道学家对善的追求。前者有自适之意,而后者有救世之心。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其中某一方面,便难免发生冲突。苏轼在评价王安石的文章时说:“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已。”[1]325朱熹却反驳道:“若使弥望者黍稷,都无稂莠,亦何不可!”[4]3099这最足以反映他们价值观念的差异。朱熹期待的是“同至一善”的境界,而苏轼显然意识到“同至一善”只是空想,强迫统一的善最终绝不可能带来黍稷遍布,相反,只会产生一片黄茅白苇,可能达到的至多是“以不同为同”“以不齐为齐”的境界,因此,不妨说他憧憬的是“各存其美”的境界。美、善两者虽然可以并存,但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美、善两者难免成为对方的阻碍。在朱熹强调“善”的价值取向下,“美”必然成为“善”的阻碍,这一点决定了朱熹对苏轼的总体态度必将是否定的。
然而义理纯正与否殊不易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如朱熹所固执之是,今日反以为非。至于苏轼的文辞之妙,虽然一度被指摘,但却越来越得到认可。朱熹察觉到了苏轼重文之弊,却没有意识到自己重道之害。他一味迫使美从属于善,甚至以善为美,使得美始终处于附庸的位置,这一方面破坏了美的“纯粹性”[12]66,另一方面也并没有真正给予善合适的位置,未尝不是两失之。进而言之,善也并不是单一的,而具有“多样性”与“相对性”[13]259,因此“同至一善”的追求本身是否可以妥当也存在疑问。更重要的是,如果将这一学说付诸实践,必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陷溺文辞至多华而不实,而统一道德却可能寸草不生。朱熹应该没有料到,他想要借以转变人心的学说,最终变为禁锢人性的枷锁。钱锺书曾感慨道:“义理学说,视若虚远而阔于事情,实足以祸天下后世,为害甚于暴君苛政。”[14]1132所谓“学术终然杀天下”[14]1132,诚非虚语。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朱熹认为苏轼的思想并非纯粹的儒者之学,其中混杂了佛老之学与纵横之学,这导致他在道德领域中不能分别邪正,在政治领域内不能明辨义利。对于苏轼的文辞,他虽然有所贬抑,但也仍然承认其文辞华妙,能够欣赏其伟丽雄健,并较为客观地看待古文发展的脉络,给苏文一个恰当的历史定位。但是由于士人群趋科举事业、不务圣贤之学,而文辞华妙、义理不纯的苏文又风行科场。在朱熹看来,这将对学子的心术产生恶劣影响,使得人才败坏、风俗浇薄。基于这一现实原因,朱熹对苏轼的著述展开了猛烈批判。当然,其批判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朱熹始终以“儒者”而非“文人”作为人生目标,以“义理”而非“文辞”作为首要的评判标准。朱熹所追求的是“同至一善”的境界,他不认同苏轼“各存其美”的主张。但是朱熹只抓住了苏轼的漏洞,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立论的局限,这导致他对苏轼的批评时有偏颇,值得反思。平心而论,“同至一善”的用意固然可嘉,但如果一味执著于求善,而无各存其美之心,其流弊也将不可胜言。唯有给予善与美以合适的位置,才不致于轻启争端、重演悲剧。这或许是我们今天重检朱熹言论所能获得的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