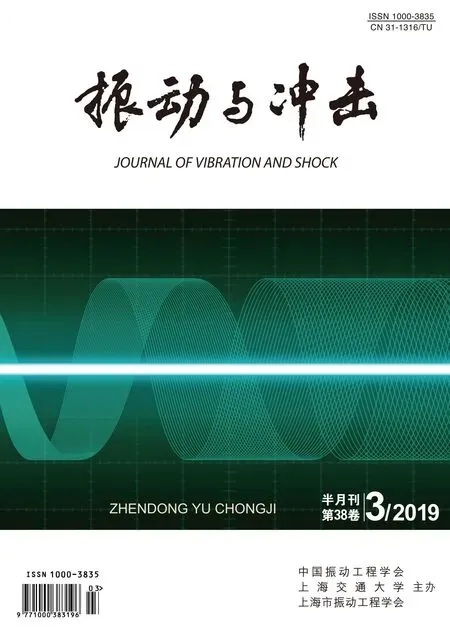移动效应的下击暴流风场特性分析
汪之松, 武彦君, 方智远
(1.重庆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重庆 400045;2.重庆大学 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45)
Fujita[1]定义下击暴流为雷暴天气中急速下沉气流猛烈冲击地面并向四周扩散而引起近地面短时强风的灾害现象,在世界各地发生的频率都很高,严重影响人的正常生活甚至危及人的生命财产安全。2012年5月6日,日本东部地区突遇下击暴流,造成2人死亡近50人受伤,约2万户家庭断电;2015年6月1日21时26分,“东方之星”客轮遭受下击暴流袭击,瞬时极大风力达13级,持续时间约6分钟,导致442人遇难。Proctor[2]根据相关资料分析认为下击暴流是一种普遍现象,在雷雨天气情况下发生的概率高达60%~70%;根据澳大利亚对输电线塔倒塌破坏的调查分析表明,90%左右的输电塔线体系的倒塌破坏事故均是由下击暴流等强风造成。
下击暴流发生频度高且破坏性强,国内外学者针对下击暴流的风剖面特性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轴对称稳态风剖面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3-7], Oseguera等[8]、Wood等[9]、Vicroy[10]、陈勇等[11]提出了平均风速经验模型。而气象观测结果表明,由于受到大气边界层风的影响,下击暴流不仅仅是静止型的轴对称模式,还具有整体水平运动的特征。这种移动型下击暴流在其运动方向上以及在较短时间尺度内,风速更强并伴随风向改变,动力效应明显,更容易造成输电塔线体系的破坏。考虑非稳态冲击风主要采用矢量合成法[12],所用横廓线模型包括:Oseguer等、Vicroy、陈勇等提出的平均风速经验模型、Holmes横廓线模型[12]、Chay等[13]提出的加以改进的OBV模型。在此基础上,Holmes等从经典的冲击射流理论出发,将冲击射流的径向风速与雷暴冲击风的风暴中心移动风速矢量合成,提出了一个能描述雷暴冲击风水平风速和雷暴移动的雷暴冲击风速模型。Chen等[14]采用谐波合成法模拟了脉动风,再采用矢量合成法和Holmes-Oliver横廓线模型,最终获得了包含脉动部分的非平稳水平平均风速时程。但基于矢量合成法获得的水平平均风速时程都无法全面考虑冲击风移动速度和射流速度对下击暴流风场的影响。
李锦华等[15]通过非均匀调制函数法证明了下击暴流非平稳脉动风速数值模拟的有效性。Letchford等[16],Sengupta等[17]在实验室里采用移动喷嘴,进行了下击暴流的物理模拟。Mcconville等[18]则通过固定喷嘴,使用移动的风速探头测量了下击暴流的风速时程,并与实测结果取得了较好的一致性。陈勇等采用可运动、可变冲击风参数的下击暴流冲击风试验装置[19],该装置采用固定喷嘴,通过驱动电机带动平板运动来模拟下击暴流冲击风的运动流场。这里用到了转换思想,小车和平板的移动速度即为冲击风的移动速度,这种近似模拟与实际风场有所差异。为了较好地还原真实气候条件的下击暴流,论文采用了可移动的射流喷筒进行下击暴流风场试验,并用大涡模拟研究冲击风的射流速度、移动速度对下击暴流风场特性的影响,并把风场试验结果和模拟结果进行对比。
1 风洞试验
1.1 试验装置
冲击射流装置如图1所示,由支架、传动带、液压缓冲器、移动平台及试验平台组成。射流喷口固定在移动平台上,可在水平方向自由移动来模拟移动型下击暴流。射流喷口包括风扇段、扩散段、稳定段和收缩段。其中风扇段为整个系统的动力源,扩散段及稳定段的主要作用是导流和整流,并加装了阻尼网和蜂窝器等整流装置来保证收缩段入口及出口气流的均匀性;收缩段主要对气流进行加速。
试验几何缩尺比为1∶1 000,射流喷口直径Djet=600 mm,喷口与底板的距离H=2Djet。为了研究风暴移动对下击暴流风场的影响,试验同时进行了静止型和移动型下击暴流试验。试验装置的移动速度Vtr、射流速率Vjet的调节范围分别为0~25 m/s,0~1 m/s,采用三维眼镜蛇探头对风速进行数据采集,自行设计风速探头支架,该探头为4孔压力探头,可对x,y,z三个方向的风速进行采集,风速测量范围在2~100 m·s-1,测试精度在±0.5 m/s,风向测量角为±45°椎体,测量精度为±1.0°,本次试验探头采样频率为256 Hz。取对应于竖向风速剖面最大值所在高度的测点(z=0.02Djet)和对应于高度为z=0.02Djet位置处的测点进行试验研究。

(a)

(b)
1.2 试验的测点布置与工况
静止型下击暴流试验测点布置如图2(a)所示,在距离喷口中心r=1.0Djet处布置测点,移动型下击暴流风场试验测点布置如图2(b)所示。试验主要研究了喷口移动速度Vtr与射流速度Vjet对风场的影响,试验工况如表1所示。
2 数值模拟
论文建立了缩尺和足尺模型来验证移动型下击暴流数值模拟的可靠性,并验证了缩尺和足尺模拟结果的无差异性。缩尺模型与模拟工况均和试验保持一致,缩尺比为1∶1 000。计算域示意图和网格划分如图3所示,计算域长17Djet,宽11Djet,高3Djet,喷口移动区域长7Djet,宽和高均为1Djet,射流直径Djet=0.6 m,喷口到地面的高度Hjet=2Djet。采用UDF函数定义入口边界条件,通过UDF函数控制移动速度、射流速度和喷口直径等参数的大小,喷口移动区域四周采用光滑壁面,无剪应力,地面和计算域四周分别采用无滑移壁面和压力出口。网格划分采用三维结构化网格,总数约600万,计算时间步长为0.001 s,喷口移动区域的网格进行了均匀加密处理,如图3(b)所示。

(a)

(b)


工况编号移动速度/(m·s-1)射流速度/(m·s-1)102020.510311040.5205120
党会学等[20]从相对速度原理的角度出发,在数值模拟中将下击暴流的水平移动速度转化为地面的相对移动速度而保持下击暴流静止不动,这种转换思想与实际的移动下击暴流有所差别,为了改善上述转换思想的不足,本文采用UDF函数控制喷口移动,可以更真实的模拟实际的下击暴流。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实测风速显示,下击暴流产生的近地面强风的最大风速可超过60 m/s。受试验条件限制,喷口的移动速度和射流速度取值较小,和实际的下击暴流相差很大。为了尽可能反应下击暴流的真实尺度,研究移动速度和射流速度对实际下击暴流近地面风场的影响,建立了三维足尺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射流直径Djet=600 m,计算域的网格划分、边界条件设置以及Fluent计算中的求解设置都与缩尺建模保持一致。数值模拟工况如表2所示。

(a)

(b) 俯视图

(c) 主视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3-d computation domain and mesh generation

缩尺与足尺模型均采用大涡(LES)模拟,采用SIMPLEC显式解法对速度和压力的耦合进行求解,空间离散采用二阶迎风格式,动量、湍动能、湍能耗散率、雷诺应力均采用二阶精度的中心差分格式进行离散化。计算过程中采用增强壁面处理,使用壁面模型法模拟近壁面区域的复杂流动,考虑到近壁面区域的湍流发展不充分,对近壁面网格进行了加密处理,如图3(c)所示。地面首层网格厚度为2×10-5m,满足无量纲距离y+≤1。
3 结果与分析
3.1 试验与缩尺模拟结果的对比
图4中(a)和(b)分别给出了当h=2.0Djet,Vjet=20 m/s时2个测点在不同移动速度下的风速时程曲线,图中u为沿径向的水平风速。由图可知,静止喷口在z=12 mm高度处径向风速在1.0Vjet左右,而在z=60 mm时风速平均值集中在0.8Vjet附近,这一现象符合下击暴流近壁面径向风速下大上小的分布规律。
图4中(c)和(d)分别给出了当h=2.0Djet,Vtr=1 m/s时2个测点在不同射流速度下的风速时程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射流速度下,曲线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即风速曲线在t=1.6 s附近达到正峰值,之后风速大致呈线性减小直至为0,此时测点位于风眼,然后风速进入负风速区域并在3 s附近达到负峰值,之后随着风暴中心与测点的距离增加风速降低,并逐渐趋于稳定。在下击暴流通过测点的过程中,风速的方向会发上180°转变。
图4中(e)和(f)分别给出了当h=2.0Djet,Vjet=20 m/s时2个测点在不同射流速度下的风速时程曲线。显然,当喷口移动时,除达到正负峰值的时间不同之外,不同移动速度下冲击风的变化趋势与图(c)和(d)的分析结论基本相似。风速时程在z/Djet=0.02高度处的极值风速为1.2Vjet左右,而在z=60 mm时极值风速约为1.1Vjet。对比发现:射流喷口的移动使下击暴流风场的极值风速显著增大,说明喷口移动对风速极值有放大效应;而且随着喷口移动速度Vtr增大,冲击风的正风速峰值增大而负风速峰值减小。根据Holmes等[12]的矢量合成法可知,下击暴流经过测点的合成风速被假定为冲击射流速度和移动速度的矢量求和,此处正负峰值的变化可由矢量合成法解释。

(a) z=0.02Djet

(b) z=0.10Djet

(c) z=0.02Djet

(d) z=0.10Djet

(e) z=0.02Djet

(f) z=0.10Djet
图5给出了在h=2.0Djet,Vtr=1 m/s,射流速度Vjet分别为10 m/s和20 m/s时2个测点在试验和模拟条件下的风速时程曲线。对比发现,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在整体上吻合较好,可以采用数值方法对移动型下击暴流进行有效的模拟分析。

(a) z=0.02Djet

(b) z=0.10Djet

(c) z=0.02Djet

(d) z=0.10Djet
3.2 足尺模拟的风场特征
图6为不同移动速度和射流速度的下击暴流在t=300 s,z/Djet=0.02高度处的三维风速云图。可以看出,下击暴流的下沉气流冲击地面后,风速逐渐从竖直向下转变为水平方向,具有明显的风速转向的特点;静止型下击暴流的风场具有对称性,而移动型下击暴流随着移动速度的增大,不对称性越来越明显,这与全球自然灾害损害报告提供的资料基本吻合。这种不对称性表现在风暴前方阵风锋加强,而风暴后方则减弱,风暴前方的极值风速要明显大于后方。这是由于风速转向后,在风暴前方形成的速度和下击暴流的整体移动速度叠加,表明移动速度对风暴前方近壁面水平风速具有显著的增大效应,但对风暴后方的风速则有一定程度的削减。

(a) vtr=0,vjet=30

(b) vtr=3,vjet=30

(c) vtr=6,vjet=30

(d) vtr=9,vjet=30

(e) vtr=6,vjet=20

(f) vtr=6,vjet=60
移动下击暴流的喷口位置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其水平风速的竖向和径向风剖面由于风暴移动无明显规律。不同移动速度和射流速度的下沉气流冲击地面前后,各径向位置的水平风速竖直风剖面呈现显著变化,而当下沉气流发展到稳定状态后,其径向风剖面表现出一定的规律。瞿伟廉等[21-22]指出,静止型下击暴流水平风速极大值出现在径向位置r=1.0Djet附近,竖向高度z=0.02Djet左右位置处。所以论文以t=600 s时下击暴流喷口中心所在位置为基点,考察不同移动速度和射流速度下相对此基点距离r=1.0Djet位置处的径向风剖面,如图7所示。

(a)

(b)
图7 距喷口中心1.0Djet位置处水平风速的竖向风剖面
Fig.7 Vertical profiles of radial velocity at the position of 1.0Djetfrom nozzle center
从图7中可以看出,不同移动速度和射流速度的下击暴流,其径向风剖面的风速随高度增加先增大到最大值,然后迅速减小,这与Hjelmfelt[23]实测的下击暴流竖向风剖面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移动速度下水平风速的最大值为1.4Vjet(42 m/s)左右,静止型大约为1.2Vjet(39 m/s),都出现在风剖面的下端大约z=0.02Djet位置处。由此可知,风暴的移动改变了风场结构,使风暴前方的极值风速明显增大。
为了考察实际下击暴流风场近地面风速的变化规律,在风暴移动中心线z=0.01Djet高度上的不同位置处布置了测点,如图8所示。对比各测点的风速时程发现变化趋势大体相同,故选取风暴移动中心线上距离移动喷口中心1 200 m、离地高度0.01Djet处的测点进行分析,研究该测点处冲击风的运动速度和射流速度对风速时程的影响。将风速与射流速度相比以获得无量纲的风速位移曲线,如图9所示。

图8 z=0.01Djet位置处风速测点

(a)

(b)
Fig.9 Comparison of wind speed time histories under different moving speeds and jet speeds
从图9(a)中可以看出,不同运动速度下冲击风在达到正峰值之后风速大致呈线性减小,直到风速为0,此时测点位于风眼,然后风向发生反转,风速进入负风速区域并达到负峰值,之后随着风暴中心与测点距离的增加,风速降低并逐渐趋于稳定。因为射流速度Vjet保持不变,不同移动速度的下沉气流冲击地面的时间相同,但达到峰值时下击暴流所在的位置差别较大,峰值所在位置大致和移动速度的大小成正比,大致满足1∶2∶3的比例关系,而曲线峰值之后下降段所持续的时间和移动速度呈反比,大致满足3∶2∶1的比例关系;不同移动速度下,风速位移曲线的峰值大小差别较大但风速为0的位置差别不大。说明移动速度对峰值的放大作用比较明显,对峰值点出现的位置和下降段所持续的时间影响较大,对风速为0所在的位置影响不大。
图9(b)中不同射流速度下冲击风的整体变化趋势与图9(a)的分析结论基本相似,不同的是,曲线达到峰值时的位置和射流速度的大小成反比,基本满足3∶2∶1的比例关系,而曲线峰值之后下降段所持续的时间和射流速度呈正比,基本满足1∶2∶3的比例关系,这和移动速度对峰值所在位置以及下降段所持续时间的影响刚好相反。
4 结 论
本文采用下击暴流冲击风试验装置、LES模拟,研究了冲击风移动速度和射流速度对移动型下击暴流风场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1) 与静止喷口相比,移动喷口在z=0.02Djet高度处的径向风速增加了20%左右,随喷口移动速度增大,冲击风的正风速峰值增大而负风速峰值减小,移动速度对峰值的放大作用比较明显,射流速度对对曲线峰值的大小影响不大。
(2) 移动型下击暴流风场具有风向转变和不对称的特点,移动速度对风暴前方近壁面水平风速具有显著的增大效应,但对风暴后方的风速则有一定程度的削减。
(3) 移动型下击暴流发展到稳定状态时的风剖面随高度增加先增大到最大值,然后迅速减小,最大风速出现在风剖面下端位置处。
(4) 曲线峰值所在位置大致和移动速度的大小成正比,大致满足1∶2∶3的比例关系,曲线下降段所持续的时间和移动速度呈反比,基本满足3∶2∶1的比例关系,而射流速度对二者的影响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