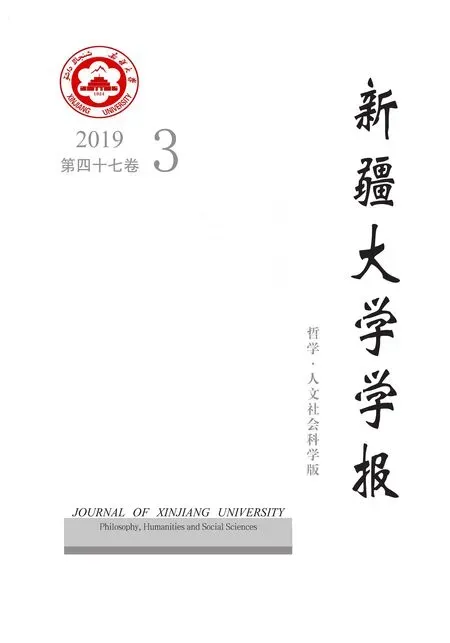“假目喻知”的“正言若反”
——《管锥编·老子王弼注·一六》发微*
彭英龙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广东 珠海 519082)
钱锺书博极群书,要从东西方人都怎么说,来看古今人是怎么想。其中特别究心于一个问题,即中外神秘主义者的思想和言说方式。这些神秘主义者,钱锺书习称为“神秘宗”,有时也称之为“神秘家”,它包括通常所说的道家、释家和基督教神学家等。这些宗派虽然观念和趋向上大有差别,但共同点是都有一定的出世倾向,强调神秘的心智修习和精神体验。钱锺书对神秘家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谈艺录》中,他就对中外神秘主义思想作了大量对比,而到写作《管锥编》时,尤为登峰造极。《管锥编》的开篇《周易正义·一》就与神秘主义研究有关。他首先区分了“一字多意”的几种类型,然后称其中最为复杂的“同时合训”一类为神秘主义思想家所热衷:
则均同时合训,虚涵二意,隐承中世纪神秘家言,而与黑格尔相视莫逆矣。[1]6-7
《管锥编》对神秘主义的探究几乎随处可见,而尤以《老子王弼注》的十九则最为集中。这十九则秉承了钱锺书的一贯风格,即,不是单纯就《老子》谈《老子》,而是将《老子》的许多思想和言论放在中外文化的大场域中加以审视。《老子王弼注·一六》的这段话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不“明”不“白”,即《文子·微明》:“冥冥之中,独有晓焉;寂寞之中,独有照焉。……”;亦即《庄子·齐物论》:“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人间世》之“以无知知”,《徐无鬼》之“无知而后知之”,《知北游》:“论则不至,明见无值”(郭象注:“暗至乃值”),《天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在宥》:“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关尹子·九药》至曰:“圣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聋;圣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圣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五灯会元》卷三庞蕴居士曰:“眼见如盲,口说如哑”;勃鲁诺亦以盲哑人为证道之仪型,示知见易蔽,言语易讹(……)。盲、聋、哑人正“沉冥无知”境界(the Darkness of Unknowing)之寓象耳。[2]703-704
《管锥编》中精彩的段落实在太多,而这一段又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为何这么说?因为这段话简要地谈到了中外神秘主义文献中的一种普遍而奇异的现象,至今少为人注意。钱锺书洞察的深刻往往为其行文的简约所掩盖,而这段话可以说是突出的例子。为了将这段话的奥义发掘出来,我们有必要进行一番“发微”和“充周”。我们的发微并非全凭空想,而是建立在对钱锺书的著述乃至其所研究的神秘主义文献的了解之上。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钱锺书这段话里的洞见,那便是:中外神秘主义文献中都经常使用一种可以称为“假目喻知”的“正言若反”的手段,来传达其思想。这句话里的“正言若反”,是采自《老子王弼注·一九》的说法,该篇对神秘主义文献中的“正言若反”现象作了一个深入的考察;而“假目喻知”则是采自孙诒让《墨子间诂》。钱锺书虽未使用“假目喻知”一词,但孙诒让所谈究的这类现象,却是钱锺书关注并一再论及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上引《老子王弼注·一六》的一段话,同时与钱锺书在别处论述的两种现象有关,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把那两种现象结合起来了。如果熟悉钱锺书对“假目喻知”和“正言若反”的探讨,再回过头来看《老子王弼注·一六》的这段话,我们将惊讶地意识到,这段话揭示了神秘主义文献中的一种奇异现象,蕴含着非凡的洞察力。
一、“假目喻知”解
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人类语言中遍布着隐喻。莱考夫、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甚至主张,人类的语言和思维就是隐喻性的。他们的立论根据之一是语言运用中的某种不可思议的规律性。他们提出的著名的概念隐喻“理解是看见”(understanding is seeing)就是建立在对大量语言表达的规律的概括之上的。莱考夫的弟子斯维泽从英语中举出的大量词语便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晦暗(opaque)、透明(transparent)、清晰(clear)、模糊(muddy)、朦胧(murky)、弄清楚(shed some light)、鲜明的(bright)、闪耀的(brilliant)、照亮(illuminate)、晦而不明(in the dark)、管窥(tunnel vision)、有洞察力的(clearsighted)、目光敏锐的(sharp-eyed)、精神/宗教视力(spiritual/religious vision)……①参见 Eve Sweetser《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39-40.这些英语词的共性是以视觉性的语汇表达智识上的状态。巧的是,认知语言学揭示的这一概念隐喻,与晚清的训诂学家孙诒让发现的“假目喻知”竟完全相通。
“假目喻知”的说法出自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子·经说上》直接将“知”比作“见”,“虑”比作“睨”,“恕”比作“明”:
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虑,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若见。恕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3]302
孙诒让《墨子间诂》于“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句下注曰:
《管子·宙合篇》“鉴察谓之明”,此假目喻知也。下文以睨况虑,言不必见,以见况知,则必见矣。此以明况恕,则所见尤审焯。取譬不同而义并相贯。[3]302
他认为“鉴察谓之明”即“假目喻知”,且指出这一隐喻具有系统性:“以睨况虑”与“以见况知”“以明况恕”等出于同一逻辑。“睨”则不必看清,故用以喻“虑”;“见”则已有所见,故用以喻“知”;“明”则不仅有所见,且所见甚为清晰,故用以喻“恕”。孙诒让将这一系统性描述为“取譬不同而义并相贯”。
“假目喻知”与认知语言学中的“理解是看见”一样,都揭示了人类语言的一种广泛分布的现象:以视觉性语汇表达智识情状。二者的偶合既证明了中西语言的相通,又证明了中西学人见解的相通。鉴于“假目喻知”这一表达更接近汉语的习惯,本文将以“假目喻知”指称这类现象。
在《管锥编》中,我们找不到“假目喻知”这样的表达。但钱锺书的确对这一现象关注颇多。最为接近的一段话来自《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三一》:
徐陵《与顾记室书》:“忽有陈庆之儿陈暄者,……妄相陷辱,至六月初,遂作盲书,便见诬谤。”按“盲书”可与“瞽说”印证,似仅见于此。《西游记》第七八回比邱国丈诃唐僧,亦曰:“你这和尚满口胡柴!……枯坐参禅,尽是些盲修瞎炼!”“盲书”者,满纸“胡柴”耳。今江南口语之“瞎说”、“瞎写”、“瞎来”、“瞎缠”等,皆指纰缪无理、虚妄无稽。以“盲”、“瞽”、“瞎”示持之无故而言之不成理,亦犹以“明见”、“有眼光”、“胸中雪亮”等示智力,如韩愈《代张籍与李浙东书》:“当今盲于心者皆是,若籍自谓独盲于目尔。”人于五觉中最重视觉(the primacy or privileged position of the sense of vision),此足征焉。[4]2294-2295
“明见”“有眼光”等,都是以“明于目”比拟“明于心”。相对的,“盲书”“盲修瞎炼”“瞎说”“瞎写”“瞎来”“瞎缠”都是以“盲于目”比拟“盲于心”。综合起来,这正好符合孙诒让所说的“假目喻知”而“取譬不同而义并相贯”。
《管锥编》另有几处对这类现象也有涉及。试举一例,《太平广记·八》“增订三”:
“肉人”之名出于道书,而“肉眼”之称传自释典,如《大智度论》卷三〇《释初品中善根供养》:“智慧者、其明第一,名为‘慧眼’。若无慧眼,虽有肉眼,犹故是盲;虽云有眼,与畜生无异。”[2]998
此处区别“肉眼”与“慧眼”。可见“慧眼”中的“眼”并非“肉眼”,而是“假目喻知”式的假设、悬拟的“眼”。
我们可以从古籍中找到大量假目喻知的语句和段落。如以下这些有趣的句子:
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5]385(《墨子·耕柱》)
墨子之于道也,犹瞽之于白黑也,犹聋之于清浊也,犹欲之楚而北求之也。[6]380(《荀子·乐论》)
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诞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聋我也,子其盲我也。[7]56(《列子·黄帝篇》)
岂独形骸有闇聋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闇聋之类也。[8]206(《文子·符言》)
除了《列子·黄帝篇》以外,其他几处都是直喻。这几句话有着一贯的逻辑:“盲”“瞽”譬拟无知,代表一种负面的、消极的价值,而“明目”则譬拟知晓,代表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价值。这几句话还有一个特点:视觉性比喻和听觉性比喻并用。从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的角度看,这可能具有一定普遍性,如根据戈林(Gred Schmidt Göring)的发现,《圣经》中经常以视觉和听觉隐喻知道或理解。①参见Gred Schmidt Göring《Sapiential Synesthesia.In B.Howe and J.B.Green(eds)》,《Cognitive Linguistic Explorations in Biblical Studies》,Berlin: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4,pp:125-127.而且,听觉性比喻遵循着与视觉性比喻相近的逻辑:“聋”通常是负面的,“聪耳”则通常是正面的。下文我们将看到,神秘主义文献中有大量语句打破了这一逻辑。
根据钱锺书《释文盲》的一段文字,可知德语中也有类似的比拟:“譬如三年前的秋天,偶然翻翻哈德门(Nicolai Hartmann)的大作《伦理学》,看见一节奇文,略谓有一种人,不知好坏,不辨善恶,仿佛色盲者的不分青红皂白,可以说是害着价值盲的病(Wertblindheit)。”[9]47“价值盲”是对德语“Wertblindheit”的精准对译,德文的“blindheit”与中文的“盲”一样,都可以表示“不知”“不辨”。
二、“正言若反”解
“正言若反”是出自《老子》七八章的一个词。对“正言若反”的含义,历来有不同的见解。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收录了几种看法:
河上公注:“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为反言。”
释德清说:“乃合道之正言,但世俗以为反耳。”
高延第说:“此语并发明上下篇玄言之旨。凡篇中所谓‘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柔弱胜强坚,不益生则久生,无为则有为,不争莫与争,知不言,言不知,损而益,益而损,言相反而理相成,皆正言若反也。”
张岱年说:“若反之言,乃为正言。此亦对待之合一。”[10]338(《中国哲学大纲》)
河上公和释德清的理解与苏辙相近。高延第则进一步认为该词“发明上下篇玄言之旨”,将正言若反放在《老子》全书的整体脉络中加以理解。张岱年则从逻辑的角度作了阐发。
在《老子王弼注·一九》中,钱锺书从中外神秘主义比较的角度对该词作了一个独到的分析:
“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按苏辙《老子解》云:“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诟为辱、受不祥为殃故也。”他家之说,无以大过,皆局于本章。夫“正言若反”,乃老子立言之方,《五千言》中触处弥望,即修词所谓“翻案语”(paradox)与“冤亲词”(oxymoron),固神秘家言之句势语式耳。[2]717
对比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收录的几种看法,可以发现,钱锺书对苏辙等人的解读并未提出异议,但作了补充说明。他主张“正言若反”实为老子的“立言之方”,并且还进一步把它界定为“神秘家言之句势语式”。这就是把正言若反放在中外神秘主义思想的大场域中加以考察了。不只是《老子·七八》中有“正言若反”,而是“《五千言》中触处弥望”,指出这点并不稀奇,因为高延第已有所见;但高延第所未论及的是,甚至也不只是《道德经》全书,而是中外的神秘主义文献,都遍布着正言若反的“句势语式”。这一判断看似大胆,却是以钱锺书超迈前人的博学精思为支撑的。
钱锺书还从修辞学中借用了两个词来说明正言若反:paradox即悖论,oxymoron即反论,又称矛盾修辞。虽然如此,结合上下文来看,我们却不能将正言若反完全理解为一种修辞手法。它们都是神秘宗“道可道,非常道”的“立言之方”。“立言之方”不等于通常所谓“修辞”,“修辞”可称“立言之术”,属于钱锺书所谓“小结裹”,重在具体的文字效果;“立言之方”属于钱锺书所谓“大判断”,重在整体的思想表达。“正言若反”的言说方式以反常悖理给人以震惊,迫使读者调整自己的思想路径,看到语言背后所暗示的另一层现实。
如果要做更加细致的辨析的话,则“正言若反”中的“反”有两种含义:一是违反逻辑,一是与世人的见解相反。这两种含义密不可分,因为世人的见解往往合乎逻辑。所以,修辞上的违反逻辑,正好可以用来传达“合道而反俗”的思想。
钱锺书进一步解释道:
有两言于此,世人皆以为其意相同相合,例如“音”之与“声”或“形”之与“象”;翻案语中则同者异而合者背矣,故四一章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又有两言于此,世人皆以为其意相违相反,例如“成”之与“缺”或“直”之与“屈”;翻案语中则违者谐而反者合矣,故四五章云:“大成若缺,大直若屈。”复有两言于此,一正一负,世人皆以为相仇相克,例如“上”与“下”,冤亲词乃和解而无间焉,故三八章云:“上德不德。”此皆苏辙所谓“合道而反俗也”。[2]717-718
按照钱锺书的这一解释,《老子》乃至神秘主义文献中的确遍布着“正言若反”的例子。就《老子》一书,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举例。如七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①本文所引《老子》语句皆出自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一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二二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四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五七章:“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六六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在《老子》之外,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如《大乘起信论》:“当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俱相。”[11]22“无名之相,不离觉性,非可坏,非不可坏。”[11]36又如《肇论·物不迁论》:“不迁,故虽往而常静;不住,故虽静而常往。”[12]20《肇论·般若无知论》:“然其为物也,实而不有,虚而不无,存而不可论者,其唯圣智乎!”[12]74等等。
为什么神秘主义文献中遍布着“正言若反”的句式?这是因为神秘主义思想家往往持有与世人迥然不同的认识,这一认识只有借助于打破语言的常规机制,才有可能传达出来。
三、“以不见见,以不知知”
了解了“假目喻知”和“正言若反”之后,我们不妨回过头去阅读《老子王弼注·一六》的那段话。我们将马上注意到一个奇异的事实:在钱锺书所引的那些话里,假目喻知与正言若反是并存的。如《文子·微明》所说“冥冥之中,独有晓焉;寂寞之中,独有照焉”,此中的“冥冥”“晓”“照”所指,皆非物理意义上的明暗,而是精神上的明暗。可见此处与假目喻知有关。“冥冥”与“晓”“照”按照常理是“相违相反”“相仇相克”的,《文子·微明》却将其调和起来。可见此处又与正言若反有关。所以,综合而言,《文子·微明》的这句话完全称得上是“假目喻知的正言若反”。《庄子·天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与此同理。而如《关尹子·九药》所说“圣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冥冥”为“晦暗”之意,但所指显然不是视觉上的晦暗,“盲”为“不见”之意,但所指也不是肉眼的不见。此处竟以“冥冥”形容圣人之言,也算是“合道而反俗”了,因而也应算作正言若反的例子。
可以看出,以上诸例中的“假目喻知”跟寻常的例子有很大的差别。在寻常的例子当中,“明”往往隐喻一种智识上的“知道”,“暗”往往隐喻“无知”,神秘主义文献却声称“明见无值”“暗至乃值”,可谓背离常理,是十足的“正言若反”。重要的是,这里的“正言若反”是跟“假目喻知”结合起来的,是对“假目喻知”的寻常路径的叛离。
那么,这一现象是否只出现于钱锺书举出的那几句话呢?并非如此。相反,这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老子》:“明白四达,能无知乎?”“明白”按常理应当指的是“知”,此处却与“无知”连类。又如僧肇《般若无知论》:“此辨智照之用,而曰无相无知者,何耶?果有无相之知,不知之照,明矣。”[12]68后文又说:“是以圣人以无知之般若,照彼无相之真谛。”[12]79“照”是指“放光往物所”,“照”之所照被称为“相”。按常理,有“照”即有“相”,而僧肇却声称“照”而无“相”。这也可以说是“正言若反”了。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穷尽相关文献中的这类语句,便会注意到一个奇特现象:神秘主义文本中既有合乎假目喻知的寻常逻辑的语句,又有颠覆假目喻知的寻常逻辑的语句。我们且以《庄子》为例。《逍遥游》和《大宗师》中存在完全符合假目喻知的通常逻辑的类比: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13]5(《庄子·逍遥游》)
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13]68(《庄子·大宗师》)
这两句话中,“盲”“瞽”都是贬义的。它们与上文所引《荀子》《墨子》的类比极其相似,其中并没有“正言若反”。但如果结合《庄子》中的其他语句来看,我们便可以看到矛盾。如根据以下这两条表述,“物彻疏明”的境界是不高的,而“缗缗”“昏”“玄”则代表了极高的境界:
其合缗缗,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13]104(《庄子·天地》)
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於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13]71(《庄子·应帝王》)
结合《庄子》的这两句话,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若昏”高于“物彻疏明”。这一结论违背了“假目喻知”的所暗含的逻辑:视力的清晰原本应当表示智识上的更高境界。类似地,《庄子·大宗师》声称“玄冥”比“瞻明”的体道境界更高:
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曰:“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于讴,于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13]62
认为“玄冥”高于“瞻明”,不仅违背了非神秘主义文献中的“假目喻知”的评价模式,甚至与《庄子》著作中的其他语句也似乎构成矛盾。如《齐物论》所说的“黮闇”和《缮性》篇所说的“蔽蒙”,跟“玄冥”“若昏”等一样是“暗”的,却褒贬不同:
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闇。[13]25(《齐物论》)
缮性於俗,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13]135(《缮性》)
“黮闇”和“蔽蒙”指的都是无知,其境界自然不会高于《大宗师》所说的“瞻明”。而庄子又处处表明,真知的境界是“明”的:
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13]113(《天道》)
圣人对真知的觉解被称为“照”。就其字面意义而言,“照”也显然近于“瞻明”而非“玄冥”,更非“参廖”“疑始”:
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13]14(《齐物论》)
“瞻明”“物彻疏明”不是与“天地之鉴”“万物之镜”“照”等完全相容吗?既然“天地之鉴”“万物之镜”“照”等都是褒义,为什么“瞻明”“物彻疏明”等却都是相对贬义?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自然不能期望这一解释:“天地之鉴”“万物之镜”原都是晦暗的。
我们还可以从《老子》《文子》《肇论》等书中补充一些例子。限于篇幅,各书只取二三例:
《老子》常用“明”来形容智慧或真道,如“覆命曰常,知常曰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见小曰明”。同时,《老子》又以“昏昏”等形容得道之士,如“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这句话里的“昏昏”是暗,“昭昭”是明,根据其上下文判断,暗却比明的价值更高。这与我们上文分析的《庄子》中的情形相似。
《文子》以强烈的光照形容得道的境界,如《精诚》:“昔南荣趎耻圣道而独亡于己,南见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晓灵,屯闵条达,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内,名立后世,智略天地,察分秋毫,称誉华语,至今不休,此谓名可强立也。……夫所谓大丈夫者,内强而外明,内强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无不覆载,日月无不照明。”[8]104-105这都属于“正论”。然而“日月”“明照”等在《文子》中并非尽是褒义。如《九守·守真》:“夫生生者不化,化化者不化,不达此道者,虽知统天地,明照日月,辩解连环,辞润金石,犹无益于治天下也。”[8]144“虽”“犹”两字表明文子对“知统天地,明照日月”的贬低。《文子·道原》甚至还以“瞑瞑”来形容古时之民的视觉:“其衣煖而无采,其兵钝而无刃,行蹎蹎,视瞑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倾,长短不相形。”[8]53“瞑”字本义为暗。《文子》对古时之民多有褒奖,可见视力不佳反而是境界高的证明。
《肇论》中,僧肇有时明确地以光的强弱比拟智慧的高低,如《九折十演者·明渐》:“经喻萤日,智用可知矣。”[12]219日光比萤火强烈普及,而为光明则一,僧肇以此比喻菩萨智与声闻、独觉智的区别,总都是褒义的。但如《般若无知论》:“然则圣智幽微,深隐难测,无相无名,乃非言相之所得。”[12]67“菩萨智”应当已是“圣智”了,前文比作日光,此处却以“幽微”“深隐”等来形容。这一类说法招致了他人的误解,所以《般若无知论》中的“设难”便说:“若无知故不取,圣人则冥若夜游,不辨缁素之异耶?”[12]93但僧肇的回应说明了,“幽微”绝不等于通常意义上的“冥”“暗”:“是以智弥昧,照逾明;神弥静,应弥动”[12]106。
为何会出现以上这类现象?其原因自然一言难尽。但我们不妨参考王夫之《庄子解》中的一段妙论。王夫之通过譬喻解释“知”“明”之别:
明与知相似,故昧者以知为明。明犹日也,知犹灯也。日无所不照,而无待于炀。灯则或炀之,或熄之,照止一室,而烛远则昏,然而亦未尝不自谓明也。故儒墨皆曰吾以明也。持其一曲之明,以是其所以知,而非其所未知,道恶乎而不隐耶?[14]91
王夫之所说的“明”,就是寻常的“知”,或者说世人所认可的知。而王夫之所说的“知”,则是神秘主义思想家所认为的“真知”。王夫之以日、灯作譬,说明了世人所说“知”与神秘主义之“知”的区别。概而言之,世俗所认为的“知”都是有立场的,有立场就意味着它有局限性,有不知的一面。真正的“知”是取消立场,而“照之于天”。神秘主义者对“知”的见解与通常的派别截然不同,通常所说的“知”在他们看来也许只能叫做“无知”,而他们追求的是某种否定或超越了寻常所谓“知”的“真知”。因其为“真知”,按照已有的“假目喻知”的思路,我们可以称之为“明”;因这一“真知”是对通常的“知”的否定,我们又可以称之为“昏”“暗”。而对寻常所谓“知”,我们既可以遵循寻常的表述和评价,称其为“明”;也可以遵循神秘主义者的独特评判,称其为“盲”“昧”等。也就是说,神秘主义者的“知”是对寻常的“知”的否定,但在行文中,神秘主义者的视角和寻常的视角缠结在了一起。正是这一双重视角造成了用词和设譬的表面上的自相矛盾。何况神秘家言常称“真知”非肉眼所能见,这为其称“真知”为“冥”“暗”等,以及贬低寻常所谓“明”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四、“口说如哑”
当然除了假目喻知的正言若反外,《老子王弼注·一六》的这段话还涉及一个平行的现象:言说与哑默。如《庄子·在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关尹子·九药》:“圣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默默”与“瘖”都是言说的反面。《五灯会元》“口说如哑”说得尤为直截、明白。而“勃鲁诺亦以盲哑人为证道之仪型”又是“盲”“哑”并举。“盲”与假目喻知的正言若反关系密切:通常“盲”表示的是无知,在勃鲁诺那里却是智慧的体现。“哑”也有正言若反的意味:世人常以为“口若悬河”的人最有才智,勃鲁诺却显然认同老子的一句话“大辩若讷”。假目喻“知”的正言若反与关于言说的正言若反是紧密相关的:因为一般所谓“知”,大多是以语言传达的,而神秘主义要超越一般所谓“知”,就必然对语言有别样的认识。对此,我们还可以参考《管锥编·老子王弼注》中的其他几则来理解。
中外神秘主义思想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一点是认为语言有局限性。《老子王弼注·二》就谈及这一点:
聊举荦荦大者,以见责备语文,实繁有徒。要莫过于神秘宗者。彼法中人充类至尽,矫枉过正,以为至理妙道非言可喻,副墨洛诵乃守株待兔、刻舟求剑耳。《庄子·秋水》谓“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即《妙法莲华经·方便品》第二佛说偈之“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亦即智者《摩诃止观》卷五之“不可思议境”。《法华玄义》卷一下所谓“圣默然”,西方神秘家言标目全同,几若迻译。[2]638
钱锺书还在脚注里标出了其所参考的西文著作。他所说的与“圣默然”标目全同的“西方神秘家言”,当为“das heilige Schweigen”“die Stummen des Himmels”及“sanctum silentium”。“Schweigen”“Stummen”“silentium”都是“默然”之意,而“heilige”“des Himmels”“sanctum”意思都近于“圣”。钱锺书称其“几若迻译”,不为无据。
《老子王弼注·一六》也提到“圣默然”,而且正是我们上边重点探讨的那段话的前文:
释典反复丁宁:“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第三又《见阿閦佛品》第一二、《中论·观法品》第一六、《大智度论·释天主品》第二七、《肇论·涅槃无名论》第四、《法华玄义》卷一O 上、《法华文句记》卷二六等),始与老、庄有契。《维摩诘所说经·入不二法门品》第九记文殊问法,“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尤后世所传诵乐道。如《世说新语·文学》:“支道林造《即色论》,示王中郎,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文选》王屮《头陀寺碑》:“是以掩室摩竭,用启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所谓“圣默然”,亦《五灯会元》卷四赵州从谂说僧灿《信心铭》所谓:“才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白。”[2]702-703
这段话完全可以和前引《老子王弼注·二》的话并观。“才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白”更是将语言的局限性揭发无遗:语言的框限往往阻碍了通往真知的道路。然而,语言又是很难完全摆脱的,因为它是交流与传达的最主要工具。神秘主义者一方面要“圣默然”,一方面为传达其思想,又不得不言说和表达。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五灯会元》中所谓“口说如哑”的情形。
视觉是获取信息的首要途径,这是人类的语言常常“假目喻知”的缘由;而知识又往往借助语言来传达。因而,视觉的敏锐、视野的明亮、言说的流利等常被认为是富于知识的象征。然而,神秘主义思想家对人的认识的限度提出了怀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关于真知的见解。为了表述其神秘思想,他们往往借助正言若反的句式,这一句式常常颠覆假目喻知这一隐喻的寻常逻辑。同时,神秘主义思想家对语言怀有一种极其矛盾的态度。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导致了“眼见如盲,口说如哑”这类的表达。它们遍布于中外神秘主义文献,纠缠铰接,蔚为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