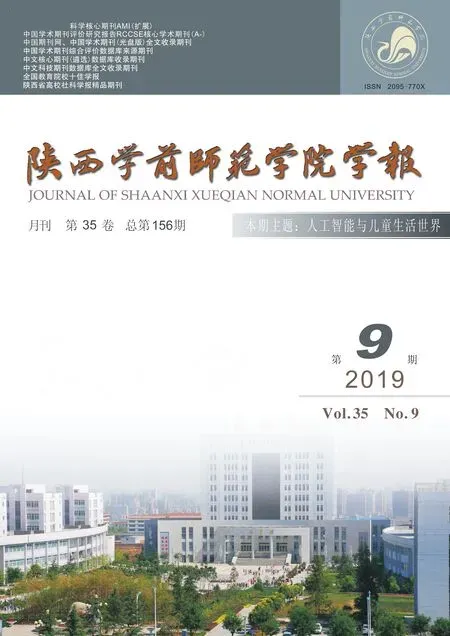美国《早期学习与教育技术政策简报》对我国学前教育信息化的启示
张建欣,蒲远波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广元 628017)
随着互联网、移动设备、移动技术、移动学习、智能技术的普及化和生活化,儿童获得技术更加便利,带来全方位和多元化的生活体验。由此,儿童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交流方式和身心发展面临着新挑战。为回应“α世代”信息化生存问题和解答“21世纪,儿童获得技术是必要的,但还不够”现实难题,美国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了《早期学习与教育技术政策简报》(Early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olicy Brief)。该简报是关于早期学习者使用技术的政策简报,旨在帮助家庭和早期学习工作者实施积极的、有意义的和社会互动的早期教育,使所有幼儿在成年人陪伴和指导下使用技术促进学习和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学习、探索、玩耍和交流的机会。本文在分析《早期学习与教育技术政策简报》框架基础上,重点解读了愿景、早期学习者技术使用指导原则和呼吁行动三部分,结合“技术变革教育世情”、“新时代国情”、“学前教育现代化”以及“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实际,建议从提升我国学前教育信息化水平、提高幼儿园教师信息素养和构建幼儿信息化生态系统三个方面开展我国学前教育信息化工作,满足我国学前教育利益相关者的“技术促进学习”时代诉求,为我国学前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早期学习与教育技术政策简报》发布背景
立足于美国学前教育信息化发展步入新阶段的期许,针对美国学前教育信息化面临的问题,受美国卫生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2015年发布的《利用技术支持幼儿实践》(Uses of Technology to Support Early Childhood Practice)和美国教育部2016年出台的国家教育技术计划(NETP)《为未来做准备的学习:重塑技术在教育中的角色》(Future Ready Learning: Reimagin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两个政策影响,2016年10月,美国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了《早期学习与教育技术政策简报》。该简报是对“α世代”信息化生存的回应,也是对“21世纪,儿童获得技术是必要的,但还不够”现实的解答。这份简报是关于幼年学习者使用技术的政策简报,帮助家庭和早期学习工作者实施积极的、有意义的和社会互动的早期教育。
二、美国《早期学习与教育技术政策简报》内容解读
美国《早期学习与教育技术政策简报》[1]是在美国教育部和卫生部指导下撰写而成,其中,美国教育技术办公室、早期学习办公室、STEM改革和发展办公室、早期幼儿发展办公室、美国儿科学会等部门以及早期学习和技术使用方面的专家也参与该简报的撰写工作。该简报共有致谢、愿景、早期学习者技术使用指导原则、呼吁行动、总结和参考文献共六个部分。其中,愿景、早期学习者技术使用指导原则和呼吁行动三部分分别从本简报出台的初心、如何指导幼儿恰当使用技术,呼吁社会各界力量协同实现本简报的初心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愿景
美国《早期学习与教育技术政策简报》的愿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所有幼儿在各个年龄段里都是在成年人陪伴和指导下使用技术促进学习;另一方面是所有幼儿都有通过多种方式(包括使用技术方式)获得学习、探索、玩耍和交流的机会。正如本简报所言,尽管美国《早期学习与教育技术政策简报》的愿景已经照进现实,快速的技术变革似乎为家庭和早期学习工作者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新学习选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适合于早期学习者,也不是所有的技术都能实现有意义学习,所以成年人需要思考幼儿使用技术问题。另外,技术机会鸿沟日益加大。基于此,教育部和卫生部旨在实现以下目标,即所有社区和所有社会经济水平的所有儿童都能在早期学习环境中公平地获得恰当的技术,并能够负责任地使用技术。
该部分还详细阐述了此简报的出台的目的、关注的对象和幼儿学习最佳方式等。此简报出台的目的为支持早期学习工作者(包括家庭教育工作者)、早期学习项目、学校和家庭为所有儿童做出幼儿使用技术的明智选择,让公众、家庭和早期学习工作者知晓支撑本指导原则的证据基础,呼吁研究人员、技术开发人员以及州和地方领导人以促进幼儿的健康和学习为初心改善技术。关注对象重点关注的是2-8岁儿童而非从出生到8岁早期学习者。本简报认为家庭和早期学习工作者应该意识到,技术的使用不应该取代无结构、不插电、互动和创造性的游戏,应该鼓励与幼儿进行面对面交流。
(二)早期学习者使用技术的指导原则
美国教育部和卫生部认识到,家庭和早期学习工作者对早期学习者使用技术问题有许多不同的选择。尽管随着更多相关研究成果发表,新技术的涌现,指导原则可能会不断发展,但美国教育部和卫生部相信这些原则也是适用的。这四个指导原则主要为:
指导原则一:恰当使用技术并将其作为促进学习的一种工具。在使用技术进行早期学习时,早期学习工作者应注意儿童的发展水平。首先应该考虑什么对儿童的健康发展是最有利,然后再考虑技术如何帮助早期学习者实现学习结果。永远不要为技术而使用技术。为了理解幼儿如何恰当地使用技术,本简报建议家庭和早期学习工作者应该理解被动使用技术和主动使用技术之间的区别。最后,详细说明了0-2岁,2-5岁和6-8岁早期学习者如何使用技术以及家庭和早期学习工作者如何陪伴孩子,努力提供平衡和节制使用技术。
指导原则二:技术应该用来为所有儿童增加学习机会。在成年人的指导和示范帮助下适当地使用技术时,早期学习者使用技术可以补充或扩展学习。然而,当一些孩子有机会积极地使用技术,而其他孩子被要求被动地使用技术时,就会出现数字使用的鸿沟扩大问题。本简报认为,如果使用得当,技术有潜力帮助所有年龄的学习者充分参与学习,提供更多的课程和改善学习成果。适当而灵活地使用技术,可以帮助幼儿满足双语言学习的需求,增加幼儿的学习机会。
指导原则三:技术可以用来增进幼儿人际关系。本简报认为技术可以增进父母、家庭、早期学习工作者、同伴和儿童之间的联系。如家长可以通过视频了解幼儿在校情况,而学校向家长提供幼儿相关在校信息。因距离或健康等障碍阻碍面对面交流时,技术也可以克服这些障碍,加强儿童、同伴、成人之间的沟通。尽管技术有以上优势,但技术不应被用来取代有意义的面对面交流。
指导原则四:当幼儿与成人和同伴互动或陪伴时,技术更有效促进学习。尽管手持设备的技术设计方便用户进行个性化体验,但对于儿童而言,在同伴或成人陪伴下使用效果更佳。在儿童观看前、中、后的不同阶段,成人采取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使技术更有效促进学习。由于“并不是每项技术都适合幼儿,也不是每项基于技术的经历都有益于幼儿发展”,因此,为确保技术发挥积极的作用,本简报建议成人应该持续更新知识,确保有意地、恰当地利用技术提升孩子的学习和人际交往能力。
(三)呼吁行动
本简报为家庭和早期学习从业员就如何在幼儿身上使用技术提供指导原则及建议。同时,鼓励研究人员、开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研究这一领域的重要问题,并制定政策和产品,确保在幼儿学习中最大化地利用技术。呼吁行动内容主要为:第一,研究人员加强纵向研究,这些研究包括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类别儿童如何使用技术、早期学习工作者如何使用技术、如何评估生产商生产的技术产品是否适合儿童学习等;第二,开发人员应以认知科学、教学设计和学习科学等理论为指导,加强与学习科学专家和儿童发展专家密切配合,开发适合幼儿的学习内容和技术工具;第三,管理人员要提升技术水平,为幼儿园教师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同时,向家长推荐家庭访问资源和制定包含早期学习和技术审计的计划。
三、美国《早期学习与教育技术政策简报》对我国学前教育信息化的启示
随着“新时代”来临、“学前教育法”出台以及“幼儿园教育环境”信息化程度加深[2]75,我国学前教育信息化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拥有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结合我国学前教育信息化发展实际,借鉴美国《早期学习与教育技术政策简报》文本中学前教育信息化现状、幼儿信息化学习理念和全员育人理念,建议提升我国学前教育信息化水平、提高幼儿园教师信息素养和构建幼儿信息化生态系统,满足我国学前教育利益相关者的“技术促进学习”时代诉求,为我国幼儿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些许有益参考。
(一)以教育信息化2.0行动为契机,提升学前教育信息化水平
2018年4月,教育部正式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教技〔2018〕6号),标志着我国教育信息化进入2.0时代。该文件中明确提出: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推动教育理念更新、模式变革、体系重构,继而实现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3]。作为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学前教育应以此为契机,结合我国国情,借鉴美国《早期学习与教育技术政策简报》文本中四个指导原则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架构,从幼儿园教育环境、幼儿园教师信息素养、幼儿园与家庭信息化交流、幼儿与教师信息化互动、幼儿使用信息化设备技能以及出台幼儿使用信息化设备规范等六个方面实施,全方位地提升我国学前教育信息化水平。宏观层面而言,需要制定并发布学前教育信息化行动计划、学前教育信息化政策等引导学前教育信息化发展方向,保障学前教育信息化行动政策的实施;从中观层面而言,需要学前教育信息化科研院所、地方学前教育管理部门制定“中国特色”、“本土化特性”的学前教育信息化理论和行动;从微观层面而言,需要从幼儿园教育环境视角而言,充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丰富幼儿娱教环境,增强幼儿与技术的互动,培养幼儿的技术探索能力,满足幼儿的好奇心;从幼儿园教师信息素养视角而言,基于TPACK知识框架,通过校本培训、国培计划等加强幼儿园教师信息素养,实现技术、教学法、知识的深度有机融合;从幼儿园与家庭信息化交流视角而言,利用家校合作网络平台,全天候推送幼儿园教学场景视频,加强学校和家庭间的信息互动和交流,提升家校联动效果;从幼儿与教师信息化互动视角而言,教师定期与幼儿通过课堂、课间、课后不同时段加强与幼儿的互动,记录幼儿的成长轨迹,提高幼儿教育质量;从幼儿使用信息化设备技能视角而言,家长和教师监控幼儿使用信息化设备行为,以脚手架的角色帮助幼儿使用信息化设备,提升幼儿使用信息化设备技能;从出台幼儿使用信息化设备规范视角而言,需要教育部、卫生部、学前教育信息化科研机构、幼儿园等部门联合出台幼儿使用信息化设备规范,指导幼儿使用信息化设备行为。总之,以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为契机,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以及从国家、学校、家庭、社会等不同维度,不同视角提升学前教育信息化水平,满足“α世代”的信息化诉求。
(二)以幼儿信息化学习理念为抓手,提高幼儿园教师信息素养
幼儿园教师是履行幼儿园教育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是幼儿健康成长的启蒙者和引路人,影响着幼儿的性格形成、能力发展和健康成长[4]。在美国《早期学习与教育技术政策简报》文本中明确提出幼儿信息化学习理念,如,教师应该始终战略性地、深思熟虑地、安全地使用技术,并将其与其他有价值的课堂材料结合到幼儿学习环境中;教师应该采取一种更加细致入微的方法确定技术是否合适,而不是简单地考虑屏幕时间限制,评估内容、环境和孩子的发展。教师应该意识到技术的使用不应该取代无结构、不插电、互动和创造性的游戏。教师应注意儿童的发展水平,应该考虑什么对儿童的健康发展是最有利,然后再考虑技术如何帮助早期学习者实现学习结果。永远不要为技术而使用技术。正如国内相关研究认为:“帮助教师有效整合信息技术与学前课程,提供信息素养培训,制定相关信息素养标准,激励教师在教学中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学会利用教学软件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以及教学研究”[5]32。鉴于此,幼儿园教师应以TPACK为理论框架,做到与时俱进,从“技术如何融入幼儿园活动或课程”、“活动中技术使用频率和程度”、“技术与幼儿关系”、“教师、技术、幼儿三者互动方式”等视角思考幼儿信息化学习,深化自身对幼儿信息化学习认知和提升自身信息素养。从技术如何融入幼儿园活动或课程视角而言,加强幼儿园和企业合作,引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于幼儿园活动或课程,帮助幼儿辨别“他我”、“自我”等,保持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从幼儿信息化学习中使用技术的频率和程度视角而言,教师通过计时、记频、行为、语言等方面记录幼儿信息化学习情况,深化幼儿信息化学习的认知;从技术与幼儿关系视角而言,教师需要辩证看待技术与幼儿的关系,思考如何促进幼儿信息化学习和深度学习,如何协助幼儿准确的语言表达和行为表达,提升幼儿的信息化素养;从教师、技术、幼儿三者互动方式视角而言,教师思考自身信息素养水平、技术成熟度和感知度、幼儿接受度和操作能力等,畅通教学信息在教师、技术、幼儿之间传递通道,确保育儿情感在教师、技术、幼儿之间表达准确。总之,教师需要树立幼儿信息化学习理念,从幼儿表达、幼儿园活动或课程、师生互动等视角思考幼儿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自己,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泛在化教学环境,实现学习环境、教学管理、教学互动,满足学生学习的个性化需求,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习效率”[6]89,继而提高教师自身的信息素养。
(三)以全员育人理念为根本,构建幼儿信息化学习生态系统
我国历来重视幼儿信息化学习。国家出台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教体艺〔2018〕3号)、《北京市学前教育信息化行动计划(2008-2010年)》、《上海市托幼园所信息化教学环境建设配置要求》、《江苏省幼儿园信息技术装备标准》、《全国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运行管理规范》、《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等文件,探索解决新时代幼儿信息化学习问题。然而,有关幼儿信息化学习的相关要求、规范、倡议较少。而美国《早期学习与教育技术政策简报》文本中提及幼儿家长、幼儿园教师、早期学习从业者、早期学习研究者、早期学习技术工具开发者以及早期学习管理者如何指导幼儿使用技术,确保幼儿健康成长。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幼儿信息化学习标准和全员育儿的相关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不利于幼儿信息化学习和家长对幼儿信息化学习指导。鉴于此,针对“幼儿如何信息化学习”问题,基于全员育人理念,从幼儿家长、幼儿园(副)园长、教师、保育员、卫生保健人员、炊事员、教研人员全程参与和通力协同视角,建议充分利用“家庭”和“学校”两个学习场所优势,充分发挥“家长”和“幼儿园教师”两个启蒙老师的特长,强化家长和幼儿园教师间沟通方式、沟通主动性、沟通有效性、沟通角色、沟通内容、沟通途径等,发挥家园合作共育的先天优势,从而有效指导幼儿信息化学习。同时,需要鼓励学前教育、教育技术、计算机技术、课程与教学论领域专家或研究者基于“以教师为主导,以幼儿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关注并深化幼儿信息化学习思维、学习心理、学习行为、学习模式等方面的研究;鼓励早期学习技术工具开发者充分利用“儿童为中心”、教学系统设计、儿科学理论、大数据理念开发幼儿信息化学习工具并运用到幼儿生活和学习实践中;鼓励幼儿信息化学习管理者以系统化思维重视幼儿园教师信息素养的培训、幼儿园教师投入程度、幼儿园信息化产出效益、幼儿学习效果、幼儿成长路径等。基于此,构建幼儿信息化学习生态系统,落实全员育人理念,达到全员参与目的,发挥全员育人作用,进而“遵循自然,回归幼儿的真实生活,幼儿在‘无为引导’下愉快自由幸福地发展”[7]60,实现幼有所教的目标,确保学前教育事业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