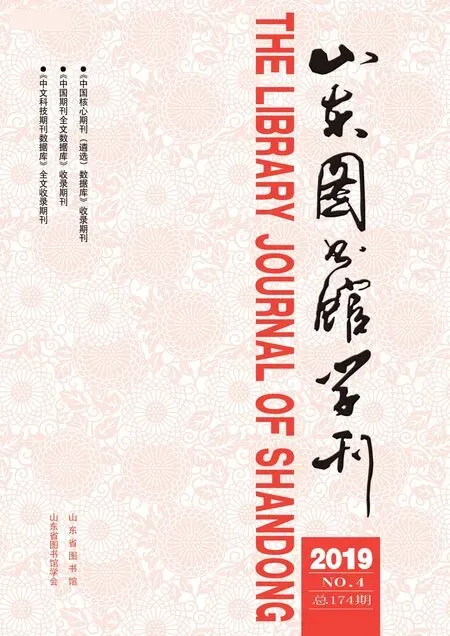方志所载历城史部文献情况析论
——以乾隆《历城县志》、民国《续修历城县志》为中心
邵剑书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 410082)
历城自古以来有“齐鲁首邑”之称,其地居海岱之间,方志载曰“泰岩南耸,黄岗西峙,龙山东镇,济清北绕”[1],复有山水相资,地势沃衍,据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古历城县至1987年撤县建区,作为县级行政建制整整延续两千一百余载。作为济南地区统合发展的重要源头,历城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6)成长为颇具规模的海岱都会,俨然已是“地方百里,户七万,田万顷,名山十三,泉七十二,簪缨相望,工贾毕集”[2]的大型都市,承担着整个济南府政治运作、经济调配以及文教事业等多种职能,是济南府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历城钟灵毓秀,代不乏人,而著述方面,历城则在经史子集四部之中皆有成果。一方面,历城最以文学著称,不仅前有李清照、辛弃疾“济南二安”闪耀词坛,更是明清“济南诗派”的活动中心,反映了历城名士汇集的文化气息。另一方面,见于县志的历城史部文献数量较多、类别丰富,各代史著均体现浓厚的地域特色。笔者认为,通过将历城县志所载史部文献加以爬梳分类,并将历城史著与济南府志所见史著对比考察,既能直观体现出历城史学文献撰写成果的侧重和得失,亦能在济南史著的大背景下,考量居文化中心的历城在济南地区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引领作用;同时,笔者进一步把历城县与兖州府的文教之都——儒学祖庭曲阜县的史部文献进行多方位的比较,展现齐鲁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激荡下,反映在两县史学文献撰写方面的异与同,以期揭示历城史部文献的特殊性,对历城史部文献产生并发展的原因提出更加深刻的解释。
据笔者统计,现存民国及以前的《历城县志》共计五部:其一为崇祯七年至八年(1634-1635)刊印、由历城知县贵养性主修、刘敕主纂的《历乘》18卷;其二为崇祯十三年(1640)刊印、历城知县宋祖法主修、叶承宗主纂的《历城县志》16卷;其三为康熙六十一年(1722)刊印、历城知县李师白主修的《重修历城县志》16卷;其四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刊印、历城知县胡德琳主修、学者李文藻、周永年等编纂的《历城县志》50卷;其五为民国十五年(1926)耆绅毛承霖总纂的《续修历城县志》54卷。笔者选取乾隆志与民国志为考察对象,原因有三:其一,乾隆志与民国志皆属“无一字不著其来历”的“纂辑体”,旁搜远绍、审慎详赅,保存大量珍贵史料,是公认的方志精品,有利考究历城史部文献的成长环境;其二,五种方志之艺文志编修质量不一,或有只以文集诗抄充顶艺文而对经史子排摈不载,或有分类不详当归于史部者错归集部,或有专以朝代编次而索性对文献体例性质不加判别,而乾隆志与康熙志于艺文着力甚多。采撷《通考》与四库十六部两种分类法,详考文献来龙去脉,兼录对文献之臧否评骘,是考察历城史部文献历史与存在状况的上佳选择;其三,二志记录的历史时段前后相接,乾隆志始于汉代历城置县,止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民国志记事则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终于宣统三年(1911),充分保证了史料的整体性与连续性。
1 山左首邑:历城史部文献情况考察
1.1 历城史部文献情况介绍
依乾隆志与民国志合载,历城县史部文献共计88部。历城史学文献的发展肇始于汉代,唐代略有增长但不明显,宋金元时期迎来数量的大幅上升,明代稍有下降,在清代进入发展的鼎盛期,史部文献数量的变化趋势基本可与历城行政区划地位的变动相对应。另据统计可以观察出,历城县的史部文献体例基本完整,除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时令类与史评类外诸体皆备,尤以传记类、地理类文献数量为多,杂史类、政书类文献数量可观,而其余诸体亦各有佳作列于其间。现将各体例文献作逐一说明。
正史类文献三种,即官修宋辽金三史,章丘张起岩任总裁官之一,与贺维一、欧阳玄、帖木儿达世共统于脱脱。张氏谙熟金源典故、道学原委,总裁三史时据理编订,展现了出众的史才史识。三史中,《宋史》卷帙浩繁、体例完备,《辽史》八表价值较高,《金史》篇章叙事详略安排得当、体例有创新、史料价值高,可谓各有千秋。
编年类六种,有起居注一种、实录三种,俱可视作补充正史的优秀史料。另有佚名撰《逢辰记》一卷,见于《通志》,其著记载建炎丞相吕颐浩的历官次序,是了解吕颐浩生平的重要文献。
杂史类七种,宋有其三、清占其四,七种文献内容各不相同,涉及帝王、后宫、伶人等多个群体,是历城史学编纂思想不拘一格、主题多样的直接体现,亦间接反映佻达疏放的齐文化对史学编纂的影响。如《北狩日记》原由徽钦二帝监守阿计替日记其事而成,后密传中国,辛弃疾得而润色之,遂成其书;《行间记》记载邑滑县知县孟屺赡破白莲教众之事;《宫闱艳史》为传说时代至先秦的后妃各为小传,其间夹杂涂抹修饰与野史论断,不可信者为多。
诏令奏议类四种。《诏对恭记》记赵于京康熙四十二年(1703)扈从奏对之语;《毛尚书奏稿》载毛鸿宾任御史、给事中、两广总督期间所撰数百篇奏议,内容多基于太平天国起义兵祸扰攘的背景,讨论选将治兵、理财济用等重大国是。
传记类共十九种,其中唐代一种,明代七种,清代十二种。从内容上看,记载宗谱族谱与亲属事迹者为数最多,共计十二种。《叶氏族谱》载叶氏居历下二百余年族谱,分《序志》《图谱》《念祖》《述事》《家训》五篇,传记精审有度,保留史事异辞,填补家史罔缺;《孙氏族谱》记历下孙家镇孙氏,为孙瓒据孙圣传所撰族谱的第五次重修,共计六十卷;《历城杨氏族谱》为杨大昆依据杨疏琦《续修谱》所撰,仅记清初先祖迁至历城之后的谱系,而对山西洪桐旧事则不再追述;《朱氏世谱》由朱畹记录自枣强迁历城的七世族;《严氏支谱》由严组璋修葺旧有族谱、补录旁支族而成。宗族谱系的修撰有助于后代搜寻谱系旧章、歌颂先功德,起到训诫教导的作用,是了解历城地区世家大姓、名门望族的重要史料。
史评、史抄、载记三类各有一种。地理类是历城史部文献的大宗,三十二种地理类文献广记河渠山水、都会郡县、古迹名胜,几乎涵盖四库地理类史部文献的所有体例。历城史部文献在地理类体例的关切自有其深刻的现实因素,不仅体现在著述者们对本地地理风物的勘察与考证,更扩而广之,体现于对其他地域情况的重视。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记洛阳园林共十九处,借以表达对纵欲享乐而忘天下的反思,《历下水记》本与《洛阳乐园记》并传,却并未流传于世。田告《禹元经》属治水之书,为开宝年间(968-976)田告为疏导澶、濮诸州河患所作;《武林旧事》为周密追忆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共十卷,作者根据目睹耳闻和故书杂记,详述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为了解南宋城市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以及都城面貌﹑宫廷礼仪提供丰富史料;元潘昂霄撰《河源志》为《元史·地理志》的重要参考,潘诸考证天下河流源头极近详实,显示元代四宇一统背景下史家之于辽阔疆域求索的强烈意愿;刘敕《岱史》广泛搜集考证泰山之星野形胜、灾祥灵迹、与夫赋税、文章碑刻,借此批评封禅祭告劳民病国;逯选《畿辅水利志略》载雍正三年(1725)兴修畿辅水利事,编纪水利设施大略,附以奏疏、水利营田图,《北河志略》载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河道原委、山川图样、道员职官,兼谈北河治理之法;叶承宗《历城县志》咨询遗迹、广取诸名家集,共十六卷、纲十二、目五十;其余方志如《潍县志》《东昌府志》《长山县志》《曹县志》等撰修俱详略得当,质量颇高。
职官类两种,政书类七种。汉代公玉带上汉武帝之《明堂图》为方志所见历城最早史学文献,详载黄帝时明堂制度;《修注大清律例》由王贤仪凡三增帙,颇有可采之处。目录类共五种。《金石录》共三十卷,由赵明诚撰写大部分,其余其妻李清照完成并校勘,著录其所见从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来,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考订精核,评论独具卓识,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金石目录和研究专著之一;《水西书屋藏书目录》《藉书园书目》均录历城藏书家周永年书目,《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则录马国翰所藏书目。
1.2 济南府视野下的历城县史部文献
历城县所隶属的济南府,正式设府始于北宋政和六年(1116),金、元时期一直沿袭未改,明代承袭行省制度,设山东行中书省不久,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官署由皇帝直接管辖。洪武九年(1376)又将山东省会由青州移至济南,并在济南设府。至清乾隆时济南共领四州二十六县,而雍正年间(1678-1735),析出济南府中泰安、武定、滨三州为直隶州,后又将泰武二州拓为府,济南府的统辖范围方最终确定下来。济南府因从古至今文教兴隆、著述繁多,而自宋明以来,济南府更是“旬宣之佐、观风之使,莫不萃治于此”[3]“名宦物,焜耀区宇,其德业勋名文章著述不可偻指数”[4],孕育出济南绵延不绝的著述传统。考济南府志中经籍、艺文二志不难看出,济南一地著述种类繁杂、特点鲜明,自汉以来以传经者为多,南北两朝颇以文集著名,唐宋以降经学史学前后接踵,明清以来则诗集文钞瑕瑜错出。史部文献作为济南府著述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史籍数量、编纂体例还是修撰质量,均属上乘、颇完备齐全,这其中又以历城县所出之史部文献最堪考究。笔者以王赠芳修、成瓘纂的道光《济南府志》为主要依据,通过梳理历代历城县史部文献在济南府史部文献中所占比例以及济南府史学文献各种体例中历城史学文献的数量,自纵向横向两方面将历城史学文献置于济南府的视野下经行观察,可以达到进一步理解历城史学文献特点和地位的目的。
据笔者依道光《济南府志·经籍志》归纳分类并统计,济南府史部文献总计269种,按朝代统计:汉代6种,魏晋3种,南北朝17种,隋代5种,唐代17种,宋金两代16种,元代9种,明代82种,清代114种;按体例统计,正史类9种,编年类12种,纪事本末类5种,别史类4种,杂史类6种,诏令奏议类47种,传记类34种,史抄类2种,载记类3种,时令类4种,地理类60种,职官类19种,政书类35种,目录类9种,史评类18种,汇编类5种。
从朝代来看,唐以前历城史学文献的发展尚处于蛰伏期,唯《明堂图》一种文献为方志所见济南地区最早的史学文献,自时间先后意义上可视为济南府史学著述的开山之作;唐代始历城所出史学文献数量占比稳步爬升,在17部中占有5部,此时的历城史部文献体例相对简单,多以帝王实录、姓氏谱牒为主,多为官方意志的产物;宋金元以来,历城史学文献体例愈见完备,并常有著名的史著现世,这段时间是历城史部文献的大发展时期,在多重原因的影响下,宋金两代16种文献历城独占14种,元代9种中历城占6种,数量上冠绝济南府治下其余诸县,体例上杂史、地理、政书相继出现,私家著史风行一时,《武林旧事》等几部地理类文献突出反映宋元两代城市环境的发展变迁,宋辽金三史的修撰以及最早金石著作《金石录》均在史学文献修撰史上意义重大;明代历城史学文献编撰侧重官箴资政、道德训诫,撰史者和受众主体变为官员,政书与诏令奏议两类体例取得长足发展,针对基层社会管理和地方政治运行所撰史著可反映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结构、社会风气的关切;清代历城地理类与传记类文献在济南府文献总量中占比较高,治河成为地理类文献的重要话题,宗族谱系的修葺亦反映出历城当地较为强烈的宗族观念。总之,通过朝代纵向观察,可以发现历城史学文献实开济南史学文献撰写风气之先,唐以前作品较少,宋至元数量一支独秀,明清体例完备并稳固发展,各时期的文献皆展现出不同的主流面貌,官私修史比例均衡,著述者知识背景、身份地位各异,史学编纂思想既活跃开放、合于经世,又有忠于政治、家族传统主题的一面,显示出气象博大、百花齐放的特色。从横向史学文献体例来看,则可以管窥历城史学文献在济南府部分文献体例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正史类中,历城据有宋辽金三种卷帙浩繁、体例完整的大型通史;编年类中,历城独有实录三种而他地皆无;目录类中,金石、藏书目录之属编撰精当,开济南目录学著录风气。除此之外,十六部中历城县之于济南府史学文献贡献之巨者,一为传记,二为地理。传记类方面,济南府三十四种历城有其十二,历城之修撰宗谱家谱不论质量与数量都高其他地区一筹,是整个济南府为数不多的几种宗族谱,其他如《思贤谱》《鉴惩录》寓道德训诫意义于传记图谱中,亦是历城地区对传记类史籍撰写思想路径的开辟;地理类方面,济南府六十种历城有其十七,历城地理类史学文献中,最先完成济南府地区文献对城市历史撰述,其次以河川水利为对象的著作不仅成为济南府地区其他同类型著作的范本,部分水利类著作在全国影响亦深刻,再次历城地区长于方志编纂,多版次《历城县志》与《济南府志》的撰修,无疑对同府其他地区方志在编撰方法、材料选取、编撰态度上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1.3 历城史部文献形成发展原因探析
历城史部文献的形成与发展有其深刻且特殊的现实原因。笔者认为共有四点:
其一,历城作为连接山东东西部的重要枢纽,自汉代以来就是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宋代济南设府后,历城成为名副其实的“山左首邑”,元代历城居腹里之地,明代历城集省府县三治于一地,可见历城县在济南府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政治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地位。由于历城政治地位的特殊性,常任于此或流寓是地的官员大吏总量极大,加之历城处三治之地,官员们不仅需要处理济南府的大政方针,同时还必须兼顾各县民情的上传下达与山东一省的各项政务,庞大的官员群体与重视政务的取向紧密结合,故历城于明清以降官员所撰史学文献数目较多,讨论治国理政、基层政治的诏令奏议、职官与政书类史籍取得长足发展,传记类中训诫正身为官的著作亦偶有出现。同时,官员层的不断扩张孕育了历城本地多个颇有名望、世代从政的仕宦望族,一代又一代投身仕途的先祖加强后人的身份认同,鼓舞了家族的政治追求,为纪念先祖、表达对先祖意志的延续,也为将勤于政事的价值观念保存后世,遂催生年谱家谱的大量著成。
其二,历城在济南府内所处地理区位极为特殊,它北临黄河,南接泰山山脉余脉,辖区内丘陵错落,水网纵横,县城则依山面水,融湖、泉于城,共同形成整个历城县复杂的地理生态环境。历城县号称“川陆悉会之地”,不仅紧邻黄河,还拥有大小清河两条与运河相通的重要河渠,一直是江北地区规模较大的盐粮、漕运中转地和物流集散地,然而河川纵横虽赋予历城重要的经济地位,因此造成的河患却成为影响历城地区安定发展的一大问题。东汉王景治河以前黄河河灾频发,黄河夺道济水更直接对历城乃至整个济南地区的发展造成影响。据载,汉成帝建始四年(前29),黄河“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败坏官亭室庐且四万所”[5]。宋元以来河患未见好转,明代据县志记载济南大小水患共五十次,其中大部分均发生在历城,大小清河原有“往年舟楫浮于二河,商盐遍于齐鲁诸道”[6]的盛景,而自永乐以来“湮塞不通,水失其经一,值天雨茫茫,巨浸坏民田庐,弗以数计”[7]。清代则有“顺治七年(1650),河决张秋,没民田数百顷”,“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黄河水溢,溃入清河。沿河民居尽被漂没,西北一带禾稼尽伤,居民附树为巢,不火食者二十余日”[8],河患之酷烈可见一斑。著述者出于对江北水利问题的重视和对历城河湖情况的关切,大量撰写有关北方河渠治理和历城水生态环境的地理类史学文献,借此表达对民生民瘼的关心和山河地理的探索之意。另外,历城具有众泉环绕、山水相融的城市环境,其中历城城市园林的建设可追溯至宋代曾巩在大明湖南岸修建的百花洲,历代以来历城县城结构愈见复杂,至明清时期历城已成为各项设施齐全完备、各功能地块鳞次栉比,城市建设堪称济南府之典范,城市发展下对城市历史的梳理与追溯无疑带动了城市历史和方志类地理文献的产生。
其三,“齐鲁文学皆天性”,历城自唐宋代以来文士荟萃,形成了独特的文人文化。宋代有范正辞、范讽父子之“东州逸党”、稍后李清照、辛弃疾之“济南二安”,金元“词山曲海”之杜仁杰、张养浩,书法文章之赵孟頫,明清“济南诗派”之边贡、李攀龙、殷士儋,名人高士不绝如缕,使历城真正成为济南府的“文会之都”。与此相辅相成,历城建有府学、县学,在科举学校着力甚多。据《明清进士碑录索引》统计,明代山东共录进士一千六百三十,其中以济南府最多,历城县进士一百六十四,德州九十九,其他县一般在三十至六十,只有少数不足二十[9]。而致力科举或非科举性的学社、书院、义学又于明清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其中尤以书院发展最为完善。文人文化与诵弦之风相互结合影响,一时间历城县“章缝家多觉其子弟以继书香,即农夫胥吏役亦知延师,学馆如云,名社相望”。偏好文采、举县向学的风气影响到史学文献的编纂,具体历城史部文献中,表现在杂史类主题不拘一格和目录类中本地藏书家藏书目录的出现。
其四,部分文献是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下撰写而成的。譬如《北狩日记》《洛阳名园记》在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前后撰写而成,而《武林旧事》与《武林市肆记》是作者在宋元易代的背景下写就的,作品均蕴含作者对故国不复的黍离之悲。另外,历城史学文献在宋金元三代的大发展与易代之际山东受兵燹之祸较少亦有直接联系。
2 齐鲁不同风:历城县与曲阜县史部文献比较研究
曲阜县隶属兖州府,位于山东西南部,北望泰山,毗邻邹城,旧为古鲁国都城,亦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曲阜县的著述传统历史悠长,其地历代所出文献,数量以经史为多,多内容精当、体例严整而有所遵循,且具有较强的道德规训意义,表现出把现世风俗、政治运作置于儒学框架中进行改造的强烈意愿。考察曲阜县所出史学文献,可以清晰观察出当地史学文献受根底深厚的经学传统影响甚巨,在体例内容与文献背后的撰述思想中俱有体现。笔者参考潘相修撰乾隆《曲阜县志》与李经野所撰民国《续修曲阜县志》,通过展示曲阜史学文献的特点,比较历城县与曲阜县史学文献各方面的异同点,探寻两种不同地域文化影响下史学文献风格发生分歧的原因。
2.1 两县史部文献情况之同异
曲阜县史部文献共计92中,按朝代分类史著数量,晋有15种,唐14种,宋9种,金3种,元1种,明6种,清44种。直观地从数量来看,曲阜史学文献的发生时间略晚于历城县。晋至唐以来史著数量颇多,对比同期历城史著数量呈压倒性优势,宋金元三代数量较历城为少,明代略有回升,最终与历城县同时在清代进入了史学文献的成熟和大发展时期。
从史部文献类别来看。曲阜县有正史类3种,编年类5种,纪事本末类1种,别史类13种,杂史类8种,诏令奏议类2种,传记类21种,史抄类1种,地理类12种,职官类5种,政书类5种,目录类7种,史评类7种,汇编类2种,与历城县相同的是,曲阜县史著体例相对完备,且传记、地理两类在整体文献数量中占比也较高,相异的是曲阜别史类文献亦是大宗之一,而历城县并无别史类一门。
若再从深入处考察,则两县在史部文献的著述者、著述内容、传达思想上各有异同。其一,曲阜县史著的著述者身份集中于地方官员和本地世家大族,尤以本地两大著名经学家族——孔氏家族与颜氏家族为主,92部文献中,孔氏家族著有58种,颜氏家族著有16种,足可体现两大家族在当地的文化话语权和累世著述的风气传统,反观历城县史著作者,身份繁多、官私皆有,包括了布衣、文人、乡绅与官员,且并无著述集中的煊赫家族;其二,在著述内容上来看,曲阜史学文献中弥漫着经学色彩,更甚者直接表达儒家文化的相关主题、述孔圣一家之史,史著有经学色彩者如晋孔衍仿《春秋》《国语》《尚书》体例纂《汉尚书》《汉春秋》《后汉尚书》《后汉春秋》等诸别史,儒家主题者如清孔衍璐《庙庭礼乐典故》,官修《圣祖幸鲁盛典》《世宗修庙盛典》俱讨论儒家礼乐典制,述孔家之史者数量更多,代表如宋代孔传《孔子编年》《阙里祖庭杂记》,孔氏家谱、族谱、世谱更不可足数,另外曲阜史学文献多有为官方服务而纂成者,如孔衍所撰之历法、孔淑所撰之一统志、孔至道《百官要理》、孔承倜《荆藩辅政录》等,而考察历城县史学文献的内容和形式,杂史主题丰富、地理类广考天下河流山川,其他诸类各有特色,较曲阜而言更为开放和多样,但在官修史著上不比曲阜;其三,在撰述思想上,曲阜县史学文献表达出明确的道德训诫意图和重视宗族情感的倾向,通过撰写各种史评、官箴和族谱,建立了稳固的、由各种道德榜样和祖先圣贤组成的“崇拜体系”,这种崇拜体系即是儒家道德主义的产物,也是浓厚乡土情感的一种体现,反观历城,其史学编纂思想较难定于一尊,史著中既存在齐文化的烙印,有时又依稀体现出对特殊时事的关怀,间有资政、对为官之道的思考,以及教育宗亲、道德规劝之意,总之,历城县不同史著的纂述思想并无法做出统一的定论。
2.2 同异原因试析
通过将曲阜、历城两县史学文献进行对比,曲阜史著风格之成熟厚重,与历城文献撰述之开放务实相映成趣。两县史著在发展时间、体例侧重、撰者身份、文献内容各有同异,自广阔的文化背景而言,其成因固然与齐鲁文化间的差异桴鼓相应,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有四点,以下分而述之:
其一,曲阜为儒家祖庭,有绵延不绝的经学传统。曲阜则是古鲁都城,最受周礼的浸润,颇讲求道德礼法、追求秩序与一致。曲阜县自源头追溯即为鲁文化的发源地,其史学文献著述不免受到累世经学传统和道德立法观念的影响。晋唐以来经学发展迅速,亦是曲阜史学文献的大发展时代:一方面,晋唐之间,虽然南方地区清谈尚玄是时代主流,然北方地区依然坚守经学传统、诂经解经成风,各立师法、各成家学;另一方面,唐代以来五经定本,官方不断通过各种形式介入经学,使经学与官方意志互相依靠、相辅相生,经学由之发展势头更为迅猛。在晋唐的经学风潮之中,不乏来自曲阜的经学大家,钻研经学而产生的学术自信和学术习惯不免渗透在史学文献的撰写之中,在体例和内容上出现经史交集、经史相藉的情况。另外,曲阜承先秦礼法之余绪,重视对政治运作的道德训诫,并希望社会风俗安定,在有关此类话题的史学文献中,遂表现出浓重的道德训诫色彩。历城县史著在道德训诫的编撰思想上与曲阜史著有相同之处,虽然历城在汉唐存在经学研究的风气,但是在唐宋肇始、明清繁荣的俗文化的影响下,经学传统反而居于次席,反映在史学文献编纂上则出现经史分明、取材广泛、主题多样的特点。
其二,曲阜土地平旷,北有高山,河流平稳,适于农业耕作及定居,而儒家文化重视家族传承和家庭伦理,适宜的自然条件和偏重稳定的文化环境共同造成了曲阜安土重迁的文化情绪,如此一来,曲阜当地的世家大族就拥有成长壮大的环境。通过统计可以看出,曲阜大部分史学文献都是由曲阜本地著述家完成的,而孔颜两大家族更是合力著写曲阜92种史学文献中的74种,贡献甚巨。通观两大家族的史学著作主题,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孔子家族历史的叙写和对儒学家族谱系的编修,可以直观反映孔颜两家族以追溯、传衍家族历史为己任的撰述思想。撰写自家宗族历史的同时,孔氏家族亦专注于编撰曲阜一地之史、整理曲阜所出文献并编次为目录书籍,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孔氏一家之史的变相编修,但无碍于表现孔氏家族作为地方文化话语权把控者的文化担当。地方家族的贡献是曲阜史学文献发展与风格养成的重要原因。反观历城,在包括史学家在内的文献撰述者上呈现出纷繁不同的面貌和身份,并无掌握文化霸权的世家大族,一定意义上推动历城海纳百川、丰富多元文化氛围的形成。
其三,曲阜因其特殊的文化地位,历代受官方推崇,帝王赐号、祭祀、拜谒者络绎不绝,即便处易代之际,征服者对曲阜这一圣学发源之地仍不减其尊崇。官方之于曲阜和孔氏家族的抬高,是道统与治统有意识的合一,有助于确立文化与政权的合法性,而曲阜当地世族对官方的亲近态度常不加排斥,凭藉官方的宣传和扶持,不仅能使曲阜世族始终保有重要的文化地位,也能使曲阜世族有机会深入政治系统,将所秉持的儒学信仰付诸实践。官方和曲阜世族的关系本质上是互惠互利的,反映在当地历史文献的撰写上,可以看出部分史著在撰写目的上存在主动迎合官方意志的取向,同时一部分史著也是在官方要求下编撰完成的。历城史著文献虽然职官、政书与诏令奏议三类文献数量较多,但多反映的是地方政治的政治制度与秩序,而曲阜史著更接近于自中央发出的政治意志。
其四,清代兖州府境内汉魏碑刻分布广泛、数量庞大,而曲阜碑刻无论自数量抑或保存情况都冠绝整个兖州府,即便将视野扩展到全国范围,曲阜所存汉魏碑刻同样也无愧“碑刻半曲阜”的美名。碑刻多有关孔家历史、名宦之迹与名胜古迹,而为整理、辨别曲阜所存大小碑刻,曲阜学者做出了卓绝的努力。故曲阜目录类史学文献中金石、碑碣之属品质上乘,至今对汉魏碑刻的研究和信息采集、秦汉魏晋历史的考证勘误,都有极为重要的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