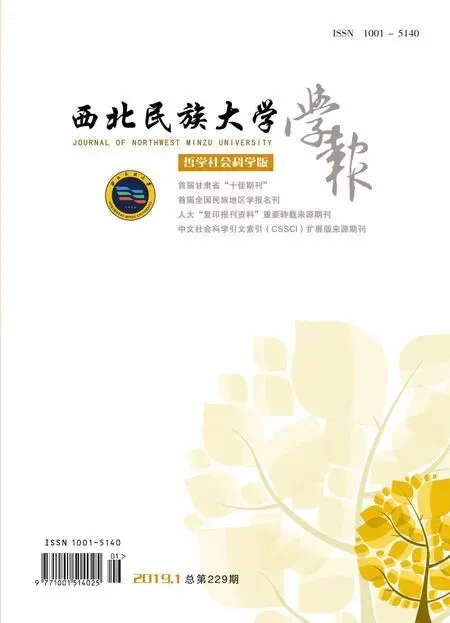论姚莹的诗学观及其诗学价值
温世亮
(汕头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又号幸翁,姚范曾孙,姚鼐侄孙,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官至湖南按察使。姚莹“以学问、经济表著于时”[1],在文学上亦有成就,不仅是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桐城派的重要作家,而且是乾嘉道咸时期经世文士的杰出代表,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即谓“植之先生同时友,才最大者,惟姚石甫先生。虽亲炙惜抱,而亦能自出机杼,洞达世务,长于经济……文章虽未精,而有实用”[2]。大体而言,姚莹虽未有专门的诗学论著传世,不过他的诗学见解甚为丰富,不惟留下了一定数量的诗序、诗跋以及相关论诗衡文的书信,为后世奉献了《论诗绝句六十首》这样的论诗诗,而且这些作品的内在理路又多相贯通,显示出一定的系统性,他在嘉道时期的诗学地位实不容轻忽。目前学界对姚莹的诗学观念虽然已有所论述,但更多的是以儒家传统诗学作为标识或准绳予以评鉴讨论,内中对传统与家族、传统与时代等因素的关联性的发覆探讨,则还有作深入厘清的必要。有鉴于此,本文即着眼于家族和时代,立足于继承和嬗变,进一步探讨其诗学观念及其诗学价值,并就正于方家。
一、诗学通变论:古今并重,唐宋兼采
清代诗坛,流派纷呈,门户标榜极为明显,师法趣尚上的复古学古、宗唐宗宋等涉及诗学通变的命题自然成为此中不可回避的话题。至于中后期,这一态势则愈见明显。如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即以复古为尚;而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则认为诗人不应该受成法之牵囿,要突破古人之牢笼,要敢于自作主宰。与此同时,对待唐宋诗这一论题他们亦多见分歧,或宗唐祧宋,或宗宋祧唐,或折中唐宋,不一而足。就实际而言,受诗坛风向的影响,对这些诗学命题,姚范、姚鼐等姚氏诗人均有所指涉。例如,姚范强调为诗须“师古而能自新”[注]关于姚范“师古而能自新”的诗学观,可参读温世亮《从〈援鹑堂笔记〉看姚范的诗学观》,《阅江学刊》,2012年第6期,第135-141页。;姚鼐于诗歌创作坚守吴德旋《叶水心诗序》所谓“拟之议之乃成变化”[3]的原则,汉魏至于唐宋,无所不窥,其诗亦有“以山谷之高奇,兼唐贤之蕴藉”[4]的特点。总体而言,姚莹则能承其先辈遗绪而发论,大体表现出兼容并蓄的诗学态度。
首先,对前人的诗学观点,姚莹极为重视,主张通过对前人诗歌的学习来获取诗歌创作的经验,复古、学古是他的诗学思想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他的同邑友人光聪谐《早起过方砥如遵道书室,时姚石甫已先至,二子论辩诗法,皆甚口,余因赋长句以调之》中有句云:“姚云是谋匪攸闻,事不师古徒纷纷。仲尼信好述不作,子舆私淑意弥殷。”[5]孔圣人坚持周礼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孔子此论,出自《论语·述而》,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何宴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1页。,而他的弟子曾参则能承其遗绪而光大之,对孔子和曾参的赞同,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师法趣尚这一问题上,姚莹是主张学古和复古的。但是学古不等同于袭古,其目的是为了开新。因此,对于明人杨升庵“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杜子美好者,亦多是效《选》诗,后渐放手,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逸不可”的诗学论旨,姚莹不仅非常赞成,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六朝人诗,字句意格,无不精造生新,故少陵云‘经书《文选》理’,李、杜大家,特变其貌耳。”[6]642强调《文选》不惟对后来学诗者具有引导和启发意义,对后人诗歌创作的新变同样关键。至于姚莹在《论诗绝句六十首》中诸如“精熟选理尽研辞”“辛苦十年摹汉魏”[7]467之类的表达,一样反映了他试图从诗歌遗产中汲取知识养分、提高诗艺才能的意愿旨趣,与其曾祖父姚范“师古以开新”的诗学思想显然是桴鼓相应的,显示出家族的传承性。
其次,姚莹不惟主张学古,其学古的眼光也是开阔的,在学古的范围上要求努力扩大取法的对象,而不囿于某时某家。他认为诗文无所谓古今,不主张强分“周秦”“建安”和“唐宋”,谓“何者周秦,何者建安,何者唐宋,放效俱黜”(《复方彦闻书》)[7]133,并强调“历代诗人,不一其体,各有长短,当取其盛者言之,岂可一语抹煞耶”[6]630。正因如此,对吴梅村“晚近诗家,好推一二人为职志,靡天下人从之,而不深惟源流之得失”之说,姚莹深表认同,甚至称其乃“有为而言”[8]。与此相适应,“多师未必皆从杜”[7]469,倡导转益多师,注重采纳历代“盛者”诗家见解以成一家之言,也便成为姚莹论诗的重要题旨。在《松坡诗说序》中,他回顾了自己的学诗历程,谓:“余自束发即好为诗,苦无师授,乃取诸家诗说观之,稍得要领。自是泛滥古人名集,溯自汉魏以迄本朝,作者数千,皆尝考其元要,究其得失。始叹诸家之说,容有未尽,盖疆域日开,后来流变,昔人不及见也。”[7]112对“汉魏以迄本朝”之“诗说”、“名集”细加研习,不仅明确指出了诗歌遗产的重要性,而且表达了厚古而不薄今的意识。至于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无疑又最为清晰展示了其古今并重的诗学观点,对此,黄季耕《姚莹及其论诗绝句六十首初探》认为它不仅“对诗骚、汉魏乐府到唐、宋、元、明、清的历代诗歌都有所论述”[9]。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论诗绝句六十首》第四十四首中宣称“唐宋元明各有人”“昔贤应畏后来人”[7]470,能够以一种较为公允发展的眼光来衡量古今诗歌,而不作轩前轾后之论。总体而言,相对于从祖姚鼐上起自汉魏、下迄于唐宋的学古宗旨,既是继承也是发展。
复次,唐宋兼宗,不执一端。钱钟书先生曾指出:“惜抱以后,桐城古文家能诗者,莫不欲口喝西江。姚石甫、方植之、梅伯言、毛岳生,以至近日之吴挚父、姚叔节皆然。”[10]146作如是论,自有其根据。不过,姚莹固然重视宋诗的优长,亦曾斥责杨升庵于宋诗之妙处“何尝知之”[6]630,在创作实践中也受到宋诗的沾溉。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唐诗的推崇,如果全然依钱氏之论而将姚莹归入宋诗派的范围,并不十分恰当。其实,在唐宋之争这样一个清代诗学风潮中,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诗人同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而折中唐宋则成为他们一贯的态度。例如,姚范论诗即有糅合古今、唐宋兼宗的诗学主张,他的《谢人惠酒茗》作为论诗诗,可以说便是最好的证据:
昔年尝诵涪翁集,半挺团龙拟必圭。马走勿教门载至,羊肠却听鼎声齐。我今银粟看愈好,客到金樽许共携。入座谁分袒左右,试汤何必厌东西。自注:“宋人诗‘酒酣玉盏照东西’,东西,酒器也。”[11]
诗作虽然不无打趣戏谑的味道,但内中“入座谁分袒左右,试汤何必厌东西”云云所包含的不论古今、唐宋兼重的意见也颇见分明。姚鼐更是明确地提出了“熔铸唐宋”[12]的学说,并将它当作自己一生的论诗宗旨。由于深受家族先辈诗人的影响和感染,姚莹不仅对四唐——初、盛、中、晚——诗歌创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在他的《论诗绝句六十首》中,诸如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韦应物、李商隐、许浑、马戴、贾岛等作者,都是被赞誉的对象。与此同时,对情韵深切的盛唐之诗则尤为爱护,并明确表达了要师法盛唐的意旨趣尚,如《论诗绝句六十首》第十五首称“王李高岑竞一时,盛唐兴趣是吾师”[7]468,即是明证。正因为如此,他对自南宋元明以来诗坛那种没有休止的唐宋之争,自是极为不满的。例如,《论诗绝句六十首》其二十九“纷纷力薄争唐宋,断港横流也未知”[7]468,认为论争者深陷在唐宋诗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洪流泥沼之中,因深受厚此薄彼思想的影响桎梏,或以情感为断,或以理趣为胜,或以格调为目,既不能正确地对待唐宋人诗歌创作的优劣,也没有打破传统以开新的勇气,更无法认清诗史发展演变走向的眼光,实则是一场徒劳的意气之争。大体而言,在创作实践上姚莹亦较好地贯彻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唐宋兼采,故其“诗亦唐、宋正轨”[13]。
综上可见,在对待复古拟古、唐宋之争等传统的诗学问题时,姚莹一方面能守家族诗学之途辙,并予以继承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是立足于当时的诗学风潮而发声,而且能规避深严的门户之见,强调博采古来诗家之长,自成法度。以此而论,他的诗歌观念不惟显示出时代针对性,实际也表现出较为明晰的通变意识。
二、艺术表现论:诗为心声,不穷不奇
言志抒情乃中国古典诗歌最为突出的特征。大体而言,重视情志的表现同样是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诗人的一贯作风,自姚孙棐至姚范,再到姚鼐,都有相关的“诗言情”的论述,他们的诗歌创作实际亦多见性情之真谛。例如,陈式序姚孙棐《亦园集》,即称其诗“乃情之所为作也”[14];姚范更是视“性情”为作诗之根本,称“夫作诗者,孰谓无性情”[15];而姚鼐《吴荀叔杉亭集序》对那些缺少现实内涵而“盛衣冠,谨趋步,信美矣,而寡情实”的“工诗者”则甚不以为然[16]45。大致而言,守传统诗学之影响,承先世之绪论,姚莹论诗亦重视“情”,而“情真”实又成其诗学之本根,并沿着“心声——个性——感触”这样一条路径层层深入地体现出来。
姚莹在《郑云麓诗序》中宣称:“夫诗者,心声也。”[7]114后来,他又在《再复赵分巡书》中指出:“若夫陶冶性情,抒写景物,则诗歌之作,即古乐之遗,所以倡导幽滞,寄哀乐于声音者也。”[7]48显然,在他的意识中,诗歌乃诗人心灵的外化,惟其如此,诗歌创作自应与诗人的心灵世界相沟通,将诗人的哀乐之情感妥善地表现出来。其“心声”之说,实则关涉性情真伪的问题。对这一意见,他在《复方彦闻书》中也进行了诠释,认为诗歌创作须以“修辞立诚为本”,而不以“专精辞赡”为能事,并力主“生平不为无实之言,称心而出,义尽则止”[7]133;也曾经在《东槎纪略序》中指出:“有志立言之士,寓所闻见,美恶皆宜据事直书。”[3]而就实际而言,无论是“立诚”“无实”,还是“直书”,其实均与情真这一题旨紧密相关。此外,在《杨升庵说诗》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谓:“古人诗不苟作,故妙;今人诗文不及古人,病正在一苟字。无情而作,无才而作,无学而作,无为而作,皆苟作也。”[6]629“苟”有随意、随便之意,而又关联“无情”“无才”“无学”和“无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可见“情真”亦是其题中之义。
由于强调诗歌表达真情,所以姚莹虽然主张学古,但是同样反对其《张南山诗序》中所谓“翦彩为花,范土为人者”[7]111那种徒以形模为工而汩没了性灵的学古作风,认为那终究是去古人甚远。正因如此,他坦言“古人贵修辞,诚至言斯立。道善义以周,体物不相袭……质重人则存,浮杂岂容入。镂琢饰情貌,当非贤所急”(《修辞》)[7]530,并且指出“诗有可以学而至者,有不可以学而至者”,至于“意趣之冲淡,兴象之高超,神境之奇变,情韵之绵邈”[7]111一类的艺术审美形态,均需要诗人的情感浸润方可表现出来,是无法从古人身上学到的,如明代的何景明、李梦阳,学古虽至,却得“形合神异”[7]111之实;至于国朝的一些诗人,虽然意识到“明七子”的复古之弊,但是一如其《廌青诗集序》所谓的自“乾隆、嘉庆以来,多避熟就生以变其体,大约不岀苏、黄二公境中,究未能自开生面”[7]289,若钱载和翁方纲之流,又每以杜甫和苏轼为师法对象,虽“日伐其毛而洗其髓”,不过“实亦古人之游魄”“真气不存”[7]111。如果要深挖这种后果的根本原因,姚莹《廌青诗集序》以为即在于一味从格调、声律、辞采等形式上学习古人,而不能“抒轴性情”[7]289,缺少感情的真正投入,所以终了也就难以见出诗人的自我个性特点。这样的诗学见解同样在姚莹的创作中得到了体现,所以即便《清儒学案》,亦一以方东树称其诗所谓之“自抒所得,不苟求形貌之似”[17]相评骘。
心灵世界或者说情感的变化,与诗人的生活经历是息息相关的。姚莹明确表示诗歌创作必须有感而发。其《孔蘅浦诗序》认为古诗之所以可贵,那是因为“奏其始也,必有所感,感于情者深厚,然后托于辞者婉挚”[7]29,因有所感而情才真。同时,他在《后湘集自叙》中,以“天下之事”作为发论的背景,同时又形象地将诗比作“箫”,而将“感”喻化为“风”,称“夫诗者,亦人之箫也。是其作也,不可以无风”[7]22-23。在此尚有必要指明的是,姚莹所谓之“感”,实际又来自于诗人“若呜呜,若肃肃,时而泠然,时而飒然”的不同生活情状。因此,他强调诗歌创作固然与诗人的才气、学问等个性修养紧密相关,但又必须将这些内在要素和诗人的生活经历耦合关联起来,方可流传于久远。换言之,这也就是其《复杨君论诗文书》所谓的“要必有囊括古今之识,胞与民物之量,博通乎经史子集以深其理,遍览乎名山大川以尽其状,而一以浩然之气行之,然后可传于天下”[7]124。又如其《论诗绝句六十首》所云:
西昆体制尚钱刘,秾丽妆成一曲休。不分他年变枯率,翻教杜曲误名流。(其二十五)
淡语幽香得未曾,宛陵知己有庐陵。均看韵格工腴甚,莫作寒岩槁木僧。(其二十六)[7]468
称梅尧臣诗能于平淡质朴中见真挚,而“西昆派”诗人则以点缀升平、翻用典实为能事,寒山子之诗则每多枯槁乏味,究其原因莫过于饱含人生经历的内在真情的缺失。对于这些优劣之品评,姑且不论其正确与否,但实际都是着眼于有无现实生活的浸润和情感的蕴藉来展开论析的。
既然重视诗歌创作与创作主体生活历践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对中国古典诗学批评史上的“发愤著述”“不平不鸣”“穷而后工”说,姚莹自然是交口称誉的。例如,在《答张亨甫书》中,他提出了“不穷不奇,不奇不可以大而久”[7]132的诗学命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奇”与“工”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是又互为包含,而姚莹命题的谋划构建又是以周公、孔子、老子、庄子、屈原、贾谊、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等作为立论依据的,认为这些前世贤哲的诗文,之所以能够且“奇”、且“大”、且“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作者大都有过“困穷忧患”的人生经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如果诗人一旦失去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洗礼、烛照和铺垫,那么他的诗歌生命力也就会因此趋于式微,乃至悄然枯竭。如其《论诗绝句六十首》其八云:
任沈诗名未足殊,江郎才尽尚齐驱。车前收得雕龙奭,不愧骚坛一世趋。[7]468-469
江淹早年身历家国之痛,能于诗文中寄托身世之感;晚封醴陵侯,养尊处优,再也写不出前期那种血肉丰满的篇章。“江郎才尽”的故实在此确乎成为他引证“不穷不奇”论旨的典型例证。此外,他还专门提出了诗文贵“沉郁顿挫”[6]620的论旨,不过,同样是以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等举世瞩目的大作家为理论依据,指出他们的创作因具备了“沉郁顿挫”的特点故可不朽于世。而论其个中原委,则以为除与他们的学识、修养相关之外,同时又与他们“身历困穷险阻惊奇之境”同样有着内在的联系。由此可以看出,这一论说实际与史迁“发愤著述”、韩愈“不平不鸣”、欧阳修“穷而后工”等传统文学论题相呼应。从某种意义而言,强调创作与诗人生活历践的关系,强调“愈穷——愈奇——愈大——愈久”,实际也是姚莹诗歌重情理念的延伸、拓展和深化。
总的看来,一如姚莹《复管异之书》所谓“天下艰难,宜问天下之士”[7]234,这种关涉情感的艺术表现论旨的提出,大都关乎天下之事,恰恰又是在政治每见荒芜、民愤愈发深重以及外侮趋于频仍的嘉道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历史转关时期提出来,而并不是完全步趋照搬或者依偎迎合于传统,所以自有其更为深刻的内中意味。简单地讲,姚莹的这种诗学论旨不仅显示出其作为嘉道时的经世士人自身所具有的开阔的时代眼光和积极的社会担当意识,而且也为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乃至于桐城派诗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活力,与姚范、姚鼐等家族先辈以义理为重的诗学追求判然有别。当然,关于这一点,还有必要在后文作更进一步的论析。
三、创作主题论:道与艺合,经济天下
时至乾嘉两朝,与经学考据风靡朝野相应,性理之学趋于式微,政治每见荒芜,道德走向沦丧,这也就是段玉裁在《与陈恭甫书》中所讲的“愚谓今日之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表率之过也,故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18]。因信守“程朱”,崇尚道义本是桐城麻溪姚氏家族的家学精义。而有感于世道人心之日下,姚范便在《校上北齐书录序》中作出了诸如“文章关乎世运,学术系乎风俗人心”[19]之类的申明,着眼于“义理”谈诗文之法度;姚鼐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义理、词章、考据”三者相结合的论学宗旨,并将“义理”作为统摄“词章”和“考据”的中心,在《敦拙堂诗集序》中表达了追求“道与艺合”[16]49这样一个崇高的文学境界的意趣。实际上,姚鼐的学术思想和文学精神不仅为他的弟子如方东树、梅曾亮、管同、刘开等人所继承,也被其家族后裔文人所延续。作为拥有姚门弟子和姚氏后裔双重身份的姚莹,论诗衡文既不回避、排斥“义理、词章、考据”的统一,又在其间添入了新的成分,在姚鼐诗学思想传承过程中同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对姚鼐“道与艺合”的诗学主张,姚莹是完全认同的。其一,他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道”在诗歌创作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和引导作用,而且明确表示诗文只是载道的艺术,只有将道与艺有机结合起来,这样的诗文创作方算得上是真正的工和善。例如在《复杨君论诗文书》中,他指出:“诗文者,艺也,所以为之善者,道也。道与艺合,斯气盛矣。”[7]124在《黄香石诗序》中又称:“文章之大者,或发明道义、陈列事情,动关乎人心风俗之盛衰。”[7]112在《郑云麓诗序》中则称诗乃“人才学术之所见端,亦风俗盛衰之所由系……诗歌似非所先然,以持正人心、讽颂得失,实有切于陈告训诫之辞者”[7]114。俨然将“道义”和正气的弘扬当作诗文创作最为关键的题旨,或者说最为核心的内质。值得注意的是,透过这些论说,我们并不难看清家族先辈诗学于姚莹的映照,而其传承家学的深刻意识亦借此得以彰显。
其二,因重视诗的道义教化功用,所以姚莹也非常讲求诗人的道德修养。其《黄香石诗序》以为,要想诗歌创作“传于天下后世”,为后人所表彰、所传布,仅仅靠诗人自身“得于天”的“才”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忠义之气、仁孝之怀、坚贞之操、幽苦怨愤郁结而不可申之志”[7]113。与此同时,在对待诗文创作是否属于“古”之范畴这一实际问题时,姚莹所持守的最为重要的标准,便是他在《复陆次山论文书》中所谓的它是否具有“雅驯高洁、根柢深厚、关世道而不害人心者为之,可观可诵”的特点。也正是因由了这样的意识,对于那些“急求华言以悦世人好誉”[7]282-283的诗文,由于其中裹挟着太多的个人名利因子,即便在艺术上已经算得上足够优秀,也无法纳入到被他所肯定的范围之中。总体而言,我们不可否认姚莹的这些主张依然带有浓厚的封建君臣伦理意识,如其言说中“忠义之气”“仁孝之怀”都是这一意识的外在表征;但是他能将人才、学术、诗歌、风俗之盛衰等因子关联起来探讨,如在《黄香石诗序》中强调“夫人之一身有子臣友之责、天地民物之事”是发为举世而称诗文的前提条件,而不作孤立之论,这实际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不近凡俗的诗学追求。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在认同“道与艺合”的同时,姚莹又提出了经济天下这样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诗学主张。其《重刻山木居士集序》谓:“古人文章所重于天下者,一以明道,一以言事。”[7]288并以姚鼐“义理、词章、考据”三结合论旨为基础,在《与吴岳卿书》中指出:“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四者明贯谓之通儒。”[7]120综合起来看,“道”的内涵已显明晰,“事”在此则指向“天下之事”,也就是他一贯追求强调的“世务”;而“事”与“道”并举,更将“经济”“多闻”等因素纳入到为学术、为文词的题旨之中,已非常清晰地展示出其言关天下、忧国忧民的社会担当意识,如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述,那就是《黄香石诗序》中褒奖黄香石而说的“夫香石平生所自命虽不知较古人如何,要其讲求世务,隐然有人心世教之忧,不可谓非有心之士”[7]113。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姚莹既反对本朝以来后学规模迷信王士祯之“神韵”和沈德潜之“格律”“以诗言诗”(《黄香石诗序》)的做派,每每流于空疏,或徒于声调形式;相反,对儒家传统的“兴观群怨”诗学观却至为推崇。如,其《复吴子方书》直言“汉之苏李,魏之子建,晋之渊明,唐之李杜韩白,宋之欧苏黄陆”为何足以千古不朽,除了他们的才力学问之外,更因为他们怀有“忠孝之性”而能“无悖于兴观群怨之旨”[7]125。对于那些变风变雅、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诗歌,姚莹则表现出由衷的欣赏赞叹。他在《谣变并序》中声称自幼读诗即“喜言‘兴观群怨’大意,每至《古风》《式微》诸章,未尝不反复流涕;及汉以来乐府歌谣,辄低徊咏叹,以为古诗之存,独有此耳”[7]410。诗史上诸如屈原、杜甫、白居易、陆游、元好问、陈子龙等“讲求世务,隐然有人心世教之忧”的诗人更是成为他扬誉礼赞的对象。譬如,他在《论诗绝句六十首》中称晚唐李商隐“牙旗玉帐真忧国”[7]468,又称清代遗民诗人屈大均“分明哀怨楚湘累”[7]468,钦羡之情甚见明晰。与这一情况相反,对时下那些不关风雅道义宏旨而一以自我性情愉悦、个性张扬为旨归的诗人诗作则是痛下针砭,在《孔蘅浦诗序》中他指出:“近世虚憍之流,又以其豪艳獧薄、伤风败俗之辞,倡导后生,自比铁崖,然铁崖当日已有文妖之目,斯又下矣。”[7]29将“世道人心”与“经济天下”相提并论,彰显的正是一个留心世务诗人的本应具备的胸襟。
不可否认,这种道与艺合、经济天下的诗学见解虽不是姚莹的首创,但当它出现在风云骤变、歌哭无端的历史年代,则无疑具有了特殊的诗学意义。应该说姚莹的诗学观虽然本乎姚范、姚鼐等家族先辈,但他并未故步自封,而能立足时代现实予以拓展,由“道义”的宣扬深入到“世务”的省察,将诗以载道的理念明确落实到经世致用的深度,显示出更为强烈的现实性、针对性和批判性,相较其家族前辈的论旨,明显有了质的变换,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传统的发展。
四、姚莹诗学观之诗学价值
总的看来,受家学的影响,在诗学方面姚莹有其坚守传统的一面,在对待诗歌通变问题时,姚莹能折中而论,强调古今并重,唐宋兼采,转益多师。同时,他既强调诗歌必须表现真情,必须有感而发,又追求诗歌的道德教化功用,奉“道与艺合”为旨归,显示了较为浓烈的人文关怀。除此之外,姚莹又是一个心忧家国和胸怀天下的有识文士,而政教颓废、民怨载道、外辱频仍的乾嘉道咸时期的社会格局,又使他能于诗学的阐扬中凸现他的经世宏愿,他的诗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显示了柯劭忞《慎宜轩诗集序》所谓的“变风变雅”[20]的旨趣,个性之自觉意识与“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大夫情结熔于一炉,时代特色尤见鲜明,充满着激昂的风云气息。确切地讲,这样的表现与嘉道时期“言关天下与自作主宰的文学精神”[21]无疑是同步相应的,足以纳入到那个特定时代的最强音当中。
惟其如此,我们完全可以作如是观:姚莹的诗学观念正是在家族、传统以及时代的多重作用和多重互镜中展示出继承与新变的双重性质,内中已然折射出嘉道以降经世文士所特有的精神面相,或者说精神依归,现实观照意义是显在的。
还必须注意的是,如所周知,桐城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10]145,而姚鼐承桐城派诗学之绪论,蔚为桐城诗学大宗,姚莹则是嘉道时桐城派的重要作家,又是此间经世文士之代表,“虽亲炙惜抱,而亦能自出机杼,洞达世务,长于经济”。又一如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所谓“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10]146,乾嘉以降,桐城诗派渐趋佳境,已然成为晚清诗坛不可轻忽的一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大致可言,麻溪姚氏诗人足称清代桐城诗派的核心力量,在乾嘉至于晚清诗坛均占有一定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姚莹的诗学观所呈现出来的承变态势,无论于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诗学还是桐城派诗学,乃至于晚清诗学,其所具有的转关意义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凸显。质而言之,对姚莹诗学观念作进一步的探讨实有其必要,有着不可轻忽的诗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