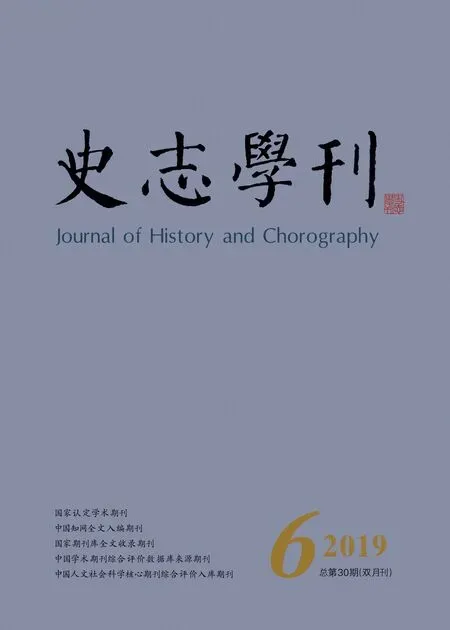共识与分歧:中国20世纪早期报刊的“独身主义讨论”
林晓萍 杨艺帆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000;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长春130000)
20世纪初期中国出现主张“独身主义”之风潮,在各大报刊上引发了围绕“独身主义”的奉行群体特征、产生原因、社会效应、是否应杜绝及杜绝措施等的诸多讨论。例如当时北京蔷薇社妇女周刊部落便刊登特别启事,言及蔷薇社妇女周刊部落于1925年1月28日(第八期),出《独身主义研究号》,邀请社外同志投稿,将予以微薄报酬[1]北京蔷薇社妇女周刊部落.本刊特别启事.妇女周刊,1925,(6).(P8)。可见当时独身议题在社会之热。而比起“独身主义”之风潮,近代“反独身主义”之潮似乎也尤为兴盛[2]此方面的研究可参考:杨艺帆,林晓萍.个人与社会:20世纪初反独身叙述何以可能.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目前关于近代独身研究大多为以探索“独身主义”风潮兴起原因为着眼点,注重描绘“独身主义”这一现象的具体表征,截取呈现报纸所谈及的关于“独身主义”出现原因,而有些研究则结合时代背景,进一步分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3]例如,雷若欣.近代西方废除独身制与中国提倡独身制的原因.妇女研究论丛,2002,(48);马方方.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代知识女性独身原因的再探讨.长白学刊,2008,(3);张国义.五四时期知识女性独身论试探.妇女研究论丛,2008,(2);吴志凌.中西视域中的五四独身叙事缘起及困境.兰州学刊,2015,(12)等.。然而,研究对象多是以“独身主义原因”与“独身群体”的特征等为核心的“独身主义问题”,未论及中国近代早期在报刊上出现的,关于“论争”这一现象本身的内在理路。本文通过整理20世纪早期报刊关于“独身”问题的讨论,拟以“论争”本身为研究对象,尝试梳理表面上“独身主义”与“反独身主义”的针锋相对,背后千头万绪的“分歧”与“共识”关系。下文将一一呈现、论述、并分析这一包裹在近代意识觉醒中的复杂现象。
一、“独身主义”讨论的背景及定义
目前笔者可以看到关于以“独身”为关键词的较早报刊是1907年的《独身税》与1908年的《杂俎:侏儒女子之独身》,前者主要是描绘了南美亚尔然丁共和国“课独身者以税”,为了增加人口数量对不同年龄层的单身者收取不同金额这一外国趣事[1]佚名.独身税.东洋,1907,(3).(P75);后者则介绍了印度有侏儒女子擅长跳舞及音乐。在妊娠时“因构造不完不能分娩”,于是医生用刨腹助产,顺利诞下一子,“皆生涯独身也”一事[2]佚名.杂俎:侏儒女子之独身.四川,1908,(1).(P4)。此时,社会对独身问题的理解,仅限于与“独身”这一现象而非当作一种“独身主义”。在描述“独身”现象时,也没有将自古以来存在的独身现象视为重要的近代社会问题,而仅将其视作异域趣闻加以介绍。然而进入1910年后,“独身”现象开始转化为“独身主义”问题,并引起以报刊为主要平台的、全社会范围的“独身主义问题”讨论[3]相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近年的美国社会之中。美国学者艾里克·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在《单身社会》一书中提到:贝拉·德保罗为了让人们重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单身日益增加这一现象,还创造了“单身主义”一词。这意味着单身作为一种一般社会现象,只有在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时,才会被“主义化”。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对“单身”“独身”与“单身主义”“独身主义”进行区分是有必要的。具体请参考(美)艾里克·克里南伯格.沈开喜译.单身社会.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P172)。
在分析“独身主义”问题之前,有必要对核心概念“独身主义”进行定义,并区分一下“独身”与“独身主义”之别。
首先,报纸虽然围绕“独身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但是在文章起始,详细介绍或者界定讨论对象的文章却比较少。而李宗武《独身问题之研究》是少数对“独身”加以定义的文章之一。李宗武认为:“‘独身’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是和一切家族、朋友、亲戚都断绝关系不通问闻,不相往来。”“狭义的是专指不结婚而言,其他如社交、事业、行动等仍和平常人一样。”[4]李宗武.独身问题之研究.妇女杂志(上海),1921,(第7卷第8期).(P1)同样的定义亦被枕流所接受,枕流也认为独身有两种,一种是广义的独身主义,“是和一切家族,朋友,亲戚,都绝断关系,不通问闻,不相往来”;一种是狭义的独身主义,“是专指不结婚而言;其他如社交,事业,行动等,仍和平常人一样”[5]枕流.独身主义的研讨(上).礼拜六,1933,(528).(P586)。
从上述的介绍可知,近代以来人们所理解的“独身”并非稀有之物,更非舶来之物,而是社会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但是,近代的“独身”理解比之旧时,有着自己的时代特点。比如孔襄我在《独身的我见》讨论独身定义问题时认为:独身(Celibacy)的界说,“只要不娶或不嫁,过单独生活的,都可以叫做‘独身’。普通社会都是实行一夫一妇制度(Monogamy),如果有奇特的男女不娶不嫁,终身过单独生活的,于是便特别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独身者’(Celibate)”[6]孔襄我.独身的我见.妇女杂志(上海),1922,(第8卷第10期).(P10)。接下来作者将独身分为两种类型,认为独身包括两种:“(1)未婚的男女,即立志不娶不嫁,终身营单独生活的。(2)既婚的男女,因配偶者半途死亡而营单独生活的。”[6]孔襄我.独身的我见.妇女杂志(上海),1922,(第8卷第10期).(P10)并且有意识的认识到,时人所讨论的主要是第一种现象。
其次,讨论独身问题时,主要的议论对象是因各种缘由而抱独身主义的青年“智识阶层”,而这一“智识阶层”中,女性更为热衷于奉行“独身主义”。虽然也有针对男性独身问题进行讨论文章,比如张若谷《独身汉自白》[7]张若谷.独身汉自白.千秋(上海1933),1933,(1).、黄粱《花花絮絮:由我爱我夫会到独身俱乐部》[8]黄粱.花花絮絮:由我爱我夫会到独身俱乐部.晨光(杭州),1933,(第2卷第6期).、佚名《结婚呢?还是抱独身主义呢?》[9]佚名.结婚呢?还是抱独身主义呢?中国青年(上海1923),1925,(第3卷第74期).(P374-375)等,但是社会对女性独身主义者,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女性独身主义者的关注更为炙热[1]比之近代日本对于独身主义的讨论便可知,中国的独身问题讨论中男性角色的相对边缘化:在日本,虽然讨论后期有川崎利太的《结婚读本》等书强调女性的社会使命以反对独身(详见川崎利太、『結婚読本』、佐藤新興生活館1936年版),但在小畴三郎在《结婚哲学》一书中,将独身主义称为“无妻主义”,以强调男性对独身生活的选择。(详见小疇三郎、『結婚哲学』昇文館1906年版、第91頁。)由此可知,不同的独身主义讨论者往往出于不同立场对男性或女性独身行为有着差异性认识,日本的独身主义问题作为东亚文化社会中的一个比较对象,也很值得深入研究。。都良便认为“现在国内一般新式女子,很多有标唱独身主义者。稍微受过教育的人更容易倾向这种主张”[2]都良.一部分女子的独身问题.礼拜六,1922,(188).(P32)。徐江左在《民国日报·妇女周报》上直接谴责到“在这个婚姻成为问题的时代中,有些想逃避这问题的人们,胡乱用了一刀两断的态度,标榜了什么独身主义;尤其是有些女学生”[3]徐江左.言论:独身主义底危险.民国日报·妇女周报,1924,(54).(P3),将矛头直指女学生。甚至出现以《为什么独身女子这样多》[4]东心.为什么独身女子这样多.女青年月刊,1929,(第8卷第10期).(P17-21)为题进行讨论的文章。
而且,除了对社会独身问题进行“全面”分析的文章之外,关于男性独身问题的文章多是男性自白自述,谈论自身愁闷或不得已独身之原因,而女性独身问题的叙述除了自我外,也常常作为讨论“客体”存在。女性在近代独身问题讨论中常常被放到社会中,被迫接受他人的审视。这种两性差异叙述,比如在胡宗瑗的《独身主义之研究》[5]胡宗瑗.社说:独身主义之研究.妇女杂志(上海),1919,(第5卷第2期).(P1-5)一文中便可以看到,文章强调女子独身之理由与男子相同,但有两种区别:“(一)避生产是也;(二)畏束缚是也。”作者认为“女子之天性,终弱于男子”,因此女子一旦结婚,难免渐渐事事依赖男子。而顾寅则深入分析女性奉行独身主义的话会对身体造成何种伤害[6]顾寅.女性独身生活之上的不合理(待续).十日旦报,1933,(37):10-11.女性独身生活之上的不合理(续).十日旦报,1933,(38):12-13.。承福章也从医学角度说明男女性交有利于女性身体健康,“据德医马意爱儿说,有些女子的子宫生来发育不全,所谓‘小儿子宫’的,结婚以后,自然会发育增大。又说,处女月经不潮或月经困难,以及特别发生于妙龄女子的贫血病,结婚以后都有自然痊愈的可能性。”[7]承福章.结婚后女性生理变化——抱独身主义的女性是违反自然且不合于生理的要求的.康健杂志(上海1933),1935,(第3卷第1期).(P17)这都说明近代独身问题不仅是一个独身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性别问题。
最后,还有必要区分一下“独身”与“独身主义”。君诤在《杂感:独身:卖淫》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认为“独身”与“卖淫”是一样的。两者皆是由于恶社会所导致,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应该“加以怜悯和被损害者的同情”[8]君诤.杂感:独身:卖淫.民国日报·妇女周报,1924,(43).(P7),但绝对不应该将其视为高洁,甚至将其奉为主义。认为将被迫的独身选择,变为独身主义的行为无异于提倡“卖淫主义”[8]君诤.杂感:独身:卖淫.民国日报·妇女周报,1924,(43).(P7)。这里作者认为,即使独身成为了近代社会现象,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独身”获得了“主义”的身份呢?而君诤的答复是:不是。在其眼里独身是一种被迫选择,并不能获得“主义”这一高尚的身份。这里也和近代以来,各种“主义”风行的社会背景和“主义”表述的理论性相关。严冷馨亦表示:“……我以为,独身不必看作什么主义,心理上生理上觉得需要而又得到相当伴侣就嫁,否则可以从缓,再候物色。”[9]严冷馨.读者信箱:自立与独身.生活(上海1925A),1930,(第5卷第37期).(P623-626)1919年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0]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1919-7-12.事实上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主义”之风的兴盛。因此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在运用“独身”或者“独身主义”时候要注意到其中的所包含的价值判断表述含义这一问题。葛敬洪也认为:“独身主义这个名词在我们中国本不成问题;因为除了那些在庵堂庙里敲木鱼的僧尼和道姑有的过独身生活之外,其他青年男女不因别的缘故,纯粹抱独身主义的人,实在是很少数。”“可是自五四运动澎湃以来,智识界受了一番很大的改变”[1]葛敬洪.论说:独身主义的批评(待续).青年友,1924,(第4卷第5期).(P9),独身问题渐渐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乃至于渐成一种“主义”,也即特定群体所秉持的某种价值观。
综上,可以简要地对20世纪早期的这场讨论风潮中的“独身”与“独身主义”含义进行界定。显然,此时人们所讨论的“独身主义”问题,实际上是包括了历史上的“独身”现象的,也即通俗意义上的“不婚”“单身”等,其中最具近代色彩的一面在于,“独身”不仅是一种普通的现象,而且成为“主义”,成为某种价值观,且立于舆论之中心的对象是以独身为“主义”的受过教育的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学生。“智识”与“性别”这类伴随着近代化而展开的因素开始通过“独身主义”这一社会性议题的讨论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2]正如上文所引用的时人的“独身”定义一般,其实大部分报刊作者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独身”与“独身主义”之别。这里可以简单举个例子,碧梧撰写《问题的探讨:献给独身的姐姐们》是写给年龄三十左右而奉行独身主义的“姐姐们”。但从作者介绍这些“姐姐们”奉行独身的原因来看,可知作者所探讨的独身问题不限于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女性未婚女性,而是包括“中年遗孀”“离婚妇女”等诸多情况(碧梧.问题的探讨:献给独身的姐姐们.女声(上海1932),1934,(第3卷第4期):18)在的此对“独身主义”与“独身”进行区分,意在表达这场讨论中的“近代”色彩。。
20世纪初期围绕“独身主义”问题,独身主义理念支持者与反对者进行了激烈地争论。经过史料爬梳整理,笔者发现20世纪初期出现的这场“独身主义讨论”,不仅是独身主义支持者与反对者理念的简单对立。围绕独身主义议题,独身主义支持者与反对者的逻辑理路其实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本文将全面介绍两者的关系,分析两者间的共识与分歧。
二、共识下的分歧:恋爱至上观与优生学话语
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在对农村单身现象进行研究时,十分强调城乡差异等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人们处境的影响[3]具体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姜志辉译.单身者舞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而20世纪早期的这场“独身主义讨论”也与当时中国的内外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20世纪早期的报纸内容来看,在独身主义问题的讨论中,独身主义者和反独身主义者皆积极地利用从西方舶来的“近代话语”为自己的理念服务。正如有考察五四时期女性独身问题的研究者便指出,五四时期的独身论延续了清末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关于家庭婚姻等方面的主张,并受到西方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是在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氛围中形成的对当时知识女性产生极大影响的一股思潮[4]张国义.五四时期知识女性独身论试探.妇女研究论丛,2008,(2).(P49)。而反独身也积极地利用社会进化理论,并强调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积极参与社会竞争的必要性。反独身主义者以文明开化这一进步目的抬高“社会”“国家”主体的重要性,要求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5]杨艺帆,林晓萍.个人与社会:20世纪初反独身叙述何以可能.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P60-61)。可见随着西方近代思想的流入,西方话语开始在中国智识阶层的讨论中成为一种权威象征。在此西潮之下,恋爱至上观与优生学话语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独身主义支持者与反对者围绕上述两个议题,展开角逐。
(一)恋爱成为“美好婚姻”的必备因素[6]关于近代“恋爱问题”研究还可以参考:海青.“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瞿骏.花落春仍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困境与新路.三联书店,2017;(美)周蕾.蔡青松译.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8;徐仲佳.性爱问题:1920年代中国小说的现代性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等著作.
一方面,对于近代青年来讲,“恋爱”往往是美好婚姻的必要前提。当时关于独身主义问题的文学作品,也往往强调“互生情愫”是人们由独身转向婚姻的必要条件[1]洪白萍.小说:独身主义.心潮,1923,(第1卷第1期).(P13-15)。另一方面,诸如李宗武等强调独身危害者,也常常赞同人应该追求理想伴侣之说[2]李宗武.独身的倾向与危险(未完).晨报副刊,1925-7-19.(P3)。“盖结婚以恋爱为基础此言也,已反复言之矣”“今既不满足自己之理想,则恋爱亦何从而发生;既无恋爱,则何能结婚;苟勉强结合之,势必陷于惨淡冷酷黑暗之生活中……”[2]李宗武.独身的倾向与危险(未完).晨报副刊,1925-7-19.(P3)也即,部分反独身者承认恋爱之于婚姻的重要性。
但有了恋爱是否一定能有利于进入婚姻或维持婚姻关系,则未尝如此。反观之,由于恋爱已经成为近代婚姻中的重要要素,使得无恋爱的婚姻变成了“无道德”婚姻,从而催生了部分独身者,因为未得到理想的恋爱而拒绝进入婚姻之中。例如,聿文在《评坛:恋爱与独身主义》中对“自由恋爱之说一起,所谓独身主义也跟着发生”的说法进行分析,指出“自从所谓一些新道德灌输到青年脑里,于是都以无恋爱的结婚为不道德”,故“因事业上经济上及其他种种事情不能寻得恋爱的对手的,便只好独身了”[3]聿文.评坛:恋爱与独身主义.妇女杂志(上海),1922,(第8卷第5期).(P13-14)。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独身者开始着重讨论何为“美好婚姻”。例如,瑟庐在《文明与独身》一文中也同意恋爱对于近代婚姻的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近代婚姻的合法性重要来源就是恋爱。作者在谈论怎么介绍独身现象时,除了谈及“只有使男女地位,完全平等,婚姻的离合,更形自由,使实际生活能够尽量提高,与他们的理想生活吻合”[4]瑟庐.文明与独身.妇女杂志(上海),1922,(第8卷第10期).(P5),才有可能减少这类独身一方面外,同时积极提倡恋爱。他引用日本社会主义者贺川丰彦的著述,其谈到“我们不可不用恋爱来建设真正的社会。没有恋爱,社会单位的家庭,永远不能出现,只可住在由生理的有机的社会本能所支配的族长主义社会罢了”[4]瑟庐.文明与独身.妇女杂志(上海),1922,(第8卷第10期).(P5-6)。这里体现了当时认知中的两种家庭,一种是以感情为基础,具有平等自由关系色彩的近代家庭;另外一种是以生理或权力为基础,具有男尊女卑的族长主义旧式家庭。在性关系上,作者认为应该把“恋爱作为性的关系的唯一标准”[4]瑟庐.文明与独身.妇女杂志(上海),1922,(第8卷第10期).(P6),为婚姻外性关系提供了合法性。瑟庐之外,葛敬洪面对如今独身现象,提出三条解决方案,其中第二条便是婚姻与恋爱,认为“经济既然独立了男女若没有恋爱所结的婚姻,还会不能免除不良的婚姻发生”[5]葛敬洪.论说:独身主义的批评(续)(附表).青年友,1924,(第4卷第6期).(P12-18)。
综上可知,近代个人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后,由对个人自由之重视到对个人情感之重视,使得男女是否两情相悦成为“美好婚姻”的重要衡量标准。无论是独身主义者或反独身者,均承认这一标准。而主张恋爱自由的主要抗争对象,则是传统“礼教”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男女结合模式。张惕须便在《读“配偶选择号”:现代婚姻的烦闷与独身潮》中传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部分人之所以选择独身,是对现存婚姻制度的不满,认为现有的中国社会导致他们青年不得已奉行独身,且认为这种情况无异于“剥夺了他们个人人生的幸福,更其是阻止全体人群的进化”[6]张惕须.读“配偶选择号”:现代婚姻的烦闷与独身潮.妇女杂志(上海),1924,(第10卷第1期).(P279)。
(二)兴起的优生学话语
如上“剥夺了他们个人人生的幸福,更其是阻止全体人群的进化”这一表述可知,独身与婚姻的讨论之中,不仅包含了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也包含了对社群发展的期许,也即“进化”的观念。寄生在这种进化论下的种族主义思想,其或以“种族学”为名,或以“优生学”为名,或以“遗传学”为名出现[1]这种优生学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更是影响了整个东亚。例如,日本的独身问题讨论伊始,黑岩泪香以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细胞病理学”等为社会与个人之原理,强调独身违背人性,乃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幸之事,且对于国家、社会的长远发展的不利。黑岩的文章中批判了社会万能论,认为个体不能期待社会能解决个人所有问题,个体的衰竭必将导致社会的衰竭。(黒岩涙香、「独身生活の理想を読みて 由分君に質す」、『精力主義』、隆文館1904年版、第153頁)。结合该时期之前文献,可将由分君的《独身生活的理想》(载于《万朝报》1902年7月11/12两日)与黑岩的回应视为日本近代对独身问题讨论的开端。由于资料有限,未能看到由分君的观点,但从黑岩的质疑来看,讨论初始的重心在于独身之于个人与社会之关系,并在此后的讨论中发展为“种族”的论述,如『結婚論』(湯朝観明、文禄堂1906年版)、『結婚読本』(川崎利太、佐藤新興生活館1936年版)等。事实上,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提出的社会进化论并不是一般我们所认知的受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这在人类学研究领域这是早已释明的。黑田信一郎指出生物进化论并未对社会进化论造成影响。认为是斯宾塞使得“进化”这个词得以广泛流行,并首先提出了“适者生存”。虽然理清“进化论”生成逻辑与实际历史境遇是十分重要的,可惜笔者能力与精力有限,尚未能对此逐一梳理。但是无论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化论之间的关系如何,可以确定的是两者确实进行了深入的互动,并且由其产生的文化进化论也对近代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详见黑田信一郎.文化进化论.收录于(日)绫部恒雄.周星等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6.)。
部分反独身主义者认为“照优生学说社会上的独身者愈多,社会的堕落愈不堪设想”[2]葛敬洪.论说:独身主义的批评(续)(附表).青年友,1924,(第4卷第6期).(P9),认为现在奉行独身主义者尽是那些“智识阶层中人”[2]葛敬洪.论说:独身主义的批评(续)(附表).青年友,1924,(第4卷第6期).(P9)。而按照优生学的角度,这些智识者竟然不为国家繁殖优质国民,反而奉行独身,让“一般愚昧无知的人造下孽种,贻害社会”[2]葛敬洪.论说:独身主义的批评(续)(附表).青年友,1924,(第4卷第6期).(P10)。在当今国际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纵犯罪作恶的人日见增加”而自己独身去,是无视“本种族退化”,威胁国家独立的表现[2]葛敬洪.论说:独身主义的批评(续)(附表).青年友,1924,(第4卷第6期).(P10)。而李宗武在《独身的倾向与危险(续)》中《独身之危险》一节便主要强调从遗传学上讲,“好种始得好果,好果之来,必自好种”,而现在独身者一般为智识阶级,智识阶级不生产,“势必逐渐递减;而无智识阶级,则依然竭力发挥其生殖本能”,从而导致“低能之男女,或更特别多产”[3]李宗武.独身的倾向与危险(续).晨报副刊,1925-7-21.。
面对此类指责,独身主义者则反向利用这一“种族”叙述,以家国危亡之际不应拘于个人情感,而应以社稷为先来予以反击。反独身者黎景云便在《论独身主义之当否》中针对独身主义者以家国危亡之名,来倡独身这一个人本位的行为进行批判。他指出,奉行独身者则往往认为“国家多事之秋,正匹夫有责之时,而热血男儿,须眉巾帼,往往因家室之牵,有怀莫遂,所谓英雄气短,内顾多忧者,蓋指此也,此其所以持独身主义者二也”[4]黎景云.论独身主义之当否.潭冈乡杂志,1930,(第11卷第2期).(P8)。对此进行反驳道:“然则此主义当耶否耶,曰,其自为谋也,未尝不善,若为家族谋,为国家谋,则吾未见其可也,当二十世纪以还,无一非弱肉强食,乡蛮械斗,强凌弱也,国际战争,强吞若也,苟此主义实行,人皆效之,斯种不期弱而自弱,不期灭而自灭,岂非自取败亡之道哉,吾之所以不能无疑者,蓋为此也。”[4]黎景云.论独身主义之当否.潭冈乡杂志,1930,(第11卷第2期).(P8)除了独身主义支持者与反对者争相以“救国”之名争夺行为之正当性之外,也可见到中国智识阶层通过借助舶来的生物进化理论,从强调种族优越性的角度对个人婚姻自由进行干涉。社会舆论在一方面试图将个人婚姻从传统礼教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却不认同将个人从“个人之必须的囚笼”的婚姻中拯救出来,甚至借助将种族学,将其与近代国家内忧外患的处境相结合,使得个人之自由再度臣服于社会。唯一不同的是,这个“社会”是奉行传统礼教之社会,还是所谓的“近代”之社会。
准确来说,不能将独身主义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对立置于“传统”与“近代”“个人”与“国家”的对立中,而是一种基于改造社会愿望的不同表达。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给独身主义者从个人主义的视角下大声疾呼“摆脱传统婚姻”“恋爱自由”的勇气,从集体主义出发的反独身主义者便将其转换为对“美好婚姻”的期许,进一步,“美好婚姻”又被转化为族群进步的动力源之一。而在近代强势的“国家”叙述之下,独身主义者本以“个人本位”之需求而倡恋爱自由,却因借助家国叙述而难以自圆其个人主义至上之说[1]实际上,究竟是个人主义借家国之名义以获取正当性,还是原本便从集体主义出发来获得独身的正当性,往往难以厘清。在日本,独身主义被视为是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主张。如小畴三郎在《结婚哲学》一书中提出,随着社会的文明开化,人口不断增加,终究会面临资源不够、供给缺乏的问题。加之社会组织不完善,通过优胜劣汰、生存竞争,世风日下,贫富差距日益变大,弱者越发脆弱。在这样不完善的社会中,独身主义是必要的。独身者不能适应社会趋势,并且较为理性的人会发现自己太过弱小,认识到不可能结婚,于是有了维持独身主义的倾向,这是社会必然的倾向。劳动力的减少,同时也能维持国家社会的善良的风俗,减少罪恶。所以独身主义是善与美。(详见小疇三郎、『結婚哲学』昇文館1906年版、第96-100頁。)。
由此可以总结如下,一方面,独身主义支持者与反对者对于恋爱的重要性以及追求民族的进化(进步)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另一方面,由于独身主义支持者和反对者对于个人优先还是社会优先问题有着根本分歧,导致双方对于应否独身这个具体问题相持不下。从双方引用近代话语情况来看,隐约可见“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也存在某种共谋关系,即近代语境中个人之自由与社会对个人之控制的矛盾。这一矛盾本身也是西方近代话语的内在矛盾。正是这一笼统被归为“西方理论”或者“近代理念”内部的复杂性,给予独身主义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在西方话语中“各取所需”的机会。
三、分歧之中的共识:“传统”的失势与“社会改造”的兴起
虽然独身主义支持者与反对者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认识产生了分歧,但是在反传统礼教与鼓励社会改造问题上,双方却在无形之中站在了一致战线上。并且,通过在报刊的激烈争论,间接将社会改造这一迫在眉睫的社会议题展现在民众面前,营造了社会改造的舆论氛围。接下来,本文将就“传统”与“社会改造”问题对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观点进行分析。
(一)失去合法性的“传统叙述”
正如李银河所说:“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个传统的‘三位一体’的标准模式,即性生活、家庭生活与生育三位一体的行为模式。”“所谓‘三位一体’首先是指缺一不可,即要有性生活,就要有家庭生活,还要有生育行为。不可以有无家庭生活的性生活,甚至不可以有无生育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其次,三位一体模式被中国文化行为规范视为正当,对它的任何偏离则被视为不正当或越轨的行为”,并指出这种模式“已成为理想的行为方式,或一种‘集体无意识’(荣格)”[2]李银河,冯小双.独身现象及其文化含义.中国社会科学,1991,(3).(P91)。这种三位一体模式说法可以说是一种对我们理解传统婚姻观念十分具有启示性的概括。
而在独身主义者的“独身与恋爱一样,都是人的自由,他人本无须加以可否的批评”[3]周建人.中国女子的觉醒与独身.妇女杂志(上海),1922,(第8卷第10期).(P7)的语境下,传统的“三位一体”标准婚姻观念迅速成为社会有识者的激烈批判对象。周建人呼吁人们警惕中国社会中,一些恐惧旧式家庭却因为经济压力,而必须走向婚姻的群体,主张改良家庭[3]周建人.中国女子的觉醒与独身.妇女杂志(上海),1922,(第8卷第10期).(P7-9)。枕流亦指出解决独身问题的必要性,并针对传统社会通过婚姻将个人束缚在家庭之中这一问题提出了三条解决方案:一是家庭制度的改革,改变旧式家长权威,主张建立夫妻互助,完全平等的家庭;二是允许自由离婚,免除部分因为害怕遭遇不幸婚姻却无法结束婚姻关系者;三是儿童公育,以减少人们的经济担忧[4]枕流.专著:独身主义的研讨(下).礼拜六,1933,(529).(P610)。
从枕流的叙述中可以发现,近代反传统家庭逻辑亦将生育与性别作为重要的斗争场地。李宗武亦认同儿童公育说[1]李宗武.独身问题之研究.妇女杂志(上海).1921,(第7卷第8期).(P6),而葛敬洪则更进一步讨论到婚姻与节育的问题,这与作者的优生学主张相契合,认为传统礼教盲目鼓励人多育子女并没有考虑到培育成本等诸多问题,主张贫穷夫妻节育[2]葛敬洪.论说:独身主义的批评(续)(附表).青年友,1924,(第4卷第6期).(P12-18)。可见,此时被视为传统礼教糟粕的诸多价值理念,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合法性,性、家庭生活、生育的关联也被切断。
在“传统”话语失效的时刻,即便是认为奉行“独身主义”乃是“躲入‘高尚理想’的玄宫”[3]亦琼.问题的探讨:独身主义的理想与现实.女声(上海1932),1935,(第3卷第7期).(P18)的反独身主义者,也紧张地与反对个人自由的传统礼教保持距离。亦琼在《问题的探讨:独身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结尾便强调:“但是最后还得说明,我们认为‘独身主义’一存在的‘不合理’,绝非基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思想’,也绝非如一般社会人士主张‘妇女结婚是唯一职业’来劝妇女结婚”,将“妇女看作附属品的结婚,须得我们妇女的努力与反对。”[3]亦琼.问题的探讨:独身主义的理想与现实.女声(上海1932),1935,(第3卷第7期).(P19)从此,“传统叙事”在社会中失去权威性,而取而代之的是以近代化为名的“西方话语”,而后者的权威身份并不仅仅由于其人文气质,更在于其作为近代强国们的主要价值这一层身份。正如黄金麟在研究中国近代之身体时所指出的:“过去那些用来规约个人身体的圣王之理,已经被一些世俗的生活规则和一些攸关群体生活的权利与义务观念所取代”[4]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P80)。
当然,必须要说明“传统叙事”并不是在刹那间失去了合法性,此时仍有为“传统”捍卫的声音存在。潘光旦将国外的基督教、佛教等与中国传统礼教相比较后,认为近年来青年攻击礼教其实并不完全有道理,一则传统礼教并没有像宗教一样鼓励独身,反而十分重视家庭与婚姻;二则传统礼教虽然阻碍浪漫的自由,但是“并没有阻碍了性的正当发展”;三则礼教虽然支持受贞守寡,但是为了挽近代末流之弊[5]潘光旦.优生副刊:独身的路(续完):现代婚姻讨论之二(未完).华年,1937,(第6卷第19期).(P372)。作者还将批评礼教的青年成为“冒失的”青年[5]潘光旦.优生副刊:独身的路(续完):现代婚姻讨论之二(未完).华年,1937,(第6卷第19期).(P372)。这一种声音的存在,也是需要注意的。
但是,20世纪早期,中国在这种“近代思维”下埋下了“歧视”传统文化的种子。沟口雄三便认为这种及“近代思维……就是把中国的近代看做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式的继承”[6](日)沟口雄三.孙军悦译.作为方法的中国.三联书店,2011.(P12)。沟口雄三这一观点很富有创见性,亦提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文化进化路线。
(二)独身者的处境与社会改造的需求
伴随着“传统”话语的失势,如何进行社会改造的命题被提上日程。如何改善独身者的处境,是独身主义者与反独身主义者的共同关怀。
当时有两则这样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人们对独身现象如何认知:
《海天话乙:独身女子之保险会》[7]佚名.海天话乙:独身女子之保险会.神州女报,1913,(2).(P149-150)与《1923号.青年独身的人可以不保人寿保险吗?》[8]佚名.1923号.青年独身的人可以不保人寿保险吗?华安,1920,(第2卷第4期).原文译自Nalaco,April 1923号.(P51-53)都以独身者,尤其是青年独身者作为保险推销对象。《1923号.青年独身的人可以不保人寿保险吗?》列举了七条青年独身者应该购买人寿保险理由,第七条认为人生对于意外损伤或疾病的侵袭是防不胜防的。青年独身的人,遇着这种侵袭,若非他早已有了自助的方法,还有何人来助他的医药费养病费呢[8]佚名.1923号.青年独身的人可以不保人寿保险吗?华安,1920,(第2卷第4期).原文译自Nalaco,April 1923号.(P51-53)?两者均体现社会对独身者自助自立一说持消极看法,也某种程度上反应了独身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境遇。
独身主义者罗元骏自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独身者所面临的困境。他强调奉行独身主义乃是一件普遍、自然之事。着重提出“近来男子不娶,女子不嫁,抱独身主义者,各国人数日众,在我国数亦不少”,而奉行独身主义的大学预科生罗元骏不过是“其一”[1]罗元骏.论著:我的独身主义.华北大学旬刊,1923,(4).(P8)。强调个人选择不同“人之嗜好,至不相侔”[1]罗元骏.论著:我的独身主义.华北大学旬刊,1923,(4).(P9)。但我们可以看到,罗元骏虽然对反对独身者的指责进行一一反驳,但最后的表述却是“然元骏固甚屏情思于脑外,永度畸人生活,得以清闲之岁月,自由之身体,浸淫于学术,尽瘁于社会,毋不幸而为儿女之情所纠缠”[1]罗元骏.论著:我的独身主义.华北大学旬刊,1923,(4).(P10)。从其表述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反驳,仍然只能将奉行独身行为称为“永度畸人生活”。作者的独身行为得到“慈母明达不欲干涉”[1]罗元骏.论著:我的独身主义.华北大学旬刊,1923,(4).(P9)之默许,并将人生追求与为社会奉献相联系,也无法在社会中获得完全的合法性,只能以“畸人”自认。一方面,可见此时的“独身主义”虽然已经成为社会话题,但奉行“独身主义”并没有获得社会合法性。另一方面,独身者的自嘲中也投射出了社会亟待改造的实情——无论独身是自主选择,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何改变独身者经济上、健康上所处的不利处境?
正如上文所谈及的,近代报刊中的反独身主义者其实与独身主义者一样反对专制,反对吃人礼教。潘文柔在介绍“妇女独身会”时便强调参加独身会的成员,或因为丈夫品行不佳、经济困难;或丈夫喜新厌旧,为丈夫所弃;或难忍专制家庭[2]潘文柔.妇女独身会.礼拜六,1921,(130).(P17-24)。《读者园地:读“为什么独身女子这样多”以后》则认为至于夫妇双方牺牲的地方,若说女子的牺牲比较得多,这句话也许是真的。但这不能谴责男子的不是,一大半须归罪于社会制度的不良[3]吴罕庸.读者园地:读“为什么独身女子这样多”以后.女青年月刊,1930,(第9卷第2期).(P66-67)。可见,此时变革社会是独身主义者与反独身主义者的共同目的,而这种变革社会的思想也是导向社会革命的契机之一。
《女子独身生活的研究》认为守独身,怨社会制度不良、怕发生悲剧苦痛,避去个人发展的妨碍,显示女子没有勇气、积极的奋斗力和改造力。希望教育家、社会学家就这个现象,劝导感化之[4]小江.女子独身生活的研究.妇女杂志(上海),1926,(第12卷第11期).(P28)。《专著:独身主义的研讨(下)》提倡“家庭制度的改革,改变旧式家长权威”[5]枕流.专著:独身主义的研讨(下).礼拜六,1933,(529).(P610)。《读“独身主义的内幕”后一点小意见》作者号召姐妹“打倒独身主义的虚伪”“别被虚荣所陶醉,或无意思时情丝所缠绕,别做男子‘玩物’!”[6]静雅.读“独身主义的内幕”后一点小意见.皇后,1934,(5).(P25)认为所谓“独身主义”只不过是男子的诡计。而《问题的探讨:献给独身的姐姐们》甚至建议摆脱独身主义这一消极抵抗方式,号召大家革命。认为“社会所以要改造,要革命,无非是求它更合理,更能增进人们的幸福,所以鼓励姐姐们结婚,亦是即所以鼓励姐姐们以改造独身生活的勇气,来改造社会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呢!”[7]碧梧.问题的探讨:献给独身的姐姐们.女声(上海1932),1934,(第3卷第4期).(P19)当然独身主义者也不落其后,在《谈话:独身主义的我观》高唱在这“茫茫的世界里”“这个金钱势力支配着的世界里”“在这暗无天日的社会里”,青年因难寻一理想伴侣,才不得已选择独身主义。所谓独身主义绝不是禁欲主义,而“实是渴望女性到了极点才生出来的主义”!或有人会提议既然如此,青年们“把现今的社会制度打倒”,而不是去空谈主义,但作者认为,“革命的功程尚在开端,消极的独身主义正是积极的社会革命的引子啊。”[8]曹钧,石薛.谈话:独身主义的我观.民国日报·觉悟,1925-9-3.
从上述讨论中可知,近代“独身主义讨论”或者说“独身主义争论”中支持者与反对者存在着复杂的分歧与共识。虽然独身主义支持者没有彻底实现“个人主义”,但支持者和反对者却在争论热潮中,尤其是探索解决独身问题的过程中,共同提出了社会改造或者社会革命观点。虽然从报刊上我们无法详细衡量当时报纸上的社会改造呼吁,对社会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但是至少可以得出近代知识阶层在“讨论”中,借助西方个人主义、进化论等观点,在“无意识”中营造社会改造的舆论氛围。进入30年代后,国家局势日益紧张,在救亡图存的思潮下,“独身”与否这一具体问题的讨论日渐清冷,这一讨论所埋下的“个人”解放之思路却延伸到现代中国的建设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