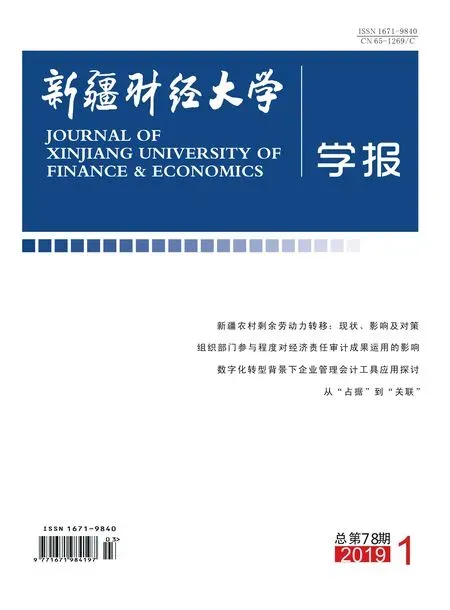从“占据”到“关联”
——城市空间图景的演绎与进化
张 莉
(新疆财经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830012)
城市最初的样貌如何?以今天的城市构造与生活节奏已难以想象旧时的城市。城市初建之时,空间概念已相伴而生,旧的街市巷道、古城的真实空间如何演变为今天的高楼林立、虚实交叠?人们感知城市,获取城市空间为自身知识并进而视其为自己的“地方”,这期间经过了怎样的变化?在城市空间的演变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和技术介于其中?人与城市的关系在技术介入后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些问题似乎很难联系起来,但笔者认为,讨论人与城市的关系,必须要将问题放置于事物持续发展的脉络里,在特定的语境和框架内,才能看到这些问题的参照与联系。本文试图描绘城市空间演变过程,并在这样一个演变的脉络里,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与回答。
一、城市空间演变的媒介技术逻辑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是被当作使用工具的动物而认识的,这种对人的定义从某种程度上割裂了人与技术的关系。在现象学家看来,技术并非单纯的工具,而是生活方式,是世界构成的主要方式。刘易斯·芒福德认为,技术起源于完整的人与环境每一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技术是人的实现方式。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现代性的突出现象,起着支配与提示的作用,是真理的开显方式。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对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产生,我们的任何一个延伸,都要引进一种新尺度。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人对技术的认识过程,其实反映着人对自身的认识,也反映着人与技术、人与环境之间某种相伴共生的联结。这种技术逻辑可以解释城市空间的演变,其本身有一种内在动力,这一演变与媒介技术发展恰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媒介既呈现着实体空间也创造着新的空间,拓宽并丰富了人对空间的感知。
(一)身体占据的空间与古代城市的出现
人的身体是最直接的媒介,人与外部环境交换信息,获取对周边环境的掌控,首先是通过身体。
婴儿在爬行和翻身的过程中可以感知距离、认识空间,因此人类对空间的最初感知来自于身体。诸如要步行多远到达河边,爬上多高的树能看到多远的地方……人类在不断的训练中拓展着空间概念。但空间本身却是不断变化的,因而段义孚说人类智能主要表现在对空间变化的适应上[注]详见段义孚著、王志标译《空间与地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所以,人们对空间最初也最本质的理解是,空间是一种秩序,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秩序。
那么,作为秩序的空间是如何被感知、被确立的呢?刘易斯·芒福德在谈到古代城市的起源与本质时曾指出,古代城市大多始于一些神圣的地点,因其能令散布于各地的人回到这些地点进行祭典仪式,但不论在什么地方,“城市的兴起都伴随着大力突破乡村的封闭和自给自足”[注]详见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和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和105页。。由此可见,古代城市的诞生有着鲜明的空间拓展的特征,即对封闭的乡村的突破,这种突破包括地域与空间。古代的社区或乡村过于封闭稳定,不易接纳新鲜事物及其他生活方式,城市由此成为解决此类问题的最好方式。城市空间的拓展性,决定了它可以对各类人物给予接纳与包容,陌生人、流浪汉、商人、逃难者、奴隶等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因而城市的“容器”功能成为了其最主要的功能。芒福德因此说,城市是“贮藏库、保管者、积攒者”,并且“这种为着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社区边界的浓缩作用和贮存作用,便是城市发挥的独特功能之一,一个城市的级别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功能发挥的程度”[注]详见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和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和105页。。作为“容器”的城市首先具有物理空间的可创造性和伸展性,一个实在的空间确立着身体居住的安全感与稳定感。此时,与广阔零落的乡村地区相对,城市的建筑、街道、市场、标记指示,都提供了这种空间的参照与边界,使空间感觉成为人的身体适应与感知,成为具体的身体规范与熟悉程度,最初的客观秩序也由此建立。
那么,人又是如何获得空间能力,即把对空间的识别能力变为一种知识呢?或许我们天然会以为这是依赖于人的视觉能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验表明,人的空间能力是在一系列的学习活动中发展出来的触觉动觉模式。人们去往一个目的地时,总是由对近处的方向和判断等经验逐步扩展到远处。比如我们走到一个地标时,根据最近的经验就会知道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走,目标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地标或标识所串联起来的。所以,当一个陌生人进入一个城市时,总是会以他居住的地点为中心,通常以公共交通等出行方式为主,慢慢将熟悉的地域扩大。当我们对空间完全熟悉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属于我们的地方。在此,城市为人们提供了发展空间能力的场所。
人们感觉到的空间并非空洞无物,而是充满了各种约定俗成的意义,也就是物理空间中被人感知到的等级、权力、象征等意义,但对其如何划分与呈现,实则归因于人的建构。“由人与世界抽象出的更简单的思想,即身体与空间,前者不仅占据了后者,而且通过意义控制和规范着它,身体是活生生的身体,而空间是由人类建构的。”[注]详见段义孚著、王志标译《空间与地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空间中的客观参照点、地标和主要位置,要符合人类身体的意图,人在其所掌控的空间中才能感觉到轻松自如。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尤其以北京的都城为代表,皇帝所居住的位置,以及坐北朝南的传统方向,都是对中心的追求。“从午门进入皇城后,人们会因里面的地面和建筑都沿南北轴线方向修建而感到震撼……本来,紫禁城代表的是皇帝居所,表现的是天体最上方的北极星,即皇帝位于由170多颗星辰组成的星座(紫微垣)中央的情景。”[注]详见斯波义信著、布和译《中国都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因为天坛是祭天的地方,因此其外形呈圆筒形(天圆)。坛基也呈圆形,每部分都是9级台阶,是共计3屋(天地人)的设计形式。3层基坛各层的栏杆数都是360根,代表了一年的360天及360度的圆。这些设计都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天子是代表天来统治包括首都在内的天下所有的土地、人民以及广阔的宇宙。”[注]详见斯波义信著、布和译《中国都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这种人为的主观秩序,规定了人的社会性的生活状态,它与客观秩序一道,用 “占据”空间的方式将人纳入到城市空间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大众媒介的传播与工业化城市空间的形成
“城市空间”这一概念诞生于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西方现代城市化运动。这一不同于乡村和古代城邦的新型生存空间,体现了信息流动打破空间障碍的质变,从而培育出对空间的兴趣和关注[注]详见殷晓蓉著《传播学视野下的“城市空间”》,原载于《复旦学报》 2013年第5期,第136~142页。。
新闻纸出现后,人们开始意识到传播与城市空间有着内在而密切的关系。首先是因传播的信息是在空间传递与发布的;其次是大众媒介及其传播过程本身在创造着超越物质空间之外的某种“媒介空间”,这种看不见却能感知到的空间,构建起人们精神世界的独立领地,在讨论公共事务以及对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认同中开始发挥作用。因此,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认为,在现代传播媒介产生对社会的联结作用之前,传统社会是依靠村落、行业、家庭这些基本单位进行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的;而在现代城市空间中,却是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媒介,使“非常相像的个体”组成集群,并使之“不必谋面或认识就形成了紧密的联系”[注]详见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特里.N.克拉克编、何道宽译《传播与社会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39 页。。哈贝马斯也认为因为大众媒介的传播,构筑出了一个可以讨论公共议题的“公共空间”。他认为的公共空间由咖啡馆、出版机构、大学、图书馆等构成,而在咖啡馆中举办的沙龙尤以阅读报纸为中心,这个空间呈现的便是“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核心的公共交往”[注]详见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9 世纪中叶后,城市人了解外在空间和世界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必要的生活资料,并且成为了城市空间的重要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造纸技术带来的广泛影响,“造纸工业靠近市区,因为在这里,市场需要纸,造纸用的碎布也货源充足、价格低廉。造纸工业的发展使写作从修道院向都市转移。接着,印刷业促进了都市化的趋势”[注]详见哈罗德·英尼斯著、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02 页。。20 世纪初,面向大众的杂志有了各种各样的类型,杂志虽然晚于报纸出现,但却集中显现了城市空间的各种要素,而以“专门化”为特征的“城市杂志”,其内容和发行主要限于城市区域,“侧重于提供城市生活、生活方式、娱乐选择以及社区需求和问题等方面的信息”[注]详见萨梅尔·约翰逊和帕特里夏·普里杰特尔著、王海主译《杂志产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8 页。。在对这些城市杂志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印刷媒体正是通过阅读的方式展开对空间限制的“突破”和“征服”,但这种“突破”仍然是缓慢的“有限突破”,直到电报的发明,现代电子通讯技术真正打破了空间障碍而实现“瞬间传播”,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并最终成为“确定世界远距离传播界限的标志”[注]详见阿芒·马特拉著、陈卫星译《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2 页。。
在此,大众媒介不仅超越了作为首要功能的跨越空间传播信息的任务,也因其技术本身开辟了传播空间的研究,实现了对城市空间认识的突破。与身体占有空间以及以象征性划分空间的等级不同,大众媒介所建构的传播空间通过符号的方式进行空间生产,城市空间是构成“象征符号”的主要公共领域。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街头、电视、刊物上大量出现的图片、广告、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作品,商场橱窗中的装饰物,商业区内餐厅与咖啡馆的装修风格等,这些符号背后的能指,占据着场所,也表征着场所,并借助符号生产着空间。空间符号因此具有了替代性和生产性。替代性就是当“‘真正的’刺激物在实物形态上并不在场时产生复杂行为的能力”,而生产性是指“掌控符号的人有能力在有限的符号元素基础上生产无数个表征”[注]详见詹姆斯·W.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 年版,第15页。。因此,符号的空间是象征的,象征空间的特点在于同构性,在于一旦两个事物之间建立起同构关系,那么不管它们之间在时空上、在分类上悬殊多大,都将被看成是本质相同的。
(三)电子媒介与流动的空间
齐格蒙特·鲍曼在对现代性的研究中涉及流动的空间,她引用塞纳特对城市的定义,认为城市是“一个陌生人可以相遇的聚居地”,从这个角度出发,城市就是人们持续经过的场所。城市中拥有很多公共空间,如广场、机场、旅馆等,但这只是人们礼貌相遇又漠然分开的地点,而大型的购物天堂,也只是福柯意义上的小船,是一个漂移的空间,孤独而自我封闭。与此同时,城市里还存在着许多人们未曾到达或感觉已经消失了的地方,但实际上它们却是在地图上存在着的“虚幻空间”。人们分享并使用着空间,公共空间似乎是固定的,但却在人的来来去去中被赋予了流动的本质。鲍曼说,因为交通工具的速度越来越快,时间被压缩的时候,意味着能够到达更远的空间征服更大的空间,而沉重的、越大越好的现代性因此转向轻盈流动的现代性。“空间被控制首先来自于时间被驾驭,并使它内在的推动力变得无效,简言之,即是时间的一致性和协同性。”流动的空间,来自于“每一时间单位日益增长的吞没空间的能力”[注]详见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0~181页。。在流动的空间中,时间与空间具有了同构性。
鲍曼的流动的空间是在现代性研究层次上的解释。从媒介角度来看,流动的空间也指电子媒介所建构的某种“虚拟空间”。互联网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信息传播与共享方式的变革,也意味着全新社会结构的出现。“在新技术范式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一种由电子通信技术组成的结构——具有发展动力的社会网络。当然,它是技术,但它也是网络化社会结构和蕴含在网络化逻辑中的具体关系组合。”[注]详见《信息论、网络和网络社会: 理论蓝图》,原载于曼纽尔·卡斯特主编、周凯译《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 46页。卡斯特指出,这种社会网络的结构是网络逻辑和具体关系的组合,因而网络社会是围绕信息、技术、资本等的流动而被建构起来的,网络社会催生了新的空间逻辑,卡斯特将其称为“流动空间”。“具有完整界定的社会、文化、实质环境和功能特征的实质性的地方,成为流动空间里的节点和中枢。”[注]详见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54~389页。
在这个流动空间里,节点成为了关键词和新动力,打破了整体与中心的限制,所有进入网络和网络社会的机构、企业、个人都是网状构造中的组成部分,各节点的运动促成了网络社会的流动,在广阔的互联网领域内,大量节点不断地涌入,不断地生产与消费,又在不断地消失,像永不停止的星系运动。它们共享着某一时间里的平行空间,又随即消解着这一空间;它们即时创造着某种互动通联的空间,又随时终结着这一空间。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恰恰成为一种常态性与稳定性,因而其所形成的空间结构既非均质也并不对等,亦无法呈现明显可描述的规律性,并且永远处于流动之中。“这样一个流动的空间是一个混合物的世界”[注]详见约翰·厄里著、李冠福译《全球复杂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79~80页。,在这样的流动空间里,其特征是“流动空间没有明晰的构造,没有明确的中心与边缘之分,而是节点和边际随时变化着的、半透明的拓扑空间”[注]详见冯雷著《理解空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页。。
那么流动空间中的非均质性又是如何发生的呢?约翰·厄里认为是通过节点对信息的处理来实现的。“各节点通过更多地吸收信息并更有效地处理这些信息来增强自己在网络中的地位;而如果它们的表现不佳,其他关节点则会把它们的任务接过……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要节点并不是网络中心点,而是网络中起转换作用的关节点,这些‘转换者’遵从网络运行逻辑,而不是命令逻辑。”[注]详见约翰·厄里著、李冠福译《全球复杂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2 页。流动空间能揭示电子媒介时代城市空间的本质特征:首先,流动是城市空间运动的动力,如果停止流动,那么这个城市空间就不会存在;其次,局部流动的缓与急也解释了全球性空间为何是不平衡的。
(四)“融合媒介”与关联空间
流动的空间和关联空间都与电子媒介技术紧密相关,前者是从电子媒介特征的角度出发来认识空间,而后者则是从空间角度出发来认识的结果。
什么是关联空间?麦奎尔在《媒体城市》中指出,关联空间是指社会关系的地平线在其间变得大幅开放的当代状况,当媒体变得越来越有机动性、可测量性和互动性,媒体城市中社会经验的新模式就具有了关联空间的特征。高度开放带来的是构筑跨越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关系的新自由,这种新自由无法被拒绝,具有自反性和现代性[注]详见Couldry Nick 和Anna McCarthy,Media Space: Place 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这里对关联性的理解是指一种非结构不可预测的可能性,指某两种或多种元素的接触碰撞所触发的新形态、新表征和新感知等。这种不同元素的接触类似广义上的“融合媒介”概念。在今天的城市中,城市居民拓展出了更大的身体感知空间——地下、楼群丛、商业区、广场、站台等,在身体的移动中与各种形态的空间发生着穿越、聚合、离散,实现着德·塞托式的散步,包括着德·塞托式的散步,又颠覆着德·塞托式的散步。关联空间还表现为个体或群体在空间元素的添加和空间创造想象上的自由发挥与特立独行,如主题电影院、咖啡馆,提供餐饮、网络、观影及交流区的书店,古代建筑群里的现代商业街,北京798艺术中心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艺术空间呈现,等等。“城市不再受制于高高在上的专家,而是变成了可以随意重置的个人愿望的动态网络化表达。从空间的角度来看,范围从房间到城市的老式建筑结构将失去其稳定的轮廓。”[注]详见斯科特·麦奎尔著、邵文实译《媒体城市》,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2和139页。基于此,“电子媒体的意义在于其自身的空间属性以及由此开拓、重塑出更多空间的可能性”[注]详见斯科特·麦奎尔著、邵文实译《媒体城市》,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2和139页。。“而空间的意义在于承载于实践或事件中又带有空间性所具备的一种‘潜能’,存在于人们‘行动的时刻和呈现的选择’当中”[注]详见Jiménez Alberto Corsín,On Space as a Capacity。。
电子媒体本身也在不断地开拓相关的空间,人们在互联网平台上观看到的直播,以及很多网络游戏中设置的由真人扮演的角色,在进入到游戏空间中时,已很难分辨网络空间与真实空间的边界。在这种情形下,关联空间拥有了超空间的特征,超空间的显著特征是空间的非连续性和事物的虚拟性,“我们习惯于认为具有时空统一性的物体或事件才是真实的,但是在超空间中,由于时间与空间分离了,所以物体或事件不具有时空统一性,因此我们便觉得它们是不真实的,或者说是虚拟的”[注]详见冯雷著《理解空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电子媒体使时间不断被加速而空间不断被压缩,人们认识的空间形态和划分空间形态的标准已经开始改变,建构、参与及分配空间的要素越来越复杂多元。超空间阻断了人对空间的感知与定位,一旦置身其中,人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来组织空间体系。“人的身体和他的周遭环境之间的惊人断裂,可以视为一种比喻、一种象征,它意味着我们当前思维能力是无所作为的。”[注]详见詹明信著、陈清侨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97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周遭世界无从掌握。按照唐·伊德的解释,在诠释学关系中,世界首先被转化为文本,而文本是可读的。因而借助诠释学关系,“我们仿佛能够将我们自己置身于任何可能的不在场的情形中理解”[注]详见唐·伊德著、韩连庆译《技术与生活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7和72页。。
然而诠释学的文本关系也许需要重新认识,关联空间的另一种形态可能更值得我们思考,即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人的身体可以和机器相结合并将拓展出更广阔的关联空间,“它是另一种秩序,是我们语言的附加物,是数字的辅助语言,是洞察、剖析和揭示事物的秘密、隐含的意图和未用的能力的方式”[注]详见Emmanuel Mournier,Be Not Afraid。。
约翰·厄里也描绘了这种人与电子产品的混生状态,“这些居住机器是迷你型的、私人的、移动的,而且还依赖‘数字能’。……这些居住机器渴望拥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小型化以及轻便化,并且想展示自己与人的身体之间的相互交织的关联性。……这些居住机器使得‘人们’能够更迅速地在空间中移动,或者停泊在某一个地方”[注]详见约翰·厄里著、李冠福译《全球复杂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58~159页。。在这样的机器秩序图景中,机器成为人的一部分,人也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人与机器互为功能互为对象,机器与人的共存使人进化为一种“新物种”,虚拟与现实的概念被消融,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进化为一种新的空间形态,被分离的时间与空间再次交织缠绕,人存在于时空交织的网络中。
二、空间演变中人与城市的关系
人创造了城市空间,还是城市空间塑造了人?在城市空间演变的脉络里,我们可以梳理出人与城市的伴生关系,城市最初的形成,为拓展人的空间感知能力、为人与空间知识的互动进而将其转化为人的空间智能提供了物理基础。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空间的丰富性不断地满足着技术发展的需求,技术促进了城市空间的演变以及人们对其所进行的探索与研究。媒介技术的发展,在人对空间认知的转变以及城市空间研究的丰富性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城市空间的形态并非依照先后顺序相继发生,如流动的空间和关联空间可能是重叠的,其区别在于内在的深层形态。电子媒介不仅提高了空间形态的发展速度,也加速了空间形态的进化与裂变,拓展了空间研究的深广领域与无限可能,但城市空间不管如何演变,仍然有一些可以探讨的基本意义。
(一)技术以中介的方式参与空间的演变
唐·伊德在探讨人与技术、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具身”关系的概念。所谓“具身”关系是指“借助技术把实践具身化,这最终是一种与世界的生存关系”[注]详见唐·伊德著、韩连庆译《技术与生活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7和72页。。比如,不借助任何工具时,我们的视线能够看到的距离,我们的身体能够感知到的方向,前后左右等都因具体物体的参照而限定,所以月亮、山脉、远方等距离或者方向都是稳定的体验。但人身体的空间感觉是可以借助“人工物”得以拓展的,比如望远镜发明后,通过望远镜,月亮被拉近到我们眼前,借助工具改变了之前我们对月亮的距离感知。也就是说,空间含义的每一层面都发生了改变。哥伦布的航海是借助把地图与航海图上的位置读成我们身体感知的位置得以实现的;同理,现在的导航技术不仅有平面的方向、距离等,也有俯瞰式的,是多维立体的,使我们对上下左右复杂叠加的空间可以获得错落感知,有了比之前更深刻的体验。
因此,通过“具身”的方式,媒介或媒介技术作为一种中介在城市空间的演变中发挥着作用。在这里对于中介的理解至少应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媒介介质本身,信息得以传递,媒介处于观众与世界之间,实现着事件发生时超地域的“共同观看、倾听与感受”。二是媒介与人的共在关系,使得中介物具有象征性,由于物体介入了人的交流过程,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可能通过物体的中介来进行,“于是身体的直接交流转变为依赖于中介的间接交流,这样,充当中介物的物体便在功能性之外具有了象征性”[注]详见冯雷著《理解空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页。。中介是一种能够把彼此相连的方式与可能,通过中介的方式,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城市空间演变的来源。
(二)关系生产是城市空间的核心
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中提醒我们重视空间中的关系生产,社会空间“不仅仅是一个事物、一种产品,相反它不但包容了生产出来的事物,也包纳了事物的共时态的、并存不悖的、有序或无序的相互关系”[注]详见陆扬著《空间何以生产》,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198~210页。。媒介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城市构成的基本要素,造就了全新的空间研究的领域与版图,正是基于此种情况,米切尔才说现代城市是一座“比特之城”,这样的城市“较少依赖物质积累,而更多地依赖信息的流动;较少依赖地理上的集中,而更多地依赖于电子互联;较少依赖扩大稀缺资源的消费,而更多地依赖智能管理”[注]详见威廉·J·米切尔著、吴启迪等译《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约翰·厄里也说电子媒介发展了诸多网络构造了诸多“关系”,同时也只有“关系”才是根本[注]详见约翰·厄里著、李冠福译《全球复杂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空间构成因素的变化,信息流动、电子互联、智能管理等,将人与电子的关系纳入城市空间的领域与层次中,那么如何理解新型电子媒介与人构造出的关系呢?或许克劳斯·布鲁恩·延森的思路会带来更多启发。延森将人的身体、大众媒介及数字元技术视为三重维度的媒介,他认为以数字化的元技术为逻辑,三重维度的媒介交融在一起,会整合为全新一代的媒介[注]详见克劳斯·布鲁恩·延森著、刘君译《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媒介既不能与实在割裂,也并非受到实在的推动而发展,它们的交往实践构成我们感知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方式,亦成为我们拥有‘世界’的基础。”[注]详见黄旦和李暄著《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原载于《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第13~20页。人与媒介、人与世界这种多元交织、相融一体的关系,恰恰是当下城市空间的属性,也是空间研究的核心意义。
(三)人是城市空间研究的落脚点
空间的物质形态在发生变化,但单纯的物理空间本身并不构成城市与国家,西美尔认为“社会性”才是社会空间的真正意义,城市的凝聚力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而非物理的和规模的,“单纯的地理要素不能构成国家和城市,各种精神力量和心理力量才可以建成它们”[注]详见盖奥尔格·西美尔著、林荣远译《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这种认识与芒福德不谋而合,其认为城市是为使人类的生活更美好而存在,这也是城市存在的根本意义,因此城市不是一种实体存在,而是一种文化存在。
在城市发展史上,近现代大城市的发展崛起与大工业生产和工业化进程紧密相关,大工业生产方式所要求的空间集中促成了现代工业城市的诞生与发展。在这种逻辑关系下,“工业城市巨大的物质生产力,表征着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向着摆脱人的依赖的新的依赖状态的迈进”[注]详见孙江著《“空间生产”——从马克思到当代》,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30页。,但同时,工业化生产方式下的空间延伸又造成了空间的新的断裂与差异,“它冷酷而又坚决地把原本黏合成一个整体的空间撕裂开来,把一部分人变为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成乡村动物,用其固有的、与生俱来的交往理性销蚀农业文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造就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注]详见崔波著《刍议城市传播研究的空间进路》,原载于《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2~7页。。不可否认,类似工业化的现象既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也是城市存在的问题本身,甚至在今天的有些时候,光怪陆离的城市空间景象与美丽乡愁的乡村想象都是被作为对立面来看待的,城市空间的这种断裂性提醒我们,空间研究并不是脱离人的纯粹与虚拟的空间研究,就如芒福德所言,应该是新型的文化现象的研究。
那么,作为文化现象的人工智能及电子媒介技术带来的全新的空间状态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新媒介带来的不仅是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范围,还是标准、规则、感知比率等的全新塑造[注]详见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全新的空间感提供着新的尺度,激发出人与城市相处依存的新形态,现代城市聚焦了大量的人群,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物质产品,有序而规则运行的系统化生活,将每一个个体附着在电子关联的大网上,城市居民的距离与彼此的依赖感前所未有地更紧密、更强烈,但人与人心理上的感觉也必然更亲近、更热情了吗?城市依然是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吗?从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的发展是合规律的发展,总体趋势符合人性并有利于人性发展,城市的空间生产是人与城市和谐共生的要义,也因此,只有建立在此种认同基础之上展开的空间研究,才能在城市如何使人更美好的问题探索中有扎实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