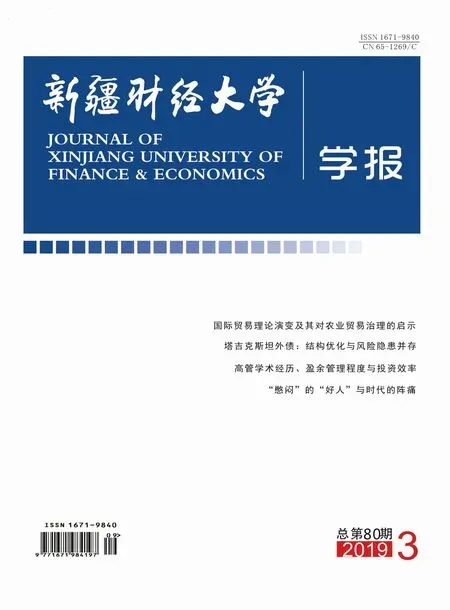李劼人“大河小说”对话的五种类型
秦俊明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对话是李劼人“大河小说”①“大河小说”原是法国文学术语的日译用名,意即史诗文学,现指李劼人创作的连续性多部长篇历史小说,即指《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详见徐廼翔著《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小说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中极具个人风格的艺术形式,为了深入认识李劼人“大河小说”中的对话②日常生活中的对话一般是有问有答,有“来言”也有“去语”,但若只有其中一种我们也可认为其属于对话的范畴。因为对话的核心在于反映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交流和关系(形而上地说是反映主体间的交流和关系),而沉默也是一种交流、一种回答。小说作品的人物对话也一样,“来言”“去语”只要有其中之一我们便认为其属于对话。另外,为了阐释文本对话的丰富性,我们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这种基于作品文本的交流关系也考虑进来并作为一种对话进行研究。,确立对话的基本单位并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的策略是值得尝试的,而把“场”作为对话研究的基本单位也是合适的。因为“场”既结合了戏剧学中对场次的区分,也考虑了语用学语境理论中对场合的阐释。理论上讲,“一场对话”是对话起止和延续的时间、对话的场景(地点)、对话的参与者(说话人、听话人)、对话的主题(话题)、对话的方式、对话的目的(意图)等因素的统一;而实际上,只要做到场景、话题、对话参与者这三个基本要素的某种统一就可以了。在故事表述的一段延续的时间里,只要对话参与者不变,场景或者话题中的任何一个发生改变或是两者同时发生改变,都不会使一场对话变成另一场对话,从而保持了对话自身的稳定性。进一步来说,“一场对话”包括了场景、话题、人物这三个基本要素的统一和变化的四种情况。
在作品里一场正在进行的对话中,当场景、话题、对话参与者这三个基本要素相统一时,就是标准的一场对话(可称为“标准型对话”)。但在这三个要素中某些要素出现了变动而“一场对话”依然成立又有三种情况,即对话参与者和话题不变而场景改变(可称为“话题支配型对话”)、场景和对话参与者不变而话题改变(可称为“场景支配型对话”)以及对话参与者不变而话题和场景改变(可称为“人物支配型对话”)。除前述四种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在“大河小说”中,作者—叙述者在场的痕迹非常明显且在作品的表现中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此类对话可称为“作者—叙述者主导型对话”。
上述五种情况分别对应了五种类型的对话。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李劼人“大河小说”中所有的对话区分为五种类型——作者—叙述者主导型对话、标准型对话、场景支配型对话、人物支配型对话、话题支配型对话,以便展开进一步的观察研究①这里就话题进行一些必要的说明。因为在对文本对话进行归类时可以发现,确定一个话题是较为困难的。一场交流大量信息的对话中,可能对话围绕一个话题展开,也可能围绕好几个话题展开,这些话题可能有层级关联但也可能毫无关联。早在2006年,吉林大学王巍的硕士论文《会话话题分析——话题在会话结构中的运行规则考察》就已表明了话题在语用学界的争议性,而且该研究认为话题是“将会话参与者所说的相关的话语有规则地组织起来的动态的网状结构”,这就更加大了确定一个话题的难度。因此只能小心避开对话题的繁琐考究,在必须提及和运用它时权作这样的处理:在运用人物、场景、话题三个基本要素对不同场次的对话进行分类时,将涉及的话题要素分缩小化、扩大化两种情况来考虑。在认定标准型对话时,将话题作缩小化考虑,即将这三个基本要素统一的情况压缩到最小化,乃至压缩到一句对话的程度,这至少能保证这样的一句话是标准型对话;在认定话题支配型对话时,则将话题作扩大化考虑,用来统摄那些人物不变而场景改变的对话,这样可以保持这场对话的完整性;在认定场景支配型对话时,则无需对话题进行清晰区分。需要强调的是,将话题分缩小化和扩大化两种情况的考虑是基于实际操作的需要,与之前界定的区分几类对话并不冲突。。
一、“大河小说”中的作者—叙述者主导型对话
从作者—作品—读者的意义上讲,可以把李劼人“大河小说”看作是作者—叙述者对读者的单方面对话。这种作者—叙述者主导型对话存在的前提就是作者—叙述者形象的存在。“大河小说”作品文本中的作者—叙述者是一个贯穿三部曲的“我”。第一部曲《死水微澜》序幕中出现了自称是“我”的人物,而序幕之后则是“我”讲述的故事,但自此叙述者不再指称自己。根据序幕内容来看,这个“我”讲述的故事明确囊括了整个《死水微澜》的故事内容,虽然“我”不在第二、三部曲《暴风雨前》和《大波》中出场,但根据李劼人创作三部曲的意图来看,《暴风雨前》和《大波》应该与《死水微澜》是同一个叙述者。“我”是作者虚构的一个存在于正文故事外围的人物,他既是同叙述者也是异叙述者。在第一部曲序幕中,“我”是讲述自己故事的同叙述者,而在之后的第二、三部曲中,那个叙述者“我”已是一个讲述他人故事的异叙述者了,而且不再指称自己。在整个“大河小说”中,叙述者充当的都是一位自然而然的叙述者,而非自我意识的叙述者。虽然大部分时间他是一位较为客观的叙述者,但有时也会变成一个具有干预性的叙述者。作家以独有的生命体验、浓重的情感温度、鲜明的个性气质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文本,使叙述带有极强的感受性,这也产生了刘勇所指出的“在冷峻客观的描写之中奔腾着炽热的情感潜流”②详见刘勇著《思考:嵌在“每个微小的词里”——略谈李劼人三部曲的语言艺术》,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第203~208页。的效果。
如果将作品中直接引语之外的部分称为旁白,那么可以说这种旁白才是作者—叙述者主导型对话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大河小说”中的旁白可谓非常丰富。作者—叙述者时而陶醉于成都以及周边地方的名物与风俗,时而贴近人物甚至与人物视角重合来讲述故事,他有时站在某一个具体人物的立场,有时又站在一群人物的立场,还时不时地跳出来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论。
在介绍地方风俗名物时,作者—叙述者仿佛是一位对地情极其熟稔的民俗学家一般,用精练隽永的语言慢条斯理地将道路、城镇、街道、公馆、公园、店铺等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除了对这些有历史价值的静物进行传神描绘之外,最能显示“大河小说”的作者—叙述者深厚艺术功底的就是他用生动凝练的语言讲述城镇的那种鲜活的扑面而来的整体的生活氛围。比如在谈到赶集时他谈道:“而千数的赶场男女,则如群山中的野壑之水样,千百道由四面八方的田塍上,野径上,大路上,灌注到这条长约里许,宽不及丈的长江似的镇街上来。你们尽可想象到齐场时,是如何的挤!……赶场是货物的流动,钱的流动,人的流动,同时也是声音的流动”①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这是多么鲜活的社会生活场景,原本是原生态的嘈杂与紊乱的场景,到作者—叙述者这里便充满了美的律动了。
作品在讲述大背景时,作者—叙述者一般使用非聚焦的方式多角度多方面地反映要表现的对象,而当作者—叙述者在认真讲述具体的人物或事情时,则会转而使用不定内聚焦的方式,将视角贴近人物甚至与人物视角重合。比如在讲述邓幺姑偷听父母和媒人的对话时讲道:“她很着急,很想问个明白,但是房里那么多人,怎好出口?打算下一次再来问,老无机会,也老不好意思。”②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这就生动贴切地揭示了少女邓幺姑羞涩难禁的心理。这种不定内聚焦的方式可以比较自由地在不同人物之间转换观察和讲述的立场。同时,在对事件和人物进行评论时,作者—叙述者也得以得心应手地插入简短精到的评论。比如在讲述邓幺姑触到了从韩二奶奶那里传来的成都的繁华梦之后,作者—叙述者突然评论道:“其实,她应该怨恨韩二奶奶才对的。如其不遇见韩二奶奶,她心上何至于有成都这个幻影,又何至于知道成都大户人家的妇女生活之可钦羡,又何至于使她有生活的比较,更何至于使她渐渐看不起当前的环境,而心心念念想跳到较好的环境中去,既无机会实现,而又不甘恬淡,便渐渐生出了种种不安来?……”③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5页。这种富于同情心、充满正义感的对话声音往往成为故事的点睛之笔,而这个话语既是针对故事,同时又是指向读者的,这就以整个生活样态启发着读者的生存之思。
当然,最能够凸显作者—叙述者主导型对话其对话性一面的就是在讲述中直接指称和召唤读者,用“你”来提醒读者注意此刻两人的对话关系。比如在谈到成都北道的猪时,李劼人写道:“它的肉,比任何地方的猪肉都要来得嫩些、香些、脆些,假如你将它白煮到刚好,片成薄片,少蘸一点白酱油,放入口中细嚼,你就察得出它带有一种胡桃仁的滋味,因此,你才懂得成都的白片肉何以是独步。”④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其实,在向读者谈论这一类话题时,横亘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是一种生活样式,是与故事不直接相关的话题。若将“大河小说”当成故事来看,就会显得这部分内容累赘多余,而若将“大河小说”当成一场作者—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来看,这些内容就好理解了。这种旁白,在整个“大河小说”中实际上承担了再现整个恢宏的社会历史变革大背景的任务,而具体的故事和人物是这个背景氛围下的交响曲,具体的人物对话声音则是一个个音符,它们的绝妙组合让“大河小说”之曲动人心魄。
二、“大河小说”中的标准型对话
标准型对话是指在一个对话单位中,人物、场景、话题这三个基本要素相统一。由于话题这个因素的不确定性,因而我们只能将其作缩小化考量,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标准型对话的形态,因此所能得到的比较确定的标准型对话也都是最小化的标准型对话。这种标准型对话最常见的形式是由一句“来言”和一句“去语”构成的一轮对话,或者“来言”“去语”二者仅有其一的一句对话。从“大河小说”中的标准型对话中可以看出体量最小的对话单位所具有的基本特质,虽然灵活性和凝练性特征为所有对话所共有,但这种特质在标准型对话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品文本中对话的插入会造成读者逻辑理解的中断并转而触发其形象思维的开启,从而使得整个“大河小说”具备一种日常生活叙事的风格。在“大河小说”中,相对于其他几种类型的对话,标准型对话的体量最小、分布最琐细、数量也最少。它的前后被陈述语或者其他类型的对话包裹着,其是作者在行文中突然插入的一种对话。它具有行文中的突然性和灵活性、形式上的不容反驳性以及表现空间上的拓展性等特征。
其一,“大河小说”的标准型对话具有行文中的突然性和灵活性。它一般是作者在讲述背景、故事和人物的过程中根据表述需要突然插入的一句人物对话语言。比如在《死水微澜》的序幕中,叙述者在描述了蔡大嫂的外貌之后突然插入一句标准型对话,“大姐问她,这样打扮是从哪里学来的。她摇着头笑道:‘大小姐,告诉了你,你要笑的。……是去年冬月,同金娃子的这个爹爹,到教堂里做外国冬至节时,看见一个洋婆子是这样打扮的。……你说还好看吗?’”①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这样的一句话就表明了蔡大嫂谦和、爱美的性格以及她的教民妻子的身份,也透露了她再婚的经历,同时从中也能看到外国文化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虽然只一句直接引语,但这句话会唤起读者对包括人物、场景、话题等所有因素在内的整个对话场域的想象、体验和感受,从而组合成碎片化的生活场景,这完全是由这句话在被听到的一闪念的瞬间所触发的。由此可以看出标准型对话独到的表现力,它是具体的、浓缩的、丰富的生活的结晶。
再如在讲到叶文婉的母亲打算将她婚配给郝又三时的一句标准型对话,“她的母亲早就有意思将她说给郝又三的,她哥哥嫂嫂没有话说,只她三弟说了一句:‘人家说的,调换亲,不吉利;彼此都该慎重一点的好。’其实,是郝又三不大愿意……”②详见李劼人著《暴风雨前》,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她三弟”说的那句话完全可以不引,而转述为“只她三弟不同意”,但作者没有作这样的处理,他尽可能地将故事的情节还原为对话,哪怕只是一句标准型对话,也足以引出一闪念的生活碎片,造成逻辑理解的中断并转而触发形象思维的开启。
其二,“大河小说”的标准型对话一般还因其只有说没有答的形式而具有形式上的不容反驳性。这种有说无答的情况有时是故事所表现的生活情境中的实际情景,有时是作者对答话一方对话的省略造成的。
第一种情况体现出了一种话语权下的压抑意味。比如在《死水微澜》中讲到从成都嫁到乡下的韩二奶奶思念城市生活却不被周围人理解时的情况,“虽有妯娌姐妹,总不甚说得来;有时一说到成都,还要被她们带笑地讥讽说:‘成都有啥子好?连乡坝里一根草,都是值钱的!烧柴哩,好像烧檀香!我们也走过一些公馆,看得见簸箕大个天,没要把人闷死!成都人啥子都不会,只会做假!’于是,例证就来了。二奶奶一张口如何辩得赢多少口,只好不辩”③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在这种尖酸的反对声中,对话另一方韩二奶奶的声音就被压抑下去了。如果说这里作者还只是直接表现了对话一方在另一方的压抑下失声的情况,那么到了沉默的蔡傻子那里,作者就表现了对话一方在整个周边社会的压抑下失声的情况,这也是通过标准型对话来实现的。
第二种情况意味着作者对顺畅交流情况的省略表现,表明了说话者的诉求得到另一方的理解和默许,达成了一种共识。比如学堂先生准备斥退伍安生,吴金延来找郝又三求情的情景,“大先生,这事要请你做主,千祈向监督说个情,从轻发落。这娃儿是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家境不好,读书一切都是我在帮忙。娃儿本来烦点,只求监督交跟我,我会好好管他的。学堂里不好打人,我领他回去,教他妈打他。就是他的妈,也会感激你大先生的。”①详见李劼人著《暴风雨前》,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虽然郝又三没有答话,但接下来叙述者就讲到他实施帮忙的行动了,实际上这是直接以行动作为回答,缺席的对白语言让读者对人物的心理活动产生意味丰富的想象。“大河小说”的标准型对话中这两种单方面对话的表现创造出了丰富的意蕴空间。
其三,“大河小说”的标准型对话还具有表现空间上的拓展性。这种拓展性主要表现为对话所具备的较强的拓展故事人物的能力。通观“大河小说”作品可以发现,故事中大部分非主要人物往往是通过标准型对话关联起来的,甚至一些只在作品对话中出现一两次的人物也出现在这种标准型对话中。比如《死水微澜》中韩二奶奶的妯娌姐妹,《暴风雨前》给郝香云看病的大夫、郝又三学堂的监学、体育教习、运动会学生,《大波》中的傅华封等人。“大河小说”作为社会历史小说,其中大量存在的社会中各个阶层、三教九流的人物是对作品文化含量极大的充实,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作品才能有层次地容纳如此众多鲜活的人物(出场人物265人,提及姓名但未出场的人物133人,合计近400人)②详见李旦初著《李劼人评传简编》,原载于《李劼人研究》第284页。。
三、“大河小说”中的场景支配型对话
“大河小说”中的绝大部分对话都是场景支配型对话。场景支配型对话是对特定场景中各色人物对话的表现,这种对话能产生丰富的话题,可以对当下的人物、事物进行充分讨论,对生活发出感慨,甚至在构建社会关系等方面也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表现。李劼人特别重视把对话放在特定的空间场景中,这是保证对话艺术真实性的必要条件。“大河小说”中的场景支配型对话主要包括家庭场景、茶馆场景、学堂场景、市井街头场景、会议场景等五种主要场景支配下的对话。基于不同的场景形成不同的人物关系,故而讨论的话题也不一样,其描绘的就是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活画面,从而反映出特定时代日常生活的典型面貌。
“大河小说”中的大部分对话都是发生在家庭场景中,话题也都是日常生活的话题,如婚丧嫁娶、婚外恋情、谋事做官、社会新闻、生活琐事,等等,李劼人把笔力聚焦在那个发生大变动时代下的一个个家庭,写出了社会各阶层的关联和变动。随着三部曲的进展,从最初发生剧烈变动的社会底层民众袍哥和教民的冲突,扩展到处于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的演变,以及社会中上层官僚之间复杂的利益冲突,最后发展成一场牵涉社会各阶层的全民社会大变动。为了更好地通过对话来传递社会信息,作者将笔触伸向了茶馆、学堂、市井街头这些公共场所,到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高潮时期,对话更是延伸到了政治会议场所。这些社会变动的信息经口口相传,形成了一条条信息传播链,进入每一个家庭后引起热烈的讨论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社会的剧烈变化在各个场景支配的对话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值得注意的是,对话的中心依然是在一个个家庭里,所有从外部传来的消息最后都会在家庭中被充分讨论和发酵,最终演变成全民运动。这种日常家庭对话场景支配的叙事策略使作品具有了坚实的生活真实性和丰富性。
比如《死水微澜》中的对话主要围绕在家庭和公共场景中展开,如“我”的家庭(地主绅士)、邓幺姑的家庭(农民)、韩二奶奶的家庭(农民)、兴顺号杂货店(小市民家庭经营)、顾天成的家庭(乡下粮户)、曾师母的家庭(教民)、顾辉堂的家庭(城里粮户)、郝公馆家庭(半官半绅),除了这些重要家庭场景之外还有一个客栈、一个茶馆和一个烟馆。兴顺号杂货店既是蔡大嫂的家庭场景,也是罗歪嘴的聚会场景,因此这个场景中的对话主要呈现的就是袍哥界视野下的社会景况,蔡大嫂和罗歪嘴之间的爱情将这些丰富的对话声音聚集到了这个场景中。作为延伸的线索,顾天成的家庭受到了罗歪嘴的打击,恰好因邻居的关系,虽受到了曾师母的支持,却又受到顾辉堂家庭的反对,但是最终洋教得势,顾天成娶到了蔡大嫂。全书正是通过生动精彩的场景支配型对话以及不同人物的活动和冲突将所有事件呈现了出来,最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故事。在这一系列故事发生的过程中,场景支配型对话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这也正是李劼人对话艺术中闪光的唯物主义因素和现实主义因素。
《暴风雨前》从郝公馆家庭场景拉开了序幕,家里下人纷纷谈论着红灯教发展的情况,家庭里的主子开始了对维新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反抗洋人的斗争和镇压人民的冲突从这里的对话中讲述出来,新旧思想的冲突也从这个场景的对话中显示出来。自郝又三进文明合行社、进学堂开始,这些场景的对话中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想的声音以及很多调和的言论,反映了那个新也新不得、旧也旧不得的时代。但是随着郝又三在学堂中认识了伍安生,拉皮条的吴金延便开始把他带向了这个暗娼家庭。这个底层家庭中充满了粗俗的语言,暴露着人性的自私,在对话中充斥着彼此间的口角冲突。留学回来干革命的尤铁民为躲避抓捕而躲进了郝公馆家庭,并在这里和郝香云上演了一场革命英雄的世俗恋爱故事,他还在饭桌上豪气地说出了“拿破仑自有他的约瑟芬!”①详见李劼人著《暴风雨前》,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这样意味丰富的话。郝又三参加运动会经历了警察和学生间的冲突事件,在对运动会这种大型场景下的对话进行描写时,李劼人用速写的笔法快速抓取了这个宏大场景中不同人物的对话和对事情的反应,总督、教育总长、官员、参赛队员、学生、教习、观众、警察等众多人物的对话都充满了现场感和画面感。
在《大波》中,作者灵活地将视角在家庭场景、茶馆场景、学堂场景、市井街头场景、会议场景中来回转换,全方位地展现保路事件发酵成全民社会运动的整个过程。为了更好更流畅地衔接这些场景,作者—叙述者主导型对话也相应地增多了。中学堂学生楚子材和半官半绅的表叔这一对人物设定直接关联了中学堂和黄公馆家庭两个场景,秉着“情史结合”的风格,也为了加强楚子材和黄家的关联,作者还给楚子材安排了和黄太太偷情的关系。在市民方面,作者安排了伞铺掌柜傅隆盛家庭的出场,他是联系会议中心和市井街头两个场景的关键。虽然落职管带吴凤梧是有家庭的,但在整部书中都没有出现在他的家庭场景中的对话,他作为一个特别活跃的人物经常出现在各个场景中,积极参与新的社会关系的构建。在这部书中,极具特色的就是对黄澜生家庭在大变动中慌乱的家庭对话和对会议场景对话的表现。“地皮风”频繁被煽起,黄澜生家庭中充满戏剧性的家庭对话真实地反映了那种可怖氛围下市民的紧张心理。对会议场景的表现,有一个从旁观到深入内里的过程。书中第一次写到会议是楚子材带着吴凤梧去围观铁路局的保路同志会的发起,他们以观众的旁观视角听到了会议的号召性内容。但后来的会议渐渐暴露出上层官僚内在的实质性矛盾,而这种实质性矛盾的不可调和渐渐让社会局势失控。会议频繁地召开与“地皮风”不时地被煽起,这是由内而外地表现矛盾的波动。会议是矛盾的中心,而“地皮风”正是会议没有解决好矛盾所造成的市民恐慌。《大波》从家庭场景、茶馆场景、学堂场景、市井街头场景、会议场景等方面全方位地展现了矛盾高潮时期成都社会的混乱状态,而生动的场景支配型对话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四、“大河小说”中的人物支配型对话
人物支配型对话的特点是聚焦对话中参与对话的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话题和场景都发生变化而人物保持不变。在“大河小说”中,人物支配型对话既不像标准型对话那样碎片化,也不像场景支配型对话那样受制于场景,而是以转换于不同场景间的人物为焦点,能够较为连贯地表现人物的对话活动。同时,它可以深刻表现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并将各个分离的空间场景连贯起来,从而形成更贴近生活实际的艺术世界的有机整体,同时也能随着场景的变化而拓展新的话题。
在“大河小说”中,人物支配型对话所属的情节能够非常清晰地反映出故事的进展和主要脉络。因为人物支配型对话是故事人物在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而“大河小说”又是一部专注于描写社会变化和走向的小说。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是由人的社会活动来推动和反映的,因而这些参与社会活动的人物的对话就成了反映甚至推动社会进展与变化的关节点。以上这些情节主要发生在两类空间场景中:一类是公共空间场景,如客栈、街道、商场集市、茶楼、会场、学堂等;另一类是家庭场景,如邓大爷家、蔡傻子家、郝又三家、伍大嫂家、赵尔丰总督府、黄澜生家、傅隆盛家等。人物不停地往返于公共空间场景和家庭场景之间,又最终回到家庭场景中来讲述和讨论社会动态。故事中很多人物都是与特定的场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人物走出自己所属的场景而在公共空间中与其他人物发生联系,他们的活动和对话便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恰恰是社会变动最明显和最直接的征兆。
在人物支配型对话中对对话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和人性有着深刻表现。比如在刘三金色诱顾天成情节的人物支配型对话中,就生动展现了刘三金的狡猾和顾天成的好色与愚笨,在连续两个篇幅的讲述中,刘三金接连魅惑顾天成,使其在赌场上分心,直到最后一天输了个精光,而此时刘三金便撕破脸皮、翻脸不认人。第一天刘三金的话是,“要是真心爱她,明天再商量,她可以跟他走的”①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第二天她说的是:“你今天输了,我咋个还好意思要你的东西!”②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但三天以后则找借口说:“算了罢!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③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而顾天成只是笨嘴拙舌地理亏说不清。从对话中顾天成的被动地位可以看出其愚笨,同时凸显了对话另一方刘三金的狡猾。
在罗歪嘴买鱼给蔡大嫂定情的一段人物支配型对话中,作者通过描写两人不伦之恋的欢愉深刻表现了其不拘礼法的奇特性情。罗歪嘴提着鱼来兴顺号杂货店送给蔡大嫂并在交流中表示,“从今以后,我有啥子,全拿来孝敬你一个人”④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接下来罗歪嘴、蔡大嫂、蔡傻子在饭桌上谈到了家室问题,罗歪嘴借赞蔡傻子“讨了这么一个好老婆”⑤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来夸蔡大嫂,而蔡大嫂则夸罗歪嘴“你到底是个男子汉,有出息的人!”⑥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他们在这个话题上越聊越深入,直到蔡大嫂说:“那你当真爱一个人,不是就永远不离开了?”⑦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这二人终于通过对话达成了情人关系。不过在二人中间还夹了一个蔡傻子,因此两人在语言表现上难免有点遮遮掩掩,但也正因为这样,对话的技巧和表现才如此醒目地凸显出来。这样的人物支配型对话在对人性的深度刻画以及建构新的人物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人物支配型对话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理解场域,它具有理解、生产意义。在这里,没有难以理解的人,也没有难以理解的人物关系,作品中主要人物之间的冲突和结合的对话过程在人物支配型对话中交待得明白透彻,就算有理解的空白区,那也将会在与其他对话的撞击中意渐明朗。
五、“大河小说”中的话题支配型对话
话题支配型对话是指那些人物和话题不变而场景改变的对话。虽然对话题的把握难以精准,但聊天中话题出现根本性的转向却是较易感觉到的①这里使用扩大化的话题概念,对话题不作精细的区分。。“大河小说”中的话题支配型对话,一般不仅跨越了不同的场景,而且也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其是作者基于自己的阅历对生活进行深度观察后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凝练的生活样态,是极具生活经验与生活哲理的生存洞见,具有意味深长的品味空间。不同于人物支配型对话,话题支配型对话专注于特定的话题,是所有立场各异、性格各异的人物的不同意见汇集的表现。总体来看,“大河小说”中的话题支配型对话在《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中分布较多,而在《大波》中分布较少。这些话题支配型对话大致有三种表现:一是表现故事人物的奇特性格和奇异的生存状态;二是揭示世俗生活苍白的一面,把富于象征与想象的生活事件、生活仪式、生活俗套最苍白的一面用直白的话语说破;三是对故事中人物、事件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
首先,“大河小说”中的话题支配性对话在表现故事人物的奇特性格和奇异的生存状态方面,往往是在短短的一场对话中呈现出人物在复杂环境中的生存困境,而这种人物的奇特性格和奇异的生存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这种复杂环境下生存困境的对抗、宣泄或者妥协。比如在《死水微澜》中,罗歪嘴自己对家庭的态度和对保护表弟婚姻的态度的那一场话题支配型对话就表现了袍哥奇特的性格特点。罗歪嘴自己认为“家就是枷!枷一套上颈项,你就休想摆脱”②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但对表弟的婚姻,他又很仗义地加以维护。这种亦邪亦侠的性情跟他不寻常的袍哥身份的生存状态有关,袍哥作为地方黑势力,骨子里有蛮霸的一面,但同时还得有让人信服的一面。从罗歪嘴的这段话题支配型对话中可以看出,作者将罗歪嘴的黑社会属性刻画到性格深处去了,这种基于社会真实性的性格充满了艺术魅力。
而在讲述罗歪嘴、蔡大嫂情爱之迷狂时的一场话题支配型对话则充分反映了二人在这奇异生存状态下生命力的宣泄。“蔡大嫂说:‘人生一辈子,这样狂荡欢喜下子,死了也值得!’罗歪嘴说:‘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几岁?以前已是恍恍惚惚的把好时光辜负了,如今既然懂得消受,彼此又有同样的想头,为啥子还要作假?为啥子不老实吃一个饱?晓得这种情味能过多久呢?’”③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一个是表弟媳,一个是丈夫表哥,这两个作者在视角上亲近的人物的不伦之恋发展得这样热烈,蔡大嫂无处实现的野心、罗歪嘴无处安放的痴心在彼此那里都找到了归宿,从某种角度上看,这难道不是人物在生存困境面前激发生命力与之进行对抗式的宣泄吗?而蔡傻子那颗懦弱的心背后的奇特的忍气吞声性格难道不是在这种生存困境中作出的妥协策略吗?
其次,“大河小说”的话题支配型对话还表现在揭示世俗生活苍白的一面,将富于象征与想象的生活事件、生活仪式、生活俗套最苍白的一面用直白的话语说破。比如罗歪嘴向人承认他爱蔡大嫂并受到众人宽容嘲讽的一场话题支配型对话就展现了封建道德的禁锢在底层市民社会的苍白无力。“事情是万万掩不住的。罗歪嘴倒有意思隐密一点,而蔡大嫂好像着了魔似的,偏偏要在人跟前格外表示出来。于是他们两个的勾扯,在不久之间,已是尽人皆知。蔡大嫂自然更无顾忌,她竟敢于当着张占魁等人的面与罗歪嘴打情骂俏,甚至坐在他的怀中。罗歪嘴也扯破面子,不再作假,有人问着,他竟老实承认他爱蔡大嫂,并且甚为得意的说,枉自嫖了二十年,到如今,才算真正尝着了妇人的情爱。他们如此一来,反而得了众人的谅解,当面自是没有言语,俨然公认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即在背后,也只这样讥讽蔡大嫂:‘正经毕竟是绷不久啦!与其不能正经到底,不如早点下水,还多快活两年!’也只这样嘲笑罗歪嘴:‘大江大海都搅过来的,却在阳沟里翻了船!口口声声说是不着迷,女人顽了便丢开,如今哩,岂但着了迷,连别人多看她一眼,你瞧,他就嫉妒起来!’”①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在这种凝练的话题支配型对话中,针对蔡、罗之爱情,二人连同周边的人乃至叙述者都发表了意见,一场在封建社会极令人不耻的不道德的乱伦事件就这样稀释、消解在日常生活的对话中,变成了极其稀松平常的事情。道德的神圣和崇高在无形中被瓦解了,大家沉浸在一种戏谑和狂欢的氛围中。
再比如在《暴风雨前》中,郝又三跟朋友和妻子谈论新婚之乐的一场话题支配型对话便揭示了婚姻苍白的一面。“几个少年未婚的亲戚朋友,偶尔问到他新婚之乐如何,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笑道:‘有个女人伴睡,睡得不很着罢了!’……他有时也在枕上问他的少奶奶:‘你嫁跟我后,觉得有哪些与前不同?’……他的少奶奶也是摇头笑道:‘并不觉得有啥子大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把称呼改了,有点不方便。’”②详见李劼人著《暴风雨前》,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历来的美好青春爱情故事(青春文学)都在宣扬两个人双宿双飞、共结连理的快乐,而“大河小说”中的“中年文学”却直接将这种世俗生活苍白的一面展现了出来。或者这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深刻洞见,毕竟人到中年,自有新的格局和境界,可以直接透过生活事件、生活仪式、生活俗套的象征和想象层面,更加个人化也更加社会化地对生活进行深刻思考。
最后,“大河小说”中的话题支配型对话还表现为对故事人物、事件矛盾冲突的集中展现。比如在韩二奶奶跟邓幺姑说成都的美好而邓大娘跟邓幺姑说成都的残酷那一场话题支配型对话中,就充分展现了城市美好而残酷的两面性。“她母亲虽是生在成都,嫁在成都,但她所讲的,几乎与韩二奶奶所讲的是两样。成都并不像天堂似的好,也不像万花筒那样五色缤纷,没钱人家苦得比在乡坝里还厉害:‘乡坝里说苦,并不算得。只要你勤快,到处都可找得着吃,找得着烧。任凭你穿得再褴褛,再坏,到人家家里,总不会受人家的嘴脸。还有哩,乡坝里的人,也不像成都那样动辄笑人,鄙薄人,一句话说得不好,人家就看不起你。我是在成都过伤了心的’……但是邓幺姑总疑心她母亲说的话,不见得比韩二奶奶说得更为可信。间或问到韩二奶奶:‘成都省的穷人,怕也很苦的罢?’而回答的却是:‘连讨口子都是快活的!你想,七个钱两个锅盔,一个钱一大片卤牛肉,一天哪里讨不上二十个钱,就可以吃荤了!’”③详见李劼人著《死水微澜》,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这种话题支配型对话集中将城乡差异、阶层差异表现了出来,而且这种近一个世纪以前的差异与现在的城乡差异没有太大的不同,这也正是李劼人通过对话来写史的深刻之处。
在全城传说的官府惩办打教堂捡财喜的平民的一场话题支配型对话中集中表现了“洋人的官府”镇压人民的残酷。全城都在传说“洋人全在制台衙门守着……茶铺里所讲论的,全是……‘某人家里搜出一本洋书,全家男子通通锁走了,家里也扫了个精光。……某人本是好人,还有一个亲戚在盐道衙门里当师爷,被人寄了一口箱子,搜出来了,尽是洋人的衣裳,这下毁了,连一个大成人的姑娘着几个丘八踏得不成名堂……某人不是吗?只那天在门口拣了一块呢垫子,也着捉去了……’”④详见李劼人著《暴风雨前》,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页。这是典型的话题支配型对话,没有具体的说话人,也不限定在某一个具体的场景中,但都围绕着同一话题展开,在这种对话中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打教堂事件所引发的社会冲突。而对重大社会冲突的表现,到了《大波》中,话题支配型对话在集中表现故事人物事件冲突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在争路闹到罢市罢课后引起的官员与保路会主持者的一场话题支配型对话就直接反映了保路事件箭在弦上的紧张矛盾冲突。
从前述分析不难看出,在同一个话题支配下,不同人物的不同立场、不同信念和想象等矛盾冲突通过对话的方式如此鲜明地汇集在了一起,产生了丰富的文化意蕴,这正是话题支配型对话的魅力所在。
以上,我们对李劼人“大河小说”中五种类型的对话——作者—叙述者主导型对话、标准型对话、场景支配型对话、人物支配型对话、话题支配型对话进行了深入观察,讨论了不同类型对话的结构和起作用的具体方式。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分析的成分偏多,但本文努力将这样一个观察的框架结构置入小说文本中,以方便读者更有条理地把握作品中的海量对话。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还可以概括出李劼人“大河小说”的一些艺术特色。如在艺术形式上,作品存在着对话和故事两种艺术形式交融的关系;在阅读效果上,大量的对话使作品具有“生活化的历史”的特色;从作品表现的主体来看,作品对社会中具体的个体和群体的声音有着非常充分的表现;从作品表现的人的生命状态来看,作品对强者的意志和弱者的呻吟都有关注;从作品的思想倾向来看,作品中怀疑的声音表明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等等。但由于篇幅有限,只能另文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