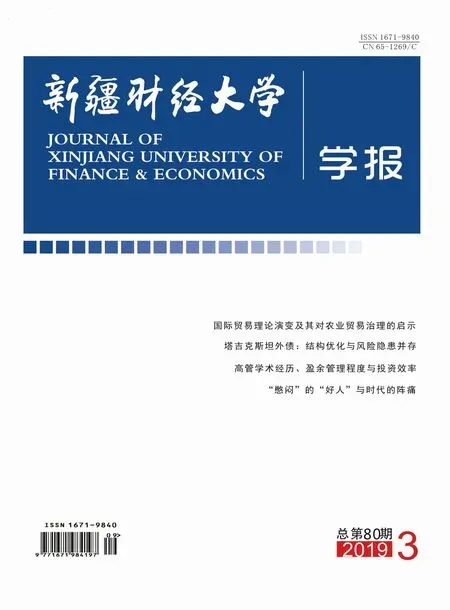“憋闷”的“好人”与时代的阵痛
——论石一枫新作《借命而生》
彭 超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102249)
自2014年出版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开始,石一枫的小说就将关注的眼光放在了底层青年身上,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勾勒出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打拼,失败后又重新回到农村的“失败青年”形象。作为一位出生并成长于北京的作家,石一枫选择将叙事空间设定为北京,陈金芳的打拼则是通过成为“顽主”的“傍家”完成的。此后,石一枫在一系列作品中再次将北京作为重要的叙事空间,而他本人也被称为后王朔时代的“北京顽主”,或“新一代顽主”。他的作品对社会现实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力,书写出时代转型时期人物的微妙心理,正如孟繁华所言,“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揭示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巨变背景下的道德困境,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塑造了这个时代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①详见孟繁华著《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变》,原载于《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第174~186页。。在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借命而生》中,石一枫围绕着“憋闷”的“好人”警察杜湘东经历的种种事情,继续探讨了从外地来到北京打拼的青年如何在北京遭遇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书写了时代转型时期的“罪与罚”。为什么被称之为“好人”的杜湘东时常会感到“憋闷”?这种“憋闷”与北京有着怎样的联系?在长久的“憋闷”之后,“好人”杜湘东能否与时代和解并寻找到生活的出路?笔者将围绕上述问题,品评《借命而生》这部直击现实之作。
一、“憋闷”:当理想遭遇现实
《借命而生》的叙事并不复杂,所有的故事都是围绕着警察杜湘东发生的。但是,警察杜湘东却时常感到“憋闷”,且他的“憋闷”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理由。
小说一开端就说“俩犯人被押送到看守所时,警察杜湘东正为调动的事儿憋闷着”②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这里点出了杜湘东的身份和他“憋闷”的第一个理由。
杜湘东1985年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郊县第二看守所,而他是刑侦专业的,在警校学习的时候,各项考核成绩都是全队前三名,毕业时却被分配到北京郊县的看守所。由于他是“异地生”,如果不服从分配,就只能回湖南老家。为了留在北京,落个北京编制,他选择了去看守所。他将希望寄托在工作调动上,虽说风光的刑警与乏味的管教都是警察,但是“风霜雪雨搏激流”和“少年壮志不言愁”毕竟要胜过“在阴森森的走廊里巡视犯人的吃喝拉撒”①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那是一种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与浪漫。
王蒙在1956年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设置了林震这样一位“新人”,通过他观察到工作中存在的矛盾,他要指出并改正这些现实问题。在《借命而生》这部作品中,作为看守所的“新人”,杜湘东所关注的焦点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是如何将一身本领用到破案建功上,获得理想的实现。若将林震与杜湘东进行对比,便能够清晰地看到时代与个人关系的变动。在林震的年代,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的安排,林震从未质疑过为何将他安排到区委组织部,他的斗争对象是官僚主义,这是一种“利人”的举动。在杜湘东的年代,不再是仅强调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安排的时代,而是更注重个体解放和理想实现,他认为自己被分配到郊县看守所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利己”的考虑。从林震的“利人”到杜湘东的“利己”,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比较,而是这种变化本身昭示着新时代的到来。杜湘东的“憋闷”在于此,他的寂寞也在于此,在一个“大时代”里,他不甘心做“小人物”,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让他感到痛苦和压抑。
如果说对工作的不满是杜湘东感到“憋闷”的第一个理由,那么婚姻问题就是第二个理由。刘芬芳往平静的水面扔进一颗石子,在杜湘东的心里荡起了阵阵涟漪,又渐成惊涛骇浪。
他们的恋爱过程也展现出了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与浪漫。作为一名高中毕业的冷库管理员,刘芬芳的业余爱好是读席慕容的诗歌和三毛的散文,喜欢聊人生与理想,时常发出抽象的抱怨,“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或是“可惜明天又要和昨天一样”,这种抱怨经过文学化的表达,无时无刻不透露出她想要改变现状的冲动与对未来的向往。她所展现出的对生活的不满集中于精神层面,并不涉及具体的日常生活。但是,当刘芬芳的“忧愁”与杜湘东的“憋闷”结合在一起,考虑步入婚姻生活时,他们就要从精神层面落入物质的窠臼之中。他们面临着现实的难题,刘芬芳不愿从城里搬到郊县,她鼓动杜湘东调回城里。在得知杜湘东调动不成时,刘芬芳决定退回信物。
爱情与婚姻题材向来为作家所钟爱,考察从恋爱进入婚姻这一转变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阻碍,能够清晰地发觉时代的更迭与价值观的变化。且不说古有《西厢记》崔夫人要求张生考取功名,后有《小二黑结婚》《登记》等作品中落后父辈和封建思想的阻挠,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青年人的婚姻向来是不容易的。单看《借命而生》,父辈不需要出场,年轻人便会自觉主动地从多角度来考虑自己的婚姻。观察杜湘东与刘芬芳的关系,便能知晓在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婚姻中,什么是重要的要素。恋爱时,双方多颇费心思地营造出一种精神追求高于一切的意境,而一旦落实到婚姻上,就都会务实地考虑具体的物质要求。这并非要批判他们对现实物质的追求,而是要理解这背后暗含着怎样的时代价值观。这是一个正在变换的时代,人人都在变换着自己,对美好物质生活的追求契合了时代精神。
工作调动和结婚的接连受挫足以让人憋闷,但这都是暂时的,“越狱事件”才真正让杜湘东陷入漫长的“憋闷”,也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姚斌彬和许文革的入狱是因盗窃了一辆放在厂里维修的皇冠轿车的发动机。入狱之后,他们以自己的精湛技术赢得了杜湘东的信任和善待。在姚斌彬说自己手疼的时候,杜湘东甚至愿意请自己的法医同学来看守所为他看病。对此,姚斌彬是感激的,他对杜湘东说,“您是个好人”②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页。。杜湘东完全可以对姚斌彬的手疼视而不见,但他却秉持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和内心的善良,愿意帮助一个入狱青年。如果故事仅停留于此,或许杜湘东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还不至于过度“憋闷”。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姚斌彬的家中,见到了姚斌彬的母亲,作为其母,她承受的艰难与蒙受的耻辱让人心疼。正是这极具偶然性的一见,让杜湘东对她充满了同情,也让他对姚斌彬和许文革更多了一份理解和善意。当杜湘东拿着猪肉大葱馅儿的包子送给许文革并表现出一种关心的态度时,许文革再一次道出,“您是个好人”①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页。。两个犯人先后对同一位警察说出“您是个好人”,这让杜湘东感到意外,警察的好坏哪里轮得到犯人来评价?对此,偏偏杜湘东是受用的,这至少说明他的工作是不赖的。他也的确是一个好人,这种好表现在他对姚斌彬母亲定期或不定期的主动探望,这种探望甚至在其随后的岁月里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并赢得了姚斌彬母亲的称赞——“好警察”。
“技术”与“情感”构成了杜湘东与姚斌彬、许文革建立起信任关系的重要内核,同时也是杜湘东长久“憋闷”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姚斌彬和许文革作为厂里的青年工人,他们所掌握的技术以及对技术表现出的专业态度和热爱情绪值得尊重。即便在狱中,一种信任关系也能够在管教和犯人之间建立起来,这种信任建立的基础就是杜湘东对姚斌彬、许文革所拥有的技术和能力的肯定,而杜湘东对自我的认可也是建立在自己的能力之上。他们都认同能力对时代的重要性,都不满足于现有的环境,都持有一种“奋进”的精神状态,也都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所以才会有“憋闷”与后来的故事。
杜湘东的“憋闷”,归根结底是由自我认同失败带来的。他无法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定位,他所秉持的理念是传统的,他注定是要做一个“好人”,注定要为做“好人”而付出代价。他服从集体安排,即便不情愿,也来到看守所当了管教;面对婚姻的现实难题,他尊重姑娘的想法,委屈自己的人生;他天性善良,所以才会对犯人抱有同情,关心犯人的家属。他竭尽全力去做一个好人,所以只能不断牺牲自己的宏大理想,将自己的人生摔得支离破碎。
二、城与人:“憋闷”在北京
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探寻过城与人关系的文学表达,“一个大城与它的居住者,一个大城与它的描绘者”②详见赵园著《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石一枫在《借命而生》中将叙事空间设定为北京,通过讲述城与人的故事,来表达一种“中国经验”。
杜湘东的“憋闷”与北京分不开。若是将杜湘东的故事背景换一座城市,那就不是《借命而生》了。作为首都的北京是小说的叙事空间,其特殊的地位放大了这种“憋闷”。作为一座不断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它的历史是由无数个杜湘东这样的外地人和本地人共同建构的。“北漂”这个词倒是很能说明这一点。无数的外地人带着梦想来到北京,希望能够在北京寻找到实现理想的途径。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和故土,选择孤身在北京打拼,将自己的命运与时代的脉搏联系起来,试图在北京找寻生活的乐土。杜湘东也不例外,从他选择毕业留京开始,他的命运便与北京的发展密不可分。作为外来者,他成为了这座城市的观察者、居住者和描绘者。
杜湘东最初的“憋闷”便与留京有关。作为外来者,杜湘东认为留在北京是值得的,这意味着他在未来会拥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但彼时的北京,郊县与市区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杜湘东被分配到的北京郊县看守所较为荒凉,出了永定门还要往南走,看守所建在菜地边缘的山底下。在杜湘东看来,这都不算北京了。他留京的初衷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却被分配到郊县看守所,理想和现实的落差让他感到“憋闷”。这种郁郁不得志的感觉,因在北京而引起了更深一层的思考。为了更好地发展,北京需要吸纳优秀的外地人,可是如何能够真正人尽其才,为优秀人才提供发展空间,这也是小说揭示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在杜湘东逐渐适应郊县的寂寞之后,与北京姑娘刘芬芳的恋爱让他的价值观再一次遭遇现实的冲击,他又一次感到“憋闷”,而这“憋闷”同样与北京有关。
冷库管理员刘芬芳是北京本地人,家住宣武区,高中毕业,工人编制,但在旁人看来,她与大学毕业、干部编制的杜湘东却是“登对”的。从中我们得以窥见外地人在北京的婚姻关系中处于怎样的境地,以及北京这座城市是如何影响人们对婚姻、配偶的选择。
进入谈婚论嫁阶段,二人因杜湘东的工作地点而面临散伙的危机,这也是与北京分不开的。刘芬芳是城里人,不愿去郊县生活,“就是哪儿也不去,站在长安街上看看电报大楼的灯,心里也是舒服的”①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当杜湘东提出权宜之计时,这个高中毕业的姑娘出乎意料地举出几个刚和中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官的例子,甭管多忙多重大的场合,大使和大使夫人都是寸步不离的。这个举例着实有北京特色。作为北京人的刘芬芳不仅对时事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还能够将其联系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尽管她的生活与大使夫人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后来,杜湘东因孤身追捕持枪逃犯的英雄壮举而重新赢得刘芬芳的青睐,但这并不意味着横亘在两人之间的城市与郊区的矛盾得到了解决。
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得益于北京的城市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北京逐渐成为全球化的现代大都市,企业不断发展、更迭,这就势必带来工人的流动,没有技术傍身的工人首当其冲。与此同时,北京的郊县不断发展,进行着城市化运动。当刘芬芳成为下岗女工时,她已被这个时代逼迫着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作为北京人的她不得不前往郊县寻找生存之道。在时代与北京的“合谋”之下,他们终于在郊县“团聚”了。
犯人的逃跑让杜湘东陷入持久的“憋闷”,这种“憋闷”伴随着时代的推移,最终将一个敬业的看守所管教转变成了“一个别人眼里的北京人”,即“北京大爷”。这是非常吊诡的事情,一位优秀的外地人不是通过工作和婚姻融入北京,反而是通过“堕落”,最终成为别人眼中的北京人。当他的北京妻子为之抱怨时,杜湘东感到不忿,难道他就没有堕落的权力吗?而他妻子在权衡之后,居然认为“比之于奋发的杜湘东,堕落的杜湘东才是适合于当丈夫的”②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4页。。
杜湘东的“堕落”与他面临的现实生活压力有关。当杜湘东不再是单身汉之后,他就需要为家庭进行务实的考虑,“从云端跌落回了地面,从抽象还原成了具体,从恢宏分解成了细碎”③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5页。。伴随着杜湘东的警服从“八九”式更换到与国际接轨的“九九”式,刘芬芳的忧愁也转变为抱怨,抱怨自己的命苦和杜湘东的无能。作为一个并不富裕的人,杜湘东开始向生活投降,年轻同事们看他的眼光与若干年前他看老吴的眼神如出一辙,饱含着一种亲热但又不屑、怜悯中又夹杂着几分无奈的情绪。但他与老吴又是比不得的,老吴是北京郊县人,已然借助北京城市的发展而获得了阶级的超越。杜湘东决定要赶上北京的发展步伐,开始学着利用权力来谋得私利,而这让他显得更为可悲。他将刘芬芳二姐公司淘汰的冰柜从二环边儿运到郊县看守所对面的河岸上,让下岗女工刘芬芳摆摊卖冷饮做小买卖。当城管来的时候,杜湘东便穿着警服带着所里的小兄弟们“罩着”,让刘芬芳的小摊获得了小小特权的庇护。这无疑构成了一种反讽叙事。当年毕业其他同学利用关系被分配到好单位时,杜湘东曾深感不公;而如今他也学会了利用自己的小小关系,让妻子得以在看守所对门摆摊。
“堕落”更深层的原因是他无法直面自己失败的人生,在面对现实时,他感到乏力,尤其是与自首的许文革相比。
许文革与杜湘东的人生形成了镜像关系,与杜湘东的“堕落”相比,许文革是一个“迷途知返、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他的眼中始终有着孤注一掷的光芒,并最终将自己的人生从逃犯改写为他人眼中的时代传奇英雄。这才是真正的个体解放,许文革以敏锐的洞察力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反观杜湘东,他的一生屡屡受挫,始终被时代推着往前走,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反差是巨大的,一个在逃的犯人以成功人士的姿态重新回到看守所来自首,也重新回到阳光下;一个警察却始终生活在逃犯的阴影之中,并不得不为适应“许文革回来了”这一现状而表现出“堕落”,以伪装自己的“毫不在乎”。“如果说以前堕落,是因为不知道许文革身在何方,那么现在堕落,不妨可以算是他为了适应‘许文革回来了’这一现状所做的努力”①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4页。。这种“堕落”是杜湘东不得不为之的举动,除此之外,他无法让自己的人生再次重写,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慰藉,所以,他只好进一步向生活低头,以掩饰自己内心的创伤。在经过漫长的“憋闷”之后,当年意气风发的“好人”终于在时间的长河中“堕落”成“北京大爷”,骑着破自行车去钓鱼、嗜酒、养蝈蝈儿,以一种不关心事业只关心生活的姿态融入北京郊县的生活中。这不免令人叹息。
杜湘东的“憋闷”与北京长久地纠缠在一起,他的工作、婚姻甚至整个人生都与北京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首都,北京的发展表征着一个时代的变化,一座城市的发展和一个时代的发展都离不开杜湘东这样的外来者和建设者,他的遭遇是时代的缩影,他的痛也是北京的痛,这些经历也让他成了北京历史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三、失掉的主体:“好人”与理想的降落
当我们将目光再次聚焦杜湘东的一生,观察他是如何由一个“好人”堕落为“北京大爷”时,不由得想起潘晓的来信。
1980年5月,《中国青年》发表了一封署名为“潘晓”的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所流露出的彷徨和迷惘触动了无数青年人的心,中国青年杂志社随即展开了一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在这场人生观大讨论中,大家探寻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对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思和质疑,渗透到一代青年人的精神骨髓中。
与潘晓在信中流露出的苦闷与怀疑不同,杜湘东从警校毕业时对人生充满了憧憬,他在职业生涯之初是纯粹的,有着一股年轻人特有的力量感。吊诡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朝着“越走越窄”的方向行进,并从“好人”“好警察”成为了同事们敬而远之的“杜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这与时代的变迁和价值观的转变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杜湘东的一生有几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是他递交调动报告,第二个是刘芬芳劝他辞职,第三个是许文革自首。
先看杜湘东递交调动报告的时间节点,“人人都说时代正在变换,因而人人都在迫不及待地变换自己”②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唱出“你何时跟我走”,在这个一无所有的年代,“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面对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失落、痛苦、迷惘、无奈的年轻人正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世界中艰难地找寻自己的社会定位。杜湘东在这个时候提出调动,代表着那一代年轻人的想法。自由与个体解放的旗帜已经高高扬起,杜湘东在这面大旗的感召下投入时代的潮流中。如果他的调动报告被批准,他也可以像他的那些成功同学们一样,拥有一个远大前程。
然而,杜湘东的申请被拒绝,接连引发的破戒行为以及随后的逃犯事件给杜湘东的事业画上了休止符。没想到的是,追捕持枪逃犯的行为给他的婚姻带来了转机,“它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在那个春天,人们都在渴望改变什么并且相信自己真的能够改变什么”③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0页。。一种浪漫的冲动让刘芬芳暂时把现实考虑放下,她做出了结婚的决定,他是一个英雄。观察刘芬芳对待杜湘东前后态度的转变,思考她对婚姻的考虑,从最初的精神契合,到被城市与郊县的距离打败,再到目睹英雄归来,现实与精神在不断地进行着斗争,最终精神取胜。这是20世纪80年代最后的浪漫之举。待到他们结婚,现实的困难和生活的琐碎逐渐压倒精神,刘芬芳的忧愁也变为抱怨。杜湘东不再对生活充满憧憬,而是逐渐进入“熬”的状态。这是刘震云在1991年出版的《一地鸡毛》中所描述过的20世纪90年代的生活,刘芬芳变成了“小李”,而杜湘东几乎变成了“小林”。
在“越狱事件”的第六年,同样也是一个春天,杜湘东的人生迎来了新的机遇,那就是去刘芬芳二姐工作的外企去当物流部的小组长。在刘芬芳看来,这是不错的前途,“工资翻番儿不说,他们还给租城里的公寓”,并且“过不了几年保证升职”①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她极力劝说杜湘东从看守所辞职,“铁饭碗不如金饭碗”。这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时代的更迭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编制、警察职业都比不上高工资和好福利,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重要内容。
这实际上是价值观的更迭,甚至在杜湘东放不下逃狱事件而去请教以前的老同学时,他的老同学在世界观上也是如此启迪他,“人都活在现在,能顾得上也只有现在”②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8页。。时机是转瞬即逝的,一旦落伍,就可能永远都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杜湘东并非不知道时代变了,但他迈不过去那个坎儿,于是在拒绝刘芬芳的美意之后,他决定主动出击,假借探病去山西追捕许文革,上演了一出具有“千里走单骑”意味的好戏。杜湘东的千里追捕,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这也让小说具有了一种悲剧色彩。山西不断被开采的煤矿吸引着大量务工人员,不健全的管理机制给许文革提供了藏匿的机会,化名为姚文林的许文革成功地藏身于一个远离城镇的煤矿。如果不是寄给姚斌彬母亲的汇款单暴露了地点,可能杜湘东永远都无法在流动的社会中锁定一个具体的方向。这无疑也显示出时代的变化,人们不再固定在特定的岗位或地区,而是在社会中四处流动。这一时代的资本生产方式是粗放的,煤矿开采时常会有事故发生,私人承包的煤矿更是矿难频发。许文革便是借由煤矿塌陷之际,从杜湘东的眼前再次消失。杜湘东的再次受挫,加之现实的巨大压力,让他不得不向生活低头。
2001年春,许文革归案,这是杜湘东人生的第三个转折点。长久以来的“憋闷”原本可以就此放下,那么是不是杜湘东可以就此释然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见到许文革的“成功人士”作风之后,杜湘东反而更加恼怒与愤懑。许文革是他心理的暗疾,在漫长的岁月中折磨着他,姚斌彬的两次似笑非笑让杜湘东深深反思和质疑自己的观察力及判断力,而现在许文革也对他露出了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这触到了杜湘东的痛楚,多年之后,许文革依然保持着当年的硬汉风格,而杜湘东已然学会了以权谋私和变态报复。这种对比让人触目惊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让杜湘东释然的是这样一句话,“许文革说,您也不容易”,律师还转述,“说到您,他只有一句话:这是个好警察”③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8页。。这是小说第四次出现“好人”“好警察”的评价。
J.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中提醒我们要注意小说中的“重复”现象,“它们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时这些重复还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多样化的关系”④详见J.希利斯·米勒著、王宏图译《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一种价值观在这种不断的重复中得以重建,那就是关于如何来评价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借命而生》在不断引导读者去探寻“好人”“好警察”的评价标准,在不同的时代,杜湘东都得到了这样的评价。在故事的起点,姚斌彬、许文革、姚斌彬的母亲都以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标准对杜湘东作出了高度评价。基于个人道德原则和职业责任准则,杜湘东的行为是令人尊敬的。经历时代的更迭,这种“好”遭遇了市场经济时代的考验,在以金钱作为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时,它显得有些“落伍”和“过时”。到了21世纪初,一个事业成功的商人许文革对杜湘东再次作出这个评价时,显然不是以金钱为评价标准,而是重新回到了道德标准上,以良知来判断和衡量他。就是这样一个“好警察”的评价让杜湘东放下了所有的敌意,他甚至愿意为许文革在矿难时的救人举动作证。毫无疑问,“好警察”的评价是对杜湘东职业生涯的最高认可。相较于赚钱,杜湘东更看重的是精神性存在,许文革的评价让杜湘东重新肯定了自我,认可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从那一刻起,杜湘东得以成为他自己,他正视了真实的自我,找回了自己的存在感。这无疑是荒唐又可悲的,警察和逃犯,在某种意义上说成为一种惺惺相惜的存在,一个警察的自我肯定居然来自于一个逃犯的认可,而这如此真实地发生在这个时代,发生在杜湘东的身上。
与此同时,杜湘东的另一种情绪也被许文革激活了,那便是他萌生了对“公平”的质询。许文革今日的成功是建立在昔日姚斌彬的“自我牺牲”之上的,是姚斌彬主动拿起了老吴的枪,将自己变为追捕的重点对象,从而给了许文革进入新时代的机会。杜湘东要为姚斌彬向许文革讨个说法,向这个新时代讨个说法。他动员老同学帮他调查许文革的发家史,甚至在许文革出狱之后时常盯梢,要以他的方式找回“公平”。这种行为有些不合时宜,老同学再次开导他,“许文革是顺势而为,我们要动他就是跟政策对着干”,“说到底也是环境使然,如果只揪着他一个人不放,那也不公平”①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7页。。
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平?从1988年姚斌彬和许文革的被抓,到2008年谜底的最终揭开,对于姚斌彬、许文革、杜湘东来说,他们的命运都是被时代裹挟的,谁能告诉他们什么是公平。
在进入新时代的关节点上,这三个人象征着不同的命运。姚斌彬是清醒的思想者,最先嗅到机遇的味道,他感到新的时代就要到来,要提前做好准备,成为有本事的人。为此,他提议拿厂里的皇冠轿车来练习汽车修理技术。可惜,他的右手被砸成粉碎性骨折,这让他失去了进入新时代的资本。所以,在越狱的时候,他主动拿走那把枪,把生的机会让给了许文革。相较于姚斌彬的敏锐,许文革是有力的行动者,他替姚斌彬活着,替他照顾母亲,替他学技术、做生意、开工厂,替他完成他想干而干不成的所有事。许文革背负着两个人的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终于替姚斌彬活成他想要的模样。与姚斌彬和许文革相比,杜湘东是善的坚守者,他固守着一种“古老”的道德准则,这让他在经历社会转型时感到异常痛苦,面对活出了模样的许文革,杜湘东控诉道,“可因为你,我够窝囊的,我他妈才是白活了”②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1页。。是啊,许文革活着,对姚斌彬而言是不公平的,对杜湘东而言同样也是不公平的。这不公平与不公平之间,有着生与死的差别,更有着时代的差异,杜湘东的一生都生活在逃狱事件的阴影当中,他又要去何处寻找公平?许文革的生命因姚斌彬的牺牲而获得一种存在的价值,那么杜湘东呢?他的价值何在?
小说在不断追问,在时代更迭、社会转型之时,是什么原因让杜湘东成为失败者?他原本不甘于在“大时代”做“小人物”,可最终成为了“小时代”中的“小人物”。他为何无法抓住属于自己的机遇?他又是怎样在时代的进步中一步步“掉队”而成为社会转型的“牺牲者”呢?
这必须回到20世纪80年代,回到效率与公平那里去寻找答案。换言之,我们需要重回历史语境,去追寻杜湘东如何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失掉主体性,从而出现“好人”的“堕落”。正如陈晓明对此作出的概括,“不满与期待,忿恨与躁动,希冀与梦想,混为一体;挡不住的诱惑,摸着石子过河,跟着感觉走……人们既为现实的不公不平痛心疾首,也为眼前的机会激动不安。在这初具规模的竞争年代,人们需要成为强壮的自然之子。”①详见陈晓明著《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毫无疑问,小说在此叩响了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大门,杜湘东关于公平的追问、许文革在商界的成功,让人联想到邓小平在1985年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以此来实现加速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这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转型中,许文革凭借过硬的技术实现了“先富起来”,得以在一场效率与公平的较量中获胜。反观杜湘东,一个高学历的看守所管教,一个失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得不让人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90年代转型时期的溃败②这涉及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又是另外一个复杂的话题了。。
四、时代反思:那条漆黑的路被走到头
借用福柯的论断,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因为故事讲述者身处的社会现实往往会影响既往的历史故事被如何讲述。当我们阅读《借命而生》时,需要反思的是,石一枫在作品中将20世纪80年代形塑成怎样的年代,他是如何看待时代变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作为一个失掉主体性的知识分子,杜湘东所走的路提醒着我们应怎样对时代保持警醒态度和批判精神。
小说中一再提到“好人”“好警察”,这无疑是对杜湘东的一种评价。相较于许文革所拥有的在竞争环境中极强的生存能力,杜湘东的“好”究竟能不能给予他主体性?在这里,绕不开李泽厚对主体性哲学的探讨。他认为“主体性”包含着两个“双重”含义:第一个“双重”是指“工艺—社会的结构面”和“文化—心理的结构面”,第二个“双重”则是“人类群体”和“个体身心”。这四者是相互交错、不可分割的。作为对主体性哲学讨论的补充,李泽厚提出“道德正在于自己决意如此行动,从而自己负责。作为伦理道德的核心的自由意志正在于,它标志主动选择。不是外在的环境、条件、规范、要求,而是由自己自觉自愿地选择了、决定了自己的作为,这就是道德”③详见李泽厚著《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1期,第14~21页。。小说中几次对杜湘东的评价都使用了“好”这个词,也提醒着我们从道德的层面去理解杜湘东的主体性。他将外在的束缚内化为自身的自觉命令,形成一种道德自律,仿佛这“好”是纯然起源于“本心”和“良知”。这也让杜湘东的举动显示出一种“本体的崇高”,显现出“主体作为本体的巨大力量和无上地位”④详见李泽厚著《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1期,第14~21页。。但为何杜湘东又呈现出一种溃败的知识分子形象呢?在精神文明的世界中,他是崇高的,但在物质文明的世界中,他又是卑微的。这种形象的差异和错位,从某种意义上说透露出时代转型的艰难。在理想和现实的中间地带,“好”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迷惘都转化为一种当下的道德安慰,起码,“我”还是一个“好人”“好警察”。杜湘东的“好”支撑着他度过时代转型的困窘岁月,让他在社会变迁中能够找寻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小说在描述杜湘东为姚斌彬请医生时,用了“人道主义”一词,这也让人思考杜湘东的“好”与“人道主义”、与当时的社会思潮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更深层的联系。“人道主义思潮在7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的基本历史语境,一方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新时期’的提出,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审判‘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和为‘右派’平反、由中央发布‘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方式,终止并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也就是说,开启‘新时期’与审判无产阶级专政被滥用的历史,这两者往往被看成一体的两面,人道主义思潮则既是这一历史转折的动因,又是对这一历史转折的呼应。”①详见贺桂梅著《“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在杜湘东思考着自己善待犯人,给姚斌彬看手是符合“人道主义”的时候,这也在广阔的社会思潮与文化语境中获得了一种与时代同步的节奏。一边是看守所的管教,一边是被关进监狱的犯人,这里没有警察对犯人居高临下的审判,而是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同情,杜湘东是新时代的同路人,他表征着拥有无数历史可能性的新时代,他是知识分子在一个时代的缩影。他所走的路,无疑也具有了一种象征意味。
在结束对许文革的盯梢之后,杜湘东终于学会了“与往事干杯”,而许文革也陷入了困境,从熟悉的工厂实体经济到陌生的金融资本游戏,许文革的对手早已发生变化,这宣告着新的时代的到来。小说在结尾处,许文革向杜湘东告别,再一次似笑非笑。杜湘东又一次感到“憋闷”,然而这一次的“憋闷”与以往的“憋闷”不同,他在暗夜中奔向工厂,奔向停放皇冠轿车的屋子。哦,又是那辆皇冠轿车,让姚斌彬着迷又让姚斌彬死掉的那辆皇冠轿车。从1988年的稀有物,到2008年的老古董,这辆皇冠轿车见证了时代,也改变了两个年轻人的生命轨迹。现在,杜湘东也来到了这里,他从死神的手中将企图自杀的许文革救回来,他的心中涌动着悲怆的豪情。他破了人生中第一桩案件,不为抓人,只为救人。杜湘东告诫许文革不能死,因为他的命是向姚斌彬借的。那么,杜湘东的命呢?是不是也是向别人借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个体存在的价值依赖于周围的群体,依赖于时代的整体评价。所以,杜湘东的命也是向别人借的,是向姚斌彬、许文革、刘芬芳他们借的,是向世上所有的人借的。最终,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漫天焰火中,杜湘东的“憋闷”一扫而空。
杜湘东一直在渴望“发光”,但最终他在那条漆黑的路上走到了尽头,他的痛苦和“憋闷”都将成为历史的记忆。小说在结尾处写道:“男人战斗,然后失败,但他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②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5页。。他们对价值的追问、对存在意义的质询、对理想的渴望,他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时代前进步伐中的重要一环,他们的痛也是时代的痛。这位“憋闷”的“好人”以自己的战斗和失败将自己化为时代的缩影,并最终与时代达成了和解。正是这突然降临的和解,给小说增添了一点“鸡汤”的味道,这和解的达成是因杜湘东救了许文革一命,破了人生中的第一案?还是在目睹了许文革的自杀后,他终于明白大家都只不过是时代浪潮中的无名者?
《借命而生》带着我们重审20世纪80年代,小说所展现出的美学特征正如蔡翔等人所言,充满着“挣扎着向上的欲望”,“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对现代化的热烈憧憬,又有对自身的更高的美学追求;既有对现代性异化的批判,又有对专制社会的强力抗击……它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型态,使人在种种困窘之中爆发出强烈的奋进精神。但是不能据此把八十年代处理成一个温馨的或者肤浅的乐观主义时代,尽管这个时代充满高歌猛进的青春精神。八十年代同样充满凶险,道路坎坷,而且我以为这一代理想主义者身上具有浓郁的悲观情结”③详见蔡翔、罗岗、薛毅著《理想主义的昨天与今天》,原载于《山花》1998年第7期,第69~75页。。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并没有将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简单化和平面化,也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去指点杜湘东,认为他应该放下自己的坚持,改变他的“轴”,去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而是紧紧地贴着人物的心理和时代的变化来书写,将时代转型时期的艰难历程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好人”或者说“理想人物”失败的故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杜湘东的最终和解,也是一个自我道德认可得以实现的故事。
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小说在结尾处提到“那条漆黑的路被他们走到了头”④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5页。。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那条著名的路,即鲁迅在小说《故乡》中的最后一段中写到的路,“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日本学者藤井省三考察鲁迅《故乡》的阅读史,认为进入新时期,《故乡》有了一种新的解读,那就是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联,在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知识分子与小市民的叙事,“在这一时期,民国时期的知识阶级所无法比拟的庞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小市民阶层正在形成。这种邓小平时代出现的、一边向民国时期的‘阅读’回归一边呈现出新动向的对《故乡》的阅读,也许并非是将文本作为旧中国破产的故事,而是作为共和国遭遇的挫折的故事来阅读的。”①详见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译《鲁迅〈故乡〉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7页。鲁迅笔下的“希望之路”,从诞生之初的知识阶级批判色彩,到看重文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功用,再到表征新时期“共和国遭遇的挫折”,承载着现代中国的复杂历史记忆。
小说借用崔健的歌曲来表达作者对未来的思考,1986年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唱出“你何时跟我走”和“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试图召唤的主体是一代青年人,询问的是要不要“走”、什么时候“走”的问题。而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在哪一条“路”上走以及怎样“走”。1986年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同样追问的是“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两句歌词“将社会激变中的20世纪中国重构为一条‘路’”②详见白惠元著《电视剧〈西游记〉与80年代中国文化》,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4期,第61~73页。,那么这一条“路”与杜湘东所走的那一条“路”是同一条路吗?
将20世纪80年代看作是接续五四的“新启蒙”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中国面临着相似的历史语境,表现出相似的情感形态:对改变现实充满热情,对现代化充满憧憬,怀着一种时不我待的心情去摸索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在鲁迅的《故乡》中,回到故乡的知识分子“我”面对产生隔膜的闰土,产生了一种深切的反思。在《借命而生》中,“堕落”的知识分子杜湘东看到成功的商界传奇许文革,反而生出了一种自卑与自怨的情绪。何以在穿越岁月的河流之后,知识分子的形象呈现出这种分歧?
这条“路”,在《借命而生》中被表述为“漆黑的路”,那又为何是漆黑的?石一枫将杜湘东与许文革这一对冤家最终安排在一起,他们共同走上了那条漆黑的路,并走到了头。这又让我们追问,这条漆黑的路是否可以理解为艰苦的历史转折之路?他们最终在漆黑中摸索出一条路来,那是一条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路。现在,他们在这条路上走到了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达成和解或是取得了最终成功,因为面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商界传奇和溃败的知识分子都会面对失败。他们不得不向现实妥协,进而承认自己在时代中掉队或再次掉队。
小说在结尾处,将时间定格在2008年8月8日晚,这一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鸟巢体育场顺利举行,彰显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预示着中国的国际化程度将再次提高,这看似是给悲剧故事加上了光明的尾巴,杜湘东的“憋闷”也伴随着奥运会开幕式的焰火一扫而空。正如崔健在《一无所有》中所唱,“告诉你我等了很久”,中国等待这一天也等了很久。但这幸福的许诺让人心生疑虑,这条路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国内走向国际,这种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叙事,将引导我们走向何处?这在小说中并不明了。在这未来的叙事中,也未曾言明谁将取代知识分子成为新的主体。文末仅在只言片语间透露出信息,是什么力量让许文革的工厂关闭,“刚开始以为是几个商人组成的私募基金,后来又听说有外资和国资的参与,再后来才发现是个什么领导的什么亲戚在背后撑腰”,而这些金融资本的操纵者对工厂实业并没有兴趣,他们只是要利用国有企业的“壳儿”和地皮,“整合出一家地产公司再打包上市,此后连一砖一瓦也不用盖,到股市里迅速圈钱走人”③详见石一枫著《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5页。。这暗示着一个全球化金融资本时代的到来,它摧垮了许文革的实体经济,造成商界传奇的陨落,也暗示着未来道路的艰辛与复杂。在这一刻,即便杜湘东的“憋闷”一扫而空,那也只是中场休息的片刻轻松,未来的路将往何处走仍是不可知的。杜湘东学会了与“与往事干杯”。《与往事干杯》是改编自陈染同名小说的剧情片,故事的主人公少女蒙蒙在经历了童年的心理创伤之后,试图寻找治愈自我的方式。她无法在美国洛杉矶完成与华裔青年“老巴”的婚礼,她只有回到中国才能修复童年的创伤。以此为例,小说并非是要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的那些艰辛往事“干杯”,而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冷静思考,没有回归到中国本土经验,历史的创伤将无法修复,未来的走向也不会清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难题,因国情的特殊性而无法去复制和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未来的路究竟该如何“走”,仍是需要继续探索的难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必须回归到中国经验。
从20世纪80年代的憋闷与摸索,到90年代理想与现实的挣扎,再到新世纪的妥协与和解,杜湘东的这一条“漆黑的路”终于走到了头,而这一条路也是知识分子探寻中国未来发展之路,他的豪情、他的悲壮、他的痛苦,让他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有力见证者,也提醒着知识分子要时刻保持着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