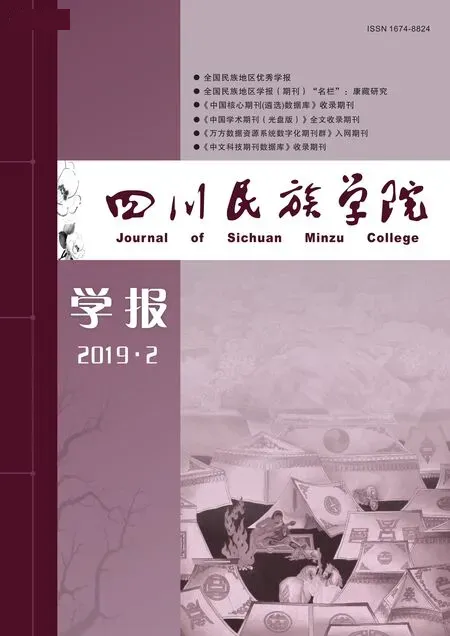浅析天主教对康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以康定为例
于 潇 孙露娇
前 言
康区,又称东部藏区,指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地区、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等部分。因其处于四川与云南、西藏、青海交界地带,近代历史上多指称川滇边[1]。该地区作为藏族三大聚居区域之一,由于地处藏区东南部的边缘地带,地形复杂,交通相对不便,使之长期处于汉藏两大势力的末梢。近代以来,国际国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我国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逐步提升,康区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康定地处川西,为出入西藏的重要门户,是茶马古道上的经济重镇,是康区的经济贸易集散中心,1729年置打箭炉厅后,更是成为沟通藏地与内地的枢纽,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体。因康定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多重中心的代表性,本文以天主教在康区的主要根据地——康定为例,通过考察天主教在康定的传播与发展情况来论述天主教在医疗卫生方面对该地区的具体影响,希望为天主教对康区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 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播与发展
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早在17世纪就曾进入藏区,并有了一定的发展。近代以来,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被与西方国家的对华侵略关联在一起,因此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抵制。加之,藏民族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对天主教的接受度很低,使得天主教在西藏腹地的传教十分困难。但是天主教并没有放弃进入西藏。他们开始寻找新的契机,并将传教阵地转移到靠近西藏的川滇边地区建立新的传教点,“设法在西藏的大门口布置主教场地,以便等待时机,以待将来”[2]。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康区成为了天主教进入西藏的前沿据点之一。
天主教在康区的发展及相关活动如下:
1856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杜多明被任命为西藏教区主教,由于当时西藏地区正驱逐外国传教士,无法入藏,后留驻康定,在达林埠(今大林坪)建立了主教府。天主教自此正式进入康区。
1857年8月,西藏与川西北、川东南教区商定并划分各主教区界限,明确了康定属于西藏教区。此时康定还没有教堂。
1864年,法国神父吴依容被派驻打箭炉,开展教务。
1864年,法国传教士丁盛荣任西藏教区主教,并于二月从云南出发经打箭炉赴任。因西藏驱逐传教士,遂驻足于康定,在该地区开展教务。
1877年,丁盛荣客死康定,毕天荣任主教。
1901年,毕天荣逝世,倪德隆由副主教升任主教。
1910年,罗马教廷下令取消西藏教区,成立了以康定为中心的打箭炉教区(1946年改名为康定教区),直属于罗马教廷。康定教区所辖范围较广,居全国八大教区之首。
倪德隆任主教期间(1901-1936),天主教在康区有明显的发展。他在康定购置土地,修建教堂、真原堂和公教医院等。此外,天主教在康定还设有善牧堂,其中包括育婴堂,专门收养弃婴、孤儿及教友寄托的子女。虽然天主教在康定开办教会医院、兴办免费医疗卫生事业等更多地是为了传教,但是它们本身具有宣道和施医的双重功能,所以不可避免地对康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天主教对康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
(一)医务传教
19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国力强盛,武器先进,这一时期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也带有强烈的优越感,他们想凭借自身的先进文化征服广大中国民众。但这一方式遭到了中国传统观念、文化习俗的强烈抵触,引起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冲突。由于人们的仇视和敌对,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举步维艰。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教,传教士们决定采取以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营造一个有利于天主教发展的良好环境的新传教方式。为此,许多传教士将主要精力投向了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慈善等多种社会事业领域,注重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影响和改造,最后走向由中国人“自传、自治、自养”的本土化传教方式[3]。
天主教最初在康区传教时,也带有强烈的优越感,采取排他主义,对藏传佛教及其僧人进行贬低和抨击。而藏传佛教对康区民众的影响根深蒂固,天主教的传教方式使其与藏族民众之间的隔阂加深、冲突不断。加之藏民普遍的仇洋情绪,使得天主教与当地民众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导致教案频发,藏民袭击传教士、打毁天主教堂的事件时有发生。为了更好地在康区传教,改变传教方式势在必行。
医务传教方式并不是天主教在康区独创的。天主教徒受耶稣的影响,历来就有救助医治病人的精神和传统,利用医药来辅助传教则在唐朝景教传入中国时就已被采用,明末清初将这一方法运用得更加广泛。“可以说早期的医学传教士为后来的传教士树立了榜样,提供了经验。”[4]天主教兴办教会医院、诊所,给予贫苦民众医疗上的便利,无疑可以更好地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铺平道路,从而获取更多的信任。“医学传教一度被各传教团视为传播基督福音的最佳途径之一。”[5]
天主教进入康区后,一方面为了减缓当地民众的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康区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使传教士感触颇深,传教士决定以医疗辅助传教事业,采取医务传教的方式笼络人心,随之在当地租、买土地,建立教堂,修建教会医院。有的教堂还设有施药处,在宗教气氛中为汉藏民众治病疗伤,密切与当地人的关系,借以传播教义。
(二)天主教对康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
天主教在康区以传教为目的而开展的一系列医务活动,虽然不是单纯的治病救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医务传教的形式有利于让当地民众接纳西医西药这种外来医疗手段,对改变康区民众的医疗卫生观念也起着重要作用,又客观上促进了藏医药的改革。而天主教兴办的教会医院既为康区创办近代医院提供了一定的管理经验,又为康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接纳西医药
就康定而言,西方医术也是伴随着天主教的传入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虽然清末改土归流也曾涉及到医药卫生方面,但由于当时的改革是以武力作为后盾,带有强迫性,所以遭到了当地人的抵制。在天主教开办诊所,建立教会医院,采用西医技术为康区民众治病之前,该地区还未有西医传入,因此西医进入之初人们对其多有排斥心理。但是由于西医见效快,加之人们对医药的需求,使得他们逐渐降低了对西医药的抵触心理,传教士也由此慢慢获得民众的信任,进而方便传教士向病人及其家属宣扬教义,以便获得更多的信众。虽然这种传教方式有它的目的性,但是客观上却为康区带来了一些西方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推动了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1911年,法国传教士倪德隆用南门外的教堂余房,建立“仁爱医院”,因其院长、医生都是修道士,当地人们又称其为修道院。该院分住院和门诊两部,有医生5人,病床85张,大病房2间、小病房3间。“这是最早建于该地区的西医院,也是康区最早的西医医院,西药业便从此在康区发展起来。”[6]
刘文辉在康区施政时期,极力推动并实施科教文卫改革,对于推动康区医药卫生的近代化发展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加之,随着教会医院的发展,西医药的影响逐渐增大,为后来康定乃至康区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促进公共卫生观念的转变
康区民众之所以能够快速地接受天主教这种异域文化,跟天主教兴办教会医院,带来公共卫生新知识有很大关系。
在传教士没有将西医药带入康区之前,人们感受不到对医药的迫切需求,但一旦见证过西医药治疗疾病的效果后,人们便不再逃避求医问诊。刘龄九曾说:“边胞生活苦,需要改善是事实,但边胞自己并没有感到这种需要;边胞文化低,需要提高是事实,但边胞本身也没有感到这种需要;边胞迷信深,需要有正确的信仰去纠正,也是事实,但边胞更感觉不到这种需要。惟有疾病的痛苦,死亡的威胁,使得边胞无法不感到医药救济的迫切需要了。”[7]
“解放前,康定县境广大农牧民,受封建迷信的影响很深,一有病痛则问于巫师(端公)、巫婆(观仙婆)等,在城内有的人家则请端公给病人打保符,跳绳念咒经,叫病人戴符,服神水治病。”[8]如康定金玉坛以抉占为病人治病,抉占人是通医术的,他们按病处方来开药,却托为神赐,以此愚弄病人。而在康定的木雅地区,地理位置偏远,文化十分落后,广大民众群众深受鬼神观念的影响,再加上家境贫困,生病也无力进行医治,有病则是去寺庙求神拜佛,请喇嘛念经。
妇幼疾病在康区尤为普遍。人们长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视妇女生产为肮脏之事,认为在室内分娩会污秽神佛,招来灾祸,故常在牛圈内生产,又无产婆帮助,常发生产褥热和其他妇科疾病,危及产妇健康和生命;婴儿发生破伤风死亡者也不少。危及儿童身心健康和生命的疾病还有天花,由于缺医少药,加之迷信鬼神,小儿患此病则听天由命,多不治而死。
当时因小病死亡的人不计其数。1906年前后,木雅地区近半数的人口因患伤寒致死。迷信鬼神的传统医药意识,使得康区许多人认为“夭寿在乎天命”,还没意识到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的生命。
传教士在给病患治病的过程中,使用西医的诊治形式,注射器等西方医疗工具让藏民满怀恐惧,抗生素、麻醉剂等的神奇功效却又让他们惊叹不已,对西医及传教士的印象因此有所改观。尽管习俗、观念等相异,但因缺医少药和现实需求,使得西医在此时具有很强的文化穿透力[9]。
康定地区的公共卫生状况十分差,“普通民众对于卫生常识一无所知”[10],在解放之前,折多河沿岸有许多私厕,人们将生活垃圾随意扔入河中,导致河水细菌滋生。但是,人们又将该河内的水用做饮水,用来洗米、洗菜、洗衣等。由于卫生意识的缺乏,眼病、天花、麻风病、鼠疫等许多传染病爆发,导致很多百姓无辜死亡。此外,康定地区的卫生防疫措施也不到位,对于一些患传染性疾病如麻风、天花等的患者,不将病人隔离开来进行治疗,而是将他们逐离家庭活动范围,任其自生自灭。
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医院成为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和开展的中心[11]。传教士向当地民众宣讲饭前洗手,不随地吐痰,不喝生水脏水,不吃腐烂的食物,勤洗澡等基本卫生知识。先后在康定南门附近、康定金汤和驷马桥等地建立了麻风收容所,并对症治疗,施以饮食。
虽然天主教的这些行为多是为传教服务的,具有十分强烈的目的性,并且他们传入康定的时间尚短,影响有限,甚至在传教过程中还出现传教行为与教条教规相矛盾的地方。如仁爱医院成立后,一些教徒请求设置产科,而“守贞是天主教的重要宗教修行之一”[12],这导致即使是女性修道医生,都是未出嫁的贞女,她们不愿为人接生,因此,产科病房在该医院久久未成立。“直至1946年,在多数教徒的请求下,报经教会批准,修道可以为人接生,才增设产科病房。”[6]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康定民众的医疗卫生意识,让他们开始改变一些落后的卫生观念和行为。
3. 推动藏医药的改革
在天主教传入康区之前,该地区只有藏医和少数中医药铺、诊所。康定的藏医多数习医于西藏和德格,其来源局限在少数的喇嘛和贵族之中,主要是为上层人士服务的。据《康定县志》(1995年版)记载,康定藏医主要分布在折多山以西的木雅地区(今营官、沙德、塔公3区),在民间行医者仅7人,折东的康定城镇只有1人。同时,藏医对藏药的辨认技巧及炮制方法,除授予学徒外也并不对外传授。虽然民间在医疗方面也不乏传统的“土方子”,但带有投机性和偶然性的治疗方法往往也不能根本上做到对症下药。在这样一种缺医少药、救治对象有限的情况下,广大的农牧民很难得到相应的医疗卫生服务。“这也造就了藏民的一个传统,当他们患上某些疾病后,首先会请喇嘛为其占卜,以确定疾病原因,而确定该念什么经,再按占卜所说请人念经、敬神、送鬼以及求医。”[13]
天主教传入康定后,建立仁爱医院,免费为当地贫苦大众看病,对需要住院的病人免收其医药费、住院费和伙食费。西医施用的药品相对于藏药和中药来说,见效快、疗效突出,康定天主教医院“每月就诊者数百人,康定无良好中医,恃此而活者,年亦数百人。”[14]这使康区民众对西医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后来包括康定在内许多地区的农牧民甚至部分喇嘛对西医的信赖度要超过藏医,感冒发烧等采用西医治疗,除非像胃病等西医无法根治的慢性病,才会采用藏医的治疗方法。传教士对来就诊的病人,尤其是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病人和影响广泛的病例,必然尽最大的努力为其治疗,将其治愈,“以收治好一人一病,收一村一寨之效。”[15]
作为一种外来势力,天主教的这些做法势必会对当地社会产生冲击。“地方僧俗则以审慎的眼光考量着‘洋喇嘛’们的到来,并在现实宗教利益、政治利益以及经济利益的主导下,对洋教的冲击进行回应。”[16]尤其是那些与藏医藏药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喇嘛和上层人士。天主教宣扬的宗教思想,更是触及了他们所构建的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是他们所最不能容忍的。喇嘛们不满洋教挑战自己的宗教权威,以自然灾害为借口引导藏民驱逐传教士,“暮春即酷暑难耐,麦苗枯槁,七月山荞未刈,即遇严霜,使小民终年辛苦无颗粒之收,当差百姓差务照常供支。有出无入,民不聊生,群疑满腹,互川传说,均以教士作祟,无不痛恨洋人,此教堂之所由毁也。”[17]但是,喇嘛们和上层人士对于天主教的排斥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的,西医的传入使传统藏医的弊端日渐暴露,西医与藏医并存于藏区,两者相互竞争,间接推动了藏医药的改革。后来,藏医技术不再只是为喇嘛和上层贵族服务,而是更多地服务于大众。
4.为康区卫生事业现代化奠定基础
整个康区原有的医疗卫生事业都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据州统计局资料显示:至1950年,康区的医疗机构仅有2个,普通病床的人均占有率极低,总床位共15张,医药卫生人员十分稀缺,共有19人。1951年8月中旬,天主教革新委员会请求人民政府派人协助接管仁爱医院。当时医院有病床15张,工作人员11人,包括6名卫生人员。该院被接管后更名为“康定革新医院”,并于同年9月1日正式恢复诊疗业务。1953年,改建为康定县卫生院。1956年更名为康定县人民医院。仁爱医院的医药卫生资源,是当时整个康区所有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由政府接管该院,既可以让原有医务人员继续从业,又可以使医院病床、仪器等资源不被浪费。不仅如此,教会医院的管理经验也为后来康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了一定参考。
综上,教会医院作为医务传教的产物,为康定创办现代医疗机构提供了经验。教会医院作为一种资源,本身又为康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结 语
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播为当地民众带来了一些西方医药知识,随着这部分知识的渗入,打破了人们固有的观念和传统的思维模式,使得整个康区的医药卫生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传教士“医务传教”的方式不仅为康区西医和现代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还对提高康区民众的医疗卫生意识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推动了藏医药的改革,进而影响了康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基于对口述史料的文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