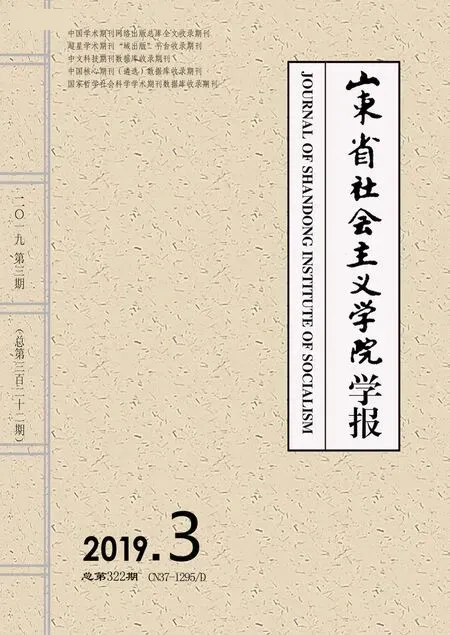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民族政策比较分析
孙 军 余文兵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标志着国共两党首次合作的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从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历时三年半。期间,基于双方各自的利益考量和共产国际的努力协调,国共两党在主要政治诉求方面趋于接近,但在民族问题上仍存在着明显差异。
一、国民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下文简称《国民党一大宣言》)被视为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正式形成的纲领性文件。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接受了“民族平等”思想,提出要扶持国内“弱小民族”实行“自决自治”,并且公开宣示“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目标和“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这不仅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升华,也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立场。
近年来,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学界普遍认为,《国民党一大宣言》是在孙中山政治顾问鲍罗廷主导下起草的,主要内容来自于共产国际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但是这份决议关于“三民主义”的解释,特别是对当时中国民族问题的政策设计和路线干预,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与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相悖,包藏了苏联国家利益的私心,不仅在国民党内引发激烈争论,也引起了孙中山的强烈不满和明确反对。
孙中山的民族思想经历了一个随时局变化而不断调整的过程。早年孙中山基于满汉对立立场,倡言“排满建国”,提出要通过“民族革命”来“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1]。这一时期,孙中山是以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解释排满革命运动,将民族看作是“血缘、语言、文化、地域”基础之上的概念。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民国政府接受了立宪派倡导的“五族共和”理念,并将其作为维系国家统一、建立共和国家的政治纲领。孙中山也认可这一主张,并在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到访北京,发表了一系列支持“五族共和”的演讲和谈话,为实现“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而积极奔走呼吁。但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蒙古、西藏分离运动有加剧之势,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与瓜分也愈演愈烈,加之北洋政府逐渐背离民主共和精神,致使在1920年前后,孙中山转而对“五族共和”主张采取批判态度。孙中山认为,民国建立以后,国家之所以四分五裂,很大程度上在于采纳了“五族共和”之说。这一时期,孙中山受到美国解决移民和族裔问题的“熔炉”模式影响,并结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国情,对以往民族思想做出了重大修正。在他看来,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很低,应当学习美国经验,以汉族为中心,在“民族同化”和“融合”基础上,“把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进而把中国建成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2]。
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革命,就在孙中山依靠地方军事势力反对北洋政府的努力陷入困境之时,孙中山决定与苏俄方面展开政治合作,并汲取苏俄经验,着手改组国民党。然而在民族问题上,国民党立场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要求相距甚远。特别是在民族自决权落实问题上双方立场尖锐对立。共产国际方面要求国民党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原则,而且告诫国民党“不要忙于”同少数民族“建立某种组织上的合作形式”。对此,国民党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以致在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期间,双方围绕“民族自决权”多次发生争论。甚至在宣言发表前一天,孙中山还紧急约见鲍罗廷,要求收回草案。但是为了争取苏俄援助,在综合考量利益得失之后,孙中山还是做出让步,原则上接受了由鲍罗廷主导起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而只是在文字上做了必要的修订。
国民党之所以会在民族问题上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存在分歧与争论,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国民党基于自身阶级立场,并不认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对苏联和共产国际宣扬的阶级斗争始终心存顾虑。孙中山在国共合作前夕的多场演讲中反复强调,国民党旨在学习苏俄革命精神,而非采用苏维埃制度,以打消国民党人顾忌。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表演说,向党内同志解释,国民党以往革命屡遭挫折,原因在于“专靠兵力,党员不负责任”,及“尚未有良好方法”。联合苏俄只是“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而非“主义”[3]。甚至在国民党一大闭幕式上,孙中山仍然提醒与会代表,“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4]。由此看出,国民党“以俄为师”进行改组,只是在工具层面对苏俄理念的借用,绝非制度的照搬移植。
二是国民党对苏联方面以“民族自决”为名染指中国边疆心存警惕。应当承认,《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更多体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意志及对中国边疆领土的私心。从冷战以后逐步解密的大量历史档案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共产国际通过的若干涉及中国问题的决议,以及国共两党的诸多文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具体到民族问题上,焦点便是外蒙古问题。自1911年哲布尊丹巴在沙俄支持下宣告“独立”以来,外蒙古问题便成为中俄之间的外交公案。“十月革命”之后,北洋政府由于内部军阀割据混战和派系斗争,错失收复时机。1921年7月,在苏俄支持下,外蒙古成立亲苏政府。于是从1922年开始,北洋政府与苏联方面围绕外蒙古主权问题展开外交谈判。在与北洋政府进行谈判的同时,苏联也积极寻求与国民党方面的政治合作。为争取得到国民党信任,打消孙中山顾虑,苏联代表越飞承诺苏俄既不向中国输出共产党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也“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5]。然而,苏俄方面的许诺并不令人信服。就在《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签订生效不足半年,外蒙古即在苏联支持下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仿照苏联制定“宪法”并允许苏联长期驻军。苏联方面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沙文主义立场,不仅使国民党对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动机和目的产生了怀疑,也给党内右派提供了攻击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政治口实。由于中共二大、三大提出少数民族有实现民族自决的权利,国民党右派抓住机会大造舆论攻势,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维护俄国人的利益”,进而要求改变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受到严重动摇。
三是不满苏联和共产国际要求国民党放弃对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国际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解释为“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因此要求国民党“不要忙于同这些少数民族建立某种组织上的合作形式,而应暂时只限于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随着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再建立组织上的联系”。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则表述为“自当随国内革命势力之伸张,而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至于具体期限,至少要等到“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再“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一个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6]。这样的要求,无异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对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这与国民党长期坚持的革命理念有相当大的差别,也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路线背道而驰,自然令国民党方面相当不满。
综上所述,《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表述,并不能反映国民党在此问题的真实立场,只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下,双方各取所需、相互妥协的产物。即使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人也多次利用不同场合宣讲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纲领,以澄清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提出的民族理论对党内和国人可能造成的影响。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
中国共产党对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认识,是在其革命实践中逐步深入的。党在成立之初,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当务之急是在城市立即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的统治。同时囿于活动地域,与境内少数民族接触不多,在民族问题上缺乏“很充分的材料”[7]。因此不可能对民族问题进行系统思考,也没有条件深入民族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伴随大革命风暴席卷桂、鄂、滇、川等多民族省份,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内民族问题有了认识。基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两党达成的合作方式,在国民党改组以后,中央党部的工人部、农民部实际上都由共产党人领导,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人也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或候补执委,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工农运动,也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党的民族纲领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及领导民族地区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国共合作的实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主张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时任共产党北方组织领导人的李大钊,便以国民党员身份,在北京《民国日报》上发表了《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一文,向蒙古族人民详尽阐释党的民族政策。文章说“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8]。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多份针对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在这些文件中,处处体现出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颁布的各类文件还多次提到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各项民族权利,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如1925年在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案中提出,“内蒙古农民中的革命工作……不应当掩没蒙古人的民族利益”[9]。1926年提出不要损害回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10]。
二是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对于号召少数民族共同参加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实早在国共合作之前,中国共产党便有目的、有计划地对乌兰夫、吉雅图等少数民族干部进行培养,但主要限于北京地区的蒙古族。国共合作以后,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在民族地区从事革命工作的汉族干部。1924年5月,黄埔军校成立,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选派了一批少数民族青年和来自民族地区的汉族青年。这些各民族青年在军校学习期间,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教育,并参加了北伐战争。此外,为加强民族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还在各地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包括蒙古、回、满、壮、瑶、朝鲜、土家等民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干部。
三是在民族地区建立革命组织,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革命斗争的开展。要加强党对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的领导,就必须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并建立党的组织。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在这之前,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尚未建立党的组织。于是从1925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派出大批党员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做掩护,到民族地区建立革命组织,开展建党工作。以内蒙古地区为例,1925年中共中央关于蒙古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国边境农工群众中的工作,对于我们的党,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内蒙古的工作”[11]。其实早在1924年,李大钊就在北京蒙藏学校发动成立了少数民族第一个党支部,培养了乌兰夫等一批少数民族革命者。国共合作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内蒙古地区开展革命工作,筹建共产党组织。经过艰苦的工作,在内蒙古很多群众运动高涨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为了更广泛发动内蒙古各阶层人民参加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还与共产国际配合,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坚持在内蒙古地区开展革命斗争。
总体而言,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关于民族平等、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教育和风俗习惯等的民族政策已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有所提及,但以纲领性论述为主,具体政策较少,理论上照搬经典作家论述的成分较多,受到苏维埃俄国民族工作实践影响较大。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的民族政策差异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在民族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政策主张,开展了一些开创性工作。但也都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留下了各自发展程度的印迹,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历史局限性。
20世纪20年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面临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即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对内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12]。国内民族问题则是民主革命问题的一部分。中国人民通过反对帝国主义革命达到民族独立和自主,而通过反封建民主革命则要实现国家统一。综观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期间的民族政策,在这一认识上态度一致。但在共识之外,也有分歧,主要表现为双方对中国境内民族问题现实根源的认识,以及解决民族问题的路径选择。
诚如前文所分析,《国民党一大宣言》的通过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国际对民族主义的解释,更不能代表孙中山接受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革命理念。而在民族问题上,其与共产党之间的争论也始终没有停止。双方分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民族自决权的理解。1922年中共在二大宣言中首次提出“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政策主张,即少数民族有实现民族自决和建立民主自治邦的权利。在1923年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民族自决”[13]。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以反对帝国主义入侵和军阀混战、支持民族自决权、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作为主要任务。因此,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是明确的。陈独秀、肖楚女、李大钊、瞿秋白等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都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只是囿于时代条件,没有对自决权的内涵作出具体诠释。国民党方面,虽然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将民族自决权写入政治纲领,但由于对苏联觊觎中国领土野心的忧虑,以及不满共产国际要求放弃对国内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导致国民党对“民族自决权”这一主张始终心存警惕。
二是对联邦制的看法。中国共产党依据斯大林民族理论与苏俄实践,认为“蒙古、西藏、回疆等处”“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依据经济不同”和“尊重边疆人民自主”的原则,“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14]。而国民党为解决民族问题所设想的路径则是国内各民族先团结,再融合为国族,进而共同奋斗,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而非联邦制国家。
三是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又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主张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中共四大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和“多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的目的是“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15]。共产国际则希望,“(国民党)应当理解,必须同工农国家苏联建立统一战线……必须使中国的解放运动同日本的工农革命运动和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发生接触和建立联系”[16]。鲍罗廷也极力向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应“同其他被压迫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及与我党有着共同目的……为争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而斗争的世界革命运动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势力的统一战线是必不可少的”[17]。而国民党基于民族主义立场,对于建立世界革命统一战线并不积极。早在孙中山与苏俄接触之初,即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制度”保持警惕。对于共产国际的建议,国民党表面“完全赞同”,但内心并不认同。特别是随着外蒙古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国民党对苏联方面援助中国的政治动机产生了怀疑,进而批评中国共产党因“幼稚”而“盲目模仿苏俄”,指责共产国际“不过是苏俄侵略之工具”[18]。
客观分析国共两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差异,一方面体现出两党根本不同之阶级立场,另一方面也是两党处在各自不同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党的领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社会民族问题的特点缺乏深刻了解和认识。因此在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民族政策时多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和苏俄经验,而且在提法上也有不成熟、不完善的方面。例如,只是提出了诸如“民族平等”等解决民族问题的一般性政治原则,并没有提出相应的具体措施;对“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等原则,也只是机械照搬,对这些纲领原则在中国的具体适用尚未有独立思考。后来历史也证明,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它忽略了列宁在论述民族自决权问题时特别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的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个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考虑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19]
对国民党来说,与苏俄的政治合作,并非基于共同的阶级立场和政治主张,而是基于双方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的现实考量,是凸显了功利色彩和实用主义的政治选择。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政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中国国民党在主张“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和“各民族一律平等”方面,与中国共产党持有相同立场,但对于给予少数民族绝对的自决权,以及建立联邦制国家则有所保留。
当然,在分析这一时期国共两党民族政策时,我们不能绕过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相关决议,不仅明显有悖于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论述,而且也对国共两党的民族政策以及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制度设计制造了一定的理论误区和负面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共产国际以“国际主义”为名,替苏联国家利益背书,甚至不惜牺牲他国主权的行为也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