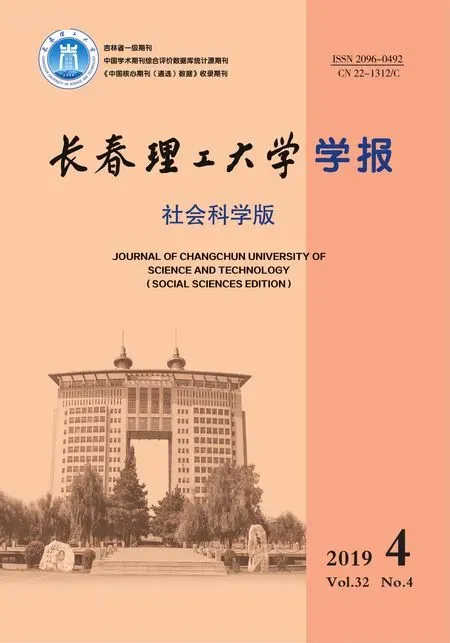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视域下的文化自信问题初探
孙 慧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一、文化自信何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十九大报告将“坚定文化自信”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并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坚定文化自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的理论自觉。文化自信何以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笔者认为可以从共时态和历时态两个维度予以考察。
首先,从共时态的维度来看,“坚定文化自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化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具有作为实践的根据、标准和尺度的重要作用。西方现代文化哲学的代表人物卡西尔将文化视为人的存在方式[1],认为包括神话、宗教、科学等在内的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差别,不是单纯形式和构成要素上的差别,而是不同实践方式带来的世界观的差别。例如,原始人所形成的神话观念,不是在原始人已经具有了现代人的科学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又为了丰富精神世界而创造的可有可无的艺术作品。在卡西尔看来,神话是原始人类借以把握世界统一性的全部的世界观,其全部观念系统是原始人类儿童需要从小学习才能掌握的,是原始人思想和行为的全部根据、标准和尺度。同样,科学作为现代人类把握世界统一性的重要方式,是在与神话和宗教的不断斗争中艰难确立其具有统治性的世界观的地位的。今天人们普遍以某某观点是否“科学”作为判断一种观念或行为是否具有真理性和正当性的标准。如今被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所拱卫的西方主流文化恰恰是以一种“价值中立”的“科学”面目出现,自视为衡量其他文化和文明进步与否的坐标,即与之相符合的才是文明的和进步的,反之就是不文明的和落后的。
因而,从共时态的维度看,文化作为人们在不同的实践方式中形成的内化于头脑中的世界观,作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是要使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人民普遍接受的,规范自己思想和行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2]。因为只有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民群众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现实实践活动的精神指引,真实地践行这些思想、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才能更好地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只有将文化理解为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才能理解“坚定文化自信”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其次,从历时态的维度来看,“坚定文化自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作为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的文化对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具有重大的反作用。马克思曾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对于二者的辩证关系,可以以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帮助新兴资产阶级确立起自身行为合法性的文艺复兴运动为例。文艺复兴在西方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但其从来不是与现实无关的单纯的文化观念变革,而是借助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形式来表达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主张。当时的商人和高利贷资本家构成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主体。可是当时的占统治地位的神权文化把放贷收息等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行为视为是严令禁止、大逆不道、要下地狱的行为。也就是说,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行为因无法获得主流社会文化的认同而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因而无法继续扩大其经济行为的范围,也无法在社会中获得统治地位。而文艺复兴运动中尊重人性的主张,对人的世俗生活、现实幸福的肯定,使新兴资产阶级通过放贷收息等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逐渐获得了主流社会文化的认可,即确立起其思想和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使得新兴资产阶级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成为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文艺复兴称为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同样,马克思·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从宗教改革的视度阐释了作为宗教改革众多方案中的一个分支——新教改革,如何因其教义中阐述的社会伦理(例如,社会中的个体能够增加社会财富是上帝乐于看到的事情等)与资产阶级追求不断增殖的利润的利益诉求不谋而合,二者相互拱卫,使资产阶级不断追求资本增殖的行为方式获得了主流社会意识的认同,获得了正当性和合法性,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及意识形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的生动阐释,也是展示社会文化形式与经济基础之间辩证关系的恰切例证。
因而,从历时态的维度看,作为社会意识、上层建筑的文化对于社会存在、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坚定文化自信具有巨大的实践力量,从而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需要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更要构建文化自信,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具有的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实现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资本主义文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
文化自信问题提出的背景恰恰是西方文化霸权现象,即西方主流文化以其自身作为衡量其他文化和文明进步与否的坐标。而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视域下,西方主流文化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文化,是与现实的资产阶级物质关系和经济结构相互拱卫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例如,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是“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质上是在资本逻辑统摄下资本增殖链条不断扩张,进而先发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到资本增殖的链条当中的进程。在这一全球化进程中,由于跨国资本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原材料等低廉的价格组织生产,并将其成品重新卖给发展中国家市场而攫取了巨额利润,从中“深受其益”。因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宣扬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等观念来维护其剥削发展中国家以获得巨额利润的资本循环模式。或者说,西方将集中体现在商品流通领域内的自由、平等等观念宣称为是普世价值,其实质是将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本身分离开来,不顾所谓普世价值思想得以生产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而使这些观念独立化的结果。这些统治观念之所以具有普遍性的形式,是因为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4]在此,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是作为遮蔽社会矛盾的意识形态工具而存在的。在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扬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产生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矛盾都被遮蔽了。
而马克思毕其一生所从事的理论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正是要揭露资本主义文化——包括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宗教、艺术等多种文化形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正如他写作《资本论》绝不是单纯为了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辩论,而是写给广大工人的,是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理论支撑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虚假本质。后者不是揭露了现实矛盾,而恰恰是掩盖了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现实矛盾,使无产阶级自觉自愿地走进劳动力市场并以低于自身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卖劳动力,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自身不断再生产。因而,这些资本主义文化本身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因素。
然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工作指出,对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绝不是将其斥之为虚假、错误的言论就可以将之否定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在于,它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视为合理的、必要的,作为人类朝向实现自由的过程的必然环节来再现。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各种形式,如文学、宗教、艺术、哲学等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萦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空的幽灵”。[5]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反映在资本主义文化中,但是这种反映并不是真实的,因为产生于一个特定的有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物质关系之中的伦理、政治、宗教和审美表述,将永远把这种统治描述为必要与合法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都强调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绝不是对资本主义物质关系的消极被动反映,不是只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就一并烟消云散,而是和资本主义现实生产体系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现实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在坚定文化自信的进程中,要想使资本主义文化彻底失去根基,需要像马克思那样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相互拱卫着的物质关系和经济结构进行双重批判。
三、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视域下的坚定文化自信的方法论初探
构建文化自信,说到底是构建或者说选择一种怎样的“标准”和“价值追求”作为人们实践活动中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性图景的深层根基,为实践活动树立真实的社会理想和合理的价值诉求,从而引导实践活动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在1853年至1862年间撰写的关于中国问题的18篇文章中,揭示了中华传统文化及其实践在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文明构建自身中作为“他者”的重要作用,当时处于前现代化时期的西方各国对于中国文化及其实践有着极高的评价,很多西方国家将中国文化及其实践的“标准”和“价值追求”视为合乎理性的先进文化及实践方式,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及其实践在世界文明领域的优势地位一直持续到近代时期。而文化自信成为问题,源于“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在体制的意义上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而在文化的意义上则是空前的价值观剧烈震荡的过程。”[6]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从“被动现代化”到“主动现代化”的过程,中华文化生态结构在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对撞中,并未趋同于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优势地位的资本主义文化,而是呈现出复杂的生态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信问题不是单纯的思想、文化等观念层次上的问题,在其深层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标准”和“价值追求”作为中国在现代化实践进程中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性图景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双重批判的方法论原则可知,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绝不是仅仅通过分析文化史、观念史的单一维度可以解决的,而应该诉诸于对资本主义文化及其深层根源的资本主义物质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双重批判,在对比中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及实践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需要补充的是,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当然离不开对市场和资本的利用,但绝不能任由资本逻辑及其文化表现成为统摄一切领域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具体来说,在马克思双重批判的视域下,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在揭露当代西方主流文化体系的核心概念、基本假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的同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与以资本逻辑统摄下的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通过前文阐释可知,资本主义核心文化理念与其现实运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文化理念的资本主义文化,在其现实运用中所导致的却是“反自由”、“专制”、“两极分化”的现实社会矛盾。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于“以人民为中心”,其价值追求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革命文化中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井冈山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思想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处处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内涵。当然,这里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内涵应在“超越资本逻辑”的原则下进行理解,即新时代美好生活不应是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主导下的对物、货币的无限追求,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下的,超越资本逻辑增殖内在要求统治的,以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对物质文化生活等多方面需求的满足。
另一方面,在揭露资本主义“一元现代化”道路陷入的文明困境的同时,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解决人类文明的当代形态带来的问题,超越人类文明的当代形态,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变革所具有的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主要是以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在全球扩张,从而把全世界纳入到资本增殖的逻辑链条下的全球化过程。然而,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一元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矛盾,使人类文明陷入困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及其实践,揭示了资本主义“一元现代化”并不是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唯一可行路径。以“超越资本逻辑”为内在要求的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的新发展理念对于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矛盾,构建“超越资本逻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大贡献。
综上所述,在当下,离开对“现实的历史”——当前占全球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文化表现资本主义文化的真理性认识,就无法穿越通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重迷雾,从而形成真实的社会理想和合理的价值诉求。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我们认清现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及其实践的“标准”和“尺度”的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