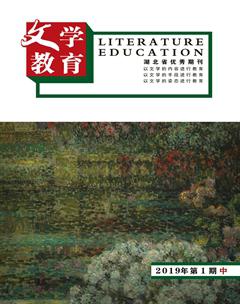奥斯汀小说中的乡村景观与英国议会圈地
姚颖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将奥斯汀的主要作品重新置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聚焦奥斯汀笔下以树篱和新农舍等乡村生活的新景观,阐述其作品中折射出的英国乡村在议会圈地运动中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剖析作家奥斯汀对这些改变的真实态度与想法。
关键词:奥斯汀 乡村景观 圈地
奥斯汀在“两寸象牙雕”上以真实而严谨的笔触描绘出摄政王时期的乡村新图景,将自己长期生活的乡村、出游沿途的景色、亲友们住宅的设计改建精确地描绘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尼克森(Nigel Nicolson)这样想象:“悠闲的旅行让简奥斯汀可以四下张望乡村和集市广场……她观察窗外掠过的城镇与乡村的房屋,将它们添置进自己脑子中对建筑风格的储备中。”[1]本文聚焦奥斯汀笔下的乡村景观,以树篱与农舍为例,展现奥斯汀笔下在议会圈地时期发生巨变的农村生活,并探究作者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真实态度。
一.树篱
圈地运动的规模在1760- 1815年间由于政府和议会的支持而迅速扩大,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结构,而且将地质面貌改变成一系列“数学网格”,因为圈地,确实就如字面意思,在土地周围筑墙、筑篱或是种树篱,将之与周围的地产区别开。莱恩(Maggie Lane)指出奥斯汀时期的圈地改变了英国的景观,漂亮的树篱框架将田地变得整洁。[2]奥斯汀表达了对圈占土地的线条和结构的美学审美,比起索瑟顿庄园这些呆板死气的高墙和铁栅栏,奥斯汀更喜欢在小说中描绘更具生机的树篱。
“草地的四周有高墙围着,第一块花木区过去是草地滚木球场,过了滚木球场时一条长长的阶径,再过去是铁栅栏,越过栅栏可以看到毗邻的荒地上的树梢。”[3]在1813年一月底写给卡桑德拉的一封信中,奥斯汀说:“如果你发现北安普敦郡是否是四处灌木树篱的乡村,我就会高兴了”(29 January 1813)。此时她已经着手写作曼斯菲尔德庄园有一段时间了,小说的场景就是在北安普敦郡。伍尔夫(Virginia Woolf)认为,由于奥斯汀对“真实性”的严苛,“当她发现树篱在北安普敦郡并不生长,她就删掉,也不冒险捏造不可能存在的东西”。[4]达克沃斯(Duckworth)也同意这一说法。[5]
事实上,北安普敦郡就是个灌木树篱的乡村。克拉格(Cragoe)发现北安普敦郡是被议会圈地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6]而议会法案明确规定圈地者必须建造篱笆与种植树篱来标识出圈占的土地。奥斯汀-利(Austen-Leigh)在后来的《回忆录》(Memoir)提到,“斯蒂文顿的美主要由树篱构成。在那片乡村,树篱不是一条窄窄的正式的树篱划分线,而是矮树丛与树木构成的不规则的边界,经常宽到可以容纳一条曲折的小径于其中。牧师居所之外两条如此的树篱向外扩展出去。”[7]故而,《曼斯菲尔德庄园》提到的“一排不像样的树篱”便可能是指的圈占的边界,因为从文中其它迹象表明曼斯菲尔德邻近的环境都是圈占的。第二卷还提到了两处树篱:法妮与玛丽·克劳福德坐在牧师住所的灌木丛时,此处已经变成了粗糙的灌木树篱;当亨利·克劳福德在描述他意外拜访的桑顿莱西时,也就是埃蒙德任职牧师后居住的村莊,见到“坐落在平缓山坡上的一个幽静的小村庄”,“前面是一条必须涉水而过的小溪”,除了“又大又漂亮”的教堂与“一箭之地”的“一幢上等人家的房子”外,“周围再也看不到一处甚至半处上等人家的房子”,田野里唯一可见的人却是在忙于修树篱。[8]亨利没有费神去问村庄的名字,而是提到“有人在修树篱”便认为这里便是桑顿莱西。
维修树篱的强烈隐喻让人想起华兹华斯的《布莱克大娘与哈里·吉尔》中的情节:
“对布莱克大娘来说,还有什么
比一道干枯的围篱诱人?
得承认,是有那么好几趟,
当她感到已冷到骨头里,
她便离开炉子或离开床,
走向那哈里·吉尔的围篱。
…
哈里实在是高兴,因为他看见
大娘一根根地抽着围篱;
哈里藏身在一丛接骨木后面,
等到她围裙兜得满满的。
她刚带着这柴火转过身,
想要沿着那小路走回去,
哈里猛地冲出来喊一声——
朝可怜的布莱克大娘扑过去。”[9]
在后圈地语境中,十分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从树篱里抽取柴火。树篱生长的很快,马丁斯(Martins)认为如果生长环境好的话,树篱七年以内便可“抹去”“公田的所有痕迹”。[10]范妮在格兰特太太的灌木丛中和玛丽聊天时,提到相关的时间跨度是一样的:“我每次走进这片灌木丛,就觉得树又长了,林子更美了。三年之前,这儿只不过是地边上的一排不像样的树篱,谁也没把它放在眼里,谁也想不到它会成什么景色,现在却变成了一条散步林阴道,很难说它是可贵在提供了方便,还是可贵在美化了环境。也许再过三年,我们会忘记—差不多忘记它原来是什么样子。时间的作用与思想的变化有多么奇妙,多么奇妙啊!”[11]
二.农舍
1882年由本特里公司(Bentleys)出版的首部奥斯汀小说全集将奥斯汀的形象与英格兰农村的建筑——乔顿乡村教堂和史蒂文屯牧师住宅的木刻画——联系起来。这种将“奥斯汀”与田园古宅相连的传统还传达了奥斯汀对乡村农舍的由衷喜爱。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奥斯汀主要描绘的农舍不是穷苦的农舍农的居所,而是达什伍德太太这样落魄乡绅阶层,或是埃德蒙·伯伦特等这样的牧师,或是韦斯特先生这样的新兴力量所居住的新农舍。虽然比不上庄园的豪华与现代,却也方便、舒适,功能齐全。
农舍在18世纪成为了“谦逊”的代名词。诗人圣—波尔·鲁(Saint-Pol Roux)曾言,“作为暴富农民的我忘记了城堡的初衷是为了以反题的形式向我揭示茅屋”,[12]这几乎就是奥斯汀小说中的情境。《劝导》中的厄泼克劳斯村有一座地主庄园和一座牧师公馆改建的农舍毗邻而立:庄园“高强大门,古树参天,气派豪华,古色古香,”保持着英格兰的古老风格;农舍“设有游廊、落地长窗和其他漂亮装饰”,同样引人注目。[13]《理智与情感》中达什伍德母女搬离诺兰庄园,来到巴顿农舍。从外观来看,农舍不仅象征达什伍德一家落难乡绅的新地位,而且从建筑上呈现了中贯穿的圈地的内在动态。奥斯汀对巴顿农舍的描述说明她充分意识到农舍是农村生活中阶级斗争的文化象征,:以约翰为代表的庄园主的圈地行径使很多世世代代依靠公田为生的农舍农生计难以维持,[14]他们被迫离开的农舍成为了追求别致景象的旅游者的追捧对象或者像达什伍德太太这种失势乡绅的新居所。
另外,农舍相对与庄园,是灵活设计的理想结构。这个时期英国的专业建筑师们,例如理查德·爱尔塞姆(Richard Elsam)、埃德蒙·巴特尔(Edmund Bartell)、波科克(W.f. Pocock)等抓住本土建筑风格来满足没有贵族血统但又有经济能力为自己获取相当舒适的生活方式。[15]巴顿农舍是一处方便、健全、现代的建筑,与其他粗糙、杂乱、古旧的农舍完全不同,但是还是会让住惯了大庄园的人觉得不够舒适,缺陷包括“房子造得太正规,房顶铺瓦,窗板没有漆成绿色,墙上也没有爬满冬忍花”。[16]达什伍德太太很快就有了改建计划,“可以把一个个房间装潢得更漂亮些”。[17]这充分反映了农舍的新主人所处的教养阶层不是要将农舍作为农民或是农村工人家庭的功能性居所,而是将其作为装饰性的建筑,也说明了为什么农舍在逐渐扩大的中产阶级中成为理想建筑的原因。而中产阶级正是奥斯汀小说的主要读者群。
同样重要的,农舍的相对舒适感给农村新乡绅阶级心理和生理的限制自我的居所。马尔顿(James Malton)是在《论英国建筑》(Essay on British Architecture,1798)中在比较观者对大庄园和农舍的反应比较时强调小空间影响心理膨胀。农舍隐藏在山谷之中,边界狭小但是令人感到平静的愉悦。当达什伍德家的女人们为离开恢宏的诺兰庄园的悲伤之旅接近尾声,映入眼帘的巴顿山谷令她们“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这地方景色宜人,土质肥沃,林木茂密,牧草丰盛。”“巴顿乡舍作为一所住宅,尽管太小,倒也舒适紧凑。”[18]如果达什伍德母女对农舍的喜爱和满意表达含蓄,小说中的先生们就更直白了。威洛比说巴顿农舍是“可以让人获得幸福的惟一的建筑形式”,[19]甚至声称要把他的产业按照这处农舍改造(55)。罗伯特·费拉斯说他极其喜欢乡舍,“这种房子总是那样舒适,那样幽雅。我担保,假如我有多余的钱,我就在离伦敦不远的地方买块地皮,自己造座乡舍,随时可以乘车出城,找几个朋友娱乐一番。我劝那些要盖房子的人都盖座乡舍。那天,我的朋友考特兰勋爵特意跑来征求我的意见,将博诺米(当时著名的建筑师)给他画的三分图样摆在我面前,要我确定哪一份最好。我一把将那些设计图全都抛进了火里,然后说道:“我亲爱的考特兰,你哪一份也别用,无论如何要建座乡舍”。[20]
显然,农舍成为有地阶级在乡村庄园和伦敦城市住宅之间的小站。克拉克认为,农舍的空间是幻像的空间,充满了夹杂着希望和幻想的不确定与含混,并加以真实的面纱;这也是隐藏着距离与不贞的私密空间,体验爱情、失去爱情的空间。[21]农舍的内外景观重塑也正是圈地运动在农业和情感上的趋势。
三.结语
树篱和农舍虽然在奥斯汀的作品中不如庄园那般引人关注,却同样是作者细致描绘出的英国乡村景观中的重要一笔。英国乡村在议会圈地运动中在政治、经济、社会阶层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奥斯汀虽然以男女爱恋婚嫁为主题,却通过乡村景观的细致描绘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变化,并隐晦地透露出自己地态度。
注 释
[1]Nicolson, Nigel. The World of Jane Austen: Her Houses in Fact and Fict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Ltd ,1991:14.
[2]Lane, Maggie. Jane Austen's England. London: Robert Hale, Ltd., 1986,pp.19-20.
[3]簡·奥斯汀[英]著,孙致礼译.曼斯菲尔德庄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79页.
[4]Qtd in Southam, B. C. Jane Austen: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2. 1987. London: Routledge, 2002,pp.242.
[5]Duckworth, Alistair M.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state: A Study of Jane Austens Novel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4,pp.33.
[6]Cragoe, Matthew. “Enclosure and the Church of England, 1700-1850.” Landscape and Enclosure. Oxfo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17 May 2008.
[7]Austen-Leigh, J. E. A Memoir of Jane Austen and Other Family Recollections. Ed. Kathryn Sutherland. Oxford: OUP, 2002,pp.23-24.
[8]简·奥斯汀[英]著,孙致礼译.曼斯菲尔德庄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07页.
[9]威廉·华兹华斯[英],黄杲炘译.华兹华斯抒情诗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6-27页.
[10]Martins, Susanna Wade. Farmers, Landlords and Landscapes: Rural Britain 1720-1870. Macclesfield: Windgather, 2004,pp.46.
[11]简·奥斯汀[英]著,孙致礼译.曼斯菲尔德庄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80页.
[12]巴什拉[法]著,张逸婧译.空间的诗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68页.
[13]简·奥斯汀[英]著,孙致礼、唐慧心译.劝导.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35页.
[14]Cottager农舍农是指以公田为生,不付地租,也不拥有自己土地的人.
[15]Park, Julie.“The Poetics of Enclosure in Sense and Sensibility”. Stud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ulture(42), 2013,pp.244.
[16]简·奥斯汀[英]著,孙致礼译.理智与情感.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8页.
[17]简·奥斯汀[英]著,孙致礼译.理智与情感.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5页.
[18]简·奥斯汀[英]著,孙致礼译.理智与情感.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8页.
[19]简·奥斯汀[英]著,孙致礼译.理智与情感.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63页.
[20]简·奥斯汀[英]著,孙致礼译.理智与情感.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47页.
[21]Park, Julie. “The Poetics of Enclosure in Sense and Sensibility”. Stud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ulture (42), 2013, pp.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