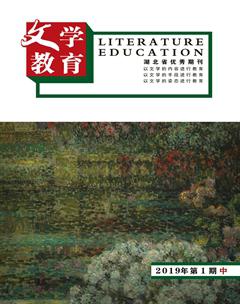北岛诗歌《触电》的一种解读
李宇涵
内容摘要:北岛《触电》一诗发表于1985年,深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诗人综合运用通感、视角转换、蒙太奇、超现实主义等艺术手法,表现出了一种悲喜剧意识。目前对北岛《触电》一诗进行阐释的文章大多都采用“传记式批评”或“印象式批评”。本文旨在通过借鉴新批评、阐释学、接受美学等批评方法对《触电》所体现的艺术手法及目前读者对其作出的阐释进行分析。
关键词:北岛 《触电》 艺术形式 文学接受
一.前言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做过建筑工人、编辑和自由撰稿人。其诗歌写作始于1970年,1978年在北京创办地下文学杂志《今天》,担任主编至今。自1987年起在欧洲和北美居住并任教。
《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诗歌卷》中评论北岛的诗歌艺术是这样说的:“北岛坚持了诗的独立品格,以现代诗学意识改造被腐化的中国诗学,将西方现代艺术的蒙太奇、变形等手法纳入诗学范畴,推进了中国现代诗在沉睡30年后的复活与繁荣,丰富了现代诗的表现手法,为中国现代诗重返世界文学格局提供了积极的努力,北岛是20世纪中国现代诗承上启下,走向未来的有力的一环,一座不可忽略的里程碑”(张同道等:《独自航行的岛》,载《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诗歌卷》)。
北岛诗的“质地”是坚硬的,是“黑色”的。他的诗有强烈的否定意识和批判精神。洪子诚先生认为,北岛之深刻不仅在于对所处环境的怀疑和批判,更是因其涉及人自身的分裂状况。以北岛的《回答》为例。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岛早期的诗歌流露着一种否定的、宣言式的诗情,坚定的、不妥协的意志。这贯穿在这个时期北岛的很多作品里。
北岛80年代以后的诗作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而不同于其早期作品。北岛说:“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已经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另外,我还十分注重诗歌的容纳量、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捕捉。”[1]
北岛的这种艺术主张充分体现在他80年代后的创作中。诗人运用多种艺术手法,“使他的诗在朦胧的底色上更呈现了错综、奇诡、扑朔迷离的味道。”[2]发表于1985年的作品《触电》正处于北岛诗歌创作的转型期,综合运用了通感、视角转换、蒙太奇、超现实主义等艺术手法。而目前对北岛《触电》一诗进行阐释的文章大多都采用“传记式批评”或“印象式批评”。本文旨在通过借鉴新批评、阐释学、接受美学等批评方法对《触电》所体现的艺术手法及目前读者对其作出的阐释进行分析。
二.《触电》的艺术形式
触 电
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我的手被烫伤/留下了烙印/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他们的手被烫伤/留下了烙印/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总把手藏在背后/可当我祈祷/上苍,双手合十/一声惨叫/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了烙印
我们首先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阐释此诗。全诗共三节,呈递进式结构。三节内部各由属于过去时间的动作形成瞬间连锁反应。第一节,由“我”和“无形的人”握手导致“我”惨叫、被烫伤、留下烙印;第二节,由“我”和“有形的人”握手导致“他们”惨叫、被烫伤、留下烙印;第三节,由“我”双手合十导致惨叫、内心深处留下烙印。纵向来看,第一节“我”与“无形的人”握手到第二节转为“我”和“有形的人”握手再转为“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第一节我的手被烫伤留下烙印,到第二节他们的手被烫伤留下烙印,再到第三节我的内心深处留下烙印,三次重复和转换使意义得到延展。
我们或许可以把“握手”解释成接触,接触即意味着建构。人生而被建构,烙印即被建构的标记,来自于无形;“我”又将其施于他人,人为自己建构,为自身寻找存在的意义。每一次建构,无论源于无形,亦或施于有形,无论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自觉的,皆是一次重构,烙上一标记。
北岛自身即注重用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分析文学作品,他说:“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好处是“通过形式上的阅读,通过词与词的关系,通过句式段落转折音调变换等,来把握一首诗难以捉摸的含义。说来几乎每一首现代诗都有语言密码,只有破译密码才可能进入。但由于标准混乱,也存在着大量的伪诗歌,乍看起来差不多,其实完全是乱码。在细读的检验下,一首伪诗歌根本经不起推敲,处处打架,捉襟见肘。故只有通过细读,才能去伪存真。但由于新批评派过分拘泥于形式分析,切断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最后趋于僵化而衰落,被结构主义取代。”[3]
(一)整体与通感
《触电》这首诗具有强烈的构成性,是整体与通感的。通感一般是把分属于不同“感觉域”的词或词组,通过特定的语法手段组合在一起,使核心意象的词义发生变化——感染上其他“感觉域”所特有的色彩,从而形成通感意象。
诗歌的題目“触电”就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官刺激。所谓触电,就是当发生人体触及带电体时,或带电体与人体间闪击放电时,或电弧波及人体时,电流通过人体与大地或其它导体形成闭合回路。人体触电时,电流通过人体,它的热效应会造成电灼伤,它的化学效应会造成电烙印和皮肤金属化;会对人体产生刺痛和痉挛;会干扰中枢神经的正常工作,造成呼吸停止、心室震颤。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会自然地把触电的感受带入其中,而如电流般的诗句也自然会给读者带来触电般的感受。
诗中“有形的人”或“无形的人”诉诸视觉,“握手”诉诸触觉,“一声惨叫”诉诸听觉,“烫伤”诉诸触觉,给人以痛感的想象。北岛将几组意象并置,给人不同的“感觉域”以触电般瞬间的刺激,最终刺激感由肉体进入灵魂,通过读者的想象深入内心,增强诗歌对读者感官的冲击力。
(二)三重角度
朱光树先生曾对此诗的三重角度做出过阐释,他认为,“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我的手被烫伤/留下了烙印”是从“我”对外界事物的感觉写的。“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他们的手被烫伤/留下了烙印”是从外界事物对“我”的感觉的角度来写的。“可当我祈祷/上苍,双手合十/一声惨叫/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了烙印”是从“我”对“我”的感觉的角度来写的。三种不同的角度:“我”、“无形的人”、“有形的人”虽然感觉的方位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留下了烙印”。从而表现了自我与环境、自我与别人、或自我本身所存在的矛盾。[4]我同意朱光树先生对此诗的三重角度做出的阐释。但是,我还以为,这三重角度最终还是指向了“我”的自在矛盾,“我”、“无形的人”、“有形的人”被烫伤都是由“我”来感知的。感觉的方位不同,实质也并非一样,烙印由“我的手”转向“他们的手”,最终转向“我的内心深处”,即感觉由自身的表层向外扩展,最终进入内心。这三重角度既是并置,也是递进,先扩张进而内化,层层深入。
(三)蒙太奇:组装意象
蒙太奇(montage),原是法语建筑术语,意即装配、构成,后来借用到电影领域,就是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剪辑,组接镜头的意思。蒙太奇是电影所特有的叙述方法,它是“借助于电影艺术而发展到极完善形式的分割和组合方法”。将蒙太奇运用于诗歌创作有利于更好地组合意象,以强化诗的强度和密度,使之产生审美多层次和多空间,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
洪子诚先生认为“镜头”即诗的意象,从而对北岛早期诗歌中的意象群展开分析。他提出了两组基本的意象群。一个是作为理想世界、人道世界的象征物存在的,如天空、鲜花、红玫瑰、橘子、土地、野百合等。另一个带有否定色彩和批判意味,如网,生锈的铁栅栏,颓败的墙,破败的古寺等,“表示对人的正常的、人性的生活的破坏、阻隔,对人的自由精神的禁锢。”[5]北岛早期的诗意象的涵义过于确定。到了《触电》这里,我们会发现其意象的设置与北岛早期诗歌有明显的不同。《触电》中的意象,如“握手”,所指不明,与日常生活和传统意象都有距离和阻隔,只给读者一模糊的感知,却难以找到词语明确地与之对应。
三组镜头呈现三个瞬间。三个瞬间不断出现手和手的接触、惨叫、烙印的反复。三组镜头的并置,就可以产生一种不同于它们单独存在时的涵义,也就是产生一种独特的新的质,从而使诗具有独特的深度和强度。此外,蒙太奇通过将核心意象集中于瞬间镜头,使意象产生瞬间性,再加以反复呈现,使意象处于高度密集的状态。这瞬间的感受往往是诗人对生活的高度忠实,是一种内化的真实。
(四)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的部分方法是把不寻常的性质归于平常的事物,使明显无关的事物、概念或词语互相遇合,以及任意使事物和环境的位置发生错乱。首先,我们先区分一组概念。约翰逊把玄学派奇喻(conceit)定义为“被强力枷在一起的……性质迥异的思想”。奇喻之有奇喻效果,正是依赖貌似异质的思想之间可以表明的而又符合逻辑的联系。他辨别出了感觉与感觉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对应或类似,并隐喻表达这一无形的关联浪漫主义意象因而斡旋在获得了灵感的知觉和传达这一直觉真实的需要之间。它是一种折衷的方法——表达无法表达事物的方法。但对于超现实主义者来说,意象不是不可名状之物。超现实主义作家不是获得了灵感,而是获得了激发灵感的东西。意象不是代表某种思想状态或强化的感觉。它是通过兼为手段与目的的那种跳板。正如勒韦迪在1918年所说:“意象纯系精神的创造物。它不可得自比较,而可得自两种或多或少相去遥远的真实的遇合。这两种被结合的真实的关系愈疏远,意象就愈强烈——它就将具有更多的情感力量和诗歌真实。”[6]
《触电》一诗中的意象,即得自这种“相去遥远的真实的遇合”。“握手”、“双手合十”这种手与手的接触与“烫伤”、“烙印”在现实中的关系很远,但正是由于这两组意象“真实的关系疏远”,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官冲击。但北岛的诗与超现实主义作品不同的是,超现实主义追求的是无秩序的自由想象而北岛的创作仍是基于理性。
(五)标点的使用
标点符号作为一种语言事实,参与到现代文学的构建之中,却常常被忽视。北岛《触电》一诗中,只存在三个“逗号”,却隐去了其它标点。我以为,诗人并非故意地不用标点,而是有意地运用标点。在前两节中,诗人两次将“握手”分离出来,置于下一行之始,与“一声惨叫”并置,以逗号隔开。通过这种有意的安排,“握手”这一行为以及此行为导致的结果“一声惨叫”得到突出,使触电时电流通过体内的瞬间之感得以呈现,并因此将“握手”与“触电”联系起来。在第三节中,诗人将“上苍”分离出来,置于下一行之始,与“双手合十”并置,以逗号隔开。从文本呈现出的对“上苍”一词的突出,并将其与“双手合十”并置,我看到了一种反讽。当与他者的接触被“我”否定,我以“双手合十”这样一种祈祷的姿态诉诸“上苍”,诉诸一种形而上的价值,却是更深的痛苦,“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了烙印”。
三.对《触电》的文学阐释和接受
(一)阐释学
传统阐释学力求使解释者超越历史环境,达到完全不带主观成分的理解,而把属于解释者自己的历史环境的东西看成理解的障碍,看成误解和偏见的根源。赫施的客观批评理论就主张一切阐释以作者原意为准。实际上目前对北岛《触电》一诗阐释的文章大多都是“传记式批评”或“印象式批评”。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阐释不只是一种诠释技巧,他把阐释学由认识论转移到本体论的领域,于是对阐释循环提出新的看法。在他看来,任何存在都是在一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的存在,即定在,超越自己历史环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我们理解任何东西,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的接受,而是用活动的意识去积极参预,也就是说,闡释是以我们已经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东西为基础。这种意识的“先结构”使理解和解释总带着解释者自己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成分,所以不可避免地形成阐释的循环。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的循环并不是一个任何种类的认识都可以在其中运行的圆,而是定在本身存在的先结构的表现”,它不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它是认识过程本身的表现。换言之,认识过程永远是一种循环过程,但它不是首尾相接的圆,不是没有变化和进步,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并不是摆脱这循环,而是以正确的方式参预这循环”。[7]
对于《触电》的阐释,读者大多会将其指向“文革”,将文本中的“我”与北岛本人联系起来。诚然,诗人北岛是在“文革”中生长的,他的创作自然源于他的社会经验和生命体验。文革的创伤对北岛影响之深远,从他的诗中即可见到。
“即使年轻的愤怒和伟大的进军已成记忆,但依然没有离诗人的生命远去,革命的伤口依旧会刺痛诗人的梦境,伤口就是革命在身体上所留下的烙印,而伤口上的盐依旧会加深这种记忆的疼痛。”[8]让我们来看一种较为普遍的阐释:
第一次握手对象“无形的人”似为虚指信念和理想。和理想“握手”后之所以会发出惨叫声,显然是十年浩劫信念被摧毁后产生的强烈痛苦情绪,即“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的反映。第二次握手对象“有形的人”则是现实社会及社会中的人。相对“无形的人”来说,“有形的人”似容易接触、亲近,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月,现实显得丑恶而冷酷,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乃至仇恨,无关心人、爱护人的情感可言,所以“握手”后发出的仍然是“惨叫”声。之所以写“他们的手被烫伤”而不写“我的手被烫伤”,一来是为了不和上句重复,使语句有变化,另方面“我”在那个年代里,也不可能超时代不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群众斗争中很可能伤害过别人。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我”只好向神灵祷告。祷告时“双手合十”,所发出的也仍是惨叫声。这反映了“我”内心矛盾无法克服的痛苦,以及由痛苦带来的孤独情绪。[9]
《触电》的情景确实可以与现实形成对应,北岛在他的散文集《城门开》中回忆道:
我曾很深地卷入“文化革命”地派系冲突中,这恐怕和我上的学校有关。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考上北京四中,“文革”开始时我上高一。北京四中是一所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我刚进校就赶到气氛不对,那是“四清”运动后不久,正提倡阶级路线,校内不少干部子弟开始张狂,自以为高人一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公开信就是四中的几个高干子弟写的,后来四中一度成为“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一个极端的老红卫兵组织)的大本营。我们也组织起来。和这些代表特权利益的高干子弟对着干。
但上述阐释中,仍有几点疑问,“无形的人”与“有形的人”所指不明,“握手”意象是否就可以与表示亲近关联,“我”祈祷的对象是什么,又为何要以“神灵”填充空白?读者在阐释过程中是一定要找出与之对应的词语。这种阐释文本是由词语构建的,读者自身以及词语的限制最终会导致阐释的差异。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受意识的“先结构”所制约
(二)接受美学
波兰哲学家罗曼·英伽顿认为文学作品的本文只能提供一个多层次的结构框架,其中留有许多未定点,只有读者一面阅读一面将它具体化时,作品的主题意义才逐渐地表现出来。英伽顿分析了阅读活动,认为读者在逐字逐句阅读一篇作品时,头脑里就流动着一连串的“语句思维”,于是“我们在完成一个语句的思维之后,就预备好想出下一句的‘接续——也就是和我们刚才思考过的句子可以连接起来的另一个语句”。换言之,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本文的信息,而是在积极地思考,对语句的接续、意义的展开、情节的推进都不断作出期待、预测和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读者不断地参预了信息的产生过程。而激发读者的想象,就靠本文中故意留出的空白。
伊塞尔认为文学作品有两极,一极是艺术的即作者写出来的本文,另一极是审美的即读者对本文的具体化或实现,而“从这种两极化的观点看来,作品本身显然既不能等同于本文,也不能等同于具体化,而必定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读者的作用根据历史和个人的不同情况可以以不同方式来完成,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本文的结构允许有不同的完成方式”。“暗含的读者”作品本文的结构中已经隐藏着一切读者的可能性。[10]
我认为以伊塞尔的介于两极之间的观点看待对北岛《触电》一诗的阐释是合理的。《触电》文本至今的阐释之所以大多指向文革也是由于阐释者与文本产生的间隔不长,文革作为民族的创伤还在隐隐作痛,人们通过回忆来感知伤痛。但文学作品之能超越时代,不仅在于其对特定时代的反映,还在于时代的伤痛逐渐消褪后,文本所剩余或增生的意义。
四.北岛与现代主义诗风
北岛为中国新诗的现代转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诗自诞生以来,先后有象征主义和诸种现代主义的引入和实验,但大多仍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抒写。建国以后,50、60年代“颂歌”风行,文学艺术价值不高,“文革”期间,诗人食指的出现尽管对一代青年产生了深刻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心理层面上的。食指的诗基本没有脱去浪漫主义的基调。“在《今天》派诸诗人中,应该说,只有北岛才是最早步入现代主义诗歌的轨道,并以其无可怀疑的现代诗歌的创作实绩开启了现代主义的诗风的。”北岛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因素源自荒诞年代对诗人现代主义意识的激发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
北岛尽管是“朦胧诗派中最早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诗人”[11],但是北岛的诗并非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简单移植,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诗歌有明显的不同。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曾对这二者做过比较:“现代诗从坡的时候起即被理解为‘纯诗,照雨果·弗里德里希的说法,它是独立的、自成一格的,与其它事物无关,它首先是语言而不是对外物的描摹。然而这些定义都不适合北岛,因为北岛笔下或者以‘我,或者以‘我们为面目出现的抒情主体,都带有强烈的道德化倾向,都在追求人和社会的真理,在整理自己掩埋在文革中的经历,并对这段历史的本质进行着思考。”[12]这表明,北岛是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而进行创作的,他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中引入某些因子,而非亦步亦趋地模仿。
参考文献
1.北岛:《时间的玫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2.北岛:《履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聯书店,2015年.
3.北岛:《城门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4.北岛:《谈诗》,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1985年.
5.毕光明,姜岚:《艺术之光照彻心灵——北岛谢冕会谈记》,《批判的支点 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
注 释
[1]北岛:《谈诗》,老木编《青年人谈诗》,1985年,第2页.
[2]赵敏俐,吴思敏:《中国诗歌通史 当代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37页.
[3]北岛:《时间的玫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5页.
[4]宗鄂:《当代青年诗100首导读》,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
[5]洪子诚:《北岛早期的诗》,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18卷.
[6]比格斯贝:《达达和超现实主义》,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年.
[7]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93页.
[8]吴晓东:《文学的诗性之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273页.
[9]古远清:《海峡两岸朦胧诗品赏》,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00页.
[10]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96-197页.
[11]赵敏俐,吴思敏:《中国诗歌通史 当代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40页.
[12]赵敏俐,吴思敏:《中国诗歌通史 当代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