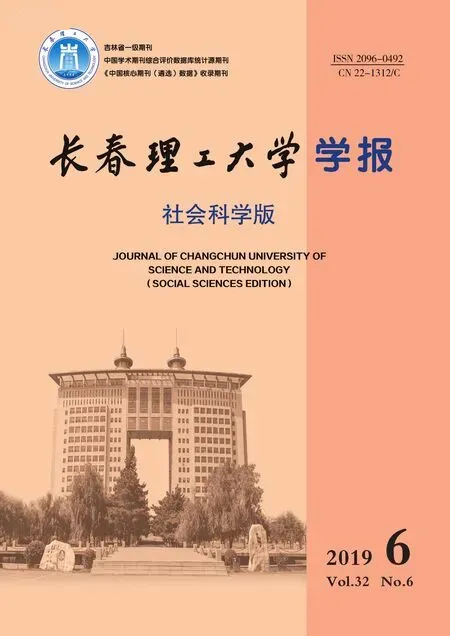从“回避”到“超越”:论《金罐》的怪诞风格
黄 峰
(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泰安,271000)
和德国19世纪早期浪漫派诸如海德尔堡派、耶拿派等代表作家相比,E.T.A.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1776-1822)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其创作风格颇为另类,连海涅这样的大作家也认为“霍夫曼到处看到的只是幽灵鬼怪,……他的作品只不过是一声长达二十卷的可怕的惊呼怪叫。”[1]102-103以小说《金罐》为例,作为一部充满玄幻风格的叙事性作品,它讲述了大学生安泽穆斯一连串混合着现实与幻境的成长之旅。由于文本中有着各式夸张离奇、神秘可怖的意象,单从叙事风格上来看,《金罐》确实显得十分怪诞。但正是这样的风格本身,或许才真正暗示着霍夫曼的小说创作具有与众不同的内在旨归,召唤着读者对其进行更深入的透视,而不是仅仅停留于对外在风格的判断。
一、怪诞风格的体现:复调式叙事
小说《金罐》从安泽穆斯撞倒一位老太婆开始全文的叙述,并勾勒出他所经历的一系列离奇事件。这一过程中,文本中各式人物都有自己的想法或计划,夹在他们中间的安泽穆斯就像海浪中的一叶小舟,既不断地游走于现实与幻境之间,也不断地游走于各种观点与声音之间,“代表不同立场的人物的声音始终处于持续的动态与张力中。”[2]整个文本就像是一个有着众多暗门的叙事迷宫,安泽穆斯无论选择何种声音或计划,都会将故事结局导向不同的方向。可见,霍夫曼并没有将文本叙事设计成封闭的整体,而是力图将各种可能性予以呈现。就此而论,《金罐》既可以被视为安泽穆斯作为一名大学生的社会成长记录,也可以被视为不同角色展现各自观点的呈现记录,它采用了典型的复调式叙事手法。换言之,复调手法的使用是导致文本风格怪诞的主要原因。
复调(polyphony)最初来源于音乐领域,是指乐曲没有主旋律和次要旋律的区别,所有旋律都按照独自的音调进行,这样就形成了多旋律的复调式音乐,有着不同于单一曲调的音韵效果。苏联文论家巴赫金将其引入文学批评领域,认为与传统“独白型小说”相对应的即是“复调小说”。独白型小说之所以是独白的,根源在于所有人物与事件都是作者在统一写作意愿下的被动呈现,都是作者思想的客体性载体。虽然文本有着丰富的人物形象,但却不会独立于作者意志之外,只能构成拥有统一声部的独白作品。而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则因拥有各自独立的声调或思想意识,彼此之间具有同等的表述地位,并不会被相互取代或压抑,亦没有被统摄于作者的统一意愿之下。在众声喧哗般的复调背景下,每种声调都是一种独立的主体,并呈现出独立的思想意识,此时的复调小说充满了对话性,不再是封闭的文本。
以此观点来看,《金罐》无疑采用了复调式叙事手法。首先是叙事视角的不断转变。几位主要人物都具有与众不同的个性化思想,但文本叙述时并没有暗示或排斥某一角色,也没有强调哪一种声音或观念是正确的,只是对它们有着共同的书写。当安泽穆斯进入玄幻世界,并不断自我诉说时,世俗世界的各色人等没有给予任何的理解,反而对此有着不同的态度:弗洛尼卡为了实现想象中的宫廷枢密顾问夫人的美梦,力图借用外力促成安泽穆斯对她的好感;鲍尔曼副校长则力图将其从疯癫中拯救出来,使之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正常人;赫尔波兰特文书则不断出谋划策,既迎合副校长的观点,又暗中算计着自己的好事。每当一位人物展示出自己的想法时,整个文本的叙事视角也就以其为主,此时的安泽慕斯并不能被视为主人公,“主人公”随着复调而在不断换位。
其次,处处可见二元对比。《金罐》采用了大量的二元对比技巧,以此营造出多元对立的复调效果。在人物方面,安泽穆斯面对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进路:现实与幻境,到底该选哪一个一直是他也是整个文本不断处理的问题,所以可见他游离于两者之间,经常性地自我对话、自我安慰以及自我否定。弗洛尼卡和塞佩狄娜是两个世界中的两位女性,前者是世俗的化身,是物质世界最直接的体现者,后者则是抽象的美善化身,居于形而上的灵性世界,彼此都在争夺安泽穆斯的好感。在处境方面,奇异而又充满诱人魅力的幻想世界与鄙俗而又功利的现实世界,在文本中不断地穿插出现,其频率之大以至于出现幻想与现实界限不清的叙事效果,如馆长到底是真变成鸟飞走了,还是安泽穆斯自己的幻觉。在细节方面,老太婆会变成门上的铜锁,馆长亦可成为副校长家里的咖啡壶,前者有猫作为帮手,后者则有鸟作为忠心随从。这些处处可见的二元对立环节无疑是复调手法得以成行的基本叙事空间。
第三,作者、读者的叙事狂欢。除了文本自身人物的多元声音外,霍夫曼在文本中先后四次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大发议论。这其中,霍夫曼不仅将自己的观点予以呈现,也力图将写作过程中的瞬时状态与具体想法直白地呈现出来。更为夸张的是,在最后一章,霍夫曼甚至取消了文学创作(虚构)与现实世界(真实)之间的隔阂,直接参与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林德霍斯特馆长居然知道霍夫曼写作的不易,并给他写了邀请参加宴会的信函。这种叙事技巧起到一种独特反讽的效果,霍夫曼或许在提醒读者要留意现实与幻境之间有可能存在的互通可能,也即留意到读者自身也有机会参与到文本叙事的可能性。而一旦读者参与到文本的叙述中,那么文本叙述本身也将充满了对话的张力。独白型小说所特有的作者权威必然会被破解,人物、作者、读者都处在一种动态的对话当中,文本叙述意义由此被极大地扩充了。
对于《金罐》而言,多种不同纬度上的众声喧哗,给同一个事件(安泽穆斯的成长经历)的呈现带来了多样的叙事视角。复调叙事的结果就是,使这一核心事件的定性有了多种的可能性,哪怕其中有些可能性(选择弗洛尼卡)或许并不是作者自己所希望的,但却是现实中可能大量出现的事实。毕竟更多的人是无法抵御物质世界的功利诱惑,而选择放弃或无视内心的灵性世界。因此,《金罐》采用的复调手法,在既保存现实可能的情况下,也为选择美善的形而上途径留下了一份诗意可能。
二、怪诞风格的诞生根源
分析小说《金罐》以及考察霍夫曼的整体创作实践,都离不开对19世纪早期德国社会现实的考察,尤其当其“创作深深扎根于现实基础之上时”[1]103。此时的德国,一方面与欧陆其他大国相比,依然处在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不仅没有统一的强力政权,也没有国内统一的经济市场;另一方面,德国国内敏感的知识分子虽然对现实十分不满,但面对1789年法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又表现出明显的畏惧和抵触心理,这种矛盾的心态自然在很多领域有所体现。因此,本文认为,霍夫曼创作上的怪诞风格并不是他的偶然为之,而是有着更深刻的诞生根源。具体来说或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文学内部原因,二是文学外部原因。
其一,文学根源,也即文学创作危机。德国文学在19世纪之前,一方面深受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则深受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影响,自身发展较为僵化,并没有多少创新之处,并不利于对本民族文化或现实的反映。因此,当德国传统文学在面对法国大革命冲击之时,也身处创作危机之中,即如何从传统的创作中走出来就成了当时德国作家创作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对此,19世纪早期德国文学(包括浪漫主义文学)具有普遍的形式创新特点,比如蒂克、格林兄弟等作家对收集整理童话、民谣等充满兴趣,史莱格尔兄弟则执着于强化文学创作中的宗教神秘因素,试图从中世纪宗教氛围中寻觅力量之源。同样,霍夫曼在创作手法上也是不乏创新之举。
在《赌运》中,霍夫曼采用了重复的手法,设置了三个叙事层,隐喻着赌运之于人类的不可摆脱性。在《雄猫穆尔的生活观》中,霍夫曼采用视觉对立的手法,将一只猫和一个艺术家的不同视角或经历交织在一起,起到了对现实中艺术家的不幸遭遇不断渲染的叙事效果。此外,霍夫曼通过对“献祭以撒”故事的象征性扩写,在《沙人》中进一步凸显了幼年创伤之于个体成年后的深刻影响。而在小说《金罐》中,正如上文所言,霍夫曼则最大程度地发挥了自己的虚构能力,将现实与幻境融合在一起,将神秘因素置入现实生活中,形成了光怪陆离的叙事效果。但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作技巧在当时文坛还并不被认可,不仅同时代的歌德、席勒等人评价甚低,就连批评家勃兰兑斯也认为“霍夫曼的命意则显得病态而古怪。”[3]173但在文本看来,这种怪诞风格本身,正是对传统文学创作的革新行径,虽然是带有非理性色彩的革新行径。
其二,社会根源,也即生存危机。德国社会现实的四分五裂,造成了国内社会的一片混乱,不只是敏感的作家,就是普通民众都会深深感受到生存之艰难。“1813年,霍夫曼在德累斯顿经历了多次小规模战斗和一次大会战;他亲临到战场,身受过饥荒和一次随着战争而来的瘟疫——一句话,这个时期所有恐怖现象丰富了他的想象力。”[3]162对于有良知的作家而言,如何起到帮助人们清醒认识现实、对陋俗进行革新的目的,就成了文学创作的关键。因此,生存危机倒逼着作家们采取文学突围的方式,用新颖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对当下德国文学的不满与革新企图,这既是现实危机下的一种出世态度,也是传统文学危机下的一种入世策略。不过,有关德国未来发展之路该何去何从,并没有统一的说法,社会上充斥着各式观念。就此而论,《金罐》中的复调式叙事手法或许正是对这种社会现实喧闹的艺术再现。复调下的叙事视角不断发生转变,不仅给《金罐》的结构层次带来了迷宫般的叙事效果,也包容着众多声音。由于文本叙事过程中,叙事视角一直在发生变化,带来的效果不仅有文本内部不同人物的个性化声音,也有文本外部包括作者、读者在内的共同参与。这样,整部作品就是一场大合唱,始终处在持续性对话中。这种对话不仅是有关文本范围内的情节发展之讨论,也是有关文本范围之外的创作思路之讨论,实质上都是对现实危机之大讨论的隐喻指涉。
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可以清晰地意识到怪诞并不是霍夫曼无意为之的效果。怪诞风格作为表述层面上的艺术形式,正是来自于霍夫曼对现实的极度不满与绝望,也来自于对传统德国文学身处发展困境的一种反思。但不论是何种缘由,很明显的是,怪诞代表着一种否定的思维态势,象征着对某种现状的超越行径。由此观之,文本中安泽穆斯对小绿蛇塞佩狄娜的选择之旅,虽然反映了外在世界对其有种种的误解、非议与阻挠,但也象征了安泽慕斯终不会被现实所彻底羁绊住。对霍夫曼而言,小绿蛇只不过是一种隐喻,一个可以远离世俗世界牵绊的具象化符号,而怪诞也不过是一种对抗现实的手段而已。整个文本叙事的关键,不在于呈现多维声音,而在于隐喻着任何个体在现世的嘈杂中,不论经过多少犹豫与反复,依然最终选择听从自我内心之灵。所以,虽然安泽穆斯(也包括霍夫曼)一时受困于不同的困境之中,但对当下困境的摆脱或超越,必然是其最终的旨归。
三、怪诞风格的真正旨归:超越创伤
“一则现代童话”是《金罐》的副标题,作为小说体裁的它为何用童话来界定自己,倒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般而言,童话不会直接传授什么大道理,更不会通篇充斥着道德说教,而会通过通俗易懂的故事和形象鲜明的人物演绎某一深刻的话题,擅长借用隐喻、象征等手法来实现作者的潜在意图。对于《金罐》而言,我们同样需要留意霍夫曼在童话这一层面的用意,他绝非只是虚构一则充满怪诞色彩的奇异故事,而应是言此意彼,有着更多的内在指涉。就此而言,本文认为,《金罐》有关安泽慕斯成长过程的叙事,是一则有关现代人期望可以克服创伤的象征性童话。
文本一开始就讲述了一段离奇的经历,安泽慕斯在着急赶路的时候,不小心碰倒了老太婆的苹果篮,后者因为苹果满大街的滚落,并被挤碎几个而愤怒不已。虽然安泽慕斯忍受着她的恶毒指责,也甘愿用自己为数不多的钱予以补偿,但老太婆还是对其予以诅咒,诅咒他将被关进“水晶瓶”中。虽然之后在很长一段内容中,都没有再提及何为水晶瓶,但由此次意外碰撞而带来的诅咒,却像是巨大的枷锁一样困扰着安泽慕斯,既导致他在此之后遭遇一连串令人不安的经历,也迫使他一直都力图摆脱诅咒以及由此而来的厄运。安泽慕斯自称“我真是一个生来就注定要经受种种不幸和痛苦的人啊!”,实际上是显示他从开始时就经历了精神上的创伤,这不仅深深伤害到了他的自尊,也使其长时间无法摆脱这一创伤体验(Trauma experience)。从创伤批评的视角来看,该文本是典型的有关创伤体验的书写。这一精神层面的创伤体验不会立即得到缓解或治愈,往往会潜伏下来,成为个体日后成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潜在因素。因此,本文认为文本有关安泽慕斯的后续情节,既可以说是一种成长过程中的选择之旅,也可以视为一种摆脱诅咒、创伤的治愈之旅。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在《论“诡异”》中具体分析了众多文本诡异因素的根源,认为“诡异”(Uncanny)一词最初来自德语unheimlich,而后者不仅包含让人感到熟悉、友好的含义,也包含隐藏的、神秘的语义。弗洛伊德认为不是不熟悉的事物导致文本具有诡异的色彩,而是内在潜藏事物的反复出现才是文本外在诡异的根源。“因为这种神秘和恐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奇或陌生的东西,而是某种我们所熟悉的、早就存在于脑子里的东西,只不过由于受到抑制而从我们的大脑中离间开来。”[4]据此而论,弗洛伊德提倡在心理层面展开对创伤的研究,反对将创伤仅仅视为一种肉体上的可以完全治愈的伤害,认为个体所承担的创伤体验不仅不能被完全治愈,而且会潜藏起来反复出现,并最终影响个体后期的成长。对具有鲜明怪诞风格的《金罐》而言,本文亦认为怪诞并非来自于离奇的想象力或穿越交织的叙事视角,而在于怪诞所包裹或所掩盖的源自生活的本真感受。简言之,怪诞并不仅在于创作手法上的创新性,还在于霍夫曼对创伤体验的不断再现。
结合霍夫曼的生平与创作经历可见,这种被潜藏起来、但又被反复再现的创伤体验,应有两类来源,其一源自小我,是作者本人成长经历中的不幸体验,这是一种事实性创伤;其二源自大我,是艺术家群体无法融于现实的不幸体验,这是一种象征性创伤。从小我的视角来看,霍夫曼如同笔下的安泽慕斯一样从小就遭遇不幸,“幼小的心灵接受的世界是不和谐的,它怪诞而恐怖。”[5]霍夫曼终身受此影响,并一直悲痛难忘[6],以至于成年后的他依然无法摆脱,始终都处在各式困境的侵扰中。可见,这种不断反复的创伤体验正是他怪诞式创作风格的内在根源。从大我的视角来看,身处社会陋俗环境中的霍夫曼,深刻地感触到艺术家之于生活的不易,往往只能在被误解、被排斥的边缘境地中发声,这也正是怪诞风格的文学外部根源。安泽慕斯在现实功利与精神自由之间充满犹豫,正是对现实中艺术家创作困境的一种隐喻,既离不开物质生活的支撑,又迫切地希望摆脱物质生活的羁绊,全身心地投入艺术领域的自由创作中。所谓艺术家小说系列的悲剧性就在于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某一个作家可以完全克服的。这对矛盾贯穿于所有有独创意识的作家的创作生涯中,成为他们一生中力图摆脱的创伤体验。正如对安泽慕斯而言,林德霍斯特馆长和小绿蛇塞佩狄娜,他们象征着艺术领域的召唤人,召唤着他克服外界的物质牵绊与功利引诱,投入纯粹的艺术领域。
创伤体验具有明显的不可摆脱性,但对于任何承受着创伤的个体而言,最终得以治愈创伤、恢复自我人性的完整性,是逻辑上的自然倾向。因此,无论创伤体验来源于何处,无论怪诞风格如何掩饰文本的内在旨归,对霍夫曼之类的边缘作家而言,通过虚构的文学形式达到超越现实中的各式创伤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正如文本中,安泽慕斯最终的选择是一种象征性胜利,象征着艺术对创伤体验(现实)的形而上治愈或超越,整个情节本身具有明显的仪式性。就此而论,透过小说《金罐》,我们既要看到霍夫曼对自身生存之不幸体验的不满以及渴望超越创伤的美好憧憬,也要看到霍夫曼对所有艺术家最终能够摆脱世俗物质世界的真诚期待。
不仅是《金罐》,也包括其他著作,怪诞确实是霍夫曼创作风格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但正如上文所述,怪诞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特点,它是对各式源自现实之创伤体验的一种隐喻性指涉。其中蕴含霍夫曼基本的叙事策略:从“回避”到“超越”的创伤体验。文本中霍夫曼明确说出自己的创作目的,乃是提醒众多读者要注意到“神奇国度”就在距离比我们以往所想象的要近得多的地方。这一“神奇国度”是包括作家在内所有艺术家都魂牵梦绕的超验世界。不光是文本中人物与作者本人,就连读者都可以看出现实的丑陋,理想无法在现实中存在,只能寄希望于诗意的超验世界。可见,霍夫曼宣扬的不是怪诞奇异的奇幻故事,而是通过艺术拯救现实的艺术拯救论,力图建构起乌托邦式的美好彼岸,一方面映照出现实的陋俗与卑屑,一方面召唤人们摆脱现实创伤的困扰,在超验世界寻找终极幸福。这样的拯救论虽然有明显的唯心与理性色彩,但却是霍夫曼(也包括德国19世纪早期其他作家)在无法克服现实困境之后的突围之举,也即,通过艺术领域的想象性超越来企及现实中的事实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