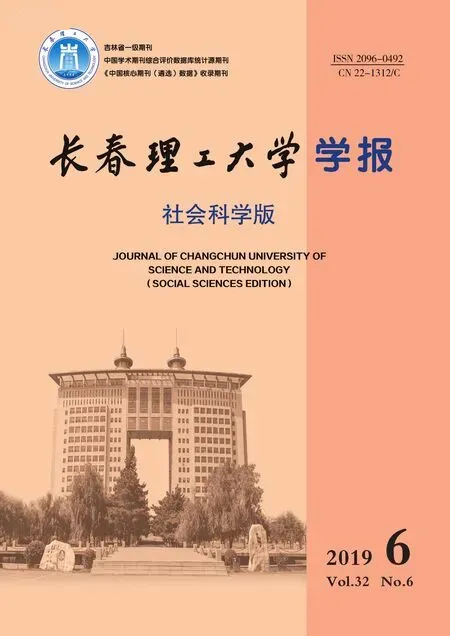尘世批判: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变革与超越
——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高 洁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是恩格斯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其廓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费尔巴哈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中还蕴含着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宗教思想的吸收与变革。恩格斯看到并承认了费尔巴哈宗教思想的“里程碑作用”,在汲取其思想内核精华的基础上回归世俗基础,对其进行深入批判、解构和重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系统成熟。
宗教问题作为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1]因此,在当前深入重温、研究《费尔巴哈论》的相关论述,有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思想武装头脑,进一步“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
一、从抽象虚幻到历史真实:恩格斯对人的本质的变革
在宗教思想上,费尔巴哈较之以往的哲学家有超越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进步意义。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把虚幻的宗教精神归结于一定的物质基础,从而“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3]228,消除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矛盾争端。恩格斯高度肯定了这部著作的解放作用,并指出在其影响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3]228可见费尔巴哈作为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对恩格斯宗教观念的形成有着独特影响。
费尔巴哈认为“上帝本身并不是别的,只是幻想或想象的实体,只是人心的实体。”[4]90在看到了上帝的虚幻性后,费尔巴哈便以心理根源为切入点,分析宗教的起源。他注意到,“人的信赖感,是宗教的基础”。[4]1费尔巴哈将宗教的最初形态——自然宗教作为分析对象,清晰佐证了这一观点。自然作为宗教的最初原始对象,与人类生存紧密交织。人一方面要依靠自然获取生存资料,另一方面又因其不可控而表现出敬畏、惶恐与崇拜之情。在谋生需求下,人产生了满足自我欲望的利己倾向,进而形成依赖感。为保证物质充足与心灵平和,尚显愚昧的人往往会将山岳、树木、河川、动物等自然对象奉为独立异在的“神”。而“神”,或者说是“上帝”,获取了人所投射的一切超人格、超自然的愿望与品质,并通过不断地“收缩”、“舒张”,致使人的本质反复“外放”、“回收”,最终凝结出高超特质。由此,上帝以其无限、完善、永恒、全能、神圣之特性成为“完全的积极者”,与完全消极的人对立、分裂,这也成为宗教的起点。因此,费尔巴哈认为,宗教“只不过是依赖感,只不过是人的感觉或意识”,[4]2自然、感性的人创造了宗教,为其宗教哲学打上了明显的人本学烙印。
“神学之秘密是人本学,属神的本质之秘密,就是属人的本质。”[5]349在厘清了宗教起源后,费尔巴哈进一步以异化概念来透视、批判宗教本质,认为宗教的秘密在于“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5]39也就是说人不断否定、剥夺自己的品质、本质,并将其让渡给上帝,最终成为对象化了的自身所操控的对象。归根结底,“对象所加于他的威力,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的威力。”[5]8简言之,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诚然,费尔巴哈将宗教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摆脱了唯心主义的牢笼,其进步性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但应当看到,费尔巴哈只着眼于人的自然性、生物性,忽视了社会性,仅仅是在抽象意义上直观地借宗教本质推导出人的本质,而非着眼处于特定历史中的人。因此,他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把许多单个人纯粹自然联系起来的抽象的类,认为其“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15可以说,费尔巴哈在迈出重回唯物主义的重要一步后便停滞不前,无法与现实世界相融。
在恩格斯看来,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3]237这恰恰是费尔巴哈无法看到的,也就导致其最终重陷于唯心主义的泥沼。由此,恩格斯指明了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方向,即用现实的人取代对抽象的人的崇拜,把“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3]247人们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思想意识也是不同的,这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生产关系。
恩格斯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自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3]260-261也就是说,人的观念的形成不仅受到对外部自然认知的限制,还依赖于外界社会关系对人这一“自然系统”的作用。恩格斯超越了费尔巴哈的观点,强调人是处于历史变迁中的具体的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具体来看,在物质生产匮乏的时代,人们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的高度支配。人的知识水平、交往关系尚不发达,由此产生对自然资源的崇拜,进而产生自然宗教。基于此,便容易只看到人受限于自然的感性、孤立和被动。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人们在生产实践中不断结成生产关系,继而时刻处于社会关系的交织包围中,生活方式据此改变。“神”或“上帝”的形象便逐步从自然物转化、蒸馏为社会人,其在神话故事中也成为与他者存在交往关系的形象。由此可见,人是历史、实践、具体的人,“不能单纯的在个体角度把握人的本质,而要把它放在社会关系中,通过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才能对宗教的本质有正确的认识。”[6]16
正如恩格斯所论述的那样,他批判地消灭了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的形式,但救出了通过这一形式获得的新内容。也就是说,恩格斯突破、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哲学,从历史实践、社会关系维度理解人的本质,并合理变革、纳入了其与宗教本质之间的关联。由此,恩格斯实现了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代替了费尔巴哈新宗教的核心——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筑牢了支点。
二、从天国批判到世俗批判:恩格斯对宗教异化的透视
费尔巴哈指出,“人越是剥夺自己,则上帝就越是低微、凡俗”,[5]41人所让渡的愿望、本质越多,上帝的“人性”就越显著,“神性”便相应弱化,反之亦然。应当看到,虽然费尔巴哈透视了宗教的本质,在当时有着极大的进步意义,但他对宗教的批判仍然停留在“天国”,没有完全落于现实社会。他认为宗教上的关系颠倒导致上帝和人之间产生了裂缝和间隙,出现宗教异化的现象。因此,只要摆正“颠倒”了的关系,就能打破幻觉,实现人的解放,进而看到“真理的纯净光辉”。要用“爱”、“心”等抽象情感征服上帝,让其放弃“神性”,最终实现全体和解、异化消除。很显然,费尔巴哈试图“以思想消除思想问题,以意识解决意识问题”。[7]可以说,费尔巴哈在打开了“人”这个缺口后,又退回到了唯心主义,其宗教异化观有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
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跳脱于现实社会之外。缺乏历史性。“人们的愿望是怎样的,他们的神便是怎样的。”[4]91费尔巴哈进步性地指出“神”其实就是人主观愿景的反映,某种程度上为宗教问题和人的异化找到了世俗基础。但是,人本主义宗教观让他无法看到具体的、实践的人,也就无法进一步追问:人们的愿望从何而来?费尔巴哈未曾发觉的这一问题,恩格斯提出并予以了解答。
恩格斯指出,人的愿望由社会存在决定。“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3]238显然,人们的思想以及思想形成的过程,归根结底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这就找到了行为的动力。宗教作为更纯粹、离物质生活最远的意识形态,同样由现实的经济条件和阶级关系决定。正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指明的,宗教的“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3]230但停留在观念的意识层面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还应找到意识、精神产生的原因。蒙昧时代中落后的物质生活条件制约了人的精神发展状态,导致当时的人们产生愚昧无知的观念。宗教并非直接产生于愚昧无知的观念,而是脱胎于导致此类观念出现的社会存在。
通过回顾民族宗教的兴亡历程,恩格斯发现“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3]261更为有力地证明了宗教对社会物质基础的依赖。随后,他以基督教为例,梳理了世界宗教的形成脉络,逐步撕开了阶级利益披着的宗教外衣,指出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观念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3]263-264挖掘出了宗教发展规律的秘密。深入来看则可以认为,发生异化的不是精神领域,而是现实的社会领域,尤其是生产领域。
天国批判由此转向尘世批判,恩格斯以“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劳动异化”的逻辑链条让费尔巴哈的缺憾得到了解决。恩格斯通过着眼于宗教改革,令国家、政治与宗教间隐含的关系变得明朗,展现了宗教异化的社会政治基础,揭露了市民社会对国家意志、法律、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扭转了以往认为国家决定经济基础的错误观点。当宗教高度渗入国家肌体后,为了动员群众参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3]262宗教事实上已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特质。恩格斯认为,当宗教进入它的最后阶段,就已无法成为进步阶级的抗争武器,而是堕落为统治阶级获取剩余价值、维护阶级利益的统治手段。“政治制度同时也表现为宗教制度,政治生活同时也表现为宗教生活,政治异化与宗教异化存在诸多相似之处”,[8]所以,要破除不合理的政治制度,让被异化的人成为真正解放的、自由的人。
正因对政治进行了批判,恩格斯继而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催生的苦果。在资本逻辑的催化下,货币成为最高的善,思辨、科学失去了培育热土,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3]265如此一来,对资本的迷狂逐渐“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正像他把工人的活动变成抽去一切活动的纯粹抽象一样”,[9]“人”彻底被降格为“物”。“人”日益被资本控制,与“物”不间断地相互拉锯、斗争,劳动终被异化。从某种程度上看,劳动异化与宗教异化也有共同点:人都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钳制,收获与付出呈现反比关系。为了彻底消除劳动异化,就应当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同理,为了让人脱离宗教束缚,就应冲破宗教樊篱。而这种观点,恰恰是幻想建立“爱”的宗教的费尔巴哈不可能提出的。可以说,恩格斯把对宗教的批判引入深处,到达了费尔巴哈不曾企及的高度。
三、从颠倒关系到颠覆神性:恩格斯对宗教幻觉的破除
费尔巴哈高呼:“宗教是精神之光”。[5]293他认为宗教是伴生于情感关系、天然存在的,“宗教是人之最初的、并且间接的自我意识”,[5]18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宗教是不可消灭的。在他看来,感情是人固有的本质,“是人里面的至贵、至优和属神的东西”,[5]13“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之道德上的各种关系,本来就是的的确确的宗教上的关系。一般说来,生活,在它的各种本质重要的关系中,乃具有完全属神的性质。”[5]350因此,费尔巴哈不赞成消灭宗教,而是致力于恢复、高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建立一种新的“爱”的宗教来代替过去的宗教,以此实现其完善和圆整。
诚如上文所述,费尔巴哈把人的利己主义,以及由此而生的依赖感视作宗教产生的基础。因此对他来说,要让人从宗教束缚中超脱出来,就必须把依赖感转移到新的对象上,即转移到人与人之间纯粹的感情联系上。也就是说,只有用存在于人际间的爱代替对“神”、“上帝”的爱,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对于费尔巴哈而言,宗教可被划分为两种类型:有神的宗教、无神的宗教。他抨击有神的宗教,认为这种宗教具有欺骗性、虚幻性,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应当予以消灭。但“爱”的宗教作为无神的宗教的代表,能够帮助人们消除以往的宗教幻想,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费尔巴哈指出,当“人们使感情成为宗教的主要东西以后,基督教的曾经是非常神圣的信仰内容,就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了”,[5]13对“上帝”虚幻的爱也随之覆灭。从这里不难发现,费尔巴哈并未打算根本、彻底地废除宗教,而是试图用一个意识问题解决另一个意识问题,体现了其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缺陷。
既然“爱”的宗教能够解决一切问题,那么,又该如何建立?费尔巴哈指出,过去颠倒了的宗教关系阻碍人的感知、中断情感联系,这就容易导致人单向地被宗教控制。要建立“爱”的宗教,就要“把宗教上的关系颠倒过来,始终把被宗教设定为手段的东西理解成为目的,把被宗教认为是自从属的、次要的东西,把被宗教认为是条件的东西,提升为主要的东西,提升为原因”。[5]355这样人得以诉诸于心、爱,天然的情感关系将弥合人与“上帝”间的裂缝,从而打破宗教幻觉,实现人的真正解放。
但是,费尔巴哈所论证的“宗教就是情感关系”确实成立吗?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只是从词源学上理解宗教的含义,“宗教一词是从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就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3]240-241费尔巴哈犯了用“概念”解释“概念”的唯心主义错误。恩格斯指出,人际间的情感关联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着的,“宗教也许明天就会完全消失,但是爱情和友谊的实践并不会发生丝毫变化”。[3]240显然,人与人的情感纽带与宗教没有直接、内在、必然的关系,费尔巴哈不过是为宗教的合理存在找一个永恒的“支点”。
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费尔巴哈所强调的“纯粹人的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一方面,费尔巴哈自己并不真正在意人际之间基于相互倾慕所形成的关联,例如“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纯粹的情感关系。他只追求为这些关系打上宗教的烙印使之神圣化、完满化,从而把这些关系上升为新的、真正的宗教。“很显然,这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客观性的否定”,[10]消解了费尔巴哈最后一点革命性。另一方面,恩格斯认为已不存在纯粹的、静态的情感关系和道德关系。或许曾经存在,但已“被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破坏得差不多了”。[3]242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教育、环境等因素影响,形成符合所属集团的道德和情感关系。因此,各阶级、各行业都有独属自己的道德谱系,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存在彼此冲突的可能。于是,本应联合一切人的“爱”,就转化为人对人的“剥削”了。费尔巴哈不是从历史维度去考察现实的人,他所醉心的普适性的爱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一旦落于现实,就如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
对宗教社会作用的错误评判,或许是费尔巴哈不愿废除宗教的又一原因。费尔巴哈认为“人类的各个时期仅仅由于宗教的变迁而彼此区别开来”,把宗教变迁视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认为意识、精神能够推动历史发展。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出发,批驳了费尔巴哈的错误观点。他指出,社会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随,只是针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而言,不能套用于原始宗教、民族宗教。且必须看到,“这种作用是伴随性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作用”。[11]恩格斯进一步说明,只有在13世纪到17世纪,即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一般的历史运动才带有宗教色彩。而这种色彩,不能“用人的心灵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以往的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来解释。”[3]242简言之,历史变迁是由现实的政治、经济等状况推动的,宗教并不具备决定意义。
基于对宗教的种种透视,恩格斯否定了费尔巴哈试图颠倒宗教关系,重建“爱”的宗教的主张。他认为必须批判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制度,从根源上颠覆神性,彻底废除宗教,实现自由人的真正解放。
在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确有其伟大之处,但他没有从根本上完成对宗教的批判。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与经济基础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仅停留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天国批判”是不可能消灭宗教的,只会令人陷入唯心主义的循环怪圈。不同于费尔巴哈,恩格斯看到了人的现实性、社会性,由此在社会历史领域展开了“尘世批判”。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压迫,更看到了人的物化、异化。当“人”被“物”掩埋,势必会产生痛苦与抗争的倾向,而宗教恰恰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为人提供不切实际的、远在彼岸的幸福幻想,如同“鸦片”一般压制人的不安、麻痹人的理性。正是看到了如此景况,恩格斯坚定地认为要批判、变革不合理的现存社会制度以及由此而生的劳动异化,摧毁业已扭曲的经济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宗教,破除其带给人的安慰和幻觉,最终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
在新形势下,宗教问题、宗教治理仍然是我国工作的一个重点。从某种程度上看,宗教问题就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因此,重温《费尔巴哈论》,以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熏陶、武装大脑就显得正当其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宗教工作将更为深刻地实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始终掌握宗教工作的主动权,真正实现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