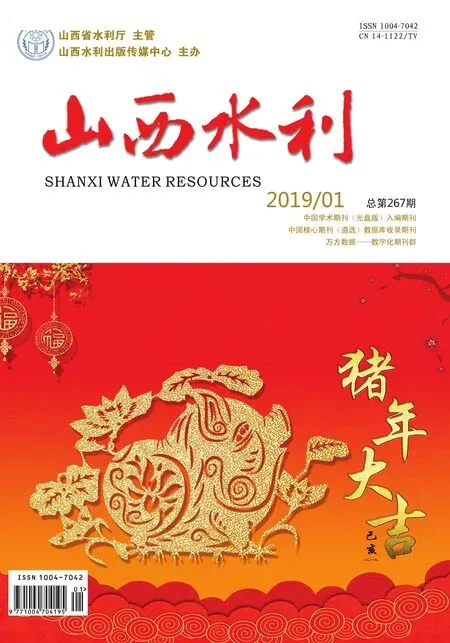水权交易体系建设探析
张敬尧,王欢欢
(晋城市水务局,山西 晋城 048000)
在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指出:水权包括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水权交易,则是指在合理界定和分配水资源使用权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水资源使用权在地区间、流域间、流域上下游、行业间、用水户间流转的行为。建立和完善水权交易制度是优化配置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破解水资源瓶颈问题的重大举措。
水利部将水权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水利改革的重要任务,在7个省(自治区)启动水权试点,经过3年积极探索,初步形成了多种水权交易模式。经过试点实践,各地在水权确权的基础上,培育水权交易市场、创新水资源配置管理。目前执行的水权交易制度与相应法规中,主要完成水资源的确权工作,水权及水权交易主要涉及其中的使用权与转让性,对责任方面规定较少。
1 水权体系分析
上述水权,仅为所有权分割出的部分权利。霍诺里(A.M.Honoré)曾分析并提出了“所有权”的11个特征: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入权、资本权、保障权、转让性、无限期、禁止滥用、履行责任、剩余处置权(布罗姆利,1994)。这11个特征可视为权利分割与交换的基础。
一是水资源受其独特的流动性与循环性影响,对其权利依照上述标准进行清晰分割与转让变得较为困难,相应的责任也难以界定。二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水资源属于国有资源,其占有权是固定的。三是水资源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由国家予以保障相对合理。因此,将资本权、无限期、禁止滥用、剩余处置并入管理权合,增加入生存权,将前述11特征化为生存权、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入权、保障权、条件转让性、履行责任8项,并依照权责是否随用水主体变换的影响,将水权分为两类:固有权利与交易权利。国家享有水资源的固有权利,即:占有权、管理权、生存权。其余权利可依实际情况,随用水主体变换而进行权利转移。
如某用水户依法获得当地一定水量的水资源取水权,在取水权有效期内,可以依法对该部分水量进行使用并获利,通过节水措施或调整产品结构,节省下来的水量可以通过水权交易、出让并获得相应补偿。用水户合法取水及转让行为受法律保护,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并依法承担水资源相应保护责任。受让方在接受取水权转让,享有法律保护取水权利并获利的同时,也同样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并依法承担水资源相应保护责任。国家享有水资源的所有权,掌控水资源的管理权,并保障人民的生存权。
根据以上理论,将水权定义为受法律保障、可依法进行流转获利并须履行相应保护责任的取水权,根据“生存为先、权随水走、责随权走”的思想,以水权许可为基础,以水权交易为手段,以行政执法为保障,对相应水权交易体系进行构建。
2 水权体系重构
2.1 基础体系
水权交易,是基于水量分配方案,经确权登记后,实行的水资源配置方式,与取水许可制度息息相关。作为水资源管理的最基础制度,取水许可制度可谓水权体系的雏形,指经水量核定后,对用水户合理取水量进行规定,使用水户在限定时间内拥有对相应水资源的取水权并对退水提出要求,是对用水户的取水权与相应责任进行确认与规范的制度。针对水权的划分与重构,建议在取水许可基础上建立分时分权的水权许可制度。
设立水权许可证,替代旧的取水许可证。以水权许可证对用水主体的生存权与可交易水权予以分别确认,即以证对用水户的生存权、使用权、收入权、保障权、条件转让性与履行责任予以规范,重点在于对生存权、使用权、转让权分别设定时间与要求。
生存权,依照用水定额对用水主体的生活用水予以确权,该项水量依实际情况设定有效期,以简化水量复核工作为原则,可设定为与其他取水权限期相同或长期有效,但涉及水量不允许进行水权交易。
交易权,依照取水许可管理办法对取水权的确认流程,规定许可取水权与有效期。用水户通过节水技术改造等手段,实际取水量低于许可批复取水量,多余部分增设转让权,参与水权交易,对交易水权与有效期予以独立确定。转让权的有效期过短会降低用水主体的节水积极性,过长又不利于水资源的高效流转配置,所以转让权有效时间可参考节水奖励机制与行业标准。不愿参与水权交易的用水户可不按此项办理。
其余交易权利,收入权与保障权可视作取水权的附加权利,不予单独体现,相应责任可依照取水用途与取退水要求等方式体现。为降低管理难度,可在旧有取水许可上增设交易水量与有效时间,以此作为过渡方案。
2.2 水权交易制度
水资源属于公共资源,个人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极易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因此,在水权交易制度实行中,有效的管理制度必不可少。
2.2.1 管理模式
很多国家都采用经济手段来调控水的供求关系,成立水权交易市场,由市场来改善水的使用效率,同时,政府在这一水资源规划与分配中依然起到很大的作用。要建立完善的水权交易制度,不能单纯交给市场调配,亦不能由政府行为完全主宰,要保障公众与非公组织对水权事务的合理参与。水权交易制度应由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与价格指导者,以市场为交易执行者,以公众参与作为监督者。
2.2.2 水权交易主体
现有水权交易体系中,交易主体有三类,即行政区域、纳入取水许可的取用水户和灌区农业用水户。水权交易中存在行政区域之间的取水权交易行为,即政府既是水权交易的管理者,又可能是水权交易的参与者。在涉及区域之间水权交易行为时,要严格确定水权交易主体的界定,保障政府在参与水权交易时享有合理权利。针对政府难以纳入水权许可制度管理的现状,建议建立多级水权交易市场,以低级区域水权交易市场作为主体,办理区域水权许可后,进入高级区域交易市场参与水权交易。当交易主体是纳入取水许可的取水用户和灌区内农业用水户时,在纳入水权许可制度后,可视为同等交易主体参与交易。
2.2.3 水价的确定
水权要进入市场流通,就必须由市场赋予其价值,即水权定价。水权定价要考虑的影响因素有:供水工程成本、水资源条件、水资源分配导向、水资源保护责任、交易成本、用户承受能力等。
考虑到上述因素,应根据当地水资源条件,对不同用途取水权设定不同的指导底价;不管是否参与水权交易,用水户的水资源使用成本(水价或水资源税)均应依照制定结果执行。
居民生活用水,涉及国家对人民生存权的保障,只考虑供水与保护成本及用水户承受能力设定政策性水价,其价格波动仅受用水定额与供水成本变化影响,不参与交易。对工业用水,则更多考虑水资源保护责任与水资源分配导向的影响,通过制定合理水价,使水权市场充分起到水资源的高效调配作用。对于灌溉用水水价的要求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在保障生产的同时可以促使用水户积极节水。指导水价,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水权交易市场公布,作为水权交易的重要依据,交易主体在相应指导价的合理波动范围内约定成交水价。
2.2.4 水权交易流程管理
对水权交易制度的规范即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交易行为须在水权交易市场内进行。市场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水权交易进行分级管理。
如某县(市、区)行政区域内经确权后确认享有5 000万m3水权额度,该县管辖范围内水权交易市场就针对这5 000万m3水权额度作为总额进行分配交易,交易主体为该县内参与水权交易的用水户,交易水权总额不得超过5 000万m3,该县若与邻县涉及到水权交易,则以该县水权交易市场为交易主体,在市级或省级水权交易市场以5 000万m3的水权额度进行额度交易。
水权交易是以经济行为对水资源进行调配,交易过程中必然涉及补偿等经济往来。水权的转让行为很多时候会造成取水用途的改变,也会造成水价的变动。为进一步优化差异水价的作用,在水权交易中,可提供由交易市场对水权交易出让方回购水权,和将水权出售给交易受让方的服务,回购价与出让价依据不同取水用途制定成交水价并实时公布。对于直接由用水户之间达成协议的水权交易行为,要上报水权交易市场与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纪律部门与公众对该行为予以监督。
按照市场规律,水是商品,市场会把水配置给利用价值最高的用户。作为居民生活用水的盈利率很低,水权交易完全由市场决定,会对居民生存用水的保障权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在建立水权交易体系的同时,必须如同保障基本耕地红线一样,坚决保障人民的生存用水权,这也是水权许可明确生存权、设定水量并严禁交易的原因。
2.2.5 保护责任
用水户在享有取水并获益的权利时,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水资源保护责任。随着水权额度的交易,受让方在获得更多水权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水资源保护责任。该项责任应与当地水功能区划相适应,并以水价或水资源税的形态予以体现。如果水权交易造成水资源的破坏,交易双方均应承担相应补偿责任。水权交易市场可对破坏水资源的水权交易行为采取惩罚性水价,对于严重破坏水资源的行为,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叫停水权交易并追究相关责任。
2.2.6 公众参与
随着社会力量的不断壮大,非政府公共组织和公民对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管理的需求日益增长,水权交易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也在不断提升,这也是公众以参与管理的方式维护自身生存权的体现。
同时还可建立水论坛等学术与应用的交流平台,使水权交易制度真正成为公众、非公组织、用水户、交易市场、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参与,共同管理的行为,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
2.3 保障措施
水资源是一种战略资源,需要从战略角度考虑水权交易问题。在水价制定上,政府须建立保护机制,当水权交易陷入混乱,市场无法有效调节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时,政府需要强势介入市场,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必要时可以强制收回水权;在水权交易过程中,政府也应做好信息发布平台与交易指导的作用,保障交易双方或多方公平参与水权交易。
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在完善的用水计量监测与严格的水行政执法上,要严格执行用水计量监测,严厉打击违法取水行为。以完备的监督体系、严明高效的水政执法推动保障水权交易健康发展。同时,加强公众与纪律部门对水权交易中参与方的监督,严格杜绝权力寻租。
3 存在问题与建议
3.1 水资源破坏补偿标准问题
有权必有责,责权必相称。取水权对应的责任即为对取用水资源的保护。作为一种流动性的公共资源,人们在开发利用水资源,享有相应取水权利的同时,也会对其他用水主体产生影响。如果用水主体对水资源造成破坏,那它在损害了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影响其他用水主体的合理权益。对渔业等其他用水主体影响相对容易界定,但对航运、旅游、生态等主体则难以界定侵权行为与侵权后果。由于水资源损害责任与侵权影响的难以界定,这一项工作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如何简单高效的界定水资源损害责任与侵权影响,并确定相应补偿标准,则是水资源管理者在水权制度实施中所要面临的一大考验。
3.2 水权额度问题
在水权体系构建中,提到了水权交易市场总额,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用户通过节水措施等扩大交易权利,或是受客观因素(干旱或突发事件等)影响,水权额度减少的现象,会对区域水权市场的水权总额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上级水权市场,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出现水权交易的混乱局面。如何合理确定水权市场额度、提高管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需要注意。
3.3 管理难度问题
水权交易制度的构建,对水权予以分割确认的同时,也提高了水权管理的难度与复杂程度。需进一步研究,做到管理模式的简单有效。
4 结论
将水权定义为受法律保障、可依法进行流转、获利,并须履行相应保护责任的取水权。根据“生存为先、权随水走、责随权走”的思想,以取水许可为基础,以水权交易为手段,以行政执法为保障,对相应水权交易体系进行构建。还需要进一步简化管理模式,并对水资源破坏补偿标准和水权交易行为中额度变化的管理予以研究。
面对水资源危机的挑战,不仅要从技术上解决水与自然的问题,更要从社会的角度解决水与社会的问题,使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成为人类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