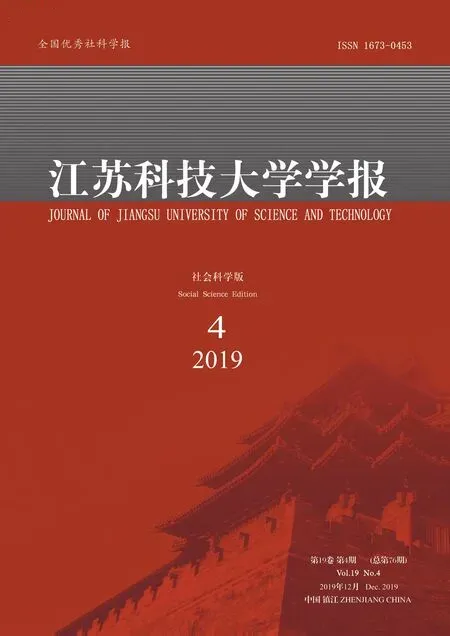出土文献对神话研究的贡献
尹秋月,陈良武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中国古代神话是先民想象力和智慧的结晶,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然而,由于神话的留存数量非常少,且多散见于诸多典籍之中,因此仅仅依据传世材料进行神话研究难免存在许多局限。
20世纪初,伴随着甲骨卜辞、简帛等文献的大量出土,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将纸上材料与地下新材料相结合以考证古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受此影响,神话学研究者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研究,解决了诸多疑难困惑,厘清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对已有成果进行梳理,能够补充前人的研究,进一步明晰出土文献的重要意义,并为神话学研究对出土文献的使用指明方向,推动神话学研究的长足发展。
一、 提供神话研究新材料
研究中国古代神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文献不足。而出土文献带来了传世文献中没有的新材料,可以弥补研究材料不足的缺憾。这一点,在中国创世神话和始祖神话的研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直以来,传世文献中的创世神话较为完整且广为人知的当属盘古开天辟地,但这个故事始见于三国时代的《三五历纪》中,不仅年代相当靠后,而且一直有其来自印度而非中国本土的质疑之声,因此中国创世神话的研究始终难以推进。直到《楚帛书》的出土,为创世神话研究带来新的发展。
1942年,长沙出土《楚帛书》,其中的《四时》篇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创世神话。经过诸多研究者的释读,虽然在个别字句的辨识和句读上还有少许不一致,但其整体意义已经可以把握和理解。《四时》篇分为两段,讲述了伏羲女娲生四子,创造四季与昼夜,制定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则,一个秩序化的世界就此诞生。这是一个完整的创世神话,解释了宇宙的起源和四时昼夜的形成。董楚平先生赞叹:“在现有的中国先秦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还没有比它更完整、更明确的创世神话,其珍贵是不言而喻的。”[1]
值得注意的是,《楚帛书》中的许多神话形象并不是陌生的,伏羲、女娲的神话早已家喻户晓,四季神的形象亦可在传世文献中找到一些痕迹。杨宽将四季神像与《山海经》相比较,发现“秉司春”人面鸟神的神像与《山海经·海外东经》中的句芒形象一致。“句芒”是形容植物的屈曲生长,这正是春神的工作。以这样的思路在《山海经》中可以找到四季之神的身影:夏季之神是祝融,秋季之神是鲧,冬季之神是禺强[2]。刘信芳关于春季神、夏季神、冬季神的考辨与杨宽持相同看法,只有秋季神“玄司秋”的“玄”,刘信芳认为应释读为“糸”,是“丝”的初文,与“茲”声同,而“兹”与“蓐”又同义,因此秋季神应当是蓐收[3]。
传世文献中的四季神在《楚帛书》中各司其职,可见出土文献对神话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判断神灵出现的时间,明确神灵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建立中国神话的谱系。
周始祖后稷的诞生,在传世典籍文献中多有记载,《诗经·大雅·生民》便是对后稷出生的记录: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4]294
毛郑皆以此为姜嫄祭祀郊禖之神、踩上帝脚印、有感而孕的记录。闻一多认为这是对姜嫄祭祀求子之礼仪的记载:“上云禋礼,下云履迹,是履迹乃祭祀仪式的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5]《史记·周本纪》中也有类似内容:“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6]“武”意为脚印,传世文献将后稷的孕育归结为姜嫄踩天帝或巨人的脚印有感。后稷的感生神话情节非常简单,似乎只是踩一个脚印的事情。但是上博简《子羔》篇借孔子之口记录了姜嫄祈子的过程:

如果依照毛郑的观点,姜嫄求子有一个完整的仪式,那么简文所记载的仪式明显比典籍文献记载的要复杂得多。从简文中可以看出,姜嫄求子的仪式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游于玄咎内”,其次是“荐芺”,最后才是传世文献中所提到的履人迹。简文中的脚印属于“人”,而不是传世典籍中所提到的“帝”或者“大人”。在这里,“串咎”和“芺”“攼”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注意。马承源认为,“串咎”可读为“串泽”,“芺攼”为“芺蓟”或“芺鉤”[7]197。张富海认为,释读为“串咎”是不妥的,应当为“玄丘”,并联系《诗·大雅·生民》毛传:“古者立郊禖,盖祭天于郊,而以先媒配也。变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礼以玄鸟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天子亲往,后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4]291由此推测这就是祭祀郊禖的处所,“芺”是指春夏季节的草,冬天出现可见神异,“攼”是“拔取”的意思[8]。廖名春赞同简文应释读为“玄丘”,并指出“玄丘”即“圆丘”,与“郊”同义,因此“游于玄丘之内”就是《诗经》中记载的“禋礼上帝于郊禖”,“芺”指香蒿。姜嫄的求子仪式为:冬至到圆丘祭天,拔下香蒿焚烧,让香气直达上帝,结果上帝为其精诚所动,出现巨人脚印,姜嫄踩之并祈祷子嗣。简文后半部分祈祷的祷辞残缺,廖名春加以补充,认为祷辞是“帝之武尚使我有子,必报之”[9]。结合诸位学者的研究可知,简文记载的是姜嫄求子的仪式,传世文献中仅留下“履人迹”,而出土的简文中却留下了祭祀的完整过程及其冬见夏草的神异部分,恢复了后稷神话的全貌。
二、 剥离神话的历史外衣
从早期的口耳相传到记载进典籍的过程中,中国古代神话不断被加工,其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究其原因,茅盾先生在分析中国古代神话留存数量少的时候解释为“神话的历史化”。茅盾先生认为:“神话的历史化,固然也保存了相当的神话;但神话历史化太早,便容易使得神话僵死。中国北部的神话,大概在商周之交就已经历史化得很完备,神话的色彩大半褪落,只剩了《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10]可见,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得相当早,在写实主义影响下,神话不再具备神话的因素,失去神话的色彩,而成为单纯的历史记述。出土文献长期封存于地下,不曾受到后人的修改,因此神话的早期面目得以留存,将其与传世典籍中的记载相对比,从中便可以了解神话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变化,有助于恢复神话的本质。
“黄帝四面”的神话原本带有神异色彩,但是在典籍记载中,其已经融入历史,被历史化了。《吕氏春秋·本味》篇:“故黄帝立四面,尧舜得伯阳续耳然后成。”[11]高诱注:“黄帝使人四面出,求贤人,得之立以为佐,故曰立四面也。”《太平御览》收录了一段《尸子》的佚文:
《尸子》曰: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12]
在孔子的解释之下,“黄帝四面”的神话意义完全泯灭。袁珂先生曾经指出:“神话转化做历史,大都出于有心人的‘施为’,儒家之流要算是做这种工作的主力军。……如像黄帝,传说中他本来有四张脸,却被孔子巧妙地解释作黄帝派遣四个人去分治四方。”[13]这正如孔子将《山海经》中的一足之兽夔解释为夔是个通晓音律的能人,有一个就足够了。这种释读既不合情理,又消解了神话的意味。
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道德经》乙本前有一段佚文,其中就有较为完整的“黄帝四面”神话:
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像),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定。吾受命于天,定立(位)于地,成名于人。唯余一人乃肥(配)天,乃立王三公。[14]
帛书的记载明确表示,所谓“黄帝四面”的意义正是黄帝为自己制作的形象,是方方正正的四张面孔,归附于一颗指挥着人们行为的心。叶舒宪将其与《尸子》中的记载进行对比后发现,帛书中的说法更加具体、详细,并且帛书的叙述“透露出黄帝神话的影子,而叙述本身已是神话的历史化了,因为黄帝的身份已由天神变成了人王”[15]。可见,帛书是更为原始的材料,帛书中的神话已经有一些历史化的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黄帝在最早的时候是神话人物。另有研究者注意到,帛书在其他地方称黄帝为“黄帝”,只有在这里称“黄宗”,意为“黄帝的宗主”。古代的宗主之形正是四方木或四方石之形,“特殊的是,传说中黄帝自己做成的四方状宗主上刻画有自己的形象”[16],由此产生了“黄帝四面”的神话[16]。可以看出,“黄帝四面”的神话故事从“宗主之形”开始带有历史的意味,到了“取四人,使治四方”则完全成为历史。如此一来,“黄帝四面”的神话及历史化过程得以厘清。
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对神话学研究提供极大的帮助。借助新的出土材料,神话原始形貌和情节得以恢复,这为神话学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可信的研究材料。在此基础上,研究者的成果更令人信服,神话学的发展也因此更为稳健。
三、 解决神话研究中的争议
中国古代神话材料零散,不成体系,典籍中的记载往往相当模糊,许多细节都模棱两可,甚至互相矛盾,进而导致在神话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争议。而出土文献则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伏羲、女娲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创世神,但是最早出现伏羲的《易·系辞》中并未提到女娲,而最早出现女娲的《楚辞·天问》也一字未提伏羲。可以说,传世先秦古书中几乎没有对伏羲、女娲的关系予以定性,因此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或许这二人原本是无关的。最早提及伏羲、女娲关系的是《路史·后纪二》中所引的《风俗通》佚文,即“女娲,伏希之妹”[17],也就是说,伏羲与女娲是一对兄妹。
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一文中将目光投向少数民族神话与石刻绢画材料,由此整理出苗族洪水神话的共同点,即“中心母题总是洪水来时,只兄妹(或姊弟)二人得救,后结为夫妇,遂为人类始祖”[5]8。陈建宪收集的资料显示,一些流传于民间的洪水神话便记录了伏羲、女娲两兄妹在洪水中幸存下来并结为夫妇繁衍人类的故事[18]。在传世文献及石刻绢画中,时常出现的“蛇身二首”的形象便是伏羲、女娲交尾像,如汉武梁祠石室人首蛇身交尾像画像,由此可以证明二人确为夫妇关系。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伏羲、女娲是兄妹、配偶的关系。

禹子夏启的出生一直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谜团。在传世文献中,夏启出生、其母化而为石的故事片段散见于诸多典籍中,如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引用《淮南子》的佚文:
《淮南》曰:禹治鸿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21]
启生而母化为石的故事从汉代一直流传下来。由于典籍的记录各有不同,其真相愈发神秘难测。直到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的睡虎地11号墓出土了秦简《日书》,其中有与夏启出生相关的记录:
癸丑、戊午、己未,禹以取(娶)梌(涂)山之女日也,不弃,必以子死。[22]113
《日书》中“必以子死”道破涂山氏生启难产而亡的真相,王晖进一步推测,“化为石”是“化为僵尸”的委婉说法。也就是说,“启生而母化为石”的说法是在流传过程中以讹传讹产生的误会,其真相是涂山氏在生产时难产而亡[16]。还原这个神话故事原本面目的正是出土材料《日书》。
大多数出土的简文是第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也有一部分简文,其内容在传世文献中已经被引用过,然而由于简文的亡佚,转引材料的真实性也大打折扣。幸而在后世,埋藏于地下的简文被发现,验证了传世文献中转引的内容。如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神话,其文献记载始见于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但是,袁珂先生早已指出嫦娥奔月实际上“始见于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后来亡佚了的《归藏》”[23]165。这个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文心雕龙·诸子》中便提到:“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弊十日,姮娥奔月。”[24]在《昭明文选》中,谢希逸《月赋》之下李善注:“归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药奔月。”[25]600王僧达《祭颜光禄文》之下李善注:“周易、归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25]2609可见,早在战国时期,嫦娥奔月的神话就已经出现并具备较为完整的情节,即嫦娥从西王母手中得了不死之药,服下后奔月成精,获得永生。这个故事里的嫦娥借助药物飞升成仙,寄寓了人们对肉体不灭、灵魂永生的向往。只不过到了汉代,《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26]501嫦娥窃取了丈夫羿的不死之药,成为一个背弃丈夫的妻子,她的永生也成为一种惩罚。嫦娥奔月是对丈夫的背弃还是对永生的美好追求,关于这一问题,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直到1993年王家台秦简《归藏·归妹》的出土,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这个问题。其中记载与嫦娥奔月有关的两支简文如下:
□《归妹》曰:昔者恒我窃毋死之……
……□(奔)月,而攴(枚)占……[27]
简文的残损程度非常严重,但是比照李善的转引,可以把握其内容即恒我(嫦娥)窃药奔月。传世文献对《归藏》的引用和如今看到的《归藏》文本中都没有提到羿。在《淮南子·览冥训》之下,东汉高诱注曰:“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26]501从这里开始羿与嫦娥才有了关联。除此之外,羿的神话中也从未有嫦娥的身影。因此,有学者推论,“羿与嫦娥的夫妻关系,当是两汉时人撮合的结果”[27]。由此可见,嫦娥奔月原本就是独立的神话,与羿射九日的神话并无关联,更没有从属关系。
借出土文献材料作为参考,传世神话中许多不清楚的地方明晰起来,看似不合情理的矛盾之处也有了合理的解释,神话本来的情节和形貌得以还原。
四、 考证神话的流传
出土文献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将神话从历史等其他材料中剥离出来,复原神话原貌,还在于能够通过确定文献的记述年代考证神话形成的年代和流传情况。
通过对殷墟卜辞的释读,殷商时代的生活画面逐渐清晰可辨,其中也收藏着殷商先民创造的神话。如《卜辞通篡》第398片:“于帝史凤,二犬。”郭沫若先生解读为:“视凤为天帝之使,而祀之以而犬。……足知凤鸟传说自殷代以来矣。”[28]凤鸟作为先民想象力的成果,被收入商王朝的占卜甲骨中,可见其在当时已经广为流传,其使者的性质也受到先民的关注和承认。以鸟雀为神灵使者、传递消息的传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的。《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29]凤鸟来自天上,作为神灵的使者,肩负着向下界传递神灵意旨的责任。但是,只有一个凤鸟是不够的,职责分之又分,最后由四只鸟雀负责传递节气更替的消息。这四只鸟雀中,玄鸟、伯赵(伯劳)、丹鸟都能够在人间找到对应的形象,唯独青鸟与凤鸟一样,是想象力的产物而非真实存在的动物。于是,最先出现的凤鸟形象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既与音乐相关,又象征着祥瑞,甚至还是楚文化中的保护神,而由凤鸟分化出来的青鸟则担负起凤鸟最原始的职责——使者。《山海经》中便以青鸟为西王母使者:“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30]这一形象一直流传下来,甚至在诗歌中也频频出现,从李白的“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麻姑”到李商隐的“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由此,青鸟形象象征的意义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极为重要的使者形象。
除上文提及的涂山氏生启的神话外,秦简《日书》中还有与牛郎、织女相关的二则简文,简文如下:
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三弃。[22]108
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22]113
这两条简文记录了牛郎和织女的婚姻悲剧,以此证明二人成亲的日子是不吉利的。李立指出,“不果”说的是牛郎织女的婚姻悲剧,“三弃”“不出三岁,弃若亡”是戊申、己酉娶妻导致的不吉结果[31]。这条简文是借牛郎织女的婚姻悲剧向求卜者发出警告,告诫求卜者成婚要避开这个日子。据考证,挖掘出《日书》的秦墓属于一个秦时小吏,卒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因此《日书》的成书不可能晚于这个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日书》中列出楚秦月份对照表,对此吴小强认为,之所以需要这份对照表,是因为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秦国刚刚攻占楚国的国都郢,秦的历法正在推行,但是民间仍然习惯于使用楚国的历法。因此,“《日书》最后成书应当在昭襄王二十八年以后不久”[22]294。
在传世文献中,牵牛和织女首现于《诗经》。《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4]229此时牵牛与织女还只是两颗星星。到了汉代,牵牛、织女相恋成婚已经成为文学中的常用典故。如,班固《西都赋》“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25]21;张衡《西京赋》“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25]65。《古诗十九首》之《迢迢牵牛星》更是直言二人相恋却不得不分开的悲痛:“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25]1347蔡先金认为,“然而,我们也可以从此发现从诗经时代到两汉时期有关‘牵牛织女’记载文献上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缺环,即从《大东》到《迢迢牵牛星》之间何时出现牵牛与织女婚配的故事要素,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的出土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失”[32]。从《诗经》中的两颗星星到战国时期牛郎织女神话的形成,再到汉代广为流传,牛郎织女故事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渐渐明晰。
除了对故事产生时间的判断,许多研究者也十分关注故事流传的地点。林剑鸣将放马滩秦简《日书》与睡虎地秦简《日书》对比后认为,前者所解决的是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后者则对鬼十分关注,可以说是通篇言鬼。细分析到一些用词上,睡虎地《日书》中的用词缺少人文色彩,较为抽象而无具体内容,“《睡》简有较多的礼制影响和较浓的神秘色彩,反映了楚文化的特点;《放》简则相反,显得质朴而具体,因此少有礼制。道德以及鬼神的影响,反映了秦文化‘重功利、轻仁义’的特点”[33]。王朝阳也认为,《日书》呈现了秦楚文化杂交融合的特质与现象。因此,可以推测,牛郎织女的故事开始应该流传于楚地汉水流域[34]。从《日书》中的措辞和反映的文化背景来判断《日书》流行的地域,由此可以推断神话流传的地点。
五、 探析先民对世界的认识
关于神话的起源,袁珂是这样解释的:“在长时期被求生存的困难和与自然作斗争的困难压迫着,生产力又是这么低下的原始社会的人们,当他们用从劳动的双手发达起来的日益聪慧的头脑开始一面劳动、一面思索、探求自然的奥秘,并初步创造了一些最简单的神话以为解释的时候,现实世界的生活刺激着他们。”[23]61蒙昧时期的先民通过想象和总结经验对世界进行解读,因此在神话中隐藏着许多来自远古时代的原始意识,带有民族的生命密码。借助神话对先民的思想意识和精神世界加以探析,是神话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神话的解读可以看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类将世界看作一个有规律的整体,这个规律是简单而有效的,能够被把握且在各个方面是互通的。先民在现实生活中试图探索其中的规律,渴望脱离对未知的恐惧。
胡厚宣在《甲骨学商史论丛》中曾经对庐江刘晦之所藏的甲骨文字和中央研究院发掘所得的一片龟甲文进行研究,其上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四方神名及风名,胡厚宣认为其与《山海经》中所记录的四方之名及其风名是吻合的[35]。这两篇甲骨文引起学界的注意。杨树达在《积微居甲文说》中对四方神名加以释读,认为四方之神名与草木的生长相关:东方之神名“析”,意为春日到来,草木发芽;南方之神名“荚”,意为夏季草木勃发;西方之神名应当为“枣”,意为草木的果实,正是秋季;北方之神名为“宛”,意为草木潜伏,是冬季的现象。从中可见,四方神名与季节的变迁紧密相关,“殷人以为草木各有神为职司,其神为四,分为四季……殷人以四时分配于四方,为《尧典》所自本”[36]。冯时将刻辞与《尚书·尧典》中记载的物候进行对比,认为四方神名来源于四季的气候,风名来源于动物在四季的活动。如,东方神名为“析”,析训为分,意指春分之时昼夜平分;其风为“协”,意即阴阳合和而交,正是《尧典》中说“鸟兽孳尾”[37]。李学勤结合诸位学者的释读,将刻辞与《山海经》对比,认为是大致吻合的。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随着季候的推移,一年之中风向有所变化,昼夜的长短也有不同,这不仅仅是神话,也是当时人们科学知识和宇宙观的结晶[38]。可见,在先民看来,四季与四时是紧密相关的,正如丁山所说:“殷商时代四方风名,确涵有四时节令的意义;其四方神名,则全是天空上的岁次。”[39]这其中是先民对经验的总结,也是先民借助想象力对世界进行的探索。
除了文字上的相通,在图像方面亦可发现先民将四方与四时相配。刘信芳在《出土简帛宗教神话研究》中指出,战国早期墓葬曾侯乙墓中的衣箱E66以箱体之六面表示六合,衣箱的四侧分别绘有四方神,这四方神无论是名字还是形象都与楚帛书中的四季神相合,东方神为句芒,南方神为祝融,在祝融身旁又绘有一只表示南方的朱雀,西方神为弇茲,字形上与蓐收相通,北方以一片漆黑表示玄冥[40]。
四方五行之观念在汉代十分流行,其学说源头或许在战国。顾颉刚曾指出,“这种思想虽不详其发生时代,但其成为系统的学说始自战国,似已可作定论”[41]。但是进一步探求,这种思想的根源实质上源自人类对世界的探索。出土文献是最为原始的文献资料,其中包含着先民对世界最原始的认识和解释方式。
神话来自于远古时代的先民对世界的解读,是经验的总结和想象的结晶,其中凝结着人类充满智慧的思想和美丽的想象力,蕴含着先祖塑造的独特文化性格。出土文献则保留了远古时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为原始和本真的思想,将其与其他材料共同使用,能够带来新的灵感,复原蒙尘的灿烂神话,进而破译民族血液中的原始密码,以期推动神话学研究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