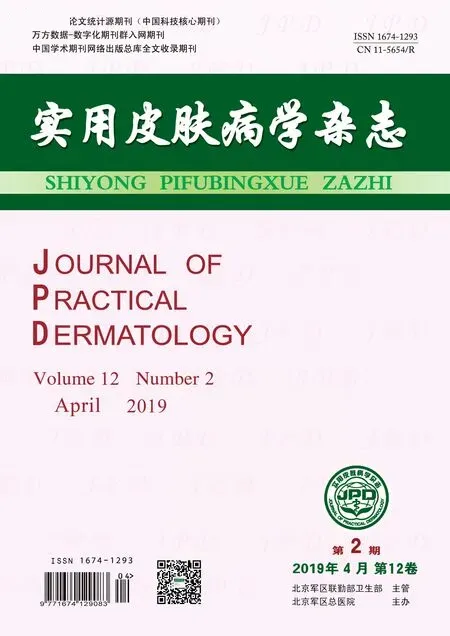毛囊皮脂腺微生态与痤疮
曹 珂,侯霄枭,鞠 强
正常微生物菌群与宿主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构成人体微生态系统,皮肤微生态系统是人体微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皮肤微生物群主要分布于人体皮肤以及与外界相通的腔道如外耳道、呼吸道、消化道、泌尿生殖道等部位[1]。健康成年人皮肤存在大约19种微生物[2],主要包括放线菌(52%)、厚壁菌(24%)、变形菌(17%)和拟杆菌(7%)。皮肤微生物和人体皮肤细胞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环境,成为皮肤防御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皮肤微生物的定植与皮肤温度、湿度、pH、氧含量及宿主遗传、激素及年龄、性别、免疫功能、生活方式等多种内外因素相关[3]。当微生物之间或者其与宿主之间的平衡受到破坏,会导致皮肤功能紊乱、免疫调节异常、致病微生物繁殖,进而引起皮肤疾病发生或加重,许多皮肤疾病如银屑病、特应性皮炎、痤疮与玫瑰痤疮等均发现与皮肤微生态失衡存在相关性。
毛囊皮脂腺单位与皮肤表面有着不同的微环境,从而构成毛囊皮脂腺微生态,与痤疮的发生发展及治疗密切相关。本文就毛囊皮脂腺微生态与痤疮之间近年来的进展作一综述。
1 毛囊皮脂腺微生态
毛囊皮脂腺单位是由皮肤附属器毛囊和皮脂腺共同组成的皮肤结构,皮脂腺开口于毛囊并通过毛囊分泌脂质,构成皮脂的主要成分。毛囊皮脂腺单位不仅富含脂质,同时充满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包括丙酸杆菌、表皮葡萄球菌以及马拉色菌和节足动物蠕螨等。毛囊皮脂腺单位中富含脂质及厌氧环境使得丙酸杆菌成为优势菌群,约占微生物数量的89%[4]。
微生物在维护毛囊皮脂腺单位正常生理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丙酸杆菌可将皮脂中三酰甘油分解成短链的游离脂肪酸,对皮肤表面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白假丝酵母菌和皮肤癣菌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等致病菌均有一定抑制作用[5]。此外,表皮葡萄球菌能分泌自溶酶,可溶解一些潜在致病菌和过路菌,对保持常住菌的稳定性,维持微生态平衡起重要作用。马拉色菌占皮肤真菌的80%,包括球形马拉色菌、限制性马拉色菌、合轴马拉色菌等,存在于不同的解剖部位[6]。蠕螨是一种寄生螨,目前有两个种属被发现在皮肤上定植:一种是寄生于毛囊中的毛囊蠕螨,另一种是定植于皮脂腺或眼睑缘的脂蠕形螨[7]。毛囊皮脂腺单位中的各种微生物与机体和环境和谐相处,维持平衡,参与生物学尤其是皮肤免疫功能的构建,当平衡受到破坏时,就会导致毛囊皮脂腺单位相关疾病如痤疮的发生。
2 毛囊皮脂腺微生物与痤疮
痤疮是毛囊皮脂腺单位慢性炎症性疾病,雄激素作用下的脂质大量分泌、毛囊皮脂腺导管角化异常、痤疮丙酸杆菌为代表的微生物及炎症和免疫反应等因素目前认为与之有关[8],其中毛囊皮脂腺中的微生物因素在痤疮发生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1 痤疮丙酸杆菌与痤疮
痤疮丙酸杆菌与痤疮密切相关,但痤疮患者皮损中其数量和类型与痤疮之间的关联目前仍有争议。Kelhala等[9]对25例痤疮患者和16名健康人面颊、背部、腋窝拭子样本中细菌的16S rRNA基因扩增子测序发现,健康人和未经治疗的痤疮患者的毛囊皮脂腺中痤疮丙酸杆菌均占主导地位,且痤疮严重程度和痤疮丙酸杆菌含量正相关。但Fitz-Gibbon等[4]通过对49例痤疮患者和50名健康人鼻部皮脂腺单位中痤疮丙酸杆菌的16SrDNA序列的测定,指出痤疮患者与健康受试者毛囊皮脂腺内的痤疮丙酸杆菌数量并没有显著差别,但在菌株亚型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可能与痤疮有关。多位点序列分型方法将痤疮丙酸杆菌分为3型,Ⅰ型又分为IA1、IA2、IB、IC[10]。研究发现,IA型痤疮丙酸杆菌定植在痤疮患者毛囊皮脂腺,而IB、Ⅱ、Ⅲ型菌株主要定植在健康人毛囊皮脂腺内[11];此外,核糖分型鉴定出的痤疮丙酸杆菌发现Ⅳ型和Ⅴ型(ribotype Ⅳ和ribotype Ⅴ,RTⅣ 和RTⅤ)可能与痤疮发生密切相关,而Ⅵ型(RTⅥ)则与健康人群相关[4]。也有研究表明,来源于克隆复合体CC18的痤疮丙酸杆菌以及常被认为是抗生素耐药的克隆菌株序列类型3(sequence typing3,ST3)与痤疮的发生有关。相比于菌株亚型上的差异,痤疮患者对痤疮丙酸杆菌的易感性也是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12]。
针对痤疮丙酸杆菌IA、IB、Ⅱ和Ⅲ型菌株的作用机制也有了进一步研究。Nazipi等[11]发现,除Ⅲ型外,其他类型痤疮丙酸杆菌均含有透明质酸酶(hyaluronate lyase,HYL),能降解透明质酸。其中包括HYL-IA型和HYL-IB/II型,前者活性高,能导致透明质酸完全降解,后者活性低,导致透明质酸不完全降解。此外,Hunyadkurti等[13]对健康女性皮肤上痤疮丙酸杆菌IB型6 609菌株进行全基因组序列测序,显示该菌株是一个长度为2 560 282 bp的单一环状染色体,GC含量为60.01%,含有2358个编码序列、45个tRNA位点和6个rRNA位点,属于ST10谱系,并且在角质形成细胞中没有诱导促炎递质的表达,说明这可能是一个共生菌株。研究进一步发现IA型痤疮丙酸杆菌可以产生与痤疮有关的硫酸皮肤黏附素(dermatan-sulphate adhesins,DsA)1和2,而痤疮丙酸杆菌IB型、Ⅱ型或Ⅲ型却不能产生[14]。
痤疮丙酸杆菌在痤疮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介导炎症反应方面。它不仅能够通过激活Toll样受体 (Toll-like receptors,TLRs)、NOD 样受体(nucleotide 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like receptors,NLRs)、蛋白酶激活受体,引起下游一系列级联反应,释放炎症因子,诱导炎症反应[15],还能将三酰甘油水解为游离脂肪酸,促进炎症因子的分泌[8]。痤疮丙酸杆菌能通过对TLR-2,白细胞介素(IL)-8和金属蛋白质 -9(matrix metalloprotein-9,MMP-9)的刺激加重促炎效应,使炎症从毛囊皮脂腺扩散到真表皮,这种促炎效应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化脓性链球菌的5倍[16]。此外,它还通过激活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IGF-1),促进角质形成细胞增殖和分化[17]。而在痤疮的后期,痤疮丙酸杆菌大量增殖则通过获得性免疫反应加重了痤疮,调节CD4+T淋巴细胞的应答,诱导出不同表型的Th17细胞,从而产生不同的细胞因子[18],导致痤疮的的发生。此外,痤疮丙酸杆菌还能以脂质为营养基质,形成促炎型生物膜,抵抗外界环境及抗生素的影响[19]。最近研究发现维生素B12能调节痤疮发病机制中皮肤微生物的转录组[20],但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更多的研究。
2.2 葡萄球菌与痤疮
表皮葡萄球菌是一种凝固酶阴性的革兰阳性菌,也是毛囊皮脂腺单位中正常的微生物菌群。表皮葡萄球菌可能是皮肤微生态平衡中的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分泌自溶酶,溶解并杀灭一些潜在致病菌,维持微生态平衡。另一方面其参与痤疮的致病机制,可能主要与其形成的生物膜以及激活TLR2,诱导炎性因子的表达,促进和加重炎症反应有关。另外,表皮葡萄球菌与痤疮丙酸杆菌一样,能分解三酰甘油为游离脂肪酸,加重炎症反应[21,22]。但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否参与痤疮的发病还有较大争议。
Dreno等[23]对55例痤疮患者面颊、前额、下颌部进行分析显示,葡萄球菌在痤疮皮损部位(粉刺、丘疹和脓疱)较无皮损部位丰富,并且随着痤疮的严重程度的增加,其比例也相应增加,而痤疮丙酸杆菌在这些皮损中分布<2%。提示与痤疮丙酸杆菌在健康人群皮肤中的主导地位相比,葡萄球菌可能是痤疮发病机制中另一重要因素。此外,葡萄球菌与痤疮丙酸杆菌的关系还表现为表皮葡萄球菌能通过发酵甘油产生琥珀酸降低细胞内pH,从而增强对痤疮丙酸杆菌的抑制作用。反之,痤疮丙酸杆菌通过水解三酰甘油和分泌丙酸的方式调节毛囊皮脂腺单位的pH值,从而限制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化脓性链球菌的繁殖[24],推测这种相互作用对于维持正常毛囊皮脂腺微生态平衡有重要意义,也为通过微生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在痤疮治疗中的作用提供新思路。
2.3 其他微生物与痤疮
Numata等[25]对100例痤疮患者和28名健康人皮肤拭子的取材研究证实,痤疮与马拉色菌之间有显著相关性。Thomas 等[26]发现马拉色菌可使角质形成细胞分泌 IL-1β、IL-6、IL-8 及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使IL-10分泌减少,加重炎症反应。此外,Kelhälä等[27]发现虽然痤疮患者与健康受试者毛囊皮脂腺内的痤疮丙酸杆菌数目并没有显著差别,但是有5种菌群(链球菌、梭形杆菌、兼性双球菌、颗粒链菌、奈瑟菌)在正常人群和痤疮患者的面颊部的含量大不相同。Somboonna等[28]发现泰国健康青少年面部占主导的菌群为芽单胞菌、浮霉菌、硝化螺旋菌,而患有痤疮的青少年以及健康的年长女性面部则是厚壁菌更常见,这与美国和中国的研究不同。因此在考虑毛囊皮脂腺微生态与痤疮关系时,年龄和地域也是要考虑的因素。其他微生物,如幽门螺旋杆菌、消化道链球菌等可能与痤疮相关,但其相关性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明确与研究[29]。
3 皮肤微生态失衡与痤疮
正常微生物之间存在着竞争和制约的关系。微生物以活性、休眠和失活3种状态存在,微生物的不同存在形式,其组织病理机制也不尽相同[19]。根据Blaser和Fallkow 的假设[30],微生物某一种群的减少或是消失是由于另一种群的过度生长,从而导致整个微生态失去平衡,如西方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痤疮丙酸杆菌在人体皮肤的优势,可能与西方饮食习惯和抗生素的滥用有关[31],从而使原本无害的微生物种群转变成条件致病菌。
皮肤微生态失衡也会通过影响皮肤屏障进而影响痤疮。皮肤能产生糖皮质激素、多肽和神经递质等,这些化学物质会影响皮肤微生物的黏附、生长和毒力。有研究表明汗液中P物质在压力诱导下增加,其与痤疮的发生和屏障功能破坏有关,而这种P物质的改变与皮肤微生物群变化密不可分[32]。抗痤疮外用药物和化妆品的不当使用及皮肤的过度清洁会导致经表皮失水量增加等一系列皮肤屏障功能损伤[33]。因此,科学合理的使用治疗痤疮的外用药物,避免耐药性的产生,以及选择适当的皮肤屏障修护剂也是痤疮治疗方案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4 皮肤微生态与痤疮防治
毛囊皮脂腺微生态与痤疮密切而复杂的关联在痤疮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临床上首选四环素类如多西环素、米诺环素等低剂量抗生素控制中重度痤疮的炎症反应。但是Ozuguz等[34]发现,口服四环素3个月,会导致痤疮患者口腔和鼻腔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携带量增加,提示抗生素治疗不但会导致微生物耐药性,还会破坏皮肤微生态平衡。Kelhälä等[27]发现痤疮患者口服异维A酸和赖甲四环素对面颊、背部、腋窝的皮肤微生态产生影响,2种药物均能显著降低痤疮丙酸杆菌的含量,异维A酸是通过减少皮脂分泌而减少痤疮丙酸杆菌,但皮脂分泌的减少,可能导致链球菌和葡萄球菌比例上升,产生类似于特应性皮炎患者皮肤微生物的组成。
抗菌肽参与皮肤固有免疫应答,可以对抗包括痤疮丙酸杆菌在内的革兰阳性菌。角质形成细胞中的人类 β-防御素 -2(human beta-defensin-2,hBD-2)在炎症反应时上调,并且在皮肤中集聚,从而发挥抗痤疮丙酸杆菌的作用[16]。细菌的噬菌体也可以用来对抗痤疮丙酸杆菌,以此减少抗生素的使用[35]。Huang等[36]认为,宿主对于痤疮丙酸杆菌的适应性免疫调节促进了痤疮疫苗的发展,痤疮特异性抗体可以在不影响皮肤微生态、人体内稳态的状态下改善痤疮炎症反应。还有学者认为,痤疮是一些系统性疾病的早期表现,如胰岛素抵抗、肠道微生态失调、营养不良等。植物性食品和补充剂的摄入,特别是富含纤维和多酚的食品,可以为寻常痤疮提供天然、低风险的干预,所以皮肤毛囊皮脂腺微生态也可能通过干预肠道-皮肤轴来调节[29]。微生态与痤疮密切的关系也提示可以通过微生物之间相互抑制从而减少致病微生物在毛囊皮脂腺内的定植,从而达到治疗痤疮目的。针对无毛小鼠的动物实验表明,口服益生菌可以调节角质层的完整性,减少氧自由基的产生,减少在紫外线照射下的经表皮失水量[37]。在临床试验中,口服益生菌可影响皮肤IGF-1和FOXO1蛋白(forkhead box protein O1)的基因表达,两者均可调节皮肤炎症和局部修复过程[38]。但如何通过外用皮肤益生菌干预皮肤微生态尤其是毛囊皮脂腺微生态的平衡来达到预防和治疗痤疮,未来仍需要更多研究。
5 结语
毛囊皮脂腺微生态是人体皮肤微生态重要组成,与痤疮等毛囊皮脂腺疾病密切相关。对皮肤微生态包括毛囊皮脂腺微生态的认知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需要开展更多研究去探索外界环境、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对毛囊皮脂腺微生态的影响,以及微生态的变化是如何导致痤疮的发生发展,并以此为基础更好地研究开发抗痤疮新的预防和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