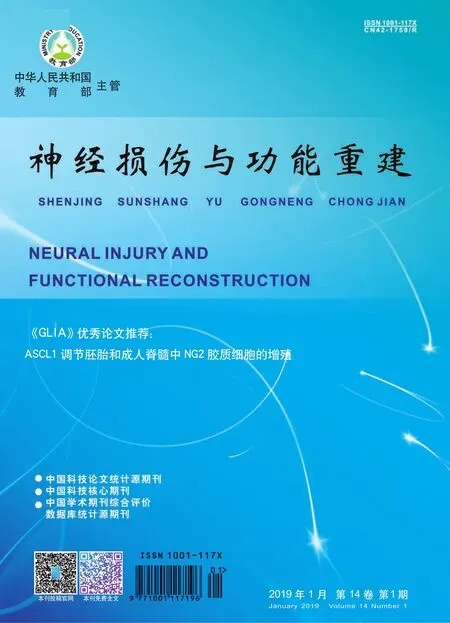小胶质细胞极性调节与神经损伤修复研究进展
张智静,罗涛
小胶质细胞(microglia,MG)是属于单核巨噬系统的中枢神经髓系细胞。作为高度活跃的先天性免疫细胞,其与神经创伤、卒中等密切相关。随着神经损伤的发展,MG也呈现出动态的亚型转化。一方面,MG释放大量促炎因子及神经毒性物质,加重损伤;另一方面,通过其吞噬功能及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MG可促进神经修复。本文将对小胶质细胞极性调节与神经损伤修复进行简要综述。
1 MG的极化
在生理条件下,MG并非完全静息,它们负责维持神经活动,保持内环境的稳定[1]。未活化的MG呈分枝状,突起长,细胞胞体小,核周细胞质较少。而一旦微环境改变或受到病理性刺激,MG会被激活,此时细胞体增大,突起变粗回缩,突起上可见小棘。它们将迅速迁移到损伤部位,增殖、分化。随着损伤的进展,MG的形态逐渐呈“阿米巴状”,参与神经修复的过程[2]。
活化的MG根据其目前较明确的功能及标志物,可分为 M1、M2亚型。干扰素(interferon,IFN)-γ、Th1细胞因子、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4,TLR4)相关配体、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s,LPS)等可诱导活化M1型MG,其主要参与抗原呈递及细胞内病原体的清除。因此,许多相关受体及酶的调节都涉及其中。例如,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Ⅱ,MHCⅡ)、CD86及Fc伽马(fragment crystallizale gamma,Fcy)受体上调以促进MG的抗原提呈能力和增加与其他免疫细胞的信息交流。正常情况下的MG活化有利于机体清除坏死的细胞及病原体,但一旦MG被过度激活,M1型MG将产生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IL-6和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等大量的炎症因子及神经毒性物质,进一步加重炎症反应,扩大神经损伤。M1型MG是IL-12的主要来源,这提示可根据高表达IL-12、低表达IL-10的特点和上述MHCⅡ、CD86、Fcy等常见的标记物以鉴别M1型MG。
与促炎的M1型MG相比,M2型MG则倾向于表达抑制炎症的相关细胞因子及受体,当中包括分泌IL-10或几丁质酶-3样蛋白(chitinase 3-like 3/YM1)、鸟氨酸、多肽等细胞外基质保护蛋白以下调炎症细胞及促进创伤修复;上调更多的吞噬相关受体以清除死亡细胞的碎片及异常积累的蛋白等[3]。根据不同的环境刺激,M2型MG能进一步分为3种亚群:①M2a型,由IL-4、IL-13诱导得到,通过增加精氨酸1(arginase1,Arg1)、清道夫受体等吞噬相关受体,抑制核转因子-κB(nuclear factor-kappa B,NF-κB)等通路,控制炎症。②M2c型由IL-10、糖皮质激素或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活化得到。该亚型似乎参与炎症被抑制后的组织重塑及基质沉积。③当暴露于免疫复合物或TLR被激动时,可观察到M2型MG的第三种亚型——M2b型。M2b亚型与M1型MG相似,具有高水平MHCⅡ及CD86的表达,提示M2b型MG仍保留刺激T细胞的能力,该亚型可能在M2型MG反应中扮演着启动及调节的角色。另外,M2b型MG虽也具备高表达IL-10、低表达IL-12的M2型MG的一般特点,但却缺乏Arg1、YM1或FIZZ1(found in inflammatory zone1)等M2亚型的特异性标志物[4]。
2 MG在神经损伤中的作用
2.1 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
SCI是神经系统的一种严重创伤。脊髓的组织修复及功能重建在SCI后难以进行,这不仅与神经细胞微弱的再生能力相关,还与SCI后快速出现的阻碍轴突再生的胶质疤痕有关。而这种继发性损伤,可造成MG空间及时间上的活化区别[5]。不同亚型MG的活化,可影响SCI的预后。已有研究观察到,在SCI模型中,M1型MG神经毒性明显,表现为神经元的数量减少,轴突生长受抑制。此时,神经元轴突分枝多,呈短树枝状。而M2亚型未引起神经元上述病理改变,且神经元轴突长度增加,分枝减少,呈单极或双极的轴突生长。同时,SCI后,与神经修复密切相关的M1(CD86、CD16/32)跟M2亚型(CD206、Arg1)的蛋白及RNA均上调。然而3 d后,M1型MG活化继续增强,M2亚型下降[6],提示M1型MG是持续损害及缺乏修复的原因之一。Antje等不仅观察到相似的现象,同时还发现不同物质引起的MG的吞噬功能可影响其极性调节。其中,MG吞噬髓鞘后,NF-κB信号通路被抑制,M2型MG活化加强,神经突长度及分支的总数量均增多。TNF虽不影响MG的吞噬功能,但可减弱吞噬作用介导的M1亚型向M2型MG转换,CD86、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等M1亚型标记物显著增加。同时,细胞内铁的累积,可通过促进TNF的分泌,使MG向M1亚型极化,加重神经损伤[7]。
目前研究表明,药物治疗诱导MG表型从M1亚型向M2亚型转变对于缓解SCI有实际性意义。CX3C趋化因子受体1(CX3C chemokine receptor 1,CX3CR1)是MG特异的趋化因子受体。最近,Freria等[8]发现,脊髓损伤后,CX3CR1-/-小鼠新生突触的形成及运动神经元数量较CX3CR1+/+增加,前后肢协调性也得到改善。这提示,CX3CR1可作为特异性干预靶点,减轻SCI后巨噬细胞或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改善神经损伤。此外,TLR2特异性受体激动剂Pam2CSK4,可增强M2型MG的活化,对激光诱导的SCI有神经保护作用[5]。给予SCI小鼠醛糖还原酶(aldose reductase,AR)抑制剂后,M2型MG标志物Arg1表达增强,SCI的炎症反应及脱髓鞘病理改变缓解,运动功能恢复[9]。
2.2 脑创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
M2型MG可通过神经、髓鞘、血管及少突胶质细胞的再生,促进TBI的恢复[10]。但在TBI 1周后Arg1+细胞已减少至不能被检测到的水平,而M1型MG及促炎因子在损伤后数周到数月仍持续存在[11]。为了进一步验证M2型MG在TBI中的作用,Hsieh等[11]使用老年小鼠建立TBI模型,相对于年轻小鼠而言,其M2亚型的应答减弱,结果发现老年小鼠损伤面积更大,提示M2型MG可促进TBI的神经修复,损伤后期M2亚型的不足,可能是TBI难以恢复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利用转基因动物及药物的干预,使MG在TBI中的调节作用得到更深入的探索。Morganti等[12]使用CCX872、CCR2选择性拮抗剂,能显著减少M1及M2亚型巨噬细胞多种相关基因的表达,同时促炎因子和神经毒性介质减少,认知功能改善。与此观点一致的是,CCR2-/-小鼠,在控制性脑皮质撞击(controlled cortical impingement,CCI)或TBI模型早期,巨噬细胞的数量较野生型减少,运动、认知功能及神经元的存活均改善[13]。除此以外,现还有几类药物已被证实可有效地改变TBI中M1及M2亚型MG的活化,如骨形态发生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BMP)内源性拮抗剂[14]、α-7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4]等。
Hsieh等[11]认为,TBI的急性及慢性期神经损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不同亚型的MG介导的。考虑到M2型MG在TBI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在损伤后使用药物干预以改变MG的亚型及功能,可能是TBI新的治疗方案。
2.3 卒中
在缺血性卒中中,MG在缺血核心及边缘区域活化得到的亚型是不同的[15,16],受伤的程度将影响MG的活化。卒中及缺血再灌注引起的炎症是中枢系统组织损伤的重要原因,卒中所造成的微环境变化有利于促炎小胶质细胞亚型的活化,M1型MG在缺血性损伤发生的14 d内持续增多,促炎反应在当中占主导地位。但抗炎相关信号分子也正试图参与炎症的调节[16]。在缺血性卒中后的12 h,M2型MG达可被到检测到的水平,并在1~3 d达到高峰,但在损伤的数天后数量逐渐减少。恰当的M2型MG活化能增强缺血性卒中后的抗炎作用,促进轴突重塑及血管再生[15,16]。与此观点一致的是,M2亚型诱导信号IL-4、IL-10的上调,能改善缺血性损伤小鼠的功能恢复[17,18]。
相较而言,MG在出血性卒中的极化尚未明确。在颞叶出血后6 h,M1亚型急剧增多,随即在损伤后14 d内呈下降趋势。相反的,M2型MG在损伤后第1天开始增多,并可持续到14 d后[19,20]。虽然在第1天到第3天内M1及M2型MG是共存的,但在损伤后的7d内,M1亚型有逐渐向M2亚型转化的趋势[21]。
在血管内直接注射M2型MG后,脑实质的重塑因子,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TGF-β,及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9)等增多,可促进血管再生,抑制神经元凋亡。此外,巨噬细胞分化 抗 原 1(macrophage differentiation antigen associated with complement three receptor function,Mac-1)的上调,使M2型MG可透过血脑屏障到达脑实质损伤区域[22]。与M1亚型相反,M2亚型似乎在损伤愈合及神经保护方面起积极作用[20]。
Abdullah等[23]证实,在小鼠的大脑中动脉闭塞(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MCAO)模型中,干扰素调节因子4(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IRF4)可明显促进M2型MG的启动及活化。在离体MG中,Fingolimod作为鞘氨醇1-磷酸盐受体调节剂,可调节STAT3信号通路,促进M2型MG活化及少突胶质细胞再生,缓解认知功能障碍及白质完整性的损伤[24]。天然产物Pinocembrin通过TLR4信号通路抑制M1亚型的活化,进而缩小病变面积,改善脑水肿及神经缺损程度[25]。目前有数种药物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19],选择合适的时机及恰当的程度以调节MG亚型的转化,这有可能是未来卒中治疗的一个研究方向。
2.4 M2亚型是否总有益?
并非所有观点都认为抗炎性M2型MG是一种有利的细胞类型。目前有学者证实,肿瘤细胞的炎症反应及迁移能力与M2型MG有关[26]。M2型MG可通过上调热休克蛋白70家族成员葡萄糖调节蛋白78(glucose regulated protein78,GRP78)的表达,从而使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因子3(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3,STAT3)磷酸化。随即,肿瘤细胞内的炎症因子IL-1β和TNF-α释放增加,引发炎症反应,进一步促进肿瘤细胞转移。除此之外,抗炎治疗的神经修复作用也尚未得到确切的验证:非甾体类抗炎药(non-steroid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s)用于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患者的治疗缺乏明显的疗效[27];最近的一篇Meta分析也表明NSAIDs似乎并不能改善PD的患病风险[28]。抗炎性M2型MG在不同疾病的进展中,或体外诱导亚型转化用于阿尔兹海默病、卒中等疾病治疗的过程中,其可能已经成为一种失去正常功能的无效、甚至有害的细胞。
例如,在Chakrabarty等[29]的实验中,将携带IL-4的腺病毒载体注射进TgCRND8阿尔兹海默病小鼠CNS中以促进M2型MG的激活,与前诉观点不同,其中枢神经系统内的淀粉样蛋白反而增加。另外,即使M2亚型表达的Arg1有助于伤口修复、基质沉积及轴突再生,但过多的多肽不利于神经修复;抑制过量多肽的产生可减轻中枢神经损伤[30]。与此同时,Desestret等[31]发现在大鼠MCAO模型的亚急性期,抗炎性M2亚型的增加并不能改善缺血性卒中的预后。虽然,该实验缺乏剂量反应曲线及长期效应,但也浮现关于MG治疗的一些担忧。M2型MG在神经损伤修复中的特定时期可能具有潜在损伤作用,其具体机制尚待进一步阐明。
3 展望
MG的极性调节在神经损伤修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MG亚型的动态变化,对于神经修复的调节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关于M1/M2极性调节的研究日渐增多。但仍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大量不同类型的受体是如何有效干预MG活化,其活化机制是怎样的,M1/M2活化亚型的最佳平衡状态如何,最佳平衡状态的潜在调节机制如何。
尽管MG的极性调节为促进中枢神经损伤修复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治疗方向,但临床的运用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许多M1或M2活化亚型诱导剂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全或无,而是与时间和剂量相关的。此外,M1亚型的潜在益处可能尚未被发现。因为若哺乳动物进化出M1型MG,这种细胞只能促进炎症,没有任何积极作用,这不大可能。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M2亚型长期维持在高水平可能会对免疫防御产生负面影响,并导致严重的后果,如肿瘤的发生。因此,研究者必须谨慎地在适当的时间增加正确的亚型,以加强在中枢神经损伤后的修复过程。最后,研究者对MG极性调节的认识大多来自啮齿动物,啮齿动物细胞的细胞特性是否真的适用于人类,仍是一个重要的疑虑。
随着MG的活化机制及特定的极性调节诱导信号的进一步阐明,MG与神经系统疾病的关系会趋于明朗。如何有效适时地调节MG的极性,平衡M1/M2亚型之间极化,这将成为促进神经损伤修复的重要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