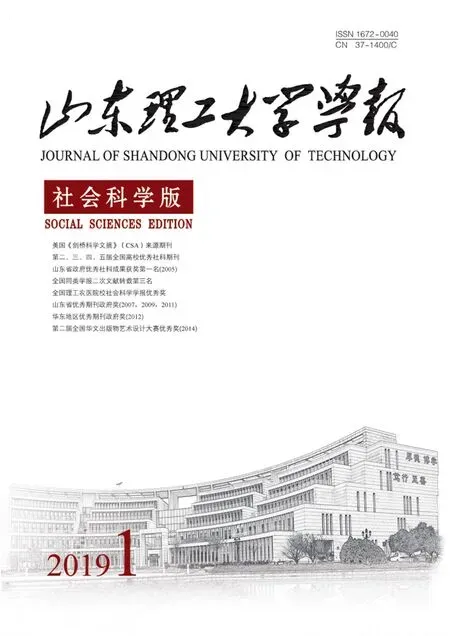论新世纪中国侦探小说的深层结构模式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255000)
侦探小说是融情、智、理、趣为一体的现代小说类型。它往往以侦探人物为主人公,展示其通过逻辑推理,或借鉴科技手段,揭开罪案之谜的过程。作为一种典型的叙事性文体,侦探小说的情节结构是诸多研究者以及阅读者关注的重要问题。英国侦探小说作家P.D.詹姆丝认为这类作品“一定要以一个谜案为中心,小说到了最后,解谜破案的方式要合理且令人满意……应该要从书中尽管有意误导却仍如实呈现的线索中抽丝剥茧,推论出答案”[1]9,强调谜案在情节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认为侦探小说结构可划分为“犯罪的故事”和“侦破的故事”两部分,前一个故事讲述实际发生的案件,是一种隐形的故事,未在小说中露面,却具有真实可靠性,对应着文学术语中的“素材”,而后一个故事则解释读者如何获悉真相,借助其他人(侦探)向读者转述证人看到的场景以及听到的对话,在小说中现身说法,对应的正是对素材的演绎方法[2]5-7。英国诗人W.H.奥登把侦探小说的情节概述为:“一件神秘的罪案发生了,许多人涉嫌,最后除真凶外均被排除。罪犯被捕或死去”[3]397,后被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简化为“凶案发生,嫌疑产生,发现真凶,绳之以法”[4]73,更为简单清晰。
新世纪阶段获得进一步发展的中国侦探小说,在情节结构方面仍遵从于该类型的固有模式,对其情节模式和结构模式的探讨,即是对侦探小说相应模式的研究。同时,受全新时代背景以及多元创作群体影响,该时段的中国侦探小说情节结构产生了新的特质,亦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一、新世纪中国侦探小说的表层情节模式
考察侦探小说的情节模式,研究者需要提取小说的主要情节要素,俄国文论家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普罗普的“叙事功能”理论,恰为研究提供有益参照。在《故事形态学》一书中,他从人物行动着手,对100个俄罗斯民间故事进行研究。在归纳故事情节的内在规律时,他提出人物的31种角色功能,包括“外出”“禁止”“最初的反抗”“宝物的提供、获得”“归来”“举行婚礼”等。这些功能是故事中稳定不变的因素,数量有限且全部属于一个轴心,而且大量功能成对排列出现[5]24-59。作为小说中人物的行动体现,这些功能连缀为一体,清晰展现了小说主要情节的发展走向。受普罗普的理论影响,论文对侦探小说的情节结构进行探讨时,首先会对其表面叙事素材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一种确定的文本秩序,以此体现出小说的整体叙事内容以及事件走向。同时,论文将会比较多个文本的叙事走向,从中找到被固定化乃至程式化的发展趋势,从而确定出该类型的情节模式。
以新世纪中国侦探小说具体作品为例,鬼马星的《风的预谋》沿袭了古典解谜派的小说写作。在小说中,几起连续发生的凶案引起警方注意,凶手“星光之箭”在极度诡异的谋杀现场留下相应物品,并预留数字与字母作为线索,暗示警方下起凶案情况,使案件侦破变为警匪双方的斗智游戏。刑警高竞与女友莫兰联手,从“星光之箭”留下的种种线索入手,推断凶手的真实身份以及作案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但在侦查过程中,几起凶案接连发生,一方面为二人的调查增加难度,另一方面也提新的线索。最终二人依靠逻辑推理以及线索指证,成功找到真凶,并对几起案件真相进行还原。小说的主要角色功能可概括为:命案发生—警察(亦即侦探)介入—警察调查现场并询问相关人员—警察依据线索推理—新的命案发生—警察调查现场并询问相关人员—警察获取新的线索并依据线索推理—警察锁定真凶并还原案件真相。
雷米的《心理罪之画像》以“犯罪心理画像”作为侦探破案的重要手段,对人的内心世界观照使其更贴近心理悬念派的写作路径。在作品中,某大学连续发生数起凶残命案,从事犯罪心理画像研究的大学生方木,受警方委托参与调查,他试图从已发生的几起案件中梳理有效线索,但“凶手”孟凡哲的主动伤人行为使其被警方逮捕,宣告案件终结。紧随其后,新的案件发生,促使主人公继续调查,最终,方木综合多条全新线索,锁定真凶为图书管理员孙普,在“自卫”的情况下将其击毙。小说的主要角色功能可以概括为:命案发生—侦探受委托介入—侦探调查现场并询问相关人员—侦探依据线索推理—“凶手”暴露且案件“告破”—新的命案发生—侦探调查新的现场并询问当事人—侦探获取新的线索并依据线索推理—侦探锁定真凶并还原案件真相。
社会推理派代表作品《R的悲剧》以真实的“小悦悦事件”为蓝本,采用第一人称多视角的叙述方式,使7个案件相关人物相继登场,以来信、声明、会议发言、内心独白、作文、日记、遗书、自首、结案陈词等不同言说方式,阐发不同社会个体对于整个社会以及“美娇事件”的认识。文本的核心事件是小美娇被汽车撞倒碾压,肇事车辆逃逸,警察石康需要查找凶手。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目击者之一的彭浩君因“意外”死亡,牵扯出一个“替天行道”的“R”,向曾目睹事故现场却不曾施以援手的人发出恐吓信,要求他们在媒体上公开承认不作为的“罪行”,否则将对其施以惩罚。石康借助现场调查以及逻辑分析,找到肇事逃逸凶手,并锁定害死目击者的“R”。如果将小说错综复杂的多人叙述还原为单线时间逻辑,那小说的主要角色功能可以概括为:肇事案件发生—警察(亦即侦探)介入—警察调查现场并询问相关人员—警察依据线索推理—“疑似”命案发生—警察调查新的现场并询问相关人员—警察找到肇事凶手—警察锁定真凶并还原案件真相。
上述三部作品归属于不同的侦探小说流派,情节叙述侧重点亦有所差异:古典解谜派强调作品核心谜题的构造与解答,心理悬念派则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窥探和审视,社会推理派更关注对社会问题和人性丑恶的揭示。但通过上述几部作品的主要角色功能分析,侦探小说的基本叙事情节却保持高度一致,其情节模式也可以被概括为“案件发生—侦探出场—侦查线索—真相大白”。“案件发生”这一存在于过去时段中的“犯罪的故事”,通过现在时段的“侦探出场”以及“侦查线索”,在未来时段还原案件原貌,促使“真相大白”,完成“侦破的故事”,三个不同时段被侦探行为有效整合。
如果从单个文本的角度审视这一情节模式,这无疑符合法国学者克洛德·布雷蒙提出的“逐渐改善”[6]159-167叙事序列:侦探人物在面对案件发生这一“情况形成”时,“采取行动”(调查活动以及推理线索),通过“任务的完成”(查清真相)、“对敌的消除”(锁定凶手)以及“酬报和惩罚”(将凶手绳之以法)等结果的实现,完成促使事情逐渐好转的叙事目的。但如果对多部侦探小说,特别是构成系列的侦探小说情节模式进行分析,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提出的“平衡状态—平衡状态被打破—平衡状态恢复”[2]59叙事模式更为契合。在第一个案件中,初始的“平衡”状态被压缩至较小比例,自“案件发生”亦或“犯罪被人发现”开始,文本即进入“打破平衡”状态(稳定的社会秩序被罪犯破坏),侦探的相关探查行为以及指证凶手尝试,目的都在于恢复已被破坏的社会平静,最终的还原真相行为,亦真正使文本“恢复平衡”(社会秩序重归稳定),但案件侦破后的“平衡”状态与案件发生前的“平衡”已无法等而观之。随后的案件中,已被恢复的“平衡”状态再次被打破,侦探进入新的侦查活动中,目的即重新“恢复平衡”,每个案件都在重复同样的事件流程。
二、新世纪中国侦探小说的深层结构模式沿袭
值得注意的是,侦探小说的情节模式对应着“编码—解码”的过程发展,其“故事的焦点应是根据主要物证构成的实情查明已发生的一系列若隐若现、扑朔迷离的事件的实际顺序与意义”[7]61。在这种情况下,被置于错综复杂的事件脉络以及交错繁复的人际关系中的侦探人物,调查相关人、物证明,理清主要线索并进行侦缉推理,最终揭开真相,无疑是小说情节的主要构成部分。在这一部分之中,存在着重要的二元对立以及转化模式,“这些二元对立面形成隐藏得很深的行动素模式的基础,单独的故事表层结构就是从这种模式的结构中派生出来的”[8]352。具体来说,侦探小说中的“真—假”二元对立以及转化关系构成其独特的深层结构模式。
侦探小说的情节发展最终指向事情真相的还原,无疑呈现为“真”的存在状态,但在事件发展抵达“真”的过程中,小说中出现的丰富人证与物证提供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线索,反而会将侦探导向各种与事实相悖的假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事、物都具有了“假”的性质。《迷离之花》中的周怡,甫一出场就被女儿项青作为“替罪羊”,后者以“大义灭亲”的姿态,向警察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怀疑。兼之周怡情人的被杀,更加重了她的嫌疑,导致案件侦查阶段的事件发展一直蒙着“假”的面纱。《危险家庭》中的普晴,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对家人造成伤害:将丈夫和女儿置于煤气泄露的家中,并以刹车失灵的电动车带女儿冲下陡坡……在旁观者眼中成为精神错乱的典型。但在小说的真相还原阶段,普晴之夫为了实现离婚目的,伪造多个事故现场的险恶用心得以暴露时,案件侦查阶段的各件事情皆变成“假”的障眼法。《心理罪之第七个读者》中,出现在图书馆同一张借书卡上的部分学生先后被杀,了解案情者都将借书卡称为“死亡借书卡”,主人公方木推断被害者应是从这本书中获知了凶手的秘密,并在案件侦查阶段一直坚持这种看法。但在结尾处凶手自陈心迹时,多人的死亡并不是因为书籍中隐藏的秘密被泄露,而是因为“死亡借书卡”这一物件所激起的惊恐、猜疑唤醒了他作为杀手的力量,促使其继续行凶。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借书卡”一直是迷惑侦探侦查的“假”道具。
更重要的是,这些以“假”的状态存在的推理、凶手指证以及结论会一再重复出现,直至最终真相还原。《清明上河图密码》中的“范楼案”,曹喜被视作杀死好友董谦并割下其头颅的元凶,只是因证据不足,暂时被放回家中。赵瓣儿受朋友委托,决心查出案件真相。在听完目击者的证词后,她作出“曹喜醉酒,真凶杀死董谦并成功借助曹喜掩护自己”的推论,但嫂子温悦提出的三个疑点将推论驳得千疮百孔,促使她与朋友前往现场进行调查。随后,瓣儿接连怀疑过酒楼仆役穆柱以及酒席陪客侯纶的凶嫌身份,也被既有的事实推翻。在拜访死者父亲时,完全疯癫的董父说了一句“那不是我儿子”,无意中揭示出案件的新一种可能——死者并非董谦。瓣儿由此大胆推测出“董谦搀扶酒醉的曹喜进错房间并遭遇凶杀现场”的“真相”,但进一步结合现场情况进行分析,董谦并非无意进错房间,而是有意将曹喜置于犯罪现场承担罪责。至此,董谦的策划人以及加害者身份彻底暴露,此前案件呈现出的假象以及瓣儿作出的“假”的推理被一步步推翻。以此观之,“假”的状态在侦查阶段一再出现,甚至作为固定状态被维持着,直到还原事相阶段,“真”才成为小说叙述的真实状态。基于此,侦探小说的基本叙述逻辑可被概括为:一系列假的事情不断产生、发展,借助侦探人物的有效行动,最终指向或抵达确定的真实结尾,“假—假—假……—真”是对这种发展状态的简要概括。
上述涉及的多部小说,多属于单线结构,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叙事发展逻辑,直接体现出小说“真—假”二元对立以及转化的深层模式。除此之外,多线结构以及嵌套结构也是新世纪侦探小说的常见结构。多线结构作品如上文所分析的《R的悲剧》,综合多条线索后可被整理为清晰的线性发展过程,仍是“真—假”二元对立模式的有效证明。嵌套叙事则打破了线性叙事不断回到原初事件、核实矫正细节、直到真相大白的惯有流程,以多层叙事构成小说内容。这种结构的多层叙事多由以下几个层次构成:文本最内层,也是核心层,是传统的侦探叙事,按照单线结构发展,“真—假”二元对立以及转化深层模式依然存在。但在“真相大白”阶段,该叙事层会发生偏转,导向偏外层叙事。偏外层叙事的存在,既补充了侦探叙事层面的重要遗漏内容,也指出侦探叙事层面的虚构性,即侦探叙事层是由本层叙事所虚拟出的一个故事。其后不断向外扩展的各叙事层延续了上述关系。
以文泽尔的《荒野猎人》为例,小说的第一、二部分讲述了主人公“我”在林间木屋经历的四次离奇“案件”——熊、蛇、狐狸以及渡鸦四种动物分别被以“不可能”的方式杀死在木屋这间密室中。第三部分则是来自于设谜人的解答,一方面叙述了设谜人对“我”的刻骨仇恨,另一方面将诸种诡计的内情娓娓道来。上述三部分共同构成小说最内层的侦探叙事,完整地还原了“案件”的全貌,“真—假”二元对立以及转化的深层模式得到体现。但紧随其后的第四部分是一个小女孩的日记,点明一、二部分以及第三部分分别出自她的父母之手,是关系矛盾的二人以小说笔法完成的较量式写作,被自己重新组合后呈现出来,蕴含着孩子对父母重归于好的期望。在这种情况下,前三部分的侦探叙事从现实事件变成了单纯的“纸上游戏”。第五部分进一步瓦解前文叙述的现实性,写作者以“作家后记”的形式申明前文全是自己的艺术虚构,并从叙事形式、人物构成、案件谜题等多个方面畅谈个人的创作意图。最后一部分“真正的后记”,则是本书的真正写作者,所书写的常规书籍都具有的普通后记。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所包含的六个部分涉及四个不同的叙事层次,除了最外层的现实叙事,其它多个层面的叙事都被证明是虚拟的,具备了人造的“假”的状态,与现实的“真”形成新一重“真—假”二元对立以及转化关系。
三、新世纪中国侦探小说的深层结构模式新变
新世纪中国侦探小说在遵循“真—假”二元对立以及转化深层模式的基础上,试图探寻新的发展可能,引入了“非真”和“非假”两种全新状态。二者是介于“真”和“假”之间的特殊状态,因小说世界中的“事实层面”与“认知层面”差异所产生。两种状态兼具“真”“假”双重因素,只是程度存在差异,与清晰明了且确凿无疑的“真”与“假”相比,具备模糊暧昧的特性。
“非真”状态多存在于历史推理作品中。所谓“历史推理”小说,一般以历史事件、案件或谜题为推理对象,由同时代人或现代人进行案件调查以及逻辑推理,最终实现还原历史“真相”的叙事目的。小说中的历史事件、案件或谜题多为史实,部分则是经典文学作品虚构出的历史故事,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都曾被新世纪侦探小说作品化用改编。在这些作品中,部分侦探为现代人物,因为特殊原因与历史案件产生联系。他们根据能够查证的历史资料,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诸多客观因素,进行逻辑推理,彻底颠覆公众信以为真、习以为常甚至奉为圭臬的历史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真相”的假面被剥落,事实得以呈现,但这是仅限于侦探以及少数人知情的事实,因为在多数受众的观念中,历史“真相”已经根深蒂固。基于此,假象以“真”的方式存在并被推崇,取代“真”的位置,似乎成为“真”,具备“真”的因素,但究其实质,它仍是“假”的内容。在小说中,“事实层面”或者说本质上具备假的特质的事物,在公众的“认知层面”却具备真的价值,亦即公众认可的“真相”,正是“非真”状态的直接体现。20世纪上半叶,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和约瑟夫·铁伊分别以短篇小说《断剑》和长篇著作《时间的女儿》,对公众认知与事实真相之间存在的巨大裂隙进行揭示,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更在其短篇小说《叛徒和英雄的主题》中,以向《断剑》致敬的方式,书写出革命运动中的荒诞“幻象”。美国作家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的硬汉侦探菲利普·马洛,虽然接触的并不都是历史案件,但却以个人判断为标准,有选择地将事件真相告知当事人,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小说结局的“非真”状态实现。
在新时期阶段的中国侦探小说创作中,部分侦探继承了传统侦探的人道主义精神,有选择地将事件真相告知当事人,为小说结局预留了一个“非真”的发展可能,如莫怀戚的《饮鸩情人节》以及尹曙生的《教授之死》,但并未对其进行深入探讨。直到新世纪阶段,中国侦探小说创作在向历史题材不断开掘时,真正将这一状态视作重要问题进行表现。E伯爵的《七宗罪之愤怒》以多封信件构成,讲述维克多·麦肯道尔向亚森·加达神甫求证多年前父亲死亡事件真相的故事。在信件中,他附上了当年的多篇新闻报道以及案件经办人特雷尔探长的几封回信,以此勾勒出事件原貌:十五年前,他的父亲麦肯道尔爵士救助落水好友未遂,二人双双遇难,但其壮举仍被民众称颂。作为唯一了解真相的在世者,神甫在回信中肯定了探长对事件过程的讲述,但却提供了不同版本的解读:爵士并非舍己救人的道德楷模,而是痛下杀手的真凶,因诡计被神甫识破而被迫自杀。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认知中的“英雄爵士”只是被美化过的虚幻“神话”,其罪恶行径也在被贵族阶层颠倒黑白后,变成大家称颂的“真善美”德行。更可悲的是,这种“以假为真”的行为方式始终无法在小说所营构的世界中得以纠正,因此,杀人凶手将永远被视为“英雄”而受到民众敬仰。事实层面的“假”无法战胜认知层面的“真”,使小说结局留在“非真”状态之中。
与此相对应的是周浩晖的作品《摄魂谷》。在作品中,中国西南边陲的某少数民族部落,一直坚信流传数百年的传说,将明末清初大将李定国视为部族的最大仇敌。通过侦探罗飞的调查,历史真相得以显露:李定国本打算帮助该部族击退清军攻击,却在内奸手下的诬陷中成为部族的敌人,并被部族勇士杀死。部族祭司基于众人了解的“事实”,决定对李定国的灵魂施以最恶毒的诅咒。虽然部族首领之女了解真相,但为了捍卫手下民众的民族信仰与荣誉感,她被迫隐瞒事实。基于此,被民众视为“民族历史”的错误观念仍代代流传,而真相永无见天日之时,只是少数人知道的秘密。小说最终虽向读者揭示出真实事件,但仍无法纠正文本中民众获知的“非真”信息以及树立的“非真”信仰。
“非假”状态的产生,往往与现代人复杂幽微的内心世界波动以及精密严谨的犯罪行为技巧有关,亦是新世纪这一全新时代的独特产物。与传统社会犯罪行为的简单直接(以刀枪等武器进行犯罪行为,简单掩饰犯罪痕迹)相比,现代犯罪分子往往会布置复杂的犯罪现场,采用高端的犯罪手段,并将人的内心世界作为博弈斗争场所。在小说结尾处,侦探虽破解犯罪手法,还原事实真相,但对部分难以触及的内容,仍无法完全还原。这导致小说呈现出的最终“真相”,虽符合事件发展过程,但因某些部分的“差之毫厘”,造成全局的“失之千里”,严格意义上只构成一种“非假”的状态。如果以上文所提到的两个层面进行界定,那就是小说结尾的真相,在“事实层面”具备“真”的特质,如真凶伏法、真事再现,但在“认知层面”,社会大众的理解与事实产生偏差,呈现为“假”的样貌。
别问的《记忆碎片》采取多线性叙事,从犯罪嫌疑人韩平的心理活动、犯罪嫌疑人韩平的日记叙述(作为警方的重要证物)以及警官冯阳的侦破活动三个方面同步展开小说叙述。在第一条叙事线索中,韩平个人近乎呓语般的心理活动,使事件过程显得模糊不清,但暗合第二条叙事线索。在第三条叙事线索中,冯阳凭借现场调查成功破解韩平制造的物理密室,并将其抓捕归案。二、三两条叙事线索结合,韩平的杀人动机暴露无遗:他先被女教师诱惑,后被无情抛弃,决定报复杀人。这一动机也为他赢得公众同情。三条叙事线索相互佐证,看似形成完整、清晰的闭环,但文末的第一条叙事线索突然翻转:韩平的心理独白指出日记的不可靠性,后者的价值即是被伪造出来混淆公众视线。同时,在韩平的内心独白中,真实杀人动机浮出水面:女教师害死韩平心爱的女生,他愤而为对方报仇。小说结局处的凶手被捕似乎实现了“真”的普遍状态,但真实的杀人动机仅为凶手本人所知,永远将公众隔离在外,则使案件带有一丝“假”的意味,最终只能将事件维持在“非假”状态中。
而紫金陈的《高智商犯罪2:化工女王的逆袭》以陈进独自帮助女同学甘佳宁复仇为小说的叙述主线。小说结尾,陈进本可逃脱出国,但他选择伏法认罪,并通过认罪陈述和诸多预先策划的行动,故布迷阵,令警方以及公众相信自己还有同伙。他的目的,即以虚假的“同伙”威慑伺机向甘佳宁的家人寻仇的被害者家属,保证甘佳宁家人的生活平静。警方对陈进的依法逮捕本已经使事情水落石出,达到“真”的状态,但并不存在却生活在公众幻想中的“同伙”却削弱了“真”的可靠性,使小说结尾呈现出“非假”的状态。
“非真”和“非假”状态的存在,并未动摇侦探小说的“真—假”二元对立深层结构模式,毕竟小说叙述所提供的上帝视角,使读者清晰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对事件真相产生直观认识。但就文本所建构的世界而言,这两种状态却具有重要价值。它们以自身模棱两可的状态属性,昭示出社会现实层面与公众认知层面的多重差异,促使阅读受众对文本中确定无疑的“事实”进行思辨,发掘其中不为人知的真实因素。更重要的是,两种状态的存在,突出了小说中的一类特殊群体——社会公众,他们或被蒙蔽,或被思想控制,或在真相显露眼前时坚持原有偏见,“决不允许旁人对他们的真理有所质疑,也决不允许旁人持有他们所认为的谬论”[9]57。“乌合之众”即是对这一群体的形象概述。这也为阅读受众提供了一个观照自身的对应物,使其在阅读过程中认真审视对方,继而认识那些“涌动个体生命激情的人”,以及个体生命如何“成为一俱俱充满活力与不断迸发着生命激情的血肉之躯”[10]86,以此思考现实中的个体以及群体真实处境,完成小说的现实指涉功能。基于此,产生于新世纪中国侦探小说中的“非真”“非假”状态,作为现实状态的文本投射,具有重要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