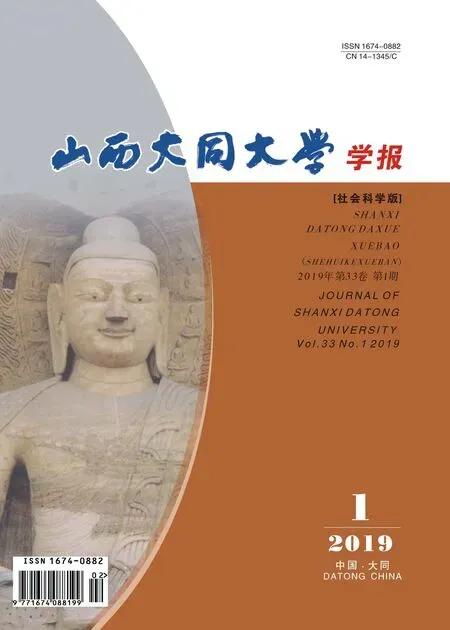王朔小说的快感表达及其意义阐释
张 伟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人文与传播系,安徽 芜湖241000)
引言
快感是一个非常复杂、多义的概念。最早指的是生理意义上的性快感,后转为古典主义美学倾向,成为理性的对立面,是一种“恶”的化身。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快感衍生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即被视为一种对抗体制和权威的先锋形式,是一种政治解放和经济生产的力量。
根据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思想,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够成为大众文化的文本,只有那些与大众具有相关性并能给大众提供快感的产品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文本。[1]王朔小说作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先锋和代表,不仅为大众读者提供了相关性,而且具有多种快感表达方式,这是王朔小说成为大众流行文化代表作最主要的原因。本文即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关注快感,也即约翰·费斯克所称的“大众文化的快感”。
一、王朔小说中快感表达的内容
王朔小说给读者提供的快感内容主要包括:
(一)话语快感 王朔小说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他的语言表达方式。他的小说语言幽默、犀利、口语化,敢于进行语言先锋实验,在有些对话中故意不加标点,这种语言表达方式使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既能获得一种情感的宣泄,又能获得一种话赶话的“速度感”和现场感觉。同时,王朔的小说还注重调侃,在调侃中消解、玩弄权威和权力体制,这也给读者带来一种戏耍、反抗和规避宰制力量的快感。如王朔经常把宏大的政治话语用于日常生活琐事,使人感觉到威严、宏大的政治问题受到了嘲弄和戏耍,通过这种戏耍,小说达到了一种消解权威、颠覆政治的效果,使读者产生一种话语诡计得逞的快感。
(二)“毁灭”的快感 王朔小说中的另一种快感形式是一种“毁灭”的快感,包括观看小说中的人物对自身的生活及对美好的人或事物的毁灭而产生的快感。例如,读者在阅读《过把瘾就死》、《空中小姐》时感受到了一种毁灭理想、爱情和婚姻而产生的快感。这种快感类似于悲剧所产生的效果,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打碎而产生的心灵震颤的感觉。除了对爱情和婚姻的毁灭,读者还可以通过阅读“顽主”们颓废、糜烂的生活感受到一种毁灭生活的快感。王朔小说中的“顽主”们什么都不“吝”,什么都不在乎,他们的生活方式给那些终日生活在重重压力下的普通读者带来一种放纵的快感,让他们在阅读中享受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这种对自身的放纵、对生活和理想的毁灭都具有一种拒绝和挑战社会体制的意味,属于躲避式快感的一种。
(三)叙事快感 王朔小说中还有一部分“单立人”悬疑探案系列故事。在这部分作品中,他把侦探、悬疑、色情、凶杀等元素融为一体,其代表作品有《玩的就是心跳》、《人莫予毒》等。这类小说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叙事和“生产”的快感。例如,《玩的就是心跳》讲述的是主人公方言有一日忽然被怀疑是杀人嫌疑犯,为洗脱嫌疑,他不断追踪、回忆十年前的一周生活并最终揭晓谜底。这是一个类似于迷宫的叙事文本,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猜谜的过程,通过不断预测故事的结局及起因,并不断印证自己预测的对错。这个过程会产生如同足球赛前观众预测哪支球队会赢得比赛一样的快乐感觉。这种快感属于“生产”的快感,不管读者预测得对与错,在这个过程中,读者都会生产出自己的文本,感受到一种生产新产品的快感。
(四)意义共享的快感 王朔小数所描写的人物大多处于社会底层,他们的生活是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顽主”们的生活方式、语言和行为方式,可能读者也曾经历过,所以,当读者在阅读这些小说时会感觉小说中的人物正在演绎着自己现在或曾经的生活,从而对他们产生一种认同感。由于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这使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之间有了一种意义共享的空间,这种共享的意义可能会迁移到读者的现实生活中,影响读者处理问题的方式。如读者可能会从小说中人物对事情的处理方式上获得解决自己生活问题的方法,当故事中的人物吐露了他们的心声或者做着某些他们也曾经做过的事情并且获得成功时,读者也从中获得了胜利的快感。读者会发现原来他们并不是孤立的,读者会从小说中获得一种认同和支持的力量,这种力量给了他继续生活的勇气和理由。
二、王朔小说快感表达的意义
王朔小说中的快感表达多种多样,具有多义性的特点,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中获得自己独特的快感并建构自己的意义空间。大体来说,其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神圣性的消解 快感发展到今天,早已超出了它原有的生理学上的意义,而成为一种政治解放的力量。这种力量虽然不会产生政治革命或激烈的对抗行为,但它所代表的进步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它时刻提醒着宰制力量自己的失败,并迫使统治阶级采取有利于社会大众的施政策略,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它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王朔小说中这种对抗宰制力量的政治意义,具体表现在对传统政治和文化神圣性的消解方面。这种消解让统治阶层苦心经营的神圣形象彻底崩塌,使人们认识到权威的虚伪和脆弱,并在阅读中获得一种对权威和体制冒犯的快感,这为人们摆脱旧的价值体系,建立一种更加合理的新型社会体制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首先,通过对宏大叙事话语的戏仿达到对权威神圣性的消解。王朔小说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通过戏仿假、大、空的革命政治话语和叙事方式,使读者认识到“文革”时期思想意识形态的错误和不人道,从而实现戏耍政治、解放思想的目的,以使人们更快地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生活。例如,在《千万别把我当人》中,王朔虚构了一个寻找“大梦拳”传人为国争光的故事。这虽然是一个荒唐的故事,但其内涵却非常丰富。王朔首先通过对政府机构及民间团体名称的戏仿,虚构了一个“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然后让他们煞有其事地以“为国争光”之名对唐元豹进行训练,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件为国为民的好事,但事实却刚好相反——这个机构的领导人只是一些无事可做的社会混混,他们成立“全总”也只是为了能够更加容易地骗吃骗喝。当获得人们的信任以后,他们并不像原先所承诺的那样,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而是争先恐后地利用公款大吃大喝,中饱私囊,利用人民的信任,欺骗人民的感情。王朔正是通过这种虚构和戏仿的方式揭露了一些社会上真实存在的不良现象,这种揭露使“为国争光”这个本来重似千斤的话题和类似于“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这样的政府机构成为滑稽的笑料,在轻松的欢笑中,他们本来所具有的政治严肃性、庄严性也就随之消解。既然“政府机构”只是玩笑,“人民公仆”只是一群骗吃骗喝的小人,那么,还有什么值得人们敬畏的呢?于是,权威消失了,敬畏消失了,读者为作品中对这些不良现象的揭露、揶揄、嘲讽而拍手称快,并从中获得一种揭开神圣面纱后面丑像的快感,在想象中实现了对这些权威机构象征性的反抗。
其次,通过对父亲权威的消解达到颠覆传统伦理体制的目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君父”一直是并提的。对于子女来说,父亲不仅具有血缘上的意义,还象征着一种体制、一种权威、一种集权制度。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的形象大多是高大、伟岸、积极正面的。而在王朔的小说中,父亲却经常处于缺席状态,就算出现,也经常是以懦弱、无能、委琐的形象出现,王朔通过破坏、颠覆传统父亲的美好形象,使读者获得了一种摆脱束缚、争取自由的勇气和力量。例如在《我是你爸爸》中,王朔通过讲述一对单亲父子的生活琐事实现了对传统文化中父亲高大形象的瓦解。单亲父亲马林生在比自己弱小的儿子面前经常使用武力使他屈服于自己,但是在面对比自己更强大的社会恶势力时却只能低眉敛目,默默忍受。小说通过这两件小事的对比叙述,使马林生这个懦弱、无能、恃强凌弱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也使他努力保持的完美的父亲形象彻底坍塌。
最后,通过调侃作家、教师、文学家达到颠覆知识分子和一切传统文化的目的。作家、教师一向被认为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社会的精英阶层,但是,在王朔的小说里,作家都是“心黑脸皮厚”的人,而且“既没偷抢的胆儿又没有做生意的手腕还阳痿”。[2](P896)知识分子在王朔小说里也大多是虚伪、懦弱、恶毒的形象。如《顽主》中的德育教授赵尧舜是一个好色、虚伪之徒。《玩的就是心跳》中刘炎的父亲是一个懂得多国外语的学者,但却做出了强奸自己女儿这样禽兽不如的丑事,为人师表的音乐老师私底下也是一个诱奸自己女学生的禽兽。通过类似的情节,王朔使读者认识到知识分子并不是像表面上颂扬的那样清白,他们也有肮脏黑暗的一面,甚至比一般人更加龌龊、虚伪。通过对这些阴暗面的揭露,王朔消解了人们对知识及知识分子的敬仰,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在读者心目中美好的传统形象,实现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阶层的象征性反抗。
总而言之,王朔通过对看似非常宏大、庄严、美好的事物的嘲弄、调侃和戏仿,使之失去严肃性、崇高性和厚重感,变成令人嗤之以鼻的滑稽可笑的事物,这为人们打破旧生活的神话和偶像,挣脱旧的体制的束缚与压制,轻装上阵走向新生活,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新价值观提供了必要的“启蒙”。
(二)平民的狂欢 巴赫金认为,中世纪的人们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压抑的日常生活,另一种则是放纵的狂欢节生活。在狂欢节中,人们戴上各种假面和装扮走上街头恣意狂欢,在这里,僵化的体制、秩序和规范遭到嘲讽和抨击,官方文化被推翻和颠覆。狂欢实际上表现的是对权威和压制力量的一种反抗,体现了人们抵抗统治阶级压迫,反抗等级制度的愿望,以及对自由、平等、民主精神的倡导和向往。实际上,狂欢历来被看成是反抗压制性文化的有效方式,用狂欢化的叙事方式表现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和不满一直是作家惯用的手法。王朔在小说中也运用了这种狂欢化的叙事手法以展现自己对宰制力量的不满与反抗。这种反抗主要是通过对小说的主人公——顽主们日常生活的狂欢化叙述体现出来的。例如,王朔小说中的主人公从不按部就班地上班和学习,而是整日搓麻将、侃大山,或者纵情于各个声色场所。他们在这种生活中体验的是一种躲避式的快感,这种快感就如中世纪狂欢节上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快感一样,由于平时生活中的过度压抑,在狂欢节中也就更加放浪形骸,并通过自己放荡不羁的言行来表达对社会体制和等级制度的不满。《玩的就是心跳》中有这样一段话:
那段日子我们无牵无挂,一心想的只是尽情享乐。我们在吃饭……不间断地在各种不同环境的餐馆吃饭……我对面是高晋、许逊。右手是汪若海和一个风流女子——我们大家的情妇乔乔,我旁边是另一份公共财产夏红,夏红左手是高洋,高扬攥夏红的一只手……[2](P590)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生活的颓废,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名副其实的狂欢。首先,他们有狂欢的场所,在各种饭店。其次,他们有狂欢的内容,“总是在吃饭”说明他们有丰盛的筵席;“共同的情妇”、“另一份公共财产”说明他们性生活混乱;小说后文还有他们在宾馆的寻欢作乐、招摇撞骗、纵情声色的狂欢内容。最后,他们的活动也产生了狂欢节的效果:笑,各种意义的笑。
他们的狂欢是一种身体的狂欢,表面上他们玩世不恭,放纵生活,逃避责任,而其狂欢的实质却是他们痛苦、焦虑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他们放纵生活主要是因为他们对生活的不满。他们本来出身优越,但退伍后却一文不名。巨大的心理落差反映在生活上就是对常规生活秩序的破坏,他们通过狂欢、偷盗、欺骗等手段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通过非常规的方式生活,展现自己与社会的决裂。
除了具有反抗压制的政治意义外,王朔小说中的狂欢化叙事还体现了一种对阶级消退、等级消失、自由、平等的乌托邦社会的向往。这种对自由、平等社会的向往,在《我是你爸爸》中有明显体现。小说叙述到父亲马林生在传统教育方式失败后,为改善父子关系,主动要求与儿子以“哥们儿”的身份相处,虽然这种方式最后也失败了,但至少它说明了马林生愿意与儿子以平等的、没有特权与等级压制的关系相处,也反映了作者建立平等、自由的父子关系的愿望。
(三)大众文化的崛起 王朔小说的快感表达能够获得读者青睐,说明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具备了发展大众文化的成熟环境,中国大众文化开始兴起。同时,王朔的成功还预示着中国文坛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过去一直被精英文化压制、鄙视的大众文化开始由边缘化地带走向主流地位。
王朔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历史必然选择的结果。他的个人成长见证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发展。
王朔为什么能在这个时期获得读者青睐并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这与当时中国大众文化消费的社会环境基本形成是分不开的。
首先,经过了近十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已深入人心,但“文革”浩劫给人们思想上、生活上留下的创伤却难以磨灭,对比十年间前后生活的变化,人们对过去那种假大空的革命文学充满了反感,对过去那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文学充满怀疑,这时的他们更愿意看到一些能够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这为王朔小说的流行提供了思想基础。
其次,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以后,商业的发展促使了一个新的群体——市民阶层的崛起。市民阶层在以前一直是被边缘化的、处于被压抑状态的群体,当他们在经济上崛起后,他们开始要求在文化上的利益,他们需要有自己在文化上的代言人,他们需要那些描写他们的生活、讲述他们的故事、反映他们的思想情感的文学作品。同时,他们对文学通俗性、娱乐性的要求也进一步增强。总之,市民阶层的出现和他们的特殊需求为王朔的小说的流行提供了必要的读者群。
再次,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传媒技术开始逐步普及,读报、看电影成为人们日常休闲生活的一部分,电视也开始逐步普及,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客厅,这为王朔小说利用影视媒介扩大影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已基本具备了大众文化发展的条件,而王朔的出现刚好与历史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合谋”。在内容上,他站在了大众的视角上,以写实的手法为大众描述市场转型时期都市生活形形色色的变化,这是普通读者所熟悉的生活;在语言上,他幽默风趣,采取市民阶层熟悉的口语、流行语以亲近读者;在叙事手法上,他采用传统的叙事手法以满足读者的阅读习惯;在思想上,他的小说显示出反叛的思想和对社会的思考,如他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揭露嘲讽,所有这一切既满足了市民阶层对通俗性、娱乐性、休闲性的需要,也满足了他们对政治的反叛姿态,使他们产生了阅读的快感。于是,王朔成了当时大众流行文化的不二之选。
结语
王朔是一个时代转变的标志,他站在中国历史变化的节点上,既代表了那个理想的革命时代的终结,又代表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新时代的开启。他在小说中运用的快感表达策略对于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具有开先河的意义,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对后来的大众流行文化,王朔小说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如《疯狂的石头》、冯小刚的贺岁片电影、《夜店》等都有王朔小说的影子。及至今日,王朔在语言上的调侃风格仍然发挥着他特有的魅力,成为很多文学作品模仿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