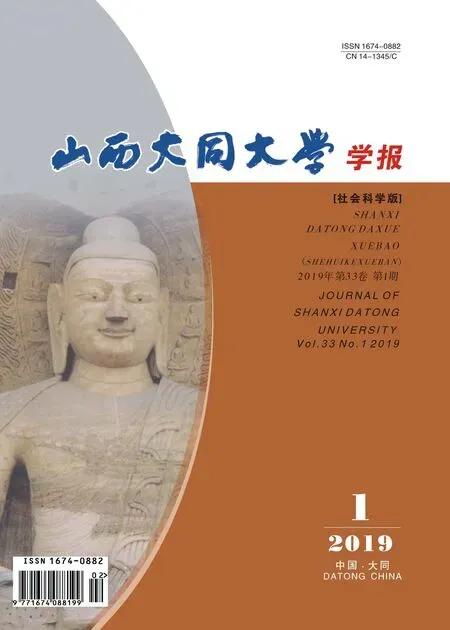索隐考疑事探赜照文心
——姜剑云教授《文史索隐》和《文史探赜》的学术史意义
李剑清
(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721007)
姜剑云教授的《文史索隐——晋唐文学杂考》和《文史探赜——古代文学纵横论》(以下简称《文史索隐》和《文史探赜》)两部学术论文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给2017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如果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比作一大块“织锦”的话,那么,姜剑云教授的这两部著作就是两朵“团花”,让这块“织锦”变得光鲜明艳,亮丽耀眼。
一、人学烛照的治学理念
《文史索隐》是姜剑云教授三十多年来沉潜文史、索隐考证的学术见证,以朴学考据见长;而《文史探赜》则是建立在扎实考据之上,贯穿着人学的哲学烛照与文学精神和诗性精神的美学思考,以理论思辨见长。他在《释“文学是人学”》一文如是说:“对于文学批评家的原则要求是这样的:必须掌握朴学之手段,必须运用人学之思维,必须坚持文学之本位,必须具备美学之眼光,必须达到哲学之境界。”[1]这种治学理念也始终贯穿在《文史探赜》里面。他希企自己的文学研究是一种以文学为本位、具有美学意味的文学批评,而不是枯燥乏味的、了无生气的考据学、谱牒学,也不是一种脱离政教伦理的学术游戏。正是有这样的治学理念,才让他的著作具备了哲学和美学的品格。
细读《释“文学是人学”》一文,就能明白这种治学理念的“问题域”与形成路径。《文史探赜》一书以孔融、傅玄、陆机、陆云、谢灵运和中唐时期的各个诗派为研究对象,《释“文学是人学”》夹杂其中,好像显得有些违和,其实这篇文章恰恰是他的文学观念和治学理念的自觉阐发。一位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那么,何为文学?如何研究文学?如何看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问题?他正是带着这些问题意识,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曾经时髦一时的理论话语——“文学是人学”。当然,旧话重提,绝非怀旧。“文学是人学”这一理论曾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人的价值再发现”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姜剑云教授重释“文学是人学”,是要建构文学批评学式的文学研究。他认为:“文学批评学的建构,应该明确为艺术哲学的属性,而不应该毫无规范地越位蜕变为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或者演变为考据学、泛文化学,诸如此类。”他以辩证法的方式辨析“文学与人学”的关系,通过“文学是人学”和“文学不是人学”两个命题,把握了文学“通过对假恶丑和真、善、美的充分而真实的映照与展示,如愿以偿地看到了现实中的人和历史上的人,看到了活生生的‘人’和‘完整的人’,从而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有所取舍和扬弃”的人学价值与功能,[1](P294)同时也把握住了文学的审美本位。也正是认识到“文学是人学”的丰富内涵,明确提出文学批评学“应该责无旁贷地在美学科学思想的统摄下,与别的姐妹艺术一道分担艺术美之神圣使命”。[1](P301)正是看到了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变成泛文化研究、文献学考据等学术现象,他才倡导建立以“文学为本体”的文学批评学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他清醒地意识到文学的人学思想底蕴,进而思考文学精神与诗性精神,因而主张将它们放置到中国思想史的具体历史场景之中去探索。正如姜先生所说:“先秦时期,……人学思想没有太多的禁锢,文学创作主要受到原始诗性精神的驱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文学特质表现出天然稚拙、情真文朴的朦胧文学状态。自汉初至唐末一千年,人学思想从经学一统天下,到玄学逐步兼容杂糅一切任心任诞的学派内核,再到舍弃玄虚而兼取三教精华以娱心益世,文学创作由自发而自觉,诗性精神、文学精神都有了滋生和勃发的土壤与温床,文学样式日新月异,文体大备,文学经验日积月累,层出不穷,总体上反映了士人作为社会文化创造与统治阶层的雅文学特质和状态。宋元明清约一千年,人学思想主要以儒家理学占领统治地位,文字狱大兴,八股文流行,理性精神驱动下写出的教化文字积案盈箱,士人失落了风流飘逸,诗赋文章大要以复古为创新,唯词曲小说随市民文化阶层的壮大而兴盛,文学总体上呈现疏离传统、走向世俗的俗文学特质和状态。”[1](P290-291)这种以人学的哲学烛照下的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在《论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一文中阐发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他十多年前出版的《太康文学研究》这一部著作的问题意识和精髓所在。姜先生所说的“诗性精神”是糅合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新科学》中的“诗性思维”和现代哲学家尼采的“酒神精神”,指涉着“人”的那种原始冲动、自发的生命力量,但他洗练了西方哲学话语与知识谱系,而运用中国文学的知识话语建构“诗性精神”的理论话语。从人学思维看,“完整的人”正是元气淋漓的、原始冲动的生命状态。而“文学精神”正是“为艺术的与审美的,自觉为文的精神”,是饱含了真善美追求的“完整的人”对“世界的美”的探询精神。当探寻到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的关系之后,他的古代文学研究便具有了审美的眼光和哲学的品格。
二、考探疑事的治学路数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治学路数上,姜剑云教授把朴学的考据方法运用到精致入微的程度。《文史索隐》一书可以看成是他的“朴学之手段,人学之思维,文学之本位,美学之眼光,哲学之境界”治学理念在具体研究中的落地生根。
《文史索隐》一书以考据为主,读者会以为他厌恶空洞的理论演绎,醉心于飣饾考据,其实不然。姜先生在《文史索隐》一书的《前言》中说过:“作家作品的疑案,有待考证;文史奇观的揭示,源自于考证。”[2](P2)笔者在《文史索隐》的小序中也说过:“《文史索隐》不过是先生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鳞半爪。虽多是考据之作,但他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将考据镶嵌在宏观的义理思辨之中。像太康时期的张华、张协、陆机、潘岳、潘尼等著述、生平考述,皆是为揭示太康时期作家的人生道路与人格精神,进而思考文化风尚对作家的影响。再如对谢灵运著述、翻译与佛教人士的交游等考辨,也是放置在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整体观照之中。”[2](P7)
他之所以重视考据的方法,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不仅仅是个人治学的需要(如编年谱、释疑案等),更是20世纪90年代学术风气转向的结果。纵观20世纪的学术研究风气及其转向,不难发现,90年代之前的中国学界,面对西方(包括前苏联)的“他者”,试图用义理性质的理论思想来建构“中国”——“想象的共同体”和中国文化的图谱,或论证中国思想文化的民族性格——文化本位的建构,或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政治本位的历史叙述,或论证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新启蒙”的必要性——思想本位的理论呼吁,都表征出“以论带史”的趋向性,抹杀了历史的丰富性与现实的复杂性,而把历史与现实装进预先假设好的思想模子中。而90年代的学术界厌倦了这种“宏大的历史叙述”以及理论先行的文化逻辑,向清代乾嘉朴学投去钦羡的“一瞥”,李泽厚称其为“思想的淡出与学术的凸显”。[4]古代文学研究界兴起了以朴学的实证精神为核心的考证之风。“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确实能够改变“以论带史”的粗鄙与暴力。受此风气濡染,姜先生坚持“孤证不立”的考证原则,力求摒弃空疏。他认为考据是扎实为学的基本功,是从事文史研究的前提。姜先生的考据涉及某一时段文学的编年、重要作家的年谱、重要作品的写作年代以及社会交游等问题。他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这些考据为进行魏晋文学研究、中唐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正是基于《文史索隐》中对相关文学疑案的深入考证,才有了《文史探赜》中精妙绝伦的审美阐发。王志清教授在《纠谬解疑 揭示千年文史疑案》中这样评论:“由于姜剑云的研究从做年谱开始,避免了缺乏确凿有力实据的主观化推论的随便拿捏,也避免了缺乏思考与主见的人云亦云的学舌,形成了他研究的严谨特点与公正评判。”[3]
在《文史索隐》中,姜先生考探疑案的手段已经达到了精致入微的程度,腾挪跌宕,飞针走线,来回穿梭,针脚细密,连缀得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充实而光辉,空灵而蕴藉。他以涸泽而渔的气魄收罗众家所说,精心拣择原始材料,合理有序的排比,精当入微的辨析,使千年以来的文学疑案涣然冰释,水落石出。比如对左思《三都赋》作年的考证,他先罗列出学界四种代表性观点,然后排比八种相关的原始文献资料,包括《晋书·左思传》、《世说新语·文学篇》、《世说新语·文学篇》的裴注引、王隐《晋书》、臧荣绪《晋书》、《文选》李善注等相关资料,最后运用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等思维原则进行精当辨析,推翻了陆侃如先生的“太安二年(303)说”,牛世金、徐传武先生的“295年左右”说、姜亮夫先生的“元康元年”说以及傅璇琮先生的“吴灭前”之说,根据史实资料,进行严密的推理,水到渠成地得出了太康二年(281)的结论。像这样精致入微的考证,在《文史索隐》一书中比比皆是。可谓是“披沙拣金,往往见宝”。这种精致入微的考据功夫,是经历了长久的坐冷板凳的功夫才练成的。当然,坐冷板凳,搜集资料,并不见得都能做到精致入微。要把这种考据功夫做到精致入微,还要慧眼独具,以及积久弥真的学术训练。
三、启人深思的学术垂范
承蒙姜剑云教授不弃,笔者冒天下之大不韪,已序过《文史索隐》,那就再评骘一下《文史探赜》一书的学术业绩,寻绎其学术示范价值。
一是点面结合、立体透析的手段,垂范后学。如果说《孔融之死新探》《傅玄文体风格观念》《左思辞赋“尚用宜实”的文学观念》《陆机“谢朝华于已批,启夕秀于未振”的文学精神》《陆云文贵清省的创作主张》,以及有关谢灵运佛学思想等文章是对文学史上具体作家的“点”上的多方拓展与深入挖掘。那么,有关太康文学情多气少的主题取向和袭故弥新的体裁范型的探讨,有关中唐时期的通俗诗派、雅正诗派、怪奇诗派乃至金源后怪奇诗派等一系列文章,则是对文学史上文学流派的“面”上的要言不烦的梳理。这种点面结合的立体透析,几乎使得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题无剩义,又给相关的专题研究辟出了新的路向。按照专题研究的模式,这些诗派研究大概可以用几十万字的专著去探讨。当然,任何研究都要有明晰的问题意识与现实指向,仅仅为了探讨某一诗派的专题研究,就会陷入了无生气的文献堆积,迷失在历史的“黑色森林”之中。
二是据真义坚的学术观点,既提高了晋唐文学的研究水准,也为后学研究晋唐文学提供了“云梯”。《孔融之死新探》一文将孔融之死视为曹操势力极度膨胀所致,孔融成为曹操向“周文王”这一目标奋斗的祭品,这一观点令人信服。但至于孔融是否算成熟的政治家,尚有商榷的余地。此文已经触及汉末建安时代的社会阶层升降以及汉末世族阶层的历史命运。《论魏晋之际傅玄的文体风格观念》一文,不仅彰显了傅玄“引其源而广之”的赋学观念,而且揭示了傅玄的文体风格观念在“文学自觉”历程中的作用——作为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傅玄将理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糅合,客观上促成了魏晋时代文学精神的滋长。而论及左思辞赋“尚用宜实”的文学思想,则揭示出左思既批评总结汉代以来的政教文学,又反思了西晋缘情绮靡的审美主潮,由此得出“尚用宜实,与绮靡自妍,共同促成了太康的‘文章中兴’”的结论,令人信服。论及陆机时拈出《文赋》中的“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一句,经过点化,揭示出陆机所代表的魏晋时代的文学精神。他在太康文学研究上用力最勤,阐释了“情多气少”的主题取向以及“袭古弥新”的体裁范型,足以洗刷20世纪60-70年代对西晋文学的鄙夷与贬损态度。姜先生的太康文学研究,对笔者惠泽颇多,在拙著《西晋文风演变研究》以及有关陆机研究的若干论文中多次引证。在谢灵运研究方面,他在考辨谢灵运与佛教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谢灵运诗文中的佛教文化因素。尽管文人多采取“六经注我”的态度与气魄,汲取哲学或宗教思想,与“我注六经”式的学人研究不同,更与虔诚信仰的宗教信徒不同,但这足以启发后学深刻把握佛教在魏晋时代的传播与接受状态,或者说了解佛教传播历经了从皇家走向文人的历史趋势。
三是风清骨峻的文风足以垂范后学。“文如其人。”凡与姜先生有过交往的人,都会被他的真诚、和蔼与热情所感染。这两部著作行文风格上,风清骨峻、灵动真率,让人备感亲切,与近些年讲究学术规范、堆砌文献、生吞活剥外来理论的那种“酷不入情”的学术论著完全不同。情采斐然的文章才能脍炙人口,才能更好地交流思想、传达情感,学术论文亦当如此。那种密不透风的文献堆砌,生吞活剥理论话语的文章,只会让人蹙额掩鼻,难以卒读。
“索隐考疑事,探赜照文心。”三十多年来,姜剑云教授一直在汉魏文学研究、晋唐文学研究中辛苦耕耘、不断探索,集腋成裘,现在结集为《文史索隐》和《文史探赜》两部大著。无论是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还是其治学路数和治学理念,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值得后学多加揣摩,多方学习。
——论《江格尔》重要问题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