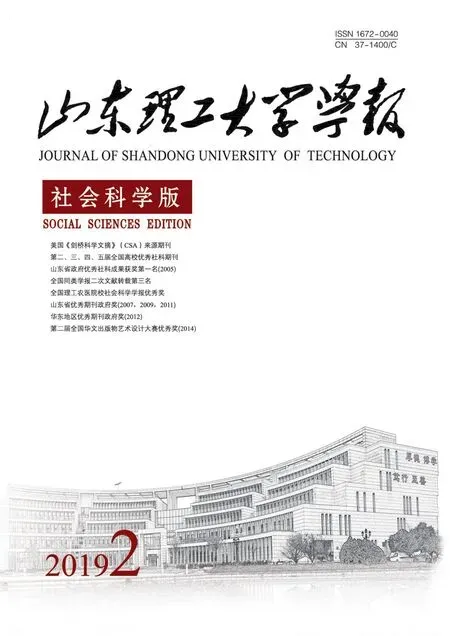刘咸炘书法思想探微
吴 国 良
( 山东理工大学 美术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四川双流人,清光绪丙申年十一月出生于成都纯化街“儒林第”祖宅。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其家世传儒学,幼年早慧,博学多才,遍涉经史子集和西方学术,生前曾经担任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成都大学和四川大学的教授。刘咸炘的一生只有短暂的三十六年,但是著述丰富,在刘伯榖、朱先炳《刘咸炘先生传略》中记载:“计先生所著之书,共二百三十五部,四百七十五卷,总名《推十书》,推十者,先生书斋名也。”[1]45在书法方面刘咸炘对于真、草、隶、篆等字体具有深入的研究创作,他的书法理论著作《弄翰余沈》内容丰富、论述公允、不迷信权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一、书法艺术的价值
毛笔书法艺术是中国特有的一门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物,它是由中国毛笔这种特殊的书写工具中产生的视觉艺术。书法艺术的审美价值在于通过千变万化的线条传达丰富的哲思和情感,书法中的节奏、线条和结构,通过联想可以使人欣赏到如同音乐、诗歌、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一样的审美感受。清朝末年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中国传统艺术受到剧烈的冲击,在书法方面单是书写工具的变化就是一场新的审美变化的革命,这种影响一直延伸至今。曾经一度有人认为由于书写工具的更新,毛笔这种书写工具将逐步遭到废弃,相应的书法艺术也会成为一种落伍的艺术。随着计算机科技的发展,也有人认为钢笔等传统书写工具也应该沦为历史的遗物。但是更多的人秉持这样的观念:由于汉字的特殊结构,即使工具加以改变,但是对于汉字的审美要求没有改变反而加强了,大多数人还是以拥有一手好字觉得骄傲,字体设计专家还在推陈出新地设计出新的字体,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文化的力量和书法的生命力。
刘咸炘很早就意识到书法艺术的重要价值,他认为西风东渐以来谈论艺术的人大多以为西方最主要的艺术成就是雕塑,中国最主要的艺术成就是绘画。民国以来有多部中国美术史出版,但是缺少书法史的著作,这时期绘画大行其道而书法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片面崇洋忘记自身之根本造成的。
刘咸炘认为西方的字母字体简单朴素、缺少变化所以难以成为艺术作品,但“华夏艺术书画并重,而书之变化尤多,尤足表现个性”[2]4。他认为书法艺术与绘画艺术同等重要,强调了书法艺术也是中华传统的宝贵财富。他的这些思想发端于20世纪初,对于当代人而言也是值得反思的。
二、书法与文学的比较
晚清文艺批评家刘熙载在《艺概》中说:“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3]422时代不同书法艺术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之美,不同朝代的书法作品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形态、社会风尚、审美诉求有着无法隔绝的联系。刘咸炘认为清代的书坛在乾、嘉时期以前是沿袭唐宋元明的传统,之后则是返回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统,这与清朝的文学风气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由于清朝前期康熙皇帝酷爱董其昌的书法,所以盛行圆转丰润的帖学。雍、乾时期盛行文字狱,使得文人致力于金石考古,于是碑学逐渐兴起,这才导致阮元在复古旗号的引领下进行了书法的革新。
刘咸炘认为一切艺术都存在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所以他主张对于艺术的评价只可以采用美丑的标准,不能采用新旧和古今的标准。他认为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间没有评定高下的标准,同样在书法领域篆书、隶书、魏碑、楷书之间也不存在评定高下的标准。汉字在历史长河之中的多次演变有其自身规律,书法艺术犹如波浪一般盛衰起伏,对于书法历史的研究要秉持公允的态度,不能偏激和绝对化。诚然书法艺术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反映时代的面貌,但是不能不加分析地推崇一类贬低另一类。文学与书法两种艺术之间的存在同样的发展变化规律,刘咸炘的书法理论研究所采用比较研究法,具有历史辩证的观念在里面,因此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依然值得重视。
三、书法入门的主张
学习书法如何入手在民国之前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公学和私塾的学生都会在先生的指导下学习规范的楷书。现在许多书法教育者仍然主张书法先从欧颜柳赵入手,绝对化地认为这是最为规范的楷书,甚至说学楷书如同学走路,学行书如同学跑步,不会走如何会跑。殊不知学行书才是如学走路,楷书是走正步。
以历史的角度看书法的入门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不存在绝对的方式,也不可能存在适合所有人的统一途径。刘咸炘就强调学习书法应该根据个人情况而定,“吾谓学书不当骤谈高格,宜先求笔笔坚实,墙壁树立,如同作文之先求成句、成段落”[4]44。他主张先把基础打好,掌握正确的执笔、入笔、运笔和收笔的方法,掌握基本笔画的书写规律。元代赵孟頫提出“用笔千古不易”的主张,刘咸炘对这种模棱两可的结论不置可否。刘咸炘肯定用笔的重要性,研究书法艺术不能忽视用笔,所以肯定地说所谓用笔之法,就是执笔和用笔的方法。由此提出用笔的多样性并不是永久不变的,因为“盖变化而统一,乃一切艺术之原则”[5]921。刘咸炘的用笔实质就是执笔与运笔要因人而异。实践证明从楷书入手是有效的学习方法,但当时有人认为艺术表现应该多样化和个性化,主张入门应当从本源开始,也就是从篆隶开始,他们的理由是篆隶是我国文字的发端,由此开始可以领悟汉字的创造奥秘。其实书法就毛笔蘸上墨汁留在纸上的痕迹,书法水平的高低一方面是基本功的扎实与否,另一方面是个人修养高低的问题。楷书的练习可以掌握字体的结构,隶书的练习可以适应笔法的提按顿挫,篆书可以较快解决笔画的力度,草书的使转可以领悟运笔的诀窍。不论从哪种书体入手都有正确的一面,即使是从楷书入手也应当有意识的融入篆隶和行草才会有更大的发展,而非绝对化。书法教育者不应该单凭自己的经验和传统的套路,而是应当根据学生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入门途径。
四、对康有为书法思想的澄清
清代乾、嘉时期在书法方面兴起一股提倡碑学贬抑帖学的书法风气,究其原因是与当时压抑沉闷的社会风气和学术风气有关。阮元崇尚古法,他认为:“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贞石也。”[6]460包世臣同样认为:“北碑字有定法,而出自自然,古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式,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7]154到了康有为时期这种提倡碑学贬抑帖学的风气更加严重了,康有为把乾、嘉以来的金石考据成果作为材料依据写成了《广艺舟双楫》。但是康有为是出于维新运动的政治目的来写作此书的,并不是从学术的角度研究书法艺术的来龙去脉,只是通过这部著作来作为自己变法思想的理论支柱,是一种出于政治目的把变法维新与书法革新杂糅在一起的产物,所以许多的观点带有偏激的色彩。在书中专门列出一个章节《卑唐》,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8]228事实上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并非如此。
《广艺舟双楫》对当时书法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对刘咸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刘咸炘对其中的观点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理性吸取其中合理的成分,并直接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他主张书法的评价标准应当把书法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作为准则,不能单单从崇古和创新的角度来考察。在书法的实践上,刘咸炘并不刻意追求枯干精瘦的用笔,也不刻意采取漫涨肥滞的用笔,在整篇文字的取势上既要避免呆滞刻板;同时也要避免散乱随意。他认为一切艺术都有一个兴衰的过程,一种形式兴盛到顶点就会形成刻板的定势,很难再焕发出新的生机,这时候就需要别开生面,所以对于任何一种书体都应该分别进行考察。对此刘咸炘说:“康氏尊南北朝而卑唐,其言往往太过。”[2]48
五、对阮元南北书派论的肯定
阮元在他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中提出书法有南北之分的观点。他认为:“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9]197在此之前董其昌根据禅宗中的南北宗之分提出“画分南北宗说”,董其昌这是从个人重笔墨轻丘壑的个人风格发表的言论,很早就受到质疑。清初阮元提出书法上也存在南北之分,这是步董其昌的后尘了,这种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影响,直到清末在康有为那里才得到众多的响应,但是阮元对于碑学的兴起功不可没。
依著名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1864—1945)的学术观点,不做系统的方法论陈述,而是通过方法论的实际应用来理解,用形式分析的方法对风格问题做宏观比较和微观分析,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就一目了然。不论是阮元,还是董其昌都是对同时存在的两种艺术风格进行对立化,支持一种属于自己的风格,贬抑另外一种不属于自己的风格。同董其昌一样,对于阮元的主张很早就有许多的反对者,并且拿出确凿的证据辩驳他的观点,更有甚者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南北之分。董其昌和阮元提出画学和书法的南北宗,其实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驳斥这种观点。佛教的《六祖坛经》载:“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10]3
刘咸炘从艺术风格区分的角度肯定了阮元的观点,赞成书法有南北之分,他说:“北碑南帖自有确论,岂可举一二例外而破之乎?”[11]342他认为反对者的意见都不可信,并举出许多与之相反的事例。中国历史悠久,不可否认书法艺术特征上的共性。由于历史、地理、民族、政治、生活习俗等因素的差别,南北书法风格的不同成为必然。对于这种不同应当正视,不能走极端,不顾事实地贬抑一方赞誉一方。总之,依据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学来看,阮元所阐释的还是书法不同风格的问题,只是后来被康有为等人出于政治目的加以利用了。
六、对碑学和帖学的公允态度
碑学是一个崇碑贬帖的书派,因为乾、嘉时期金石考据学的兴盛而崛起,是对以往宋元明帖学一家独大的不同意见。碑学的兴起和发展给清代的书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后来被具有偏激政治倾向的康有为所利用,成为维新运动的理论工具而不是公允的学术思想。刘咸炘不仅不赞同康有为对南碑和魏碑的赞颂,对于其他学者的有关碑评也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价。谭复堂认为:“《崇高灵庙》和《爨龙颜碑》南北对峙,为汉分正脉。”[2]129刘咸炘对于《崇高灵庙》则认为粗糙疏率只有十几个字算得上是精美,《爨龙颜碑》则认为是因为丰富的变化成就了书体的美好。对于许多名家交口称赞的《李仲璇碑》,他则认为是擅自加入篆书的笔法,过于纤弱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书体。但是他对大多数的魏碑还是有着相当高的评价。魏碑是北魏在碑刻上流行的一种书体,流行的时间并不长,传播的范围也不广,并且魏碑字体在用途上也较为单一,所以刘咸炘认为“凡是魏碑都是好的”的这种观点不足取。刘咸炘对待碑版的态度不是人云亦云,注重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分析的研究方法值得今日学者效法。
帖学是崇尚法帖的书派,主要是针对楷书和行草的研究,其中主要以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为研究对象。唐朝的多位皇帝都喜欢“二王”书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此确立了“二王”书法的正宗地位,压倒了魏晋以来以钟繇等人为代表的书体,之后各朝各代延续这种书风,加之科举制度的日渐兴盛,对于帖学日益依赖。凡一代艺术皆有盛衰,阮元提出并由康有为发扬的碑学,给清代颓靡的书风带来一股洪流,虽然在短时间、小范围内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但是从书法发展的整体上来看还是弊大于利。书法发展自有其规律,人为的左右其发展必定导向歧途,更不用说把书法当作仕途晋升的工具了。在书法艺术的宝库中,千百年来的优秀人才佳作汇聚其中,单单因为一己私利就把他们的功绩一笔抹杀,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千百年来的优秀人才性格各异,其作品也是风格各异,又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古代没有现代的印刷技术,为了书法的传播往往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这与刻碑的方式非常类似,所以说碑与帖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刘咸炘认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的用笔虽然圆润内裹,但是在转折处还是出现方正停顿的地方,这与魏碑《刁遵墓志》和《太公吕望表》有相似之处。所以他认为学习王羲之的书体如果单是凭借法帖并不是最好的方法,而怀仁集王羲之《大唐三藏圣教序》丰润、多筋骨则是学习“二王”的书法首选。
七、结语
刘咸炘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的初期,西方文化影响到中国固有传统是多方面的,书法艺术上所引起剧烈变化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20年代钢笔等书写工具的使用几乎在各个领域代替了传统的毛笔,进入21世纪更是中西文化的大融合时期,计算机的使用已经普及,以至于钢笔的使用相较以前也是大为减少了,就在人们因传统的丧失感到惋惜的时候,传统文化又焕发出新的生机,书法艺术近十年来又走进人们的生活,这是国家繁荣和人民重拾自信的原因。在反思书法传统的时候,刘咸炘的书法思想必然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其意义首先是刘咸炘能够肯定书法艺术的价值,肯定书法艺术是中国固有文化根本之大项,是值得当代及后世尊重和继承的珍宝;其次是刘咸炘对于书法贯通式的研究方法,因此他才不会为时代的流行风气所左右,即使面对阮元、包世臣和康有为这样影响巨大的大家依然不为所动,依然能够冷静客观的从史学角度和审美角度进行分析;再次就是刘咸炘踏实的学风,既不因循守旧也不执其一端,这主要表现在对书法入门的态度上。刘咸炘的书法思想现在看来毫无陈旧过时之感,其具有强烈的实在感和现实感,这就是其当今仍值得重视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