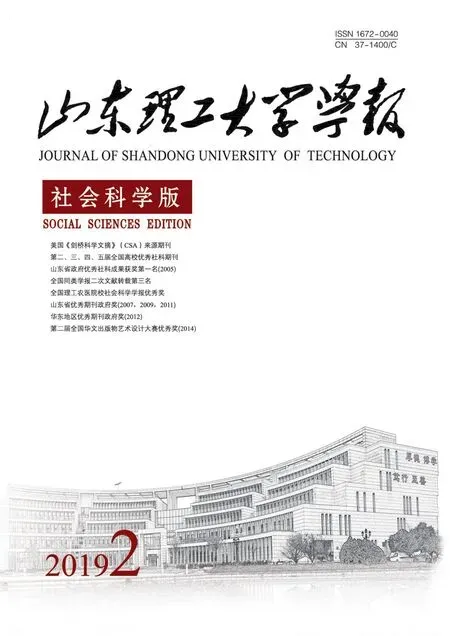大学生价值观心理生成及引导机制分析
——基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侯 倩,刘东峰,秦伟伟
(1.山东理工大学 美术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2.山东理工大学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从1990年周星驰“无厘头电影”娱乐风格的确立到近期“慰安妇表情包”闹剧、“精日女生发表辱华言论”等负性事件的发生,近三十年间,后现代主义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正以本土化隐蔽的方式发挥着越来越强的意识形态渗透作用。根据后现代主义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性质以及与主流价值观的关系,可以将大学生价值观分为消极型和积极型。受后现代主义影响,消极型的大学生价值观主要倾向于用否定的方式对当代主流价值观进行抵抗和消解,这给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青年大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震荡。抛却青年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仪式抵抗”,分析后现代主义对青年大学生影响的心理生成机制,积极探寻主流文化价值对青年大学生的价值引导路径,应当成为可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借鉴、思考和探寻的视角之一。
一、后现代主义的内涵及其基本主张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起源,目前学界较为统一的看法来源于“《1882—1923年西班牙、拉美诗选》中用于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逆动’”的“后现代主义”一词[1]9。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以后,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在一片争议声中才逐渐被国内学者所知晓,但却由于本身所涉及领域的庞杂,以及本身使命的反现代性,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概念来界定和阐释后现代主义的内涵。
后现代主义以反现代、反科学、追求“多元化”“怀疑论”“相对主义”为主要特征。后现代主义中的“后”即表明其与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的决裂和对抗,力图追求“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和行为实践”[2]3。其基本理论主张在于:一是反结构主义,提倡相对性、多样性和去中心化;二是反本质主义,提倡多元性、开放性、流动性;三是反整体主义,提倡片段性、差异性、微观化;四是反理性主义,提倡非理性和无意识。基于以上的主要价值主张,总体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主体性、中心化、整体性、统一性、权威性特征的解构,重在强调个体价值、微观存在及非理性,在某些方面与无政府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纠葛不清。基于此,厘清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基本价值主张,对于分清后现代主义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地开展大学生价值观培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后现代主义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一)后现代主义对青年大学生价值观的积极影响
激发个体自主意识,利于发挥青年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后现代主义提倡多样性和差异性,注重以人为主体,强调人的主体价值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个体自我意识的激发和个性的自由解放,利于青年大学生个性的独立和人格的完整,继而促其形成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念。而这样独立自主、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念在大学生开拓创新思维、开展创业实践活动过程中尤为可贵,这对于大学生端正正确的价值选择和取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
促使思维方式多元化,利于提升青年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后现代主义提倡多元化和开放性,注重思维的跳跃性和革新性,强调用开放的视野和充分的想象力、创造力,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去审视看待事物,以此对事物进行多元化理解。这样的思维方式利于青年大学生打破思维定式,激发他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索激情。从这个层面而言,后现代主义有利于提升青年大学生的创新意识、素质和能力。
提倡合作意识培养,利于青年大学生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后现代主义提倡去中心化和非理性,否定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个体之间的平等性,注重个体的情感体验,这些价值主张如果放到青年大学生与人交往方面,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中,都有利于青年大学生提升与他人的合作和共情意识,促其在与人交往过程中注重换位思考和平等交流。对于青年大学生而言,有利于优化团队成员之间、团队与团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二)后现代主义对青年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过于膨胀的自我意识,容易导致青年大学生利己实用的功利化观念产生。后现代主义提倡主体价值和个性解放,虽然有利于促使个体自主意识的觉醒,但也容易导致自我意识的膨胀——从自我实现到唯我独尊,从个性张扬到自我膨胀。如果任由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膨胀意识发展蔓延,最终容易使大学生形成自我、自大、自负的性格特点和价值观念,使其倒向个人主义的怀抱,最终否定个体的社会属性及集体主义原则,最终形成利己实用的功利主义倾向,这不仅会影响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更容易消解他们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坚持。如果将这样的价值观念渗透到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养成的过程中,容易促使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功利化、社会责任感淡漠等现象发生。
价值标准和选择多元化,容易引发青年大学生道德失范。后现代主义提倡多元化和开放性,冲击了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使得在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大学生无所适从。如果不能对这种多元化价值主张进行适时纠偏,任由其奉行“怎样都行”的价值原则,容易导致大学生忽视对传统和权威的尊重与服从,最终会消解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遵从,促其形成道德相对主义观念,从而扭曲其道德价值观,淡漠其社会责任感。如果这样的价值观念渗透到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养成的过程中,容易促使青年大学生产生多重价值标准和选择,导致其脱离主流价值观引领的轨道,走向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
去中心化、非理性、反权威,促使青年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产生质疑。后现代主义提倡去中心化、非理性和反权威,虽然有利于建立个体平等的关系,有利于个体合作意识的养成,但也容易促使对主流价值观的游移不定和政治价值观的暧昧不清,使处于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持怀疑态度,从而走向对无政府主义的中和立场。无政府主义不会永远忠于或反对“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或任何一种思想形式”[3]220,无疑,这种政治主张会引发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优越感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怀疑,最终导致大学生政治观念淡化、政治意识及立场模糊。如果将这样的价值观念渗透到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养成的过程中,容易促使青年大学生丧失对主流价值观念的遵从,甚至会导致其对主流价值观的解构、质疑甚至抵抗,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地位的夯实产生负面影响。
三、基于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大学生价值观心理生成机制
社会环境的复杂化、大学生追求个性解放的需求及价值判断力弱等影响因素的交织,导致处于价值观建设和形成期的大学生心理世界处于冲突动荡的不稳定状态。当大学生无法用常规主流的价值观进行压力的化解和矛盾的解决时,心理缓释或心理代偿机制就会促使大学生产生逃避、戏谑、反抗等表征其个性化、差异化、自主化的价值认知方式。鉴于此,从心理生成机制而言,受后现代主义影响所产生的消极型价值观是大学生试图解决认同危机时的反应方式。
(一)基于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大学生价值观源于张扬个性、获得认同的心理诉求
随着改革开放进入到“深水区”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攻坚阶段,社会环境的复杂化、多元化引起了人们价值观的巨大变化,也使得正处于价值观形成期的大学生思想信念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和混乱。正如德国哲学家斯普兰格所指出的,“在人的一生中,再也没有像青年时期那样强烈地渴望被理解的时期了”[4]218。处于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大学生在心理状态上正处于不稳定和“未完成”状态,在心理诉求上更渴望获得主流社会的价值认同。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表达方式的多样性、直接性、娱乐性、易解读性更契合了当代大学生的心理诉求,使其价值主张能够浅显、直白、轻松地渗透到大学生价值观的养成中。比如,张扬个性的“晒秀文化”“粉丝文化”“恶搞文化”“御宅文化”“弹幕文化”“丧佛衰文化”等泛娱乐倾向的亚文化现象的存在[5]107,正反应了大学生基于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心理诉求与表达方式。
(二)基于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大学生价值观源于对自身价值与责任探求的心理代偿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作为现实的个体,人的存在和价值的实现都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主流社会对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养成的要求更侧重于对社会责任、使命担当、价值贡献等利他价值取向。然而,正如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所阐释的,每个人的人格结构中除了“本我”“超我”以外,还有负责处理现实世界的“自我”。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青年大学生需要接受主流价值要求遵从社会规范,完成个人角色的社会化。这样就使得处于本我角色的个人价值被挤压。加之,处于经济不独立状态下如遇学业或工作上的低迷期,会使得大学生的存在感降低。处于价值形成期的个性张扬与社会规范、感性认知与理性判断之间的价值冲突长期积聚而得不到合理的宣泄与释放,将会导致心理问题的产生或社会隐患的爆发。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提倡相对性、多样性、多元性、开放性、差异性、非理性和无意识,为大学生的自我需求与价值实现提供了良好的心理代偿或转移机制。被心理代偿或转移的心理表达方式带有个性解放和张扬的特性,如果翻越社会道德的管辖,则容易转向对主流价值的仪式抵抗甚至显示为批判或颠覆,比如黑客文化、恶搞文化、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虚无主义等。
(三)基于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大学生价值观源于对社会压力回避或抗拒的心理缓释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大学生,承受着来自学习、就业、情感、交际等各层面的社会压力与心理落差。在成长成才和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对未来生活和发展的不确定性,缺乏有效社会支持和价值引导的客观现实,使得其身心难以承受过多的社会压力。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非理性和无意识更容易促使青年大学生产生选择回避社会压力的价值取向,他们通过调侃自身的现实境遇,在自娱自乐的同时,引起群体共鸣,排解不良情绪,缓释社会压力,比如近期比较流行的包括“葛优躺”、青蛙 PEPE、四肢咸鱼、漫画“懒蛋蛋”、公马男波杰克等表情包与流行语录在内的“佛”文化、“丧”文化、“衰”文化等[7]76。对社会责任承担的羸弱性,被称为“草莓一代”“鸟巢一代”到 “玻璃化一代”的青年大学生更容易表现出人性脆弱和社会主义责任淡漠的一面[8]16。在这样的价值选择和取向的情况下,青年大学生更容易受到后现代主义相对性、多样性、多元性、开放性、差异性、非理性和无意识的价值影响,崇尚“御宅文化”而走向价值虚无的“犬儒主义”。
(四)基于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大学生价值观源于对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心理参照
“从自我的社会属性这一维度出发,自我可以划分为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三大类”[9]11-12,这说明自我并非一个独立的心理结构。个体自我在价值层面上更多地体现为个体的个性张扬和个性解放,这就促使青年大学生在价值选择时需要进行自我参照。在后现代主义多样性、多元性、开放性、差异性的影响下,青年大学生主体意识与个性化逐渐增强,他们更倾向于把自我的个性特点作为参照,采用独特的符号或语言来彰显个性、表达自我,挣脱主流价值的束缚和限制。与此同时,处于社会大集体中的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价值要求青年大学生价值选择需要进行社会价值的他者参照。但这种他者参照并没有完全超越主流社会价值的藩篱,往往又将社会主流价值的特质包含其中,比如比较流行的“涂鸦文化”“反鸡汤文化”“泛娱乐文化”所体现的“叛逆不叛道”的特点。
四、基于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大学生价值观心理引导机制
为了降低后现代主义对青年大学生的消极影响,促进兼容协调、多元有序的社会价值秩序的生成,消除和抑制消极社会心理的形成,应从心理层面上对青年大学生进行积极引导。这就要求加强主流社会价值观对青年存在价值和利益诉求的认同和满足,注重对亚文化或次文化价值的整合与疏导。
(一)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身份认同
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青年大学生在社会中的身份定位处于模糊不确定的状态。层出不穷的亚文化现象的产生,正反映了青年大学生对身份认同的心理诉求和社会期待。后现代主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促使主流价值观与多元化的价值观相互交织。就自我身份认同而言,需要积极引导青年大学生自觉主动适应主流价值观,积极构建相对稳定的社会身份和个人价值,将自我参照与他者参照、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统一于青年大学生价值养成过程中。与此同时,也需要社会客观看待并接受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建设和成长这一特殊时期,具有差异性和不稳定性等特点,关注他们在价值表达和身份认同上的心理诉求和社会期待,积极探索并构建能够让青年大学生进行情绪宣泄和话语表达的心理代偿与心理缓释机制,为青年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定位提供合理而科学的社会支持。
(二)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利益认同
价值是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价值认同的产生与实现取决于利益认同。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利益诉求与青年大学生的个体利益诉求有共性的一面,但也存在差异性的一面。后现代主义关于去中心化、多样性、差异性的价值主张,容易促使青年大学生对自身个体利益诉求的看重。这就使得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利益与青年大学生个体利益诉求契合程度发生分化。然而,二者之间的契合程度正是实现价值引导的关键。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社会、个人层面利益诉求的高度统一;然而,现实生活中部分青年大学生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虚名化,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多地出现在青年大学生的口中、笔中但却没有进入他们的心脑。究其原因,在于对青年大学生现实个体利益诉求与主流社会诉求契合度挖掘和引导不够。鉴于此,多视角多层面认真思考并积极回应青年大学生的利益诉求,培育并激发他们的道德情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础。
(三)为青年大学生提供必要而合理的社会支持
作为社会中现实的个体,青年大学生在整个价值观形成过程中需要来自同辈群体、家庭、社会、国家等多个层面的社会支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这些层面所抱有的价值观的影响。然而,从心理诉求与契合度上讲,受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处于心理“未完成”状态下的青年大学生更容易受到来自网络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支持系统的熏染,片面强化他者的心理参照,以此缓释来自主流价值观规范的社会压力。从社会支持效能视角出发,需要为青年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以及正确价值观的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增加利于其发展的教育投入、完善教育德育体系、提升价值观教育的实效,等等,为青年大学生的生存及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和社会支持。与此同时,与时俱进地倡导多元化的成功标准,畅通与青年大学生对话机制,及时回应青年大学生的心理困惑,接纳并及时治疗青年的心理障碍,引导并强化青年大学生对社会和国家的归属感,为青年大学生健康心理和正确价值观的养成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样至关重要。
(四)加强对多元价值观的整合与吸纳
与其他社会思潮相比,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除了包含消极的成分以外,也不乏有积极的成分存在。鉴于此,在对青年大学生价值引导的过程中,应变刚性的“收编”为柔性的整合与吸纳。伯明翰学派主张用“收编”的方式解决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抵抗”。然而,“收编”一词容易将主流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置于彼此对立的地位,这样并不利于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积极成分的借鉴,也不利于对消极影响的合理消除。对青年大学生价值引导应着力于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的扬弃,将其合理的价值因素有机融入对青年大学生价值构建的过程中。因此,当层出不穷的亚文化现象出现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首先应客观地分析这些现象背后所反映的利益诉求及形成机制,真诚倾听并积极地回应青年大学生的利益关切,合理适当地为其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和心理缓释机制提供有利的社会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性”与青年大学生的“个性”在价值观层面上达成共识,才能用互动式的价值对话完成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的合理“收编”,也才能化解青年大学生陷入后现代主义泥潭不能自拔的危机[10]128。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现代性的全方位批判和解构,在大学生自我意识养成、创新能力提升、多元批判思维拓展等方面有一定的激发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在主流意识形态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网络思政阵地坚守、反主流社会思潮批判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消极负面影响。主动把握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积极分析并掌握大学生价值观生成的内在规律和机制,因势利导地整合并吸纳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非主流社会思潮和亚文化理念,立足思政课程并积极耦合全方位思政育人要素,才能在价值观层面有效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与个体思想价值取向“互动式”对话体系和渠道,才有可能避免大学生价值观形成期的心理震荡和价值冲突,从而降低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抵抗和消解的可能性,以此提升对大学生思想引领和价值培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最终夯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