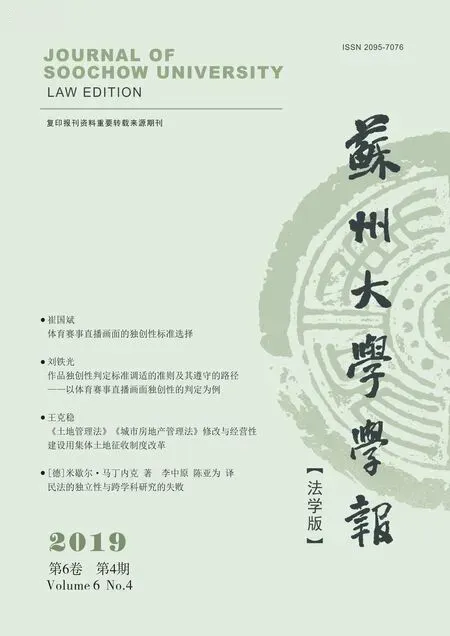国际刑法的一般功能 :法益原则与损害原则的妥当平衡
——再论国际刑法的基础理论*
[德]凯·安博思 著 张志钢 译
一、引论 :研究对象与目的
本文关注的是法治国中刑法理性这一基础性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动用刑法?它的一般功能和目的是什么?我的兴趣点既涉及刑法,也涉及国际刑法。不过,鉴于国际刑法原理依赖于国内刑法(只要考虑到国际刑法是刑法的一个分支),我的研究也需要以国内法语境下的相关讨论为起点,进而向前推进以检验国际刑法这个相对比较新的领域。
我将刑法的一般功能问题与更具体的专门问题即刑法处罚的目的区分开来,后者在道义论(报应/报复)与功利主义/后果主义(威慑、规范稳定/强化、沟通主义)之间摇摆,而且我已经在他处处理过了。(1)Ambos (2002, pp.312-323);新近的文献见Ambos (2013a, pp. 67-73)。因而,本文仅仅在探讨其与刑法的一般功能的关联时提及刑罚的目的。
刑法一般功能的问题可以视为关于犯罪化正当理由的争论,一如国内法中最重要的犯罪化理论之发展所表明的。也即认为法益足够重要因而需要刑法保护的法益(英文可直译成legal good)理论(下文统称为法益概念),以及认为刑法的主要功能在于预防损害(harm principle)的理论,前者在德国体系中占据主导,后者则在英美体系中居于优势。如上所述,国际刑法还不是独立的一门学科。事实上,即便国际刑法有些部分不为国内刑法所支配,也仍需要刑法理论,这就使国内刑法有关法益和损害的争论成为发展国际刑法犯罪化原则的理想起点。(2)我不打算在此进一步为这种观点辩护,只是随着争论的进展这种观点的合理性有望愈发明显。因此下文也就先介绍这些国内法理论,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更适合国际刑法的法益——损害结合理论(a combined Rechtsgut-Harm theory)。
二、理论起点 :保护法益和防止损害作为刑法的一般功能
(一)引言
刑法功能所涉及的首要问题是,立法可以并且应当通过刑法威慑禁止其公民的哪些行为。但立法者应该以何种标准决断这一问题?哪些行为是国家应当或可以禁止的?是否应当赋予国家将任何它认为不道德、淫秽的、反社会的行为都予以犯罪化的权力,或者是否附加将行为犯罪化之前必须满足的标准?
最后一个问题在德夫琳勋爵(Lord Devlin)和H. L. A. 哈特(3)See infra note 44 and main text.之间存在着著名的争论,当然,在他们之前和之后的学者中这些争论都存在着。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不道德或有关不道德的社会观念并非犯罪化的充分标准,法律实践所反映的情况也远非如此。事实上,社会道德在决定刑法范围方面具有核心作用,因而也就不存在统一的、一成不变的和普世的刑法内容。尽管旨在保护基本利益和价值(如生命、身体完整性、自由)的核心罪名,可以在实践中得到普遍支持,但是,多数犯罪所禁止的内容都随时间的推进而改变,一如与这些犯罪有关的惩罚措施。不同的犯罪行为在世界不同地方的正当性,也是如此。今日受处罚的行为,可能为明日的社会所接受(而非犯罪化),因为社会中公民的价值观变了。
况且,一些自由主义者其实也已意识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刑法的合法性依赖于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赖。与社会认知不一致的刑法不会得到尊重和执行,而对行为的非犯罪化被视为禁忌,因为这会有损公众对刑法体系的信赖。在国际刑法的脉络下情况尤其复杂,因为有关犯罪化方面难以实现全球性共识。在以被激起的大众情绪作为正确刑事政策之基础方面,我们必须持审慎态度——只需想一想纳粹的“健全国民情感”(gesundes Volksempfinden)。当然,我们无法彻底忽略那些理据充足的社会态度。这也说明了,一个社会价值观的急剧转变,会造成一个国家刑罚的引入或者放弃。
刑事司法体系之适应性的一个重要象征是,它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不受特定道德或宗教秩序的约束。毫无疑问,西方世界政教分离,但其中依旧存在国家认为应该处罚的道德犯罪。当然,在宗教支配的法律体系中就很少具有灵活性,在那里宗教和法律紧密关联在一起,这种情况尤其在“伊斯兰”国家可以看到。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伊斯兰法严厉禁止饮酒,就是实证法需要一定程度的适应性与相对性的例子,至少对一些论者来说如此(在此又一次存在解释的空间)。如果国家视伊斯兰教为一种措施,那么饮酒就是被禁止的(不过在我们的文化中其他某些药物则被禁止)。在面临社会态度变迁时,则更是如此。所以,如果社会共识在犯罪化中起着关键性作用,那么法律就应当远离这些一成不变的道德律。
上已述及但仍然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在将行为犯罪化时应尽可能减少对社会道德的干涉。社会道德常常压制个体的自由和少数群体的权利,所以应承认其他的犯罪化标准。在国际刑法中无法形成道德共识,则进一步为在社会道德标准之外提出其他犯罪化标准提供了支持。下文就致力于探讨一些可能的标准。
依照当前理解,刑法专门服务于一个特别的一般性目标 :刑法所保护的是,共同体中人们和平的共同生活。(4)See, e.g., Jescheck and Weigend (1996, p.2).只是,在刑法为实现该目标究竟保护或应保护什么上存在着争议 :法益(Rechtsguter)?利益(Interests)? 规范(Norms)?抑或刑法是/应服务于预防损害?接下来,我们就依次讨论这两种主要的正当化根据——法益保护和损害预防。
(二)法益保护
刑法旨在保护法益的观点,由德国刑法学者弗兰茨·比恩鲍姆(Franz Birnbaum)、 卡尔·宾丁(Karl binding)和冯·李斯特(von Liszt)发展起来。法益概念原本是作为反对权利理论之论题提出来的;依据权利理论,只有存在权利侵害,才能将犯罪合法化。所谓权利理论的主要缺点是,它排他性地依赖于国家的社会契约理论。法益概念则不是以任何社会契约权利为前提,而只是以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利益(goods)”之存在为前提。因而,法益概念在遭遇理论攻击时,不会那么脆弱。
但什么是法益?很难对此问题做出精确回答,这早已被证实了。不同学者都对法益下了不同定义。其中,一些学者只涉及法益概念的功能,而与内涵无涉(如法益被定义成认识论概念,即法益是与法规范关联的基本自由),另一些学者尽管触及了内涵但也只是空洞的循环论证(如值得法律保护的最低限度的利益)。(5)言简意赅的文献评述,参见Roxin (2010, §2 mn.3)。
当前有许多学者主张,至少部分地回归到契约论的前提条件。当前法益定义的其中一个例子即是,法益是指有益于个人自由发展及其基本权利,以及保障这些目标实现的国家制度之合理功能的条件和目标。(6)Roxin (2010, §2 mn.7-9).这些条件和目标是潜藏在法律中的抽象价值,还是在社会领域中现实存在——即便不是有形的实体,则颇具争议。(7)See Roxin (2010, § 2 mn.3, 66-7) with references.无论是这种路径还是其他路径,法益概念起码大多数时候——尽管不总是——在抽象价值层面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
现代法益概念的定义,无论如何是旨在对刑法保护基本的法律利益方面做出合理限制,因而要求法益概念具有批判的、自由主义的潜力。为了展示这种批判潜力,我们可以检验社会中同性恋行为的犯罪化 :对于绝大多数公众来说,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利己主义的行为,并不代表对人类的不尊重,但被社会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确实会影响到公众情感;但公众情感并不是法益。(8)具有说服力的说明见Hörnle (2005)。因为,公众情感不具有个人发展条件所具有的特性和价值,不是实现个人的基本自由所必需具备的,对于确保这些自由的国家存续而言,也不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因此,在接受法益思想的体系中,同性恋的犯罪化不具有合法性。
不过,法益概念自由的、批判的要求是否存在充分根据,则存在争议。姑且不论,对法益概念在不同的变化场景中所呈现的不明确性、任意性和不连贯性的那些批评,(9)基础性批判参见Amelung (1972, pp.261-272) (p.271:不具概念明确性) 以及 Stratenwerth (1998, pp.378-381) (“各种各样无根据的定义”); conc. Insofar Roxin (2006, §2, mn.2-3); 还有新近的Wohlers (2000, pp.213 et seq., 2003, p.281), Hörnle (2005,pp.11 et seq.), von Hirsch (2003, p.18), G. Seher (2003, pp.44, 46), Frisch (2003, pp.216-218) :相对性、宽泛性和模糊性(p.217)。法益概念自身就未能提供实体性的(规范性)标准来决定,哪些利益(goods/Interests)是刑法应保护的,哪些不是刑法应保护的。该决定压根儿就取决于已取得共识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先存在的)法益。可以说,法益保护思想本身并没有回答特定犯罪化决定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反而是从对该问题的回答中推断出奠定犯罪化的价值判断或合法性根据的。因而法益概念是派生性概念而不是原生性概念,它自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分析性能力(10)Stratenwerth (1998, pp.388-389), von Hirsch (2003, p.25), Seher (2003, p.39), Frisch (2003,pp.216-222).,因而有解读认为这造成了法益概念的超负荷(11)Seher (2003, pp.44, 54), Frisch (2003, p.222), Hefendehl (2003, p.119).。此外,也有对法益概念未能为刑法的扩张提供限制性原则的质疑 :法益概念声称,为预防对(集体)法益造成(抽象)危险而允许对只有危险行为的犯罪化(危险犯),如此,刑法就延伸到对那些仅仅是阴谋、预备和/或危险的行为(即便行为距离现实的法益的距离非常遥远而无法合法的犯罪化?)。(12)参见Eser (1965—1966, p.411),他提倡“足以涵盖所有犯罪侵害类型的”的定义。与该问题相关的是法益概念更为普遍的缺点,即法益概念与具体社会现实的松散关系。法益概念主要是作为一个价值有涉的抽象规范概念发展起来的,在社会现实中这些价值的实体化充其量被视为背景事实。相应地,理论上致力于考察价值与“现实”尤其是有形的社会现实之间关联的努力,就非常少了。这就为承认含糊不清的法益概念,如“公共和平”和一般性“公众对法权威的信赖”,开启了大门。这些缺点在本质上有损于法益概念的批判潜能。
在此脉络下,就不会奇怪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在评估刑法条文与基本法的一致性时,并未赋予法益概念任何分量。(13)对该案批判性的分析见Schünemann (2003, pp.142-149);批评的观点Roxin (2006, §2mn.86-87, 89, 2010, pp.580-582)。法益概念多种多样的定义和解释使法院应接不暇,以致于认为法益概念在合宪性审查时并不是特别有用。事实上,这已经为乱伦案的合宪性结论所证实了。法院的观点是,与传统合比例性宪法审查相比法益概念并没有提供更严的要求。而在合宪性视野下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是否认为犯罪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合乎比例,或者这种限制是否有助于保护一般公众或者个人而具有正当性。(14)BVerfG (para. 35) :合比例性原则……有助于刑罚规范对他人或整个共同体的保护。具体而言,刑事禁令需要考虑所追求目标的必要性、适当性以及狭义上的合比例性。(15)BVerfG (paras.36-37).至于作为一般的决定标准的后者,则需要在干涉基本权利的严重程度与干涉原因之间衡量,不能不合理、不公平、不恰当。
显而易见,在批判性地评价刑事禁令方面,宪法法院的立场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宪法审查比法益概念更无效——法院认为乱伦罪符合合比例性原则。(16)BVerfG(paras.51-62).尽管法院是在沿着强化刑法“合宪性”的方向走,也尝试推动宪法甚至取代法益概念,但合宪性的结论却暴露了宪法路径所遭遇的问题,也即宪法缺乏限制刑法尤其有关侵害个人权利的专门规定,(17)Böse(2003, p.91), Swoboda(2010, p.36).合比例性审查还不足以精确到通过特定方式就能预见其结论。(18)Bunzel(2003, p.111) (认为立法者受益于其在追求目的方面广泛的特权)。事实上,可以说宪法审查及其价值决断是如此具有开放性以致于可以证明任何结论。换句话说,刑法规定只是在非常例外的情形才有可能被宣告违宪,或者说可以预见违宪的结论只是例外——在无法被任何更高位阶的社会目标正当化时。
这也反过来表明,至少与宪法上的合比例性标准相比,法益概念不像我们所批评的那样空洞、模糊。无论如何,如果对法益概念的妥当解释得到采用,与宪法上的合比例性标准相比,其在限制刑法的潜能方面则更有效、更有价值。比如,乱伦罪在法益概念下就是不合法的。所以,法益概念至少可以作为刑罚规范与不确定的比例性标准之间的中间概念来用。尽管这种调节可能不会走得足够远 :一如我们所看到的,法益概念有其自身的缺点,尤其是在存在论、社会学方面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在此,损害原则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现在我就转向损害原则。
(三)损害预防
英美法中同时进行的讨论则以损害原则为中心,即人之行为犯罪化的正当化理由围绕损害概念建构,尤其是要求对他人造成(事实上的)侵害。不过,一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损害原则也被证实无法令人满意。可以说明该原则说服力太弱的事实是,有关通过动用刑法来强制推行道德的持续性争论。此外,更为时髦的路径也扩张了原初的损害原则,如涉及“损害的风险”和“自我损害”。
对损害原则原初思想的阐述可以追溯到约翰·斯图加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文《论自由》。(19)J.S.Mill(1859, 1948).密尔在该文中指出,“权力违背文明社会中的成员之意志,正确对其实施干涉的唯一目的,是预防对他人的侵害”(20)Mill(1859, 1948, p.73).。密尔的观点是高度自由化和自由主义的,它的目标是阻止社会只是依据道德信仰就去审查个人。损害原则也被发展成为限制任何形式的社会和政治干涉,尤其是限制以刑事制裁的形式介入。
需要注意的是,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损害原则在刑法理论中仍具有高度争议而未能充分发展,一直到沃夫登报告(Wolfden Report)及其引起的哈特-德夫琳(Hart-Devlin)之间的论战(21)一方参见Devlin(1965),另一方则参见Hart(1969, pp.50-52, 71, 1983, pp.49, 78) :赞同沃夫登报告。Hart的观点后来也被Raz采纳,Raz(1986,1989, p.420) and Hörnle(2005, pp.11 et seq., 467 et seq.)。才使其成为关注中心。哈特-德夫琳论战围绕的是损害原则的效力,或者是否支持进一步的犯罪化标准而超越非道德性。相应地,它没有提供太多有关概念的意义及其范围的考虑(即便哈特确实是在父权主义语境下接受了该原则的某些限制,这点非常有趣。)
在英美刑法的论辩中,损害原则最终因美国法哲学家乔尔·范伯格(Joel Feinberg)以其四卷本的《刑法的道德限制》系列著作,而获得巨大的实质性突破。(22)Feinberg(1984, 1985, 1986, 1988).不过,范伯格对犯罪化之正当化根据的讨论,不仅限于“对他人的侵害”,(23)Feinberg (1984).他也肯定对严重侵害他人感觉之行为的犯罪化,就此而言,范伯格已经超越了密尔。(24)Feinberg (1985).此外,范伯格也讨论了法律父权主义和法律道德主义,但他否定对这些行为犯罪化的正当性可能。范伯格对损害他人的讨论以下列原因引人注目。首先,他将损害定义成被行为“利益的妨碍、撤回或挫败”(25)Feinberg(1984, p.33).。乍看起来,损害概念要比法益概念广泛,后者仅仅涉及对利益的阻碍;不过在此存在着适格性标准 :只有错误的损害(wrongful harms)才能为刑法所禁止。(26)Feinberg(1984, p.34)。错误概念的定义如下 :“当一个人的行为无根据(不正当或不可宽宥)地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就是错误地对待他人……”(27)Feinberg(1984, p. 34).。换句话说,使得他人的利益受阻。这就是“损害原则可能的表现形式中该术语(即损害)必须承载的规范意义”(28)Feinberg(1984, p.34).。错误性的要求,给纯粹的工具主义——自然主义导向的损害原则增添了一些规范性分量,该原则就变成“有关错误行为造成的侵害”(29)Simester and von Hirsch(2011, p.52);但要看到与损害无关的错误行为(pp.50-51)。的原则。不过范伯格并没有给他的规范性标准增添多少具体的规范性内容 :相关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并没道出多少“不可原谅”的标准或者说这中间的哪些行为是“不可原谅的”。退一步而言,即便范伯格所述是指,对于利益的阻碍不具有正当化事由或宽恕事由,该规范化标准也十分有限——这也几乎无法在妨害哪些利益构成损害和妨害与哪些利益不构成损害之间做出区分。范伯格确实在“福利性利益”“隐秘性利益”及其与必需品之间的关系之间做出了些许区分,但是仍未足够精确而无法提供必要的标准。换句话说,范伯格认识到了损害原则的不足即损害原则纯粹的自然主义特征,且指明了克服其不足的方向,但最终未能提供克服其不足的完整理论。
范伯格的考虑也因其他原因而引人注目。范伯格提倡,在评估损害是否发生的过程中,以(相关利益的)“前进(advance)还是后退(retreat)”作为衡量的“基点”或“基准”。(30)Feinberg(1984, p.53).由此,损害的发生就总是取决于潜在受害人的“原初状态”。如此一来,“损害”就成为“相对性的概念”,即损害总是相较于潜在被害者之状态而言的 :“一个人是否受到侵害取决于他原来在哪儿,及其状态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31)Feinberg(1984, p.54).不过,也可以不从相对性角度理解“基准”概念,即如果行为人的利益被限制在中心线以下,而且陷入了遭受损害的境地,就可以认为该人遭受了损失。(32)Ibid.
无疑,范伯格对损害原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对损害原则极富弹性的定义,仍是高度自然主义和实体性的。该原则规范根据仍十分模糊,损害原则的内容和范围也就依然不够充分清晰而具有高度争议。
其他一些学者也试图通过补充一些更为具体的内容来改变损害原则的空洞性。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以自由和自治的概念解释损害原则,他称之为“自由原则”。(33)Raz(1986, 1989, p.413).个人自由与损害预防之间关系可作如下说明 :自治性存在于人类具有不同行为的可能性,以及利用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任何剥夺这种可能或利用这种可能性的能力之行为,都是对他人的侵害。所以,损害包括降低行为选择可能性和自律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之减少。(34)Ibid.
事实上,拉兹的自治性是以其他原则为基础的,我们可称之为自治性原则或非干涉原则。阿图尔·爱泼斯坦(Arthur Ripstein)则称之为自主权原则(sovereighty principle)。(35)Ripstein(2006, pp.215-245).相应地 :
每个人都被授权可以充分利用其权利,其他人也是如此。这种权利的共同实现有赖于参与者不受干涉并自愿合作。任何人都不允许在未经他人同意的前提下,利用或者侵犯他人的财产。如果所有人都容忍如此行事,那么他就从属于他人。(36)Ripstein(2006, p.233).
因此,将那些并未通过不适当方式干涉他人自由的行为犯罪化,是错误的。
与建立在自治或自由基础上的观念相关的问题,是其潜藏基础明显缺乏精确性。爱泼斯坦的观点是,“为设定或追求他/她自身目标而干涉他人行为的唯一理由,只能是保护他人的自由”。人们很容易和他达成一致。(37)Ripstein(2006, p.245).但该观点仍然没有回答基本的前置性问题,也即哪里是一个人自由的终点和另一个人自由的起点。更重要的反对意见认为,这是建立在自治基础上的概念,而自治与自由意志实现的前提是预先的规定得到保护。这就意味着不具有自治性的人,比如小孩子或者具有精神疾病的人不具有这些特征,却特别需要得到这些保护。
所以说,尽管对损害原则的这些解释都在为以前的自然性定义提供规范性,但似乎只是为这种规范性提供了可能的起点而已。完整的规范理论必须能详细说明影响自治的各种类型,从而证明所施加的刑事制裁(而不是其他较弱的社会和法律措施)具有正当性;而且也应进一步对非自治的保护做出解释,可能的途径是补充相关元价值。
损害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因相当宽泛而导致产生歧义。这与损害原则规范性的价值一面尚未充分发展的现实有关。但另一方面,损害原则似乎要比法益原则的范围狭窄 :损害原则强烈的自然主义甚至实体主义面向,极大限制了犯罪化的范围。这在刑法的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潜在影响,不过我更愿意将关注点集中在特殊领域——危险犯。之所以关注这一领域是为了说明维持损害原则的批判潜能和在某些领域放松控制的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
原本狭义上的损害原则是指犯罪的现实性侵害。换句话说,是侵害了具体权利而带来了有形(原本)的损害(该要求于此高于法益原则)。即便只有损害危险(risk to harm)也可满足损害原则,在今天已无异议。(38)Simester and von Hirsch(2011, p.44) :直截了当地禁止作为候选对象。因而,范伯格也将损害原则拓展到前阶段的行为即对他人损害的风险,以尽可能阻止犯罪。(39)Feinberg(1984, p.190).在将只是造成风险的行为犯罪化时,范伯格主张立法应考虑3个方面要素 :损害的大小和损害的可能性、“制造风险的行为之独立价值”。(40)Feinberg(1985, p.191).这些情形中的相关行为,“既不是完全无害的,也不会直接或必然造成损害……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制造了危险。就此而言,这也是对立法者的“粗略规则”。(41)Feinberg(1984, p.216).安德鲁·冯·希尔施(Andrew von Hirsch)称之为包含了3个层面的“标准的损害分析” :(1)确定最终的损害的严重性及其可能性;(2)在损害严重性与行为的社会价值以及这类行为犯罪化对行为人行为自由所可能造成的限制之间进行权衡;并且(3)兼顾犯罪化的附带限制,如对隐私权和表达自由的侵害。(42)von Hirsch(1996, 2003, p.261),也参见Simester and von Hirsch(2011, pp.54-56)。
道格拉斯·胡萨克(Douglas Husak)将损害原则扩张到对损害风险的预防。他尝试重新界定过度扩张的损害原则,(43)Husak(2008, p.159).尤其是通过四重累进性要求来遏制犯罪化 :被禁止的行为必须制造了“实质的风险”(44)Husak(2008, pp.161-162).,禁令必须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45)Husak(2008, p.162) .、由第三人的行为所引起的损害能够被合法禁止(完整的损害)(46)Husak(2008 Query, pp.165-166) .、行为人行为时“具有一定的可谴责性”(47)Husak(2008, p.174) :行为人不承担责任,除非该行为所制造的风险对于最终损害的风险具有一定程度的责任。。
(四)法益原则与损害原则相结合拯救自由主义刑法
上述简短的概览表明,损害原则虽然在一些方面区别于法益概念,但两者并不具有十分明显的差别,却总遭遇相似的批评与困境。尤其值得关注是,有关损害原则与法益概念所谓的不同道德根据。与法益概念不同,损害原则是基于后果主义原则的传统思维,它关注的是禁止行为之效果;相应地,只有对他人存在潜在危险的行为才能予以犯罪化,即犯罪化的目标必须是为了预防损害,可称之为“预防性的损害原则”。基于损害原则和法益概念的上述理论分野,我们可以预见二者在适用中的不同问题。
前已述及,可以对损害原则做不同的解释 :或者聚焦于行为本身,或者审查该行为自身在一定程度上的危害性(或损害风险)。这些解释使得损害原则接近于法益概念的道义论基础,如此,就可以为观察两者的相似性提供线索。
区分对损害原则的两种解释,不仅在概念上是适当的,在实践中也是重要的 :预防性的损害原则为受影响的利益进行功利性权衡留有空间,而道义论的路径则不考虑后果。在国际刑法的视野下这些区分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决定是否对利用定时炸弹实施国际犯罪的行为人施加酷刑。
损害原则只关注行为的直接损害,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过于狭窄了。而预防性的损害原则似乎又过于宽泛,“几乎任何潜在的刑法规范都必然能预防某种损害行为的发生”(48)Tadros (2011a).或避免范围更广的损害性后果。这也表明,作为批判工具的损害原则与作为过度限制工具的损害原则之间的界限,明显是虚幻的。
法益和损害原则在指向犯罪化的理论方面具有类似性,用道格拉斯·胡萨克的话说,就是将“可以正当化的刑法和不具有正当性的刑法”区分开来的规范性框架。(49)Husak(2008, p.3).二者都是刑法自由主义目标的组成部分,自由主义刑法遵循着刑法的最后手段性特征(尤其是将那些仅仅违反道德行为予以非犯罪化),以及责任原则、合法性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等众所周知的基本原则。就损害所表述的是实体的、可以把握的结果或对法益的侵害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损害原则作为法益保护原则的消极侧面来理解。在损害原则被法理“理念化”或“规范化”(跟权利理论和法益理论一样)之前,(50)Cf.Amelung(1972, p.10).历史上对社会损害(社会危害性)作为所有犯罪的经验性、自然主义之根据的理解(依照社会契约理论),(51)See supra note 15.似乎可以确证这种解释。
另一方面,法益概念可以为损害原则提供规范内容,使其——在法益作为其侵害对象的视角下——“实体化”或“规范化”。换句话说,如果法益概念能够充分发展为规范性理论,就可以回答何种损害应由刑法禁止,而这也有助于确定刑法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损害之合理内涵。这与范伯格对利益的讨论并随之尝试损害原则的规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但这有可能只是提供一个更加限制(或只是更详尽)的犯罪化标准 :在相关联的意义上,损害仅仅存在于特定的在道义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利益,即法益受到了不正当的侵害。法益概念是意在说明值得刑法保护的利益之精致理论;因英美刑法只关注损害,法益概念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损害可被定义为,侵害事实或潜在上具有重要社会意义或为宪法所认可的利益,也即损害的是位于法益背后所具有的利益或价值。可如此理解的规范性的法益理论,为空洞的损害原则(对什么的侵害)加入实体性的内容也许这说明了法益“实体性”的潜能,即为什么有很多人认为法益概念相较于损害原则具有优势。(52)See Fletcher(2007, pp.40-41), Dubber(2005, pp.501 et seq.)
在今日的法律现实中,反观这两种概念的历史起源可以启发我们提出 “再规范化”这些原则的可能途径。比如,19世纪“权利”理论和“利益”理论融合成法益理论,就可能为今日的法益理论与合宪性/人权理论之融合描绘出蓝图,也即在保护公民免受国家对其基本权和人权侵害的视角下提倡法益理论(包括损害原则)的进一步规范化。这不外乎就是增强刑法的“合宪性”,一如我们所看到的(53)Supra note 31 and main text.——这却是以牺牲法益理论为代价。
法益概念与损害原则的结合,并非自动就能确保自由主义刑法的魔幻公式。尽管这两个概念均具有自由主义的潜能,但无法忽视的事实是,二者未能阻止现代刑法愈演愈烈的非自由趋向。如果认识到前面对法益概念歧义性和“空洞性”的批评,再加上与对损害原则批评的比较,平心而论,两种概念都足够灵活以致于能够为几乎所有行为的犯罪化提供正当性。基于此也就不会特别奇怪,该概念非但没有阻止,反而积极推动刑罚扩张至特别刑法的所有领域(比如,经济刑法和环境刑法被认为是由其他部门法领域所规制)和大量违反公共秩序的犯罪——从性有关的行为(如卖淫或同性恋)到毒品滥用行为。一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概念还进一步拓展到仅仅具有损害风险之行为(54)See supra notes 67 et seq. with main text.——无论是间接性侵害还是仅仅对(集体)法益的(抽象)危险——的扩张,这就波及到了预谋、预备和/或危险的行为,易言之,最终任何所谓的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行为都可能被犯罪化。
不过这两种概念的充分结合——如上所述,重视这两种概念自由主义根源的结合——有助于阻止这种非自由主义趋势。随之而来的思想体系从对这两种概念批判性、自由主义式的理解转变成,对不自由的公共政策事项予以正当化,也只有对该体系所潜藏的规范化面向——犯罪化的合法性原则(55)See G.Seher(2003, pp.45-56) and previously supra note 24 and main text.——进行重新发现、阐释并且转换成更具体的理性刑事政策导向时,该体系才可以维系。法益——损害结合理论的批判能力,可能在适用公正归属标准(客观归属理论)时会得到进一步提高。客观归属理论可以为这些概念再增加“规范性的内容”,毕竟所有刑法罪名最终都要归属于实施该犯罪行为之人。
三、 在国际刑法层面的转换
如果我们现在将这些概念在国际刑法层面进行可能的转换,首先就使得国内法对过度犯罪化明显违反法治原则的质疑显得不那么重要。这跟国际刑事司法的局限性及其所关注的主要事情有关。国际刑法除了以其(普遍管辖权的)适用范围区别于国内刑法外,另一个更本质的原因是国际刑法仅仅限于保护基础性的法益并预防这些法益在事实上受到损害。国际刑法恰恰建立在对这些基础性法益的保护上且以预防对这些法益的侵害为导向。国际刑法局限于这种兼具基础性和普遍性的利益和价值,说明了国际刑法合法性的严格要求 :国际刑法中不会有相对主义挑战存在空间。
不过,国际刑法中有关犯罪化的范围所存在的其他挑战,可以借助法益——损害理论的结合解决。国际刑法只涉及为国内法所禁止的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因而可以提出分析这些行为的特殊框架。在国际刑法的发展中,我们必须结合国际刑法的效力受国家主权限制来理解,哪些行为可以在国际法的层面合法的犯罪化(以及哪些行为不适合国际刑法处理)。与当前案例式地逐个讨论有关犯罪的严重性相比,法益——损害结合理论可以画出一条更为原则化的路径。我们接下来检验其可行性。
在与国际刑法“超国家性”(56)Ambos, supra note 1.有关的地方已经说明,在世界和平/国际安全和基本的公民权/人权方面,国际刑法所管辖的范围兼具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意味国际刑法具有两类保护主题。第一类是有关“作为整体的国际共同体”和人类的集体性主题。(57)Thereto Werle(2009, mn.86 et seq., 627), Triffterer(2002, p.342), Neubacher(2005, pp. 100 et seq.), Ambos(2006, pp.111 et seq.), Cryer(2005, p.4), Cryer and Wilmshurst(2010, pp.6-7), Melloh(2010, pp.83, 86, 88-89).这类主题聚焦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集体性一面,尤其是《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集体维和行动体系,不过,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也表现出群体性要素——见下文。第二类则在有关人类基本权利和基本人权(因而也涉及人类尊严)方面,国际刑法核心罪名也保护个人利益。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个人维度相对于集体维度具有优先性。就此而言,灭绝种族罪保护的是——除了作为人类一部分的族群之存在外——作为族群成员的个体权利免受侵害(尤其是生命、身体完整性和自由)。(58)Cf. Lüders(2004, pp.43 et seq., 166), Melloh(2010, pp.90-91), Bock(2010, p.92).类似地,危害人类罪——基于大范围的和系统性的要求——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集体层面,但同样保护集体与个人的尊严、生命、自由等权利。(59)See Luban(2004, pp.86, 120, 159-160); conc. Ambos(2011, pp.281-282), Bock(2010, pp.97, 101-102), see also Melloh(2010, pp.91-92).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战争罪。战争罪的人道主义目标必然涉及遏制冲突和促进世界和平,但这些罪名同样也保护人之尊严及其生命、身体的完整(这里保护的是平民),即便在武装冲突时期也是如此。(60)Melloh(2010, p.92), Bock(2010, pp.115-116).因此,国际犯罪中总是存在集体性或群体性要素,这意味着相关个体性受害者,并非基于其个体,而是作为特定群体或集体利益之成员或代表而遭受攻击,这反过来又代表了人类。这点在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中非常明显,但战争罪中敌对方平民受到攻击就不同了。在这种集体——个人主义范围上,国际刑法的存续及其效力是能够为人们所预见的,同时也为超国家的刑罚权提供了规范基础。
我们接下来更深入讨论这种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管辖范围。如上所述,国际刑法所保护的个人,是作为人类的一员或者作为人类组成部分的群体中的一员。这点与国内法不同 :在国内法中,诸如“国家安全”一类的集体主义概念只有从相应的个体中获得道义力量。而在国际刑法中,诸如“人类”“人道”或“种族”等集体主义的概念则自身即携带着某种程度的道义上的力量;此外,个体也可以从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道义力量中受益。因此,国际犯罪具有双重的价值面向,通过某种途径阐明二者的关系有助于说明国际刑法的合法范围 :第一层是国际刑法特有的集体价值一面,第二层是具体存在于集体中之个人价值一面。
在理论层面结合这两方面需要发展出合适的概念。一种可能的路径就是拉里·梅(Larry May)所提出的,即承认国际性损害原则。(61)Cf.May(2005, pp.80-95).相应地,国际刑事执法如欲存在合法性,相关的犯罪所直接针对的就不仅仅是个人,而且“也要具有集体相关性——无论在被害人损害的特征方面还是在损害施加者的特征方面均以群体为基础”(62)May(2005, p.89).,也就是说人道受到了侵害。(63)May(2005, pp.82 et seq.).这种考虑的不足是,我们很难看到损害概念是如何说明所谓的“人道受到损害”,而“人道”几乎不会受到损害。只有受害者自身才会受到侵害,而就其价值而言,这种损害可分为两方面的内容 :一种是针对作为个体的被害人而言的,另一种是针对作为集体主义概念的人道而言的。后者的内容较之前者更为抽象和普遍,且两者也只是部分重合。说明具体的社会意义上的损害及其双重价值内容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损害理论和法益理论结合起来。
这就给我们带来另外一种可能的理论路径,也即发展出兼具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法益概念,尤其是强调法益侵害的实体侧面。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法益概念国际化和实体化;我们所认知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法益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国际化和具体化的法益概念。这就首先要求我们开发该理论与法益理论原则基本一致的特有的集体主义价值的一面 :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人性或人类普遍和抽象的集体主义价值具体化——形成一种具体的、包罗广泛的法益价值。下面试举一些例子。灭绝种族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等的存续,这类预先特定化的团体之存续价值,就是人类价值的具体化。战争罪所保护的法益是人民——在进一步的情景或语境中则是指“敌人团体”——的存续,其价值也是人类价值的具体化。在危害人类罪中,人道主义的保护法益就不那么具体了——得到保护的人正如人类社会成员都会受到保护一样;然而,即便该语境中(大范围和系统性)的要素,也要求集体主义的一面,即攻击针对的是特定团体中的人员或者常常是基于与团体有关的原因。除了价值具体化的一面,也应该关注侵害的实体一面。核心国际犯罪明确要求严重的具体损害(我们将发现,其他语境下该要求不太明显)。因而我们所明确的法益,不仅仅是刑法所应该保护的——这仅仅是“柔性的”道德声明——而是法律表明他们必须要保护的,也即存在保护他们的“强硬的”法律义务。
除了复杂的价值侧面,实体性损害的要求更值得关注。这在国际刑法的其他语境中也具有实践意义。我们通过观察恐怖主义犯罪的例子来说明,结合理论是如何回答国际刑法曾经纠结的一些难题的(64)可参见Arnold(2004), Proulx(2004, p.1009)。:恐怖主义应由国内法还是国际刑法处理?恐怖主义只是危害人类罪行为中的一个特殊情形,抑或他所独具的特征足以使法律特殊处理合法化?初始的、间接性行为,如成为恐怖组织成员,也应该被国际刑法犯罪化吗?恐怖主义侵犯集体——个人主义的利益;它不属于侵犯个人的犯罪,但是属于侵犯作为宗教或民族团体成员的犯罪也侵犯了个人,反过来成为作为集体主义概念的人道主义的代表。当一个团体因其特征而被认为不能达到人类整体(不仅仅是敌人团体)的程度时,其利益其实就变成了人道利益的实体例子,这也就满足了国际刑法的价值侧面。所以,恐怖主义犯罪兼具上述双重的价值面向。用德拉姆(Drumbl)的话说,这就是国际刑法可以更好地查获恐怖主义的“邪恶”并且允许跨文化对这种邪恶定罪的理由。因而,应由国际刑法处理恐怖主义的问题。(65)Drumbl(2002, pp.341-342).尽管这种观点在理论中尚未获得主导地位,但已有国际层面的犯罪应置于跨国刑法的类型下考虑的倡议。(66)对此参见 Boister(2003, p.953)。依照该观点,恐怖主义犯罪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刑法,(67)有关区别参见Ambos(2013b, pp.295-296, 2014, pp.223, 226-8)。而(只是)属于作为跨国刑法意义上的国际法(以条约为根据的犯罪)。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是否应将恐怖主义作为明确的犯罪类型处理。如果恐怖主义包括危害人类罪,那么就没有强烈的理由要求将之作为危害人类罪的范畴对待。如果恐怖主义行为已经属危害人类罪的范畴,将这些具有特殊价值面向的行为评价为“恐怖主义”就没有意义。恐怖主义的动机、目标及其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价值内涵已被吸收在危害人类罪的定义中了。只是,考虑到实体性损害的强烈要求,尤其是国际刑法语境中,抽象价值被期待赋予特别重要的分量,模糊的、遥远的行为,如作为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则不宜犯罪化。
照此推论,国际刑法的其他领域即遥远的损害或对法益的遥远侵害,也可以参考法益——损害理论而受益。如上所述,国内法中的刑法领域已经出现了理论难题。在国际刑法中犯罪化则是更大的难题,理论的批判功能也会赢得充分力量。在我看来,尽管当代国际刑法十分关注系统性或大规模的暴行犯罪,但这只是基于国际刑法跨国性及其具有的一般功能罢了,严格从后果视角而言,国际刑法在有些时候已有悖于最小主义原则了。尤其是国际刑法的责任模式,和/或包括犯罪参与方式,也即如上所述已经扩张到了损害的风险。最新例子是战争罪的法典化,即囊括了计划、预备、教唆等行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8条)。(68)有关批判性分析,参见Ambos(2010, pp.493-497).依照本文的辩护路径,这些规范不具有合法性,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具有超国家和普遍性管辖范围的国际刑法之组成部分。需要说明的是,国际社会中对包括侵略在内的国际刑法中的核心犯罪的诉讼,原则上以普遍管辖为基础但普遍管辖缺乏传统的属地或属人的连结点。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狭义地理解核心罪名,包括与罪名相应的责任追究模式。对行为要件(actus reus)外延的扩张与狭义上自然主义的损害要求是矛盾的;对预备行为犯罪化也会动摇对有关犯罪实施普遍管辖的正当理由(随之而来的是领土国家的主观限制问题)。
法益概念和损害原则的结合,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贡献于国际刑法理论。国际刑法保护个人免受侵害的功能,囿于其强烈的集体主义一面很难仅仅借助国内法实现。酷刑就是其中的例子 :果真如此,国家应避免将这类酷刑犯罪化,即便国家将酷刑犯罪化了,也应避免强制执行这些措施。大体而言,国家有时会过于局限于民族性而忽略了被德国宪法认定为绝对价值的狭义的人类或人性尊严即遭受酷刑(不是其他——仅指国家的——犯罪)所损害的价值。狭义的“尊严”使得人类社会成一个集体实体。危害人类罪所挑战的观念是,以人性尊严为集体特征的人类社会。该挑战的定位是人类之价值取决于其所从属的团体;但也可能以直接否定人性尊严的姿态出现,如施加酷刑。因此,对人类尊严的侵犯在理论层面符合国际刑法集体主义的一面。这也可以从法律的表述中发现,即法典要求系统性攻击方式。(69)Compare Renzo(2012).所以,通常由国际刑法来规制酷刑。损害原则和法益概念有助于确认规制酷刑犯罪的真正的潜在理性——这种理性超越了对身体甚至灵魂的保护,而达到对整个人类或人性的保护。法益概念会呼吁对人类尊严的调查(人性尊严的概念是否足够清晰而能够充当法益?我们是否可以发展专门的人性尊严概念作为法益?对人类而言人性尊严的价值是什么?);而损害原则有助于确认在对作为法益的人性尊严以某种方式被侵害的各种情形中,哪些情形可以使刑事制裁正当化,哪些尚不足以上升到这个层面(如果不是个人的或仅仅是象征性的)。
结论是,要理解兼具双重维度特性的国际刑法,就不能不结合损害原则和法益概念。损害原则无法说明为什么需要保护诸如“人类”(而不是具体的个人)这类抽象价值;至少根据对法益概念的某些解读,法益概念无法说明国际刑法中对具体的个人具有重要意义的自然后果的严格要求(而不是对“人类”的抽象侵犯)。该主张不仅是反思性的,也在国际刑法中表明结合理论具有批判性的、自由主义的重要意义 :对“人类”表象性的侵害(如象征性侵害)不应被犯罪化;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刑法对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损害的处理,应当与对个人主义的侵害明确区分。
四、结论
一如先前的研究所表明的,(70)Ambos(2013b).国际刑法的有限共识是,在存在严重侵犯人权以及对人类和平与安全的大规模威胁时,保护某国内和超越国界的人民和平共处。国际刑法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的结合,尤其是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免受非法政权(outlaw States )侵害的必要性,最终是对人类尊严的保护,是对超国家刑罚权的正当化。同时,本文也尝试通过个人——集体的观点来阐释国际刑法的一般功能 :对个人和集体的基础性法益的保护(保护对象的范围)以及预防这类法益遭受现实的损害(后果或影响)。
只要我们赞同国际刑法的一般功能与法益和损害的关联性,我们就可以批判性地评估国际刑法的范围。本文的主要目的即是提供这种评估工具。在明确国际刑法的一般功能后,继而检验诸如国际刑法中刑罚的目的等其他问题 :基于国际刑法对给人类尊严的价值给予特殊且非同寻常的地位,国际刑法中的刑事惩罚旨在建立普遍的法规范意识——在积极的一般预防和综合性预防关联的意义上附带的要求是和解,或在“表达”概念的核心意义下聚焦于刑罚(可能)的沟通功能。非常期待这类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研究能够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