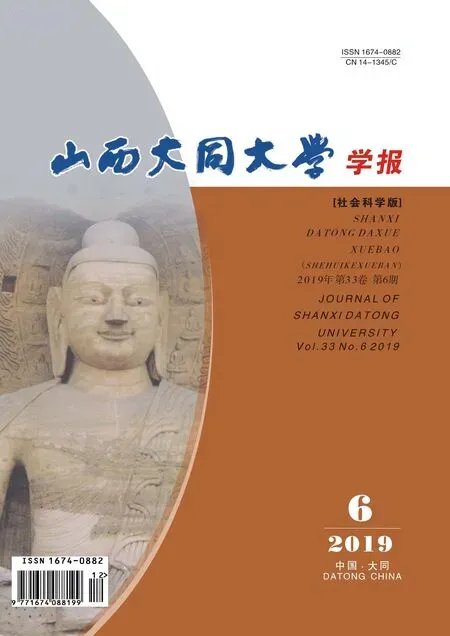口译语义加工跨学科研究:认识论溯源
陈雪梅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一、引言
Alves 和Albir 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本、跨文化交际复杂行为,同时也是译者作为主体认知行为的特定结果;但这种内在的复杂认知行为,无法通过外在观察而直接探测到,因此翻译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呼吁跨学科研究框架。[1]与笔译相比,口译的认知加工活动更为复杂,对信息传递的即时性要求很高,这使得译员必须实施更具挑战的多任务操作;同声传译的口、脑、耳并用的交际模式更是吸引了其它领域的认知科学家们的兴趣,使口译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浓浓的跨学科研究特点。
口译的语义加工是口译研究的核心问题。从现实观察来看,以口译员为中介的双语交际目的就是传递意义,而不是字词。这一点,为释意派和职业译员反复强调。从口译的认知过程研究来看,无论是释意理论还是信息加工范式,都支持意义传递是信息加工过程的核心任务。释意理论是关于意义的理论,认为意义是口译认知研究的核心问题:“无论信息输出和接受的环境多么不同,意义是翻译的核心问题”。[2]信息加工范式同样重视语义加工,信息加工流程图就是传递意义的流程图,语义加工是信息加工的核心部分。Setton[3]通过建立同传认知语用模型旨在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意义的中间表征问题,通过建立小型语料库,验证语境和语用因素在语义加工中的作用。口译的语义加工过程研究自始至终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但是口译的跨学科研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其研究视角、方法、手段和结果也受到了其它认知科学研究成果掣肘。通过回顾口译语义加工研究范式的认知论演变,会清楚地帮助我们认识当下主要口译理论或范式背后的跨学科支撑及其局限性,以便结合口译认知活动自身的特点,从新的视域更好地开展口译的跨学科研究。
二、口译语义加工研究的认识论演变
(一)结构主义视域下的符码转换观 20世纪50、6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和早期的实验心理学家仍将翻译看成符码转换行为,研究层面限于语言问题,忽视了交际功能和译者行为,因此对语言意义的处理也是符号系统间的处理。对翻译的科学探究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但当时的先驱主要是对翻译的语言方面感兴趣的语言学家,“考察语言系统与语言描述的现实、语言系统间的关系及源语和目标文本的语言组合间的关系”。[4]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信息理论数学模型的发展,翻译被看作是语言代码信息的解码与编码的转换活动,而口译员作为“发射方”和“接受方”之间特殊的“传输器”,把含有信息的一种“代码”通过“信号转换”转换为另一种代码;这种代码转换或符码转换的系列观点逐渐成为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关于翻译的一个最强有力的隐喻。[5](P55)在早期的口译实验心理学研究中,对数据的处理仍按代码或符码对等方式,忽视口译交际行为,如Oleron & Napon[6]和Barik[7]的实验,因此其实验效度,包括实验环境、选材和数据处理方式,也受到质疑。
(二)认知主义视域下的信息加工范式 认知主义(cognitivism)源于20世纪50年代认知心理学对行为主义的批判,把人的认知系统比作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心智活动被理解为心智中的表征结构及对这些结构的运算;认知过程在本质上是象征的、线性的,由一个中央认知加工系统统领。以认知主义的信息加工心理学作为理论支撑,口译信息加工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应运而生,旨在描述口译、特别是同传过程中信息的线性传递过程。信息加工范式重视信息加工过程中的技能分解,语言加工过程被进一步分解为信息处理次要任务或者分解技能,如音位和词语的识别、词汇的意义明晰化、句子处理和推断;这些问题的“自然语言处理”层面构成了认知科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领域。[5](P56)信息加工范式同样重视语义加工,信息加工流程图就是传递意义的流程图,语义加工是信息加工的核心部分。口译信息加工子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语音、句法、语义加工及注意力分配都是信息加工的一部分。
口译信息加工范式通过建模来描述译员对源语信息的识别、接受、解码、储存、转码及传递的线性过程。Gerver 和Moser-Mercer 是信息加工范式的典型代表,前者在牛津大学获心理学博士,是将口译作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家,后者长期从事口译的实践和教学,但是与其他从业实践者不同的是,她积极将其他认知科学的理论成果运用到口译研究中来。两者都是早期口译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且都于20世纪70年代选择了信息加工范式,这与认知主义在当时的影响力分不开。
Gerver[8]建立了首个同传过程模型。在该模型中,信息被接受后进入缓冲储存机制(buffer store),这一机制使译员得以在对前一信息语块(segment)加工的同时储存新信息;信息接收后,重要的两个环节是“解码”和“编码”过程。在“编码”环节中,信息流进入“源语解码及储存机制”(decode & store),源语编码块(SL-code block)被激活,信息从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进入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并返回上一层;“解码”之后信息进入“目标语编码及储存机制”(encode & store),并激活目标编码块(TL-code block),信息从深层结构进入目标语的表层结构,并返回上一层;“解码”之后,信息流进入“输出缓冲与控制机制”(output buffer and control)。整个流程图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解码、编码控制机制及储存与缓冲机制,前者负责信息加工,后者负责信息储存与缓冲。这一流程图初步模拟了译员的同传信息流动过程,但是仍有几处值得商榷。首先,信息传递呈现的是线性符号加工,无法再现同传的多任务操作过程。其次,流程图中没有阐释源语和目标语是如何转换的,只是运用普遍生成语法中的相关概念,以“源语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目标语表层结构”的语义流形式出现,但“深层结构”是否是体现两种语言的共性特征,仍存争议。最后,意义的传递完全脱离语境,且与译员已有的专题或背景知识相脱离,只涉及语言本身的转换,这一点也受到了释意派的批判。
Moser-Mercer[9]的全过程同传模型同样基于信息加工范式,与Gerver 的模型不同的是,Moser-Mercer 的模型吸收了信息加工范式中的言语理解相关理论,并借鉴了当时心理语言学关于记忆的最新成果。她区分了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与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并强调了两种记忆机制在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全程互动;不同于Gerver 的深层结构,也不同于释意派提出的“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概念,Moser-Mercer 区分了信息的声学、音位、句法和语义特征,借鉴心理语言学中的概念库(conceptual base)和概念网络(conceptual network)来描述信息的语义特征,并强调了语境在语义构建中的作用。
Gerver 和Moser-Mercer 的模型的共性特征是,两者都基于信息加工范式来模拟同传译员的线性认知加工过程,都无法呈现口译的多任务操作特征;语义传递是核心焦点,在语义加工层面,都没有区分词汇层和概念层,因此在语义加工路径上是单一的,难以解释意义翻译和形式翻译两种语义加工路径的并存现象;[10]作为抽象的、高度概括的流程图,两者也难以解释专家译员、新手译员和普通双语者在语义加工路径和策略上的差异。
(三)人文学派的代表——释意派 释意派是口译研究人文学派的代表,人文学派是相对于以信息加工范式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派而言的。释意派和信息加工范式都重视口译的认知加工过程,但释意派反对将口译信息传递过程看成语际间的符码转化,而更重视译员本体及其心理过程,从而实现口译研究的“认知”转向。[11]自然科学派曾批判释意论基于直觉式的内省,缺乏科学的严谨性;而释意派则指责自然科学派的实验研究缺乏生态效度,且对数据的分析建立在两种语言的形式对等上,主张通过对自然语境中口译行为进行观察、反思,并“借鉴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又通过长期的口笔译实践和教学,总结提炼出一套独具特点、日益完整的翻译理论”。[12]
释意理论围绕“意义”(sense),探究: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在意义的形成过程中,语言、语境和译员的认知补充如何交互发挥作用?理解后的意义是以什么形式呈现的?释意派区分了涵义和意义,涵义指语言未使用前的潜在意义;是固定的概念结构,具有共性语言系统特点;而意义是语篇意义,具有个性的言语特点。释意派提出了口译三角模型[13]和认知补充,口笔译的加工过程被认为是对脱壳后的篇章意义的重新表述;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简称“脱壳”)和“代码转译”作为两种语义加工路径:脱壳发生在译员结合认知补充、完全理解源语信息的基础上,按目标语规范重新表述脱壳后的意义;代码转译(transcodage)只适用于对术语、数字、名称等语言项的传译。“脱壳”和认知补充概念的提出并非完全出于释意派的内省和反思,而是借鉴了当时心理语言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如对Van Dijk 和 Kintsch(1983)[14]的语篇理解模式的借鉴:先理解,随后在需要的情况下进行语言分析;言语的组成和理解并不局限于语言或语法提供的信息,还要求语境、知识等其它信息。此外,意义是译员心智中非语言的心理表征,是言内意义与世界知识(认知补充)相互作用的结果。[15]
释意派围绕意义相关问题,提出“脱离源语语言外壳”(de-verbalization)、认知补充概念及“口译三角模型”,对口译学科地位的提升和口译教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释意理论所构建的是“理想”化的口译程序,要求译员的双语能力都达到或接近母语水平,且具备广博的语言外知识和“脱壳”的释意能力;“脱壳”是一种不考虑双语习得背景、翻译方向性及发言人的语速、信息密度等外在因素制约的理想加工路径;总体上难以解释口译活动中“脱离”与“代码转译”两种路径同步激活的并行加工现象。[16]
(四)具身认知的影响——同传认知-语用模型 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也称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源于 Maturana 和 Varela 的自创生理论(theory of autopoiesis),是对行为主义“刺激-反应”学习理论与认知主义的“信息加工”的符号运算和身心分离的二元对立观的批判;具身认知强调认知是身体机能与环境互动耦合(coupling)的结果,这一互动分三层系统:分子系统、自创生系统以及自创生系统与环境耦合的结果——社会与语言互动。[17]具身认知对翻译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产生了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18]具身认知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包括口笔译)认为,意义并不是以静态心理表征的形式储存在大脑中,而是通过大脑、身体和环境的动态互动得以呈现,因此,不仅考虑译员大脑的黑箱操作,还要考虑译员与外部环境中的工具、手段及翻译过程中的其它参与者的互动,这些共同塑造了译员行为和翻译产品。[19]但是,具身认知发展到极端化就会变成纯粹的身、心、环境互动论,摒弃心理表征的存在,导致没有认知机制的存在,从而无法提供形成假设的理论指导,因此具身认知需要动态的、以行为为导向的心理表征研究的支持,与心智运算的相关理论合作。[20]在视域融合这方面,Setton 无疑是代表人物。
虽然Setton 在模型的构建中提及将关联理论、认知语义学、心理模型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作为理论框架,并没有明说与具身认知的关联,但是“将同声传译的过程视为认知表征与环境耦合的动态系统已经体现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观念”。[21]在语义加工路径的呈现上,Setton 并没有摈弃表征说,在承袭了释意派的“脱壳”路径和代码转译路径的基础上,用心理模型(mental model)作为“中间表征”来表达“脱壳”后的意义。Johnson-Laird[22]认为心理模型是对真实或想象事件的内在结构性类比,这一结构在工作记忆中由语篇的命题表征、其它象征(tokens)和概念构建。关于“脱壳”和代码转译呈现的差异性,Setton 将命题表征类比成代码转译,而将心理模型等同于语篇意义和认知补充相结合的“脱壳”,心理模型和命题表征都可以作为路径,而译文最终的呈现形式“实际上可能取决于表述的表征资源是更倾向于以源语为导向的‘数码’命题,还是更倾向于更有效的‘类比’的、‘非语言特异性’的心理模型”。[23]但是,关于意义的表征是否完全与语言形式相脱离,即关于中间表征的非语言特异性,却引发学界的争论,特别是心理语言学的双语研究认为意义并不完全与语言形式分离,源语结构和方向性因素影响译语表达。[24]此外,认知—语用模型没有摆脱线性符号运算的影响,无法体现语义加工在词汇、句子和语篇层面并行加工;Setton[25]后来也意识到概念层和词汇层同步激活现象,重新运用联结主义的激活扩散模型来解释词汇层的自动转码现象,但主要基于词汇层的讨论,仍无法接受语义加工路径并行激活现象及语义加工影响要素间的互动。
三、结语
语义加工是口译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认识论的源头追溯各流派视域下的口译语义加工研究,更能揭示其利弊及认识论掣肘。结构主义的符码转换观不考虑译者及交际行为;信息加工范式的线性的符号运算无法呈现语义加工路径的并行现象;释意派理想化的意义加工忽视个体差异及方向性因素;认知-语用模型采众家之长,但是理论糅合也有其弊端,关于中间表征的描述仍值得商榷。总而言之,学界认同口译有“脱壳”和代码转译两种语义加工路径,但对于如何解释口译语义加工路径的并存及并行激活现象、语言背景和方向性对语义加工路径产生的影响及译员语义加工策略的个体差异,仍有争议或缺乏深入探讨。有鉴于此,口译的语义加工研究仍呼吁新的跨学科视域融合,其中联结主义的并行分布加工理论给口译的并行加工研究带来新的启发;[10]双语研究特别是双语记忆表征研究对语言背景和方向性影响因素与口译语义加工路径选择的关联或给出新思路;而以实证为导向的专家-新手对比范式将更好地解释语义加工路径和策略的个体差异及口译专家技能的习得过程。这些也是作者在口译语义加工研究领域后续研究的主要方向。当然,跨学科研究要保障口译学科自身的主体地位,不能过于依赖其它学科,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利弊,针对特定的环境中的研究问题,找到最合适的方法更重要。[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