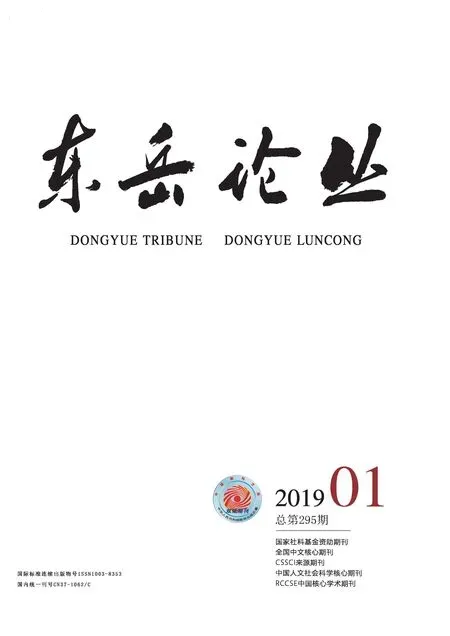论意象的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答简圣宇等教授
朱志荣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我的意象创构方面的系列论文发表以后,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和质疑,我也曾经主动请教一些学者,请他们提出批评意见。简圣宇教授的《当代语境中的意象创构论》一文,就是这些批评中的一篇,其中提出了若干重要问题。本文特专门回应简圣宇教授所提出的商榷意见。鉴于此前韩伟教授的《美是意象吗?》[注]韩伟:《美是意象吗——与朱志荣教授商榷》,《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何光顺教授的《意象美学建构:本体论误置与现象学重释》[注]何光顺:《意象美学建构:本体论误置与现象学重释》,《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两文中也涉及到其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这里一并回应,期待简圣宇、韩伟、何光顺三位教授和学界师友的批评指正。
一、“意象”与“审美意象”
中国古代的意象概念,起初确实有不属于审美范畴的“意象”,但是从魏晋南北朝时代刘勰开始,到王昌龄、司空图、郭若虚、王世贞、王夫之、叶燮、方东树、刘熙载等,从诗文、书画、乐舞评论角度所言的意象,则都是审美意义上的意象。中国古代人们很少用美来评价艺术,但是用意象评价实际上就是审美评价。因此,根据中国传统的哲学和艺术思想资源,中国古代的意象范畴,主要就是指审美意象,狭义的意象就是审美意象,我们在美学专业范围内讨论意象,就是指审美意象。从审美的角度讲,“意象”一词,其中的意是有特定含义的,是指包含着情理交融的主观情意,而不能简单地望文生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意”之象。
审美意象是在审美活动诞生和变迁的历程中生成的。就意象范畴出现以前的审美意识发展说,在审美意识的历史生成的过程中,在人类的精神活动从混沌到细化的历程中,原始意象是多种成分的混杂。原始思维是浑沌的,包括认知、道德、宗教等多种元素,因而原始意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审美意象。所谓原始意象,乃是原始先民们为着实用(如制造生产工具)和宗教巫术(如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等意图而创构的,其中无疑也包含着先民们的游戏心态和趣味,显示出对形式感追求的主观愿望,因而其中也包含着审美的成分。尤其在宗教巫术中,历来都利用了审美的方式,目的是为了借助于审美的成分感动人。当我们在运用“原始艺术”这个称谓的时候,就表示了对其中审美意味的肯定。原始实用意图和原始宗教意图所形成的意象中,也包含了对自然物象情调的感悟,这就有了审美的成分。因此,在原始意象中,审美的成分和非审美的成分是浑然不分的。主体从混沌的原始思维中逐渐分化出审美的思维,逐渐产生独立的审美意识,因而也逐渐产生独立的审美意象。
从逻辑上讲,如果说有非审美意象,也是说得通的。《周易》中“立象尽意”的意,其中的卦象,包括宗教、认知和审美等功能,就不限于审美意象的象与意。当然其中的“观物取象”的方法,比喻和象征的手法,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诗性的思维方式,就有审美的成分。所以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说:“《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注]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4页。因此,卦象中既包括非审美的象与意,也包括审美的象与意。王充《论衡·乱龙篇》在“立意于象”的基础上提出“意象”一词:“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土龙亦夫熊麋、布侯之类。”[注](东汉)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8-249页。这里的意象,则是礼仪上的象征符号。而医学上的人体生理解剖图、交通标志、几何图案和化学分子式、通过图像进行道德说教等图示都不属于狭义的审美意象,不具有情感特征,也不包含想象的创造性。如果把意象简单地理解为意加象、意中象、意之象等,都不会是审美的意象。
在“意象”一词被专门用作文学、艺术评论之后,它的基本含义大体是固定的。意象在诗论、画论、书论中长期使用的传统,都表明它体现着审美的特征,体现着审美的趣味和价值。当我们在美学中说意象的时候,意在强调意象是在审美活动中创构而成的,是具有审美特征的。中国古代诗文、书画、乐舞等理论,把意象理解为情景交融的产物,这是审美意象。审美之外道德、宗教对审美元素的运用,其中所包含的意象,还不是纯粹的审美意义上的意象。如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包含着宗教的意味。但是,早期意象常常有审美的成分。从实用到审美,从原始宗教到审美,是一个发展历程。商周青铜器很多本是使用器皿,后来用来祭祖贿神,本来具有功利的目的,虽然当时的铸造工艺还不能完全批量生产,但是也可以成对地进行生产和模仿制造,在当时至少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审美创造物,当然其中无疑也包含着对审美元素的借用。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把有限的遗存看成是艺术品,看成是审美意象。
审美意象是在主体心灵中成就的,审美意象是审美活动的成果。物象在牛眼中和人眼中是有差异的,人眼进行审美判断时,心理直觉同时作用,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乃至强化和弱化处理,对原生态的物象有所改变,再进行庄生梦蝶般地物我交融,在心中进行创造性的意象创构。意象的创构体现了中国古人俯仰自得的生命情怀,并且具有象征的意味,从有限中体悟到无限。其中的象,是空灵化的,不着痕迹的。而所谓意,主要指想象力统合下的情理统一,其中的意,体现了情感体验的独特性和意味的深刻性,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味。审美活动虽然有有意观赏和偶然相遇的情形,但总体上说,它依然是主体的主动行为,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具有主导地位,从中既体现了主体的价值判断,又体现了其能动创构。与日常取譬明理的意象(如易象)相比,审美的意象始终不脱离感性形象,在感性形态中呈现其精神价值。其中物象和事象中丰富的象征性,常常取决于它在人文传统中作为文化原型所承载的意蕴。
二、意象与形象的关系
我们把意象作为一个普遍的审美范畴来使用,必然涉及到意象和形象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既有形象这一概念,又有意象这一概念,并且在文学艺术批评中都有运用。作为非审美意义的词,“形象”一词在《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等书中均有出现,而作为艺术用语,则有《世说新语·巧艺》:“荀极善画,乃潜往画钟门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状貌如平生。”[注](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堮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5-386页。《魏书·释老志》:“乃造其形象泥人。”[注](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34页。这里指的是佛像。后来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所谓“圣贤形象”、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所谓“形象生动”等,主要是指作品中的感性形态,而且主要是指人物,但是并没有“意象”一词用得普遍。所以后来在20世纪的文艺理论著作中,用形象翻译“Image”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而朱光潜等人也曾把它译为“意象”,而译为“形象”曾经更为流行。在当代中国文学和艺术研究的语境里,“形象”一词已经被约定俗成地普遍使用了,似乎意象更侧重于自然景色,象征性物象,而形象则更多地用来指称叙事作品中的人物。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和艺术批评中,对“形象”和“意象”的使用确实也存在着偏重,当然有时候也有混用的情形。例如评论小说、戏曲和绘画等艺术中的人物,更多地用“形象”一词,而诗、词、文和书法等艺术批评中更多地使用“意象”一词。“形象”中的“形”和“象”,都是指客观因素,是同义语素构成双音合成词,意义偏在客观的外在物象或事象,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客观物象和人物,也被称为“形象”。而“意象”中的“意”则指主观因素,“象”则指客观因素,则是由两个主客相对的语素合构成双音合成词。从学科的角度,我们有必要将两者统一起来。从审美的角度讲,作为同一类的审美现象,我们也有必要将二者统一起来。而且事实上,即使是小说、戏曲和绘画等艺术中的形象,也是离不开主体的情意和创造性体悟的。刘勰写《文心雕龙》运用“意象”这个概念时,应当涵盖了文学的全体。他并没有说意象只能用来评价抒情诗歌,而不能用来评价《诗经·国风·卫风·氓》《孔雀东南飞》这样的叙事作品。葛应秋《制义文笺》说:“有象而无意,谓之傀儡形,似象非其象也。”[注](明)葛应秋:《石丈斋集》(卷3),《四库未收辑刊》(第6辑,第2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诗歌如此,小说、戏曲亦然。因此,我认为,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和审美的事实出发,意象概念和形象概念的使用,应该统一到意象中来。
意象范畴能否取代过去用来分析小说和戏剧的“形象”,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否表情达意?二、艺术家是否在创造性审美体验中激发了想象力?并且激发了欣赏者的想象力?三、是否有背景构成具体的情境?叙事作品中提供的人物及其活动的场景,包括物象和事象及其背景。文学与纪实文字的区别,绘画与解剖图的区别,就在于其中是否包含主观的情意和想象力,是否体现了以情感为中心的综合心理功能。
事实上,人物形象和事象,作为外在感悟对象与自然景色具有相类似的特点和意义。自然景色可以作为创构意象的基础,人物形象和事象同样可以作为创构意象的基础。展示人物及其活动的叙事作品,也属于具有感性特征的特殊意识形态,同样体现着主观的情意。所谓的人物形象,都不是对物象的照相式的反映,而是人心营构之象,包含着艺术家的主观情意、伴随着艺术家的想象力,而且这些人物都是通过具体事象实现对人物的传神表达的。因此,艺术作品中的人物,不同于简单的人物照片,就在于它包含着艺术家的主观情意和审美理想。从这一点说,用“形象”翻译及其所指的人物,依然属于意象,即主观情意与感性物象的有机交融。通常所谓事象,乃是由人物活动所形成的事件。其中作品中人物内在的形神关系,主体所倾注的情意和理想,都使得作品中的人物体现了意象特征。
在叙事作品中,对人物的摹写和刻画,强调逼真,强调形貌、气质、性情,让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同时又如镜中取影,以神来之笔状貌,传神写照,传达人物内在的神气。小说和戏曲通过生花的妙笔,展示人物的不同性格,并且在追求神似的基础上,同样需要传情达意,需要在笔墨之外,呈现出作者自己的喜怒哀乐。中国古代小说评点重视人物内在的情理,也说明,所谓的人物形象,乃是意象。如张竹坡《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四十三:“做文章不过情理二字。”[注](清)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第43则),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7页。《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一回眉批:“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注](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脂砚斋评,邓遂夫校订,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第100页。《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二回眉批:“至情之理之妙文。”[注](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脂砚斋评,邓遂夫校订,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第100页。皆指作品通过形象传达情理。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少康、胡经之等人都有将形象与意象归为一体的倾向。只不过张少康先生和胡经之先生囿于约定俗成的习惯,未能更明晰地推重意象概念的价值和意义。张少康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一书的第二章《论艺术形象》中曾说:“我国古代的艺术创作理论中,称客观现实的形象为‘物象’,而称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形象为‘意象’。”“如我国古代戏曲、小说理论中所说的‘世情’、‘物态’、‘物象’经过艺术家心灵的改造,被艺术地反映到文艺作品中即是‘意象’。”“我国古代用‘意象’而不用别的概念来说明艺术形象,正是为了强调艺术形象既有主观的‘意’,又有客观的‘象’,它既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是两者的结合。”[注]张少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第54页,第63页。这是在说明,传入中国的外国理论中所言的艺术形象,正是中国古代的“意象”范畴。张少康先生还多次使用“艺术形象(意象)”这样的表述,说明艺术形象等于意象。胡经之在《文艺美学》中把意象分为审美意象和非审美意象,第七章的标题就叫“艺术形象:审美意象及其符号化”。他认为:“只有当意象是审美的,并且审美意象得到物质表现,才成为艺术形象。”[注]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在这里,他试图把意象统一到形象上来,也是尊重20世纪80年代当时约定俗成的观念。他在该章的三、四、五这三节里,分别讨论了“审美意象的特性”“审美意象的结构方式”和“审美意象的符号化”。从整个行文中,可看出胡经之先生的表述方式也还在探索之中。
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夏之放则直截了当地表明了用意象取代形象的立场。他在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文学意象论》一书中,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以“形象”作为标示文学艺术特征的中心范畴和建构文艺学美学理论体系的起点,实践证明,这不利于揭示文学艺术特有的规律。夏之放认为:“‘形象’一词仅仅指的是客观事物的形状象貌;‘艺术形象’也就变成了作品中具体可感的人、事、物形状象貌,而忽视了作家艺术家的主体的态度和情感。”“人们从‘形象’或‘艺术形象’这两个术语上面所能理解到的总是客体方面,而无法体会到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态度。”[注]夏之放:《文学意象论》,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2页。他主张应当从中国传统美学中选取“意象”范畴,作为标示文学艺术特征的中心概念和逻辑起点。
三、意象中的主体问题
简圣宇在论文中提到了意象中的主体问题,他把主体分为“意象的创造者”和“意象的接受者”两类,并从这个角度对我提出批评。看起来他对我的“意象中的主体”的基本思想不够了解,所以会从这两个方面对我的论述进行肢解。我先后在数篇论文中强调,意象中包含着感悟、判断和创造的统一。审美即创造,意象是在审美活动中创造的。意象创构的过程,是主体通过直观体悟,进行判断,诱发想象,满足创造欲,力求自我实现的过程。意象由心与物象交融创构而成,体现着主体生命的创造精神。因此,在审美活动中,意象的创造和欣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意象的创构以感悟为基础,首先是主体通过视听感官对物象、事象及其背景的感知。这种感知就是郑板桥所谓的“眼中之竹”,由物象、事象及其背景激发主体的情意,通过妙悟拨动着主体的心弦,使情景融为一体,并借助于想象力而创构成“胸中之竹”,即竹的意象。主体感物而动情,激发起灵感和想象,进入到情景交融、豁然贯通的领悟状态。在审美的体验里,物我是双向交流的。主体通过物态人情化、人情物态化的审美的思维方式,感同身受,对物象、事象作同情的体验。王昌龄所谓“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注][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93页。,说的便是这种物我感通的情形。
主体在瞬间的意象创构之中,还包含着主体对物象、事象及其背景的审美判断。这是一种从感官到心灵的体验与感受,一种基于主体情意的评价。其中既具有普遍有效性,又体现了个体的独特情怀。这种判断以感悟为基础,以长期审美经验积累所丰富完善起来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作为尺度,在情感体验中对物象、事象及其背景进行审美价值的判断。在特定的民族和社群里,这种审美判断还常常体现了社会历史因素。例如中国人体悟松、竹、梅、兰意象,乃至在明月、流水和明月意象的创构中都包含着社会历史因素,它们渗透在中国人的审美判断和意象创构中。
在意象的瞬间创构中,主体在感悟、判断的同时,通过想象力实现了意象的创构。在审美活动中,物象、事象及其背景激发着主体的想象力,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乃至“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注]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8页。,超越了现实时空的限制,创构出独特的意象来。刘勰把想象称为“神思”,是在虚静心态的基础上,基于眼前现实的物象、事象及其背景,又超越于它们,激发思绪,“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注](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神思飞扬,调动起以往的审美经验,在主体情意的驱动下,超越身观的局限和现实的时空,纵横驰骋,心驰象外,让心绪自由地翱翔,形成虚实相生的意象,乃至游心于物之初,进入体道境界。顾恺之有所谓“迁想妙得”[注](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02页。,也是在说通过想象使象虚实相生,进一步传达出象的内在神韵。因此,审美活动中的意象创构,乃是主体受到物象、事象及其背景的触发,进行超越现实时空的想象,使既有的物象、事象及其背景丰满传神,也使得虚实相生的象与主体的情意融为一体,由妙悟而神合。可见,在审美活动中,意象创构中的感悟、判断和想象创造是浑然一体的。
只是在艺术意象(即艺象)中,才会有意象的创造和意象的欣赏问题,主体才有创造主体和欣赏主体的差异。艺象是对艺术家心目中所创构的意象的构思与传达。而所谓意象的欣赏,一般是指欣赏者对艺象的接受,也是一种再创造。艺术家的艺象创造,为欣赏者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同时也限制了欣赏者的想象。艺术家为欣赏者提供了意象,对欣赏者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也对欣赏者的再创造作了一定的限制。对于艺象而言,每个人首先是欣赏者,每个艺术家在创造艺象之前,都有着丰富的欣赏艺象的经验,欣赏是艺象创造的基础。每个人都可以审美,每个人都可以创构意象,但是艺象的创构和传达,则需要天才。
艺术家心中的意象就是审美活动的成果,传达到作品中,则经过了艺术家的构思和传达媒介与技巧的运用,以线条、色彩,声音,或文字符码对心象进行传达,是一种物态化,成为艺术作品中的意象,即“艺象”。这就是郑板桥所谓的“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胸中之竹”即意象,“手中之竹”是对意象的艺术传达,即艺象。文学作品用文字加以传达,文字不像绘画那样以线条、色彩构成图像进行传达,但是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文字,而是文字作为符码所传达的意象,欣赏者通过作为符码的文字对作为艺术家心象进行还原,这就像以往电报使用的数字对应意义一样。我们不能说那些数字只是数字本身,不是意义。当然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意义的传达,而是丰富的意象的创造性表达,语言本身如同意象的肌肤,本身就充满着审美的意味。欣赏者也不只是简单地、被动地接受,而是对意象的一种再创造。
人们在欣赏艺术意象时,艺术品作为特殊的审美对象,与自然等其他对象比,在体验内容和体验视角等方面,受到艺术家创造的艺术意象的主导和限制。艺术家在审美欣赏方面和构思传达方面,都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天赋。艺术活动不仅仅是对意象的传达,它对表达内容的驾驭,对传达媒介选择与征服,以及构思和取舍等等都体现了创造精神。艺术家对“意”对“象”都做了选择,优秀的艺象给欣赏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欣赏者在欣赏艺象的时候,对作品中的意象创造性地加以体验,在艺术家体验创造的基础上进行了能动的重构,即第二次创构。每一次艺术欣赏,都是一次意象的再创造,一次意象的重构。欣赏者在心领神会中,进行别具匠心的独创。美就生成于每一次体验的意象创构过程中。例如马致远的《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一方面通过拟象把我们感觉和思绪限定在枯寂萧瑟的秋色中,引发我们与浪迹天涯游子类似的共鸣,另一方面,也依然会激发我们独特的体验和联想,是作者审美意象创构的一种再体验。
四、意象与意境的关系
简圣宇教授还批评了我关于意象和意境关系的论述。他认为:“意象的时空观需在意境范畴下深入探究。”我认为,意境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是指体现在意象之中的境界。我们绝不能望文生义,将意与境两个词分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意与境的关系。审美活动必须创构意象,但并非所有的意象或意象群的整体被称为有意境,优秀的意象和意象群所构成的整体才能体现意境,这是一种高格调。意象作为美的本体,本身是时空合一的,意境的时空特征乃是基于时空合一的意象本体。因此,意境和意象不存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差异,有意境的意象通过主体的能动体悟,可以更有力地拓展时空。意境依托于由情景交融所构成的生机勃勃的意象整体,象中寓意,以象构境,是寓于意象中的特质和气质,更重视物象、事象与其背景合一的整体。独体意象如齐白石的单只虾与其背景所构成整体,也可以构成意境。
“境”和“境界”在中国虽然古已有之,但在当时的语境中,主要指疆土范围,是空间的疆域和界限,然后再到精神层次和程度的差别。“境”和“境界”用来指精神层次,乃是受到了佛经翻译的影响。佛学思想对审美的心境和心灵层次的反思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佛学中所言的境界,乃是觉悟的境界。诗歌的意境、境界,是通过感官和心灵体悟物象达成的,是以意象为基础的。意境是意象之境,意境之中包含着意与象的交融。意境的层次是奠定在意象本体的基础上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意象都构成了意境。有意境的意象,乃是对意象的层次和境界的评价。意境堪称意象中更高乃至最高的境界和层次。当我们说某个艺术作品有意境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很高的评价,而不是指一般的意象。意境主要指审美活动中象与象、象与背景构成的整体风貌所呈现的效果。意象和意境的差别是主体看待美的角度、方向的差别。
意境体现在意象本体中,意象是意境的基础。意境是意象的境界,通过意象的感性形态呈现。意境必须依托于意象而存在。意境存在于意象之中,犹如魂在体中。没有离开意象而独立存在的意境,意境是奠定在具体意象的基础上的。外在物象、事象及其背景,是主体创构意象形成意境的前提,但主体的心境格调,是形成意境的关键。王昌龄《诗格》云:“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象,如击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注]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版,第162页。王昌龄认为诗人当以心击物,对“象”的“了然”,具有穿透性,从而达到一种澄澈的境界。皎然《诗式》所谓“取境”,是指主体由眼及心的对物象的判断与取舍。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所谓“思与境偕”,这里的“境”是指物境,是主体的一种感悟和判断,主体在心境与物境或事境的统一中,体现了想象力的创构。
从意境的角度看,有物境,有事境,有心境。物境乃物象之境,事境乃事象之境,实际上也是主观的感受与体验。王昌龄《诗格》:“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注]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版,第173页。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注]罗仲鼎:《艺苑卮言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版,第40页。袁宏道《叙小修诗》也说:“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这里的境,是指物境,其中包含了物象在心灵中构成具体境界的潜质,源自主体的一种精神价值判断,说明物象在主体的判断中具体表现为格调和层次。但无论意象还是意境,其中意由心出,都指向心。意境和意象都是主体在心中成就的,但意象作为心象不是虚无缥缈的,不可琢磨的,而是具体感性形象在心中的反映。意境、意象都提到了意,但是其中都是以象为感性形态的。造化本无为,无所谓境界的追求。大千世界的所谓物境、事境,乃是主体感悟的结果。意境的概念更侧重于主体的角度,主体透过外在物象、事象,在感悟、判断和创构的统一中成就物我统一的境界。意境中体现了情景交融、物境与心境的统一。心境本无形,乃依物象、事象而现形,意境是在心物统一的意象的基础上,体现了物境与心境的统一。情景交融的意象中包含着哲理的情思,进入到体道的境界,从中便呈现了意境。
意境作为审美境界的层次,尤其体现在由意象所构成的艺术作品中,体现在艺象的创造和欣赏之中。艺术意境中包含着主体的层次、格调和境界,这主体包括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而匠心独运的传达效果也影响着艺术意境的呈现。艺术中的意境的创造和欣赏,体现了创造者和欣赏者的精神层次。在艺术作品中,意境的层次体现了创作主体的素质和格调,并非所有艺术都有意境。创构艺象的虚实相生、动静相成,以及象征、比喻等手法的运用,有助于将艺术传达发挥到极致,从而有利于境界的生成。在艺术欣赏中,欣赏者以创作者创造的艺象为欣赏对象,在心中再创造出意象,从艺象整体效果中体悟到意境,这意境乃是由艺象中所体现的格调和胸襟与欣赏者的格调与胸襟共同决定的。欣赏虽然是一种对意象和意境的再创造,但是说到底,欣赏毕竟是一种“来料加工”。没有意境基础和潜质的艺术作品,欣赏者要想从中体悟到意境,只能是一种“缘木求鱼”。欣赏者要从有意境的作品中体悟意境,该作品当契合于欣赏者的心境,才有可能。主体要先有高格调,然后才可能体验高格调,并不是所有的欣赏者都可以领悟意境。
意境不仅寓于艺术作品的意象之中,而且寓于所有的审美活动所创构的意象之中,那些彷佛出自造化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色,如作为山水楷模、情趣渊薮的桂林,充满诗情画意、美若仙境的九寨沟等,都可以被视为有成就意境的基础,在鬼斧神工的自然物态中体现了精神的价值和层次,因而它们作为物象,有生成高远境界的基础或潜质,因而可以视为是物境。主体在感悟物象或事象时,透过感性的象,由“见”(或“听”)而识,由感而悟,悟到境界。见(或听)以外象为基础,“识”以感悟为基础,是审美理想、审美能力的体现,也是主体心灵层次的体现。衡量意象的境界层次,即意境,既要考虑到物象、事象及其背景自身的特质,更反映了审美活动主体心灵的境界层次和修养。因此,意境更侧重于其中的精神层次,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的评价。
意象以其无穷的意蕴构成了境界,即意境。在意境中,境由象生,境不离象,同时又超然于象之外而呈现出高远的境界。意境究其根本既寓于意象之中,又超然于意象之表,也是一种基于意象的虚实相生。意象和意境在创构时,所体现出的超越性特征,不仅是对现实物象的超越,同样也是对主体意识的自我超越。审美活动中所创构的意象的整体的境界,不拘于意象本身,而是通过虚实相生和动静相成而拓展时空,所以有“境生于象外”的说法。同时,境界不仅是一种体验,更是一种追求,体现了主体的眼界和格局。我们通常用深远、宏阔、博大等词来形容意境,而对深远等意境的体悟,主体的眼界和胸襟起着重要作用。主体觉悟的层次,决定了心灵的层次,也决定了意境的层次。
正是由于意境依托于意象整体,意境与意象之间具有一体性和相关性的特点,才使得不少学者在论述意象和意境时,常常将两者相混淆。简圣宇则强调两者的区别,乃至认为意境比意象更重要,意境高于意象。对于我认为意象是美的本体,是意境的基础,简圣宇则批评我“对意境的重视程度要低于意象”,“有些轻视意境本身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性了”,乃至认为中国古代对意境都重视得不够,“关于意境对审美时空结构的重塑,今日有必要立足于现代美学语境加以整理和阐释”。实际上,对于意象、意境的含义及其两者的关系,中国古代有自己的阐释,简圣宇可以对它们不满意,可以站在现代性立场上对古代意象、意境的含义加以开拓和阐释,但是不能因为古代的这些思想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就根据自己的想法去以今律古,而不顾及和尊重古代先哲们的原意。
五、意象范畴的现代价值
简圣宇在论文的后三个部分,专门提出了中国古代意象理论的适用范围问题,即意象理论能否解释现代艺术,能否实现现代转换,以及意象理论是否可以作为中国经验,弥补西方美学理论的不足,实现与西方美学的互补等。此前韩伟教授曾经也有过类似的意见。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许多概念范畴,从古代一直用到今天,这些概念范畴为什么能沿用到今天?什么样的概念范畴是有生命力的?意象论能不能用来解释当下的问题?我们需要在切实深入探求中国传统意象范畴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厘清中西差异,在现代视野中加以拓展和深化发展。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这里先简单回应,以后我还将撰写专文论述。
审美意象的当代阐释问题并不是今天才被提出的。从近代以来,特别是王国维、朱光潜、叶朗和汪裕雄以及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当代学者,一直谋求从现代性视角去阐释意象。意象确实需要在现代性视野下,超越其古董价值,进行现代拓展,使其在当下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发挥反思和指导功能。在当下中西美学思想多元并存、尤其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语境中,不少人认为“意象论”思想已经过时,它只能用来解释中国古代的诗词,而不能用来解释其他文学类型和艺术类型,更不能解释当下的审美现象和艺术现象。简圣宇就认为意象不合适解释现代艺术,如嘻哈艺术、涂鸦艺术、跨媒介的数字艺术等。
实际上,意象并非只能适用于中国古代诗词,各类艺术作品都离不开具体的物象和事象,离不开对主观情意的表达。不同的艺术作品在时空呈现方式、构思技巧、语言形式上有差异,但在个性和情意的表达上,都必须通过意象呈现。当下所谓的图像研究,都离不开“象”,离不开整体构思和符号运用,离不开自由的形式。现代艺术不管在符号形式和传达手法上有多大的变化,立象尽意则是不变的。
从逻辑上讲,从古到今的审美现象和艺术现象,有变的一面和不变的一面,很多西方的美学术语,从古代一直沿用到今天,依然有着生命力。中外文学和艺术从古到今是不断变化的,但是之所以今天还称其为诗歌、绘画、音乐,说明它们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其中的审美特征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意象作为审美活动的成果,作为评价文学艺术根本特征的范畴,不仅适用于对古代文学艺术的评价,而且适用于对现代艺术的评价。各民族、各地域的艺术特征,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全新创造,现代艺术中依然包含着一定的传统艺术元素,艺术家也常常从传统艺术中汲取营养。这至少证明,中国古代意象范畴迄今依然有着生命力,依然可以用来评价当下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
不仅仅文学艺术现象,整个审美活动,都有其不变的一面。意象在创构过程中“进取诸身,远取诸物”,这个“身”与“物”作为取类联想的“象”具有普遍性。千年前的人与今天的人在形体上差别不大,古今中外的春花秋月、山川湖海也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意象所取之物象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意象论当然也能进行处理。而发生了变化的事象及其背景,从根本上来说,也在意象论的范围之内。
审美意义上的意象理论从出现开始,就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开放的、不断丰富发展的。意象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和文学理论范畴,从《文心雕龙》开始使用,到唐宋时代不断得以阐释,其适用范围也逐渐扩大到对近体诗、戏曲、绘画和书法等的评价和研究中,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意象思想既然在中国古代曾经是与时俱进的,在审美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那么它现在依然有着生命力,依然会在当下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与时俱进。我们不能认定它已经死亡了,在古代就已经寿终正寝了。因此,既然意象这一概念在古代的适用范围在不断扩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继续扩大它的运用范围,运用它来评价现代艺术。
简圣宇认为,当下“田园牧歌生活被机械化大生产毫不留情地撕裂,社会整体物质条件提高的同时又产生了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个人的渺小在这种背景下格外突出。”所以,“以‘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为特征的古典艺术无法应对”这种语境的转变。而我认为,恰恰相反,意象论与一些西方现代相关学说有相契合的一面,这是意象范畴现代性阐释的基础。其中的物我为一、情景交融的主客观统一思想内涵,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现代美学尤其是现象学的方法克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合拍的,因而它也具有现代性因子。如果说西学在寻求克服异化的道路,意象的现代性探索同样在探求本体生命的本真显现。可以说,意象理论不但可以处理异化问题,甚至能够给异化问题寻找一条审美的出路。在处理与西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将中国古代的意象理论放到中西美学的大背景中去领会,激活意象理论中有价值的成分,可以进一步深切地体会到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西方现代的文学和艺术,在象征和表意的追求上,也与中国传统的意象理论有着相似和相通的一面。英美意象派对诗歌意象的借鉴和创作,以及理论探讨,不仅在现代视野、而且在异域,在探索其普遍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意象自身的贴切性,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范畴,我们不能仅仅用它作为西方美学理论的注脚。我们需要激发意象本身的内在活力,尤其要避免以古人意象理论的片言只语包装西方的理论,从而把西方的理论混同于中国古代的意象理论。现代审美和艺术批评中的意象范畴的运用,鱼龙混杂,有的是西方的Image,有的是使用者自己所赋予的含义,也有许多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意象范畴的含义。中国现代用来翻译西方相关词汇的意象,与中国传统的意象含义是有区别的。朱光潜用“审美意象”翻译康德的“Asthetiche Idee”,又并非中国传统的意象美学思想。中国传统的意象理论与西方的意象观念之间,既有相同点,又是有着一定的差异的。在中西融合碰撞中,如何使中国传统的意象资源具有现代价值,是当下美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总之,中国传统的意象理论,有其特定的含义,有其特定的贡献。我们对它的阐释和激活,应当基于其基本含义,立足于中国古代传统加以阐释,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它进行任意整容和改造,以期把它变成自由表达主观意旨的工具。任何过度阐释或牵强附会都不利于激活意象本身。作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核心理论,意象理论需要返本开新。我们应当认识到意象理论具有现代阐释的基础,对于它的价值我们应当加以重视和发扬光大,为未来多元统一世界美学的建构奠定基础。在当代美学建设中,借鉴、继承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否定意象是错误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我们不应当再抱守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以西方思想来作为评判中国传统思想是非的唯一尺度。我们既不能固守和拘泥于古代意象理论的思想资源,让它们只具有博物馆意义,又不能简单地把所接受到的意象理论,用中国古代的文献包装起来,把它们说成是只属于中国古代的理论。当然,意象的现代性问题,不只是我们从逻辑上加以阐发和论证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我相信,意象范畴在当下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将继续得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