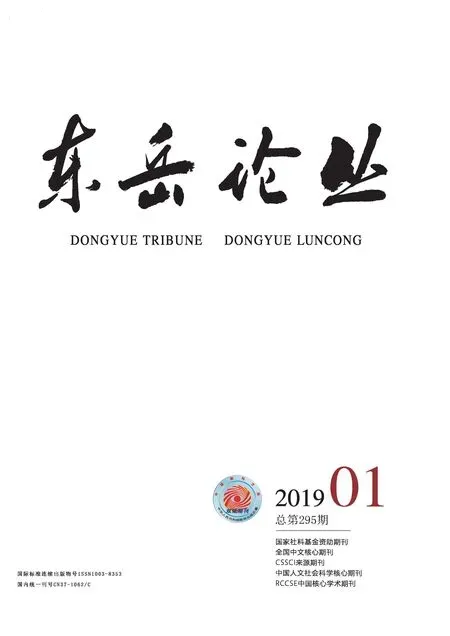郭沫若《庄子批判》之批判
周泉根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00)
一、导论:郭沫若一生的庄子情结
郭沬若很早就读《庄子》,《十批判书·后记》(以下简称《后记》)中说:“《庄子》书是我从小时候便爱读的一种,至今都还有好几篇文字我能够暗诵……起初是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注]其在《少年时代》中也说“特别喜欢《庄子》”。郭沫若:《少年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9页。早年在成都求学就读了章太炎的《齐物论释》,只是觉得章氏“用佛学来解《庄子》,觉得比《庄子》的原文还要莫名其妙”[注]《郭沬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为行文简括,以下郭氏文章凡出自《全集》者,皆只在文中夹注篇名。有互校之本,则说明于正文。(《我的学生时代》)。第一次留日期间(1913-1923)拟作《庄周评论》,因兄长郭开文反对而作罢。1918年开始,与成仿吾、郁达夫和张资平等同仁之间开始桴鼓相应,斯为浪漫主义倾向浓重的“创造社的受胎期”。1921年写了先秦文史研究第一篇文章《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其纵横恣肆的文风已露端倪。这些声息都可通乎庄子。1923年写了取材老庄的小说《柱下史入关》和《漆园吏游梁》。
这期间,泛神论思想极大地鼓荡着他,而这离不开庄学精神的援引,他说:
“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书,如象他的《伦理学》《论神学与政治》《理智之世界改造》等,我直接间接地读了不少。和国外的泛神论思想一接近,便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了。我在中学的时候便喜欢读《庄子》,但只喜欢文章的汪洋恣肆,那里面所包含的思想,是很茫昧的。待到一和国外的思想参证起来,便真是到了‘一旦豁然而贯通’的程度。”(《创造十年》)
“我在思想上是倾向着泛神论的,在少年时所爱读的《庄子》里面发现出了洞辟一切的光辉。”(《我的作诗经过》)
又曾用郭氏典型的浪漫外溢语气说:
“我爱我国的庄子,我爱荷兰的斯宾诺莎,我爱印度的加皮尔,我爱他们的泛神论。”(《三个泛神论者》)
“我有过一个时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那是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的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的时期。那时我因为沾染了泛神论思想,崇拜着斯宾诺莎、歌德,耽读泰戈尔的诗。在中国古人中则崇拜着庄子和王阳明。”(《创造十年续篇》)
到1942年,他依然充分肯定庄子对中国文艺的影响,他说“应该读《庄子》的”,“庄子固然是中国有数的哲学家,但也是中国有数的文艺家,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拔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他的书中有无数的寓言和故事,那文学价值是超过它的哲学价值的。中国自秦以来的主要的文学家,差不多没有不受庄子的影响,就是鲁迅也是深受庄子影响的一个人,除他自己曾经表白之外,我们在他的行文和构思上都可以发现出不少的证据”。(《关于“接受文学遗产”》)其实,与其说鲁迅,不如说是郭氏借鲁迅来夫子自道。郭氏文章,即使学术研究类,都能令人感受到那种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的气质。至于诗集《女神》和剧作《屈原》,其浪漫主义、激情洋溢的风格,更不待言,其精神皆可标心千载之上与庄子遥相呼应。即使后来在《李白与杜甫》(1971)褒李贬杜多为后学诛心,然与郭氏偏至浪漫主义也不无关系。这一点郭氏曾多次自证过,其在《后记》中就说:
“我和周秦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最先接近的是《庄子》,起初是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这嗜好支配了我一个相当长远的时期,我在二十年前曾经讴歌过泛神论,事实上就是从这儿滥觞出来的。”
郭氏之泛神论、郭氏与道家等问题,海内外已有很多学者论及,如蔡震、李向阳、张顺发、吴定宇等[注]如:张学植:《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张牛:《郭沫若早期如何受庄子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5期;李向阳:《郭沫若与庄子的思想渊源关系》,《郭沫若学刊》,1988年第1期;王世德:《郭沫若从泛神论到新浪漫主义》,《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佀同壮:《郭沫若对庄子美学的新开拓》,《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张顺发:《庄子与郭沫若》,《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1期;吴定宇:《自然与逍遥——郭沫若与道家文化》,《郭沫若学刊》,1998年第2期;蔡震:《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与我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郭沫若研究》(第2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等等。,兹不赘言。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郭沫若对庄学思想进行了清算,如在1965年写的《〈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中说:“魏晋地主阶级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之好玄谈、尚旷达,确实是依仿于老庄。”“泛神论的作用,它不仅可用以麻痹斗争,而且还可用以陶醉自己,说穿了不外是更巧妙的一个阶级骗局。”虽则,郭氏的庄学气质并未转移。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刘剑梅对郭沫若一生的庄子情结做过分期式总结,颇可参考[注]刘剑梅:《郭沫若对庄子态度的变迁》,《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在抗战时期的后方著作的《十批判书》(以下简称“《十批》”)中有《庄子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一章,文中重申并分析了老庄的自由浪漫精神:“道家特别尊重个性,强调个人的自由到了狂放的地步。”《十批》是学术著作,是郭氏对先秦诸子的一次总结性研究,自己非常看重。出版之初即受到极大关注[注]如齐思和在《燕京日报》(1946年6月版第30期),朱自清在《大公报(天津)》(1947年1月4日)都撰文评议,丁山在《东南日报·文史(上海)》(1947年4月9日)写了《十批判之批判(上下)》等。,也引来持续至今的各种评价。但专注研究《庄子批判》的则较少。杨海文曾就其中的一条自注,细细对勘过《庄子批判》各种版本,并从思想史的角度指出“庄子即儒家”并非八卦、设题诠释恰恰能丰富思想史本身[注]杨海文:《庄子本颜氏之儒:郭沫若“自注”的思想史真相》,《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下引杨氏之说,如无特别注明,皆出自此篇,不另出注。。我们不妨接着杨海文先生的话,继续往下说,就《十批判书》之“庄子批判”一节,略作梳理,有几条事实几点意见,供大家指正评议,重点探讨一下与《庄子批判》相关的儒道通变、新学学风和我们之于学术史的态度等等问题。今所谓“批判之批判”,乃取郭氏研究之原意。
二、《庄子批判》的自注与渊源
郭氏高材捷足,著论多旬月即成。据《后记》,《庄子批判》在重庆更是止用五六日便写就。时间是1944年9月21日至26日。当然这篇也是十批判中篇幅最短的一篇。他自己说写起来“相当吃力”。这个吃力固然有难以厘清《庄子》材料在庄子与后学之间的分属情况的原因,但也未尝不是感慨五六天写出来的最短这一篇新意不够。也许正因如此,原本想续写的郭先生最终发现到底“无甚新意”,略有想法处也“终觉勉强”,只好“把它抛弃了”(《后记》)。既已成篇的核心观点暨通篇基础之论——“庄子出自孔门颜氏之儒”,也是完全袭自章太炎。这也是郭氏亲自揭陈的。重庆群益出版社于1945年9月出版的《十批判书》,郭氏在“我怀疑他本是‘颜氏之儒’”一句下加注曰:
“章太炎曾有此说,似于坊间所传《章太炎先生白话文》一书中见之。”
前此初版于成都的《大学月刊》(分刊于1945年第4卷3月的第1、2期合刊本和6月的第3期)并无此注,此后1954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时,“似于”又修订明确为“曾于”。杨海文曾就这条自注的前后有无和细微差别做过分析。通观杨先生的分析,大致情形应该是这样的:郭氏先于《儒家八派的批判》中认为庄子“心斋”“坐忘”说乃引自颜氏后学之“重言”,后在《庄子批判》中进一步怀疑“庄子本颜氏之儒”,行文到最后几乎认定此说,十批判开始一笔下来,未做呼应,待重新结集时检讨发现有章氏之影响,故不敢掠美,又战乱无书,注以“似于”,十年后再修订明确为“曾于”。这一解释,我以为大致同情而合理,但还有一些可深入对勘分析的地方。总得来说,郭氏这一观点,话里话外可见其在到底是阅读章氏时留下草蛇灰线的旧启发,抑或切入儒家八派批判时自己的新体悟之间颇难取舍。只因该说乃《庄子批判》核心观点,毕竟章氏在前,且后者曾明确参阅,“吃力”之说,盖由乎此:难有新意。杨海文曾从庄子与颜子、与孔子、与儒道三方面细细比对章郭二氏之说,从观点到遣词几于如出一辙。杨还指出,《章太炎先生白话文》一文并不存在,故推想应该是章氏某白话文写就之文章。考诸章氏晚年著述,讲“庄子即儒家”主要见于:其一,1922年讲演并出版的《国学概论·哲学之派别》;其二,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的《菿汉昌言·经言一》;其三,1935年讲演并发表的《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三种文献只有《国学概论》为白话,郭氏记忆及自注,杨海文认为当是指其中《哲学之派别》那篇。
这条越描越清晰的自注,表现了郭氏为学的诚实。郭氏基本全袭其意。除了杨海文在文章从三个方面对勘章郭之同外,还有如,章氏重申神仙家、道士与老庄无关:
“道士以登仙为极则,而庄子有齐死生之说,又忘老聃之死,正与道士不死之说相反也。汉武帝信少翁、栾大、李少君之属以求神仙,当时尚未牵合神仙、老子为一。《汉书·艺文志》以神仙、医经、经方同入方技,可证也。汉末张道陵注《老子》(《宏明集》引),其孙鲁亦注《老子》(曰:想余注《老子》。想余二字不可解),以老子牵入彼教,殆自此始。后世道士,乃张道陵一派也。”(《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注]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页。
对勘可知,郭氏也用了不少文字,解说了庄子眼中的“有道之士”“古之博大真人”,被后人盗了去,“他所理想的‘真人’,不一二便成为阴阳方士之流的神仙,连秦始皇帝都盗窃了他的‘真人’徽号”,“齐国的方士们,他们之迷恋神仙真人,也分明承受了庄周的衣钵”。郭氏还感情激愤,就此做了价值批判,指出虽然被神仙道家明抢了去,却并不代表与道家有相同之处,因为“这是聪明的庄子所不曾预料到的”。显然与章氏之道家道教无关说毫无二致。
再如,章氏以为孔氏之门,颜回最高,子贡子路皆从政入世派而已,不得与闻至道,他在前论“尤以心斋一语为精。宋儒亦多以晏坐为务”之后,说道:
“孔子之徒,颜子最高,一生从未服官,无七国游说之风。自子贡开游说之端,子路、冉有皆以从政终其身。于是七国时仕宦游说之士,多以孔子为依归,却不能依傍颜子,故庄子独称之也。”(《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注]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郭氏则说:
“颜回和孔子都是有些出世倾向的人。一位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一位是‘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孔子曾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只有他们两个才能够。这是表明其他的弟子大抵都是入世派了。聪明的子贡曾经叹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但这性与天道之说是子贡得未曾闻,并不是孔子得未曾言。孔子是因材施教的人,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会做生意的子贡何须对他谈性与天道呢!那种有出世意味的东西,假使要找一个对象来谈,那他的颜回便不失为是很好的对象了。于是在《庄子》里面便出现了孔子的‘心斋’和颜回的‘坐忘’之说。”
郭文除了刊落章氏以念兹在兹的佛家义理格义庄老外,其他论调和论证,几无二致。
三如,章氏多处指出道家传儒家、儒家又复传道家之统系:
“道家传于孔子为儒家,孔子传颜回,再传至庄子,又入了道家。”(《国学概论·哲学的派别》)[注]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以下所引《哲学的派别》皆在第30-55页,只夹注文中,不再脚注。
郭氏于此亦如是说:
“庄子是从颜氏之儒出来的,但他就和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卒于‘背周道而用夏政’一样(《淮南·要略》),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宗派。”
郭氏不仅通篇袭其意,而且常常径袭其语,如上文郭氏“庄子是从颜氏之儒出来的”,章氏在《菿汉昌言》中说“庄生传颜氏之儒”[注]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菿汉微言、菿汉昌言、菿汉雅言札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
再如,郭氏说:
“《庄子》书中虽然很多地方在菲薄儒家,如像《杂篇》中的《盗跖》《渔父》两篇更在痛骂孔子,但那些都是后学者的呵佛骂祖的游戏文字,而认真称赞儒或孔子的地方,则非常严肃。”
章氏在《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中亦如是说:
“杂篇有孔子见盗跖及渔父事,东坡以为此二篇当删。其实《渔父》篇未为揶揄之言,《盗跖》篇亦有微意在也。七国儒者,皆托孔子之说以糊口,庄子欲骂倒此辈,不得不毁及孔子,此与禅宗呵佛骂祖相似。禅宗虽呵佛骂祖,于本师则无不敬之言。庄子虽揶揄孔子,然不及颜子,其事正同。禅宗所以呵佛骂祖者,各派持论,均有根据,非根据佛即根据祖,如用寻常驳辨,未必有取胜之道,不得已而呵佛骂祖耳。孔子之徒,颜子最高,一生从未服官,无七国游说之风。自子贡开游说之端,子路、冉有皆以从政终其身。于是七国时仕宦游说之士,多以孔子为依归,却不能依傍颜子,故庄子独称之也。东坡生于宋代,已见佛家呵佛骂祖之风,不知何以不明此理,而谓此二篇当删去也。太史公谓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剽剥儒墨。今观《天下》篇开端即反对墨子之道,谓墨子虽能任,奈天下何?则史公之言信矣。惟所谓儒者乃当时之儒,非周公、孔子也。其讥弹孔子者,凡以便取持论,非出本意,犹禅宗之呵佛骂祖耳。”[注]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呵佛骂祖”,虽是庄学史上援庄入儒以调和儒道关系时一以贯之的思维和口实[注]章氏谓苏子不明呵佛骂祖之修辞,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冤枉了东坡。东坡高明地认识到庄子正言若反的修辞,说总体上认为“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只是怀疑《盗跖》《渔夫》等非庄子之文。“正言若反”用于以意逆志,则阐释的边界是很难厘定的。较之苏轼区别对待,章氏一意要将《庄子》三十三篇悉数坐实成庄子之文,反有悖于今人对秦汉古书的常识。章氏且连带回护太史公之“庄子剽剥儒墨”之说,自与太史公一道援庄入儒,这就不免如陈寅恪所说“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了。苏轼说见氏著《庄子祠堂記》(《苏东坡全集》卷三十六),文繁不引。另,以庄子之寓言为呵佛骂祖,明觉浪道盛说得最多。然苏子之后,南宋之朱熹、程大昌,都以各自的方式揭陈这一语言策略。尤以程大昌《明矫》为千年道家学史之圭臬。朱子说见《朱子语类》(卷125),文繁不引。程大昌《明矫》中说:“老氏之绝弃圣智仁义,深知其以者曰:此特矫耳,非其本心也。而古今率多咎之,为其迹与经戾也,然而听言之道,以其事观之,则实理著见,不可诬矣。……以老氏之事言参而求之,则其矫而非实也,亦昭昭矣。至庄子推大其教,又从而广之,曰剖斗折衡而民不争也。此语尤其累老教,而致讥诮者也。然而其中有理焉,又可以自用其说而自明其矫矣。结绳之制,老庄二子皆相与力主,以为己教之尝效乎古者也。然而结绳也者,何自而有也……庄子自伤其矫已甚,而又于篇终自为之明曰:周之辞荒唐而说谬悠也。”(载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大旨》卷下)我一直以为《道德经》总体上是批判的哲学,与孔孟荀的建设的哲学,恰好构成“儒道互补”“绘事后素”之关系,其所谓“大音希声”“大方无隅”之大音大方都是极而言之,是理想,是一种价值,并非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实在,其目的是批判礼乐之声和诸侯扩张,旨归于“希”和“无”的批判。“小国寡民”“结绳记事”等等,亦复如是。今人多把价值论当知识论去研究,必欲实事求是,然攘臂扔之,终无以应矣。南宋程大昌泰之先生曾用矫饰来说明这个道理,指出这是老子的著述策略,并指出庄子漫衍卮言正是矫饰修辞的直接展示。此论最获我心。,但郭文从《渔父》《盗跖》到呵佛骂祖,几乎是据章文檃栝而成。
又且以上所袭之语,皆不出白话之《国学概论》,反出自文言之《菿汉昌言》和《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章太炎随行施教,入室弟子众多,讲述著论都能及时刊布,且广为流传。郭先生虽一而再从“似于”确定为“曾于”,但可能记忆仍有可纠正之处,即,不只是白话文,以上著作皆有参考。
又,据笔者披览所及,亦可能不止杨海文所提三种,在1915至1916年间口述吴承仕笔述整理后出版的《菿汉微言》亦可能有参考。如章氏在《菿汉微言》中有论:
“《记·中庸》曰:‘不诚无物。’诚即佛典所谓根本。”
“《中庸》言诚既为无明痴相而庄子渔父云真者精诚之至也。”[注]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菿汉微言、菿汉昌言、菿汉雅言札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2、43页,第37页。
郭氏《批判》持论可谓仿佛而成:
“庄子后学和思、孟学派接近的倾向,在《杂篇》中颇为显著,屡屡把‘诚’作为本体的意义使用,和思、孟学派的见解完全相同:修胸申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撄(《徐无鬼》)……这无疑是《中庸》和《孟子》七篇的影响。”
孔老颜庄的传承世系,端倪最早也见于《菿汉微言》,中有曰:
“庄子田子方篇,孔子见老聃,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胜义谛,非老子不能言,非孔子不能受,非颜回无与告也。”
又曰:
“颜渊坐忘,所至卓绝。”[注]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菿汉微言、菿汉昌言、菿汉雅言札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2、43页,第37页。
由章氏上溯,还可检讨诸说之滥觞。如道家与道教之别,章氏自己已指出:“司马温公已见及此……神仙家、道家,《隋志》犹不相混。清修《四库》,始混而为一。其实炼丹一派,于古只称神仙家,与道家毫无关系。”[注]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页。
再如庄子本颜氏之儒说,据笔者所见,较早触及此题的有黄宗羲。南雷先生,一则以儒家为正道、以孔孟为正统,对子贡、子张、子夏、庄子皆不入其法眼;又受唐韩子影响,不加辨析因循陈说,以庄子为子夏之徒[注]黄宗羲:“七十子之徒,朝夕相依,各陈孔子之业,则微言岂易绝哉?惟失此举,其后子夏居魏,子张居陈,子贡居齐,漫无统一。阙里散后,诸贤再无丽泽之资。西河之人,疑子夏为夫子,而荀况、庄周、吴起、田子方之徒,皆学于孔子,而自为偏见,惟其无以就正之耳。”卷十四:“子贡多学而识,正坐一一以求证,子夏之徒流而为庄周,其学焉而就其性之所近,未范围于圣人故也。”(《明儒学案》卷二十七)。但另一则,从颜回心斋坐忘之说看庄周却也是始于黄氏:
“嗟乎!庄周不读孔子《鲁论》之书,又安知心斋由于博而后得于约邪?”(《明儒学案》卷五十一)
以庄子非子夏子张等入世派则始于明杨慎。杨慎说庄子是拨子夏子张氏贱儒之乱反于尧舜周孔之正的“翼孔”者。他说:
“庄子愤世嫉邪之论也。人皆谓其非尧舜罪汤武毁孔子,不知庄子矣。庄子未尝非尧舜也。非彼假尧舜之道而流为之哙者也。未尝罪汤武也,罪彼假汤武之道而流为白公者也。未尝毁孔子也,毁彼假孔子之道而流为子夏氏之贱儒子张氏之贱儒者也。故有绝圣弃智之论。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诗礼发冢者矣。诗礼发冢,谈性理而钓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晚世,今犹未殄。使一世之人吞声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庄子而复生于今,其愤世嫉邪之论将不止于此矣。”(杨慎《杨升庵集》卷四十六卷《庄子愤世》)
当然,杨慎有言在彼而意在此,目的似乎在批评当时以诗礼孔孟为口实的伪道学。但升庵以庄子为儒家拨乱反正之关键,南雷将庄子与颜回相关联,却是章太炎批评韩愈庄子本子夏而主张颜氏之儒说提供了基础,即使章氏自我发明,杨黄之论至少称得上颜回说的先声。
以上是为郭氏《庄子批判》诸说之渊源。
三、儒道之间:通变与互补
章郭之间,虽不属于各自“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现象,但也常见于学术史和发明史,即只要循一理路,新见新事往往呼之欲出,而不必就滥觞于何时、破题者何人等问题论高下,如莱布尼茨、牛顿之于微积分,如华莱士、达尔文之于进化论。问题本身的价值才是最值得深入辨析的。
庄出儒门之说,就今天可稽考的资料看,始于韩愈。此后以儒解庄不绝于史,如两宋之王安石王雱父子、苏轼、吕惠卿、楼钥、程大昌、林希逸、黄裳、王云、程俱等,明清之杨慎、沈一贯、觉浪道盛方以智师徒、林云铭、黄宗羲、宣颖、姚鼐、章学诚等。晚近以来,有如王闿运周逸师徒、廖平、刘鸿典、刘文典、刘师培、杨文会、谭嗣同、顾实、阮毓崧、李泰棻等等。以上有泛说儒门者,有明确指陈宗门谱系者。明确宗门又有二:一则始于韩愈的出于子夏田子方之门说,一则起于近代的颜子或后学之门说。除王闿运周逸师徒兼两说之外,主张颜氏说的有章太炎、钟泰、郭沫若、钱穆、童书业等。
泛说儒门如北宋苏子瞻说“庄子盖助孔子者”,明末高僧觉浪道盛说庄子“非老聃之嫡嗣,实尧孔之真孤”,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今人杨伯峻、崔大华、刘长及等仍然泛说庄子与孔门关系莫大。而子夏田子方之说则甚为粗糙,章太炎曾批评自己的浙东前辈学人章学诚浑沦因袭韩愈之说:
“章实斋以庄子为子夏门人,盖袭唐人率尔之辞,未尝订实。以庄生称田子方,遂谓子方是庄子师,斯则《让王》亦举曾、原,而则阳、无鬼、庚桑诸子,名在篇目,将一一皆是庄师矣。”[注]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71页。
笔者也曾仔细推勘过,田子方的师承当以《吕览》为是,乃于齐受学于子贡[注]韩愈关于庄子出子夏之门的说法对后世影响巨大。然而,他的观点却是建立在误读《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阎若璩早就指出田子方、段木干等“受业于子夏之伦”是“承上文子路、子张、澹台子羽、子夏、子贡言”,并未一一对应田子方受业于子夏。《吕氏春秋·当染》则明确说田子方学于子贡,《庄子·田子方》还说他师东郭顺子。战国秦汉时期,东郭氏和田氏绝大多数为齐人,子贡也刚好终于齐。《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又载“田子方从齐之魏”。所以,基本可以肯定田子方乃齐人,而非前人多以为的魏人。其受业于齐,《吕览》说他师子贡,可视为实录,而《庄子·田子方》一文人物年辈多符合历史,其寓言风格虽不可坐实也曾师事东郭子,却与后者可能有交往。从除《庄子》外的所有关于田子方材料看,田子方无疑是正宗儒家思想。“田子方从齐之魏”时已然名家,且曾一度要接济居于卫的子思(《说苑·立节》),所以,虽常与子夏一起见称于魏阙,年辈在师生之比,却并非师生。详细论证,笔者拟另辟篇章。。而“本颜氏说”除庄子反复称道颜氏外,还能就思想义理处细细阐发勾连,足成一家之说。郭氏在《儒家八派的批判》论及见诸《庄子》的颜回论“心斋”“坐忘”时说:
“要说是假托,庄子为什么要把这些比较精粹的见解托之于孔、颜而不托之道家系统的人,或率性假拟一些人名呢?因而我想,这些应该都是‘颜氏之儒’的传习录而在庄子是作为‘重言’把它们采用了的。孔、颜当时不一定便真正说过这样的话,但有过这样的倾向,而被颜氏之儒把它夸大了,这不能说是不可能。”
一笔写到《庄子批判》时,则进一步说“我怀疑他本是‘颜氏之儒’”。到后来就确定不移了:“这种文字必然是出于颜氏之儒的传习录,庄子征引得特别多,不足以考见他的师承渊源吗?”
章氏的老孔颜庄统系说萌蘖于《菿汉微言》,至《菿汉昌言》明确立论说“庄生传颜氏之儒”,又于多有从义理处辅证这一观点。除上文所引之外,又在其他讲论如《诸子略说》中重申:
无我之言,《老子》书中所无,而《庄子》详言之。太史公《孔子世家》:“老子送孔子曰:‘为人臣者毋以有己,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二语看似浅露,实则含义宏深。盖空谈无我,不如指切事状以为言,其意若曰一切无我,固不仅言为人臣、为人子而已。所以举臣与子者,就事说理,《华严》所谓事理无碍矣。于是孔子退而有犹龙之叹。夫唯圣人为能知圣,孔子耳顺心通,故闻一即能知十,其后发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论,颜回得之而克己。此如禅宗之传授心法,不待繁词,但用片言只语,而明者自喻。然非孔子之聪明睿智,老子亦何从语之哉(老子语孔子之言,《礼记·曾子问》载三条,皆礼之粗迹,其最要者在此。至无我、克己之语,则《庄子》多有之)![注]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第206-207页。
后文又说到:
庄子自言与老聃之道术不同,“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此老子所不谈,而庄子闻其风而悦之。盖庄子有近乎佛家轮回之说,而老子无之。……然庄子所以好言不死不生,以彭祖、殇子等量齐观者,殆亦有故。《庄子》书中,自老子而外,最推重颜子,于孔子尚有微辞,于颜子则从无贬语。颜子之道,去老子不远,而不幸短命,是以庄子不信卫生而有一死生、齐彭殇之说也。”[注]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第206-207页。
庄自儒门足成一说,除义理可寻绎外,还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可资参证。儒者在孔子之前,大体以相礼司仪,尤其是祭祀专家的面目出现,或者以文胜质则史的文章博学以备顾问的史官身份出现,然不管儒家原本出于何种王官,春秋中后期,儒家以孔子为宗盟,变小人儒为君子儒,变文史星历为行己有耻、居仁由义的君子,变府库档案为六艺经传,变王官之学为民间私学,儒者变成文化的传承者,是学院派,居师者之地位。
《史记·儒林列传》载:“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可见七十子之徒多行教四方[注]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段干木,《史》称受业于子夏之伦,之伦承上文子路、子张、澹台子羽、子夏、子贡言。”(阮元《皇清经解》卷22,鸿宝斋光绪十七年缩印本。)。吴起曾师事曾子,梁惠受学于子夏,墨子本儒门学子,告子,则说兼学儒、墨。又,荀卿在稷下三为祭酒,李斯、韩非皆出其门下。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说李悝(克)、吴起是子夏、曾西弟子[注]《魏文侯礼贤考》第121页;《吴起去魏相楚考》第176页;又谓法源于儒(《商鞅考》第212页)。。郭沫若在《批判》中说:“前期法家的批判中指出李悝、吴起、商鞅都出于儒家的子夏,是所谓‘子夏氏之儒’。”所以,《天下篇》“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当是实录。
章太炎说:“荀、孟是以所学定其主张,告子是超乎所学而出主张的。”(《国学概论·哲学的派别》)不惟告子,我一直主张,“百家”是从主张而言,从学源论,“诸子”大体皆受业于师儒辈。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儒家多为老师。所以《庄子·天下篇》说:“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即所谓“诸子”与“百家”。故,庄子受学于颜氏之儒,虽为推论,然于理确合乎当时之实情。且如告子,庄子六艺经传通习于师儒辈,而思想主张则可自出机杼。
所以,师从儒门何派是一事,“超乎所学而出主张”又是一事。于是,在“庄出于颜氏之儒”的大前提下,章郭二氏都继续阐扬庄子的出于儒入乎道思想辙迹。
儒道关系,是中国文化史上之一大题。孔老之间,尚有师生相得之雅。到庄孟时代,诸子蜂出,百家争鸣中强调尔汝之别,“道术为天下裂”。太史公说庄子剽剥儒墨、诋孔子之徒、发明老子之术,本归于老子之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此言一出,遂成公论。潘雨廷说:“战国时的儒道之辨,实起于孟子与庄,于老与孔的生前,并不如是,此不可不明辨之。”[注]《易与老庄》,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儒道互补说,正是在这种儒道之辨的基础上深化出来的。通俗地说,即如林语堂语:“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学术史上,互补说代有其人,今人冯友兰、李泽厚,牟钟鉴等也都做过推阐。习见通论,兹不赘述[注]如冯友兰氏认为,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两者统一在圣人的人格上,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又《中国哲学简史》说:“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也是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互补说所关联的乃是同源同归说。儒道互补说可用“绘事后素”来比喻这种关系。朴素与繁华、返璞与化性之间,同源说便蕴含其中。儒道区别于墨家,即在于,儒道或仁爱克己或求放心或化性起伪,或法天贵真或返璞归真或逍遥齐物;又或尽情尽性、赞天地之化育、不失赤子之心、率性修教、求放心致良知;或含德之厚比于婴儿,复归于婴儿等等,皆基于自然人性之基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两者并不相违碍,而墨家兼爱却是近乎宗教性的设计,既不起于自然,又不归乎自然。
在理想上,儒道皆从“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出发,在致广大而尽精微处,以形而上、先天地生之道为基础;以和、明、诚、三无五至[注]出土文献证明此说并非道家阑入。上博藏简《民之父母》可证《礼记》《家语》中“五至三无”可信。另,今本《老子》第19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在郭店楚简《老子》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虑,民复季子。”儒道对立消解很多。再如,据敦煌《论语郑注》,孔子所谓“窃比于老彭”之老彭非前人所疑为彭祖一人,郑玄即注作两人,老极有可能即是老子。越来越多出土文献都直接或间接证明儒道关系并非势同水火。、内圣外王(《庄子·天下篇》)、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无为无不为等为自然、政治、艺术、人格之最高境界;秉持“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老庄书中之“和光同尘”“不累于俗”“曳尾于涂”“与麋鹿共处”“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等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独立自由的生命主义精神;秉持“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老子》六十章)的理性主义精神。再如,老聃取法“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荀卿主张“虚一而静”(《解蔽》),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孔颜乐处、曾点之学,是儒家之道学,心斋精诚、坐忘丧我又是道家之儒学。所以说,儒道互补的基础是在极致处同源又同归,这也决定了儒道在历史上“通变”的可能和必然。
章郭二氏正是以颜回和庄子为接应,深入地论述了“儒道通变”。这既是“庄子师颜氏说”的深化,也是“庄子师颜氏说”的价值所在。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郭氏认为这正说明“儒与道之比较相近,至少是说明了一部份的真实的”。章氏认为,儒道同源异流,“其殊在量,非在质也”:
周秦诸子,道、儒两家所见独到。这两家本是同源,后来才分离的。《史记》载孔子受业于徵藏史,已可见孔子学说的渊源。老子道德的根本主张,是“上德不德”,就是无道德可见,才可谓之为真道德。孔子的道德主张,也和这种差不多。就是孟子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也和老子主张一样的。道儒两家的政治主张,略有异同:道家范围大,对于一切破除净尽;儒家范围狭小,对于现行制度尚是虚予委蛇;也可以说是“其殊在量,非在质也”。(《国学概论·哲学的派别》)
庄子乃是同源分流的一个关键节点。章氏说:
孟子和荀子是儒家,记载颜子的话很少,并且很浅薄。庄子载孔子和颜回的谈论却很多。可见颜氏的学问,儒家没曾传,反传于道家了。庄子有极赞孔子处,也有极诽谤孔子处,对于颜回,只有赞无议,可见庄子对于颜回是极佩服的。庄子所以连孔子要加抨击,也因战国时学者托于孔子的很多,不如把孔子也驳斥,免得他们借孔子作护符。照这样看来,道家传于孔子为儒家;孔子传颜回,再传至庄子,又入道家了。(《国学概论·哲学的派别》)
郭氏则说:
庄子是从颜氏之儒出来的,但他就和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卒于“背周道而用夏政”一样(《淮南·要略》),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宗派。他在黄老思想里面找到了共鸣,于是与儒、墨鼎足而三,也成立了一个思想上的新的宗派。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庄子既是儒家又是道家,章氏说:
庄子的“无我”和孔子的“毋我”、颜子的“克己复礼”也相同,即一己与万物同化,今人所谓融“小我”于“大我”之中。这种高深主张,孟、荀见不到此,原来孔子也只推许颜回是悟此道的。所以庄子面目上是道家,也可说是儒家。(《国学概论·哲学的派别》)
郭氏解释庄子自命为儒士而要毁儒时说:
儒之中本来也有多少派别,在孔子当时已有“君子儒”与“小人儒”;在荀子口中则有所非难的“贱儒”或“俗儒”。庄门虽自命为儒士而要毁儒,那是丝毫也不足怪的。但就由于庄门之非毁“儒、墨、杨、秉”,而道家的根基也就深固起来了。
较章氏更详赡更进一步,郭氏在根基深固处,不仅指出庄子出乎儒入于道,还进一步独到地分析了儒道与墨家的形神离合,黄老与庄老的旨趣差异和庄子在刑名之外更造道家之功。郭氏认为,庄子缵黄老散入刑名法家之余绪,继关尹老聃正统之绝学,而为道家之马鸣、龙树,他说:
黄老思想本来经受齐国的保护,在稷下学宫里面是最占优势的,然而他们里面有些分化,宋鈃、尹文一派演化而为名家,惠施在梁承受了他们的传统;慎到、田骈一派演化而为法家,关尹一派演化而为术家,申不害与韩非承受了他们的传统。真正的道家思想,假使没有庄周的出现,在学术史上恐怕失掉了它的痕迹的。道家本是汉人的命名,而在事实上确因有庄周及其后学们的阐扬和护法,才有这个宗派的建立。
又:
《天下篇》把关尹老聃称为“古之博大真人”,在庄子或其后学自然是以关尹老聃为合乎他们所理想的人格了。然而从庄子的思想上看来,他只采取了关尹老聃清静无为的一面,而把他们的关于权变的主张扬弃了。庄子这一派或许可以称为纯粹的道家吧?没有庄子的出现,道家思想尽管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受着温暖的保育,然而已经向别的方面分化了:宋鉼尹文一派发展而为名家,田骈慎到一派发展而为法家,关尹一派发展而为术家。道家本身如没有庄子的出现,可能是已经归于消灭了。然而就因为有他的出现,他从稷下三派吸收他们的精华,而维系了老聃的正统,从此便与儒墨两家鼎足而三了。在庄周自己并没有存心以“道家”自命,他只是想折衷各派的学说而成一家言,但结果他在事实上成为了道家的马鸣、龙树。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记·太史公自序》)。此处道家更多是黄老道家。黄老之术,是治道之一种,乃入世法,庄周之学,是逍遥之大成,乃出世法,从黄老到老庄,兼义而有所偏,黄老乃清净无为之为,无为而治之治,老庄乃清净自然而然,逍遥自在之在。章郭当时从儒道通变的角度即是这样认为,庄子虽“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不过目标不是平天治下之术,而是行己逍遥之道,政治哲学色彩淡了,人生哲学色彩浓了。郭氏在《批判》中约略地揭陈了这一点:
庄周比关尹老聃退了一步,是并不想知雄守雌,先予后取,运用权谋诈术以企图损人利己而已。这是分岐的地方。庄周书,无论内篇外篇,都把术数的那一套是扬弃了的。这可以说,是这一派在消极一方面的特色。
另外,章郭二位也通过比较儒道与墨家之别,尤其是庄墨之别,进一步证实儒道通变。郭说:
自有庄子的出现,道家与儒墨虽成为鼎立的形势,但在思想本质上,道与儒是比较接近的。道家特别尊重个性,强调个人的自由到了狂放的地步,这和儒家个性发展的主张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冲突。墨家是抹杀个性的,可以说是处在另一个极端。
郭氏认为庄墨之间实际上貌合神离:
有一点深刻的区别,便是庄子一派主张生活恬淡,摒弃情欲,或甚至死后裸葬,虽然比墨家的非乐、节用、节葬犹有过之,但庄派是主张自发,而墨家是主张强制,这是绝大的不同。自发是听其自由。
章氏则说得更生动,把墨家看成后世吃菜事魔的邪教:
老子之言玄妙,孔子之言洒落,而墨子终不之信也。且墨子明鬼亦有其不得已者在。墨子之学,主于兼爱、尚同,欲万民生活皆善,故以节用为第一法。……用宗教迷信之言诱之,使人乐从,凡人能迷信,即处苦而甘。苦行头陀,不惮赤脚露顶,正以其心中有佛耳。南宋有邪教曰吃菜事魔,其始盖以民之穷困,故教之吃菜,然恐人之不乐从也,故又教之事魔,事魔则人乐吃菜矣……节用之说,孔老皆同。老子以俭为宝,孔子曰宁俭。事俭有程度,孔子饭疏饮水,而又割不正不食,固以时为转移也。墨子无论有无,壹以自苦为极。其徒未必人人穷困,岂肯尽听其说哉?故以尊天明鬼教之,使之起信。此与吃菜事魔,雅无二致。
章郭皆鄙薄墨家而以孔老为高深。最后郭氏和盘托出,认为庄子与墨家貌合神离,超乎墨家,从颜氏之儒而出,而超越儒家。郭氏说:
从大体上说来,在尊重个人的自由,否认神鬼的权威,主张君主的无为,服从性命的拴束,这些基本的思想立场上接近于儒家而把儒家超过了。在蔑视文化的价值,强调生活的质朴,反对民智的开发,采取复古的步骤,这些基本的行动立场上接近于墨家而也把墨家超过了。因此他们在思想上提到墨家上来的时候绝少,似乎认为它是值不得批判的。所以一样在反对儒墨,而对于墨家是淡漠,对于儒家是白热。
我曾有则读书笔记,大致是说,墨家忍情,庄学任情,一个自发,一个强制,一个高度设计,一个究竟自然,正是庄墨非乐与大乐,节俭与返璞之区别所在。郭氏在当时墨学推尊的时代,能分剖精微如此,是相当值得致敬的。庄周为道家之马鸣龙树之说,也因此深固起来。
本来儒道两家、孔孟老庄,“孟子之学为孔门大宗嫡派”[注][日]伊藤仁斋:《孟子古义》《总论》,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第3页。,而“老之有庄,犹孔之有孟”(焦竑《庄子翼序》)。结果剧情被翻转成庄子“言至道之精微,多与《中庸》相表里;其推尊孔氏之处,且蔑以加:是则孔门之嫡派大宗也”[注]阮毓崧:《庄子集注》(1928年初版),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版。,“非老聃之嫡嗣,实尧孔之真孤”(明觉浪道盛语)。只是,历史上援儒入庄主流还是旨在缓和儒道关系,其本多在于张大儒学,甚至与其说援儒入庄,毋宁说援庄入儒。但章郭二氏则无特别要为儒家站队的意思。墨者杜国庠曾说郭氏“有点袒护儒家”,有读者说他“大为儒家扶轮”,都被他否定了。他最多承认有点袒护孔子,而“儒家那个名词,便是非科学的东西”,“怀抱着什么新儒家的执迷,那可以说是恐龙的裔孙——蜥蜴之伦的残梦”了[注]分别见于1945年《后记》和1950年改版书后《蜥蜴的残梦》。。章郭说庄子出颜氏之儒,一则寻绎了儒道通变的辙迹,一则要揭示庄子为道家注入的新生。这是《庄子批判》的主线。以笔者自己学习笔记归纳,大致理路如下:在庄子本颜氏之儒的基础上,阐释儒道二家在周秦两汉历史上的交织与变奏。交织即互补,一言以蔽之,“绘事后素”。变奏即通变,庄子从儒家精微之学出,超越散入刑名诸子之黄老管晏之学,重整的老庄正统,转帝尧黄老无为而治之入世法而为博大真人任逍遥、齐生死之出世法。虽说战国开始儒道派性意识越来越强,但因儒道在基础和目标上旨趣大同,庄孟之后的思想史,两家仍不断孳乳通变。如冯友兰就曾这样看待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在三、四世纪有些道家的人试图使道家更加接近儒家;在十一、二世纪也有些儒家的人试图使儒家更加接近道家。我们把这些道家的人称为新道家,把这些儒家的人称为新儒家。”[注]冯友兰:《三松堂全集·中国哲学简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这也不算多新鲜,明清之际的潘平格所说的“朱子道、陆子禅”因一语中的而在后世竟寖成俗语,显示出儒道之通变乃两千年思想史之常态。
四、余英时的《互校记》与钱穆的《庄老通辨》
近代以来主持庄学通儒之说者,不仅海内云集,且谓一时之秀。这背后所关乎的儒道通变问题确实也是思想史的大题。陈引驰说:“《庄子》与儒家之关系确乎不是贬斥、排诋那么简单,由《庄子》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理解儒学是无疑的。”[注]陈引驰:《庄子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杨海文正视这一问题提出的价值,并希望继续深入:“做出‘庄子即儒家’议题的命名,并凸显它独特的思想史价值;期盼‘庄子即儒家’议题如其所是地敞开自身,并真切地汇入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洪流。”[注]见于2016年杨先生《庄子本颜氏之儒:郭沫若“自注”的思想史真相》一文。笔者于2016年底草成此篇初稿,发表于2017年春季举办的“北伐前后的郭沫若”主题会议,也算响应杨先生之说。今重新修订以正式刊发之际,发现杨先生又于2017年在《文史哲》第2期著文《“庄生传颜氏之儒”:章太炎与“庄子即儒家”议题》。比其前说,更细腻丰富,重心也从郭氏移诸章氏。文章逐一分疏了章太炎论“庄子即儒家”的五种文献,已别是一题,却也更加辅证了笔者此篇。章郭二位的研究率先感受到了庄学史这一潮流。在学术发展大势面前,总体诊断问题的真假和价值是我们最该做的。而在细微的学术自身的年轮上,与其从单线影响角度来分源流第甲乙,坐实谁因袭谁,不如综合审视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是谁在开拓、谁在发扬,深入探讨如何继续、往哪发展。略有遗憾的是,在面对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民国学风,尤其是面对求新派的热切地想重整乾坤、再造中华的学风时,我们精力过多地苛察了一些当时本是求新派彼此呼应的风气,而过少地将问题本身置于宋元以来的学术史背景上进一步推阐。
这里就不得不提及余英时挑起的郭钱之争了。余先生曾辟十二事,欲鞠治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先秦诸子系年》成铁案。文章最早于1954年8、9两日,在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第6、7、8三期连载,题曰《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以下简称《互校记》)。据说主编抱着看热闹不怕事大的态度说“觉得这正是可以为《人生》增添热闹的题材”[注]据《互校记·跋语一》,此语出自《人生》半月刊的主编王道。。果然,这事在内地学界引起了长达数十年的时断时续的反响,从白寿彝到翟清福、孙开泰、傅杰等等,呼应的、商榷的都有[注]白寿彝:《钱穆与考据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1年第2期。翟清福,耿清珩:《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郭沫若学刊》,1996年第3期;孙开泰《谈谈稷下学史料与研究──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郭沫若学刊》,1996年第3期。廖久明:《片面之词何时休——评郭沫若抄袭说》,《博览群书》,2014年第1期;丁东:《学术中不能承受之轻》,《博览群书》,1995年第12期;傅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日本《百年》,1999年11月号,等等。网上一批批阵营分明的互相攻驳的文章,尤以方舟子不折不挠的数篇传播最广。,但就是不见有从新学急切学风和千年学案等角度来调停的。期间,余氏并未改变自己的观点,且有期望更广泛传播的努力,先于1991年纪念钱穆的集子《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注]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中略作删节收入了该文,并加了一个跋(下文简称《跋语一》),又在1992年在香港《明报月刊》10月号上旧话重提,刊发《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说郭沫若犯了“严重的抄袭罪”。1994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将该文收入的《钱穆和中国文化》一书,该书系《犹记风吹水上鳞》全部与《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部分文章合成,余氏续作跋语(以下简称《跋语二》)。据编校者傅杰先生说,大概因出版纪律,做过一些技术处理。这些处理后来又添了不少话柄和花絮。
郭沫若其实很在意别人的评价,尤其是对1945年出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如董作宾对其殷周奴隶社会关键论证提出批评后,郭氏很生气,在1954年出改排本之前写的《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1950)中说:
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是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
余氏的文章正发表于郭氏书改排的1954年当年,白氏的文章发表于1961年。我们不好揣度郭老对《互校记》的反应。我们只能就一些与本文有关的事实做一些梳理分析。
首先,据《后记》,郭氏确实参看了钱氏的《系年》,但未注明。
余氏在《互校记》中指出的,郭氏在参考章太炎、梁启超、胡适时都注明了,唯独不提钱氏。确实如前文所梳理,其在《庄子批判》明确自注观点出自章氏。这一点即便是为其做洗冤的翟清福先生也是认为应该向读者交代的: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根据其日记排列了他研究先秦诸子和撰写各篇文章的日期,时间起于1943年7月3日,止于1945年2月18日。这期间,1943年9月7日在杜国庠处看到书架上有一部钱穆著的《先秦诸子系年》,便借回家去翻阅。这是余英时认为《十批》抄袭《系年》的重要证据。上述时间表说明,郭沫若在撰写《十批》的过程中,确实参阅过《系年》。这一点,是应该先向读者交代的。[注]翟清福:《十批判书真的抄袭了先秦诸子系年?》,《史学集刊》,1996年第4期。
其次,郭氏在《后记》中批评了钱氏关于《乐记》与《乐论》先后的问题,再次证明郭读了《系年》。他说:
九月七日的清早,我到金刚村去访问杜老,他依然辛勤地在研究着《墨子》。我看见他的书架上有一部钱穆著的《诸子系年》,便向他借阅。这书我是早就闻名的,但还没有看过它的内容。翻到了考证公孙尼子的一节,作者的意见和我所见的完全相反。他认为《乐记》是抄袭《荀子》《吕览》《毛诗》等书而成的东西,因而他断定公孙尼子为荀子的门人。我感觉着这样的论据实在是薄弱的可笑。
第三,对勘《系年》,《批判》中论稷下时所引刘向《别录》有笔误,余氏在《互校记》及《跋语二》中借此确证了郭先生史料取自钱氏。文繁不录。这一点,为郭氏洗冤者也都认可的。如路新生认为是“极少数站得住脚的理由”[注]路新生:《〈互校记〉与〈先秦诸子系年〉之史源发覆》,《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翟清福、耿清珩说:“我们不妨相信郭沫若所引的上述材料是从《系年》转引的。”[注]翟清福,耿清珩:《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中国史研究》,1996第3期。孙开泰说:“这在抗战期间的重庆,书籍缺乏,研究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注]孙开泰:《谈谈稷下学史料与研究──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郭沫若学刊》,1996年第3期。我同意孙先生的看法,当然也再三证明郭氏写作时,手边是有书参考着的。
第四,余文十二事,无一及《庄子批判》。不知是否与郭氏自注有关。抑或别的原因。
第五,余氏业师钱穆先生后出的《庄老的宇宙论》(1955年)[注]后收入《庄老通辨》,香港:新亚书院研究所,1957年版。一文与章郭二氏同调,认为庄周推尊孔子,出颜氏之儒,且为儒道通变之契机。钱穆说:
试就庄子书细加研寻,当知庄子思想,实仍沿续孔门儒家,纵多改变,然有不掩其为大体承续之痕迹者。故《庄子》内篇,屡称孔子,并甚推崇。……
韩非称儒分为八,盖自孔子卒后,其门弟子讲学,已多分歧矣。孟子常引曾子子思,此为孔门一大宗。荀子极推仲弓,此当为又一宗。子游子夏,各有传统,而《庄子》内篇则时述颜渊。若谓庄子思想,诚有所袭于孔门,则殆与颜氏一宗为尤近。韩非八儒,即有颜氏,此证下逮晚周末叶,儒家仍有传述颜氏说而自成一宗派者。《易·系传》成书,尤较《老子》为晚出,故其陈义多汇通老庄,殆可为晚周末叶后起之新儒学,而《易·系传》于孔门,亦独称引颜渊。此证颜渊于庄学有相通也。下逮东汉,道家思想渐盛,而颜渊乃独为东汉诸儒所尊推。北宋理学兴起,必溯源于周濂溪,而濂溪《太极图说》,上本《易·系》,其论宇宙观点,显然近于道家,而其《易通书》,亦盛尊颜渊。此又证孔门诸贤,独颜渊最与后起道家义有其精神之相通也。今欲详论颜氏思想,虽憾书阙有间,然谓庄周之学,乃颇有闻于孔门颜氏之风而起,则殊约略可推信也。[注]钱穆:《庄老通辩:庄老的宇宙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3页。
同时还认为道家取邻于儒,而远于墨:
《齐物论》于儒墨是非,兼所不取。然内篇引孔不引墨,则庄子心中,对此两家之轻重,岂不已居可见乎?(《庄老通辩·庄老的宇宙论》)
又:
中国学术,原本先秦,而儒道墨三家为之宗:研究人生修养,尤为中国学术精华,顾墨家于此独缺,以此其流亦不畅。儒道两家,各擅胜场。(《庄老通辩·比论孟庄两家论人生修养》)
钱氏比郭氏小三岁,太炎先生是郭、钱二位之长辈学人,郭氏书晚章氏二三十年,钱氏书又晚郭氏十年,除了已为出土文献所否定的老庄关系上颠倒之外,持论皆同于章郭:庄周本于颜氏,将无同于儒道,源流互补,通变有常,墨家为儒道之异质等等。
第六,郭氏自注义袭章氏,钱氏则未注出处。
笔者无意证明钱氏“没有学术诚实”(余氏评郭氏语),更不是要搅混水,用比烂的下流招式来说明洪桐县里无好人。而是如上文所说,学术史自有年轮,风气所至,大势所趋,英雄所见往往略同。宾四老早年即留意庄学,1921作《伊壁鸠鲁与庄子》[注]刊出于两年之后的《学灯》1923年3月4、5日。《师友杂忆》回忆作:“论希腊某哲人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二三十年代考辨“先秦诸子系年”,于庄子生卒及时代更是详加求索,与郭氏书出版的1945年当年也有《比论孟庄两家论人生修养》《记魏晋玄学三宗》两篇论庄子的文章。1957年出版的《庄老通辩》乃是旧文结集,据笔者披览所及,此前有十多篇庄学研究文章[注]《南郭子綦考》(1947年);《郭象〈庄子注〉中之自然义》(1948年);《庄老与易庸》(1951年);《中国道家思想之开山大宗师庄周》(1953年);《道家政治思想》(1953年);《庄老太极无极义》(1955年);《王弼郭象注易老庄用理字条录》(1955年);《释道家精神义》(1956年);《〈庄子〉外杂篇言性义》(1956年);《〈老子〉书晚出补证》(1957年);《王弼论体用》(1957年)。此后,庄学文章有《〈庄子〉书言长生》(1960年)一篇。,《庄老的宇宙论》即是其中之一。同是浸淫稽古之学,在同一学术环境和风气下,相切相磋,相摩相荡,所见略同既是自然,发挥新知、发扬呼应更是责任。我辈后学当更瞩目问题本身,而慎于挑动前贤斗前贤。再进一步说,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郑振铎,甚至闻一多等等以新我国学、更造文化为己任的新学派,其著论横议之间,往往相互呼应,如非后来政治分野越来越大,今天我们未必有这么多话头[注]这一观点,是在与邵宁宁教授讨论时加深拓展的。再举两例,如当年俞樾在学术上不向章太炎落井下石,尚为学生的傅斯年、顾颉刚对新来的教师胡适不屑其学问却加持其方法,等等,都是相求相和之反应。这一现象甚至还可前溯廖平、康有为那一辈学人。。
所以,郭沫若在文章中说,“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做尽可能的耕耘”。想来郭氏并非掩人耳目以表明自我力取而得。而余英时在批评文章说:“政治上对立,更应在学术上严谨,以免成为政治宣传,一切带着学术面貌的政治宣传都没有丝毫价值”。想来余氏本意也不是要欲盖弥彰,弥彰其政治上之成见。所以,在对待前辈学人时当“功疑惟重,罪疑惟轻”,于宾四门徒,更应行文宽厚谨慎,以避免陷入门户意气。余先生一文重判郭先生“是一个完全没有学术诚实的人。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态度了”。余先生是笔者最钦敬的前辈学人之一,但此文此说至少急躁了些。定谳一个学术问题尚且待敞开献疑求教多方而后可安,何况遽然由此判断一人之品格以及诛连所有作品。其文其说确实气盛了些。难怪外围风议不顾余氏自明无政治偏见之表态反说其“政治偏见很深”。余先生虽然三十年后依然坚持己说,且有所补正,但也承认自己“对他确是有偏见”,是自己“年少好事”,“行文也流于轻佻刻薄”,自己“从来便不喜欢自己这篇少作”[注]《〈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跋语一。。惜乎余氏在重刊的两次跋语都未能深省自己所引王国维论戴东原的话:“平生尚论古人雅不欲因学问之事,伤及其人之品格。”[注]《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收在《观堂集林》卷十二。就“庄子批判”一节,从王闿运、章太炎、钟泰,到郭沫若、钱穆、童书业,都殊途同归,正体现了庄学史之一潮流,很难从单线影响角度来分源流、第甲乙,又何况新学学风普遍急切,当年都有协力廓清再造之普遍价值诉求,只是历史弄人,同志难同道,终究劳燕分飞,南渡北归,后学气盛不同情地进入彼时之当下,而以当下入彼时,质证前贤,岂非以孟庄时代儒道质诸春秋时代之孔老!憾哉!
五、《庄子批判》结语代结语
郭氏于文苑、儒林两擅场,生前身后在家事国事、创作行履等方面都留下相反而难以相成的诸多争议。笔者从《庄子批判》自注出发,力图展示学术大势之前,卓识硕学如章、郭、钱等近现代诸子,皆致力于思考庄学渊源,分析儒道通变等问题。这实在值得我们薪火传承,继续深入探讨。我们当同情地理解当年急切想以新学再造文明的时代风气,以君子务本之精神,在政治、学术之间谨慎立言。为此,仅以郭氏《庄子批判》一文的结语来结束本文:
大凡一种思想,一失掉了它的反抗性而转形为御用品的时候,都是要起这样的质变的。在这样的时候,原有的思想愈是超然,堕落的情形便显得愈见悲惨。高尚其志的一些假哲学家,其实倒不如卢生、侯生之流率性成为骗子的,倒反而本色些了。[注]《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