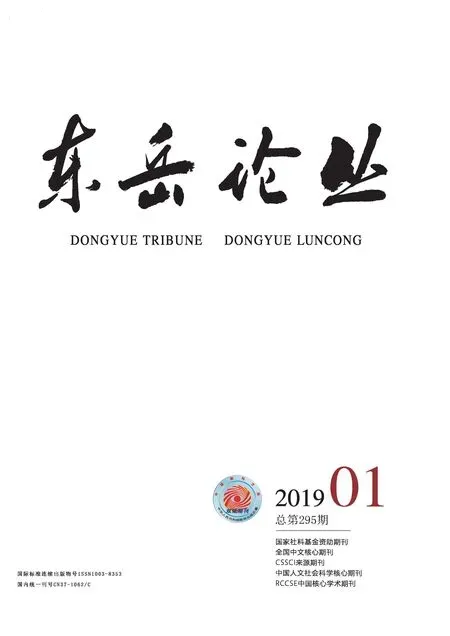麦克道尔“第二自然”概念论析
王增福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近代以来,我们主要以自然科学的方式解释与说明自然,在这种科学主义的自然观中,人类的自发性不占据任何位置并居于自然的领域之外。如果自发性没有嵌入到我们关于自然的理解中,自然也就没有理由对我们做出的判断或持有的信念承担责任。但是,我们又必须对判断或信念承担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体现在判断需要在自发性的运作中完成,更体现为信念必然受到来自世界的合理性限制。彻底的自然主义、戴维森的自然主义抑或膨胀的柏拉图主义,或者将自然完全祛魅,否认理性的自律性;或者过度提升自发性的独立地位,将理性进行超自然的解释;这些方案都无法消解由于自然的逻辑空间与理由的逻辑空间的划分所导致的自然与理性的对立,不能说明自然在何种意义上对我们的知识或信念给予合理性约束。麦克道尔通过提出第二自然的自然主义思想走出上述困境,这一立场承认人类的自发性参与了自然的构造过程,我们不仅拥有生而具有的第一自然,更拥有经过训练与教化才能形成的“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注]second nature一词最早应用于伦理学领域,意指人的一种经过后天发展而来的延伸属性,被译为第二天性。但在麦克道尔这里,second nature除了具有伦理学意蕴之外,更多的是在知识论意义上阐发自然的内涵。尽管麦克道尔关于第二自然的思想受到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阐发伦理思想时的影响,但又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思考范围。为了论述上的一致性,文中除了尊重已有译文的工作将个别哲学家思想中的second nature译为第二天性之外,其余的都译为第二自然。。他将被理性塑造的东西视为自然的,由此保证世界对我们的思想构成一种理性意义上的强制性,同时世界又不完全处于思想之外。“第二自然”是麦克道尔自然主义思想的核心范畴,是调和理性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概念,正确理解与科学评析这一概念,对说明麦克道尔如何利用第二自然发展出一种新的自然主义,而这种自然主义又能在不否认人类自成一类的特性的情况下合理解释理性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至关重要。
一、第二自然的发生学嬗变
第二自然的概念并非麦克道尔首创,它在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历史悠久,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艺术学或教育学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一般来说,“第二自然观念孕育于古希腊智者们的伦理政治问题,其正式提出却肇始于亚里士多德”[注]马万东:《第二自然研究的四种进路》,《现代哲学》,2012年第5期。;麦克道尔也指出,第二自然的观念“几乎明确地包含在亚里士多德有关伦理品格(ethical character)形成的方式的说明中”[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84,p.84,注释16,p.79,p.84.。我们从《心灵与世界》第四讲的一个注释中得知[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84,p.84,注释16,p.79,p.84.,麦克道尔是从《尼各马科伦理学》的相关论述中获得第二自然概念的灵感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的主题是讨论如何获得和养成德性(德性就是某种使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如何培养和塑造好习惯,因为一个人的好习性就是他的品质。亚里士多德在该书第二卷中说道:
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一类是伦理的。理智德性主要由教导而生成、由培养而增长,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伦理德性则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因此把“习惯(ethos)”一词的拼写方法略加改动,就有了“伦理(ethikee)”这个名称。由此可见,对于我们,没有一种伦理德性是自然生成的。因为,没有一种自然存在的东西能够改变习性。[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页。
按照他的观点,德性是在后天习惯中获得的,德性养成后就成为人的第二自然,但后天获得德性的过程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德性既非反乎自然,也非出于自然。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并非要在自然与非自然之间作出区分,而是要区别开出于自然的能力和后天获得的能力。出于自然的能力如视觉、嗅觉是我们先天就具有的本性,这些能力与生俱来,在我们使用它们之前就已经存在。而我们后天获得的其他能力,比如德性养成、设计技巧等,是需要经过学习和培养才能形成的。人的德性包括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两种;理智德性是经由后天的教导、培养和训练而成,包括理论智慧、理解和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等;伦理德性则是由沿袭风俗习惯而获得,主要包括慷慨、公正与节制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虽然这两种德性存在差异,但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都与人的本性(自然)相关联。我们通过习惯获得的伦理德性在自然的过程中演化为我们本性的一部分;理智德性虽是后天获得,但它经过教导和驯化已渗透着我们的习性和概念系统,实际上也成为我们本性的有机构成。
亚里士多德指出,在人类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拥有实践理智的正常人类成员经由自身的学习或他人的教化,渐渐知晓了现存的道德需求,并试图在自己的伦理行为中对其作出适当回应,他们的实践理智最终就会以这种方式获得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实践领域的智慧,它不同于理论领域的理论智慧,更不同于制作领域的技艺。按照麦克道尔的理解,德性所包含的“实践智慧”是对某些理性要求的回应。一个拥有实践智慧的人,一定可以在伦理实践过程中通过深思熟虑和敏锐的洞察力给出采取伦理行为的理由,从而为自己的伦理行动提供辩护。麦克道尔将实践智慧推广到极致,认为“‘实践智慧’是可以充当知性的典范的适当种类的事物。……它让我们能够认识并创造那种作为在理由空间中的放置之事的可理解性[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84,p.84,注释16,p.79,p.84.。由此看来,实践智慧就是认知主体的第二自然,人类通过伦理的教养可以进入这片理性的空间。在此意义上,麦克道尔强调,亚里士多德已经明确表达了第二自然的概念。正如麦克道尔所言:“伦理品格包括实践理智的倾向,而当品格形成之时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部分就是,这种实践理智获得了一种确定的形态,因而对于其拥有者来说,实践智慧就是第二自然。[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84,p.84,注释16,p.79,p.84.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化时期,“另一种自然”(altera nature)的概念出现。根据冯克(G.Funke)的考察,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首先提到“另一种自然”这个范畴,而神学家奥古斯丁则最早使用了“第二自然”的表述[注]Marcus Willaschek (ed.),John McDowell:Reason and Nature Lecture and Colloquium,in Münster,1999,p.41.。但是,奥古斯丁揭示的第二自然的意义与亚里士多德阐释的第二自然的内涵不同,他在原罪论的基础上谈论第二自然,因而将“第二自然”与“mala consuetudo”(坏的习惯)这一用法关联在一起。奥古斯丁认为,“原罪”(original sin)中的“原”并非“原初”的意思,罪不具有第一原初性,因为惟有上帝的创世才具有第一原初性。在原罪神学中,人的罪性与上帝创世时赋予人的原初善性相比只是第二天性。所以,第一自然是上帝给予人类的先天要素,第二自然则是第一自然的堕落,是一种不好的习惯。但是,“人处于沦落状态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却不再是第一天性,而是第二天性。与沦落的现实相比,人的第一天性,即原初之善已经变成一种潜能,在历史上要上溯到无限遥远的过去或推迟到未知的将来”[注]刘宗坤:《原罪与正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可见,对奥古斯丁来说,第二自然并不是从内在于第一自然的潜能中发展出来的,而是人类自然天性的堕落,结果就形成了某种坏的习惯,并且这种习惯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所说:“习惯就是第二天性,它摧毁了第一天性。”[注][法]帕斯卡尔:《思想录》,李斯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译文有改动。
受奥古斯丁神学观的影响,在随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哲学家们主要在消极意义上使用“第二自然”。直至法国启蒙哲学家卢梭在《爱弥儿》中区分了人的第一天性与第二天性,并认为第一天性是自然赋予我们的,因而是一种先天的能力;第二天性是通过文化、教育或习惯塑造的,是后天养成的;第二自然的内涵才由此发生了变化。卢梭指出:“我们愈脱离自然的状态,我们就愈丧失我们自然的口味,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习惯将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而且将那样彻底地取代第一天性,以至我们当中谁都不再保有第一天性了。”[注][法]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91页。显然,卢梭把违背自然视为一种人为规定的实质,认为以文化为主的第二自然不仅是对大自然的人为改变,而且使人偏离了自己的本性。从这个角度讲,卢梭是一位反文化的自然主义者[注]何中华:《重读卢梭三题》,《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卢梭在其一些作品中使用“回归自然”的口号,认为回归自然是一种与第一自然相协调的生活方式。概言之,在卢梭这里,我们可以将第二自然看作是第一自然的异化(alienation)的产物。
19世纪初期,黑格尔也提出了“第二自然”的概念,正是黑格尔关于第二自然的阐明才预示了麦克道尔在《心灵与世界》中使用这一术语的意义。如果说麦克道尔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吸取了创新第二自然概念的灵感,那他从黑格尔这里则直接领会了这一概念的旨趣。黑格尔认为,我们的观念中有两类事物可被视为规律,一类是自然规律,另一类是法律。自然界是上帝的造物,其规律是客观的和确定的,错误的只是我们对这些规律的“观念”,因此,我们可以经由对自然的认知把握自然规律,进而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但黑格尔为何将源于人之手的法律也称为一种“自然”呢?这是因为法律的领域和自然规律一样富含“理性”,同样要以观念的方式加以认知;在法律中每个人都会遭遇自己的实践理性,我们必须凭借理性来确证自己的主张;同时现代还要直面传统的“定在法”与心中应然之间的冲突,这就带来了某种认识的需要。为此,黑格尔主张通过认识自然规律的方式,将行动领域当作理性认识的对象,行动领域由此也被称为“第二自然”。
对黑格尔来说,第二自然就是人类凭借自身的理性活动所建构的规范世界,也是最终成就人类自由的地方。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把法国大革命后的“现代伦理世界”置于和自然规律相等同的第二自然。他认为,在现代伦理生活中,美德是伦理性的东西在个体性格中的反映,只有伦理性规定成为个体性格中的稳定内容时,我们才能称此人拥有美德。换句话说,使某种行为方式成为性格中的习惯,这就是人的第二自然。黑格尔说道:
在跟个人现实性的简单同一中,伦理性的东西就表现为这些个人的普遍行为方式,即表现为风尚。对伦理事物的习惯,成为取代最初纯粹自然意志的第二天性,它是渗透在习惯定在中的灵魂,是习惯定在的意义和现实。它是像世界一般地活着和现存着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实体就这样地初次作为精神而存在。[注][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0页。
人的这种第二自然是在伦理实体中熏陶、渲染、习惯而形成,这个熏陶、渲染的过程也是个体的社会化和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个体接受伦理共同体教育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讲,黑格尔是在与习惯和教育相关的意义上使用第二自然的,这一点被麦克道尔所继承。同时,黑格尔并不是在一种“坏的”意义上来使用第二自然的概念,这标志着他与奥古斯丁等人关于第二自然的传统认识的彻底决裂。与麦克道尔相似的是,黑格尔同样把第二自然视为关于第一自然潜在性的实现,而不是将第二自然视为对第一自然的异化或解放。他认为,习惯是一种第二自然,是关于心灵的本质。黑格尔指出:
一方面,自然作为一个异化的他者,是一个与直接的自然性相对的第二自然;另一方面,它就是自然,是一个存在,是如是我在,它是我的习惯(Gewohnheit),这也是自然性在其中的一个方面。[注]Marcus Willaschek (ed.),John McDowell:Reason and Nature Lecture and Colloquium,in Münster,1999,p.42,p.97.
这两段论述表明,黑格尔在“纯粹自然意志”(merely natural will)中讨论的自然是一种被自然法则所支配的领域;而对伦理事物的习惯由于“如是我所是的方式”,从而成为与直接的自然性相对的第二自然,这暗示了一种关于“自然”观念的截然不同的用法。根据这一用法,作为心灵本质的习惯,第二自然不仅作为一种精神实体客观存在着,而且可以与“本质”交替使用,这恰恰说明第二自然也是一种自然,也是自然性的一个方面。黑格尔不仅区分了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并阐明了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之间的相似性。这反映出黑格尔与其他传统哲学家在关于第二自然的讨论中所存在的差异:奥古斯丁和卢梭谈论的是另一个自然,但这个自然不是真正的自然,是一种与直接的自然性截然相对立的伪自然;黑格尔谈论的则是真正属于自然构成组分的第二自然。所以说,麦克道尔对于第二自然概念的使用更多地接近于亚里士多德尤其是黑格尔,而与西塞罗、奥古斯丁乃至卢梭关于第二自然的使用有着本质的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道尔说道:“我很有兴趣的认识到,第二自然的观念直到黑格尔才清晰地呈现,而同时并不意味着一种关于人类原初本性的堕落(像在奥古斯丁那里一样)。[注]Marcus Willaschek (ed.),John McDowell:Reason and Nature Lecture and Colloquium,in Münster,1999,p.42,p.97.
二、第二自然的内涵与形成
人们一旦由纯粹的生物学空间进入到理由的逻辑空间,也就具有了理性的自由,因为拥有理性的人能够为自己应该去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提供充分的理由,而不像动物那样仅仅依靠纯粹的生物性需求来支配它们的活动。在自由的领域内,我们可以根据合理性的要求把概念、判断、前提、结论等要素,排列成某种对推理、证明、辩护等要素来说是恰当的布局,这种布局与自然法则领域内的事物的运作方式截然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根据法则领域内的自然规律来对这种布局进行经验性的描述。要准确理解这个成年人类从动物性中延续下来却又是自身所特有的理由或意义的领域,我们就必须借助“第二自然”的概念。正因如此,麦克道尔继承并创新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等人关于第二自然的思想,为阐明理由空间的独特性、确保自然空间对知识的合理性辩护和解决理性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创见。
对麦克道尔而言,第二自然是与第一自然(first nature)相对应的。他将第一自然也称为“单纯的自然”(mere nature),这是一种相关的动物生来拥有或经过简单的成熟过程便可习得的能力,简单说就是某种单纯自然的能力,“一般意义上的第一自然包括:自然律的领域和单纯的生物学现象”[注]韩林合:《麦克道尔的两种自然学说述评》,《云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与第一自然不同,第二自然不是相关动物生来具有或经过单纯的成熟过程便可习得的,而要通过训练或教育才能获得或形成。就人类成员而言,第二自然是指一个人在出生时并不拥有,需要在语言文化共同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社会的教化、文化的熏陶或语言的训练所获得的习惯及各种能力的集合,特别是经过教养而习得的那些概念能力,也就是对理由或意义作出回应的能力。用麦克道尔自己的话来表达就是:“作为结果的思想与行为的习惯便是第二自然”[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84,p.84,pp.87-88.。可以说,第二自然主要是指我们正常成年人的一种理性-概念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得我们能够对合乎理性的要求作出响应,能够以它们为理由来开展行动。也正因如此,我们才称得上是认知主体,才得以受理由支撑信念的持有者的身份区别于其他行动者”[注]王华平:《第二自然的自然主义》,《哲学动态》,2009年第12期。。
麦克道尔在解析第二自然的内涵后,着重阐释了第二自然的产生。他认为,人类文化共同体中的成员生来就是单纯的动物(mere animals),人类与动物的连续性不容质疑也不能否定,但人类成员拥有一种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潜能,这种潜能经过教化或教育被不断激发并发挥作用,进而使人获得第二自然,将人们引领进入理由的逻辑空间,使其拥有了概念能力,最终摆脱了单纯的动物性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即具有理性-概念能力和文化-德性素养的人。可以说,人类具有产生第二自然的先天能力,这种先天能力只有通过后天的教化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所以,教化(Bildung)促使了第二自然的形成。麦克道尔在《心灵与世界》中就第二自然的产生作了说明:
通过获得一种第二自然的方式让我们的眼睛向一般而言的理由张开。我想不出关于这一点的短小精悍的英文表达式,但它就是在德国哲学中作为教化而出现的东西。[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84,p.84,pp.87-88.
我们的自然大部分来说是第二自然,而我们的第二自然之所以处于它所处的那种状态,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生而具有的那些潜在能力,而且是因为我们的教养,我们的教化。[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84,p.84,pp.87-88.
在麦克道尔看来,“教化”这一范畴最充分地体现在德国哲学的传统中,特别是伽达默尔关于教化一词的分析颇具代表性,而且自己对教化的理解也是对伽达默尔的某种延续。伽达默尔从词源学和发生学两种视角阐明了教化概念的基本内涵。洪汉鼎先生在《真理与方法》第三部分的译注中指出,教化(Bildung)一词源自Bilden(形成),包含Bild(图像),而Bild既有Vorbild(范本)的意思,又有Nachbild(摹本)的意蕴,所以说,Bildung乃是按照范本进行摹写,也即按照人性理想进行教化或陶冶[注][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827页,参见附录30。。这种观点究其根源来自柏拉图,柏拉图的理念(eidos)原本指所看到的形相,德语用Urbild(原型)来翻译eidos;按照柏拉图的理解,理念是最真实最客观的存在,现实世界中的所有事物都是理念的摹本。新柏拉图主义也由此主张,世界万物是上帝根据其心灵中的原型、范式或模式所创造的;德国哲学家使用的Bildung一词就是沿着这一路径发展起来的。
除了从词源学角度分析教化一词外,伽达默尔还梳理了教化概念在哲学史上的演变过程。在他看来,教化是人文主义思潮中的主导范畴之一,这个词最初起源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Bildung对应的拉丁文是formatio,这是从forma(形式、形象)推导而来的。根据中世纪的神学观,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在自己的灵魂中已带有上帝的形象,而且自己必须在生活过程中去铸造和发展这种形象。这个词被巴洛克神秘教派所继承,而后德国诗人克洛普施托克(Friedrich Klopstock)在《弥赛亚》中赋予教化以宗教性的精神意旨,最后德国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赫尔德把教化与教育相关联,将人类的教育规定为“达到人性的崇高教化”。伽达默尔坦承,自己对教化的理解就是从这里得到启示的。
此后的18和19世纪,德国思想界日益关注教化概念,而且将其与修养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教化首先意指人类发展自己的天赋和能力的特有方式”[注][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赫尔德赋予教化概念的这一特征,直到康德和黑格尔那里才实现。康德虽然没有直接在上述意义上使用“教化”一词,但曾强调“培植(cultura)自己作为达成各种可能目的的手段的自然力量(精神的、灵魂的和肉体的力量),是人对自己的义务”[注]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页。,认为能力或天赋的修养是行为主体的一种自由活动,人对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就是不让自己的天赋退化或消失,因而需要提升自身的修养。黑格尔则在谈到人对自己的义务问题时采纳了康德的观点,并提出了自我造就和教化的观念。他指出:“哲学‘在教化中获得了其存在的前提条件’,……精神科学也是随着教化一起产生的,因为精神的存在是与教化观念本质上联系在一起的。”[注][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这说明,人之为人的终极体现是,人脱离了纯粹动物的直接性与本能性,而之所以能够脱离这种直接性与本能性,是因为人的本质具有理性的方面。因而,人本身需要教化,教化的结果就是从总体上维护人类的理性本质,使自己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存在。伽达默尔认为,教化不仅仅指修养,即能力或天赋的培养,因为对天赋的自然素质的训练与培养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单纯手段,教化更为重要的是对某种普遍性的追求,使人通过教化而变成其所是的东西。
麦克道尔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教化一词的,与伽达默尔不同的是,他进一步深化了对教化过程及其结果的讨论。在麦克道尔看来,我们以理性为条件,通过接受教化使人类的动物性逐渐褪去并走向“成熟”,使某人成为他自己,使动物的本性转变为人的本质;教化的结果就是获得以理性-概念能力为主要特征的第二自然,并形成某种思想和行为习惯。按照他的观点,教化的过程主要体现为教育的过程,教育中最为重要的是学习语言,这不仅是因为“一种自然语言,即人类成员最初被引领进的那种语言,充当着传统的一间仓库,即一间关于什么是什么的理由这件事情的历史地积累下来的智慧的储藏室”[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26,p.125.;更是因为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人类成员知道并理解了构成理由空间布局的概念之间的合理关联,由此进入理性的逻辑空间。所以说,学会使用语言是我们通过教化获得理性-概念能力并由此获取第二自然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鲁丁格·巴布纳(Rüdiger Bubner)认为:“从教化的观点看,麦克道尔捍卫了下面的观点:我们通过语言的学习才能获得进入理由空间的机会。”[注]Rüdiger Bubner,“Bildung and Second Nature”,in Reading McDowell:On Mind and World,Nicholas H.Smith e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p.213-214.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语言让自己向世界敞开,使自己与那些依据刺激和不能做出动作的动物行为区分开来,同时经由成熟过程让自己进入拥有知性的状态并熟悉了理由的空间,进而可以接受或提出经由自然语言系统化的理由。因此,学习语言的过程也是我们接受教化的过程,我们进入第二自然就是通过成熟和教育的过程来实现的,人类幼儿的教化结果便是成年人类的社会化。正如罗蒂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能够使用语词,我们就不具有概念能力;拥有概念能力恰恰就是能够使用语词;因此,对麦克道尔而言,将非人的世界视为对话伙伴的理由就显得十分重要[注]参见[美]理查德·罗蒂:《真理与进步》,杨玉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125页。。罗蒂的这种解读可以在麦克道尔的文本中找到根据:
人类成员不是这样的:他们生下来时是单纯的动物,而且他们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被转变成思想者和有意图的施动者。这种转变有着看上去很神秘的危险。但是,如果在我们有关教化——这是人类成员正常的成熟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的构想中给语言的学习以最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便可以从容地看待这种转变。在被引领进一种语言的过程中,一个人类成员便被介绍进了这样的某种东西,在他登上舞台之前,这种东西已经包含了存在于概念之间的那些一般认定为合理的关联,而这样的关联对于理由空间的布局来说一般认为是构成性的。[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26,p.125.
麦克道尔重视语言的学习,将学习语言视为教化的主要内容,并把学会使用语言与人们进入理由的逻辑空间以及第二自然的形成相关联,这与他关注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关于语言问题的讨论有着直接联系。麦克道尔说道:“我谈到由概念中介的心灵向世界的敞开,部分地是由对传统的继承构成的。我是受到伽达默尔的启发而援引传统的。”[注]John McDowell,The Engaged Intellec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34.他赞同伽达默尔的观点,世界对于人这个此在的呈现是通过语言来表述的,同时此在的在世具有原始语言性[注][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75页。,此在的生活方式是由语言形成并被决定的。或者说,人们通过接受教育学会使用带有共同体烙印的语言,并参与到语言文化共同体所建构的语言游戏之中,在其中语言行为被整合进入某种生活方式。教化就是通过语言的学习过程来使个体从幼儿走向成熟,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概念性能力,从而可以在语言文化共同体内部与其他成员开展对话和交流。麦克道尔将教育和教化的内容视为对传统的接续,意在说明对传统的继承是人与动物延续性的体现,是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相融洽的彰显,更是要表明概念能力可以被引入主体控制之外的感性运行中。概念能力在感性活动中的参与是自发的,我们要把这种自发的理性-概念活动视为合理的,就必须将其界定为人的某种自然属性,麦克道尔称其为“第二自然”,它是人在语言文化共同体中通过语言学习从传统中习得的。可以说,如果教化过程进展顺利,那我们通由教化所获得的区别于动物应对环境的理性-概念能力就构成了我们人类所特有的第二自然。
需要注意的是,教化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并可以教会人们学习使用语言,学会言说关于世界的普遍特征,使人们获得理性-概念能力,形成自己的第二自然,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教化要在同一个语言文化共同体内进行。因此,我们必须思考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标准问题。通常而言,判定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一是成员生理结构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即生活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人们的各种生理器官及其生理功能基本上相同,没有本质的差异;二是成员在心理意识层面具有普遍的公共性,即共同体成员在面对相关事物或事件时所产生的情绪、情感以及意识等方面的精神状态具有某种可理解的相似性;三是成员在文化传统与历史积淀的背景方面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相通性,即认知主体主要是指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属于同一个民族、操持同一种语言的人们,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文化教育的内容基本相同,所继承的风俗习惯基本一致,所熟悉的历史传统和历史积淀也基本雷同,在此基础上会形成相通的历史感、类似的民族感甚至是某种集体无意识;四是共同体成员无意识之间的相似性及差异性,主要包括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相似性以及差异性,由于人们之间因为品质、性格、个性乃至阅历等方面的不同而使自己区别于他人,而这种差异性存在于所有的认知主体中,因此也成为主体之间交流沟通的一部分[注]参见王海东:《原初句:语言、事实与心灵的联结点》,《云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我们将符合上述要求的成员所组成的团体称为同一种语言文化共同体,正是在这种共同体内,人们才能以教育的方式将传统的积淀、共同体的规范与法则灌输给下一代,进而使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熏陶成功地学会共同体的语言,掌握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习惯共同体的行为规范,进而使自己真正摆脱本能性,成为共同体的一员,熟悉并拥有第二自然并进入充满意义的理由的逻辑空间。
三、第二自然的自然主义
在麦克道尔看来,理性与自然的关系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是由近代科学的兴起和演进为自然祛魅导致的。特别是伴随着近现代科学的日益进步,自然的观念就是规律的领域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由此剥夺了可感世界与构成确定思想内容的理由空间的逻辑关联,使得感性输入何以与概念思维相结合变得难以理解,理性与自然成为两个相互分离、彼此对峙的领域。尽管自然在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中经常以目的论或意向论的方式被理解或描述,但自然科学的发展与进步总是以从自然中驱除理性、理由或意义为目的。虽然休谟对近代自然主义的祛魅效果作出了强烈回应,认为“我们不仅要否认自然具有意义的可理解性,而且要否认它具有规律的可理解性”[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7,p.97,p.109,p.85,pp.87-88.,但这种回应带来的结果却是理性被逐出自然的领域。按照麦克道尔的观点,这正是康德的知识论尤其是他提出概念与直观相互交织的思想真正要解决的问题。然而,与休谟不同的是,康德哲学旨在重新为自然赢得规律的可理解性而非意义的可理解性,或者说,对康德来说,自然依然是规律的领域,因此它缺乏意义与价值。如此一来,“真正的自发性就不能出现在对于自然能力的现实化本身的描述中了”[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7,p.97,p.109,p.85,pp.87-88.,那概念内容如何指及可感世界的知识论问题仍难以解决,我们依然要么陷入一种完全丢失了经验思想与实在之间关联的融贯论,要么走向一种无法为我们的经验思想提供合理性辩护的所予神话。
按照麦克道尔的观点,在应对理性与自然乃至心灵与世界关系的本体论问题上,我们应该避免三种不合理的思维方式。彻底的自然主义通过某种还原或建构的方式企图将理由空间合并在规律的领域中,将理性重构为现代科学的对象,忽视了理性思想不能被模型化为法则领域的进程,因为理性是在给出并满足行动与思想的理由的人类实践中展现自身的,如果我们将自然等同于自然科学希望使之变得可理解的东西的话,必然使我们陷入过渡祛魅的解释模式中,自然在此解释模式下只能是科学的领地和规律的领域而不是意义的家园[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7,p.97,p.109,p.85,pp.87-88.,并且容易陷入塞拉斯所警告的“自然主义的谬误”当中。戴维森的自然主义尽管保留了理由空间自成一类的特性,该特征充分体现了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显著要素,却割裂了理性与自然或者心灵与世界之间的理性联结,使我们的思想缺失了客观的内容,无法解释我们的知识在何种意义上还能说是关于世界的这一本体论难题。膨胀的柏拉图主义拒绝理性的自然化,承认理由的逻辑空间的真实性与至上性,虽然保证了理性空间的独特性,却使我们陷入了超自然主义(supernaturalism)甚至是神秘主义的窠臼,就连戴维森保留的自然与理性之间的因果联系也被柏拉图主义所遗弃,从而使必须在理由空间内完成的辩护、推论等彻底失去了然或世界的理性制约。因此,如果我们坚持把自然等同于法则的领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理性与自然的对立难题;如果我们把理由或意义的空间视为与可感世界完全无关,心灵与世界的理性联系问题同样无法回答。
麦克道尔既反对现代科学将自然与规律的领域相等同的观点,也主张摈弃近现代哲学将理性从自然中驱逐出去的做法;既承认人类成员就其自身而言首先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又主张人是自然的存在者更是自由的存在者;所以人类的自然性不能仅仅受法则的支配,理性(规范、意义乃至自由)不能被置于我们的动物自然之外。为了走出这样的死胡同,我们不能将规律领域的自然等同于自然的全部,不能把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看作是全部缺乏意义的,而需要将概念能力与自然的过程相融合,把理性(规范、意义乃至自由)与自然重新带回到一起。正是基于上述考虑,麦克道尔求助于亚里士多德关于第二天性的洞见,深化了对第二自然的理解。如果我们拥有了第二自然的概念,那便可以把自己视为“其自然渗透着理性的动物”[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7,p.97,p.109,p.85,pp.87-88.,如此就可以解决理性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分立问题。
在麦克道尔看来,我们通常理解的自然包括第一自然(规律的领域)和第二自然(理由或意义的领域),同样包括有理性的动物在内的所有动物的自然,也包含其第一自然(单纯的生物学现象)和第二自然(通过训练而获得的概念能力)。他进一步断言,人类成员的自然大部分来说是第二自然,即培育我们生而具有的能力与天赋并通过教化成为我们本性一部分的那些方面。若如此看待自然的话,那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便不再是全无意义的,其中构成我们的第二自然的部分是充满意义的;这样既承认了经过教化养成的规范领域的独特性,又没有将其放置在自然的范围之外,更没有将自然的领域与法则的领域完全等同。用麦克道尔的话说:“给定了第二自然的观念,我们便可以说,我们的生活被理性塑造的方式是自然的,即使我们否认理由空间的结构能够被整合进规律领域的布局之中,情况也是如此。”[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7,p.97,p.109,p.85,pp.87-88.麦克道尔将这种对于自然的理解称为“对自然的部分的重新施魅”(the partial re-enchantment of nature)。尽管我们对理由空间的回应被设想为一种自然现象,但这种回应不能被还原为自然科学所探讨的现象的状态,也不能被延伸至包括世间的举止,这些举止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样就避免了一种对自然的完全赋魅。麦克道尔把以这样的自然构想为基础的自然主义立场称为“第二自然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 of second nature)、“宽松的自然主义”(relaxed naturalism)和“自然化的柏拉图主义”(naturalized platonism)。这种自然主义与现代哲学中的“彻底的自然主义”“限制性的自然主义”(restrictive naturalism)和“科学主义的自然主义”(scientistic naturalism)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麦克道尔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将第二自然的自然主义立场的理论特征描述如下:
(1)否认将自然完全等同于法则的领域,因为自然除了第一自然之外还包括第二自然;
(2)承认理由空间具有独特的可理解性,而且这种可理解性不能也不需要还原为自然法则的领域。
这种自然主义调和了理性与自然的对立,使理性成为一种自然的事务。第二自然的自然主义能够有效地规避膨胀的柏拉图主义或超自然主义的困境,从而走出彻底的自然主义与膨胀的柏拉图主义之间的摆荡与循环。一方面,第二自然的自然主义仍然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尽管这一观点否认将自然完全等同于规律的领域,承认理由的逻辑空间的独特性,反对彻底的自然主义者所从事的那种建构性工作,并且“认识到我们的自然大部分说来是第二自然”[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1,p.95,p.88,p.92,p.178.,但它主张“人类的生活,我们的自然的存在方式,已经受到了意义的塑造”[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1,p.95,p.88,p.92,p.178.,并坚持教化使我们生而具有的某些潜能成为现实,从而认为第二自然实际上是我们人类第一自然中某些重要部分的现实化。所以,虽然理由空间的结构不能使用自然法则领域内的事实进行建构,但通过教化而发现的意义与价值却居于这个空间,“意义并不是一件来自自然之外的神秘之物”[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1,p.95,p.88,p.92,p.178.,自然既是意义的居所,也为理性提供限制。另一方面,第二自然的自然主义又是一种柏拉图主义。因为它承认“理由空间的结构拥有一种自律性”[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1,p.95,p.88,p.92,p.178.,承认自发性概念的独特性,认为自发性在一个不同于自然法则领域的结构框架内发挥作用,从而无法将自发性还原为法则的事实。但这种柏拉图主义不是“膨胀的”或“疯长的”,因为它主张“理由空间的结构并不是在与任何单纯人类性的东西极其隔绝的状态下而被构成的”[注]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91,p.95,p.88,p.92,p.178.,理性的需求并非神秘的和至高无上的,人类的教养可以让其成员的眼睛向这种需求张开。所以,麦克道尔将这种柏拉图主义称为“自然化的柏拉图主义”。
如此一来,麦克道尔通过丰富并创新第二自然的概念而走出的第二自然的自然主义这条道路,既确保了理性的逻辑空间与自然科学的描述所确立的关于物理事物的逻辑空间在结构上是不同的,即承认理由的逻辑空间结构的自治性;又使经验的思想恰恰就是关于某种自然的事物(世界)的思想,而且经验性思想可以对经验做出合理性应答,即自然应对理性思想提供合理性的限制;还明晰了拥有对理由或意义做出回应的能力(概念能力)是人类成熟的标识,而且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理由的逻辑空间最初必定是诸种自然力量的产品。按照这种观点,自然不再是单纯的动物性现象,也不是纯粹的规律的领域,它也包含规范的理由空间,也是意义和自由寄居的地方。自然一方面以因果作用的方式给我们施加影响从而获得印象,以经验描述的形式来反映世界向我们呈现的事实,保证了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又运用理性-概念能力将我们带入理由的逻辑空间之中,保证了心灵与世界之间的理性关系。可以说,麦克道尔的第二自然概念拓展了自然的内涵与外延,一定意义上消解了主体与客体、思想与世界、理性与自然之间的二元论的鸿沟,驱除了由于两种逻辑空间的区分而导致的哲学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