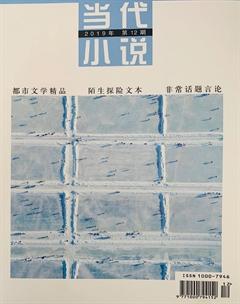天色将晚
柳喻
眼前的女人五十开外,着一件不合时宜的深紫色羽绒衣,戴一顶黑色贝蕾帽,脚上是黑色长靴。已经入春了,很少有人会如此装扮。女人迎着夏木摘下了口罩。出现在夏木面前的是一张历经岁月风霜,而又不减生活韵致的面孔。这种相貌绝非城市女性所有,从她沉着的气质上看,也不像是普通的乡间女性。女人的身上自然散发出一种淡定磁力,夏木心下不免一惊:奇怪,我怎么一见到她心里便不安起来了呢?
夏木将惊诧稍加掩饰,干巴巴站着,等待着故事发生。
女人可能觉得热了,干脆摘下了帽子。一圈盘绕在她头顶的黑色发辫立马将夏木的眼光吸引了过去。多好的头发啊。刚刚有些紧张的空气随着这一声心灵深处的赞叹而消散开去。
女人开口了。她先是叫了一声夏木的乳名儿,然后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她叫许青江。她一字一顿说,她是夏木的姨妈,而且是亲的。
这件事太匪夷所思了,夏木几乎要怀疑眼前女人的精神状况。她的生活中怎么会突然冒出个姨妈呢?别说是姨妈,夏木连母亲都没有。她的母亲过世已经二十年了。无论在母亲生前,还是在母亲过世后的二十年里,夏木从未曾听闻过母亲有什么姐妹。
可是,这个叫许青江的女人用沉着目光看着她,告诉她说:这是真的。
望着对方坚定的神态,夏木只好将她带到了报社附近的一家茶餐厅。无论真假,在报社门厅里认亲戚毕竟有些不合适。夏木是新闻工作者,她很清楚花边新闻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叫许青江的女人慢条斯理喝着茶,仿佛那碗茶是一段历史,需要她一点点去化解似的。对方身上涤荡起来的冷静气息再次让夏木不安。这神态,夏木想起来了,女人喝茶的神态像极了她的母亲。夏木望着旁边的廊柱,那上面镜子里恰好映出了女人的侧影。叫许青江的女人坐得很端直。夏木一直盯着她头顶的发辫。等女人再次开口说话的时候,夏木从她的音色里立马辨出了她母亲的音色。是啊,简直太像了。如果我的母亲活着,大约也是这么个样子吧。夏木想。
结果,许青江说:“霞哥儿,你长得和姐姐像得很哩。”这时候,夏木才发觉,女人一直在看着自己。女人目光沉静,带着五十岁女性特有的和缓和包容。
这么说,她应该是我母亲的妹妹了。夏木想。夏木的母亲离世时,夏木尚未成人。过了几年,夏木离家求学,后来又独自去了城市里生活。夏木素来不怎么喜欢亲戚往来。可以说,极少往来。她很清楚,对于她的家族往事,她不知道的很多。
夏木要了两份炒面。两个人都开始慢吞吞吃起来。似乎那一根根面条上凝结着诸多生活滋味,她们都需要一点点品咂一般。最后,面条都有点冷了,两个人都没有吃完,几乎同时放下了筷子。
服务生过来将盘子收走。许青江继续喝起茶来。喝完,她将杯子一直端在手里,用两只手不停地摩娑着杯子,仿佛在努力体验杯子的温度。
夏木的眼睛又望向了镜中黑色的发辫。许青江终于又说了起来:
“霞哥儿,你看人的眼神还和小时候一模一样。你很小的时候,我见过你两次,你就是这样歪着头看人,眼睛里好像有很多问题。”
夏木感觉到了对方冷灼的眼神,有点尴尬,于是正了正坐姿,也端起了茶杯。
她依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个叫许青江的女人。她和自己的母亲同姓,名字只相差一个字。
夏木说:“我的爹爹从未提到过你。”
许青江绕开了夏木话中的疑惑,问道:
“你爹爹还好吗?”
夏木说:“他老人家很好。”
许青江说:“那天在报纸上看到了你写姐姐的文章,上面还有你的名字和照片。我是来碰运气的,没想到真的中了彩。找一个人很难呐。我是专门从海西回来找你的。”
“海西?”
“是的,我一直生活在海西,快三十年了,这是第一次回来。”
“三十年了?”
“是啊,不知怎么就三十年过去了。我自己也想不明白。”
“我爹爹怎么从来不提这件事,好像从来没有过似的。”夏木叫服务生过来,又续了一壶水。许青江起身脱下了羽绒大衣,将衣服仔细叠了叠,搭到了旁边椅子上。
“你爹爹他不想提的事儿怕多着呢,过去的事儿并不见得件件美好,值得回忆,就像你写的文章那样。”
夏木明白了这个叫许青江的女人在指什么,那是一篇回忆自己母亲的文章。二十年了,她第一次将母亲写进了自己的文章中。对于她来说,回忆母亲是一个神圣的领域,她一直不敢轻易践足。在这篇文章里,她的母亲温婉、善良、勤劳、能干,几乎集一切美于一身。这篇文章的直接后果,就是她的面前出现了这个叫许青江的女人。
夏木注意到许青江没有带行李,于是问她住在哪里。
许青江说话很硬朗,毫不含糊其辞。她告诉夏木她是昨天晚上到达西宁,在宾馆住了一宿,一直等到夏木快下班了,才赶过来找。她不想去打搅三十年前的任何亲友。
夏木试探性地问她,想不想去父亲那里看看。
许青江拒绝了,她甚至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她的行踪。
她只想找夏木。很快,夏木知道了许青江找她的真正原因。她想让这个失散多年的外甥女儿找一找她三十年前丢失的小女兒。
女人语气很冷静,容不得半点置疑。她三言两语说明了一桩三十年前发生在夏木故宅的陈年旧事。
那时候,这个叫许青江的女人才二十五岁,她曾在夏木家住过一个月。就在这一个月里,她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女儿,然后迫于政策压力,将这个新生儿送了人。如今她老了,总是想起这个孩子,所以想托夏木找一找。
夏木一头雾水。这件事情似乎与自己的童年记忆毫不沾边。夏木一直坚信自己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在母亲离世前,她总觉得自己活在温情和快乐之中。她人生的孤寂无着就是从母亲的英年早逝开始的,所以,她的那篇忆母之文满是幸福而又伤怀的情愫。
“那段时间,你爹爹在牧区还没有回来,你去了外县亲戚家玩。再说,你那么小,肯定也记不得这些事。”这个叫许青江的女人又补充了几句。
夏木喃喃自语般说:“女儿,您是说您丢掉过一个女儿?”
“是的。”
“是在我家丢掉的?”
“是的。”
“现在您想把她找回来?”
“是的。”
望着夏木疑惑不解的眼神,这个叫许青江的女人用一种近似于委屈的声调说,在当时,这个女儿是非法出生,她不敢带着孩子回自己家去,也不好去外祖母家,何况外祖母只是她的继母,她着实无奈,总担心计划生育纠察队的人来找她,所以在孩子出生第三天的早上,她和夏木的母亲商量了一番,最终将孩子送了人。
“可是,我妈妈已经不在了。”夏木有些烦躁,她不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回忆母亲。
“我知道,你的文章里写了,姐姐已去世二十年了,我很难过。”在夏木看来,许青江的难过是真实的。这个叫许青江的女人在谈到夏木的母亲时,眼神中的平静不见了,继之而起的是一种空洞无着。女人没有流泪,夏木却已经感觉到了她心中的悲伤。
“姐姐是个好人。”女人无边无际说了一句。
夏木不喜欢用好和坏来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对自己的母亲,她拒绝任何评价。她想捍卫自己快乐的童年。
“您认为我能找到那孩子吗?”连夏木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这个问题有些尖刻。
许青江空洞的眼神中夹杂出一些黯淡,她用一种强大的意志力支撑着自己的情绪。
“以前的事情是说不清的。”许青江说,她的胸脯起伏了几下,很快又归为平静。多么顽强的意志力啊。夏木想。
夏木是个性情中人,她总是左右不了自己的情绪。
“您是说,是我妈妈送走了您刚刚出生的孩子?”不知为何,夏木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忐忑。她潜意识中一定认为,无论如何,送走别人的新生儿总归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何况人家现在找上门来了。
这次,这个叫许青江的女人没有说“是的”。她低眉垂首,有气无力叫了一声夏木的乳名,再一次说:以前的事情真的说不清。
“我的意思是说,是我妈妈私自送走了您刚出生的孩子吗?”在夏木的心目中,她的母亲一直至高无上,她从不容许任何人说母亲的不是。那是对她的一种冒犯,甚至是一种挑衅。面对挑衅,夏木总是会迎头而上,从不避让。此刻,这个突然而降的姨妈让她心里很不舒服,就像所有的不速之客一样,让她的生活出现了杂音。她不喜欢突然切入的事物。夏木端起杯子“咕咚咕咚”猛喝了几口,又用温巾仔细地擦了擦桌面。桌面上其实一无所有,可她总感觉有些污渍让她别扭。夏木有点强迫症倾向。
许青江明显感知到了夏木身上传递出来的不和谐气息。她不再摩挲杯子。她将杯子放回到桌上,继续用她的那种冷静语调说:
“是我让你妈妈送走的,那个时代不一样,你知道的,有些事情毫无办法。我们都害怕极了。不像是生了人,倒像是杀了人。起初,你妈妈一直不愿意,是我求着她把那孩子送走的。那段时间太可怕了,听见鸟叫声,我都以为是纠察队的人来抓我了。”许青江又开始喝茶,夏木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惶恐和不安。
夏木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的问题无非如此:我妈妈肯定告诉过您,那孩子送到了哪里了吧。
让夏木吃惊的是,许青江对此一无所知。这位有着一头盘发的姨妈摇了摇头,用一种陈述事实的无奈语气告诉夏木,她什么都不知道。
眼前的这座小镇叫塔镇,因为有一座存世六百余年的寺院而名闻于世,夏木走在塔镇最古老的泉涌街上,两边全是各色商铺。经过一家接一家的铜器、银器作坊,从一道道五颜六色的披肩阵中穿过去,夏木看到她的父亲正端坐在色彩更为绚丽的瓷器中,慢慢地数着他的念珠儿。自打母亲去世后,父亲迷上了念珠,这串紫檀珠子时而挂在父亲脖子上,时而在他手中缓缓转动。父亲戴着一顶宽檐礼帽,兀自沉浸在他的心灵世界里,并没有看见女儿的到来。
夏木叫了一声爹爹,父亲看见了女儿,喜悦一下子浮上眉梢。和所有的亲人重逢一样,他们互道平安,絮了几句家常话。父亲谈起了这段时间的生意,很快,父亲的话题拐到了他年轻时在草原上生活的光景。夏木发现,父亲最近几年很怀念昔日时光。
母亲离世后,夏木和父亲并没有形成相依为命的父女关系,而是各怀心事,越来越客气起来。
夏木说:“爹爹,那时候你总是不在家,家里就妈妈和我。”
父亲的念珠儿一直转着,像一段时光缓缓流淌。父亲说:“是啊,那些年可苦了你妈妈了。”
夏木愣了愣神,说:“爹爹,三十年前,我的妈妈有个妹妹,是吗?”连夏木自己都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她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呢,这话已经自己跑了出来。
父亲显然怔住了。他谈起旧友时平静而又惋惜的目光不见了。在愣怔的同时,父亲的眼睛里塞满了悲苦。父亲在努力掩饰这种悲苦,但他终究没有掩饰住。
父亲站起身,将佛珠捧至手中,仔细端详了几秒钟,然后放至一尊佛像前。可能是有点冷了,父亲从衣架上取下了一截围巾围到了脖子上。夏木以为父亲要出去,也站了起来。没有母亲的烦恼一下子盈袭而至,夏木感到孤立无援。最近,她总是思念母亲。
父亲并没有出门,他只是走了两步,拿起店门口的一截牛尾拂尘,扑了扑挂毯上的灰,又折身坐了下来。
“霞哥儿,你姨妈在哪里?”父亲直接问道。这些年,父亲极少叫夏木的乳名。夏木几乎被从父亲嘴里冒出来的这三个字扎了一下。
这个问题终究要来。本来夏木打算回答得委婉一些,能不提的就不提,而此时此境,父亲的不安冲击到了她的表达。她不愿意对父亲撒谎。她很清楚,撒谎会对父亲造成伤害。她望了望对面的街。那位托尔斯泰般的老友依舊在晨光熹微下端坐,他的目光似乎一直在看向这里。
夏木只好实言相告。从昨日午后一直到今早出发,所有的故事现在她都交给了父亲。她没有半点含糊其辞。比之姨妈许青江,比之已离世多年的母亲,她更愿意维护父亲的情感。
“噢,是吗?”父亲简单地说了几个字,便一语不发,枯坐起来。随着时间的点点流逝,夏木明显感觉到了父亲身上在升起一种火气。刚刚在晨阳下静谧的阳光开始摇摇晃晃,像强烈的白炽灯光,发出清冷之色。
“爹爹,我一直不知道我还有个姨妈。”夏木有气无力地说。早晨离家的时候,姨妈许青江送她到门口。她回望时,姨妈依旧在看她的背影。从那刻开始,夏木心中升起了一种暖暖的亲情。
这时候,父亲的眼光着实让夏木诧异。宁静消失了,不安也消失了,夏木从父亲的眼中感到了不加掩饰的凛冽之气。“你是说,她回来找那个小娃娃?”
夏木有些委屈。她不知道该怎样去迎接父亲的这种置疑。父亲一向沉默寡言。父亲再怎样对女儿客气,夏木也从未领略过父亲的凛冽之气。
“爹爹,姨妈说,她只要远远看一眼就行。”
父亲抬起右手抹了一把脸,然后将手放在下巴上,一直望着店铺外的街面。外面行人已开始多了起来,光线很强,夏木看到空气中悬浮着一些灰尘。
“她可是把你妈妈害苦了。”这句话意外之极。更意外的是,夏木看到父亲的眼睛有点蒙眬起来。夏木从未看见过父亲流泪。父亲也绝少埋怨人,就连命运的不公也绝少去评说。父亲逆来顺受惯了,而现在忽然指责起人来,让夏木一下子无所适从。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夏木像找话茬似的说:“爹爹,姨妈说,妈妈将那个小娃娃送走的时候,她是同意的。妈妈没有做错什么,也是不得已,那时政策不允许超生。”
父亲的目光依旧凛冽,像带着锐利的时光之刃。“她是这样跟你说的吗?”
夏木不知道父亲错在了哪里,只好再度用委屈的语调说:
“是的,她说她和妈妈合计了一晚上,才决定将那个娃娃送走的。”
“亏她能说出这样的话。”父亲干脆抬起右手,蒙住了两只眼睛。
夏木茫然无措,对母亲的思念夹杂着对漫长生活的隐忍。过了半晌,父亲缓缓说道:
“青江我想她也是有些苦衷吧,她从来不是一个狠心肠的人。有时候人也会由不得自己。”父亲的话有些宽慰自己。原来他一直在说服自己接受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东西。
“爹爹,那时候计划生育抓得严,妈妈和姨妈害怕得很,一定是万不得已才想到把娃娃送走的。”夏木用自己的思维理念解释着她一无所知的人世情缘。
“噢,她总是很有理由,有些事儿没有个说法怎么行,可事实上,那个娃娃好几次差点死在她手里。当初,如果不是你妈妈救下来,她那娃娃生下来就死了。”
故事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呈现出不一样的特质。夏木抿了抿干涩的嘴唇,用一种交织着不解和讶异的眼神看着老父亲,直到父亲说:你瞧你这个丫头,多大了呀,还爱这样偏着头看人,看得人心里难受。
姨妈许青江的样子浮现出来。在那圈乌黑发辫下的面庞沧桑而又坚定,容不得半丝含糊。怎么她的故事到了父亲这儿就不可理喻了呢。我是不是忽略了什么?夏木努力回想着,依然一无所获。这么说来,姨妈许青江并没有向她说实话,抑或说,这位姨妈实有难言之隐。
父亲一直在擦拭一只银壶。那把壶已经上了年头了,在父亲的擦拭下,好像又获得了新生一般,发出柔润的光泽。“那娃娃是被你妈妈送走的,可你妈妈是为了救那个娃娃呀。自从生了那孩子,你青江姨妈性情大变。那孩子是天擦黑的时候生的,生下后,你妈妈去了一趟院子,进屋的时候,看见你青江姨正用两只手掐那个娃娃。幸亏她刚生完孩子没力气,你妈妈将孩子从她手底下抢出来时,孩子还有气儿。后来你妈妈将孩子抱到了阁楼上。第二天天擦黑时,你妈妈做完饭进屋,没看见你青江姨,找到阁楼上,正好看见你青江姨居然将孩子抓起来扔到了地上。你妈妈害怕极了,所以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抱了孩子去了城里。连我也不知道那孩子送到了什么样的人家。这种事情,你妈妈自己不想说,谁也不好问。就是你妈妈,她也只跟我说过一次。”
这件事听起来未免太离谱了。夏木一时无法将昨日遇到的姨妈和父亲回忆中的姨妈联系起来。这分明就是两种人嘛。一个冷静之极,一个又狂躁不已。她相信父亲所讲的故事。她的父亲从不说假话。如果父亲不想说实话,他便会选择沉默不语。
“可是,爹爹,姨妈为什么要那么做?”
“谁知道哩,女人的心思谁知道哩。打那之后,青江两口子带着大丫头去了海西,再也没回来过。这样绝情的人倒也真少见。你妈妈伤透了心,着了病,过了几年,四十岁头上便没了。”
父亲起身披了一件外衣,这才想起了奶茶。他将茶壶放在炉子上烧了烧,倒了两碗。
奶茶很好喝,带着草原青草的气息。蒸汽腾腾的奶茶稍許化解了一下夏木心中的压抑。
女儿身上固有一种探索的精神,凡事一经上手,就爱打破砂锅问到底。父亲不太想为难女儿,于是说:“有些事儿想讲出个道理,是谁也讲不明白的,事情无非就是那样发生了罢了。青江没结婚的时候,到家里来过两次,又能干又懂事理。她成家后,我正好去了乌兰,倒再也没见过她。我想人再怎么变,大样儿不会变。可那一个月的事,总叫人想不明白。天擦黑时,你妈妈心情便不好,不爱在屋里呆着。有时候很晚了,她都不愿意将大门闩起来。你妈妈好像很怕闩门。那年月,超生了,大不了罚款。庄子里哪个家里没有个多生的娃娃。乡里人管不了那么多事的,吃肚子要紧哩。可也没有青江那样的。算啦,这些事情真的想多了没用。只要青江她过得好就行。”
此刻,塔镇已完全苏醒。街上到处是三三两两的行人。这个地方的茶马生意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了,到今天还没有中断。夏木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些年,她的父亲也绝少和亲戚们往来。父亲的人际关系几乎全部来自于这小小的泉涌街。也许正是这里的异质文化,才让父亲不至于太多地咀嚼历史吧。谁知道呢。不过,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是,夏木现在面临的绝非是意外获得了一份姨妈的亲情,尽管她渴望来自母系的亲情很久了。眼前的事分明不光是要找回一个毫无线索的孩子,而且明摆着要去化解一场冻结在时光深处的恩怨。问题的关键是,这是非恩怨似乎已很难讲明白。
姨妈许青江的故事里,那个孩子之所以被送走,完全是因为不符合政策。她和母亲害怕纠察队的人找上门来。这个故事的疑点是: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已是完整的生命体,纠察队的人来了也无非是罚款而已,何至于天未亮就将孩子匆匆送了人。又不是赵氏孤儿,到处逢人追杀。
父亲的故事里,姨媽几乎从担惊受怕的弱者一变为悍妇。仿佛那孩子是她的仇人,她分分钟都想置孩子于死地。而夏木的母亲是为了保护那孩子才将孩子送走。这个故事的疑点是:母亲怎么会因为这件事而落下沉疴呢。那年头,送走个把孩子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夏木小时候经常听闻这种事儿,有一次,她甚至在供销社门口遇到过别人遗弃的婴儿。
夏木想:回忆可真能骗人。在她的一番回忆里,她的母亲一向性情过于严谨,从不儿女情长。她几乎想不起来母亲几时拉过她的手,几时抱过她。而在另一番回忆里,母亲又是一位天使,温暖,平和,使她总觉得幼年的自己总是罩在幸福的光环里。
无论如何,夏木总是思念母亲。唯有这一点是真实的。
这天傍晚,夏木回到家中。姨妈许青江的表情告诉她:她知道夏木今天注定一无所获。
家中一改往日的凌乱,变得异常干净整洁。散落在客厅里的衣物全都不见了踪影,沙发罩散发出刚刚清洁过的爽朗气息。花修剪过了,错落有致地摆在客厅里,所有的书籍整齐划一,码放在书桌的一角,原本灰突突的地板散发出木质纹理的光泽,连夏木平时穿的拖鞋也干干净净摆在门口。一缕亲情瞬间在夏木胸膈间升腾而起。她发了一会儿呆,这才进到屋里来。
“你和姐姐不一样。”姨妈许青江说,一边接过夏木的手提袋。
“是的,妈妈绝不允许家里乱。”夏木说的是实情。她说这句话时,心里怀着对母亲的歉意。她想,等闲下来一定学着操持操持家务。
“你爹爹都好吧?”姨妈许青江问。
“好着呢。”
“你爹爹不知道那孩子的下落吧?”
“是的。”
“我想,姐姐不会说的。姐姐性格太要强了。”
这一点夏木承认。
夏木心中有困惑,她欲言又止。
黄昏很快来临,最后一抺西晒消失了。
华灯亮了起来。姨妈许青江望着对面楼体上的霓虹灯,不由再次感叹起来:多好啊,这么多的灯。
夏木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在她遥远的记忆里,她的母亲一向很节俭,可是,在一个习惯上几乎达到了奢侈的地步。但凡光线暗,或者天色近晚,她的母亲就会将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
“如果没有灯,天黑下来的时候,心里可真难受啊。”姨妈许青江像个多情的少女一样发着一系列的感慨。
夏木说:“妈妈也喜欢灯火明亮的样子。”
是的。这两个字又从姨妈许青江的嘴里滑了出来。她好像很享受这两个字,准备着随时说出来似的。
黑夜完全降临下来之后,姨妈许青江终于再次提到了三十年前的岁月。
她太害怕了,许青江说,自打那个小娃娃出生后,她一直担惊受怕,总是怕别人来抓她,怎么也睡不着。那两天,她又困又累,只想好好地睡一觉。
夏木明白了。失眠也时常困扰着她。在持续失眠的情况下,人的意志力很有可能会出现崩溃。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姨妈许青江那两天出现反常举止,完全是因为持续的失眠所致呢?这似乎也说得通。夏木的性情中有一种倾向,她能包容所有的个性和怪异之举。她想像着母亲那几日的煎熬,恨自己生得太晚,无法为母亲解围。
“那天,天还没亮,姐姐抱着孩子出了门。我听见姐姐将大门从外边锁上了,几乎是在锁子锁上的同时,我睡着了,那一觉我睡了两天两夜。”
姨妈许青江手里一直在缝补着什么。夏木这才看清,她缝的是一只枕套。她有些奇怪家里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件物品。有些眼熟,可她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瞧,这些东西放着多可惜,东西得用起来才行。这上面的花样还是姐姐绣的哩。”姨妈许青江手底下抖开的是一件手工艺品。夏木终于想起来了,这件物品来自于母亲的一只小箱笼。这些年,东奔西跑,夏木总是丢三落四,唯独一直带着这只小箱笼。作为母亲的独生女儿,她很惭愧。她极少去打开那只箱笼。她对针线活计没有兴趣。
“你的妈妈没有错。”许青江说。
我的妈妈当然没有错,她能有什么错,还不都是你闹的。夏木想。
“我知道姐姐是为我好。”
这还有什么可置疑的呢。
“我也一直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了,自己心里有个坎怎么也过不去。什么事情我都能看开,唯独这件事情我看不开。那之后,我和娘家所有亲戚断了来往。我不愿意和任何以前认识的人说话,所以搬家去了海西。在戈壁滩地窝子里住了两年,后来政府安居到了定居点,这才算有了个家。刚开始种啥啥不成,苦日子过了七八年,你姨父几次打算搬回来,可我一想到回来,就会想到孩子送走的那一晚夕,我就会心里烦躁,怎么也控制不了。后来,我想,算啦,在哪儿还不是熬日子。”
也许这就是真相吧。夏木感觉自己明白了一切。不过,不知为何,她心里依然感到有个地方不对劲儿。
很快,姨妈许青江做了解答:女人的事,谁能说得明白哩。我不明白,你不明白,姐姐她更说不明白。
姨妈许青江勉强笑了笑,夏木发现,她笑的时候,两个浅浅的酒窝浮在面颊上,给这位老妇人平添了一份妩媚。也许我的母亲笑起来也是这个样子吧。自打写了追忆母亲的文章后,她对母亲的思念便再也停歇不下来了。她望着姨妈许青江略显苍白的笑容,不由产生了一种时空恍惚感。在她的错觉里,过去和今天交叠在一起,她着实分不清昨夕与今朝了。
第三天是星期六,夏木不用去上班。早晨,她陪着姨妈许青江去了一趟南禅寺。一路上,两人都不说话。夏木只管专注地开着车。姨妈许青江静默不语,一直望着窗外出神。这是四月初,街道两侧迎春、山桃正竞相盛开,空气很明净。经过南山脚下一栋楼盘时,姨妈许青江让夏木停下车。夏木不解,不过,她还是将车停了下来。许青江说,应该就是这儿,错不了,从这个角度看上去,正好可以看到金顶。
夏木问是什么金顶。后来她才知道,原来这儿曾经是姨妈许青江的家。三十年前,她在这里生活了六年,生下了她的大女儿。
与其说是吃惊,不如说是伤痛。夏木的心不由揪痛起来。这个地方,如今寸土寸金,老住户们全都富甲一方。
“十年前,你姨父回来过一次,弟兄们闹翻了,他什么也没能要回来。后来我们都认命了。”姨妈许青江望了一下那片楼宇说,“那时候,不得不走,离开你家后,我便一直病着,不是身体上的病,身体倒一直很好。就是不想吃饭,不想说话,不想见人,也不想睡觉,慢慢地厌世起来。这才一家子搬去了海西。”
难道这就是她三番两次想杀死自己新生儿的缘故吗?夏木心想。似乎这样解释也错不了,可夏木望着车窗外一地的阳光,依然疑惑重重。一切似乎都能说得通,又似乎不堪一击。
“昨日你爹爹一定和你说了吧?”许青江问。
夏木知道她问的是什么,于是说了一声:是的。
“我想姐姐她一定是心里很苦的。”这句话有点莫名其妙。姨妈许青江不说自己心里苦,偏要说姐姐心里苦。到底用意何在?此时此境,山寺在前,街市喧嚣,她不知道该怎样去承接母亲心中的苦楚。一切全打乱了,包括她在欢歌笑语中长大的童年。
“那段时日,其实我不是故意不想说话,我是想和姐姐说话的,可我张开嘴,话根本说不出来。姐姐一定是以为我是生她的气,故意不说话的。不是的。是我莫名其妙变成了哑巴。我离开你家的那天早上,姐姐一直站在院子里,你家院子里的苹果树全开了花,姐姐就站在苹果树下,眼泪一直往下掉,她也不擦,也不说话。我望了望她,从她身边走了过去。我想叫一声姐姐来着。我们没有亲妈,姐姐是最疼我的人。可我张开口发不出声音来。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啦,我没有办法让姐姐明白这件事。我就那样走出了你家院子,走出了大门。我回到自己家,依然无法说话。你姨父从海西开荒回来,看到这个样子,才将家整个搬去了海西。车放这里没事吧。也行吧。我们走上去。没想到这山上全是楼梯,从前不是这样的。这儿院子本来是他们弟兄两个住着,说好的,往后回来,我们还住那院里,谁知道后来赶上征地拆迁,他弟兄将原来老房子全拆了,新起了楼房,就这样这院子便和我们无关了。据说后来他弟兄得了五百多万。我们什么也没有要回来。没有凭据。我到海西后,慢慢能说话了,苦日子也熬过去了。只是一想起我走那天,姐姐站在苹果树下的样子,这心便塌了。”
这三十年前的老故事,此刻又出现了新情况。夏木如坠云海雾里。不就是个超生嘛,怎么会改变了这么多人的命运?她想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古话来。此时细细品味,便觉此话很耐人寻味。她对母亲的追忆里一定缺了什么。是的,她一直在规避往昔岁月的不和谐音调。作为女儿,她应该接纳母亲的伤痛、母亲的泪水才对。那才是她真实可触的母亲啊。
姨妈许青江在南禅寺里像个虔诚的居士一样,敬香,磕头。朴素而又古老的仪式结束后,她们一起慢慢下山。路过那片楼宇时,姨妈许青江走得很快,没有再看一眼。那脚步在夏木看来,似乎是要丢掉过去,轻轻巧巧往前走。
夏木不明白菊仙为什么会让她在这里等着。夏木身上有一种执拗劲儿,只要她想做成什么事,她便會不顾一切,努力去做。比如此刻。昨日从南禅寺回来后,姨妈许青江隐隐约约向夏木提了提,不想再找那个孩子了。可夏木不依。她一定要找找看。后来在她不断地追忆旧时光的过程中,她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姑奶奶。姑奶奶已不在人世了,她的女儿菊仙在。菊仙曾和夏木的母亲亲如姐妹,或许菊仙能知道点线索。于是,这天早晨,夏木再次出现在塔镇。如菊仙所约,她站在一片广场边等着这位姑奶奶的女儿。
阳光下的塔镇再度摇摇晃晃起来。呀,这地方,夏木辨清方向后立马想了起来。这地方曾经也是她童年梦的一部分。
带着梦的痕迹,这位叫菊仙的女子踩着阳光出现在了夏木的视野里。好像真的是从时光隧道里走出来的啊。夏木感叹了一声。
“霞哥儿,好久不见了啊,有十几年了吧。”菊仙身上带着乡村女性特有的热忱。好一番嘘寒问暖,最后问得夏木都有些不自在。亲情很快建立了起来。
这个地方有一种独特的气息让夏木心旌摇曳。夏木眯着眼睛望着广场。
“对哩,这儿以前是电影院,都拆了好几年了,你总是不大爱关心这些。”
原来这儿就是曾经的电影院呐。夏木望着前方,有些发呆。
菊仙说:“那时候你妈妈总爱赶时髦,我们在这里看过两次电影呢。”
这么说,那些记忆并不是梦。在夏木好多次的梦里,母亲带着她在这里看电影。她的母亲总是渴望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霞哥儿,你知道你妈妈最喜欢哪部电影吗?”菊仙原本走在前面,这时,停下来,回头问夏木。
夏木摇了摇头,她连母亲曾带她看过什么电影都想不起来。菊仙告诉了她答案,她的母亲最喜欢《庐山恋》。
夏木不由眼睛湿润起来。我的母亲总归有些不一样的。现在,连她自己都觉得她那篇回忆母亲的文章写得真是太浅薄了。
经过一家土产用品商店时,菊仙停了下来。她打算在这里买点东西。
小店里光线有点黯淡,夏木进去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里面货架上摆满了各色实用物品。像昔日的供销社一样,小店里还将好多物品放在木制柜台里。得拒绝多少次的随波逐流,才能将这一古老的营销风格存留下来呢。一位着青衣的女子走了出来,面色白净,衣着雅洁。她望了望夏木和菊仙,径直走到菊仙身旁,拉起菊仙的胳膊,打起了招呼。她的打招呼完全表现在肢体语言和神态举止上。她用一只手一直抓着菊仙的胳膊,用另一只手快速地比划着,表达着自己快乐的心意。原来是一位聋哑人。夏木有点蒙了,想不明白这位青衣女子到底是顾客,还是这家小商铺的主人。她从未见过聋哑人开店。
对母亲的思念夹杂着对过往岁月的悲情理解,使夏木的心境如陷谷地。这个小店岁月斑驳的痕迹如此之重,让夏木几近怀疑时光的流逝。
一番亲热的肢体语言见面礼结束之后,青衣女子回到了柜台后面,从横隔下抬出来一只小木箱。古旧的箱笼上绘有几笔简单的写意兰花。青衣女子掀起盖子,哗一下,里面恍如打开了百宝盒。很快,形态各异的花样刺绣物件摆满了柜台。菊仙随手拿了两样。青衣女子拿出旧报纸包裹起来。后来两个人又用肢体语言推让了许久。一个执意付钱,一个执意不肯收。最后菊仙直接将钱塞进了青衣女子的衣兜里,又拉了拉青衣女子的手,算是一种告别。青衣女子眉目清秀,全然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夏木被青衣女子身上这种淡然的表情吸引住了。快走出小店时,她不由回望了一眼。就在她回望的当儿,她差点尖叫起来。夏木这才发现店里还有另外一个人。此人坐在一只矮凳上,在努力擦拭一只老式石英钟。夏木发现他的时候,这位拭钟人正好抬头看她。拭钟人看夏木的表情也是异常淡定。只那么静静的一两秒钟,他又继续干起活来。他的一只眼睛是盲的。
夏木产生一种穿越时空、无所适从的惶恐感。她快步走了出来,迎上菊仙的步伐。
菊仙的家在塔镇北门外。菊仙的身上依然保留着一些乡间的旧礼俗。尽管时间还早,菊仙依然用张罗饭菜表达亲戚到来的热情。
春阳下的小院落自有一番安逸,夏木简单说明了来意。
菊仙正在择菜,一语不发,听完了夏木的话,然后将菜放至一边,发起愣来。半晌,她恢复了生气。在夏木看来,她恢复得似乎有些过了头。
菊仙的话里透着一股子强硬。她说:
“霞哥儿,你这不是让你妈妈不安生吗?”
不安生,这怎么会让已经逝去的母亲不安生呢。夏木心里有些疑惑,但她没有问出来。
“姨妈想孩子嘛,这也是人之常情啊!”夏木带着软弱的辩护语气说。
“你妈妈都走了二十年了,这件事再也没有人提了,原以为就这样过去了,谁承想你又跑来寻根问底。以前的事儿是说不清的。有些事儿说清楚说不清楚都是一回事儿。”菊仙带着明显的恼怒情绪。夏木茫然不知所措,想不到重提历史会如此伤人。对父亲是一种伤害,对菊仙也是一种伤害。夏木不明白这种伤害的力量从何而来。难道每个人都是将重重伤害掩埋在历史中前行吗?
“青江姨妈这些年很不容易。”夏木说。
“是吗?”菊仙的语气很快和缓了下来。“那年头很落后,社会落后,人也落后,孩子说生就能生下来,很多人家都往外送过孩子哩。送了也就送了。如果谁都想把送出去的孩子找回来,这世界岂不乱了套了。”
夏木说:“小姨,青江姨妈说,她只要远远看一眼就行。”
菊仙说:“那还不是一样吗?”
夏木不语。
菊仙说:“她就不该到你家去生孩子。”
这么说,姨妈许青江依然在隐瞒着什么。那么,当年她执意远行到底是为了什么?她如今回来又到底是为了什么?还有,父亲怎么会将母亲生病一事归罪到姨妈身上呢?
夏木执拗劲儿上来了。她的心里带着一种火热的受伤气息。她想压住,可终究没能压住。“小姨,我妈妈和你提过那两天的事儿,是吗?”
菊仙的火气明显平息了下去。她叹了一口气说:“送那娃娃的时候,我和你妈妈在一起哩。”
夏木始料未及。“你在我家里?”
菊仙摇了摇头,她又开始择菜,择了几下,又放至一边。
“都三十年了,那件事儿怎么也忘不掉。那年开春,天气还冷得很。那天,天还没有亮,我和你姑奶奶听见外面在打门。打开门,是你妈妈,怀里抱着一个小娃娃。我和你姑奶奶吓了一大跳,一问才知是青江姐姐的孩子。你妈妈的意思是,将那小娃娃先放在我家里,等过一阵子再想辦法。那天,正好我的姑妈来了。她说,这娃娃这样下去养不活,然后抱去了塔镇,送给了一户人家。我和你妈妈回到你家,你那青江姨一直在睡觉。她居然睡了两天两夜,醒来后,她开始吃饭,但你青江姨心硬得很,她再也不肯说一句话。她就那样一句话不说,在你家住了一个月。有一天早晨,也是一句话都没说,离开了你家。这件事情可伤透了你妈妈的心。”
这段故事倒也没什么新奇,在此刻的夏木听来,已不新鲜。只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同罢了。
夏木说:“在当时的年代里,这件事情也不算是什么事情吧?”夏木觉得母亲实在没必要那么伤心。
菊仙说:“将孩子送走也许没什么大不了,可两姐妹恩断义绝却是一件大事,你妈妈就这一个妹妹。”
夏木为难了一会儿,最后还是问了出来:你的姑妈还在吧?
在夏木看来,这应该是唯一的希望了。
菊仙没有回答,而是说:“你们啊,全都这样执拗,你执拗,你爹爹执拗,你妈妈执拗,青江姐更别提了。我的姑妈已走了七八年了。”
菊仙说话语速很快,几句话就将夏木带到了灰暗之中。一种挫折感升上心来,夏木端起茶杯猛喝了几口。
菊仙起身,将夏木的茶杯重新注满了水。两个人都看着茶叶在杯中翻腾,最后归于宁静。
“过去的事儿翻腾出来不好。”菊仙似乎下了决心。
上一次见菊仙是什么时候呢。夏木想。
对啦,应该是二十年前,是在母亲的葬礼上。没错,就是在母亲的葬礼上,夏木告别了自己的童年,告别了众亲友。其实,她何尝不是一去不返。只是她的一去不返披着一层求学的外衣,有外在形式上的光环在,所以让她的绝情动机不那么露骨罢了。再一想,母亲的离世何尝不是一种绝情呢。人人都在绝情而去,为什么唯有姨妈许青江在受到谴责。
“你妈妈心气儿太高了。”菊仙说。
这一点夏木承认,她喜欢母亲的心气儿高。在她看来,心气儿高是一种美才对。夏木喜欢母亲身上这些特别的性情。母亲的酷爱整洁,母亲的讲究生活品位,在夏木的心中,永远带着一层美的光环。在那篇回忆母亲的文章里,她提到了母亲的一丝不苟,还有母亲离开人世时的依依惜别。而现在,夏木却觉出了异样的味道……难道母亲真的是绝情而去吗?
“那时候,农村里文盲多,妇女们都没文化,你妈妈念过书,村子里便选她当了妇女主任。你想啊,你妈妈心气儿那么高,样样事儿都要走在最前面。她当妇女主任那几年,正好是计划生育抓得最严的年头。你妈妈整日里跑东家跑西家,做思想工作,得罪了很多人。偏偏你青江姨妈躲纠察队的人,躲到了你家里来。她也是没别的地方可去。她原本想的是在你家悄悄把娃娃生下来,再回到城里自己家就没事了,大不了罚款罢了。她家里条件又好,不用担心罚款。这件事,你的妈妈一直瞒着人。那晚擦黑,娃娃终于生了下来,是个女娃娃,特别能哭。你的妈妈一直将门从里面闩着,可还是叫隔壁的媳妇子发现了。这下子,庄子里那些怀了超生娃娃的媳妇们不干了,合起伙来,去找你妈妈。你妈妈一直不开门,她们就拿石头往你家院里扔,骂得很难听。有两个女人还说,也要来你家生娃娃。她们在你家门外直闹到天黑透了才回去。第二天傍晚,这几个媳妇歇了工,又合起伙来,到了你家门外。她们又是砸门又是骂,扔了很多土块到你家院子里。看你妈妈还不开门,她们居然点了一支火把扔了进来。你想,我们这儿开春,气候多干燥啊,最见不得火星。你妈妈捡起火把,打开了门,她没有骂人,而是说,都回去睡觉去,一个个挺着大肚子,也不忌讳,像什么样子。有什么事情明天天亮了过来说。女人们依旧不走,还在骂。你妈妈挥了挥手中的火把说,如果明晚夕你们过来,我家的大门还拴着的话,你们就用这火把点了我家的房子。我不怪你们。说完,你妈妈将火把扔到了水渠里,然后又从里面闩上了门。”
母亲紧闭嘴唇,决定事务时要强的面孔在夏木面前倏忽一闪。在夏木幼年的记忆里,母亲一旦抉择了事情,任何人都改变不了。
“妈妈后来不再操心村里的事务,原来是这个缘故啊。”这两天,痛夹杂着辛酸和无奈一直在咬噬着夏木的心。她的心原本是麻木的,而经过了这两日的不断咬噬,仿佛苏醒了。她终于明白了自己何以绝情。她并不是想紧紧抓住童年的那点小快乐不放,而是这生活的真实表里太让她喘不过气来。她唯有逃避,才有力量自由地呼吸。她很清楚,就连她自己说不定也时刻面临着失语的危险。是啊,当一样事物的说不清楚达到极致的时候,恐怕只有失语才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你青江姨走后,你妈妈便辞去了村里的工作。其实,你妈妈一直很喜欢操心事务。她心里总是有些抱负的。”
母亲的小小抱负在此时的夏木看来,和那支暗夜里的火把一样,照亮了母亲的面孔,却又在风中闪烁不定。那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啊。门里面是刚刚生完孩子,在重重压力下已经情绪失控,时刻想杀死自己新生儿的妹妹,而大门外,母亲举着火把,站在风口里,她的前面是身怀六甲却又愤怒不已的乡邻们。这件事,母亲显然没有向父亲提及。母亲心性要强,她一定是将这件事自我化解掉了。所以,在父亲的回忆里,只有母亲忙完院子里的活,回到屋里找姨妈,后来发现姨妈将新生儿扔到了阁楼地板上这一场景。也许,在母亲的理念里,还有一层维护邻里关系的意思吧。很显然,对母亲回到屋里后发生的一切,菊仙又毫不知情。她只知道村中妇女们到大门外闹事,因此天未亮,就发生了母亲将孩子送到了姑奶奶家这件事。对所有这一切知情的人只有青江姨妈,而她又不愿意做太多的回忆。这门里门外两个世界,母亲得有多么强大的心智才能负荷。痛,夹杂着辛酸、无奈,唯其如此,才现出生活冷金属般的光辉质地。
二十年前,母親病重,几乎村中所有上了年岁的女性都来家中探望。在那篇回忆母亲的文章里,夏木将这种情谊归到了人缘好上。这是多么浅薄的一种认知。今天,夏木终于明白了,母亲为什么在临终前向所有前来看望她的女人们点了点头,一语不发。那压根就不是因为母亲伤心,说不出话。那是一种负荷着沉重历史的化解。
“那个孩子其实你已经见过了。”吃完饭,在告别的时候,菊仙站在门外,望着塔镇的方向,淡淡地说。
“我见过?”夏木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是那个哑巴女娃娃。”说完,菊仙将用报纸包着的包裹递到了夏木的手中。“听你妈妈说,这女娃娃刚生下来的时候特别能哭,按理说,不会是哑巴,可不知什么缘故,自打到了我家,就一声儿都不能哭,后来送了人,也是一样,长到三四岁,才发现是个哑巴。咱们家里可从来没出过哑巴哩,也真是一件怪事儿。你在门外看见的那个男的就是收养她的那家的儿子。他们去年刚结的婚。日子嘛,就该这样昏天黑地地过着才行,千万不能想得太明白了。太明白了,谁也承受不起的。咱们这儿不兴认孩子。就是明明白白知道孩子在哪里,也没有去相认的道理。乡间有乡间的理,城里有城里的道儿。这不一样的。那女娃娃人哑心不哑,手巧得很哩。”
晚上回来,夏木发现姨妈许青江并不在屋里,而是在院子里。春天来了,院子里樱花正在盛开。夏木闷着头穿过院子时,差点和姨妈许青江擦肩而过。她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一抬头,才发现姨妈许青江坐在甬道边长椅上,她的头顶,是盛开的花朵。有几枚花瓣落下来,正好飘在她盘起的发弯里。
“姨妈,你怎么在这里?”夏木问。
“天快黑了,家里呆不住。”
“是啊,天快黑了,今天回去事儿多一些。”
“在这里坐一坐很不错。”
夏木带着深深的疲倦,她不知道从何说起。依然是苍白的微笑。姨妈的表情告诉夏木,她已经知道了一切。那双眼睛不再恓惶,不再茫然,不再焦灼,也不再期盼,而是一种释然。
“她好吗?”许青江问。
“她很好。”夏木将报纸包裹递给姨妈许青江。许青江打开,将脸伏在五彩斑斓的挂件上。许久,许青江抬起头来。夏木发现姨妈并没有哭。
多么强大的意志力啊。夏木想。“明天我们可以过去看看。”
“其实,你早上走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
“什么?”
“明天一早,我回海西去。”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