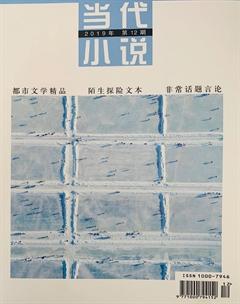文学在现实洪流中寻找人心
李超 张丽军
“我太难了!”这句网络用语现在几乎成为一部分人的口头禅,我们现在可以频繁听到这句话被使用。一句话在生活中被广泛传播,反复使用,说明它一定能够准确、有效描述一群人共同的生存状态。对物质的极端渴望与追求使“面临巨大的压力”成为现在许多人的生存状态,被生活的洪流裹挟着向前突奔的人们,在疲于奔命之余,对自我精神的“救赎”显得尤为重要。文学的价值就在于让讲述者诉说灵魂,让读者看到“精神”的光亮。
现实是如此荒诞,但这就是现实。在现实黑洞里,我们无处逃窜。张学东的《一意孤行》(《当代》2019年第5期)讲述了两起与屠师傅有关又无关的凶杀案。二十年前,当屠师傅还未满十八岁的时候,正处于热恋期的他因为“相关部门”的稀里糊涂,他睡了一觉就被当成杀死自己女朋友的凶手,鋃铛入狱。二十年的牢狱生活,把屠师傅训练成一个隐忍、守规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出狱后,他又稀里糊涂卷入一场“疑似少女谋杀案”。面对着对女同事的愧疚、二十年迷失的自我、受害人家属的胡搅蛮缠,屠师傅决定“一意孤行”,依靠“自己”寻找“少女投湖”的真相。当屠师傅“私自”把凶手扔进湖里,看到他在水面挣扎、喊叫时,二十年沉寂的心灵得到了复归,他认识到做恶人原来比被人冤枉糟糕得多。这一刻是屠师傅人性的复归,是从在这个世界之外游离到积极参与到世界中来的觉醒,在此时,屠师傅情感得到了复苏。寻找真凶的过程也是“自救”的过程。《上海文学》2019年第9期发表了默音的《迷恋》,小说塑造了一个“追星妈妈”的独特形象。女主人公乔瑛是明星陆庐的铁粉,通过乔瑛的追星经历,小说一方面为我们描绘了“追星族”的众生相,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对“人心”的倚重。乔瑛匆忙地在现实与自我两个世界中游离。她向陆庐靠近其实是在向曾经迷失了的那部分自我靠近,她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被攻击的陆庐,实际上也是在维护当年受伤的自己。李一清的《大民还乡》(《当代》2019年第5期)语言简洁,节奏轻快,以较短的篇幅讲述了中国农民(老百姓)心中的“根”与权力、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大民寻找多年的一方面是“自尊”,另一方面还涉及到一个人的“自我肯定”力量。人们往往需要从高于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寻找到“自我肯定”的力量,这样似乎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并且这个“价值体系”是自我认定的,就像大民趋向的“权力”与“文化”。屠师傅、乔瑛、梁大民都是在与“迷失的过往”对话中,寻找现实人生的新方向,他们都是通过“自救”的方式重新确立自我。
除此之外,《上海文学》2019年第9期刊载的周李立的《麻衣如雪》通过探讨“死亡”使主人公突破精神困境,表达了类似的主题。女主人公柯敏对“死亡”的思考过程也是反思自己该以何种态度面对生活的问题。重温冰冷的“死亡”,使柯敏打开了面对无奈生活的桎梏精神。这使她对生活又恢复了知觉。叙事手法上,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把“死亡”这一哲学命题赋予一个困惑中的家庭妇女,让她在厨房里、客厅里、卧室里,在锅碗瓢盆间展开对“死亡”的思考,在生活琐碎处对被桎梏的生活展开突围。另外,晁耀先的《绿萝》(《大观》2019年第8期)、冯又一的《花朵迟开二十年》(《上海文学》2019年第9期)同样以女性视角,讲述她们在情感、欲望、现实里的迷失与回归。
人们在泱泱现实里沉浮跌宕,物质、金钱把欲望死死钳住,经济社会把人变成了“趋利”的空皮囊,以“交互”为目的“经济逻辑”让人们在现实里丢掉了情感,失去了灵魂。杨映川的《住在香若樟》(《当代》2019年第5期)表面上看是说“住房”问题,实指“人心”。俞顺顺的事业竟“意外”地因“凶宅”变得顺风顺水。“凶宅”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人心”,镇压的是“邪气”。坦荡做事,在哪里都能住得“安逸”。在吟泠的《收骨头的人》(《黄河文学》2019年第5期)中,小说以主人公女儿鲁三粉为叙述视角,作者借“父亲葬礼”,以冷静的笔调勾勒出来一场“葬礼”的世俗人情。在这个什么都跟“经济”挂钩的时代,“葬礼”已经沦为经济中的一个环节,庄严的仪式变成了人情交往的工具、敛财的时机。人心早已被“世俗”的琐碎埋没,“死亡”似乎也难以唤起他们对生活的“知觉”。《江南》2019年第5期的“海外华语小说小辑”专栏刊载了六部小说。陈永和的《变脸》更是直接用“肉体”与“灵魂”直接对话的方式,批判了当下“颜值”当道,“灵魂”空虚的社会现象。施玮的《傻娘》以“傻子”荷花的视角,描述了一个残酷、肮脏的“正常人世界”。因为是“傻子”,她的一生都被“正常人世界”抛弃。不管是东子还是丈夫,都怕与“傻子”粘上关系而逃避自己真实的感情。“有没有用”成为“荷花”是否被抛弃的唯一标准。荷花的“傻子世界”是一个高度提纯的世界,同时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正常人世界”的畸形。而黎紫书的《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用平实、温润的语言讲述了生活给一个女人带来的伤痛及女人对现实伤痛艰难的“自救”。这几部作品,加上庞羽的《白猫一闪》(《人民文学》2019年第9期),它们都从精神的微处切入现实,通过穿透平凡普通的生活表层,聚焦埋藏在现实深处的精神幽光)。《收获》2019年第5期刊载了哲贵的《企业家》,塑造了一个雷厉风行、讲义气重感情并且还能时刻保持清醒的实干企业家形象。主人公史国柱有头脑,审时度势,在面对自己的事业、爱情、友情甚至处理自己与父亲的关系的时候都没有难倒自己。但是在面对自己孩子高考问题时,他一贯的商业逻辑似乎也发挥了作用,在与儿子“交换”条件后,他的商业逻辑成功了,儿子顺利考上了上海大学。但是在面对自己的儿子的提问“如果我读博士后呢?你给多少?三千万?”这个问题时,让他的脑子一团糟。表面上,用金钱作为让儿子好好学习的交换条件这一策略已经成功。但儿子的发问使史国柱对自己一贯的行事风格、商业逻辑产生怀疑。儿子史泰龙对史国柱的发问也是对这个无孔不入的“商业社会”的发问,在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似乎我们已经忽略了更多的东西。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灵魂。《人民文学》2019年第9期发表了赵志明的《参与商》,讲的是一个关于“理想”与“理想”本身腐烂的故事。阿灿是水云镇中心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他心中装着一个“诗人梦”,在他的心底里,他的“诗人模样”的生活方式是恬静的,闲云野鹤的,独自品尝着生活的诗境。但是在小镇人及父母的眼中,他就是个闷葫芦,工作十年,不结婚、不升职,是个“怪人”。被迫离开家乡往南京求学的过程中,他无意中看到了所谓城市里的“诗人模样”,跟他自己想象的“诗人模样”完全不同,他们放浪、滥情、不负责任、放荡不羁,他们自己早被物欲、情欲同化,他们把“诗人身份”昭示天下,并以此作为跟女孩儿谈恋爱不负责任的借口,懦弱、自私的伪装。阿灿在这些“城市诗人”身上看不到什么“诗境”、“诗情”。虽然朱丽娟每天的奔波与忙碌都是为了挣钱,但是他分明在旧友忙碌与奔波的尘世生活中看出比“诗人的生活”更有意味的“诗境”与“诗情”。如果诗人本身堕落了,就不能责怪时代不给“诗”立足之地。追求“诗意地栖居”不等于原地逃遁,画地为牢。文学只有自身保持“清醒”才能驻足“人心”。
一个人能够安全长大实属不易,成长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危险的,有时候可以用残酷来形容。梁大民是这样,屠师傅是这样,李智明的《往事》(《当代》2019年第5期)里的齐格与小兹更是这样。中学生齐格因为意外参与了一场打架,又因为同伴的恶作剧,齐格为了躲避警察抓捕,选择离家出走。齐格一次偏离“正常航道”的特殊经历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存在在现实生活之外的特殊世界。在主人公齐格流浪的两三天中,以“齐格”的视角,作者分别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里的嫖客、流浪者、小偷、地痞流氓等人物形象,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现实世界之下的“现实图景”。在这个“世界之外”,小偷抑或是小流浪汉小兹是这群人里一个独特的形象。他与友仗义、与恶不容,他以暴制暴,被人所伤又去伤人。在这个现实生活之下的“世界之外”,鲜活的跳动的灵魂不会因为环境的肮脏、人的丑恶而失去光彩。《当代》2019年第5期刊载了李潇潇的《小男友》,文本叙述者“我”以女友的身份参与情节。叙述者以当事人的角度叙述故事,可以从细节上把温士元的幼稚、空虚、精神畸形暴露无遗,增强对“温室里的花朵”式的“空虚”人的批判力度,同时增加文本故事的可信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全文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展开。随着不同人物之间对话的转变,故事镜头在两个时空间来回切换,随着“对话”的深入,两个时空的故事情节同时推进。这样的叙事结构增强了叙述人叙述的自由度,并且与“友人”对话机制增加了评判“故事”的叙事视角,叙述故事与评判故事同时展开,叙述人既是故事的参与者当事人,也是故事的评判者。《十月》2019年第5期刊载了陈世旭的《江州往事》,“单纯得像个婴儿一样的”谢宜修因为向自己爱慕的女同学示爱而被开除。但是坚持留长发的他保留了他在那个时代最后一丝尊严与自我;甘卫华是个完全被“政治化”、“时代化”了的人物形象,她的全部的人格、人性被“政治性”取代,是那个时代的符号化身。条子酷爱画画,因为带姑娘到家里当模特而被学校开除。韩昕可以说是个文学爱好者,是个诗人,他的激情在那个时代转化为诗情文字,但是并不能与那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兼容。这些在特殊年代的年轻人,与小兹、屠师傅、梁大民一样,他们身处危险,他们无能为力。除此之外,《收获》2019年第5期刊载的宁肯的《火车》、刘庆邦的《托媒》讲述的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往事”。不管是在历史的夹缝中探视还是对当下现实边缘的凝视,文学或讽刺、或呐喊,让我们在疼痛中警觉、反省。
与冰冷的现实和人们对生活“无感”的态度相比,马平的《我看日出的地方》(《人民文学》2019年第9期)是一篇充满温度的小说。全文以“失去枣树”、“寻找枣树”、“枣树复归”为叙事线索,讲述了一个关于亲情、爱情、友情的故事。对“家”的渴望,对“家园”的守候是文字缝隙中温度流淌的重要原因。
《人民文学》2019年第9期刊载的哲贵的《图谱》同样也与“家”有关,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家族”与“文化传承”之间的故事。小说以大学教授柯一璀的视角讲述自己的家族故事。从小跟着父亲生活在外的柯一璀通过两次拜访故乡信河街的经历,揭开了关于家族传承的故事。“图谱”是这个家族“根”的象征,守护与传承“图谱”意味着对家族“根”的传承与守护,从更大意义上讲,对“图谱”的守护与传承同时意味着担起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责任。随着时代的变迁,家族内部的技艺文化代代相传的传统模式不断被打破,新时代里,文化的傳承与坚守面临诸多问题。对文化的传承不能只倚重经济而失去根本——人心。
《江南》2019年第5期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稿”专栏刊载了卢一萍的《刘月湘进疆踪迹史》,以刘月湘进疆视角重温了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的艰辛与不平凡的奋斗历程。该专栏还包括窦红宇的《许家营盘》、赵和平的《水竹开红花》共三部中篇。它们通过对不同空间,不同人群的聚焦与叙述,记录了新中国70年来人们的生活面貌、精神面貌、生存状态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尹文武的《枪声》(《黄河文学》2019年第5期)把时间拉回战争年代,记录了一段军民合作的历史片段。另外,黄小初的《旧面》(《收获》2019年第5期)也是一部中国发展变化进程的缩影。史鑫的《人来人往》(《黄河文学》2019年第5期)以一群中年人“忆旧”的方式追忆了历史洪流中的“个体真实”。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的文学也跟着时代向前推进,作家们用犀利、敏感的笔端,或从细微处切入生活,或在历史浪潮中反观现实。只有文学“本身”保持清醒,它才能长久驻立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