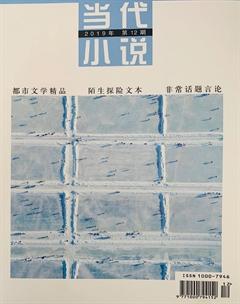我们时代的小说艺术
贺小凡 张丽军
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之际,众多的文学刊物,都以文学的方式致敬祖国。《延河》10月刊设置了“致敬祖国·《延河》经典回望”的专栏,再次收录贺敬之的《回延安》、柳青的《创业史》(节选)和贾平凹的《我们时代的小说艺术》,在经典重温中引发读者的文学思考。《西部》2019年第5期做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特刊,收录杨先的《红军爷》等作品。《大观》杂志社举办了“庆祝新中国70周年华诞作品展”,《飞天》编辑部第10期也作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获奖作品专辑。
刘建超的《将军赞》(《山西文学》2019年第9期),写老将军本不同意孙子当外交官,到后来为孙子点赞,其态度的变化反映了外交在如今世界中重要的作用,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另有韩玉洪的《长江谣》(《延河》2019年第10期),书写河山无限。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青年作家》杂志“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号”刊登了程多宝的《或许,你还没有看过日出》(《青年作家》2019年第10期),将历史的面目拉回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文学,成为了一种记忆的方式。在这场与美国周旋的等待中,“人家要的是日头,我们要的是月亮”,我们的士兵已经不知多少个日子没看过日出了。把对战争的描写加入真实的情感,更能产生动人心魄的魅力。战士们穿粗布军装、唱歌为自己打气、脸上升起的浅浅的笑纹……他们的故土和父母,对身后祖国怀有的深情,战场上扑面而来的血珠子,烧焦而模糊的血肉残肢,漫山遍野落下的弹雨,双手抠进地皮的坚强……亲临战场的实感与血肉鲜活的人物描写交织下,便是一幅个人汇入浩荡革命队伍的抗美援朝战争实景图。战场之上,新团长即将到位,旧团长还压在巨石之下。那时祖国积贫积弱,战士照样敢与美国大兵叫板,来不及擦干的眼泪飘在风里,也不能让战友暴尸荒野——以鲜血,以生命,让几十年后的我们,别忘记风里雨里行军打仗的他们。
这个秋天,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展现当下社会状态、记录时代变迁的小说创作。蔡志刚的《半米阳光》(《北京文学》2019年第9期),关注个人生活经验。自从小文考上本科,新元大学落榜开始,二人的命运便开始由时代的潮水裹挟着,不自主地走向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去。毕业后留过工厂,推销过保险,倒腾过烟酒,而后在汽车生意上“一下子发了”——小文走过的道路无疑是改革开放后无数青年人的缩影。于是,儿时的朋友及他们身上所代表的文化符码向读者传达着这样的信息——新元,这个“高大威猛,说话嗓门也大”的力量、劳动与过去处于主流地位的农耕文明的象征不再是时代的宠儿,取而代之的是“白净瘦小”的小文——掌握了文化知识,懂得用头脑与运气去顺應时代潮流的这类人。由此,回村盖起楼房的小文可以被视作乡村旧有秩序与平衡的打破者。他不仅带来新鲜的物质产品,也搅扰着千百年来卖力气生存的乡村人的头脑和心境,这正是大时代的力量普遍性地冲击着乡村旧有秩序的体现。而开始频繁出现在胡同的法官,体现着现代法治对乡村旧有秩序霸气而蛮横的干涉与入侵。孟小迷的《轿夫肖长力》(《芒种》2019年第9期)同样聚焦小人物的生活,塑造了农民轿夫老肖这一角色。经历过景点“假大师”、伪“百年老店”等种种社会乱象的齐若蘭,也曾习惯性地对这名轿夫怀有戒心。然而,他健壮的体魄和坦然的态度,打动了这个直性子的女人。于是,二人之间的情谊,由一碗新茶串联起来,竟穿透了十年的岁月,命运得以再一次透过齐若蘭的眼睛,折射出一位平凡轿夫的社会责任感。马金莲的《主角》(《芒种》2019年第9期)里的王二蛋是庄里人口中的“傻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傻子”,却莫名其妙地被一群官员簇拥起来,冒名顶替起革命烈士的后人。在权力的支配下,傻子一下子成为了所谓的“主角”,于是,从支书到局长一系列基层干部的丑恶嘴脸在他的面前一览无余。牺牲的李如山烈士,在那个时代是富户的公子。这样的一个人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谈话的当下已经是难以理解的了。那个时代的人“有理想,有追求,有信念”,而今天“好日子把人过懒了,也过残了”。这样的一行人走在烈士李如山当年走过的道路上,构成了一个极大的讽喻。或许,在这样的时刻,唯有傻子才是唯一一个尚未全然麻木的人。
对于当下社会存在的某些社会乱象,寒郁的《夺泪来云轩》(《芒种》2019年第10期)也有所反映。三十多岁的邱致虚工作上不得志,与妻子的关系也达到冰点。于是,他便把“来云轩”这家烤鱼店当作自己散心的桃花源。谁知,领导所犯下的种种罪恶,竟在这里得到了证实。小说的结尾留下一个问题,面对特权的挟持,善良的普通人唯有通过铤而走险以暴制暴,才能维护自身的权利吗?如此引发人们深思的还有周云和的《流泪并不是悲伤》(《长城》2019年第5期),于县作协的方寸之间,传达着对于官僚作风的批判。与之相对,白小川的《鸟事》(《芒种》2019年第10期)便十足地为社会风气提了一把精气神,读来鼓舞人心。这次,故事的结局是,野鸭不仅被表姐夫退了回来,年轻一代人自主创业,也得到了极大的认可与鼓励。《叶骑小小说两篇》(《北京文学》2019年第9期)的写作视角是比较特别的。其中的《一双鞋》(《北京文学》2019年第9期),以一个大山里孩子的视角,来反映对于尚未“走出大山”的他们,真正的社会关怀或许并非蜂拥而至的新闻采访与刻意煽情的摄影报道,从而引发对于当代人关怀贫困群体时应该持有何种态度的反思——真正有效的社会关怀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另一则《一生》(《北京文学》2019年第9期)则以一株绿萝的视角进行书写,以小见大地折射出都市人急功近利、不懂感恩、妄自尊大、欺弱与利用的种种病况。王语咒的《面孔》(《芒种》2019年第9期)以一所“差生收容所”作为反映社会现象的一个窗口,塑造了一批即将中考的青少年群像。在这里,生源素质和校园管理都混乱不堪,学生要么成为透明人,要么就会成为霸凌者或受害者。这些成绩不好或身体有残疾的青少年,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引导。在这里,何尝不是整日上演着鲁迅先生所言的“怯者的愤怒”——“抽刀向更弱者”。梁学敏的短篇小说《山脊清晰地露了出来》(《山西文学》2019年第9期),反映当代人为孩子上学而租房的普遍现象。无论多么破旧的老房子,只要地处学校周围,便以高价租售而出。男主人公为工作加班熬夜,浑身都是毛病,唯有借酒消愁。孙阳的《星期六改变命运》(《延河》2019年第10期)也反映了许多都市人为“学区房”奴役的社会现象。由此,小说折射出一种不堪重负的人生,这是属于无数中年人共同的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困局。与之类似以反映人在生活面前的无力与无奈的还有陈敏的《希望像只小狗》(《山西文学》2019年第9期),范小青的《你在通话我未接》(《北京文学》2019年第10期),尹学芸的《灰鸽子》(《北京文学》2019年第10期),陈学长的《安家》(《西部》2019年第5期)等中短篇小说。
寻找意义、自我救赎,是物质条件日益富足后的当代人所面临的重大课题。马可的《天使》(《北京文学》2019年第9期)写女主人公雯雯跟踪出轨丈夫的路途,却在“回忆”与“遇见”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之所向:原谅昨天,理顺今天,走向明天。小一的《在同一条船上》(《北京文学》2019年第9期)同样讲述了追寻背叛自己的爱人的故事。小说通过一男一女两个人物的对话构成了思辨的过程,天涯沦落的二人互相开解、扶持着上岸。上岸前的两人,试图为自己在当下社会中的定位寻找一个恰当的表达,当“蠢”与“老实”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中难以区分,这篇小说的反思性由此得以体现。
在当代中国,以城市为背景、以都市人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与日俱增,值得关注。《鸭绿江》9月刊的“新青年·新城市”专栏,收录了王海雪的《白日月光》(《鸭绿江》2019年第9期),《青年文学》的“城市”专栏收录了柳营的《旋转的木马》(《青年文学》2019年第9期)、《被群蚁吞噬的犀牛》(《青年文学》2019年第9期),王哲珠的《非典型创业》(《青年文学》2019年第10期)。孟小书的《凉凉北京》(《芒种》2019年第9期),触及北京都市青年人真实生活的内里,写空虚、迷茫、习惯孤独又陷于琐碎的都市市井生活。小有名气的主持人张闯闯,像其他青年一样,在面对事业或爱情的当下,总是抓住看似美好的一角便当作是救命稻草。当工作合同被毁约,焦虑与浮躁便将张闯闯整个人笼罩起来。他因为不安和倾诉的需要,去寻找利己的快餐式“爱情”,而事实上,这样的情感只能换来同样利己的对待。彼此都对对方的困境毫不关心,客套地作着无关痛癢的回应。都市人的心灵是如此脆弱,而又如此渴望着安慰,却不知道,人唯有找到属于自己坚定的精神坐标才能真正获得心灵的平静。吕传斌的《陌生人不算数》(《延河》2019年第9期)中,也有不能把婚姻当作感情来看,“必须当做生意来处理”的论调。无数人在生活的道路上摸索前行,试图挣脱黑暗,寻找到一条光明的精神之路。李立泰的《卖鸡蛋》(《山西文学》2019年第9期),似乎为人应该如何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做出了解答:只要能为社会与他人做出贡献,即便艰苦、孤独,内心也会是丰盈快乐的。赵大河的《我想把孩子生下来》(《山西文学》2019年第10期)中的朱丽,尚未挣脱生活的混沌;桂子的《坐席》(《山西文学》2019年第10期)向外追求他人的认同,王棘的《夜晚出生的孩子》(《山西文学》2019年第10期)向内寻求与自己的和解,都描摹了心乱如麻的情绪。何玉茹的《姑娘们》(《长城》2019年第5期)关注城市化进程中老年人的精神世界,既深入探寻她们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又集中表现了新的社会和时代、城乡巨大差异等不同态度。张学东的《被狗牵着的女人》(《长城》2019年第5期),以悲悯的情怀关注空巢老人的生活困境。
共和国成立七十载,这个古老的国度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城乡巨变。陈胜展的短篇《青龙石》(《芒种》2019年第9期),读来似乎有一群石匠凿凿有声,写的是原始生活情态下人们对生的祝福和对死的接受。石凌的《羊杀》(《朔方》2019年第9期),写杀了一辈子羊的杨奎娃与羊的故事,离开了那片乡土,羊的命运也映照着人的命运。同样书写大时代下普通人生活情态的还有张炜的《会议论的人》(《山东文学》2019年第9期),安石榴的《一窥》(《芒种》2019年第9期),戴潍娜的《守节的光阴》(《青海湖》2019年第10期),刘捷的《你笑起来真好看》(《山西文学》2019年第9期),雨瑞的《迷案》(《山西文学》2019年第9期),原上秋的《我的战友老潘》(《延河》2019年第9期),贺绪林的《家庭机密》(《延河》2019年第9期),海莲的《变声的安徒生》(《延河》2019年第9期),艾玛的《在班车上》(《青岛文学》2019年第9期),玉泽的《婆媳》(《回族文学》2019年第5期)等诸多作品。
文学,始终在为一个又一个的时代存照。时至今天,火种不灭,一代代写作者们依然用笔,对外抗拒外在的各种力量,对内为中华文明书写新的篇章,改变着中国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