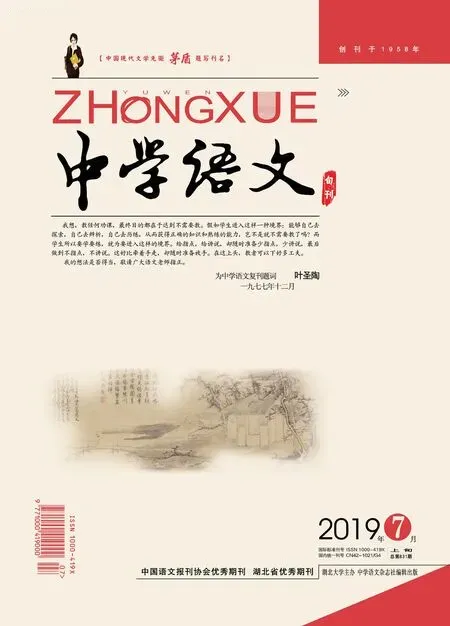探赜钩深:疾病的书写、隐喻与省察
——别样的视角深读《老王》
汤汝昭
《老王》是杨绛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据笔者翻阅相关文献察知,目前学界对《老王》文本的解读多停留在主旨探讨、人物形象分析、语言风格赏析以及细节文句体悟等层面,除张克中《作为一个“存在”的价值判断——对〈老王〉的再解读》和王开东《“老王”不过是杨绛的隐身衣》两篇文章外,极少涉及关于杨绛先生《老王》创作意图的深层探析。我们知道“在文学作品中,疾病常常成了对社会中某种缺失状态的展示,或者是对这种缺失关系、根源的揭示,通过疾病的隐喻传达出作者的一种价值判断”①。细读《老王》后,笔者发现文中多处存有或隐性、或显性的疾病书写。鉴于此,笔者试图以“疾病”视角为研究的切入点,结合文本深入剖析文中三种不同社会群体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呈现的“社会病相”,并阐释各种病相所投射出的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隐喻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读杨绛《老王》文本中折射出的理性且深刻的自省与历史反思意识。
一、众生病相:“老王”“看客”与“我”
病相,即非正常、非健康的某种情形、现象、行为与表现,它是人体疾病社会化的表征。疾病对于人来说,除身体“常态”的生理病症外,还有“非常态”的疾病,如心理的、精神的,前者在文学世界的书写中属于显性疾病,后者为隐性疾病。往往在“文学工厂”中,关于疾病书写不单是对身体疾患的客观确认,而是赋予它别样的象征寓意,这里不论是显性的疾病,还是隐性的疾病,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均被作者不自觉地生成出某种暗指性功能,此时各种病相往往与民族国家的痼疾以及社会时代的骤变悄然相关。
细读文本,笔者发现,杨绛先生在《老王》一文中巧妙构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即以“老王”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群体、以游离于文本之外的“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以普通乘客为代表的“看客”群体(鲁迅《〈呐喊〉自序》:“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看客”多指旁观者)。这三种不同社会群体在“文革”时期,各自表现出相异的病相,或生理病态,或心理病态,或精神病态,杨绛先生在文中均有冷静理性的书写。
首先,“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我们对老王病相的初次感知是从这句开始的。“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这样的描述更加确指了老王身患眼疾的事实,据此可知,老王是一个残疾者。可是,杨绛先生并没有就此止笔,“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继续暴露老王身体的羸弱,凸显其病态的行为与表现,试图在读者的思维空间极力塑造一个虚弱的病者形象,以期迅速博得读者对老王形象的怜悯和同情。杨绛先生为了顺利完成老王悲苦命运的设计,进一步撕开回忆的伤疤,勇敢直面老王的疾病叙忆,“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作者站在回忆的边上,默默不语,冷静地观察着老王的身体状况一步步走向病重,“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这些可怖的病症透过身体散发出痛苦与死亡的气息,“棺材里倒出来的”“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看似调侃且幽默的语调,在文中再一次残酷地将老王的生命推至终点。同院老李的一句“早埋了”,彻底结束了老王的文本生命。老王的疾病源于身体健康的丧失,他的死亡是生理机体在疾病面前的失败与被摧毁,文本中杨绛按照“身残—患病—病重—死亡”的生命次序平静地书写着老王命途多舛的一生,透过身体疾病的不幸,展现了底层民众在疾病抗争中的无奈和无力,生理疾病使得老王的生命意义极度 “缩水”,老王的病相客观地反映出广大底层民众在苦难年代里的生存紧张与生存压力。
其次,普通乘客以及“我”所承载的两种病相是区别于老王病相的。普通乘客为代表的“看客”群体在文中的疾病书写是间接的、隐性的,杨绛先生在文中凭借几句乘客“恶语”的披露,巧妙地将人性恶毒、心灵扭曲的“看客”形象成功地塑造出来,如“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从“看客”们病态的观人眼光与评人视角,加上毫无证据的诋毁,这就构成了一种典型的语言暴力行为,而“恶病”的猜疑与臆想则反映出普通“看客”群体心理层面的外在破裂与心灵扭曲,这更是一种心理病态的照实书写。这种心理病相产生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因素所致,既有民族心理的痼疾,也有社会道德规范的失序,还有人性良知的沦丧,等等,杨绛先生在文中都有自己隐性的思考和省察。
而游离于文本之外,又始终存于文本之中的“我”,即“习惯于隐身的杨绛,在《老王》一文中,也穿上了隐身衣,让别人看不见她。”②杨绛不仅在情感上善于“隐身”,在对待老王的关系处理上也善于“隐身”,让读者觉得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她与底层民众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隔阂与距离,这种距离透射出双方关于情感付出的认同差异和价值趋向。文中“送冰”“送钱先生看病”以及“送香油和鸡蛋”三件小事中,杨先生一直坚持用金钱来处理与老王的关系。老王的真诚与善良,在杨绛先生心里无法得到对等的情感认同,不仅如此,文中杨绛的用词也可看出,在苦难年代里,知识分子其实逐渐放弃了自我认同,开始以“货”来戏称,尊严丧失与斯文扫地,足够让知识分子面临“穷途末路”时,开始抛弃人性真善美的信仰与追求,转向以金钱标准衡量一切价值的世俗观念。另外,“我害怕得糊涂了”,这是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人文关怀精神在将死之人面前的最后消解,显然,知识分子群体在家国失序的非常态环境下精神世界逐显“病入膏肓”之态,这正是作者多年后愧怍的原因之一,知识分子对“善良的漠视与侮辱”实质上是他们精神世界一次“病态的慌乱”和集体出现的“良知衰微与规避”。
总之,杨绛在文中关于生理、心理和精神三重病相的书写,我认为是她对苦难年代里伦理道德、光辉人性与民族心理颓丧的声诉、批判与反思,作为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她人性的自我醒觉与寻真。
二、疾病隐喻:“冷漠”“扭曲”与“失序”
“疾病一旦与文学挂钩,它便不再是疾病本身,隐喻的思维方式赋予了它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③。文学作品中,无论身体的、心理的和精神的病相,我想它都是被掩蔽的某些社会现象的潜在映射,整个民族在时代变迁的语境下,文本中“非常态”的各种病相自然会与失序的道德伦理与民族国家互相指涉,联结成为一种彼此隐喻的结构模式。于此,疾病就不再是个体生命的痛苦体验,“病”成为整个社会乃至民族精神状态的复杂隐喻,其社会内涵与意义空间被重新拓展与建构。
杨绛《老王》中阐释的三种病相,其具有独特的、多样的隐喻意义,主要涉及社会现实、民族心理、与家国命运三个方面。
其一是社会现实隐喻。文本的核心人物老王,在杨绛笔下是“苦”和“善”的结合体。其“苦”产生的根源,在我看来,身体疾患和身世可怜这都是次要的,主要原因在于老王极度缺乏的社会关怀和情感互动。作为“单干户”,他是游离在车行组织之外的,得不到组织的保护和关照,职业上难以获得该有的幸福感,职业自尊时常受到欺侮,普通“乘客”背后的恶语令他心寒无望;作为拉车人,老王以为与“我”长时间的接触、交往,熟悉之后关系自然变得亲近,可惜这仅是他的“误判”,其实老王在“我”心中仍止于“只是闲聊”的关系,一边的理解是亲近的熟客关系,一边的理解是普通的雇佣关系,双方交际关系的认同差异,直接造成交往过程中情感互动的丧失,老王以善对我,我却以钱待之。临近生命最后的一次苍白解释“我不是要钱”,仍然被我无端误解,可想此时老王的心灰意冷和绝望肆起。当个体情感世界无法得到对等的回应时,外界世界对其情感的封闭,无疑逼迫着他走上生活的绝路!其实,文中老王的“苦”被作者刻意放大,“吃了什么药,总不见好”的病相,隐喻老王的精神疾苦是医术和药物难以“疗救”的,它需要整个社会力量的关注和介入。杨绛想通过这样的人物命运的书写,唤醒全社会的注意,往往社会现实的冰冷、残酷、无情与麻木会把一批批“老王”推进生命的深渊,这不仅是社会的不幸,更是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悲剧更是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沉重叩问,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莫大讽刺。
其二是民族心理隐喻。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稳定的、持久的性格、情感以及行为习惯等心理特质的总和,民族心理对于维系和稳固民族内部关系具有内聚性和共识性。而“文革”时期,恰是整个民族心理濒临扭曲和颓变的时代,深受几千年儒家文化浸润与滋养的民族心理的优秀特质在历史灾难的漩涡中也难以散发本有的光辉,甚至有些发生了歪曲、退变和消逝。如《老王》中的普通乘客,病态的观人视角和扭曲的心理揣测,他们眼中“老王”这副模样的群体皆是该有“恶病”的,语言的暴力在心理阴暗面前永远无法超越后者给人带来的精神损伤。还有车行组织对老王的抛弃,迫使他始终有种“失群落伍的惶恐”,社会组织对他的心理排斥,造成老王职业上找不到安全感和归属感,致使他产生“无家”的念头,这里实际上是杨绛先生关于社会制度的深度思考,它不仅涉及人性美丑与善恶,还关系到道德良知的消退与沦丧。另外,“我”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也变得“害怕得糊涂了”,这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尊严殆尽,无法重新找回自我认同,便幽默地以“货”来打趣自己,逐渐接受病态的社会现象,对待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人性良知的失序、沦陷与退变选择沉默、容忍并顺应。文中的“我”对待老王的真诚和善良,采取“距离化”的处理方式,原以为是一种保护,实则是一种隐形的伤害。“我”心理意识上对情感互动的故意躲让与规避,彻底暴露了知识分子群体在苦难面前表现出来的怯懦、彷徨与苦闷。殊不知,“我”刻意的人性压抑,也是致使老王之死的因素之一。老王的死,对杨绛的打击是巨大的,他的死饱含双重意蕴;一是意味着一位与命运抗争、垂死挣扎在底层生活的劳动者的完全失败与毁灭;二是代表着“疯狂年代”里最光辉、最珍贵、最稀缺的人性特质的退避和消逝,这是杨绛以老王之死向社会控诉、向时代呐喊的有力发声。
老王的死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消亡,隐喻着民族心理中光辉特质的黯淡与真善信仰的瓦解!
其三是家国命运隐喻。“国家的失序打破了个体原有稳定的秩序框架,意义世界的整体感随之瓦解,失序状态引发了身体的不适感。个体因国家失序而致病的意义,逐渐由身体现实演化为一种实际上或未发生但情感上已然如是的精神象征。”④老王的身患重疾、“看客”群体的心理疾病以及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恐慌与惊怕,种种病相隐喻着此时国家无论是政治秩序运行、精神文明建设,还是社会体系存在都已经出现了“似人”的毛病,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然而个体的身体一度超出自身属性,悄然间具有了“国家之身”的社会属性,身体疾患不再归属于个人生命的私有体验,逐渐映射出作者对家国命运的担忧和焦虑,这种忧虑在文中作者是借同院“老李”之口向世界宣告的,老李作为老王死讯的第一传告者,站在历史的台阶上,他被动地成为时代人性墓碑的树立者。其实,文中的“幸运”与“不幸”,既是对人而言,也是对国家而言,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在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是无法分割且密切关联的。所以,只有在健康、合理和有序的国家状态运行下,社会的悲剧、时代的不幸才有可能避免。
杨绛《老王》中疾病隐喻的意义,笔者以为更多的是:唤醒人们心灵深处的社会良知,引导人们在灾难中不要刻意躲避,而要学会承担起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和使命。
三、疾病省察:“生命”“救济”与“回归”
但凡具有“文革”亲历体验的作家,对“苦难”的认识、理解以及处理方式和态度都是不尽相同的,而杨绛此类的回忆性散文足见她的睿智与寻求,其女钱瑗曾喻“母亲的散文像茶,悠远”。其实,杨绛对待这段苦难经历的态度是客观冷静的,一方面她能够理性平静地回忆历史,叙述历史中的人和事;另一方面她还能从事件中剥离出来默默察看,思考藏在事件背后的社会百态。
《老王》中她对疾病的书写,给予了多重视角的交相观照。老王由生到死的生命过程形迹可寻,“残疾—患病—病重—死亡”,这是杨绛对老王生命的冷静观察,也是内心愧怍之余对生命及其意义的重新思考:生命即使卑微,精神照样伟大。多年后,心中挥之不去的“香油与鸡蛋”的影子,勾起杨绛对自我精神世界深刻解剖的冲动。试想,处于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香油和鸡蛋是何其珍贵?生活艰辛的老王却把“好香油”“大鸡蛋”真诚相送,一个将死之人将自己维持生存的物资赠送他人,这能是一次简单的赠送吗?在笔者看来,这不仅是老王在物质上对杨绛及其家人的真诚回馈,更是在心灵深处对其进行的一次精神救济。所以,《老王》一文反复品读,读出的不仅有“我”深深的愧怍之情,更有作者至情至性的自省与自剖意识。
此外,对于文革这段烟云已逝的历史,杨绛并没有避而不谈,而是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冷处理。“杨绛的散文比起其他作家的散文是克制的……尤其是文革之后,杨绛的写作更加隐晦。”⑤通常她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平凡人物如实叙述,以期从人物命运的变化展现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特征。《老王》的创作,即是杨绛对文革历史的直面与反思,反思的方式有许多,而杨绛的风格却是独特的,她以人物和故事情节的真实再现重新解读历史。当然,这样的方式追求的是客观公正、不失公允,但其回忆的历程却是极其痛苦的,或许正是“宁静节制的感情处理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含蓄蕴藉的审美感受”⑥,或许正是在这种“闲话”式的反思中,杨绛重新寻得了理性的回归。
四、结语
疾病在文学世界中,其思想内涵和意义不断被延伸、扩建,普通个体的疾病书写不再只关涉人性、生命、心理和文化等诸多因素,它对国家、历史、社会内容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指涉逐渐发展。笔者对《老王》一文的疾病窥探,发现了非常态社会背景下的众生病相,这些病态心理及行为的背后,又能延伸出哪些深刻的思考呢?我想,这才是所有一线教师执教《老王》时需要思考的问题,文本的解读不仅要重视其语言、情感、主旨和审美等方面,更要注重文本思想性的挖掘。笔者认为,只有“走到文字背后”的深度解读才能真正实现语文课堂由文字—文本—文学—文化的审美能力的层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