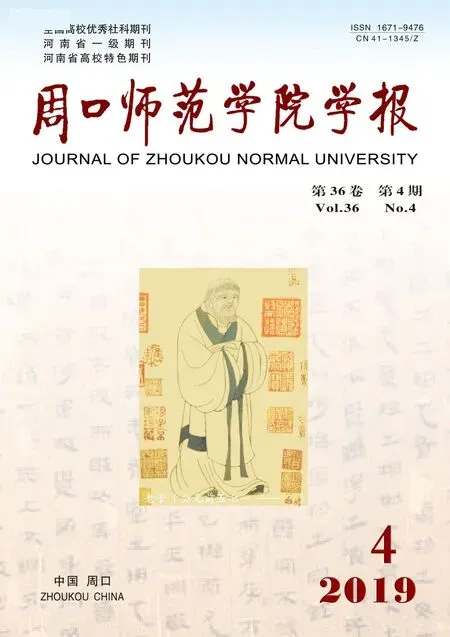双音复合词与双音短语的界域与关系
赵 莹,杨绪明
(1.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2.南宁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20世纪4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重视对汉语语法单位的研究。学者们对字和词、语素和词、词和短语的辨析研究做了很多努力,但至今仍有一些问题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尤其是对词和短语的辨析,还未能提出覆盖面广、解释力强,为广大学者所共识的区分方法。我们发现难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辨别由两个可成词语素组成的双音复合词与双音短语”上,若能提出可以区别两者的方法,就可基本解决词和短语的辨析难题。
一、双音复合词与双音短语易混淆的原因分析
(一)成词语素的跨类特点
双音复合词是由两个单音语素构成的词,两个语素通过复合法、重叠法、附加法等方式结合成词,其中的语素可以是成词语素,如“山水、提高”,也可以是不成词语素,如“视力、观察、阿姨”。如果某一个双音结构中含有一个或两个不成词语素,那么这个结构毫无疑问是一个词,只有在某个双音结构中包含两个成词语素时,才会出现词和短语定性困难的情况。
朱德熙在《语法答问》中首次提出“实现关系”的概念,它指的是汉语中词组(短语)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因为相比印欧语,汉语的句子可以直接由其下级单位——短语添加句调而实现[1]48。刘钦荣受此启发提出,“语素与单纯词间的关系也是‘实现关系’”[2]。因为语素与单纯词之间存在着实现关系,这使得汉语中的部分语素具备了跨单位的性质,身兼两职的成词语素不论是做语素还是做词,其外在形式都是一致的。尽管我们从概念上可以明确短语是包含多个词的语法单位,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很难确定双音结构中成词语素的功能是构成词的语素,还是构成短语的词。这最终造成词和短语界限的模糊。
(二)汉语词义“透明度”的多元化
李晋霞、李宇明提出“词义的透明度”,以此指“词义可从构成要素的意义上推知的难易度”,并指出词义的透明度从透明到隐晦大致可以分为完全透明、比较透明、比较隐晦、完全隐晦等四个层级,而词义透明度递减的过程即是语义词化递增的过程[3]。
区别词和短语最直观的标准是:词的意义具有凝固性,而短语的意义具有临时组合性。从词或短语的构成成分义来看,一个双音短语其意义基本等于构成成分义之和,如果借用“透明度”概念描述短语,那么结论是,短语含义的透明度是完全透明的。如短语“洗车”意为“清洗车辆”,我们可以通过构成成分义直接推知短语义。所以,一个双音复合词,如果其词义透明度比较隐晦或完全隐晦,则不会产生词和短语的混淆,因为其构成语素不具备完整表义和自由运用的能力。但事实上,对于某些词义完全透明或比较透明的词,有时我们很难厘清其构词语素的语素义与该语素作为单纯词时的词义有什么差别,其原因可能是“语素实现为单纯词的条件就是形体不发生任何改变而具备了完整表义和自由运用的能力”[2],而是否完整表义是一个较为主观的标准。
符淮青曾将合成词词义和构成它的语素义的关系分成五大类[4]218-225:第一种类型是语素义直接地完全地表示词义,如“平分=平均+分配”“哀伤=(哀)悲哀=(伤)悲伤”;第二种类型是语素义直接但部分地表示词义(还包括暗含义),如“平年=(农作物收成)+平常的+年头”“刻毒=(说话)+刻薄+狠毒”;第三种类型是语素义和词义间接联系,词义是语素义的引申义或比喻义,如“铁窗=安上铁栅的+窗户(借指监狱)”;第四种类型是合成词中的一个语素完全不用它原有的意义来表示词义,如“反水=叛变(水义无体现)”;第五种类型是构成词的所有语素的原有义都不显示词义,如“东西”泛指各种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由此可知,第一种类型到第五种类型的词,其中语素的原有意义在词义中所占的地位是递减的。
上述合成词词义和构成它的语素义的关系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汉语中存在的第一类合成词,它的词义几乎等同于其组成语素的语素义之和,如“‘火热’虽然是词,但它的意思是像‘火’一样地‘热’。我们能说‘火热’中的‘火’跟‘大火’这个短语中的‘火’、‘火热’中的‘热’跟‘很热’这个短语中的‘热’在字形、字义方面有多大差别吗?”[5]
对于符淮青所论述的第一种甚至第二种类型的双音复合词,或者是李晋霞、李宇明所阐述的词义“完全透明”和“比较透明”的双音复合词,我们在对其进行定性分析时,由于其词义的凝固性、整体性、抽象性不强,所以,从语义角度分析很容易与短语混淆。
(三)短语的词汇化与词汇用法
词的双音化是中古时期汉语发展中出现的特定现象,是汉语韵律的一个基本形式,也是汉语韵律句法研究最重要的起点之一[6]。单音节词有着向双音节发展的趋势,原有的单音节词在双音节化的过程中,有许多降级为语素,而失去独立运用的功能,这导致原本被认为是短语的语言结构变成词,即发生了短语词汇化现象。王力在论述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时,明确指出“仂语凝固化”是汉语构词法中最主要的方式[7]401。所以,从历时的角度看,由于短语与词之间存在着转化的关系,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在辨别短语和词时才会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古代汉语中“妻子”,指“妻子和孩子”;“虽然”指“即使这样”他们都可以被归入短语,而在现代汉语中他们仅作为词使用。再如,汉语中存在的一些短语的缩略语用法“疗效(治疗效果)”“五官(眉眼耳鼻口)”等,它们的功能相当于一个短语,但是其结构特点、意义特点都满足词的要求。对此,董秀芳也有相关论述,“汉语的复合词最初是由短语演变而来的,其形成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词化的过程,正因如此,汉语中短语和词的划界才困难重重”[8]。
除此之外,如果在动态的言语层面判断某双音结构,可能还会有不同的定性结果,因为短语在修辞等语用手法的作用下也会产生词的语法特点,即拥有意义的整体性、抽象性。如“吃饭”本来是一个动宾结构的短语,但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如“我们要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中的“吃饭”便不再作为短语使用,而是受“借代”修辞的影响,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词,具有了“生计” 的词义。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十分常见,如“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其中的“红旗”和“彩旗”也不再代表作为普通短语时的含义,而是用比喻义生动形象地表示“妻子”和“情人”,结构义具有整体性,它们的功能相当于词。
此外,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短语,也有可能转化为专有名词,或在某种语境中具有词的功能。如网络新词“人设”,它在最初形成的时候是一个短语,指的是“动漫人物的基本设定,包括姓名、年龄、身高等”,但是这个词后来在娱乐圈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其含义的整体性不断加强,在多数情况下指“艺人们为迎合大众喜好而人为建设的内在涵养或性格特征”,它已经成为意义抽象且使用频率很高的网络词。
二、短语和词区分方法的相关研究
“结构上具有凝固性、意义上具有整体性”是词所具备的最突出的特点,所以,对词和短语的辨析,学者们试图从研究对象的结构特点与意义特征入手寻找突破口。以往,学者们对区别汉语中词和短语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是从语法结构紧密程度分析,第二是从语义凝固性强弱入手,第三是综合考虑语法、语义甚至语音特征进行辨析(1)赵元任(1975)提出通过北京话中双音结构的重音模式来判断结构性质,但由于该方法对于判断现代汉语词或短语的普适性较低,故本文不做详细介绍。。
(一)语法结构紧密程度的分析视角
陆志韦曾提出“同形替代法”,即在同一个句型中用同类词进行替代,他将能够在一个组合关系中发挥同样句法作用的聚合都归入词的范畴[9],但是他忽视了这样的替代法也是在分析短语、语素、音位时常用的手段,并不只限于词汇的聚合。王力在《中国语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隔开法”[10]。其所谓隔开法,就是在一个组合中看能否用别的成分把它隔开:能隔开的是短语,不能隔开的是词。毫无疑问,隔开法肯定了一个词具有“结构的凝固性”这一特点。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弊端,它只注重从形式上将某个组合隔开,而不关注该组合被隔开后还是否具有与原来同样的语法功能。如“牛肉”可以在中间加入“的”字隔开,但是没有人会在具体的语用中将“牛肉”说成“牛的肉”。所以,即使一个组合可以被其他成分隔开,如果改变了其原有的功能,也不能判定该组合为短语。
陆志韦放弃“同形替代法”之后,在其《汉语的构词法》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扩展法”[11]8。他不仅强调词在结构上的凝固性,同时也强调以实际语言为依据,也就是说一个结构在扩展之后,其功能与用法不能与扩展前产生较大差异。卞觉非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区分词和短语应该在扩展法的基础上辅之以层次分析法,即在扩展某结构的同时不改变原有的内部结构关系,这样才算是符合规则的扩展,能够被扩展的结构才能被称为短语(可以称之为“保持语法结构的扩展法”)[12]。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补充,排除了许多错误的对词进行扩展并认定其为短语的情况。如我们可以将“马车”一词扩展为“马拉的车”,而扩展之后原有的“定中”结构被打破,“马”作了“拉”的主语从而不符合原有的结构层次,所以该扩展不能判定“马车”一词为短语。虽然学者们已经提出了不少能够为多数双音结构定性方法,但这些方法还有缺陷,因为它们对“离合词”的辨析几乎没有解释力。
(二)语义凝固性强弱的分析视角
除了根据组合结构是否具有紧密性来辨别词和短语以外,其实早在1954年,黎锦熙先生便提出了“意义观念论”这一方法。他认为“词就是说话的时候表示思想中的一个观念的语词”,所谓“观念”就是“一切外界的感觉、反映的知觉、想象乃至概念等,凡是由认识作用而来的都可以叫做观念。用声音或文字来代表这些单体的整个意象,都叫做词”[13]。黎先生的这种说法实际上肯定且强调了词具有“意义的凝固性”特点,一个结构只要能够具有指称某一观念的作用,即可以被称为“词”。但是由于“观念”这一概念涉及的内容太过宽泛,在这样的定义下,一个结构大到“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的经济制度,小到“人”“民”“喜”“惧”这样的词或语素都涵盖在其中。由于用该方法辨析词和短语的实际操作效果不佳,所以黎先生的这种说法在提出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
判断一个语言结构的意义是否具有凝固性时,主要依靠个人的主观感受,我们无法提出衡量一个语言结构凝固性的客观标准,所以用这种方法辨别词和短语必然会产生诸多分歧。如有人认为“微风”是短语,因为它的意思是“微弱的风”,短语义等于其组成成分义之和,不具备词所具有的凝固性。但也有人认为,“微风”指的是“每秒空气移动不超过1米的自然现象”,如果这样理解,其含义又具有一定的凝固性,应被归入词之列。所以,用含义的凝固性判断某结构的性质,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以往对词和短语的辨析研究大都集中在以上两个视角,但不可否认,这些标准自身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认为,辨析词和短语的着眼点不应该落在语法结构和意义上,而是找出词所具备的共性,根据词这一级语法单位所具有的本质特点来区分词和短语。黎锦熙先生提出的“意义观念论”,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价值不大,但是它也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因为除虚词以外,几乎所有的实词在我们的思维、观念中都存在共性,即它们都具有一定的“指称性”。
三、双音复合词与双音短语的判定
(一)词语的“指称性”
在论述汉语词类的功能时,朱德熙曾说过:英语有动词和形容词的“名词化”,汉语没有动词(含形容词)的“名词化”,汉语的动词做主语和宾语的时候还是动词[1]22。对此,沈家煊接受朱德熙先生的说法并进一步提出,汉语的动词之所以没有“名词化”,那是因为汉语的动词本来也是名词,是一种兼有动词性的名词,叫“动名词”。因为跟英语等印欧语不同,汉语的名词可以直接做谓语,名词还能受副词的修饰。这不是因为名词有述谓性,而是因为谓语有指称性[14]。
其实,不仅是汉语中的动词和形容词,大多数实词都具有“指称性”。当一名婴儿进入语言学习阶段时,首先建立的是对事物的概念性表征,然后再以语言的形式表达之,即获得了语言性表征[15]。根据儿童语言习得的规律来看,他们首先习得的语法单位就是词,而词的作用就是指称已经进入他们认知领域的客观世界中的事物、现象或情感。一个实词不论被归入什么词类,它都具备指称性,如王红旗曾论述“名词的所指物是事物,动词的所指物是动作、活动、变化,形容词的所指物是性质、状态,区别词的所指物是性质,数词的所指物是数,量词的所指物是事物或动作的量,代词代替什么词就存在所代替词的所指物”[16]。可见,一个词的指称性,通俗地讲就是在人脑刚刚接受一个新的事物、动作、感情、性质、状态、数量等一切领域的新认知时,我们为了区别每一个最小的认知单元而分别为其进行语言编码,所以,几乎每一个实词实际上都代表了某一个我们头脑中最小认知个体的名称。
王红旗在论述词的指称性时,引用了奥格登和里查兹的“语义三角”[17],指出:“语义三角左下角的‘符号’(能指)应该是双面的音义结合体,即词,属于语言世界,顶角的‘思想或所指活动’(所指)属于概念世界,右下角的‘所指物’属于真实世界。”[16]所以,词是语言世界中最小的能够通过概念世界指称现实世界的语法单位。当然也有部分实词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如专有名词,因为专有名词无须通过概念世界直接指称现实世界;另外,也有一些实词的词义很虚,像汉语中的“是”“进行”“当”“作”等等,它们与概念世界相联系但是指称性却很弱,这类词应该被当作特例直接归纳出来。
(二)双语素双音结构的定性方法
我们首先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由两个可成词语素组成的语言结构,所以当一个双音结构中存在不成词语素时,这种情况不在讨论之列。如有许多学者讨论“理发”“鞠躬”之类的离合词应该被认为是词还是短语。我们认为,“理发”中“发”、“鞠躬”中的“鞠”和“躬”,在现代汉语中是不成词语素,所以尽管“理发”“鞠躬”等结构中能够加入其他成分而意义不变,但它依然是一个词,在本文中不再对此类情况进行讨论。
1.含动语素双音结构的定性方法
大多数实词都具有指称性特征,即多数实词都是人们认知中最小概念的命名。但用词的指称性特点辨别双音合成词和双音短语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双音结构中不包含动词性语素时我们无法进行辨别,因为任何一个名词性短语都具有指称性,只是名词性短语所指称的不是人们认知中最小的单元,而是最小认知单元集合在一起所代表的概念或事物。所以我们认为,双音结构定性需要分为两种情况:判定其组成语素的性质,若语素中包含动词性成分,则用“指称性”特点区分其性质;如果一个包含动词性语素的双音结构具有一定的指称性,则该双音结构为词,否则为短语。如:
(1)主谓结构。“我吃、他洗”代表了一种陈述关系,陈述了一件在某个时间发生了或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是短语;而“拳击、面试”却分别指称了两种活动,是词。
(2)动宾结构。“洗碗、开车、做饭”代表了一种支配、涉及关系,谓语“洗、开、做”所涉及的宾语分别为“碗、车、饭”,所以是短语;而“道歉、投票、躺椅”等意义更具整体性,指称了一种具体的行为或物品,是词。
(3)状中结构。“快跑、慢走”结构成分之间是一种修饰关系,“快、慢”分别作为修饰语强调“跑、走”的特点,所以是短语;而“倾销、席卷”指称了某一种手段或态势,是词。
(4)动补结构。“吃完、说清”代表了补充关系,“完、清”补充说明了“吃、说”的结果,所以是短语;而“压缩、推广、扩大”分别指称某种动作、行为或趋势,是词。
(5)联合结构。“吃喝、玩乐、唱跳”,语素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每个结构都分别指称了两种行为,所以是短语;而“游击、合唱、推选”指称了某种战略、方式或行为,是词。
可见,当我们抓住了绝大多数实词“指称性”这一特点,对于双音复合词与双音短语的辨析,尤其是结构中包含动词性语素的双音结构(如绝大多数的离合词),就能够非常轻松地辨别。
2.不含动语素双音结构的定性方法
对于双语素结构不包含动词语素的情况,假设我们要判断的结构是“AB”,我们应该在“AB”结构中加入“C”成分(符合卞觉非“保持语法结构的扩展法”),如果在此结构中加入别的成分后,它依然能够实现扩展之前的指称性,那么可以证明成分的结构松散,应被归为短语,反之则为词。如定中短语“好人、热水、深坑”,联合短语“风雨、天地、冷热”,我们可以在它们中间加入其他成分,如“好的人、热的水、深的坑”,“风和雨、天和地、冷和热”,其指称性没有产生太大的区别。而定中结构的词“冰箱、小说、热心”,与联合结构的词“途径、人物、骨肉”,它们的结构固定、意义整体性高,不能用其他成分隔开而表示相似的含义。
(三)语境对短语性质的转化作用
通过以上方法较易判断静态下的短语和词,但在动态的语境下,短语和词之间有时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在静态语言中的短语,可能在动态的言语中失去原有特征而具备词的特征。如“红花”这一结构,中药店的老板会认为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在结构中加入其他成分便会失去原有的指称性。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短语,因为通常情况下,在它中间插入别的成分其指称性变化不大,“红花”语义约等于“红的花”,它的语义凝固性很低,是一种临时的组合。而小孩子可能会认为“红花”是一个词,因为在他们的理解中,“红花”象征着老师对自己的认可和奖励,对于他们来说“红花”所具有的象征义是“黄花”“红的花”都不具备的,而这种象征义是结构整体所蕴含的,具有整体性和抽象性。此外,如果说“明星们是电影中的红花,而群演们只是绿叶”,在这样的语境中,“红花”又代表了“主角、中心”等比喻义,也应该被看作词。
双音节是词的主导形式,但短语也有双音形式,因而双音复合词与双音短语存在着易混淆的关系。但还是存在为双语素双音结构定性的方法,对于含有动词性语素的双音结构,可以通过判断其是否具有“指称性”而为其定性,若没有指称性则为短语,有指称性则为词。若能将“指称性”判断标准与学者前辈所提出的“保持语法结构的扩展法”相结合,便能够很好地为双音双语素结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