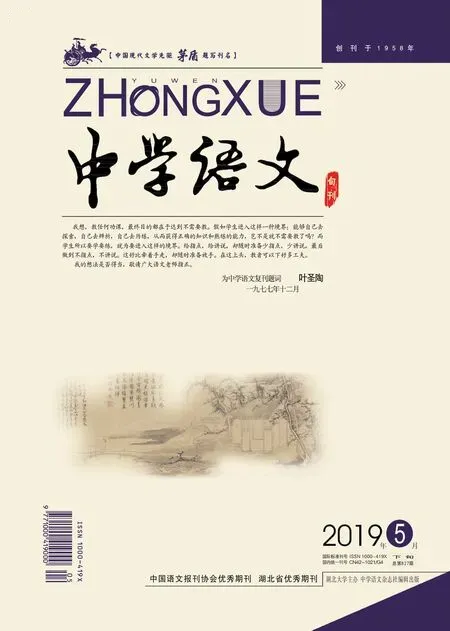角色错位与情感错位
——由《皇帝的新装》的讽刺艺术说开去
马 莉 张利波
《皇帝的新装》是一篇很接近小说的童话。说它“接近小说”,是因为文章揭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心照不宣的谎言,其讽刺意义已经超越了一般童话的道德教化价值;并且,文章也具备了小说情节(冲突)的要素。
作为传统篇目,本文在中学语文教材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在“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传统的小说情节理论的影响下,课堂教学对文本解读多流于泛泛,缺乏足够的广度和深度。笔者运用孙绍振先生的小说“错位”分析理论,从艺术功能的层面尝试对“皇帝”这个形象做一分析,以期为教学同仁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和借鉴。
一、角色错位:文学与历史共同的艺术选择
文章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这个荒诞故事的始作俑者就是一位有着奇特癖好的荒唐的皇帝。作为一国之君,他本应朝乾夕惕,宵衣旰食。但安徒生却一反常态,将人物打出常轨:
“为了要穿得漂亮,他不惜把他所有的钱都花掉。他既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喜欢去看戏,也不喜欢乘着马车去游公园——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他的新衣服。”
这个“爱衣如命”的嗜好有问题吗?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这一系列行为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所为,读者还会感到荒谬吗?或者说,文章还能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吗?显然不能。这就是角色错位带来的喜剧效应。
童话中的人物自然都是虚构的形象。但这样的虚构为什么不仅没有让人觉得“假”,反而觉得很“真实”呢?因为读者在阅读之余,能于其中看到自己隐隐约约的影子,或是文章所折射的历史现象——就帝王而言,历朝历代角色错位者并不罕见。
高雅者有之:南唐后主李煜,精书法、工绘画、通音律,醉心经籍,不问政事,终致亡国下狱。作为诗人,他是个神话;但作为皇帝,他是个笑话。宋徽宗赵佶,在危机四伏的北宋末期,除了治国安邦发政施仁修整武备等帝王之事外,他于奇花异石、飞禽走兽表现出极大兴趣,尤擅笔墨丹青,“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最终酿成“靖康之变”。
平庸者有之: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对当皇帝处理国家大事没兴趣,却对做木工活极为热心,没事就拿着刨子、锯子对着木料又削又斫,做个椅子、桌子出来,把朝政事务交由魏忠贤去处理,“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一次驾着自己设计的小船荡舟深湖,却被狂风掀翻,落水生病的朱由校服用“仙药”身亡,终年23岁。
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文学形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其位,不谋其政”。
所谓“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由“皇帝爱新装”引发了一连串的“错位”的连锁反应:本应竭诚尽节的老大臣却选择了背叛,本来诚实、高贵的官员、骑士选择了欺瞒,满城的百姓竟然也对谎言选择了盲目地认同!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闹剧,而且具有了警策的色彩,让读者由捧腹大笑转向冷静思考: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人性的异化?——这正是“角色错位”艺术手法的高明之处。
二、情感错位:将隐藏在常规背后的人性放大到极致
夸张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也是一种写作技法。除了“该干什么不干什么”这种角色的错位,文章还把皇帝对衣服的喜好做了一番夸张的描述:
“他每一天每一点钟都要换一套衣服。人们提到他,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
爱衣服这种行为本身并没有错,但一个人对一件事物爱过了头,就容易犯错。一个皇帝,每天每一小时都要换一套衣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只不过作者把“喜好新衣”做了一个放大,将这种情感渲染到了极致,人物形象、情节发展俱由此而来,文章便有了更高的审美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夸张也是一种错位,我们称之为“情感的错位”。
文学创作,尤其是批判现实的讽刺文学,似乎特别钟情于以这种手法来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限于篇幅,本文仅列举两例。
其一是严监生,最为精彩之处当为“严监生之死”的描写:
“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著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却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这段堪称神来之笔的描写,将一个封建时代守财奴的吝啬充分放大,“爱财”的情感产生了错位,超越了社会常态心理:“两茎灯草”居然成为生死关头最后的价值判断!可笑之余,又感到可怜、可悲。
其二,泼留希金。这是《死魂灵》中的人物,其经典的吝啬鬼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绝难撼动。他虽为富豪,却形似乞丐。家财万贯,但穿的衣服“后背还有一个大窟窿”,他的酒杯“装些红色液体,内浮三个苍蝇”,他的牙刷早已发黄,“大约还在法国人攻入莫斯科之前,它的主人曾经刷过牙的”,他家里的粮堆和草堆“都变成了真正的粪堆,只差还没人在这上面种白菜;地窖里的面粉硬得像石头一样,只好用斧头劈下来”。即便如此,对财富和物质的占有仍不会停歇:
“泼留希金已经不大明白自己有些什么了,然而他还没有够,每天聚敛财富,而且经他走过的路,就用不着打扫,甚至偷别人的东西。”
泼留希金对物质变态的执念扭曲了他的人格,盲目的聚敛表现出对金钱近乎无知的狂热和愚昧。果戈理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故意让“贪婪与吝啬”超越正常的“喜爱与节俭”的尺度,使之产生错位,把一个正常人沦为行尸走肉。“可笑”已经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感觉,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惊诧!
三、突变与对转:源于错位的审美功能
在梁释慧皎所撰的《高僧传·晋长安鸠摩罗什》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如昔狂人,令绩师绩线,极令细好。绩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粗,绩师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细缕。’狂人曰:‘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良匠,犹且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织师,师亦效焉,皆蒙上赏,而实无物。”
当然,这则寓言是来阐扬大乘佛教“有法皆空”的要义,但从人物和情节的角度来看,故事与《皇帝的新装》极为相似。不同的是:一个是骗子抓住皇帝的心理,从头至尾编造谎言,因错位而行骗;一个是敷衍狂人的无理取闹,先实情而后谎言,由欺骗而错位。虚幻与现实的交织,真与假的碰撞,均与“错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早就提到过“突变”与“对转”的概念,意即打破常规,形成反差,从而把人潜在的、不像他平常的那一面暴露出来。艺术创作和文本解读都应了解这个方法,否则,作品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反思,而阅读也只能停留于“形而上”的空泛分析,不易达到贴近文本的细致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