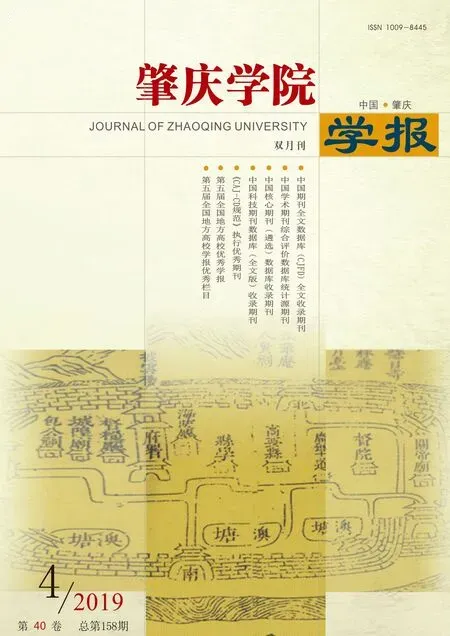失序的两种形态
——以王威廉《获救者》和陈崇正《黑镜分身术》为中心
冯 军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作为当代作家,王威廉和陈崇正承袭严肃文学的伟大传统,对当下现实有其独特的思考。以王威廉《获救者》和陈崇正《黑镜分身术》为中心的一系列作品即为他们的思考成果。《获救者》讲述了“我”“胖子”和“眉女”三人误打误撞进入全由残疾人组建的地下国度塔哈国,在参观塔哈国时不断发掘其政治、文化和人性的方方面面。《黑镜分身术》共由五部短篇小说组成,主要是围绕“半步村”和“半步村”村民发生的一系列荒诞事情而展开的乡村怪史。王威廉和陈崇正为我们展示了两幅充满失序的现代文明图景。所谓的失序,是相对于有序而言的秩序混乱、变形,它事关病态、流动、紊乱、物化等失序的现代图景。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所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都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波德莱尔也曾有言,“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2]。也就是说,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人类丧失了确定性和秩序性,社会就处于失序的状态。王威廉和陈崇正的笔下,都对现代社会的失序状态有强烈的自觉表现,现代风景的病态和混杂,诸如现代人身体的物化、分化与变形,现代人记忆时空的紊乱等。
一、失序的风景
现代小说中的风景书写,绝非仅仅提供故事发生的场域那么简单,风景是“有意味的风景”[3]。它“往往超越了背景设置的需要而具有人物和情节的功能,作为背景部分的风景甚至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因素,移动到前景的位置”[4]。正因为如此,人们在“风景”中“不仅发现自己的感觉和情感,还有自己的生命都与自然的无所不在的生命密切相连”[5]。王威廉和陈崇正都有意识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王威廉《获救者》中的“塔哈国”,陈崇正《半步村叙事》[6]中具有浓厚潮汕色彩的“半步村”继续沿用到《黑镜分身术》中。王威廉和陈崇正笔下的风景,都处于失序的状态,具体表现为风景的病态性和风景的混杂性。
一方面是风景的病态性。王威廉擅长用变形的方式书写风景。《获救者》开篇即为,“阳光耀眼得像电焊射出的弧光,在你的脸上切割着……尽力向远处望去,只有一片蒸腾的地汽如跳舞的火焰,所有的事物都变了形”,奠定了塔哈国“变形”而非常态的生态环境。《获救者》中的病态风景反复出现,诸如“成吨的蚊蝇在那里起舞”的“臭气冲天的垃圾堆”,“难以描述的恶臭”而“蜂巢样的洞壁”。塔哈国的风景与地面殊异,显示出后现代文明辉煌繁荣城市文明背后的阴暗、冷酷和恶劣。这种荒诞性和先锋性的写法,向上暗喻塔哈国政治生态的病态性,向下隐喻塔哈国民的病态躯体和病态心理。再如,王威廉《听盐生长的声音》[7]1中的“盐场”:“尽管天空湛蓝,但是湖水依然是沉郁的墨绿色,湖心的部分还混杂着青色与黄色,像一张饱含心事的阴沉沉的脸”,变形后毫无生气的风景,令人发出“那方圆十里还有其他生命吗”的质问。
陈崇正借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技法,将《黑镜分身术》中的停顿客栈、半步村小学、石狗阵、月眉谷、木宜寺、栖霞山等乡景的病态以一种社会观察式的想象表现出来。之所以称之为“社会观察”,是因为半步村的乡景很多都是来源于现实的广东农村,如桉树成片的速生林。陈崇正将现实广东农村大片种植速生林的现象引入小说。速生林“贪婪吸食这土地里的水分和养分,吱吱吱每天都在疯狂生长”,导致“鸟兽绝迹,泉水枯竭,大风一吹,尘埃在风中浮动,栖霞山瞬间苍老”的病态结果。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策略,是指小说中的乡景幻觉与真实混杂出现,例如村民患上鸡鸣病,人“异化”成鸡,在“黎明时分”“鸡鸣声穿过树林,掠过树梢,越过开满葵花的山泉湿地”。在半步村,诗意的乡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夹杂着恐怖魔幻色彩的病态乡景。
另一方面是风景的混杂性。王威廉笔下的风景混杂着光明与黑暗的双向度。《获救者》的世界观包括地上和地下两个层面,地上的风景只在三个冒险者的回忆中出现,呈现出光明的向度,而地下的风景黑暗、愚昧,上下两层的风景混杂书写,以加深塔哈国民生存环境之难的表现。正是这样的环境,甚至可以将来自地上的胖子内心的邪恶激发出来,也成为一个心灵不健全的人。在《听盐生长的声音》中,过分光明的盐场和过分黑暗的矿洞同时出现,盐场“乍一看上去,像是外星的风光,或是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不过看得久了,却发现这其中的变形夸张正是凸显了盐湖最重要的特点”。而矿洞“那种黑能把人憋死”,为躲避黑暗,小汀辞职画画,与“五彩斑斓的色彩”为伴,寻求光明而防止异化。老赵则被淹死于光明的盐湖里,而“我”也在躁动的心绪中准备辞职离开,但“我”对盐湖的不舍也恰恰说明混杂的风景对人性的异化和摧残。
《黑镜分身术》中的“半步村”的乡景叙事,并非纯粹的乡村,而是被现代城市文明“异化”后混杂的乡村:它夹杂有乡村的愚昧、迷信、落后和城市的资本、权力、信息、科技,从而创造出一个失序的混乱世界。一般而言,传统乡村秩序的建立依靠乡规、乡绅和村民三者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甚至乡村迷信活动也承担一部分维持秩序的作用。“半步村”秩序的微妙平衡被外来因素打破。破爷从外地引进“魂器”,它披着现代科技的外壳,是“苏俄”进口,动力是“柴油发动机”,还需要“接通电源”,表面上看是个“高科技”的现代文明产物。然而,其内核却依然是乡村迷信,要建一个“魂庙”“供奉”,甚至“魂庙”边上出现“插上香烛,烧了纸钱,拜祭起来”的风景。“我二叔料想魂机已经生气了,咕咚咕咚磕了三个头。咕咚咕咚只是他心里的声音,土地绵软,磕头如栽葱,其实并没有任何声响。我二叔在心里默念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这些活动,甚至还通过“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平台”“在网上公布”传播。所谓披着现代科技的离魂术、分身术,不过是城乡混杂后的“迷信”巫术罢了。
总言之,风景作为人之生存空间,王威廉风景的失序,是在现代文明的政治、权力、暴力等因素的摧残后,现代人精神失序的影射。陈崇正乡景的失序,是城乡互动的结果:资本和权力介入乡村导致乡村失序,乡村中难以拔除的顽固落后伦理因素将外来的城市文化沾染成乡村的色彩。
二、失序的身体
与风景一样,身体也是有意味的形式,“身体不仅在生理意义上是人类存在的基础,而且与人类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8]王威廉和陈崇正对身体的关注也呈现出失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身体的物化。《获救者》身体物化表现在身体的影像化。塔哈国“领袖”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他统治国民的方法是以影像传达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领袖”甚至计划以影像作为媒介,在自己死后继续统治国民,以图千秋万代。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以推翻“领袖”为目的的“叛乱”成功后,“领袖”被杀,但国民依然继续崇拜“领袖”的影像。“领袖”作为一个“巨人”,其影像化象征着身体作为权力的符号而出现,物化的身体为统治人心服务。《黑镜分身术》中,人类身体的物化有两个可能性。一是人身化植物。《离魂术》中,“半步村”村民对自然肆无忌惮地破坏,换来自然的报复,“树皮病起源于半步村,自从竹柳霸王树速生桉等进入半步村之后,一种新型的病毒也就随着入侵,树皮病毒开始只感染部分树木,主要以速生林为主,但后来逐渐感染到人身上,主要的感染人群是男人,特别是男孩。”患树皮病的村民,散发出类似香蕉烂掉的恶臭,手指、脚趾疯长的指甲、趾甲盘根错节,如同树根,头发变硬,最后变成一棵树。二是人身化动物。《停顿客栈》中,“半步村”的“树皮病”消失后,“鸡鸣病”开始蔓延,病症奇特。“日出时会鸡鸣不已,血液会逐渐冷却而变成黑紫色”,临死时头顶长出了红色的鸡冠。小说结尾提到,是一种机器利用鸡屎为原料提取药物治愈了“鸡鸣病”。一如“树皮病”,“鸡鸣病”也是一种物化人性的疾病,疾病除了带来死亡之外,还带来“道德上低人一头”[9]8和“对人格的毁灭性影响”[9]38。无论是病人生病时或弥留之际受到的各种非人的苦痛折磨和非人的歧视,还是治病需要以变相吃鸡屎为代价,都是人性尊严丧失的意义所指。有趣的是故事结尾,病人吃药时说“味道还不错,挺甜的,我这杯有草莓的味道”,这种类似于鲁迅笔下麻木不仁的村民所说出来的话,将人性尊严的解构推向极致。
其次是身体的分化。王威廉《听盐生长的声音》中,“我”醉酒后,“只是别人和自己都分别不出罢了。有时想想这样也很恐怖,好像自己的体内还有另一个人,自己只是代替那个人活着,当这个自己丧失意识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出来掌控生命了。”通过醉酒,作为主体的我一分为二,以无意识的状态进入现实生活,这其实是对现实生活各种戒律的规避。现实与虚构中各有一个“我”互相分化、互相替换,人心在复杂而重负的现实世界得到交替性的栖息。在《分身术》中,陈崇正创造出比“离魂术”更为极致的“分身术”。“分身术”其实不算是一个新鲜事物,佛教故事“若为化得身千亿”,道教故事《神仙传》《女仙传》《仙传拾遗》都有记载。最经典的可能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分身变化了。然而,陈崇正的分身术与神话传说有很大的不同。“分身术”是为应对现代人生存困境而提出,“谁也不想做自己,谁也想分身”,对现实社会和自我现状的不满,“他们是同一个人分身出来的,线性的命运被拆分成三个线段,三个人分别选择了人生的不同阶段去生活。”然而,分身导致的问题也很明显,正如陈崇正自己所言,“分身是欲望膨胀的表征”[10]。乡村在城市的面前,欲望不断膨胀,这是乡村处于失序的根本原因。例如,且帮主分身三个和尚,但三人形成类似于萨特《禁闭》中三人的关系一般,三个人互相算计、倾轧,加重社会人际关系的矛盾性。
最后是身体的变形。王威廉和陈崇正同时关注到人身体的变形这一现象。塔哈国国民全是由残疾人组成,或盲、或哑、或跛、或侏儒,在体制畸形的国度里生活着一群身体也变形的人们。在王威廉其它小说中,身体的变形依然存在。例如,《市场街的鳄鱼肉》[11]中“我”变形成为一个人脑鳄鱼身的怪物。王威廉《书鱼》[7]89开头就在讨论卡夫卡的《变形记》的“变甲虫”和蒲松龄《促织》的“变促织”,可见王威廉对变形的着迷。《黑镜分身术》的五部小说,人物身体的变形贯穿始终,诸如十二根脚趾、哑巴、瘸子等身体不健全的人物。
身体作为人之存在基础,无论是身体的物化、分化抑或是变形,都是身体失序的表现。王威廉笔下身体的失序,指向人灵魂的失序;正所谓“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图画”[12],所以说,政治奴役身体以达到奴役人的精神的目的。而王威廉主要诠释的是“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体”[13],身体的失序暗示着社会的失序。
三、失序的记忆
如果说风景是人之生存空间,那么记忆则是人之精神空间。毫无疑问,与风景、身体一样,记忆也与政治有关。“任何机制想要维持良好状况,就必须控制其成员的记忆”,使得其成员“忘记不合乎其正义形象的经验,使他们想起能够维系住自我欣赏观念的事件”“利用历史来美化自己,粉饰过去,安定人心,为所作所为正名。”[14]王威廉的《获救者》以奇特的想象力挖掘记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黑暗”的地下王国中,记忆被充当为“特殊的惩罚”,具有政治规训的功能。正如《获救者》中的耿先生所著《统治学》里的一句话:“破坏他们的回忆,然后对其进行奴役”。塔哈国国民的私人记忆与官方记忆对立而存在。官方记忆是以《塔哈史》为代表,它以正史的形式记录塔哈的建国史和发展史,呈现严密的逻辑性和正统性;与之相对的私人记忆,处于被压抑和被规训的处境,甚至于被破坏的失序状态。首先,记忆的失序体现在统治者以记忆为手段破坏被统治阶级的私人记忆。惩罚塔哈国囚犯的措施是背诵失序的圆周率,囚犯“背到满嘴水泡”“背到两眼翻白”“背到像神经病发作一样全身抽搐”“像高僧一样静静坐着”。这种对失序的记忆破坏个体的情感和意义感,从而消解个体记忆的稳定性和有序性,甚至清除个人记忆。其次,记忆的失序体现在统治者随意征用私人记忆,甚至必要时切除私人记忆。统治阶层通过仪器读取记忆,记忆成为阶级的手段,以最为极致的方式消解被统治阶级的隐私权以稳固统治。而切除记忆,是一种人为控制的遗忘,遗忘“通过扫除过去的碎片,可以走向净化和再生之路”[15]。塔哈国以机械的方式生产记忆和人性,这种在统治者看来规则性的秩序记忆对于个人而言,实则是缺乏完整性的失序状态。
如果说王威廉的记忆失序性与政治关系密切,而陈崇正的失序记忆主要表现在时空上。
一是记忆的时间性紊乱。小说的开头往往是作家构思最为着力的地方之一,《离魂术》开头:“破爷进村了,他带来了魂机。与他十几年前带来电影不同,这一次,他没有将半步村的晒谷埕霸占下来,而是将魂机直接推进我二叔的停顿客栈。村里的老人还将这架古怪的机器的到来,和一百年前传道士带着笨重的照相机来到这个岭南小城的情景联系在一起。”一百年前的照相机、十几年前的电影、如今的魂机,三个时间段和三个物件意味着:时间线性流逝,但现实缺乏实质性的变化。在半步村村民的视域中,百年记忆反复地错乱、重叠、延伸。易言之,时间在记忆面前失效,村民的记忆是以事件而非时间的形式记录,故而紊乱不堪。如果把《离魂术》《分身术》《停顿客栈》《黑镜分身术》《葵花分身术》五部小说作为五个叙事单元,并对其进行时间顺序上的排列,我们会发现,故事中反复出现“这一年”“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多年以前”“几年以后”,时间感十分模糊。而以人物出场的顺序和关系排列,我们发现问题更为复杂,五个故事似乎是同一场域同一时间段发生。这可能并非陈崇正小说的漏洞而是有意为之,作者在制造紊乱的记忆。二是记忆的空间紊乱性。魂机的作用是“将导入正常人的美好记忆,输送给树皮人,让树皮人逐渐恢复直至痊愈”。利用魂机,记忆可以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这是属于记忆的空间转变。甚至,记忆的空间转移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即“买卖记忆”:“记忆是最宝贵的,储存起来之后,日后可以制成各种游戏和虚拟现实世界。最终,是要实现从离魂术到分身术的过渡”。这意味着同一份记忆可以共享,隐私的自由流动导致记忆体和世界的双重紊乱。《黑镜分身术》中的记忆与《获救者》不同,这里记忆作为资本存在。破爷收集记忆,为了使“魂机”成为“一台具有记忆储存功能及善恶分析功能的机器,就相当于一个上帝”,尽管他反复申明“魂机不是以公开他人隐私为目的”,而是“制约”“人性之恶”。但是,这种记忆空间性的流动进入资本市场后,资本和权力的运作导致“半步村”反复谣传“莲花山工程、记忆买卖、信仰、卢寡妇通奸、绯闻、他以前的那个,等等”话题,而致使整个乡村更为混乱。
塔哈国是一个具有强大隐喻系统的“异托邦”,统治阶级对个人记忆秩序的破坏,意欲达到破坏个人精神层面的健全性,以返照塔哈国民身体上的不健全,从而使人之为人的尊严全线崩溃。陈崇正在小说中提到霍金的《时间简史》,显然,作者从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中借来时空观念处理记忆问题,以图更为真实地反映半步村记忆时空性的紊乱,以反映农村生态的动荡。
秩序素来是中国伦理道德追求的理想境界,《国语》有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即是此理。当进入资本快速运转的现代文明社会,传统秩序随之坍塌。王威廉、陈崇正先后于1982年、1983年出生,是和“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一代。而王威廉求学并立业于广东,陈崇正更是土生土长的广东潮汕人,他们对经济快速发展的广东的各种失序的现状体会甚深。不同的是,王威廉的失序,是人之精神层面的失序,人们心中的道德感随着时代大环境的变换而丧失,人心动荡不安,性恶占据上风,正因为如此,王威廉发出“世界是没有希望的,除非人心能被驯服”[16]的呼喊。陈崇正笔下的乡村,是城市文明暴力干预后的乡村,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愚昧、永恒与瞬息纠缠错节,是已然支离破碎的混乱乡村。
“失序”是王威廉和陈崇正两人小说主题的特点,但也是缺点。王威廉的《获救者》无疑是一部隐喻性极强的小说,但“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显隐关系有时过于暧昧,给读者一种想要“藏”住,但又情不自禁“漏”出来的感觉。这导致小说表达主题的愿望过于急切,破坏了小说的批判性。陈崇正的语言稍有失序混乱之感。例如《黑镜分身术》,常常在不必要的地方“爆粗口”,或者插科打诨穿插网上流传甚广的“段子”,破坏小说叙事的节奏感和严肃性,给读者阅读时造成一定的杂芜体验。除此之外,作为村民的二叔竟然张口闭口就是“另辟蹊径”“棋逢对手”“渐入佳境”“焦头烂额”等一系列文绉绉的成语,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两位作家都不足不惑之年,但都已具备描述人性或社会失序的能力,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往后的创作技巧能更为成熟,也都能对这种失序的人心和失序的乡村“恢复了秩序”[10]给出更为深入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