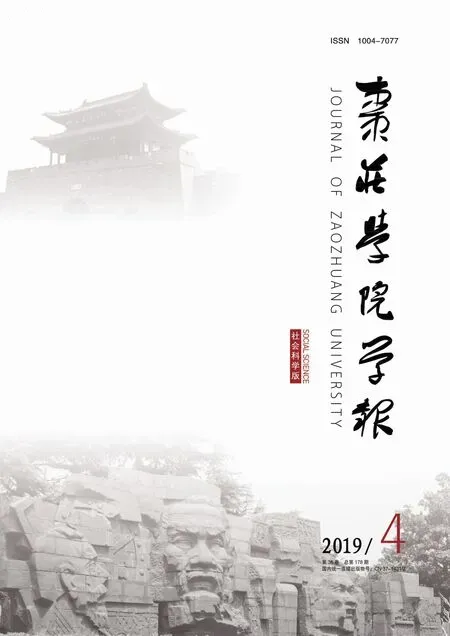历史情怀与自由伦理批评
——评路文彬《中西文学伦理之辩》
胡莎
(1.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2.华北科技学院,北京 东燕郊 101601)
出于对人们生存现状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情观照和期待,路文彬教授致力于文学伦理研究和批判,探索伦理视野中的当代文学世界,数十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日前又出版学术新作《中西文学伦理之辩》,该著作从“主体与服从”“自由与个体”“反抗与崇高”“善恶与正义”“男权与女权”等方面展开了富有前瞻性和建构意义的理论体系阐述;从学理角度辨别和厘清了常见的文学伦理认知误区,突显文学伦理建构主体本质存在及人伦和谐关系的社会功用和价值,并再度唤起我们生活感知与伦理思考在自由层面知行合一的初心。
托马斯·曼曾在《自由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了:“不要由于别人不能成为我们所希望的人而愤怒,因为我们自己也难以成为自己所希望的人。”我们承受着无限生命之重,似乎并不自由快乐。路文彬教授独辟蹊径,对此问题做出了如下回应:“我们源于命运,却又成就着命运。我们因为不自由,所以懂得了自由。总是有限给予着我们无限,这就是存在的真实境遇,命运永远是通过约束来解放我们的。设若没有有限与约束的话,我们可能压根就无从认识自身的存在。”事实上,我们拥有怎样的自由伦理观,就生活着怎样的命运。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偏重感性审美、关注“形而下”,导致中国文学至今不能以足够的理性对待自由的问题。从古代儒道文化到现代启蒙文学,再到当代文学,中国文学受缚于自由伦理,一直存在着自由伦理缺失、误读以及失范的问题。
不论是道家以“忘己”的方式践行着自由,还是儒家以“克己”的形式接近着自由,都是以主体的实质性放逐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无论秉持谨小慎微抑或洒脱超然的心态,实际上是出于顺应外界的苟且享乐,有赖于外在力量的接纳,无需激发和释放主体自我内在力量进行自由反抗。可见,反抗作为所有存在主体对于命运的责任性应答和自由力量显现的途径,在中国儒道文化中是缺场的。同时“作为一种矫正或回归,反抗乃是记忆的实践。反抗本身其实就是对于遗忘的反抗。自由乃是通往真理的道路,基于自由渴望的反抗正是在这一点上证明了自身的真理属性。”安提戈涅和窦娥的个案从主体实践层面表明,“个体的实质不是被塑造出来的,乃是以自身的自由意志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对于本质及其价值的清醒认知,没有到达一定的精神高度,便不可能有坚定付诸行动的反抗。古希腊安提戈涅的反抗正是对于自己女性本质诉求的服从。安提戈涅不仅用生命捍卫了自我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她同时凭借这种牺牲使克瑞昂终于认识到了自己过错,带来了希望。相比而言,中国的窦娥由于传统文化的自由伦理局限性,无法上升到安提戈涅的自由精神高度。
而中国近现代的启蒙者们虽然已经开始认识到自由的价值,但是其深度却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们在《伤逝》中不无失望地发现,子君虽然有着毫不妥协的自由意志,可是她依然畏惧于外在的未知世界,并没有领会到自由的真谛。涓生最终抛却了爱情责任重负,则表明了苟活者对于生命责任的无知和放弃,无以领会爱情的要义。他们更无法认识到痛苦与幸福的不可分离。唯有认识并肯定痛苦的价值,我们才能从超越幸福的角度重新思量人生的目的和启示。而《玩偶之家》的娜拉在自由真理的引领下,勇于告别安逸的日子,奔向完全未知的世界,即觉醒之后的行动,投身到那个等待她认知、发掘的新世界。对于自由的态度,以及作家对于自由、责任和命运内在联系的认知,是子君与娜拉之间本质性差异的原因所在。
近观中国新时期当代文学,《爱,是不能忘记的》《绿化树》《黑骏马》《人生》等经典之作无疑都存在致命的缺憾,那就是由于缺乏了对生命意义和人类命运的主体性思考,这些当代作家们没有深刻认识到爱与拯救的自由价值,致使正义和崇高、责任与爱在中国当代写作中严重缺场。
我们作为社会中的个体,离不开社会群体生活,然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现代人处在一种‘他’所想所说的东西都是任何人所想所说的境地,他并未获得不受他人干扰、独立思考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要知道,“自由的魅力来自于差异”(鲍曼语),没有差异便没有自由,如果社会群体代替了个体思考,那么个体将不再是思考主体,一旦缺乏自己独立人格和判断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众所周知,我们的传统非常强调记忆的重要性,从古代入私塾背诵三字经,到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纲,再到现在中考,高考,以及《诗词大会》《最强大脑》等电视娱乐节目,无一不在向我们着强调记忆背诵的重要性。可是我们在无休止的背诵中失去了很多,我们的大脑思辨能力一再降低水准,我们被迫记忆各种琐碎的事实,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和思想,更多的是为了适应甚至讨好社会风俗或者舆论观点。事实上,我们已被不自由的伪情感重重包围着。即使我们要做出发自内心的自由选择,也需要克服多重的阻力。
面对这个令人们感到棘手的问题,路文彬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主体,他必须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选择。”“自由对于主体固然是重要的,但主体对于自由的意识也许是更加重要的。主体需要自由,然而设若缺少对于这种自由的认识,主体便难以承当一个真正主体所需承当的责任。最终,这个主体将极有可能会因此丧失他的自由。”而一旦丧失了主体自由,那么责任将由于没有真实的根基作为支撑,良知因此无法同责任统一起来。这样一来,主体将缺失自我的位属,没有未来和历史,仅有当下;主体对于他者生命的爱与关怀、对他者困境的共同分担将被漠视,主体自由伦理中蕴含的痛苦甚至牺牲的本意也会被消弭。而真正的孤独者与众不同。他能强烈感受到自我的存在,同时又没有迷失在群体的喧嚣中,而是超越于这个群体,并清醒洞见到自己对于这个群体的责任。不仅如此,真正的孤独者由于借助了自由意志,从精神层面亲近和认同痛苦的真正本质,进而理解到幸福的真正本质。因此,他并不拘囿于肤浅的幸福主义论调——对痛苦和沉重持厌弃甚至畏惧的态度。相反,他泰然自若从不绝望,“最终得以找到自我的和平”并实现了内心世界的丰盈和提升。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强调的:爱包容着恨,正如幸福包容着痛苦。幸福主义已使我们陷入认知的迷途,只有以自由名义承担起反抗庸俗的责任,我们的文学才得以回归本质,实现文学命运的救赎。路文彬教授这部著作的问世,无疑彰显了他充满爱与自由的历史情怀和精英姿态,真诚而倔强地前行在文学伦理人格建构与完善的漫漫长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