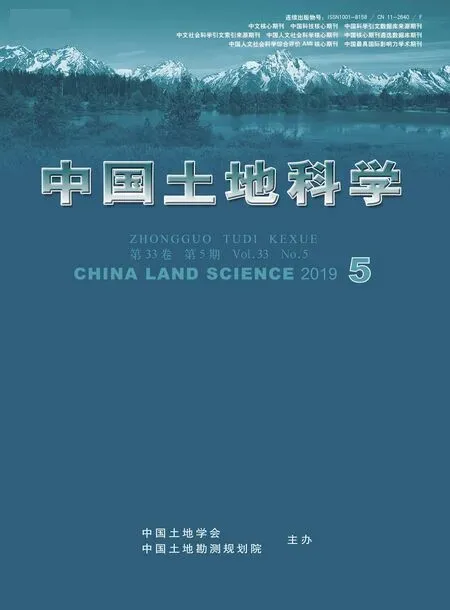宅基地“三权分置”的逻辑起点、政策要义及入法路径
靳相木,王海燕,王永梅,欧阳亦梵
(1.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9; 2.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29)
1 引言
2018年中央一号文提出,“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这是中央在总结和借鉴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经验的基础上①学界对承包地“三权分置”已展开了广泛讨论,围绕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关系,主要形成了两种代表性思路,一是“分离论”,即通过制度重构,将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分为二,以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取代之[1-2];另一种观点则可称为“设立论”,即认为时下所说的土地承包权指的就是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是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社会主体设立的下级用益物权[3-4]。这些讨论为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探讨提供了思路和养分。,提出的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一个新任务。时下,学界和地方对宅基地“三权”内涵、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出现了不同的认知,大致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宋志红等提出宅基地资格权就是现行法上的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关键在于延长宅基地权利配置链条,创设“第三项权利”[5-6]。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探索,着力在农户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宅基地租赁关系上做文章,将宅基地租赁权物权化,为宅基地租赁使用权颁发不动产证书,形成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租赁权“三权分置”格局,其背后就是这一逻辑②2018年6月20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为绍兴上虞大通市场发展有限公司颁发了全国首本宅基地及房屋租赁使用权证书。。二是夏沁等认为应当从现行宅基地使用权中分离出“资格权”,并使之成员权化,由成员权承担保障农户的身份性福利的使命,建立宅基地上土地所有权、成员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三权分置”的权利配置格局[7-8]。浙江省义乌市和德清县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中,就是从成员权的角度切入,探索了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的“落地”“变现”“置换城镇保障房”等多样化实现形式。三是徐忠国等提出从现行宅基地使用权中分离出“资格权”,并使之物权化[9]。安徽省旌德县和浙江省象山县在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探索中,就是在宅基地流转后将宅基地使用权分解为农户的宅基地资格权和社会主体的新的宅基地使用权,从而形成集体、农户、社会主体的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的权利体系。其中,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社会主体的新宅基地使用权都被视作用益物权,由不动产登记机构予以颁发不动产权证。从权利变动的逻辑看,宅基地流转后两个新的用益物权来源于流转前那个无期限的宅基地使用权的裂变,这个所谓“三权分置”的逻辑,颇受一些经济学者甚至立法部门的认同①2017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的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明确提出:“土地集体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是承包地处于未流转状态的一组权利,是两权分离;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是承包地处于流转状态的一组权利,是三权分置。”不难看出,旌德和象山对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理解,与刘振伟的说明在逻辑上如出一撤,即都是以流转与否来区分“两权分离”与“三权分置”,未流转时保持“两权分离”不变,而流转后则转向“三权分置”。。
对于以上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在延长宅基地权利配置链条上做文章,这一理论逻辑有其重要的实际意义,但由于其并未能触动现行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与财产性混同为一体的立法构造,宅基地制度在城乡融合发展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第三种观点主张在宅基地流转后,以作为母权的原宅基地使用权的消灭,换取两个在内容和责任形态上与母权不同的新子物权的设立,虽然这一做法与英美法上的产权束观念高度契合,也符合人们的生活经验,但它完全背离了大陆法上物权法的物权变动基本原理,其制度成果根本无法进入中国《物权法》②关于这一认识,笔者拟另行文深入探讨。;第二种观点着眼于破除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与财产性混同为一体的立法构造,并在成员权的范畴下理解、定位和发展宅基地农户资格权,这代表了中国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前进方向。
本文认同并拟沿着第二种观点的逻辑路径,着力厘清2018年中央一号文提出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政策要义,探索其法律内涵及入法路径。
2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逻辑起点
2.1 宅基地使用权“两权复合”构造的内在紧张
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自1960年代肇始,历经人民公社,再经过40年改革,其间虽多有演变,但总体上一直保持着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户使用权的“两权分离”构造。在“两权分离”架构下,宅基地使用权呈现出身份性居住保障权和物权性财产权“两权复合”的结构特征[7-9]。一是身份性居住保障权。《土地管理法》明确,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有资格获得宅基地,集体经济组织也有责任保障每个成员以户为单位获得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二是物权性财产权。2007年《物权法》赋予宅基地使用权以用益物权的性质,宅基地使用权得以成为农民的一项物权性财产权,宅基地及房屋成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形式。
当前实践中,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与物权性是内在矛盾的:作为身份性权利,必然要求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及保有主体限制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物权性权利,则要求自由流转。从宅基地制度的历史和内在逻辑看,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先于并高于其物权性,身份性是其物权性的前提和基础,因而身份性必然要“绑架”着物权性,限缩着物权化的广度和深度。因为,如果任由宅基地使用权彻底物权化,其身份性就很可能荡然无存,从而宅基地制度作为农村住房保障制度的社会功能定位也将彻底翻转。在宅基地使用权身份性的“绑架”之下,基于房地一体法则,农村房屋所有权也无法顺畅转让、抵押[10]。
2.2 “两权分离”架构下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困局
针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绑架”其物权性的突出矛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下,2015年以来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县(市、区)开展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天津市蓟县等59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试点。总体上看,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在保障农民取得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和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等方面作了积极探索。但试点结果显示,“两权分离”架构下的宅基地改革试点工作陷入困局:(1)宅基地有偿使用范围偏小,单纯对超标占地和“一户多宅”等收取有偿使用费;(2)宅基地流转范围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抑制了交易需求;(3)农民住房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一并抵押时,抵押物处置的受让人原则上限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导致银行业金融机构难以行使抵押权[11]。
过去三年多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表明,在宅基地“两权分离”架构下,宅基地使用权只能“一身二任”,即:既是身份性居住保障权,又是物权性财产权。在无法打破这个“两权复合”结构的情况下,对于盘活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来说,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收效也无法达到预期。特别是,很多进城落户农民早已在城市安家乐业,但仍保有其宅基地和房产,导致大量农村宅基地和农房闲置,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一困境是“两权分离”框架内宅基地制度改革不可逾越的障碍,也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逻辑起点。
3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要义
针对“两权分离”架构下宅基地改革困境,2018年中央一号文另辟蹊径,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新思路,开辟了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新境界。
3.1 文义解释
文义解释的方法,就是从文本的一般字面意义来理解其政策涵义。从文义解释的层面看,2018年中央一号文这一段表述,是讲给广大人民群众听的,不但要让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听得懂,而且更要让普通农民群众听得懂。所以,这段话不是“法言法语”,而是朴素的白话,是政治的、大众的语言,其中的“资格权”“使用权”“财产权”等术语与中国现行法上的相关概念显然并不对应。这种朴素的白话,有利于中央精神的宣传、贯彻和落实,但同时也确实给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入法带来一定的困惑[5]。但透过这段不足百字的表述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领会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基本含义:一是宅基地“三权分置”这个新提法,是指向“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的重要一环;二是要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就是要让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适度流动起来,其底线就是“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三是在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的同时,不能侵蚀农民享受住房保障的资格权,不能出现让农民流离失所的情况。
这一段文字所蕴含的内容是丰富的、崭新的,明确了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新目标,既让宅基地适度流动起来,解决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问题,又不能影响农民的居住保障;同时,也指明了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新任务,即将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独立出来,并以宅基地资格权来保障农民的居住权。
3.2 结构解释
结构解释的方法,就是要把关于宅基地“三权分置”这一段表述置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全局中来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置于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系列论述中来理解。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是乡村振兴,有关宅基地“三权分置”的论述放在“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这一节中,并在这一节中置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个题目之下。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个题目中,一号文先提出要系统总结2015年以来包括宅基地制度改革在内的农村三项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再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新论述。这表明,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在2015年开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基础上,中央审时度势后提出的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新目标、新任务。也就是说,2015年开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在解决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问题上的成效不如预期,中央这才进一步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新目标、新任务。
其一,考虑2007年《物权法》已经将宅基地使用权定性为用益物权,联系2015年开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任务和目标,以及中央关于承包地“三权分置”的要求,这个“新”指的就是要让“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独立成权,使之成为有别于宅基地使用权的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创设“宅基地农户资格权”,是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最大创新点。将宅基地资格权等同于现行宅基地使用权的认知[5-6],是对中央一号文的最大误读。至于宅基地农户资格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利、如何独立成权以及如何入法,从中央一号文则无法窥得一二,须后续的立法研究才能解决。
其二,这个新思路提出的改革突破口,就在于消解和打破宅基地“两权分离”架构下现行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居住保障权和物权性财产权“两权复合”结构。循着这一突破口而推动的改革重点任务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的独立成权,让农民的身份性居住保障权找到新的权利载体;另一面就是将现行宅基地使用权转型纯化成为典型用益物权,可以转让、出让、出租和抵押。只有这两个方面改革的同步联动,形成全新的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宅基地使用权,再加上中央一号文件讲的“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才称得上宅基地“三权分置”。
本文引言总结的第一种观点及实践中对应的做法,实质就是忽略了现行宅基地使用权的“两权复合”结构这个最大矛盾,而单纯将宅基地租赁权物权化,这其中的法理逻辑及立法例其实早已有之,实在没有必要冠之“三权分置”的新名词。
3.3 原意解释
欲准确理解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宅基地“三权分置”论述的含义,还应当深究决策者的原意。这个“原意”就隐藏在宅基地“三权分置”要解决的问题中。在“两权分离”架构下宅基地制度也使农民宅基地的资产功能被“架空”,在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潮流中,这一制度势必造成大量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如何解决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大量存在的问题,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痛点所在,更是推动“钱、地、人”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的关键着力点。在这个问题导向下,中央提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相应地,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政策目标就是既要坚持宅基地制度的农村住房保障功能定位这个“定海神针”不动摇,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又要让宅基地成为农民的资产,让宅基地活起来,可以适度流转。
追寻决策者的原意,独立成权的宅基地农户资格权承载的是对农民的居住保障功能,旨在实现农民住有所居全覆盖;而转型纯化为典型用益物权的宅基地使用权,承载的则是资产功能,通过宅基地活起来,增加农民宅基地的财产价值。将现行法上的宅基地使用权转型纯化为典型用益物权,其流转的受让人突破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范围是宅基地“三权分置”的题中之义,也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对以往宅基地“两权分离”架构的突破点之所在。允许社会主体从宅基地使用权人手中取得下级用益物权,如本文引言总结的第一种观点及浙江上虞区等地的探索,也必然构成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重要内容。
4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入法路径
4.1 宅基地“三权分置”入法的“接口”
所谓宅基地“三权分置”入法,就是要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成果最终融入并自洽于改革开放四十年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而不是自外于中国的法律体系。宅基地“三权分置”入法的“接口”就是中国《民法总则》,即首先应在《民法总则》列举的民事权利类型这个坐标系中对宅基地“三权”分别进行定性,确定其各自所归属的权利类型,在此基础上,方可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成果联接融入相应的民事权利制度体系中。
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代表了中国民事权利类型化立法的最新成果。《民法总则》第五章109~127条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公民享有的民事权利类型,包括:人身和人格权、财产权利、继承权、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其中,人身和人格权具体又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以及婚姻、家庭等关系产生的人身权利等子权利;财产权利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具体类型;对继承权、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则未再具体细分。第126条“民事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是一个兜底条款,即在《民法总则》上述民事权利类型之外,其他法律也可以规定并形成新的民事权利类型。
科学界定宅基地“三权”的法律内涵、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政治的、大众的语境下的宅基地“三权”,转换为中国《民法总则》列举的民事权利类型这个“坐标系”中的权利类型概念,使之在分别遵从其所属民事权利范畴的基本规则的基础上建构、展开并形成各自的具体法律制度。
4.2 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
宅基地“三权分置”中的宅基地所有权,属于《民法总则》第114条列举的物权类型中的所有权,这一点应无疑义。近年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经验表明,遵从物权法、合同法等私法规范,探索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的市场化实现形式,是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的着力点所在。但同时,不同于土地私有制国家的个人土地所有权,包括宅基地在内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得自由买卖,属于中国的宪制性制度安排,也因此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运作必须接受公法的拘束和规范。也就是说,根据中国现行法相关规定及其司法实践,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具有“公权—私权”双重属性,既要接受公法的深度介入和调整,也得接受民法特别是物权法的调整和规范。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应当通过公法和私法两条路径来实现,二者不可偏废。在公法规制方面,要坚持宅基地制度是中国特色的农村住房保障制度这个前提,在优化宅基地空间布局的同时,可适当拓展宅基地用于农村电商、民宿、餐饮、养老、科研、创意、文化产业和小型农产品加工业等用途;在私法规范方面,可从进一步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内部决策事项和决策程序入手。
4.3 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独立化
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的独立化,就是将集体成员专属的身份性居住保障权能从中国现行宅基地使用权中剥离出来,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类型进行建构,为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住房保障全覆盖找到和建构权利载体。《物权法》第五章初步明确了集体成员权制度框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在司法实践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是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民个体所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类型。《民法总则》第五章对民事权利的具体类型进行列举时,集体成员权未能名列其中。依法理分析,集体成员权显然不属《民法总则》所列举的人身和人格权的范畴,而是与《民法总则》第125条明定的股权相邻近的民事权利类型,均属成员对于其所在团体享有的民事权利。也就是说,在法律性质的理论分析上,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应属于集体成员权范畴的一个子权利,是农户取得宅基地的一种资格,是集体成员以户为单位所直接支配的专属性的身份利益。对于包括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在内的集体成员权诸子权利类型,依《民法总则》第126条兜底条款,可由其他法律予以确认和规范。
在实践经验中,农户凭宅基地资格权,可以取得一块宅基地,也可以放弃资格权的落地而取得货币补偿,甚至可以用资格权置换城镇保障住房。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直接支配的利益是身份利益,这一点与物权的性质截然不同。物权以权利人直接支配标的物为特征,而宅基地农户资格权中所包含的财产利益是间接的,即农户支配其身份利益的结果表现为财产利益,而非对财产利益标的的直接支配。宅基地农户资格权不是对财产利益的直接支配,不是物权中的用益物权,而是农户凭成员身份享有的对集体经济组织的请求权,是相对于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它只能通过集体所有权主体内部的分配机制实现。因此,对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的规范和保护,也只能从集体成员与集体组织的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入法的最优路径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而非《物权法》或《土地管理法》。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提出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立法任务,以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将宅基地农户资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类型进行建构,明确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的确认和公示方式、实现形式以及保护方法,以夯实中国特色农村住房保障制度的权利载体,构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4.4 宅基地使用权的转型与纯化
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纯化为典型用益物权后的新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成员依法行使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的结果。宅基地使用权一经设立,便独立于宅基地农户资格权。这时的宅基地使用权属于《民法总则》第114条列举的物权类型中的用益物权。不过,纯化为典型用益物权后的宅基地使用权是否还继续坚持无期性,仍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义乌市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探索中,明确社会主体取得宅基使用权的最高年限为70年;德清县规定社会主体取得宅基使用权的最高年限为30年;象山县对社会主体取得宅基使用权的则规定最高年限为20年。但是,对于农民凭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取得的宅基使用权是否需要规定一个最高期限,义乌、德清、象山等地的改革探索均未涉及。着眼于建立和谐、统一的物权体系,以及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对于农民凭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规定70年的最高年限,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对于纯化为典型用益物权后的新宅基地使用权,自然应当通过《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修法的方式,赋予其完整的典型用益物权的权能,应当允许宅基地使用权人享有自由转让、出租、抵押宅基地的权利,允许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其他社会主体设立下级用益物权。社会主体在宅基地上取得的下级用益物权,可以转让、出租和抵押。当然,对纯化为典型用益物权的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仍须在用途管制、社会资本下乡置地等方面予以适当限制。
5 结论及立法建议
“两权分离”框架内宅基地制度改革具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一个破除“两权分离”架构下宅基地使用权既是身份性居住保障权又是物权性财产权的“两权复合”结构的过程。宅基地“三权分置”后,宅基地集体所有权构成宅基地权利群的基础;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独立成为农民专享的一个民事权利新类型,在法理上属于集体成员权范畴的一个子权利,承载农民住房保障功能;纯化为典型用益物权后的新宅基地使用权,承载宅基地的资产功能。推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入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政治的、大众的语境下的宅基地“三权”转换为法律概念体系中的宅基地“三权”。
宅基地“三权分置”适时入法,方能巩固改革成果:(1)尽快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专章形式对集体成员权进行规范,将宅基地农户资格权作为集体成员权的一个子权利予以明确,并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层次对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的取得、公示方法及变动规则、实现方式等作出规定;(2)完善《土地管理法》涉及宅基地管理的相关规定,增加和完善宅基地用途管制的内容,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适度拓展宅基地用途,放松对宅基地流转的公法限制,优化宅基地审批的事权配置和流程;(3)修订《物权法》涉及宅基地的相关规定,赋予宅基地使用权以典型用益物权的性质和权能。
——修正的用益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