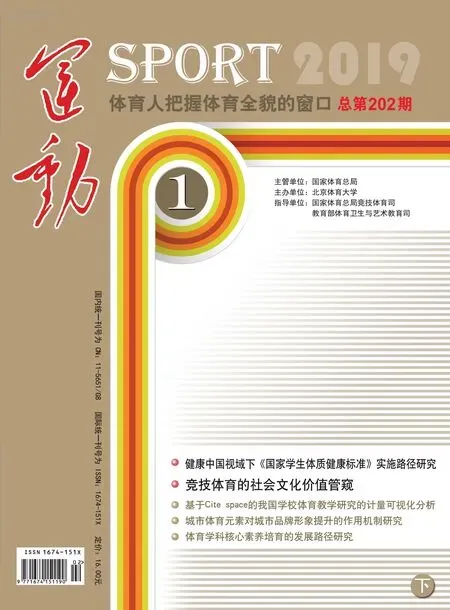社会转型期广场舞形态的社会生态考察
欧阳井凤
(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随着全民健身战略的开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体育健身需求增长。广场舞凭借其集群性、社交性等特点,获得广大中老年群体青睐。然随着“噪音扰民”等负面影响加剧,广场舞造成的非预期结果逐渐显现,引发了一系列诸如“袭粪”“鸣枪放獒”“高音炮”等冲突。广场舞被推上舆论风口成为“全民公敌”,遭受到“污名化”和抵制。本文从公共空间、代际冲突和时代背景去解读广场舞“污名化”的深层原因,旨在为广场舞冲突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路径。
1 广场舞的双重属性及治理困境
广场舞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诸多“冷热点”之一。之所以“热”在于广场舞盛行到几乎无处不在,之所以“冷”在于鲜少人关注这个近乎影响全民的事物。但这种“冷热点”形态因频见报端而开始被打破,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广泛舆论,广场舞也由“冷热点”转为“热热点”。而广场舞体现出来的“冷与热”的张力感和撕裂感刺激我们从广场舞存在状态入手去探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大众生存意境。从广场舞存在本身及其参与者来看,其并不必然导致“污名化”和治理困境,冲突的产生与其组织形式相关。广场舞具备团体操及舞蹈2属性。团体操属性青睐大规模、动作齐和节奏强的“大场面”效果。舞蹈属性需音效配合和强调表达性需求,舞蹈属性中的音效特点是噪声扰民的物理源,而表达性需求会刺激广场舞者营造更大群体化氛围或更高分贝音量吸引他人注意,这种表达性诉求构成噪声扰民的心理基础;无论音效特点还是表达性诉求都会在团体操“大场面”组织形式中得到强化,对“大场面”的追求成为噪声扰民的组织根源。
2 广场舞冲突的成因
2.1 城市对大众健身公共空间的供给不足与治理缺失
广场舞治理困境是由公共空间供给不足和管理缺失造成的。大众健身公共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居民用于健身休闲的主要载体和物质基础,是政府体育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中对健身需求预测不足和忽略,导致公共空间整体供给不足。首先,地方政府受功利思维影响往往斥巨资修建标志性建筑、景观大道等,过分寻求城市形象景观化塑造,导致大众健身公共空间建设的失落;其次,受城市高昂地价影响,无论政府还是开发商为盈利都会侵占大众健身公共用地;再次,中国官员业绩考核主要参照其所在区工业化程度,而非其公共服务质量,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最后,对现有空间管理不善导致空间有效供给不足和空间内权利冲突。大众健身公共空间布局不当导致分布失衡,城市偏远地带公共空间出现闲置,而市区广场、小区的公共空间则“供不应求”,公共空间有效利用率不高。受文化堕距影响,城市健身公共空间的治理跟不上城市化进程,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使权利主体的行为缺乏规范,而空间中权利边界的模糊则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执法难度。
2.2 代际冲突下对广场等公共空间话语权的争夺激化
广场舞冲突是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所展示出的内在张力与自我断裂。“社会转型”期集体化和个体化社会结构并存,支撑各自结构的制度体系和思想观念并行,导致身处其中的公众缺乏明确的话语体系、行为规范、道德自律等,在发生冲突时无法有效沟通而加剧代际冲突,代际冲突是两代人间因思维和行为方式差异所结成的矛盾关系。在熟人社会知识获取主要源于上一辈经验传承,代际冲突较小。进入大变革时代后,熟人社会向陌生社会转变,过往经验的失效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使代际权力发生转移,年轻人在社会地位和经济上无须再依靠父辈传承而出现代际关系的疏远。代际隔离产生的孤独感使老年人急需要新的替代关系来重新获得接纳,广场舞便成为“刷存在感”的重要形式。代际冲突的本质是话语权的争夺,在整个话语周期里老年群体处于末端,其希望通过广场舞拓展公共空间内的话语权力,达成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而处于话语周期高峰期的年轻人则渴望能代表社会主流,通过对曾占统治地位的老一辈的抨击来表达追求自我个性的思想,成为谋夺话语权的重要形式,年轻人也成为“污化”和抵制广场舞的生力军。
2.3 个体化时代对集体行为的认同分歧加剧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由“集体大众”向“个体大众”的转变,政治、经济、社会等剧烈的历史变迁,加剧了意识形态、个人信仰等方面的真空和断裂,也造成了代际间的认同危机。广场舞者多是20世纪80年代入职,而今已退休或濒临退休的中老年妇女。集体化人格与个体化社会间的裂痕构成这代人的文化危机。“文革”和“改革开放”等历史迭变使这代人先后接受了集体化时代和改革开放后的去集体化洗礼。因此,广场舞这一代人面临着集体人格和现代价值认同的冲突抉择,集体化人格特征使其注重集体主义精神和人际的亲密往来,而个体化社会的疏离感则强化了退休群体孤独感。当集体化人格对群体关系的渴求及个体化社会的孤独所引发的焦灼逐渐占据广场舞者们的无意识动机,广场舞成为进行身份认同及集体人格释放的媒介。但受改革开放个体化文化影响年轻人更重视个人空间,反感和抵制公共空间内的集体行为。这种因时代差异产生的对公共空间利用方式的不同理解使中老年人一代常被冠以“文革一代”的称号,广场舞也被媒体污名化为“文革遗风”。
3 广场舞冲突的治理路径
3.1 改善公共空间供给和管理,加强公民意识培养
广场舞冲突投射出了城市大众健身公共空间的供需矛盾与治理失位问题,公共空间供给不足是造成冲突的根源,城市公共空间结构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大众健身参与热情[6],应改善大众健身公共空间的供给。首先,政府应立足群众健身需要优先保证体育馆建设并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其次,政府部门应充分开发公园、广场等公共资源,加快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为大众健身开辟更多“免费空间”;再次,在明确政府、开发商及监管部门责任基础上建立问责制度。对占用和挪用健身用地的违法行为追责,保证公共空间用地足额供给;最后,将大众健身公共空间供给纳入地方官员业绩考核中,督促政府以公共利益为追求,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此外,还应完善现有空间治理和加强公民意识培养。首先,政府应加快大众健身公共空间管理立法,制定明确的管理制度。其次,应构建大众健身公共空间的协同治理模式。大众健身公共空间作为公共产品,涉及多方利益主体权利。在个体权利同集体利益产生冲突时,缺乏必要管理协调机制势必引发群体冲突事件。政府应承担起立法、决策、解决纠纷和平等服务的责任。最后,应建立文明公约和奖惩机制,对公共空间内的活动加以时间限制。加强对空间使用者素质和公众意识培养,对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进行规制和纠正。
3.2 重视公共空间公平性诉求,保障平等话语权力
代际权力的转移使老年群体丧失权威地位和话语权,而代际关系的疏离则加剧了老年群体的孤独感,是广场舞使该群体获得了话语权、身份等自我认同的重塑并重新获得“存在感”。但在当下“现代和发展”话语垄断下,以中产阶级为主流的群体认为公共空间应安静有序,而广场舞的聒噪与当代城市观念不符。这种对广场舞空间集群行为的排斥和抵制,原本处于话语周期末端的广场舞群体话语权利更加式微。但这种“主流话语”实际上忽略了公共空间的公平性,即公共空间对每个个体都应是平等的,恶意剥夺他人空间话语权力的行为只会使双方矛盾激化。因此,年轻人应认识到该群体的特殊性,倾听和理解其在公共空间内的正当诉求,以平和的态度去解决并尽力避免语言和行为暴力。其次,除了减少主流社会价值观念对该群体话语的压制外,年轻人还应减少对广场舞的“污名化”行为。年轻人为掌握现代社会话语权而不断推翻和否定父辈塑造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借机取代其社会地位的行为只会加剧代际间话语争夺的恶化。应正视公共空间内的平等话语权力,年轻人不应对老年群体存在偏见,更不能因鼓吹现代性而忽视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和对人的基本尊重。应加强两代人间的沟通交流,只有平等对话才能实现代际间的和解。
3.3 构建多元价值体系,规制媒体“污名化”行为
中国“文革”和“改革开放”这2个极具差异的时代断裂使当下的中老年妇女深陷身份认同危机,在公共空间跳广场舞成为该群体惯习的延续和获得自我认同的方式,但由于网络媒体对其的“污名化”和错误引导该群体备受歧视。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媒体行为的规制和引导,推动正确舆情导向的形成。媒体作为舆论的推动者,不应以带有倾向性的报道来加剧对立性,而应提供平等话语空间,让大众去倾听话语表达双方的声音。应多进行关爱老年人身心健康等相关的正面报道,呼吁社会给老年群体更多的理解和宽容。代际间在社会际遇和文化观念上出现断裂造成认同分歧时,应正视不同时代的差异性,年轻人不应通过抹灭老一辈的印记来彰显自身的现代性。在集体主义被打破,个体化生活态度和个人主义价值主导的时代,各种价值冲突和碰撞难以避免,应通过构建更加包容且体现多元价值的社会文化体系来调和。青年群体不能因时代和文化的差异去诋毁和污化老年群体及其广场舞行为,应有包容多样的胸怀和认识,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做到求同存异。
4 结 语
广场舞作为大众健身项目遭受“污名化”的背后,折射出了城市居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在公共空间、话语权力和文化认同上的一系列危机和焦虑。应通过完善空间的供给和管理、保障平等话语权力和塑造多元价值体系来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