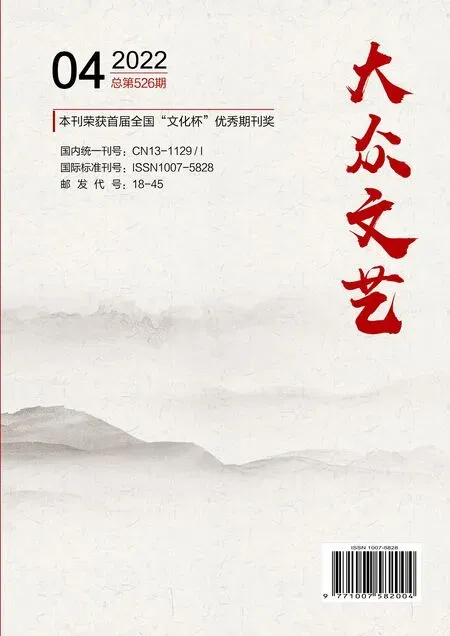唐代边塞诗与西域文化认同
——以西域边塞诗为例
王鑫悦 (宝鸡文理学院 文传院 721013)
唐诗是唐王朝为中国历史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数量之丰富,内容之广泛都足以令人称奇。《全唐诗》中收录了唐诗48900多首,边塞诗有2000多首,其中一半左右与西域有关。边塞诗的内容主要包括边塞风光、民俗风情、军旅战争等,从中可以窥见唐王朝与边疆的民族关系和文化差异,从而奠定了民族融合与统一的基础。由于唐皇室生长于北方关陇地区,血液中有明显的北方胡族的文化性格,气势恢宏、骁勇好战等特点统领了整个唐王朝的时代精神。《全唐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从边塞唐诗留下的财富中,可以看出西域与中原关系的变化与发展,本文将从西域在边塞唐诗中的异域感、认同感、归属感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边塞唐诗中的异域感
唐朝对西域的收复与治理,使得当时一大批青年之士求功心切,力图在边疆展开自己的宏图伟志,因此唐朝涌现出一大批边塞诗人。从边塞诗人的作品中也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气势恢宏、大气磅礴的西域风情。在唐朝的边塞诗人当中,最知名的莫过于岑参。岑参早期居住于嵩阳,不久又移居颖阳,由于颖阳地区奇峰峻岭,古木流泉,造就了其清新隽永、沉雄淡远的诗风。后来朝廷任命其赴安西,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掌书记。广阔的沙漠、呜咽的狂风、热烈的火山、冰冷的霜雪都成为他诗歌的素材。《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西域走马川,今玛纳斯河或呼图壁河一带的平沙、秋风、碎石、烟尘……这一幕幕都刻画出惊险新奇的环境,变化多样,为生活在中原的汉人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可以看出此时岑参的诗歌风格与其之前的清新隽永大相径庭,豪迈奔腾、新奇惊险似乎成为其后来诗风的大体走势。这种种描述不仅增强了西域对中原的神秘感,同时激发了汉人对西域的探索与渴望征服的好胜心。
除了美景,西域更多的给中原带来的是异域的风土人情。在王翰的《凉州词》中写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孟浩然“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这些诗句都为西域音乐的传入奠定了基础。李颀在《听安万善吹觱篥歌》中写道:“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傍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枯桑老柏寒飕飗,九雏鸣凤乱啾啾。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这首诗赞赏的是西域艺人所吹奏的觱篥之声,如雏如凤,如虎如龙,时而如黄云萧条,时而如春日杨柳,可见外来乐器在中原深入民心,甚至连唐玄宗也爱上了羯鼓这一少数民族特色乐器,可见交流之深入。在乐器互传之时,商业贸易也日趋频繁。以西域为主的西域文化传入中原,为唐诗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尤其边塞诗人在西域的所见所闻,使得西域的风景、歌舞、服饰都进入唐代诗人的视野。西域的舞蹈音乐通过边塞诗人的传播,在中原掀起热潮,后来甚至成为宫廷乐舞的基础。
二、边塞唐诗中的认同感
唐朝从太宗开始至玄宗,不断向外扩张,依次征服了焉耆、龟兹、疏勒、高昌等地,开通了深入西域的要道。西域对于中原的认同感一部分来自于长安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于战争的描写也经常出现在边塞诗人笔下。除了奇绝的风景和异域的风情还有字里行间的报国热情以及连年征战带来的痛苦和思乡情绪。王昌龄在进士期间来到西北边塞,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事业心强、求功心切。边塞诗通常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以王昌龄为例说明。
(一)渴望在西域大展拳脚,实现自我抱负的决心以及对报国将士的讴歌。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七首之四)
“还”字将边疆战士的心情表达的淋漓尽致,同时“不破楼兰终不还”使大唐战士的爱国无畏精神跃然纸上。
(二)战争的痛苦以及渴望和平的思乡愁绪。
秋风夜渡河,吹却雁门桑。遥见胡地猎,鞴马宿严霜。五道分兵去,孤军百战场。功多翻下狱,士卒但心伤。(《塞下曲·秋风夜渡河》)
唐代到了开元天宝时期,统治集团昏庸失当,导致出现了穷兵浪战的情形,战士思乡之情溢于言表。王昌龄深入西北边塞,亲历战争,他能够较全面的反映当时的边塞生活。因此王昌龄虽然边塞诗数量不多但篇篇皆佳品。
边塞诗人描绘的边塞场景而引发的种种感触,会不自觉地复现以往历史画面,为我们研究西域西域提供资料。同时诗人笔下的西域为我们揭开了西域世界的神秘面纱,边塞的断壁残垣、黄沙狼烟、高山大漠都是民族融合的见证者。连年的征战不仅对唐朝来说是损耗,对于当时西域诸国来说更是不小的损伤,因此与唐朝保持臣属关系是最佳选择。
唐朝在扩大疆域之后,对于西域的经营力度也十分强大。修驿馆、军民屯田、提高生产技术……互市使者应运而生,唐朝十分看重与边疆地区的互市,甚至为顺利进行互市,还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互市监。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大量西域人民流入中原,在长安日趋形成民族大融合的走势,盛极一时的长安,突破传统,打破框架,不断地引进和吸取,为历史上的长安盛世打下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
在强大的军事保障下,西域与中原的经济交流日益密切,文化交流也促进了西域与中原的民族融合。边塞诗中通常将出征的军队称为汉军,将领称为汉将,甚至边塞的月亮称为汉月,这里的汉指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代称。汉族意识从边塞诗中便不断向边疆渗透。同时,唐朝开放的政治环境吸引着无数西域人民。西域疏勒人裴沙(644-724)便由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唐朝廷任职,后甚至成为政治精英。据《裴沙墓志铭》记载,疏勒人裴沙在唐朝前期定安西四镇的军事行动中立下战功,之后居住在洛阳;中亚粟特地区的许多贵族也在此时来到洛阳。西域人民于长安任职且官居要职,这不仅是政治上的相互渗透,同时更是以西域为主的西域人民对唐朝各个方面的肯定与认同。
三、边塞唐诗中的归属感
民族融合是多渠道的,边塞诗也体现在各个方面。边塞诗的产生与一个民族的疆域意识有关。不可否认,唐朝统治者的疆域意识十分强烈,爱国情怀、领土守卫问题也随之产生。从不少边塞诗中可以看出,中原与西域的人文交流已十分深入,从边塞诗人的胡化到西域人民入长安任职,无不体现了汉疆的渐进融合。除了政治上的相互渗透,艺术歌舞上的互通也是最好的体现。充满异域风情的舞蹈在隋唐时期一度成为宫廷乐舞的基础。同时,“越罗衫袂迎春风,玉刻麒麟腰带红。”这是唐代诗人李贺对古代汉服的诗意化描述,服装、饰品、妆容也都引得西域女子的争相模仿。
唐代词人牛峤在《定西番·紫塞月明千里》里说到:“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殊不知,长安不仅是边塞诗人的梦中地,同样也是生活在苦寒边境人民梦中向往的福地。世人皆向往繁华,而当时正处于世界中心的长安又是多少人心中的梦。边塞唐诗就像一面镜子,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了参照。以史为镜,西域于唐朝时期便成为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护府的设立更加巩固了西域的稳定与安全。固西域远在天山之外,地域偏远,从史至今仍吸引着无数中原之士甘愿前往。这不仅仅是政策的需要,更是汉疆人民心于一处,血溶于水的浓浓体现。
通过梳理唐代边塞诗,不难看出以西域为主的西域地区与中原的关系源远流长,唐诗是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超越空间、时间、民族、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友谊桥梁,边塞唐诗不仅是两个民族血浓于水的纽带,也是我们不忘历史的证明。西域文化极大地拓展了唐诗的创作视野和范围,丰富了唐诗的内容和题材。同时,唐诗也为西域人民带去了中原的强大与和谐。边塞唐诗在促进中原与西域深层的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实现了两个民族内在的沟通和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