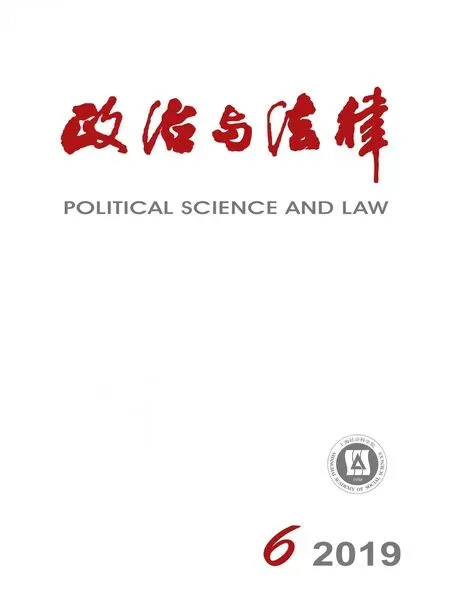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司法适用之检讨*
——基于277个案例的裁判文书之分析
(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一、问题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保险合同为约定投保人缴纳一定的保险费,保险人承诺在特定事故发生给被保险人造成损害时向其给付一定保险金的契约。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危险测算极为重要,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保险人约定保障范围进而计算保险费的基础。保险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保险标的危险增加的情形时有发生,考虑到此种危险变动是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所无法预见的,且大数法则下的保费计算也并未将这些情形考虑在内,此时如果仍强调合同严守原则,让保险人在既定保费的基础上提供同样的保障,显然并不合理。因此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会在保险成文法或保单中赋予保险人在一定条件下变更保险合同或免于保险金给付的权利。[注]在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皆在保险合同的相关成文法中规定了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在英美法上,保险人一般会在合同上约定对于由于被保险人原因导致之危险增加其免于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See Note, The Increase-of-Hazard Clause in the Standard Fire Insurance Policy, 76 Harv. L. Rev. 1472 (1963), Donald N. Clausen, Increase of Hazard as a Defense under a Fire Insurance Policy, 1955 Ins. L.J. 660(1955).也正是秉持此种指导思想,我国《保险法》第52条第1款规定了被保险人危险显著增加之通知义务,并赋予保险人在被保险人义务履行后变更和解除合同的权利(但以合同约定为前提);该条第2款则规定了当被保险人没有履行此义务时保险人可对于部分保险事故的发生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虽然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已经被纳入我国实定法,但从现有条文出发,该义务至少在司法适用层面可能面临着以下三个困境。其一,通说认为对价平衡、最大诚信与情事变更三原则构成了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则构建与司法适用的理论基础,但关键在于这三项原则的价值取向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一致,存在可能的冲突,需要协调,现有规则似乎没有妥善地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挑战,因而有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与解释论上加以矫正的必要。其二,我国《保险法》第52条虽然明文规定保险人可在被保险人违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时在一定条件下主张免责,但一旦涉及保险人是否可免责的判断,裁判者出于同情被保险人弱势地位的心态,一贯倾向于通过援引其他规范(诸如强调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来尽量限制保险人的免责可能,[注]保险实务中较为常见的做法是保险人会将法律规定的免责规定在保险合同中再以免责条款的形式加以呈现。在某些情况下此种限制并不妥当。该问题亦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其三,考虑到不同的保险合同中保险标的危险增加的情形其实有着显著的差异,实定法在危险是否增加的判断上采用了较多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在保险人可否免责的用语上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可谓留给了法律适用者较大的法律解释甚至续造的空间。这固然可以使得司法裁判保持一定的弹性,以便应对复杂的社会生活事实,但也容易产生裁量标准不一以及可能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因此如何通过理论的深入阐释和方法论的指引来提高判决的确定性,就成了学界亟需解决之难题。近年来,在共享经济的背景下,由于物的用途以及使用人随时会发生变化(典型的如网约车中自用和营业使用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晰,这两种使用方式所引发的危险完全不同),相关案件大量涌现,这也使得上述法律适用难题进一步凸显。
正是为了统一裁判尺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其第4条系专门针对危险增加的判断难题而设。笔者之问题意识由此而产生。在本文中,笔者拟首先分析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现有的法律规则设计有没有充分贯彻这些理论,于解释论上学界又进行了哪些有益补充,此为问题展开的起点;其次通过群案研究的方法对277个案例进行分析,总结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则适用过程中的疑难问题,[注]笔者在2018年5月30日以“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为全文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进行检索,由于案例库庞大,笔者仅选择了2016年以来的二审和再审案例,其中二审案例2016年为96个、2017年为153个、2018年为20个,再审案例总共为8个,以上共计277个案例,其构成了本文群案研究的基础。由于笔者在本文中引用之裁判文书都来自对这些案例的整理,以下笔者只标明审理法院、裁判文书名称及文号,不再标注其来源。并结合《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的最新规定检视这些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的回应;最后期待主要从方法论的层面并结合既有规则设计之理论基础在解释论的框架下提出上述疑难问题的解决途径。
二、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理论基础与实定法构造
(一)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理论基础——对价平衡、最大诚信与情事变更原则
在学理上一般认为,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理论基础有三个,分别为对价平衡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和情事变更原则,前二者为保险法的特有原则,情事变更原则则为合同法原则在保险合同法之贯彻。这三个原则是我国《保险法》第52条的设计和解释适用的基础。
保险法中的对价平衡原则和最大诚信原则的作用,主要在于解决具体的保险合同中承保风险与保费如何对应和可能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难题。[注]之所以强调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主要是因为在保险业发展的早期,保险人询问技巧不足,保险技术(诸如保险人搜集信息和危险评估的能力)之应用手段也较为落后,保险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投保人(被保险人)针对保险标的之告知来决定是否承保和以何种费率承保。由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特别强调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并将其引申为最大诚信原则,进而发展出了一整套相应的规则体系。参见初北平:《海上保险的最大诚信:制度内涵与立法表达》,《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范健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这些问题在保险标的危险增加的情形下都有相应的体现。一方面,在保险合同下,保险人所承担的风险转移义务并非无限,需受到对价平衡原则的限制,换言之,“保险人所承担之风险,与投保人所交付之保险费具有所谓保险‘对价’,须具有精算上的平衡”。[注]刘学生:《保险法上对价平衡原则初探》,载尹田主编:《保险法前沿(第三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此处的保险费主要是指纯保险费,而不包括附加保费。鉴于保险人在计算纯保险费时往往依据的是保险标的在订立合同时的危险状况,极少将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标的之危险变化考虑在内,合同有效期间一旦保险标的之危险状况发生显著增加,保险合同原本所追求的对价平衡就被打破,此时自应赋予保险人调整或解除合同之权利,以纠正可能产生的对价失衡。故学界普遍认为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设置是贯彻对价平衡原则的重要体现。[注]参见李志强:《对价平衡原则的证成——从保险合同到保险业监管的考察》,《法学》2017年第9期;张冠群:《台湾保险法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解构与检讨》,《政大法学评论》第131期(2013年2月)。另一方面,由于保险合同缔结以及履行过程中双方所掌握信息的不对称,无论是保险人还是被保险人(投保人)在诚信原则之下皆确实负有一定的信息提供义务。考虑到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有直接的控制权,一旦在保险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危险发生变化,也一般只有被保险人会在第一时间得知,保险人知晓的渠道却极为有限,故“基于保险契约之最大善意性,离风险最近之要保人、被保险人对于危险变动至足以影响契约程度时,应赋予通知保险人之义务,以维持契约之平等与信赖”。[注]江朝国:《保险法逐条释义(第二卷 保险契约)》,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台北),第447页。
至于合同法中的情事变更原则可谓在一定程度上对契约严守原则的修正。一般认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有一个双方皆信赖的客观环境,合同之权利义务皆是与该环境相适应的,因此如果合同成立后由于当事人不可预见的原因环境发生变化,合同中原有的权利义务也应做出一定的修正(允许一方变更或解除),才能符合诚信原则与实质公平之理念。[注]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页。结合情事变更原则对保险合同予以审视,考虑到双方当事人皆信赖的客观环境主要取决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之风险状况,而嗣后标的危险情况之变化确实有可能超出合同双方之预期,如果仍按照增加后的危险来履行原合同,显然对保险人不利,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则之设置就是在于贯彻情事变更原则,“因应社会环境变迁,以达‘法与时移’之衡平功能”。[注]同前注⑦,江朝国书,第451页。故可以将我国《保险法》第52条作为情事变更原则在保险法中的特别规定,[注]当然也有学者质疑情事变更原则作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理论基础,因为二者在变化因素、主观要求、可预见性、风险持续时间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参见偶见:《保险法中的“危险增加”与合同法中的“情事变更”———兼与江朝国先生商榷》,《上海保险》2010年第2期。然而,笔者认为,无可否认,将合同法的情事变更原则适用至规制对象主要为商事契约的保险合同法中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改造,但这种改造后所形成的差异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情事变更原则作为被保险人保险法上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理论基础这一事实。由此,情事变更原则在保险法中的一般性适用就极其罕见。
(二)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立法构造与学理阐释
1.我国保险法上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构造分析
基于笔者以上的分析可知,对价平衡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和情事变更原则共同构成了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构建的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于平行与位移中、冲突与协调中共同发挥作用。总体而言,最大诚信原则较为强调信息提供义务之下被保险人主观诚信的践行,对价平衡原则和情事变更原则更强调双方客观给付均衡效果的维持。具体来说,最大诚信原则特别关注被保险人对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并赋予保险人借此摆脱不利的权利,情事变更原则和对价平衡原则却在相当程度上对被保险人危险通知义务的履行前提条件进行了限定,并非一旦危险增加,被保险人即负有通知义务,且保险人的合同调整以及免于给付的权利也需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实定法的构造其实是上述三个原则相互妥协的产物,法律规则制定者需要在这三个原则之间进行一定的利益衡量,并达到微妙的平衡。
以此思路对我国《保险法》第52条进行分析就可以得知,现有规定可能过于偏重最大诚信原则的贯彻,对于对价平衡原则和情事变更原则的实现却有些忽略。因为实定法强调在保险合同约定的基础上,一旦有危险显著增加的情形发生,被保险人即负有通知的义务,而保险人也在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享有相应的合同变更以及解除权;如果被保险人没有履行上述通知义务,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对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现有法律规定并没有对显著增加之危险做出其他具体的描述,也没有对危险的产生原因进行区分(是否可以归责于被保险人)进而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只是一味强调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对于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解除权与变更权乃至免于给付的权利也没有进行过多的限制(诸如保险人变更权是否优于解除权,保险人主张免责时是否要对被保险人的主观状态是基于故意、重大过失还是轻过失进行考察),而更多地交由保险合同双方自由约定,因此在解释论上存在可以进一步明晰和调整的空间。
2.我国保险法上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学理阐释
虽然立法者并未完全列明,但学理基于对价平衡与情事变更之理论对于危险增加之危险构成仍予以了一定的限定,提出显著性(或称为重要性)、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或称为非预见性或未曾估计性)等构成要件,[注]参见樊启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0~91页;温世扬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155页;邹海林:《保险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43页;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台北),第294~299页;叶启洲:《保险法实例研习》,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台北),第162~164页;孙宏涛:《我国<保险法>中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完善之研究——以我国<保险法>第52条为中心》,《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6期。试图在解释论上进行可能的补救。显著性是指“危险增加的量变达某一质变程度,方可构成法律或合同基础所不能容忍的质变状态”。[注]参见上注,樊启荣书,第91页。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保险合同而言,一般认为危险增加必须达到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抑或提高保险费率的程度才满足显著性之要求(这也与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2条规定的告知义务的内容要求相一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保险合同之对价被打破以及双方皆信赖的客观环境被破坏之状态。我国《保险法》第52条对于危险增加必须“显著”的要求就是这一要件的体现,遗憾的是,现行法并未对何为“显著”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持续性要求危险必须有一定的持续状态,而非一时的变化后又恢复原状,[注]参见温世扬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55页。持续性要求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区分危险增加与突然性的危险变化直接促成事故发生这两种状况。[注]参见叶启洲:《保险法实例研习》,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台北),第163页。不可预见性是指显著增加之危险并未在订立合同时被双方当事人所预计继而成为保险费计算之依据,如果危险已经被告知或已经体现在保险费中,嗣后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即使该危险出现,也不会被认为有违对价平衡之要求和符合情事变更之法理,故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下之危险必须符合不可预见性的要求。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显著性、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的要求已被裁判者所关注,[注]参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6民终2793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5民终1691民事号判决书。成为现行法下判断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构成要件是否满足的重要补充,同时,价平衡原则与情事变更原则得以进一步贯彻。
三、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与《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的应对方案
虽然我国《保险法》第52条已经对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学界也对其进行了可能的补充,但由于该条文本身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诸如危险显著性的判断),加之实践中问题的多样性,特别是网约车时代的来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亟需解决的疑难问题,《保险法司法解释四》试图进行可能的回应,因此有必要通过群案研究的方法先对司法实践中的难题进行整理,探究理论上所预设的难题是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显现,继而探讨《保险法司法解释四》有没有给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需要先行指出的是,笔者所整理的大部分案例都集中于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保险金给付方面的争议,而几乎不涉及被保险人诚实履行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后的保险合同调整和解除问题。
(一)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1.适用前提之争议
(1)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与告知义务的区分
告知义务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皆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与履行过程中需要承担之义务,以便保险人可以有效地评估与测定风险进而计算与调整保费。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告知义务由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则是合同有效期内标的危险发生变动后被保险人所要承担之义务,判断的关键主要在于危险产生和变动的时间究竟在订立合同之前还是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注]部分问题存在于从合同订立履行告知义务到合同生效有一定的间隔期,此时危险发生变动该如何处理。对此,笔者主张可以类推适用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规定。此外,这两种义务在义务违反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当予以合理的区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裁判者基本可以对告知义务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进行有效的界分,[注]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终4052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1民终370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28民终1751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9民终1655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5民终2685号民事判决书。但也有部分判决书倾向于将两者一起加以叙述,使人产生混淆之感;[注]参见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琼97民终60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在理由部分的论述中指出,上诉人在投保时未告知保险人车辆用于出租营业的现状,投保后其又将车辆用途变更为营业使用,使得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终16886号民事判决书也存在相似的问题。甚至有判决书明确指出投保人在投保时隐瞒车辆营业(出租)的真实状况,有违反告知义务的可能,但在适用法律上仍回归我国《保险法》第52条关于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规定,而对告知义务的相关规则不予置评。[注]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民终10208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12民终413号民事判决书。可见,在理论上仍有必要对两种投保人(被保险人)之不真正义务予以进一步厘清。[注]理论上认为除一般的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之外,尚有不真正义务,其主要差别在于不真正义务的违反不会使合同另一方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只是使自己蒙受可能的不利益(诸如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丧失),不真正义务在保险法中较为常见。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页。一般认为,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皆属于保险法上不真正义务的范畴。
(2)对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条款的识别
在保险合同的相关条款中,保险人大多会对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内容予以明文约定,[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14年版)》在机动车损失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机动车全车盗抢保险中都有关于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约定。其因此受到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之约束,在部分案件中,出现了保险人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伪装成一般的免责条款之做法。对于免责条款的法效果而言,在该条款有效的前提下只要出现约定之状态,诸如投保人(被保险人)做出或未做出某种行为,保险人即可主张相应的免责。因此,与我国《保险法》第52条第2款被保险人违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既有规定相比,被保险人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要严苛很多,且几乎没有援引其他抗辩的机会。可见在个案中,为避免我国《保险法》第52条成为具文,为了实现实质正义,裁判者仍有必要对隐匿于免责条款之后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条款予以可能的识别,进而正确地适用法律。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集中于商业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争议,即保险人将机动车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作为合同约定之免责事由的情形,有关案例中的法院认为,虽然按规定进行检验主要指向控制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被保险人未按规定进行检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标的物危险显著增加和被保险人需要通知之情形,但依我国《保险法》第52条之内容,机动车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是否构成危险增加,以及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可否免责(在被保险人疏于通知时)皆有严格的法律规定,需要就个案予以判断,保险人却将被保险人的这一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伪装成所谓的免责条款,只要被保险人违背这一义务保险人即可免责,这样明显加重了被保险人的负担,导致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利益失衡,因此该免责条款的效力不应一概得到承认。[注]参见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珠中法民四终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4民终33号民事判决书。
(3)保险人对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
从我国《保险法》既有条文的文义出发,如果保险合同中存在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如果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依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此即为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9条与第10条又对免责条款的具体范围以及例外情形做了规定。实践中经常引起争议的问题在于,依据我国《保险法》第52条之规定,保险人主要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被保险人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并依法约定可能的法律后果,而在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情况下,保险人在许多情形下是可以主张免除保险金给付责任的,此种条款是否构成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所规制的免责条款,继而保险人必须履行提示与说明义务,显然存在疑问。当然,这也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9条第2款规定得不明确有关,其仅将“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排除出免责条款的范畴,对于保险人在被保险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且保险事故已经发生,其可在特定条件下主张免于保险金给付的情形,却并未涉及。
司法实践中法院的观点并不统一:有法院认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是被保险人的法定义务或法定的保险人的免责事由,保险人无需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注]参见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6民终525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黔06民终853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8民终1402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0民终2093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13民终3857号民事判决书。有许多法院以保险人违背提示与说明义务为由否定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条款下免责约定的效力。[注]参见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苏10民终144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6530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甘11民终964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申3271号民事裁定书、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4民终664号等民事判决书。因此,理论上如何看待此类约定的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条款的性质,是否可以一概免除保险人的提示与说明义务,显然有进一步明晰的必要。
2.适用条件——关于危险增加判断之争议
(1)显著性的认定
显著性的断定可谓危险增加判断的重要难点,毕竟“如果危险的加重程度轻微,并未动摇当事人之间的对价平衡关系,则被保险人无需履行通知义务”。[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7民终1315号民事判决书。如前所述,现行法并未对何为显著性做出回答,因此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许多疑难问题,当然如果套用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标准,危险增加必须达到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抑或提高保险费率的程度,才符合显著性的要求,但保险费率的计算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要参酌各种因素,其中存在如何量化的难题。毋庸置疑的是,保险人需对增加之危险具有显著性承担举证责任,法院也有必要深入探究究竟保费有无真正变化,有法院就直接认为虽然涉案汽车使用性质有所改变,但相同保额的保险费却没有增加,因此否定了一审法院对我国《保险法》第52条的适用。[注]参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1民终3969号民事判决书。
司法实践中,裁判观点较为一致的是网约车中的顺风车一般不构成危险的实质增加。较具代表性的裁判意见就认为于驾驶人与乘客顺路合乘的合意之下,顺风车为“车辆自用的基础上顺路搭乘出行线路相同之人,由合乘人合理分摊出行必要费用的活动,网约顺风车是私家车主事先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行程信息,召集路线相同的其他人合乘的行为。故此,典型的网约顺风车并不具有营运性质,事故风险也不会显著增加”。[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川01民终20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顺风车并未增加危险的观点可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2038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7民终1315号民事判决书。对于将车辆出租给他人使用的情况,法院裁判存在较大的分歧。部分法院认为将车辆出租给他人使用的情况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未必一定会显著增加汽车营运的风险,[注]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民终2150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民终2151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6民终167号民事判决书、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琼02民终1058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中民终字第625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2民终4862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9民终924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终1568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2民终2943号民事判决书。亦有相当一部分法院认为将车辆用于出租会显著增加事故发生的风险,因而同意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对被保险人的适用,如认为,“依社会生活经验,各个不特定的承租人在驾驶水平、行使区域、用车安全注意程度以及车辆使用频率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渝民申991号民事裁定书。相关判决还可以参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8132号、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6民终1075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8民终1325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7民终429号民事判决书。上述迥异的裁判观点区分标准何在,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余地。
(2)持续性的认定
如前所述,危险增加持续性要求的判断,最关键之处是要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与危险突发直接促成保险事故发生(被保险人往往存在过错)这两个不同的规则构造予以合理的区分。对于后者而言,因为危险变化的时间较短,几乎在一瞬间完成进而引发了保险事故的发生,使得危险增加不具有持续性,故被保险人并不负有通知义务。即使被保险人可能在许多情况下对于保险事故的引发或扩大存在过错,但保险人仍须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因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只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才可以免除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责任,其并未将被保险人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作为排除赔偿的事由。当然,这在立法论上仍有可探讨的空间,[注]参见叶启洲:《道德危险的除外界限与最大善意原则》,《台大法学论丛》第46卷4期(2017年12月);蔡大顺:《论重大过失行为之法律责任体系于保险法上的重构》,《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3期。但在现行法下的结论却较为清晰。
危险持续性判断在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主要体现为被保险人从事了一些较为危险的行为,直接或间接促成了保险事故的发生,但时间又极为短暂,诸如被保险人在暴雨天涉水行驶致汽车故障、被保险人捕鱼时被捕鱼器电伤、[注]参见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4民终20号民事判决书。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驾驶人允许第三人攀爬上车进而导致第三人受伤害。[注]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终3822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被保险人暴雨天涉水行驶的类案存在较多争议,部分裁判认为其不符合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构成要件,但理由各异,例如雨天行驶仍属日常生活中合理使用范畴,[注]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3民终2045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3民终2018号民事判决书。危险并未实质增加,且被保险人无过错,[注]参见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9民终297号民事判决书。不过,亦有判决认为被保险人在积水严重的路段行驶明显属于危险之显著增加,超出了保险人原有的预设风险范围,其负有通知义务。[注]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2016)粤01民终10098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2民终4156号民事判决书。就本文的分析而言,在裁判中引入对持续性条件的判断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当然,理论上的精准区分在实践中仍可能存在一定的争议,究竟危险持续多久才能符合持续性的要求仍有待于个案的探寻,毕竟“危险程度变化的持续时间的长短,不能一概而论,应当依照具体的险种及保险标的的具体情形予以认定”,[注]邹海林:《保险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43页。因此即使持续性要求被纳入法律也应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
(3)不可预见性的判断
在危险不可预见性的要求之下,此种危险变动情况必须在合同订立时未被保险人所知,也并未被纳入相应的费率计算因素,一旦被保险人在履行告知义务时已经向保险人做出披露或者保险人本身就将该危险变动作为保险费测算的基础,保险人当然不能再主张如该危险变动时被保险人应承担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如果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确告知其车辆的使用用途是非纯粹的个人使用,保险人就不能再主张被保险人将车辆改为营运构成保险标的危险显著增加的情形而要求被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注]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20民终93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苏01民终9486号民事判决书。而在土建工程保险合同中,因暴雨和洪水本就属于保险保障之范围,保险人也收取了相应的保费,即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了类似的情形,也不符合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的危险显著增加的构成要件。[注]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民终529号民事判决书。
3.适用后果——保险人免责要件之因果关系判断争议
在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情况下,依据我国《保险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如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问题在于,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有很多,此处所说的因果关系是仅需要符合条件的标准(以若无则不作为判断准则),还是需要进一步达到相当因果关系抑或是近因的程度,则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如果以条件说为标准显然保险人免责的范围较大,如果用相当因果关系抑或是近因原则予以判断,则更有利于被保险人利益的实现。司法实践中较多的法院采纳了对被保险人较为有利的近因裁判标准,如有判决明确提出我国《保险法》第52条第2款中的因果关系应以近因原则加以判断,[注]参见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1民终1761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1民终1781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1民终1825号民事判决书。更多的裁判文书虽未明言因果关系的识别准则,但往往以保险事故主要是由其他原因所造成(此时在车辆保险中,交通事故认定书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非由危险增加因素所造成为由,认为保险人不能据此要求免责。[注]参见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5民终2139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2民终268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3民终3911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6民终3032号民事判决书。
(二)《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及其征求意见稿的回应
正是为了对财产保险合同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进行回应,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并于2018年7月正式出台了《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其中皆有针对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规定,且内容不尽相同。
《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关于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规定主要为第4条,其主要是列明了司法实践中判断标的物危险增加所要参酌的因素,诸如标的物的用途、使用范围、所处环境、使用人的变化以及是否改装等,探究其实质其实是对司法实践中危险增加的主要样态予以列举;除此之外,第4条最大的亮点是将学理上提出的危险持续性与不可预见性的条件明确纳入司法解释,从而为司法裁判予以援引提供了依据。一方面,《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4条第1款明确提出判断危险增加要考虑“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这是对危险持续性要求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该条第2款也规定,虽然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但如果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内的,则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这又再次体现了危险不可预见性的要求。不过略有遗憾的是,《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曾单独规定一条文(即第4条),拟对危险增加之显著性判断予以进一步明确,[注]《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第4条规定,保险标的危险增加程度超过保险人承保时可预见的范围,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继续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应当认定为我国《保险法》第49条、第52条所称的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仔细加以分析,这一条文除了对显著性的判断标准予以明确之外,也再次确认了危险不可预见性的条件。明确规定必须危险增加达到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继续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程度才符合显著性要求。如前所述,这也于相当程度上与我国《保险法》第16条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判断基准相一致,然而,不知为何,最高人民法院在最后出台的《保险法司法解释四》正式文本中却将该规定予以删除,使得显著性判断的标准继续处于空白状态。
将《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与实践中的问题加以对照可知,《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4条的功能主要在于将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中危险判断的标准即持续性以及不可预见性纳入司法解释,从而指导司法裁判以补充成文法的不足,并对危险增加的常见类型进行可能的列举,但其对于笔者在本文中整理的司法实践中的一些主要难题皆未涉及,因此有必要结合学理和法学方法论予以进一步的延伸探讨。
四、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则适用之进一步检讨
总体而言,在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司法适用涉及的诸多难题中,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与告知义务的区分可谓较为明确,以危险之存在和变化主要是在合同缔结时还是合同履行过程中为判断标准即可予以妥善处理,[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5)苏审二商申字第00549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案涉车辆在投保时就处于运营状态,因此认定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而没有采纳一审、二审法院被保险人违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裁判依据。此外对于保险人将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约定伪装成纯粹免责条款之情形,法律规则适用者亦可以以我国《保险法》第19条为工具进行格式条款的控制和审查,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而《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4条对于危险增加类型和样态的列举也给法官判断何为应然层面的危险增加条款提供了指引。司法实践中真正的难点可能在于保险人对于约定危险增加通知条款究竟要尽到多大的提示与说明义务,危险显著性、持续性、不可预见性的判断如何具体化,在被保险人没有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情况下,保险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免责,具体因果关系该如何界定,而这些问题也是基于我国《保险法》第52条条文设计在司法实践中必然会显现的。
(一)保险人提示与说明义务程度的明确化
我国《保险法》第17条确立了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如保险人未履行此义务,则该免责条款不生效力。鉴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天然的不平等之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保险深口袋”的原理(保险人可以将已有的保险金给付通过之后的保险费收取实现损害分担社会化),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尤其是说明义务)存在被法官滥用,进而过分偏重于被保险人利益实现的可能,[注]参见于永宁:《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司法审查——以<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为中心》,《法学论坛》2015年第6期。学界也越来越倾向于对法律赋予保险人如此严苛的说明义务提出变革建议。[注]参见马宁:《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批判》,《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陈群峰:《保险人说明义务之形式化危机与重构》,《现代法学》2013年第6期;钱思雯:《保险人说明义务之解构与体系化回归》,《保险研究》2017年第9期。《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9条第2款同样持有对免责条款进行限定的必要的立场,明确规定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保险人在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的情况下可享有的解除权条款不属于免责条款,其主要理由在于“与保险合同解除相关的条款虽可能导致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这是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法律后果,而不是直接免除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故我们将解除条款排除在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范围之外,以使其符合合同原理”。[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页。《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可能忽略了,在大部分情况下保险人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才会对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务违反情况进行审视,此时因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保险人固然可以行使解除权(更为准确地说是终止权),但考虑到保险合同为继续性契约,该解除权的行使并不产生溯及效力。因此,问题之难点在对于已经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是否可以免责,保险合同中如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义务保险人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是否需要其在订立合同时向投保人履行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实践中部分法院恰是利用这一漏洞希望通过强化保险人对于法定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来限制保险人的免责可能。当然,除了我国《保险法》第52条所规定的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6条所规定的投保人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21条所规定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事故发生通知义务,也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种路径加以思考。其一,立法者已经明确规定当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告知义务、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保险事故发生通知义务的情况下,保险人可以在特定情况下予以免责,此种规定可谓法定的免责条款;考虑到法律本身具有公示的作用,即使在保险合同中将此种规定予以纳入,保险合同中的这些内容也属于宣示性条款,那些约定的免责情形是保险人依法本来就享有的法定的抗辩权,[注]参见王静:《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司法审查》,《法律适用》2013年第1期。故“即使保险人未就该类免责条款提示和明确说明,保险人仍可依据法律规定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页。回归既有的法律解释方法,即可知这里其实采取了限缩解释之方案。所谓限缩解释,是考虑到法律条文文义有时失之过宽,不符合立法意旨,有必要适当限缩其文义,以回归应有的核心概念。[注]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25页。具体到保险法中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则有必要将保险人提示和说明的对象限定为纯粹的约定免责条款,而不及于法定免责条款。其二,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和约定义务,其当然结果就是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一旦保险人行使解除权后就可以对之后的保险事故免责)以及如保险事故已经发生可在一定情况下免责,两者皆属于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违反的自然后果,且都有可能产生保险人免责的法律效果。既然司法解释明文规定保险人解除权条款不属于我国《保险法》第17条所规定的免责条款的范畴,保险人无需提示与说明,但没有涉及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可以主张免责部分,那么可以认为此处存在明显的漏洞需要填补。[注]开放法律漏洞的存在是类推适用方法适用的前提。参见屈茂辉:《类推适用的私法价值与司法运用》,《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卡尔· 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254、258页。故基于相同问题相同处理的法理,“二构成要件——在与法律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上——彼此相类,因此,二者应作相同的评价”,[注]同上注,卡尔· 拉伦茨书,第258页。保险人自然也不必对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违反后所可能产生的免责事项再予以提示和说明,即通过类推适用的成文法内法律续造的方法将这一难题妥善解决。[注]考虑到保险人以格式条款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情形十分繁杂,又不涉及核心给付义务,投保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往往不会加以注意,此时在立法论上认为保险人负有一定的提示义务较为合理。
(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以危险的显著性、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判断为例
以法律概念是否确定作为判断标准,可以将法律概念区分为确定法律概念与不确定法律概念。与确定的法律概念相比,不确定法律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注]参见前注,梁慧星书,第293~294页;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97页。不确定法律概念具有概念上的高度抽象、内涵与外延均不确定以及在法律适用层面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等特征,因而在裁判中需要予以一定程度的具体化并配之以特殊的法律适用方法。[注]参见上注,王利明书,第497~499页。毋庸置疑,在现代法律体系的构建中,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广泛存在的,立法者在法律规则设计之初就设置了大量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是估计有限的条文文义与确定的法律概念可能无法反映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与急速变迁的社会观念,故给裁判者留下一定的法律续造的空间,明文授权其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具体化。[注]参见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193页;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385页。
在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构成要件的判断中,危险显著性、持续性与不可预见性这三个特征显然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范畴(虽然《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4条第2款对不可预见性做了一些描述,但其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予以可能的具体化(尤其要注意险种的不同),而之所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原因恰在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过程“并非为同类案件厘定一个具体的标准,而是应‘case by case’,随各个具体案件,依照法律的精神、立法目的,针对社会的情形和需要,予以具体化,以求实质的公平与妥当”,[注]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页。也正因为如此,裁判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见性也就不可避免了。故有必要在法学方法论的角度对裁判者进行一定的指导和必要的约束,以防止裁判者恣意裁判。首先,法官对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具体化时,必须先在现有的规则体系下寻求可能的解释结果,穷尽法律解释、制定法内法律续造(类推适用、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的方法,而非径直进入法律原则价值补充的环节,这既是形式法治的要求,也符合尽量从现有规则出发的法律适用逻辑层次,毕竟“法教义学提供的法律规范体系为解释不确定法律概念框定了解释资源,提供了直接规则指引,属于司法裁判的正式法源”。[注]杨铜铜:《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体系解释——以“北雁云依案”为素材》,《法学》2018年第6期。结合本文的讨论可知,危险显著性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类推适用我国《保险法》第16条投保人对于告知事实重要性的认定——必须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才符合危险显著性。危险持续性的断定主要是与我国《保险法》第27条第2款被保险人因极其短暂的行为导致保险事故的发生,保险人因而可以在某种范围内免责相区分,危险不可预见性的判断也可借由危险是否是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所明知(回归投保人的告知义务的判断)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其次,当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下对不确定法律概念无法予以具体化或无法得到妥适的结果时,裁判者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予以一般性的价值补充,具体到本文的讨论中主要是结合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设置背后的三大理论依据即对价平衡原则、最大诚信原则与情事变更原则。如在对价平衡原则之下综合权衡给付的失衡程度(诸如保费增加一元是否符合危险显著性的要求,某一危险增加与某一危险减少的相互抵消可能等)、在最大诚信原则下思索被保险人违反通知义务的主观恶性(究竟是故意、重大过失还是轻过失),在情事变更原则之下着重考虑情事产生是否可归责于被保险人,进而进行动态考量。当然,如有必要,也可以考虑在三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过程中融入一些新的价值(如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理念)。最后,需要特别予以强调的是,因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过程中法官有较大的权力,所以裁判者必须进行更为详细的说理和论证,[注]参见前注,梁慧星书,第299页;前注,王利明书,第506页。从而接受法律共同体的可能检验,而在危险持续性、显著性和不可预见性的判断中,不难发现,部分裁判文书往往只有寥寥数语,根本无法反映可能的法律思维过程。这固然和很长一段时间内危险的特征判断较多地停留在学理讨论有关(除了我国《保险法》一开始就有危险显著性的明文规定),但在《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实施之后,司法解释既然已经明确了危险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的要求,法官也就有必要在以后的裁判中加强说理与论证。
(三)因果关系判断标准的明晰化
如前所述,依我国《保险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当被保险人未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时,只有当危险增加与保险事故发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时,保险人才可以主张拒绝给付保险金。问题在于,此处的因果关系是要达到相当因果关系抑或是近因的程度,还是只要该增加之危险对于保险事故发生有可能的影响或作为一定的条件即可满足,这在司法适用时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困惑。就法律后果而言,显然对于因果关系的要求越高,对被保险人的保护越为有利,保险人主张拒绝给付保险金的可能性就越低。考虑到现行法并未言明,而因果关系存在多种文义解释的可能性,存在通过借助其他法律解释方法来获得妥当结果的空间。笔者认为可以在解释论上适当区分被保险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主观状态,继而采纳不同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从而在对价平衡原则与最大诚信原则之间求得平衡:在被保险人因过失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时采近因说,在被保险人故意违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时采条件说。
之所以在被保险人因过失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时采较高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理由有两点。其一,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每一段条文都是有机地分布在法律文本中,具有整体性,因此在解释它们时自然不能断章取义,无视条文之间的可能关联。[注]参见黄茂荣:《法律解释(下)》,《植根杂志》21卷9期(2005年9月,台北),第374页。回归保险法既有的关于不真正义务的规则体系可知,当投保人因重大过失违反同为不真正义务的告知义务,如保险事故已经发生,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5款明文规定,必须是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才不给付保险金。这显然采取了极高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考虑到告知义务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同属不真正义务,且现有规则都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可主张免责的情况中采纳了一定的因果关系标准予以限定,在对被保险人因过失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保险人可主张免责之因果关系判断进行解释适用时,自然可以适当参酌告知义务的相关规定。其二,于解释法律文本时,需要着重考虑该规定出台的立法目的何在,并以探求该目的作为法律解释的关键。[注]参见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页。一般认为目的解释也是体系思考的结果,毕竟在存在多种解释可能时,如采纳合目的性的解释结果,将有利于达成既有规则所欲实现的规范目的。[注]参见曾品杰:《法律解释学之原理》,《月旦法学教室》第130期(2013年8月,台北)。从目的解释出发,立法者之所以在此处引入了因果关系之判断,主要在于防止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动辄以被保险人未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为由主张免责,毕竟很多时候被保险人未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与最后的保险事故发生可能并无关联,在此时一概免除保险人的责任显然并不合理,也有违对价平衡原则。故立法者于此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被保险人予以保护的价值取向。加之我国法上对于被保险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保险人可主张完全免除保险金给付责任,也就是说,仍以保险金给付的全有全无为法律效果,而未像域外法上那样采取比例给付的方法以兼顾被保险人的利益实现(主要针对被保险人有过失而非故意的情况),[注]德国《保险合同法》第26条就是如此。该条规定,如果投保人因重大过失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时,保险人可以按照投保人的过错程度减少其保险金给付责任。参见孙宏涛:《德国保险合同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从而避免被保险人完全丧失保险保障。故我国现有规则的法律后果实在有些严苛。此时,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如被保险人主观归责性较低时采更偏向于被保险人的解释结果即近因说,可谓较为妥当,如前所述,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也采纳了这一标准,但问题可能在于并未对主观状态进行区分而一概予以适用。[注]须特别予以说明的是,之所以采用近因说而非相当因果关系学说(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两者的判断结果趋向一致),主要是考虑到受海上保险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保险法学者和裁判者也倾向于在保险法的因果关系判断中采纳近因的标准,因此有必要在体系上保持一致,但显然此处仍存在讨论的空间,毕竟我国《保险法》并未明言。
此外,之所以在被保险人故意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时采纳条件说,主要是考虑到在此种情况下被保险人主观恶性较大,基于最大诚信原则之贯彻与恶意不受保护理念之坚持,应适当放宽保险人主张免责时对于因果关系之要求,只要保险标的危险增加可能造成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即可主张不负保险责任。
五、结 论
对价平衡原则、最大诚信原则、情事变更原则构成了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理论基础,但基于我国《保险法》第52条在立法上过于偏重最大诚信原则的实现,在解释论上通过对危险显著性、持续性、不可预见性特征的强调来限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适用实有必要。新近出台的《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4条也在相当程度上对这一做法予以认可。此外,现行法在对危险是否增加、保险人可在何种情况下主张免责以及该法定免责条款保险人是否要提示与说明等判断上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较多的争议。《保险法司法解释四》试图解决上述难题,但其规定更多地只是对危险增加的样态予以列举,对笔者所梳理的司法实践中的许多核心问题并未予以可能的回应,因此有必要在现有的理论架构下结合法学方法论对司法实践予以必要的检讨。首先,需通过限缩解释或类推适用的方法将保险合同所约定的当被保险人违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保险人对于已经发生的保险事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主张免责的条款排除出一般免责条款的范畴,认定保险人不负提示与说明义务。其次,对于危险显著性、持续性、不可预见性这三个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而言,应先在现有法律规则体系内寻找合理的解释资源,如无法得出妥当的结果,才能结合对价平衡原则、最大诚信原则、情事变更原则予以一般性的价值补充。此外,要特别强调法官在此过程中的说理与论证义务。最后,在探讨被保险人违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时,保险人可在危险增加与保险事故发生存在何种因果关系下才可主张免责时,可区分被保险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不同主观状态,采纳不同的解释方案,在被保险人仅存在过失时应从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出发,确立近因说的合理判断准则,以实现对价平衡原则;在被保险人主观归责性较高(故意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情况下,从贯彻最大诚信原则出发,仅需保险标的危险增加有可能造成保险事故发生(即采纳条件说),保险人就可主张不负保险责任。
当然,笔者于本文中主要是基于司法适用的视角对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进行探讨,就立法论的层面而言,我国《保险法》第52条关于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相关规定仍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如现行法并未对危险增加是否可归责于被保险人进行区分进而赋予被保险人不同标准的通知义务,也未像告知义务违反那样对被保险人违反通知义务的主观状态进行描述,在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上也秉持全有或全无的保险金给付效果,这都存在着很多问题,未来仍有必要在保险法上投保人(被保险人)不真正义务群的理论体系下进行通盘的检讨和可能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