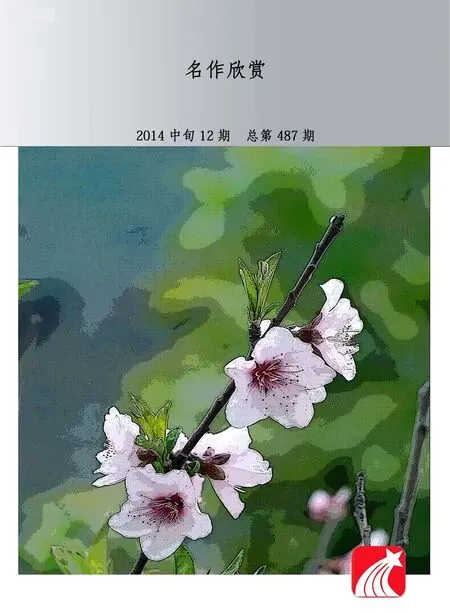管窥当代韩国读者的文学审美
——以余华小说为例
⊙林春颖 李丽娟 梁 策 [长春理工大学,长春 130022]
有关余华小说被韩国读者接受的原因,中韩研究者从接受美学和比较文学角度展开研究,并取得了十分有价值的成果。相关研究涉及余华小说的人道主义世界观、苦难叙事和家庭叙事、爱情主题与成长主题、中国现当代史背景、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生活、译者的“二次阐释”、文学传播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西方文学奖项和影视获奖的重要媒介作用等。本文在此基础上,从三方面考察当代韩国读者的文学审美。(1)读者的审美参与。接受美学重视读者的积极参与和接受姿态,在余华小说已然被韩国读者接受的前提下,探讨余华小说的可参与性是观照读者文学审美的途径之一。(2)读者的审美惯性。西方文学文化对中韩两国近现代文学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这包括对作家创作及读者文学审美的影响。余华曾不吝笔墨讲述西方作家作品对他的影响,《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以下简称《许》)被韩国读者奉为圭皋,洞察这两部小说的隐性文本结构,对管窥读者的审美惯性应具有重要意义。(3)读者的阅读倾向。现有研究关注韩国学界的评论,鲜见对普通读者书评的分析,忽略了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本文选取韩国大型网络书店“教保文库”的读者书评作为样本,分析普通读者对余华小说的反应。
一、读者的审美参与——小说的可读性与可写性
申义莲援引法国学者罗兰·巴特的可读文本与可写文本理论,认为《兄弟》既是可读文本,又是可写文本。这一观点很有启发。(1)余华小说的可读性。曾有韩国读者诟病中国长篇小说分量大、人物多、主题庞大、不知所云。但从《活着》到《第七天》,余华小说的语言特色之一便是易读。其中,《许》以对话形式推动小说发展,收效甚佳。对话使小说具有戏剧效果,因为“在戏剧中背景可能由剧中的对话表现出来”,可以设想,这也是韩国人将《许》改编成话剧和电影的重要原因之一。(2)余华小说的可写性。尽管背景尤其是家庭内景具有对人物换喻性或隐喻性的表现作用,但在韩国最受欢迎的《许》和《活着》却均淡化了历史背景,家庭内景描写也很少见。这种做法虽放弃了对事件和人物的铺陈和渲染,却给不同国家的读者以充分的想象空间。尤其是对历史背景的淡化处理,省去许多政治谈论和意见分歧,使读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故事和人。不同国家的读者将本民族文化想象附加在文本中,从而实现文本的再创造。
二、读者的审美惯性——隐性文本结构
(一)《活着》——约伯的受难与西西弗斯的命运
1.约伯的受难。 《圣经·约伯记》中约伯在撒旦的考验中从富人沦为穷人,子女相继死去,从信仰神到怀疑神,再到坚定对神的信仰,而神最终也赐予了约伯更多的财富和子女。余华不信仰基督教,但“对《马太受难曲》的喜爱就像对《圣经》的喜爱一样无与伦比”,而且“把《圣经》当作伟大的文学作品来读”。可见,余华对《圣经》推崇备至,并且对《圣经》故事有相当的了解。福贵的受难恰似约伯的受难,福贵的命运却与西西弗斯仿佛。余华把福贵经受的苦难放在显微镜下一寸一寸地观察,拉长了他受难的长度,也让读者经历了漫长的苦难。教保文库的读者评论几乎都提到对福贵苦难人生的同情和感同身受。韩国学界就《活着》的苦难主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除部分研究从政治历史角度剖析福贵受难的原因以外,大部分在观点上与国内的此类研究趋同,认为余华表现出了人对苦难的承受力。
2.西西弗斯的命运。 从希腊神话到古今小说,命运一直是文学家乐于表现的主题。希腊神话传说以及希腊悲剧基本都以命运为主题,希腊悲剧就是命运悲剧。希腊民族知道在感性的生活背后有某种只有通过理性的反思才能把握的东西。由于他们的抽象思维还未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不能确切命名,于是称之为命运。古希腊的奥尔弗斯宗教中有位手持皮鞭、具有不可抗拒力量的女神,叫作阿南刻(希腊语意为“必然性”),在奥尔弗斯神秘祭中,命运实际上已经被看作是定数。对命运的不可抗拒性的认识亦存在于东方人的思想中。中文有命中注定、听天由命、冥冥中自有安排等说法。韩国有“三千甲子东方朔也不知其死亡之日”“过得好坏皆由命”“命运难逃”等谚语。东西方的命运观都表现为恐惧、敬畏与面对命运时的无力感。精神分析学中的“集体无意识”、语言学中的“无意识结构”和布留尔的“集体表象”等研究证实,在人类历史上曾存在一个心智、社会、人类所认识到的宇宙三者高度一致的时期。这个时期奠定了人类心智中某些基本法则,正是这些法则才使得在现代不同地域、文化和民族的人之间还能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东西方对“命运”认知的相似性可在这里得到解释。福贵同约伯一样受难,却未得到约伯似的好结局,命运待他犹似对待西西弗斯。他反复品咂命运之苦,又表现出对抗命运的坚韧精神。韩国学界及普通读者对《活着》的认同在于对福贵坎坷命运的同情与感同身受,以及因福贵的达观而深受启发。
(二)《许三观卖血记》——“耶稣”般的父爱
个体和整个人类都源于对父母长时期的婴儿期依赖。最后,父亲在这方面成为个体最重要的依赖对象,可以推论,父亲必定成了整个人类的依赖对象。
自古韩国社会深受儒教文化浸润,对父亲和家族有着强烈的挚爱。余华塑造的福贵、许三观和宋凡平竭力保护子女、营造充满爱的家庭,符合韩国人对父亲形象的审美,契合了韩国读者的审美情趣,普通读者和韩国学界对上述父亲形象只褒不贬。初入近代基督教的传播在经历一番波折以后,几乎与韩国此后的社会变革并进。现代韩国社会深受基督文化影响,从出身卑微、为子/子民排忧解难、为子/子民牺牲等方面考察,会发现耶稣与许三观这一父亲形象有相似之处。(1)生长在加利利省的拿撒勒的耶稣出生在并不富有的家庭,是“微贱的犹太木匠”;许三观出生在贫穷到以卖血为生的村庄,是小城丝厂的送茧工。(2)耶稣在平民中行神迹,为其治病、创造食物,使其免受饥饿病痛之苦;许三观在窘困的条件下,卖血为儿子解决问题,保障他们的利益;(3)在细节描述上,耶稣替子民赎罪背负十字架上加尔瓦略山的情景,与许三观为救非亲生儿子性命沿路卖血的过程不乏相似之处。“耶稣”般的父爱契合了韩国读者对父亲形象的期待,使其对《许》产生了高度认同。
三、读者的阅读倾向——中国近现代史及当下中国民众的生活
教保文库网店介绍《活着》(2007 年版)的主题词是“中国小说、中国现代史、生命和死亡、电影原著小说”,《许三观卖血记》(2013 年版)的主题词是“中国近现代史、电影原著”,《兄弟》(2017 年版)的主题词是“中国现代史、中国历史小说”。可见,书店对余华这三部小说的推广热点之一便是它们是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的小说。读者书评中也多次出现从这三部小说中了解到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人的生活之类的表述。对于《第七天》,书评中出现“中国社会现实的阴暗面”之类的字眼。韩国学界研究余华小说的一大特色便是通过小说文本考察中国社会、政治、历史问题。对《活着》和《许》的指摘主要是这两部小说在揭露中国社会、政治、历史问题方面力道不足,对《兄弟》和《第七天》的推崇则在于它们正面揭露了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部分学者将余华定义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可见,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下民众生活是普通读者和韩国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而余华小说客观上契合了韩国读者的这一喜好。
① 李 承芝:《余华小说在韩国的接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河贞美:《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接受情况研究——以戴厚英、余华、曹文轩为中心》,《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金炅南《: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译介接受与展望——以余华、苏童小说为中心》《,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1期;李 惠兰:《韩国对余华作品的译介与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张乃禹:《韩国文化语境中的余华》,《小说评论》2013年第4期。
② 参 见陈思和:《我对〈兄弟〉的解读》,《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第57页。
③ 教 保文库:位于首尔的教保文库成立于1981年,与曾经的钟路书籍并称韩国大型书店双璧。NAVER知识百科,https://terms.naver.com/entry.nhn?docId=1065467&cid=409 42&categoryId=34657
④ 〔韩〕申义莲:《小说〈兄弟〉的新写作方式》,《中国学研究》2010年第51期,第87—108页。
⑤ 教 保文库:会员书评,http://booklog.kyobobook.co.kr/satu r21/1338996/?orderClick=JFP#0
⑥⑦ 〔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6页,第216页。
⑧ 赵 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4—81页。
⑨ 王 少辉:《圣经密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⑩ 〔英〕白德库克:《人类文明演进之谜——文化的精神分析》,顾蓓晔、林在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