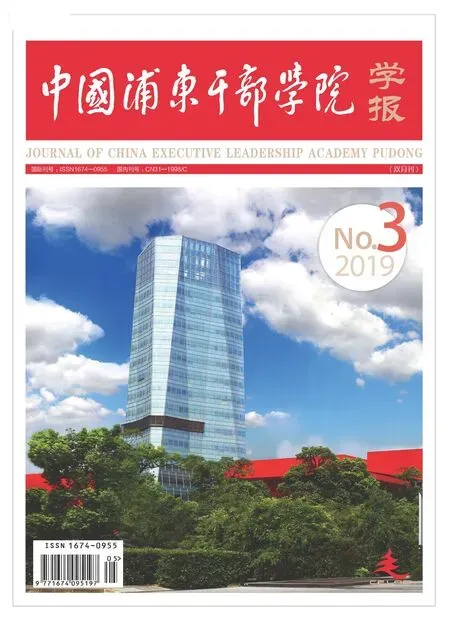作为问题的发展
——“五四”百年纪
孙 津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一
学术界言说五四运动大致有两种情况或态度,一是描述(包括“发掘”新资料)五四运动,另一是阐释五四运动的意义。显然,无论从思想(理论)还是行为(实践)来讲,研究“五四”(包括运动和意义)的作用都在于后者,也就是说,怎样看待“五四”,以及相应的做法对于今天有什么意义或作用。但是,为什么要谈论“五四”呢,或者说,“五四”对于中国真的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东西(事件及其价值和影响)吗?
我认为回答是肯定的,即“五四”的意义一直就是中国绕不开的东西。以前,这种绕不开主要在于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文化建设、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安置等任务和问题,而在今天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绕不开的根据或原因主要在于发展本身成为问题,或者说作为问题的发展。说明这种问题转换的基本含义,就是写这篇“五四”百年纪的目的。
25年前,笔者在纪念五四运动75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五四”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内在的矛盾,即一方面要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要拥护民主和科学。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矛盾,在于中国所反对的帝国主义正是靠着民主和科学的力量,尤其是按着民主和科学的逻辑(或道理)来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而这个矛盾之所以是“内在的”,主要在于中国作为人口众多且文化悠久的农业大国所陷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况,即是说,中国自己的想法和技术在效能上都是不如入侵者的。因此,不仅这个矛盾是内在的、非对象性的,而且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更是具有鲜明的道义性的。正是由于这个内在矛盾及其解决出路的性质,中国有革命觉悟的知识分子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共产主义方向,因为这种学说和方向使得反对帝国主义和拥护民主与科学不成为矛盾,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1]
事实上,正是由于上述内在矛盾的展开和转换,五四运动才被认为是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事件,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里说,如果从准备时期算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五四运动则进入了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新阶段,至于新文化运动,不过是这个新阶段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个新阶段的“新”主要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工人阶级参与进来了,学生更是走在了前头,形成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另一个则是出现了以探求和引进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特征的革命觉悟,以及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诞生提供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及条件。[2]558-559
相对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学术界那种把启蒙和救亡当成中国现代史的主题的看法就不免有些把问题普遍化和简单化了。[3]启蒙的实质就是解放思想,包括在物质手段的功能上以及生产力转化的机制上使用科学和技术;至于救亡,主要指反抗那些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入侵。换句话说,启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东西或历史任务,而救亡则被简单化为对象性的和阶段性的正义事业。显然,按照这种说法,“五四”精神就不一定是中国直到今天(以及可预见的将来)都绕不开的东西了。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即在学界对“五四”的研究以及对其精神价值和思想导向的关注中,几乎看不到与今天发展直接相关或内在关联的问题。
二
现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现实任务并没有丢掉,只是不再采取以前那种阶级斗争和武装暴力的方式了。由于主权独立、帝国主义被赶走、封建制度被推翻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反帝反封建在形式上已成为中国自己思想战线的事情,而且其重要性也已经有所隐退,或者说是依当下的建设任务需要而定。民主和科学不仅也没有丢掉,反而更加强调,但其目的更多的在于发展,也就是为发展服务,因为发展不仅成了中国的第一要务,而且被认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性或全球性主题。简括说来,最为关键的变化在于,反帝反封建和民主与科学这两方面的认识和做法都是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制定和领导的,所以这两方面不仅不再成为矛盾,而且民主与科学的意义和状况也彻底改变了。一方面,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所以不必顾忌民主是否来源于西方或者说与西方的关系如何了;另一方面,科学(以及技术)也被当成中性的工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包括中国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任务和规划。
但是,新的问题恰恰在于,不仅作为“五四”遗产最为突出或明显的延续,民主和科学仍是无需追问的正确目标,而且发展也由于被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而被当作天经地义的价值甚至道德,贫穷和不发展则都是不道德的、应予抛弃的。从哲学上讲,无需追问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毫无意义本身;从实践上讲,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不被思考和修改。因此,如果说发展突出并巩固了科学技术的作用,那么它也掩盖了对科学本身的合理性加以追问的必要和可能。尽管这些做法和情况也是“五四”遗产的逻辑延伸,即为了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世界上的强大而认同民主与科学,但是由此产生的问题却在于,作为五四运动欢迎和争取民主与科学的主要目标的现代化的性质,反而被发展的自明性掩盖起来了。
对于上述变化的“问题”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和说明。
三
其一,“发展”并不是中性的文明状态,而是也存在着反帝反封建问题的体制和机制。从实际内容和运行机制来看,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现代化的竞争。笔者在很多地方曾经反复强调,现代化就是全球范围内穷国追赶富国的运动,而现在更多的情况却是只在文明形态的意义上讲现代化的量化指标。由此,一方面现代化成了发展的程度,另一方面发展就成了这个运动的道德根据。但是,现代化的竞争并不平等,而发展的问题也不在于不平衡,因为即使撇开自然条件,仅现代化的竞争本身就注定了发展的不平衡,所以不平等所反映的其实就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不合理。在此意义上讲,现代化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等发展形态,在性质上都是资本的效能竞争和剩余价值的利润追求。[4]换句话说,不管用什么方式发展,归结到底都是资本本身的运作规律发生作用;而现实状况基本上就是按照资本运作的“规律”来发展,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就难以避免地按照所谓文明的、率先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剥削要求来发展。①参见[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上卷“导言”、下卷第20章。能够表明这一点的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于,一边是由不断的现代化的竞争以及创新发展产生出的足够多的财富,另一边则是越来越多的战乱、难民、贫穷、疾病,以及越来越突出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恶化的危机或趋势。
尽管发展的普遍性掩盖了现代化竞争的不平等,但由于不能在全世界范围进行,或者说没法进行全球性的反帝反封建,各国和各方面只好想出种种说法来掩饰这种不平等甚至不公正和不道德,包括所谓发展的“不平衡”。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当然不能到国外去反帝反封建,这不仅因为中国奉行“革命不能输出”的原则,更在于中国也一直遵循民主与科学,所以也只能在与国际(实则就是发达国家)“接轨”的同时,谋求参与制定国际新秩序、争取更多话语权等发展内容和成果,比如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二,在今天,“五四”的遗产已经不仅仅是欢呼和引进科学,而是科学和发展一体化了。由此,不仅不必顾忌科学理性以及相应的技术创新是否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来或引进,而且在把它们作为全人类的知识的同时,还必须尽可能地争取制造或创造中国自己的“产权”和发明“专利”。本来,“科学”的意思主要指对于客观规律的发现、解释和验证,包括相应的对知识的分门别类,然而由于科学的实用性,久而久之科学本身就被赋予了“合理”“正确”甚至“真理”的含义。这样一来,科学实际上也成了道德,使人们不仅不去追问科学本身的“科学性”,更不会(甚至故意不去)审视“发展”的科学性。由此,观念上的“科学性”也就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性质在今天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科学技术能否以及如何为发展服务,首先是为现代化的竞争服务。
但是,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科学和发展的这种一体化只是从重要性来讲的,甚至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其关系实质仍然是对象性的,也就是完全把科学技术当成文明手段,尤其是对发展能力的物质性支撑。科学的重要性甚至科学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都在于能够为了发展而持续地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力。在此意义上讲,即使对于所谓基础研究的重视也无非是一种长线投资,因为它不仅为技术发明提供新的根据,而且距离基础研究成果越近或者越直接的技术发明就越有价值、越具有知识产权的垄断性,也就越值钱。事实上,正是由于作为进步价值的民主的制度化以及作为理性能力的科学的实用化,发展才被赋予了文明形态的先进性,并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被普遍移用到各个领域或方面,比如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发展以及城市发展、乡村发展、教育发展、旅游发展等。
其三,这里所说的“问题”,主要是指某种事物的既有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比如由于不科学不可持续的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就是这种问题。由此,“可持续”就是针对发展的既有结构和功能提出的,但它同时也就又成为问题,即不管发展本身能否持续或者说实现“可持续发展”,都不能由此回答“为什么要发展”这个问题。如果说,发展就是为了不停地发财,或者说是资本的本质和竞争使然,那么发展的道义性就成了问题;如果说,发展是为了给人以更好的生活,那么即使撇开前述发展的公平和平等与否,问题也显然在于什么是更好的生活,或者说,这种“更好”真的是没有止境的吗?这两方面的问题不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没有想过,准确地说是故意回避,而且也超出了民主和科学的理解能力和解释范畴。作为“五四”的遗产,需要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历来的思想封闭、重农轻商,所以导致只有增长没有发展,只有商品经济没有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增长所反映的是封建保守和生产力落后的传统境况,而发展则体现为民主与科学的进步价值及其目的所在。因此,搞现代化就是要不断地发展、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然而,作为“问题”,发展赖以支撑的消费方式很可能纵容了人类欲求的过度膨胀。事实上,尽管人们总是想过好日子,但只是发展才把这种好日子建立在各种(主要是物质财富)多余或不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享受前提上。相对说来,与人口增多、分工细密、交往频繁以及生活条件改善等文明要素的自然状况相适应的经济规模扩大和财富增多叫做“增长”,而超出这个适应以外的欲求及其物质支撑才叫做“发展”,所以才说它是多余的或者对于人类需求来讲是并不必要的财富。[5]但是,制造这种多余的或不必要的物质财富既是赚钱发财的需要,也是不平等的必然结果。由此带来的问题就在于,一方面这种过度的欲求仍然是民主和科学的题中之义,所以几乎没有人想到要去反对它,或者即使想到了也不敢公开反对;另一方面制造和享用这种多余或不必要的物质财富恰恰是发展的正常状态和必然导向,所以也几乎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四
最后,概括地说,对于“五四”精神的继承或者说“五四”内在矛盾的消释,是以发展自身作为问题的方式来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胜利为中国现代化的真实实施提供了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民主与科学也随之成为现代化建设和竞争的基本手段。发展既是现代化竞争的具体形态,也是享用现代化成果的价值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反帝反封建和民主与科学既不是矛盾分立,也不是合而为一,而是在全球意义上依据发展的需要被随机安置。由此可能产生的严重问题或者说作为问题的发展的主要含义在于,发展及其动因与相应的欲求限度不再被追问,似乎它们都成了类似“科学”一样天然合理的东西,而不是一种自觉的选择。
显然,为了发展就必须有持续扩大的消费,所以不仅在各方面采取广告化运作,而且还要用不断的便捷化来促使消费更新和升级,尤其是不必要的高消费,却从来不去考虑这样做是否有悖人的生存伦理。不过,的确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由于人的活动,尤其是科学技术的介入,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生存的溃灭已经难以避免。比如美国《一周》杂志网站2019年2月17日就发文认为,地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6]然而,发展的利益驱使以及对发展成果的依赖享用,使人们一方面乐观地相信发展能够解决所有难题,另一方面却宁愿对可能的灾变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并以此掩盖或缓解灵魂空虚、生活无聊以及对溃灭的潜在恐惧。比如,科幻大片之所以火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反映并迎合了上述两方面的普遍需要。但是,解决(如果能够解决的话)上述发展问题真的十分困难,因为这不仅要求天性趋利避害的人们不想赚钱发财,还需要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放弃至少大大减少盲目的好奇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