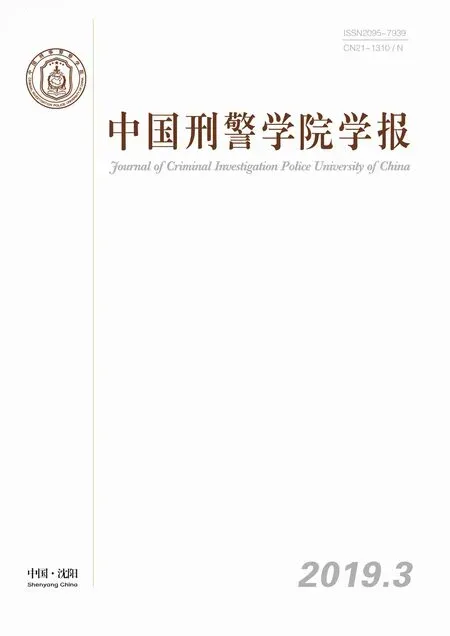警察执行强制措施方式的比例原则审查
——以欧洲人权法院Jalloh v. Germany案为例
艾 明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重庆 401120)
1 引言
警察执法活动具有较强的对抗性,为逃避警察执法,违法犯罪嫌疑人常会做出毁灭罪证、拒捕,甚至武力对抗等举动,为确保执法目的的顺利实现,法律授权警察可采取强制措施。惟法律授权警察采取强制措施与实际达到执法目的之间,仍有巨大空隙,需要警察斟酌执法情势,采取具体方式连接。实务中,部分警察只关注强制措施的启动理由,较为忽视执行方式的合比例性,轻则侵犯人权,重则酿成执法事件。
2013年发生的东莞卖淫女指认现场案,当事派出所为达到取证目的和防止逃脱目的,容许警察用一根长牛绳牵着赤足卖淫女去指认现场,此举引发网友热议。公安部认为派出所的这一举措侵犯了违法人员的人格尊严,对当事民警做出了纪律处分[1]。
2016年发生的雷洋案,检察院最后做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指出:“邢某某等涉案警务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存在使用膝盖压制颈面部、脚踩颈面部等过度控制手段……在执法过程中不履行职务和不正确履行职务,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2]
2017年发生的上海交警摔小孩事件,上海警方在通报中指出:“在该事件中,民警反应过度,未顾及张某怀中儿童的安全,采用了过激的控制方式,超出了合理的限度,造成了不良的影响。”[3]从这一通报可以看出,上海警方对民警采取强制措施的方式也给予了否定的评价。
站在警察角度,类似的指责却让他们感觉颇多委屈。因为执法情势千变万化,违法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难以预料,在此背景下,拿捏具体执行方式的力度着实困难,过轻可能会有碍执法目的的实现,过重可能会招致道义谴责和否定性的法律评价。也因此,虽然公法上有比例原则存在,但法官在运用这一原则审查强制措施的具体执行方式时,最忌抽象论证,妥当的要求毋宁是结合个案的具体情状展开细致分析,详尽说理,始符合比例原则运用的真义。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比例原则虽然在中西文化中均有其历史悠久之起源,但是其解释运用,因为说理不足,立证过少,可能致形成一种崩坏依法行政原则之元凶祸首。”[4]
为累积运用比例原则审查强制措施具体执行方式的理论与经验,本文以欧洲人权法院做出的标志性判决——Jalloh v. Germany案判决为例,展示欧洲人权法院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见解。
2 Jalloh v. Germany案的基本案情及内国法院审理程序①Jalloh v. Germany[EB/OL].(2006-06-11)[2018-08-10].http://www.echr.coe.int/Pages/home.aspx?p=home&c=。
2.1 基本案情
1993年10月29日,4名德国科隆市警察局的便衣警察在两处公共场合发现,申诉人加罗(Jalloh,居住于科隆市的喀麦隆人)将一小包塑料袋从嘴里取出,并将塑料袋交给他人取得金钱。警察怀疑塑料袋中藏有毒品,遂逮捕了加罗,在逮捕的同时,加罗快速将另一小包塑料袋吞进了嘴里。
在加罗身上警察没有发现毒品,考虑到进一步的延误会不利于调查活动,检察官下令对加罗服用催吐药,这项措施由一名医师执行,目的在于让加罗吐出藏有毒品的小塑料袋。
加罗被警察带到一家医院,医师询问了加罗既往的药物史②关于此点,加罗提出异议,他声称其未被医师询问。。在询问加罗是否自愿服用催吐药时,加罗明确表示拒绝。于是他被4名警察按住,医师往加罗的鼻腔插入一根软管直通胃部,通过这根软管,医师将捣成浆状的催吐药让加罗服下。此外,医师还向加罗注射了脱水吗啡,这是另一种类型的催吐药。在服用了催吐药后,加罗很快吐出了一小包塑料袋,袋内有0.2182克可卡因。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后,加罗被一名医生检查了身体,医生称其适合拘留。
在获得法庭批准的逮捕令状后,加罗被羁押在看守所。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加罗说他只能喝汤,而且两周内加罗的鼻子反复流血,他认为,这是插入的软管造成的伤害③关于此点,德国政府有异议,认为申诉人并没有提交医疗报告加以证明。。
在服用催吐药2个半月以后,加罗抱怨胃部持续疼痛,在监狱的医院内加罗作了一次胃镜检查,被诊断出在食管较低的区域有疼痛反应,但医疗报告并未清晰地将此种状况与强迫服用催吐药联系起来。1994年3月23日,加罗被监狱释放,他声称,他不得不接受进一步的胃部治疗,尽管他没有提交任何文件证实④德国政府坚持认为申诉人并没有接受任何医疗措施。。
2.2 内国法院的审理程序
1993年12月20日,在区法院进行的刑事审判程序中,加罗向法庭提出排除警察强制喂服其催吐药取得的证据。理由在于:强制喂服催吐药对被告人的身体造成了伤害,这种作为是德国刑事诉讼法136a条禁止的行为。此外,系争措施是一种显失比例的措施,无法由刑事诉讼法81a条的授权正当化,因为警察本可以等待其自然排泄,获得指控罪行的证据。加罗进一步主张,警察本可以采取81a条授权的其他人身检查措施,如对胃部的灌水催排措施。区法院驳回了加罗的主张,认为警察采取的强制喂服催吐药措施并不是显失比例的措施,判决加罗贩毒罪名成立,处1年监禁,缓期执行。加罗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在上诉审中,地方法院认为,系争措施符合比例原则,由此取得的证据可以使用。理由在于,系争措施之所以被采取是因为如果进一步的延误很可能会不利于调查活动。按照第81a条的规定,针对犯罪嫌疑人强制进行人身检查是合法的,该措施是获取贩毒证据必须的。在执行系争措施时,专门由1名医师执行,遵循了医疗规则,并没有使上诉人的健康处于风险中。最终,地方法院维持了区法院的有罪判决,但将上诉人的刑期减为6个月。
加罗继续上诉申请法律审。加罗主张,81a条并未授权可以采取强制喂服催吐药的措施,因为这种措施是一种威胁生命的人身检查措施。加罗还认为,系争措施违反了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侵犯了他的人性尊严。1995年9月19日,杜塞尔多夫上诉法院驳回了加罗的上诉。
为此,加罗又申诉至联邦宪法法院,主张系争措施是违反比例原则的措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系争措施并未产生任何宪法争议,无论是基于基本法第1条规定的人性尊严,还是第2条第一句联结第1条第一句派生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最后,联邦宪法法院基于权力分立原则,驳回了加罗的申诉。
3 欧洲人权法院的审理程序
加罗不服内国法院判决,又一路申诉至欧洲人权法院,主要主张有两项:第一,德国警察对他采取的系争措施,目的是为取得毒品犯罪的证据,此项措施已构成不人道及有辱尊严的待遇,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第二,内国法院使用采取系争措施取得的证据,已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2005年11月23日,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听审。2006年5月10日,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对该案做出了最终判决。
申诉人加罗主张,系争措施已经构成对他身体完整性的严重干预,并且对他的健康,甚至生命,产生了严重威胁。催吐药中含有吐根糖浆和脱水吗啡,这些物质对生命有危害效果。系争措施会对人的鼻腔、咽喉、食管造成伤害,甚至会让胃里的毒品袋爆裂,威胁生命。强制喂服催吐药的危害已被事实充分证明,在德国,系争措施已导致两名嫌疑人死亡①在德国,系争措施的运用曾发生两次恶性事故。2001年,1名喀麦隆人在汉堡被捕后,被警察采取了系争措施,结果导致他心脏病发作死亡。尸检发现,他有一个未被察觉到的心脏病状况;2005年,1名塞拉利昂人在被采取系争措施后,死在了不莱梅。调查结果虽然认为不是强迫造成的结果,但是,医学专家认为,当水渗入肺的时候,由于氧气短缺,导致了他死亡。。 欧洲大多数国家②德国政府提供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欧洲,有4个国家有将催吐药强制喂服给毒品犯罪嫌疑人的实践(卢森堡、挪威、俄罗斯和德国);有33个国家不能违背嫌疑人的意愿使用催吐药;有3个国家使用催吐药有法律基础,但不知是否在实践中运用过;有6个国家没有使用催吐药的有关信息。以及美国都视系争措施为非法③参见:胡尔贵,郭悦悦.美国毒品治理的路径与启示 [J].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8(5):51-57。。 系争措施不能因为有医学上的协助就被正当化,相反,它增加了申诉人中毒的危险。
申诉人的主张还包括:系争措施侵犯了他的人性尊严。系争措施过于暴力,执行过程使人痛苦和屈辱。在采取系争措施前,并没有医生向他询问即往病史和药物史。在后续监禁的过程中,他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医疗照顾。申诉人强调,系争措施对他的身体,尤其是胃部造成了损伤。
德国政府认为,强制喂服催吐药对申诉人的健康只有极小的风险。吐根糖浆并不是一种危险的物质,事实上,中毒的儿童经常被喂服这种糖浆。插入申诉人鼻腔的弹性软管和注射的脱水吗啡也没有危险。申诉人描述的危险仅可能由长期使用催吐药和错误使用催吐药引起。在侦查实践中,此方法已被运用了无数次,并没有带来并发症的危险。在毒品犯罪严重的州,警察需要这种措施打击犯罪。
德国政府还认为,即使采取系争措施的首要目的在于取得证据,而不是医疗目的,但从申诉人胃里及时排出毒品塑料袋仍然是有医学原因的。这主要是由于毒品塑料袋长时间地停留在人体内部,会产生泄漏中毒的严重后果。为保护申诉人免遭毒品塑料袋破裂的侵害危害,国家必须履行积极的保护义务,而按照该案的具体情况,毒品塑料袋破裂是一个真实的、急迫的危险,在此情势下,等待申诉人自然排出毒品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按照德国政府的观点,系争措施是获得毒品犯罪证据的必要手段。申诉人是在一家医院里被医生喂服了无害的催吐药,在这种环境下,系争措施并不是一种使人羞辱的手段。在采取系争措施时,是由一名医生询问了申诉人既往病史后才执行的,整个喂服过程一直处于医生的监督之下。德国政府强调,并无证据显示申诉人遭到了系争措施带来的持续伤害。申诉人仅仅是在执行系争措施后几小时内感到疲劳,这是脱水吗啡带来的效果。在内国法院审判过程中,申诉人才第一次声称他遭受到了伤害,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支持这一主张。
针对两造观点,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首先抽象阐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和原则。这也是欧洲人权法院在处理个案争议时的一贯做法,先建立相应的基准,再着手具体分析。在谈到对被逮捕的嫌疑人采取违背其意愿的医疗干预措施时,大法庭认为,尽管公约第3条规定:不得对任何人施以酷刑或者是使其受到非人道的或者是有辱尊严的待遇或者是惩罚。但是,一个有必要的医疗干预措施原则上不会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有辱尊严的措施。例如,为了拯救一名绝食的被羁押者的生命,政府采取的强制喂食措施。虽然如此,一个医疗干预措施的必要性必须清晰地存在,并且采取该措施的决定应得到程序上的保证。
即使没有医疗必要性的推动,公约第3条和第8条也不会禁止通过医疗程序以违背嫌疑人意愿的方式,从他的身体获得有罪证据。因此,公约认为像强制抽血或强制提取唾液样本等措施并没有违反公约条款。然而,任何诉诸于为获得证据进行的强制医疗干预,必须基于该案特殊事实而获得正当化,尤其是在从嫌疑人体内取得证据的场合。这种措施具有特别的侵犯性质,因此要求对措施涉及的个案的所有事实因素进行严格审查。尤其要注意的是,措施所针对的犯罪必须是严重的犯罪,政府必须证明他们考虑了可供选择的取证方法,并且措施不会对嫌疑人的身体健康带来长期损害的风险。在这样的案例中,另一些值得考虑的因素是,强制医疗干预措施是否得到了一名医生的执行和监督,是否强制医疗干预措施导致了相对人健康状况的恶化,或者对他的健康产生了持续的负面影响。
对嫌疑人采取强制医疗干预措施不得超过围绕公约第3条所构建起的案例法所指明的最低严重程度。按照人权法院已经建立的案例法,构成公约第3条性质的不人道待遇应当有一个最低严重程度。当然,对这个最低严重程度的评估是相对的,它依赖于案件的所有因素,例如措施持续的时间,它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影响。在某些案件中,还包括性别、年龄和相对人的健康状态。在labita案中,人权法院之所以认定系争措施构成不人道的待遇,主要是因为,系争措施的使用是有预谋的,嫌疑人的手指被警察持续拉伸数小时,这造成了实质上的身体伤害和精神痛苦。有些措施被人权法院认为是“有辱尊严”的,主要是因为这种措施引起了相对人恐惧的心理、极度痛苦的心理、强烈的羞辱感和贬低感,以及摧毁了他们身体上和道德上的抵抗,或者这种措施迫使相对人违背自己的意愿或良心行事。
紧接着,大法庭对本案展开了具体审查。
首先进行的是目的审查。按照德国政府的观点,采取系争措施具有医学上的目的,即为避免毒品塑料袋泄漏给申诉人造成的生命危险。对此,大法庭并不认可。大法庭认为,从内国审判程序来看,内国法院均指出,政府采取系争措施是基于刑事诉讼法第81a条的授权。在大法庭看来,81a条仅仅授权追诉机关为获取证据目的,可以在一名医师的协助下对嫌疑人采取一个侵入式的人身检查,而无需征得嫌疑人的同意,该条款并没有涵盖那些为解除一个人健康有急迫危险的措施。而且,在本案中没有争议的是,政府是在缺乏任何危险评估的前提下采取系争措施的,这种危险评估主要是指申诉人体内毒品袋所带来的风险。此外,尽管德国政府声称,之前从未对未成年毒品犯罪嫌疑人采取过强制喂服催吐药措施①申诉人生于1965年,该案发生时尚未满18周岁。, 政府在对未成年人采用系争措施时会更加谨慎。但大法庭认为,此点并不能证明系争措施的采取出于医学目的,因为系争措施对成年毒犯和未成年毒犯一样会造成健康风险。综合这些因素考虑,大法庭并不认同德国政府采取系争措施是基于医学上的目的,而认为侦查人员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申诉人毒品犯罪的证据。
在进行完目的审查后,大法庭开始进行手段审查。大法庭表示,公约原则上并不禁止侦查机关诉诸强制医疗干预措施以协助犯罪侦查。然而,任何为取得证据目的而实施的干预一个人身体完整的措施必须受到严格的审查。在审查中,以下因素特别重要:措施对实现取证目的的必要性程度,措施对相对人身体健康的风险程度,执行过程和引起的身体疼痛和精神痛苦,可利用的医疗监督的介入程度,对相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紧接着,大法庭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依次考查了上述因素,以判断系争措施是否达到了不人道及有辱尊严待遇的最低严重程度。
第一,措施对实现取证目的的必要性程度。大法庭注意到贩毒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各国都面临贩毒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然而,就本案来说,系争措施针对的只是街头零包贩毒嫌疑人,申诉人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毒品贩卖活动,这从内国法院对他的量刑中就可以看出(6个月监禁且缓期执行)。大法庭虽然同意侦查人员的说法,查清贩卖毒品的数量和质量至关重要,但是在本案中,系争措施并不是取得毒品证据必不可少的方法,侦查人员完全可以等待申诉人自然排泄出毒品,欧盟大多数其他成员国均是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毒品犯罪,因此这种方法是完全可行的。
第二,措施对相对人身体健康的风险程度。大法庭注意到这个问题极具争议,即使在医学专家内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一部分专家认为,系争措施完全无害,且符合嫌疑人的最佳利益;另一部分专家则认为,系争措施有严重风险,应当禁止使用。就大法庭自身的判断而言,大法庭并不认同强制喂服催吐药仅有微乎其微的健康风险,事实上系争措施已在德国导致两人死亡。大法庭也注意到,在相关国家,强制喂服催吐药只适用于小部分可以运用催吐药的案件,然而,死亡事故恰好都发生在这一小部分案件中。而且,德国大多数州①在德国各联邦州中,对贩毒嫌疑人采取服用催吐药获取证据的法律实践也颇不统一。自1993年来,16个州中有5个州(Berlin、Bremen、Hamburg、Hesse and Lower Saxony)都使用了这种措施。然而,一些州中止使用该措施,另一些州没有中止。在大多数涉及催吐药的案件中,嫌疑人在被告知如拒绝服用催吐药后将被强制服用,嫌疑人选择自己吞服。在另一些州,催吐药不能被强制服用。以及欧盟大多数成员国都禁止采取系争措施,这一事实也说明系争措施会引发健康风险。
第三,执行过程。大法庭注意到,在申诉人拒绝自愿服用催吐药后,他被4名警察紧紧按住。在这一过程中,警察的武力使用近乎残忍。随后,一根软管插入他的鼻腔,直通胃部,这必定会引起他的疼痛和焦虑。申诉人还遭受到了另一种违背其意愿的侵入措施,他还被强制注射了另一种催吐药。还应当考虑到的因素是,在等待催吐药发生效应的这段时间,申诉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在这段时间里,申诉人被4名警察和1名医生控制和监视。在这种环境下,申诉人当着众人之面呕吐,于他而言无疑是一种羞辱。大法庭并不认同德国政府的观点,德国政府认为,申诉人自然排泄出毒品也是对申诉人的一种羞辱。大法庭认为,尽管这一措施对个人隐私也有所侵犯,但是其对个人身体和精神完整性的干预明显小于系争措施。
第四,系争措施的医疗监督。大法庭注意到,系争措施是在医院由一名医生执行的。在执行完系争措施后,一名医生对申诉人进行了身体检查,并且宣称申诉人适合被羁押。然而本案中有争议的是,在执行系争措施之前,申诉人是否被医生询问过既往病史。在当时的情况下,申诉人竭力抵抗系争措施,加之本人不会说德语,只会讲很差的英语,因此大法庭假设他不会回答医生的提问,也不愿意提交以前的病历,而德国政府没有提交任何文件或证据证明这个事实。
第五,对相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大法庭注意到,系争措施是否给申诉人身体,尤其是胃部,造成了长时间持续的损害,双方意见不一。目前没有任何事实支持申诉人在被逮捕后进行了两个半月的胃部治疗,或者采取了后续的医疗措施。然而这一结论并不能让大法庭对上述意见产生怀疑,即系争措施并非对申诉人的身体健康没有风险。
综合上述因素,大法庭认为,系争措施已经达到了公约第3条规定的不人道及有辱尊严待遇的最低严重程度。德国政府采取了违背申诉人意愿的严重干预措施,这项措施严重干预了申诉人身体和精神的完整权。德国政府采取系争措施,并不是出于医疗目的,而是为了取得证据,而该项证据的取得本可以使用更少侵犯性的方法。最终,大法庭以10比7判决申诉人系违反公约第3条的受害者,系争措施构成公约第3条禁止的不人道及有辱尊严的待遇。以11比6判决德国政府赔偿申诉人精神损害10000欧元,赔偿申诉人由此的花费5868.88欧元。
4 由该案判决引发的对比例原则运用的思考
从表面来看,欧洲人权法院是在判定德国政府的作为是否违反公约第3条,但从判定的整个思考过程来看,人权法院实质上是以比例原则为骨架展开的。因此,深入分析该判决,有利于我们理解欧洲人权法院是如何精致化地运用比例原则审查警察强制措施的执行方式。
4.1 目的审查的必要性
通说认为,比例原则的结构为三阶结构,分别由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构成。适当性原则,又称为妥当性原则,它是指公权力行为的手段必须具有适当性,能够促进所追求的目的的实现。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小损害原则,它要求公权力行使者所运用的手段是必要的,手段造成的损害应当最小。狭义比例原则,它要求公权力行使的手段所增进的公共利益与其所造成的损害成比例。三阶结构的比例原则主要关注的是对公权力行使所选择的手段的评价,并不直接关心公权力行使目的的正当与否。
对传统的三阶结构,部分学者进行了反思,认为应当将比例原则的三阶结构扩充至四阶结构,补足对公权力行使目的的审查。例如,德国著名学者斯特芬·德特贝克在其最新版的教科书中认为,比例原则的第一阶段应为目的审查,“法院首先应当查明国家活动的目的,……然后再审查这种目的是否合法或违法。……如果国家追求一个违法的目的,就会损害权利,这种国家活动也就不再具有合比例性。”[5]135
对上述见解,本文表示赞同。这主要是因为,公权力措施及介入的事物领域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事物领域,公权力措施介入后可以比较清晰地显示欲促进的正当目的,但有些特殊的事物领域,公权力措施介入后,可能有多个目的存在,公权力措施究竟欲实现何种主要目的并不总是清晰的。至少,就本案讨论的刑事侦查领域,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一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行使有可能是为了实现法律规定的取证目的,有可能是为了保障警察自身安全,还有可能如本案这种特殊场合,是为了危害防止,消除对嫌疑人的生命威胁。尽管上述目的都具有正当性,但法官如果不首先确定公权力措施欲实现的主要目的为何,那么后续对手段必要性和均衡性的审查就会失去方向。法官只有先识别公权力措施欲实现的真实目的,才能为手段必要性和均衡性的审查提供清晰的指向。我国有学者就指出:“要判断公权力行为目的的正当性,首先应当查明真实目的。这种真实目的,应当是立法者、行政者在做出限制公民权利决定的当时所欲追求的目的。”[5]138
就本案而言,大法庭在对系争措施进行手段审查之前,首先对系争措施欲实现的目的进行了审查。按照德国政府的观点,采取系争措施具有医学上的目的,即为避免毒品塑料袋泄漏给申诉人造成生命危险。如果系争措施欲实现的目的真如德国政府所言,那么大法庭对后续手段的审查就不会采取严格的审查标准,而是会采取宽松的审查标准,结论就很可能是系争措施并没有违反公约第3条,毕竟人权法院已有判例显示,为了拯救一名绝食的被羁押者的生命,政府采取的强制喂食措施并不构成不人道及有辱尊严的待遇。
然而,大法庭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并没有认可德国政府宣称的医学上的目的,而是认为侦查人员采取系争措施欲实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毒品犯罪的证据。主要的依据有:第一,内国法院一直认为,政府采取系争措施是基于刑事诉讼法第81a条的授权。而在大法庭看来,81a条仅仅授权追诉机关为获取证据目的,可以在无需征得嫌疑人同意的情况下,采取人身检查措施,但该条款并没有涵盖那些为解除一个人健康有急迫危险的措施。第二,政府是在缺乏任何危险评估的前提下采取系争措施的。
4.2 必要性审查——坚持最小损害标准
在实践中,必要性原则常被解读为最小侵害原则。例如,姜明安教授认为,必要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必须在多种方案、多种手段中选择对行政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方案、手段实施。该原则亦称‘最小损害原则’”[6]。余凌云教授认为,必要性要求“所要采取的手段在诸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中是最温和的、侵害最小的。”[7]因此,比例原则中的“必要”并不是如在汉语中所谓的“非这样不可”的意思,而是相对不可避免的侵害而言——行政机关只能选择最小,为达目的以无可避免的侵害手段来执行任务[8]88。
从欧洲人权法院对手段必要性的审查实践来看,其也是坚持最小损害标准的。有学者就指出:“欧洲人权法院还要求,在能够达到同种目的的所有方法中,缔约国应采用侵犯个人权利的最小措施。法院首先通过经验和事实的评估寻找出可能的替代性措施,然后再通过严格的评估方法选择其中最为有效且对个人权利负面影响小的最优措施,该理论得到人权法院的普遍适用。”[9]105
必须指出的是,选择最小损害的手段应当以手段的相同有效性为前提。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十分强调“相同有效性”的功能性控制:“并非其它方案胜过立法措施的任何一项个别优点都必然导致措施违宪,作为其它选项之较温和的措施,必须在每一方面都明白地确定,其对目的之达成与立法措施在事理上具有相同价值,才能被认为是具有相同有效性。”[10]85
大法庭认为,在获取体内的毒品证据方面,系争措施和等待申诉人自然排泄出毒品具有相同的有效性。因此,系争措施并不是取得毒品证据必不可少的方法,侦查机关完全可以等待申诉人自然排泄出毒品。当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适用最小损害标准,相当于把最终确定排他性手段的权力赋予了司法[10]86。这种取向意味着毫无执法经验的法官有可能在帮经验丰富的执法人员选择适合的执法手段,这种选择的合理性何在?可能正是考虑到了这种质疑,大法庭在判决中反复强调,等待嫌疑人自然排泄出毒品,这种方法是欧盟大多数成员国在调查毒品犯罪时采取的方法,因此这种方法完全具有可行性。
4.3 狭义比例原则审查——综合考量个案因素
在认定其是否构成公约第3条禁止的不人道及有辱尊严的待遇时,大法庭在综合分析个案因素时,实际上运用了利益衡量思维,体现了狭义比例原则的特点。
从历史起源来看,狭义比例原则最早就出现在规范强制措施执行方式的场合。例如,德国黑森州1950年颁布的《黑森州公权力直接强制执行法》第4条规定:“在直接强制执行时,应当选择对相关方与公众损害最小的手段,并且损害与行为所追求的目的不能明显不成比例。”这充分说明,运用狭义比例原则评价强制措施执行方式具有天然的亲和性。
然而,如何进行利益衡量,却往往成为争议的焦点,有学者即称:“‘法益相称性’的要求则可能已成为比例原则的‘阿喀琉斯之踵’。其初衷本是更深度地保护相对人权利,但如何判断利益的大小轻重是其不得不直面的现实课题。”[11]尤其在警察执法场合,这种利益衡量更显困难,因为警察执法具有的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当目的光环,常常让理性的衡量步履艰难。例如,香港围绕7名警察清场时殴打“占中者”被判入狱2年引发的争论成为印证这一判断的最新注脚[12]。
就利益衡量的方法而言,由于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价值位阶规范,因此衡量必然是紧扣“个案”所为的,不可能也不容许抽象的利益衡量的可能。因为只有紧扣个案,才能保证法院所为的衡量至少是一个有具体指涉对象,而可能将该衡量的结果限定于该个案的情形,也才有了一定客观可理解的基准。在个案衡量时,厘清发生冲突的私人法益与公共利益是首要任务[8]98。
就本案而言,大法庭基本上也遵循了上述方法,具体而言:
就系争措施促进的公共利益而言,大法庭认为,本案中的追诉利益较小,系争措施针对的只是街头零包贩毒嫌疑人,申诉人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毒品贩卖活动,这从内国法院对他的轻微量刑中就可以看出(6个月监禁且缓期执行)。本文认为,在运用狭义比例原则进行利益衡量时,相较于私人法益损害的界定,政府所促进的公共利益的界定总会伴随争议。本案中,以大法庭雷斯(RESS)等4名法官撰写的不同意见书中就认为:“多数派的这种意见(极力缩小本案罪行严重性的努力)并不正当。事实上,正如德国地方法院判决显示的那样,申诉人在上午11点35分从他的嘴里拿出一袋毒品进行了贩卖,到了12点25分,他又从嘴里拿出一袋毒品进行交易。这些情况都被警察观察到,他们并不知道毒犯在嘴里藏了多少包毒品,这些情况显示申诉人是一个连续贩毒之人。在这种情况下,警察认为申诉人的行为涉及较为严重的犯罪,这是可以接受的。……任何一名从事毒品犯罪的人都要考虑到遭受不利措施的可能性。按照我们的观点,系争措施并没有达到公约第3条禁止措施的入门门槛。”
之所以会有这种争议,可能与大法庭界定公共利益的策略和方法有关。大法庭在界定公共利益时,倾向于采取“隔断界定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在界定公共利益时,大法庭仅依据个案中明白呈现的事实加以判断,很少依据潜在的连带的事实进行分析推断,一言以蔽之,纯粹就事论事。例如,在本案中,大法庭仅以内国法院对申诉人的轻微量刑,认定本案涉及的追诉利益较小。这种策略和方法又可能与欧洲人权法院自身的角色和理念有关,有学者在分析其他案例时,也指出了这一特点:“我们看到人权法院仅突出地强调了禁令将会给受害者的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失,并没有实质性地考虑违反英国‘司法秩序’将会带来何种不良后果。这反映了欧洲人权法院和欧盟法院在判决理念上的基本不同:前者是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适用比例原则,后者则是在适用比例原则的基础上保障人权。”[9]105
与之不同的是,一线执法人员在看待公共利益时,往往倾向于采取“整体分析法”,尤其在打击违法犯罪场合,一线执法人员认为如不遏制多发的小案,往往会带来对社会秩序更大的破坏①。 在这种策略指导下,以打击违法犯罪为己任的警察往往会更倾向于对犯罪和犯罪嫌疑人展示自身的强力形象,借此向外界传递鲜明的信号,达到遏制潜在犯罪的目的,以维护更多的社会利益。对警察执法的这个特点,美国著名法官波斯纳曾敏锐地予以揭示:“反恐情报机构最可能希望做到的就是给这个国家的敌人增加成本,希望扰乱他们的计划。如果电子监听没有截获有关下次袭击的时间和地点的信息,就认为它失败了,这个想法错了。”[13]
在界定了系争措施促进的公共利益后,大法庭逐项分析了系争措施给申诉人私人法益所造成的侵害。
第一,是系争措施对申诉人身体健康带来的风险问题。尽管在医学专家内部存在着争论,大法庭仍根据既有证据(系争措施已在德国导致两人死亡,德国大多数州以及欧盟大多数成员国都禁止采取系争措施),认定系争措施会引发健康风险。
第二,是执行系争措施的方式对申诉人所造成的伤害。大法庭认为,系争措施的执行方式首先给申诉人造成了身体疼痛;其次,等待催吐药发生效应的这段时间,申诉人还遭受了精神痛苦和羞辱。
第三,是医疗监督措施不尽完善。大法庭认为,德国政府没有提交任何文件或证据证明,执行系争措施之前,医生曾详细询问过申诉人的既往病史,这种措施的缺失也会潜在地对申诉人的身体健康带来风险。
4.4 进一步的思考:比例原则向五阶结构的演变?
以本案为基础,结合欧洲人权法院以往审理的案件,本文认为,人权法院在运用比例原则审查内国政府具体作为时,有朝五阶结构演变的趋向,尤其在审查警察执行强制措施方式的时候,这种趋向体现得更加明显。这种趋向是不是可以说明,比例原则传统的三阶结构并不是惟一、固定的结构,三阶结构只是为比例原则的具体运用提供了一个操作平台,法官在具体运用这一原则时,应当结合自身的角色定位以及审查对象的事务本质,作适当的结构扩充。
第一,是向三阶结构的前端扩充,即加入目的正当性审查。这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审查政府作为是否具有正当目的,以及在有多个正当目的情况下判断何为政府作为的真实目的,为后续的手段审查提供清晰的方向。就本案而言,德国警察采取的强制喂服催吐药措施就存在着两个正当目的:一个是取证目的,另一个是德国政府宣称的医疗目的。确定系争措施所欲实现的真实目的为何,对后续的手段评估有重大影响。例如,本案在内国法院审理程序中,区法院和地方法院先后认为系争措施没有违反比例原则,联邦宪法法院也认为本案没有引起宪法争议。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可能在于内国法院一开始认定的目的就与欧洲人权法院有别,因而后续对手段的审查持宽松立场。而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德国警察采取系争措施的目的是获取毒品犯罪的证据,并没有认可德国政府宣称的医疗目的。在确定这一目的后,欧洲人权法院对后续手段的审查选择了严格的立场。
第二,是向三阶结构的后端扩充,即在狭义比例原则审查后,进一步审查系争措施有无构成公约规定的禁止措施的入门门槛。例如,某项系争措施,通过了目的审查、适当性审查、必要性审查,也通过了狭义比例原则审查,但系争措施仍然有可能达到公约规定的禁止措施的入门门槛。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极具争议的Gäfgen v. Germany案。在该案中,德国警察为了营救1名11岁的被绑架男孩,对坚不吐实的绑匪卡夫根(Gäfgen)实施了逼供行为①美国警政学者提出的“破窗效应”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反映。参见:乔治·凯林,凯瑟琳·科尔斯.破窗效应——失序世界的关键影响力[M].陈智文,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103-110.。 如果按照德国大多数民众的理解,警察实施的逼供行为具有正当目的(为了营救一个小男孩的生命),手段必要(绑匪坚决不交待被绑男孩的关押地点,警察没有别的办法查寻下落),利益均衡(为营救生命,警察只是实施了威胁逼供的行为)。然而,欧洲人权法院仍然认为,德国警察实施的逼供行为构成不人道的待遇,违反了公约第3条。
就本案而言,欧洲人权法院也在判决中认为,按照人权法院已经建立的案例法,构成公约第3条性质的不人道待遇有一个最低严重程度(入门门槛)。欧洲人权法院这一见解的潜台词实际是指,系争措施即使通过了比例原则最后一道关口—狭义比例原则的审查,但如果仍然达到了公约第3条禁止措施的最低严重程度,仍然不具正当性。
至少就欧洲人权法院而言,其在运用比例原则时有向三阶结构的后端扩充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和欧洲人权法院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的。欧洲人权法院素被誉为“第四级法院”“准欧洲宪法宪院”,是欧洲人权公约的守护神,担当着“泛欧区域人权维护者与人权指标发展者的双重角色”[14]。在这种角色定位下,欧洲人权法院在审查系争措施时,往往具有保障个人权利的天然敏感性。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实质性地权衡公约权利与集体美德就成为法官在该权利哲学基础下适用比例原则的关键任务之一。然而,即便如此,对权利的限制并非是无条件的。任何对权利的限制都不能伤及权利的‘本质’以及‘核心’。”[9]104
5 结语
总体而言,欧洲人权法院Jalloh v. Germany案判决极具启发意义,这种启发意义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就强制措施的执行方式而言,警察要特别秉持比例原则的精神。本案涉及的强制措施是人身检查措施,人身检查措施素被誉为测试“刑事诉讼法作为应用宪法”最佳的“试金石”之一[15],侦查人员在采取人身检查措施时,不能仅以符合法律授权条件为已足,尚需斟酌具体的执行方式,而后者在实践中常被侦查人员忽视。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81a条特别指明,强制人身检查措施应在对被指控人健康无不利之虞时始可采取的前提下,德国侦查人员仍有忽视具体执行方式的情况发生。反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2条仅以极其简略的条件,授权侦查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人身检查,对这种缺乏明确要件限制的授权条款,有学者已表示了担忧:“如果立法上仅仅设定概括性的适用条件,显然不利于实务操作,甚至还会导致侦查权力的滥用,这显然不符合比例构造的要求。”[16]在我国人身检查措施的授权规定本身即欠缺比例原则精神的条件下,期待侦查人员能谨慎选择具体的执行方式似乎过于理想化。观诸侦查实践,有违比例原则采取人身检查措施的现象在我国时有发生,例如,侦查机关动辄采取大规模抽血比对措施[17],在缺乏必要医疗监督措施的前提下,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服用催吐药措施[18]。
在此背景下,Jalloh v. Germany案判决对我国警察如何遵守比例原则,选择适当的强制措施执行方式颇具借鉴意义,进而能为建立刑事执法负面清单制度提供参考[19]。
第二,就比例原则的具体运用而言,传统的三阶结构并不是比例原则惟一、固定的结构,而只是为比例原则的具体运用提供了一个操作平台,审理法官在具体运用这一原则时,应当结合自身的角色定位以及审查对象的事务本质,作适当的结构扩充。Jalloh v. Germany案判决为比例原则的这种结构扩充提供了现实例证,也为我们精致化地运用比例原则贡献了启发性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