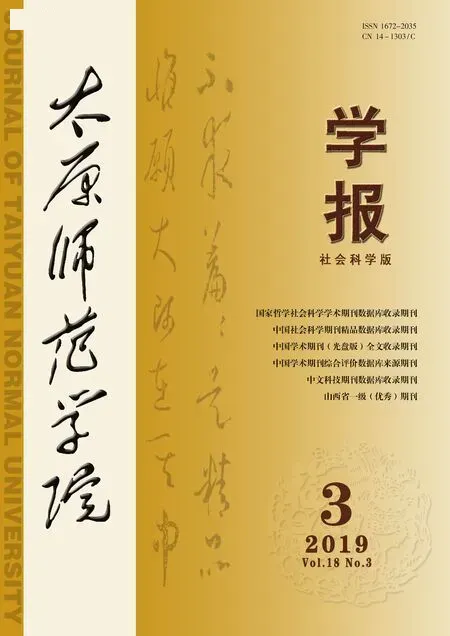《汉宫秋》与《梧桐雨》“华夷观”特点及成因探析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华夷观”在不同民族冲突或者融合中产生,蒙元时代激烈的“夷夏之辨”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相关历史杂剧创作中。
一、华夷观:立场不同,表述不同
《汉宫秋》与《梧桐雨》皆以华夷冲突为戏剧背景,作为“夏”一方代表的汉元帝、唐明皇是被迫的求和者、屈辱的受害者,王昭君、杨贵妃更是为华夷对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战争对“夏”一方是沉重而悲痛的。呼韩邪单于、安禄山作为“夷”一方是悲剧的直接责任者。但身为汉人身份的作者又不像后世《长生殿》单独安排一出雷海青“骂贼”,来证明残暴的安禄山,尽管是武力征服者,文化上却摆脱不了“腥羶”夷狄的印记。[1]129-132白朴、马致远作为由金入元的汉人,本人以及家庭可能都经历过蒙元灭金的战争,接着又亲历了蒙元灭宋的历史大事。“夷夏之辨”对战争中任何一方来说,都是逃避不了的话题。而白朴、马致远作为戏曲创作家,其戏曲内容表现出来的“华夷观”似乎既不同于站在宋人立场上的“严夷夏之防”,又不同于站在蒙元立场上的“华夷一体”。
两宋自始至终面对着强大的外族威胁,北宋亡于金朝,南宋亡于蒙元,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也占不到多少便宜。华夷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两宋名士及名臣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陆九渊、吕祖谦等无不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纷纷对应该如何处理以及如何看待华夷关系献计献策。面对各方面似乎更加强大的夷狄,事实上“用夏变夷”几乎不可能,大概率反而是“用夷变夏”。因此只能在大义名分上对夷狄进行蔑视和贬低,在实际处理办法中,主张不与夷狄计较太多,以排斥为主,任何可以唤起夷狄想象的比如佛教以及夷狄衣制、饮食文化,都加以严厉的批判,而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中国”本身的问题上。朱熹云:“某尝谓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春秋则是尊王贱伯,内中国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2]2227又云:“而今衣服未得复古,且要辨得华夷。”[2]3068这些话显示了儒家士大夫面对夷狄不够自信的态度。宋人逃避夷狄问题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于武功的软弱,防御尚且不足,更遑论开拓进取。而事实上“夷夏之辨”在本义上就已经为逃避夷狄问题准备了理论依据。《春秋公羊传》有“三世说”:所见“太平世”,所闻“升平世”,所传闻“据乱世”。每一世的内外关系都有不同的处理办法。何休云:“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狄夷。……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犹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3]2200宋人面对夷狄强盛的现状,自然无法用“太平世”来看待“夷夏之辨”,相反,企图根绝夷狄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以减少心理和实际上的威胁成了儒家士大夫的最佳选择,也即“严夷夏之防”,实际效果到底如何尚在未定之中。
蒙元作为草原征服民族,利用武功先灭金后灭宋,接着面临着以夷狄身份如何统治原有“中国”土地和人口的问题。蒙元建国后,“大一统”在现实上已经成为事实,而“三世说”在理论上也为其“大一统”提供了依据。干春松说:“春秋学‘从变而移’的诠释策略,……体现在夷夏观念中,表现为大一统帝国稳固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选择从‘尊王’的角度去解释夷夏关系,强调王者无外立场,而在帝国分崩离析,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人们又会倾向于从‘攘夷’的角度来解释夷夏关系。”[4]其结果是蒙元思想家抛弃了两宋士人“狭隘”地从“种族”“地域”“政权”等看待夷夏关系,主动包容、吸收“华夏文化”,从“文化”高度上宣扬“华夷一体”。
以忽必烈开府金莲川时期即已招揽的重要谋士郝经为例。郝经认为,汉人不一定能坚守、传承华夏文化:“礼乐灭于秦,而中国亡于晋。已矣乎!吾民遂不沾三代、二汉之泽矣乎!”“晋能取吴而不能遂守,隋能混一而不能再世。”(《时务》)[5]259而异族反而能继承、发扬华夏文化:“苻秦三十年而天下称治,元魏数世而四海几平。”(《郝经·时务》)[5]259“金有天下,席辽、宋之盛,用夏变夷,拥八州而征南海。威既外振,政亦内修,立国安疆,徙都定鼎。至大定间,南北盟誓既定,好聘往来,甲兵不试,四鄙不警,天下晏然,大礼盛典,于是具举。泰和中,律书始成,凡在官者,一以新法从事,国无弊政,亦无冤民。粲粲一代之典,与唐、汉比隆。”(《删注刑统赋序》)[5]186所以,统一天下的关键不在于地域和种族,而在于继承、力行仁义之道:“天无必与,惟善是与;民无必从,惟德是从。中国而既亡矣,岂必中国之人而后善治哉?圣人有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以是知天之所与,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不在于道而在于行力为之而已矣。”(《时务》)[5]259而忽必烈正是能行仁义之道的君主:“今主上(忽必烈)在潜,开邸以待天下士,徵车络绎,贲光丘园,访以治道,期以汤、武。岁乙卯,下令来徵,乃慨然启行。以为兵乱四十余年,而孰能用士乎?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5]103-104
宋人可以说是有理由的,“夷夏之防”是为了防御夷狄入侵;但蒙元同样是有理由的,“华夷一体”是为了一个统一的帝国。元杂剧历史剧创作主体是由金入元的儒家文人,他们是长时期复杂、激烈的华夷冲突以及民族融合的亲历者,自身又是以被征服者身份进入元朝,对故国的灭亡尚保留有惨痛的记忆,这种心态又难免会反映到文学包括相关杂剧创作中。但是杂剧创作又不同于充满个性的自我写作,往往受市场反响等种种条件的制约,因此其历史剧中的“华夷观”不同于两宋、蒙元态度鲜明而又截然对立的形态,呈现出自身的特点,而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试以《汉宫秋》和《梧桐雨》二剧为例,就此加以研究。
二、《汉宫秋》《梧桐雨》所呈现的“华夷观”特点
《汉宫秋》与《梧桐雨》在“华夷观”方面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真实性
二剧所描述的华夷实力差别基本上是历史真实的反映。汉元帝时,虽然暂时取得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北匈奴郅支单于被灭,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附汉,但汉朝此时,“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6]3027。汉臣感叹匈奴素来“万里难制”[6]3027,如果诉诸武力,面对的将是夷狄的叛降无常和国内的人、财匮乏。此时匈奴经过长期分裂和内乱,实力衰耗严重,只好选择称藩于汉。汉朝也希望以羁縻笼络换取和平,“和亲”即是羁縻手段之一。唐开元、天宝年间似乎是唐代最为强盛时期,然而安禄山叛乱以来,不到一年就接连攻陷洛阳、长安,大唐帝国轰然之间支离破碎,叛军强大或许是原因之一,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唐帝国自身内部的败坏和虚弱。随着美丽的杨贵妃被赐死马嵬驿,大唐也似乎从此失去了灵魂。安禄山的叛乱虽然最终失败,但由叛乱带来的藩镇问题始终困扰着唐朝。
《汉宫秋》呼韩邪单于要求和亲的底气是“控弦百万为君长”“久居朔漠,独霸北方,以射猎为生,攻伐为事”,但又不得不承认“宣帝之世,我众兄弟争立不定,国势稍弱”[7]1。剧中匈奴一方与主动称藩求和的历史事实庶几相近。汉人一方,元帝期望满朝大臣能退得番兵,不使昭君出塞,但“卧重裀食列鼎,乘肥马衣轻裘”[7]12的石显、五鹿充宗只是劝元帝认清事实、割情舍爱:“想纣王只为宠妲己,国破身亡,是其鉴也。”[7]11“陛下,咱这里兵甲不利,又无猛将与他相持,倘或疏失,如之奈何?望陛下割恩与他,以救一国生灵之命。”[7]12“不是臣等强逼娘娘和番,奈番使定名索取。况自古以来,多有因女色败国者。”[7]13剧中石显、五鹿充宗坚持和亲,实际是汉廷既定对外政策,元帝亦云“边塞久盟和议策”[7]2。历史上元帝时期抑制轻启边衅的行动,既使对外战争取得胜利,结果也不例外。陈汤、甘延寿有诛郅支单于之功,而中书令石显、丞相匡衡不但抑其封赏,还欲追究陈汤贪赃之罪。石显等人威福专权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恐怕还代表朝廷主和的一派,担心取侮生事,引起战争。《梧桐雨》的作者白朴与其他杂剧作者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其士人身份,因此相对于其他杂剧较大成分的“戏”说而言,《梧桐雨》更为尊重历史事实。王文才《白朴杂剧全目提要》言“本剧(《梧桐雨》)用事出入史传”[8]188,是一个准确的判断。其实“历史真实”最重要的还是人们对历史的常识和直觉上的“真实”,当华夏王朝进入衰落期,往往遭受新一波夷狄征服者侵扰和打击,相同历史反复上演,于是在华夷冲突中,华夏一惯成为悲剧的承受者。
(二)双重性
宋人或是以郝经为代表的元人,在“华夷观”上有着基于自身立场的鲜明态度,《汉宫秋》《梧桐雨》二剧却不同于此,并未站在任何一种立场,也并未表现出鲜明的爱憎态度。站在汉元帝、唐明皇的立场来说,作品固然表现出对王昭君、杨贵妃之死的悲哀和对汉元帝、唐明皇遭遇的同情,但这乃出于人类普遍的同情弱者的感情。剧中“君臣”既没有以华夏文化高于夷狄进行心理安慰,更没有在“夷夏之防”上积极、主动地付出实际行动。站在呼韩邪单于、安禄山的立场来说,作者并不否认夷狄武力强盛、君臣团结,甚至能轻易征服中原王朝的一面,但对夷狄的赞美也仅此而已。剧中呼韩邪单于迫切出兵的原因仅仅是汉宫不放昭君和亲,安禄山不但要“抢了贵妃”,还要“夺了唐朝天下”[8]18,这些都停留在满足私人欲望的层次,从来没有想到过把征服优势上升到“夷夏一体”高度的文化建设上。因此,可以说作者对华夷任何一方皆是持双重的立场,在对任何一方表达同情或赞许的同时,又对任何一方保留批判和不满。
(三)玩世、超然性
双重的立场使二剧对“华”“夷”人物都表现出一种玩世、超然的态度。也就是说,作者没有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事件,也无视拥有至高权力的君王的权威和神圣,而是对所有人物一视同仁,直接暴露其与普通人相似的人性的欲望、软弱和怯懦。作为“戏中人”,一切言行举止皆带有“戏”的色彩。“汉皇”与夷狄君主皆“重色”,汉元帝见了昭君后,“如痴如醉,久不临朝”“今日方才升殿,等不的散了,只索再到西宫看一看去”[7]10。唐玄宗自言“寡人自从得了杨妃,真所谓朝朝寒食,夜夜元宵”[8]12。呼韩邪单于点名索要昭君,安禄山两大目的之一就是“抢了贵妃”。作为元帝臣子的尚书令五鹿充宗和作为玄宗臣子的李林甫,平时不对君主宠幸后宫有任何谏诤,但当君上被逼和亲以及逃亡的时候,又把责任推到“女宠”头上,惯于逃避责任。五鹿充宗说:“想纣王只为宠妲己,国破身亡,是其鉴也。”[7]11“不是臣等强逼娘娘和番,奈番使定名索取。况自古以来,多有因女色败国者。”[7]13李林甫言:“陛下,只因女宠盛,谗夫昌,惹起这刀兵来了。”[8]21君臣因无能正遭受事实上的损害,却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强要面子,极具讽刺意味。当元帝想要送别昭君时,尚书令云:“只怕使不的,惹外夷耻笑”[7]13。对于最能触痛华夏神经的宫闱秽事,作者偏偏津津有味,安禄山、杨贵妃私情,大部分同类作品都作删节处理,《梧桐雨》剧中却借当事人之口两次说出(安禄山:“别的都罢,只是我与贵妃有些私事,一旦远离,怎生放的下心。”[8]6杨贵妃:“此人(安禄山)猾黠,能奉承人意,又能胡旋舞。……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8]11),丝毫不想给代表华夏的唐明皇留什么面子。总而言之,作者是以一种超然于物外的旁观者玩世态度来创作,华夏君臣的软弱、逃避和屈辱似乎成为作者嘲笑的对象,而实施粗暴的掠夺和破坏的夷狄反倒成了作者欣赏的对象。
(四)悲剧性
对华夷冲突造成的悲剧,隐藏着作者深层的悲痛情感。汉元帝听“长门雁叫”,唐玄宗闻“秋风梧桐”,内心悲伤而孤独,但又不是一般的孤独,曾经的繁华歇绝、热闹成灰,最美好的已经失去,是不再有希望的孤独。《汉宫秋》《梧桐雨》二剧又皆有“梦”的描写,“梦”包含两重意蕴。第一重,借以逃避现实的失望和痛苦,至少在梦境中令人暂时忘却难以接受的现实,重温昔日美好。《列子》有老役夫“侵晨错而弗息”“筋力竭矣”,但夜则“梦为国君”“其乐无比”,人生的痛苦和快乐犹可各占一半。[9]101而积极逃向梦境的人,恰恰可以从反面看出其在清醒的现实中饱受无穷无尽折磨的悲惨。汉元帝希望“高唐梦”“楚襄王枕上雨云情”[7]23,唐玄宗希望回到“长生殿排宴”时,都只能够寄托于梦境。第二重,他们期望的“梦”并没有实现,汉元帝的梦境不乏刀光剑影,唐玄宗“好梦将成还惊觉”[8]39,梦境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片刻的抚慰,“梦”也是令人失望的。也就是说,他们无论白天黑夜、何境何地,都无法得到安慰,只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痛苦。这已经是哲学层次上的人生悲剧,充满痛苦而且欲逃避而不得的情感体验,对人类来说是共通的、普遍的,也是深沉的。对有生活经验的观众来说,主人公的情感遭遇易于得到同情和理解。面对辽、金、宋、元复杂的华夷冲突局势,总体上谁压倒谁是一回事,但对各方的普通人来说,都承受着冲突和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作者借汉元帝和唐玄宗说出了观众心底最真实的感受,在热闹的戏场上成为观众的知音。这种饱满的情感力量,恐怕才是《汉宫秋》《梧桐雨》二剧动人之处以及魅力所在。
三、原因探析:作者、时代与观众
《汉宫秋》《梧桐雨》二剧“华夷观”呈现以上特点的原因,既与作者人生经历与创作态度有关,也与杂剧这种“戏”的创作要求有关,还要考虑到二剧皆是用于舞台表演的“戏”曲,更要照顾观众的欣赏需求。
(一)作者的情感与态度
作者抱有“玩世”的心态,却融“至情”于杂剧。存世的白朴生平资料较多,因此较易于了解其人生经历。白朴出生于金国簪缨名族,七岁遭蒙元灭金国难,八岁围城中仓皇失母。白朴先随元好问居冠氏县,后随父华依真定史天泽习律赋专门之学,准备应举。元代长时期废除科举,使士人通过科举途径贵显的希望落空。但文士并非没有进身之路,世祖中统二年(1261)四月即命宣抚司官举文学才识茂才异等列名上闻,白朴在此次被荐之列。但三十六岁的白朴“再三逊谢”,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至于其放弃的原因,大概与其父降元求官不得反招屈辱带来的心理阴影有关,另外还有元好问金亡不仕的榜样,以及元代士人入仕身份卑微的现实因素。个性方面,白朴“放浪形骸,期于适意”(王博文《天籁集》序)[10]206,“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节,又不欲使爵禄以污其身,于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孙大雅《天籁集》序)[10]206。所谓“玩世”,是指士大夫一种独特的处世方式,士大夫本来应该有为家、为国、为天下的胸怀和抱负,并且通过不断的努力来完成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但当形势不允许,甚至履行责任反而会招来巨大的灾难时,只好通过种种形式,来躲避或者故意显示已经放弃本来的追求,而只求一己之适意,采取的形式往往是放浪形骸、游戏人间。白朴有玩世滑稽的充分理由,特别是在其中体验到了乐趣和成就感。以士大夫眼光来看,杂剧创作无疑也是“玩世”的一种,而在表现剧作中“华夷观”时也抱有一种玩世心态,因此在剧中呈现出双重、矛盾、超然的特点也就不足为奇了。马致远同样如此,起初以儒求仕,热心进取,但近不惑之年才谋得了一个江浙行省务官的卑微吏职,饱受压抑和痛苦,失望和幻灭之余,逃离官场并专心于杂剧创作。张大新说:“从马致远晚年自号‘东篱’的情况推测,他是自动离开官场而放浪江湖的。”[11]事实是否如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曾经以“拿云手”“栋梁才”自命的马致远最终也以“玩世”的心态对待生命及创作。这种心态在马致远的小令创作中表现尤其明显。“本是个懒散人,又无散经济才,归去来。”([南吕]《四块玉·恬退》)[7]200一旦打定主意,原本牢笼般束缚人的世界就变得有趣多了,“共诗朋闲访相酬和,尽场儿吃闷酒,即席间发淡科,倒大来闲快活”([南吕]《四块玉·恬退》)[7]206。而世事无非一场大戏,供我醉中消遣,任现实中风云变换,“醉了由他”([双调]《蟾宫曲·叹世》)[7]212,“不如醉还醒,醒而醉”([双调]《床东原·叹世》)[7]222。
但是“玩世”不过是马致远、白朴人生和杂剧创作的表象,更深一层是内心深处的“至情”。面对史天泽的举荐,白朴“再三逊谢”;对“监察师巨源”的举荐,白朴更是峻拒,甚至赋词决绝表达绝交之意(《沁园春·监察师巨源将辟予为政,因读嵇康与山涛书,有契于予心者,就谱此词以谢》)[10]91。上述情形对两位举荐人来说,不过是没有出现如愿的结果,本身也不是什么大的事情,然而却鲜明地表达了被荐人白朴的态度。举荐人作为白朴的旧交、知音,对白朴的才华、志向应该是了解的,也很清楚白朴应该走的路。也就是说,从他们本身来看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出于好意为朋友尽心。但白朴屡次表现得避之唯恐不及,就不能用“玩世”来解释了,应别有深隐苦衷,而白朴自己给出的理由——“志在长林丰草间”,反而显得太官样文章。《木兰花慢·歌者樊娃索赋》言:“天公不禁自由身,放我醉红裙。想故国邯郸,荒台老树,尽赋《招魂》。青山几年无恙,但泪痕,差比向来新。莫要琵琶写恨,与君同是行人。”[10]119由此可以略见其隐衷。故国之荒台老树,尚且“尽赋《招魂》”,而过去“花月少年场”(《风流子》)[10]131的快乐,“金明老眼,华胥春梦,肠断故都池苑”(《永遇乐》)[10]143的思乡病,曾经家族荣耀、世事巨变、物是人非的记忆,无不交织缠绕、魂牵梦萦,温暖与美好、泪痕与悔恨兼而有之,却四顾徘徊,无可寄托。作者遇到昭君和亲以及唐明皇、杨贵妃故事题材,情感忽然有了宣泄的出口。没有比皇帝更高的地位,没有比华夷激烈冲突更能造成时世的巨变,但在华夷冲突中,即使贵为皇帝也不得不面临失去至为珍惜的美好的境况,并为此陷入无穷无尽、无所安慰的伤悼、痛苦、自责、悔恨之中。汉元帝长门雁叫,唐明皇秋雨梧桐,此情此景,何尝不是马致远、白朴自我心境的写照。在最惨烈的华夷冲突中,最有权势的皇帝,无奈地失去最珍视的美好,没有什么情况比这更能抒发其内心情感了。事实上蒙元灭金源、灭南宋,正是冲突剧烈时期,不仅统治阶层深陷其中,普通人更要在惊涛骇浪中感受身不由己的命运。《汉宫秋》《梧桐雨》二剧借汉元帝、唐明皇抒发作者之“至情”,真挚深沉的情感也让华夷冲突中的普通人感同身受,深深打动着当时的观众。青木正儿评“两种戏曲的收场法,是元曲中不见他例的有力的作品。神韵缥缈,洵为妙绝”[12]92,恰是作者“至情”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之注脚。
(二)“书会”团体与汉人世侯
“书会”团体以及汉人世侯统治对作者杂剧创作“华夷观”特点的形成也有着深刻影响。白朴是大都玉京书会重要成员,马致远是大都元贞书会重要成员[注]《录鬼簿》“李时中”条贾仲明补挽词:“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粱梦》。”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204页。。《录鬼簿》“赵子祥”条贾仲明补挽词:“一时人物出元贞,击壤讴歌贺太平。传奇乐府时新令,锦排场,起玉京。《害夫人》、《崔和檐生》,白仁甫、关汉卿,《丽情集》,天下流行。”[13]188挽词看似简单,其实揭示了很丰富的内容:其一,在元贞年间,有书会这样的创作组织,并出现了很多创作人才,这些人才可能就是书会中人。其二,创作内容方面,有小令、乐府以及传奇,也就是包括了元曲中所有的小令、套数、杂剧三个次级文体。其三,书会还可能出版作品选集,如《丽情集》就是一种书会作者选集。其四,书会还负责组织演出,所谓“锦排场”,可能是指演出阵营豪华。其五,书会之宗旨理念,或者书会创作人员之写作导向,是“击壤讴歌贺太平”。“书会”是民间组织,其宗旨与国家统治阶层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是很有必要的生存策略。杂剧写作的复杂性要求杂剧作者有长时期的学习过程,剧本进入演出市场后,也不能不考虑到演出影响,因此作者除遵守杂剧自身创作要求外,还要遵守“书会”创作导向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像《汉宫秋》《梧桐雨》这样需要表现作者“华夷观”的比较敏感的题材,如果宣扬“夷夏一体”,可能会让对故国还有感情的遗民不满;如果宣扬华夷对立,则又与国家政策相违背。其双重立场以及玩世、超然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比较适宜的折中策略。《汉宫秋》第三折固然有不惜一死决绝反抗的昭君,《梧桐雨》第三折也有请求冒死破贼的乡里百姓,但是起到的作用是进一步衬托统治阶层的可笑以及软弱。慷慨赴死以及忠义报国的行为本身值得赞美,而与“夷”或者“夏”的立场没有太大关系。
汉人世侯本是地方豪族集团,本身具有一定对抗盗贼以及自保实力,先是附金,接着在金元战争中降元,并因战功而被授以显职,与蒙元合作的好处是成为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并能够世袭权力。世侯为巩固其统治,一方面保境安民,一方面招揽知识分子。如真定史天泽,“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贤乐善,偕来游依,若王滹南、元遗山、李敬斋、白枢判、曹南湖、刘房山、段继昌、徒单侍讲,公为料其生理,宾礼甚厚,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其张颐斋、陈之纲、杨西庵、孙议事、张條山,擢用荐达至光显云”(《丞相史忠武王》)[14]123。知识分子与世侯的合作,使自己或者家庭免祸于残酷的战乱,还可能在新的政权获得一定的地位,这使知识分子持感激的态度。白朴和马致远也都有歌颂蒙元统治的作品,在惯于“嘲风咏月,惜玉怜香”的创作中显得极不协调,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作为一种姿态,配合其保护人向朝廷表示忠心耿耿。蒙元虽然以法网宽纵、“未有文字之狱”[15]191著称,但世侯们始终难免被朝廷猜忌,不得不处处谨小慎微。像《赵氏孤儿》这样明显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似乎只有大都作家有此胆量。白朴、马致远等受汉人世侯卵翼的文人,在主流价值观上只能与保护人保持一致,具体到“华夷观”上,对“夷狄”态度缓和,没有像《长生殿》那样出现主动为华夏避“秽事”以及故意设置“骂胡”情节,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多样的观众
观众群的多样性也反过来对作者“华夷观”倾向起着重要作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杂剧为元代之代表体裁,风气所至,作者众多,并非只有不得志的文人投身其中,据《录鬼簿》记载,官僚兼杂剧创作身份者比比皆是。元杂剧作者也并非只有汉人,据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西域地区以及女真、蒙古民族亦多有元曲作者。演员上,“我朝混一以来,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青楼集志》)[13]7。创作家之间互为读者,大量演员、艺人往往也是戏剧作品先睹为快的一批人。著名演员又跟文人士大夫以及权贵阶层来往密切,天然秀之母刘氏“尝侍史开府”[13]23,聂檀香,“东平严侯甚爱之”[16]21。据《青楼集》记载,女伶与名公才人的交往更是频繁。名公才人不论,权贵如史天泽同时也是散曲作家,因此文人士大夫以及权贵构成最有欣赏能力的观众。马致远有散套[南吕]《一枝花·咏庄宗行乐》,庄宗“内藏院本三千段,抹土搽炭数百般”[7]256,可视为影射蒙元皇帝对杂剧的喜爱,皇族可以说是资源最多、地位最高的观众。杜仁杰有散套[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描绘了一个快活的庄家人,可能是第一次到城中勾栏看戏,[16]7114-7115又可以说是最低层次的观众。杂剧的观众覆盖社会上下各阶层,拥有一切的皇帝自不必说,庄家人只要付“二百钱”随时可以一饱眼福,而富有的商人阶层更是杂剧演出消费的主力。元世祖时代的黄文仲所作《大都赋》言:“若夫歌馆吹台,侯园相苑,长袖轻裙,危弦急管,结春柳以牵愁,伫秋月而流盼,临翠池而暑消,褰绣幌而云暖。一笑金千,一食钱万,此则他方巨贾,远土谒宦,乐以消忧,流而忘返。”[17]638元人熊自得《析津志·岁纪》记每年二月八日,大都西镇国寺起庙会,“寺之两廊买卖富甚太平,皆南北川广精粗之货,最为富饶。于内商贾开张如锦,咸于是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18]214。金钱的注入是艺术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商人阶层可以说是有特别贡献的一批观众。蒙元地域空前广阔,蒙元治下,民族成分极其复杂,许衡言:“国朝土宇旷远,诸民相杂”(《时务五事·立国规摹》)[5]428,诸民族之中,有征服者如蒙古族;有征服者之合作者,如善于经营商业的穆斯林民族;也有被征服者,如原西夏之党项、原金源之汉人、原南宋之南人。基于自身立场,他们在“华夷观”上亦有自身之态度、思想和感情。而这种情况又反过来作用于作者,得罪和失去观众对杂剧作家来说不是什么好事,采取并不特别偏向“夷”或“夏”的方式处理“华夷观”,显然是明智之举。作者按照市场需要照顾观众的情感并不是观众对作者的反向作用的全部,事实上,无论是白朴选择的唐明皇、杨贵妃恋爱题材还是马致远选择的昭君和亲题材,在同时代还有其他作者大量同题材创作,而白朴、马致远仍然选择这类题材,归根结底是观众对其抱有浓厚兴趣。旧题材中融入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注入饱满的情感,借戏剧说自己,而观众也在戏剧中看到自己。《汉宫秋》《梧桐雨》二剧都是关于毁灭与失去的悲剧,观众在如泣如诉的音乐和如怨如慕的唱词中,感受到基于“永恒生命”的陶醉与满足,最终成就如尼采所说的“最高艺术的悲剧”[19]97。
四、结语
“华夷观”在不同民族冲突或者融合中产生,蒙元时代激烈的“夷夏之辨”,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相关历史题材杂剧的创作中。《汉宫秋》《梧桐雨》二剧的“华夷观”呈现出基本尊重历史事实、双重性、玩世超然以及蕴含深沉悲剧情感四个特点。从作者自身因素、作者特定生活环境的限制以及观众多样性对作者的反向作用上,大体上可以分析出呈现以上特点的原因。除此之外,杂剧创作更加需要注意其为戏曲创作的特殊要求与特别之处。《汉宫秋》《梧桐雨》二剧作为一代杰作,既受“杂剧”这一文体的约束和限制,也有现实中具体演出的种种限制,因此需要设置戏剧冲突。为在同题材戏曲中占有市场,作者的写作艺术以及写作策略也是关键。因此《汉宫秋》《梧桐雨》二剧与其说呈现的是作者的“华夷观”,不如说是杂剧创作在特定时代与多重现实因素合力作用下呈现出来的特定的“华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