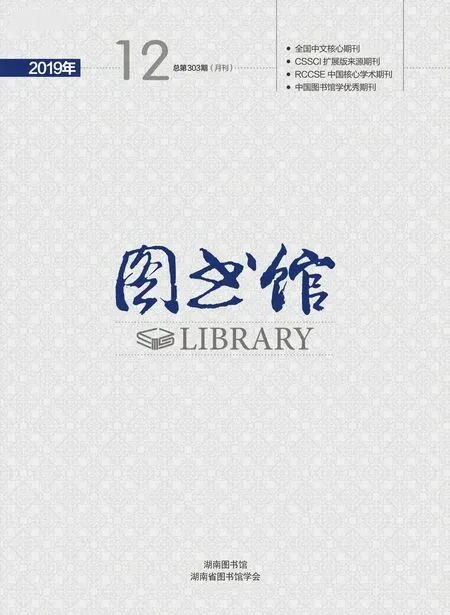章学诚读书观研究及其对当下阅读推广工作的启示
汤谷香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089)
1 引言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他的《文史通义》之著、“六经皆史”之说对后世影响深远。美国著名哲学家、汉学家倪德卫曾如是说:“章学诚是中国曾经出现过的最富吸引力的思想家之一。”[1]2尽管章学诚在生前不为一时通人所认可,茕茕孑立,知音寥寥,然而他的不俗建树,终为后世广泛认同和肯定。自20世纪20年代始,章学诚研究成为显学。一百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章学诚在史学、文论、目录学、校雠学、方志学、教育学等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
回顾章学诚的一生,遭遇的多是坎坷磨难。他自以为迂疏,终未步入仕途,书院讲学成为他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之一。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开始,此后十余年间他先后在定州定武、肥乡清漳、永平敬胜、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主讲。多年求学治学经历,加之书院讲学的经验积累,章学诚对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都很有见地,这从他所写的《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清漳书院条约》《清漳书院会课策问》《清漳书院留别条训》《论课蒙学文法》等文章中即可见一斑。事实上,章学诚这些阐述教育的文章中也蕴含了他丰富的读书观。然而,学术界对他的读书观却鲜有关注。在当今“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过程中,通过对章学诚读书观的研究,探求古代阅读精神,或将给当下阅读推广工作以启迪并使之有所借鉴,这也正是文章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2 章学诚的成长经历与阅读
章学诚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深受家庭“痴书”氛围的熏陶和滋养。史载他的祖父章如璋晚年常常闭门谢客,沉溺于书海,致力于研究《资治通鉴》中所揭示的“天道人事”,这在当时人们普遍笃信天命和天意的时代,可谓相当难得[2]。他的父亲章镳更是秉承章如璋的嗜书品性,但囿于家庭经济困窘,章镳只能以借书来“充饥”。据载,章镳曾借《郑氏江表志》以及五代十国时杂文史籍数种,因这些史籍文体破碎,他甚感遗憾,干脆边抄阅边修改边增删,如此删润之后文章更显练达,内容也更翔实了。后来,章镳还特地将手抄本装订起来,并题为“章氏别本”。可以说,同其父亲章如璋比起来,章镳对书籍的痴迷有过之而无不及。
章学诚并非天资聪颖之人。他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每日诵读仅百余字,不久又因病而不得已中止学业。他年仅十四岁便娶妻,当时还没有完成四书的学习[3]799。显然,章学诚并没能接受系统、持续的教育。此后章学诚的科举之路亦不顺利。乾隆二十五年(1760),他第一次赴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未能中举。隔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他屡试不第,迟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方中进士,时年41岁。中进士后,授官国子监典籍,章学诚却自以为迂疏,于是放弃,终未步入仕途。可以说,章学诚一生坎坷崎岖。然而,在这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中,章学诚从未间断读书,隆冬盛夏读书常至午夜不倦。通过阅读,他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和极强的思辨力。对此,倪德卫曾言及:“在他的思想架构中他展示了极强的原创精神和想象力。”[1]1章学诚亦非中规中矩之人,但他对阅读饱有热情,在思想上也充满活力。乾隆十六年(1751),章学诚父亲章镳受任湖北应城知县。十四岁的章学诚于是随父母前去应城,此时他的父亲为他延请了擅长举业的塾师。然而,他却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并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试图将其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为此他花了三年时间,后来被塾师阻止而作罢。二十岁时,章学诚用节省下来的钱购得吴注《庾开府集》,其中有“春水望桃花”的句子,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其父章镳抹去其注另加评语:“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3]819看到父亲的评语,章学诚顿觉吴注索然无味,也意识到阅读不能被训诂所束缚,而要多思考其中的义理。此后,章学诚读书之时,不再受文本分析的诱惑,亦不陷于支离破碎的训诂,而是能识其大体,理解作者的本意而形成自己的观点。他曾感叹:“乃知吾之廿岁后与廿岁前不类出于一人”。章学诚回顾自己的读书之路总结得出,二十岁以前,性情迟滞识趣寡淡,每天所能看的书不超过二三百字,时间长了,还容易忘记,文字方面尤其对于虚字一窍不通。二十岁之后,逐渐开窍,纵览群书,尽管对经训依旧很难懂得,但阅读时却能领会其意,并能知悉书中的利病得失[3]824。可以说,对于章学诚而言,二十岁是一个分水岭,之后他成了一个如饥似渴的阅读者。值得一提的是,在章学诚阅读的狂热期,他来到了京师大学士朱筠门下学习,得以尽览其丰富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交流,俨然鱼儿回归大海,可以恣意阅读,学业也大有长进。
3 章学诚的读书观——以《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为切入点
乾隆四十六年(1781),章学诚主讲肥乡清漳书院,所教虽以科举时文为主,但谆谆于“大义乃通经之源,古论乃读史之本”,所传为读书、作文、治学的基本方法[4]。他在清漳书院教学期间留下数篇文章,有施教期间与生徒的“条约”,有内容更为丰富的“留别条训”。尤其是《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以下简称《条训》),章学诚从“言别”之语道起,说“人生聚散,固无常期,师友切磋,要契终始”,因故“中道别去,良用抚然”,“自问学植疏芜,凡所指陈,率多浅近”,但临别之言“或为诸生行远升高之助”[3]605。可见,自谦的同时更流露出惜别之际对生徒的留恋和关切。该《条训》洋洋洒洒三十三条,长约一万五千言,条分缕析,殷殷之情,溢于言表。其中有关于他教育思想的真知灼见,也自然流露出他丰富独到的读书观。
3.1 尊经典而读——追本溯源
《条训》开篇第一条,章学诚便谈到:“凡天下事,俱当求其根本,得其本则功省而效多,失其本则功勤而效寡。……诸子百家,别派分源,论撰辞章,因才辨体,其要总不外于六艺。”[3]605在章学诚看来,天下之事皆有其本,读书之事也不例外,虽典籍众多,其根本却无外乎《诗经》《尚书》《礼记》《易经》《乐经》《春秋》这“六艺”。若读懂根本典籍,则能以简驭繁,因枝振叶,沿波讨源。其后章学诚进一步梳理,认为《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左氏》《公羊》《毂梁》《国语》《易》《诗》《书》这十五部经典,“学者纵或不能尽读,不可不知所务者也。”[3]606同时,在《条训》行将结尾时,章学诚再次提及经、史、子、集以及策论中的经典典籍:“家若稍有余资,则经部之十三经与《大戴》《国语》,史部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子部之《老》《庄》《管》《韩》《吕览》《淮南》诸家,集部之唐、宋八家李、杜二家全集与《文选》及《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皆不可缺,而《玉海》《通考》《稗编》之类,又可为策部之资粮也。”[3]624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章学诚建议将这些典籍买下来以便随手研读。
当然,章学诚并非简单的罗列经典典籍清单,他还将这种尊崇经典阅读的理念融入到书院教学之中。譬如,在《条训》第九条章学诚提到:“文字之学,约有三类,主义理者当宗《尔雅》,主形象者当宗《说文》,主音韵者当宗《广韵》。非谓三书足以尽三类之学也,谓其欲究古人之学,宜于是为始基耳。”[3]610他建议童蒙识字以《尔雅》《说文解字》《广韵》为准,这样在初学之时可受到方为正统规范的教育。接着章学诚补充道:“《尔雅》固列十三经矣,《广韵》《说文》部帙无多,各置一册,以时展阅。”[3]610章学诚甚至建议将这几部典籍置为案头常备读物。再如,在讲授论事之文时,建议学生精读《左传》,因为《左传》既有论事,又有事实,是理想的临摹样本。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左传》,可辅之阅读《易》《书》《诗》《礼》,因为这四部书记载了三代及以前之事,这样方可领悟《左传》中所引用的该四书的正文文辞[3]412。
3.2 贵积累而读——铢积寸累
章学诚在《条训》首条明确十五部经典典籍后,接着便在第二条指明积累的重要性,他认为:“学者功夫,贵于铢积寸累,涓涓不息,终成江河。”[3]606治学贵在积累是朴素的真理,章学诚深谙如此,他认为治学也好,读书也罢,就如同涓涓细流,通过一点一滴地积累,而终能成为江河。接着,章学诚核算前文推崇的十五部经典典籍的字数,“亦只六十四五万言而已。中人之姿,日课三百言,不过七年可毕。或遇人事蹉跎,资禀稍钝,再加倍差,亦不过十年可毕。……若移无用之力,而为有本之学,则膏沃者光未有不明,本深者叶未有不茂,事半功倍。”[3]606在章学诚看来,只要坚持不懈,系统地读完十五部经典典籍指日可待;若能潜心阅读,集中精力,更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同时,在积累的过程中,章学诚并不建议走捷径。当时很多士子对时文读本趋之若鹜,章学诚对此极不赞同,他甚至将前人所纂的解读《五经》的《五经类编》《四书备考》等书,视为街市上买来的酒肉,虽有吃却不知其味[3]606。反之,在读书的过程中,若能精读经典,涵咏咀嚼,积少成多,“不嫌识大识小,亦佳事也。……其与仅读评阅选本者,获效多寡,不可同年而语矣。”[3]618此外,章学诚在《条训》第十五条又阐述道:“刘知几论史有三长,才、学、识是也。岂惟作史,天下凡事,莫不皆然。……不知所谓读性,即他日积之而成其学焉者也;所谓作性,即他日积之而成其才焉者也;所谓悟性,即他日积之而成其识焉者也。”[3]613章学诚在刘知几“史才三长”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读性、作性、悟性”之说,读性积而成学,作性扩而成才,悟性达而为识,而这皆是通过多读书、多积累读书经验与心得而逐渐达成的。
3.3 循规律而读——别类分求、分别正闰
其一,遵循记忆发展规律。《条训》第三条:“人生诵读之功,须在二十内外,若年近三十及三十外者,人事日多,记诵之功亦减,自不能如童子塾时专且习也。然年齿既长,文义亦明,及此施功,亦有易于童年记诵之处也。如必不能记忆,则用别类分求之法,统汇十五经传,大而制度典章,小而名物象数,标立宏纲细目,摘比排纂,以意贯之,则程功课效,自能有脊有伦,学问既得恢扩,而文章亦增色采。记诵之功,虽不能全,而贯串之效,则已加敏,是亦不可不知所务者也。”[3]606可见,章学诚并不一味强调诵读之功,他认为读书应遵循记忆发展规律,总角、弱冠之年正值记忆力最佳之时,宜着力于记性,中年之后因诸事纷扰,记忆力下滑,则不必执意于强记硬背,通过对所读之书进行分门别类,把同类的典章故实从书中摘录出来,按照某一脉络进行二次整理,从而达到融会贯通之效。现代心理学认为,记忆可分机械记忆、有意记忆与意义记忆。幼年与少年时期,机械记忆较强;而有意记忆与意义记忆则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增强。由此可见,章学诚的观点与现代心理学的观点不谋而合。事实上,在章学诚所处的时代,高声诵读是常态化的读书场面。曾有外国传教士用惊异的语气来描绘这种场面:“每个学生被指定读书上的一两行,他的‘学习’就是尽其可能高声地朗读。……然而,意义和表达则完全被忽视了……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背诵。”[5]诵读是中华文化记忆传承和知识传播的重要形式,据《周礼》载,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6]然而,章学诚并不拘泥于此,在诵读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读书方法——别类分求,以弥补记忆力下降之憾。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可谓新颖。百余年后,梁启超将这一观点发扬光大。光绪年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分四次连载《变法通议》之《幼学》篇,提出教育改革的全套主张,其中梁启超指摘旧式蒙学偏于“记诵”弊端,关于“悟性”与“记性”,梁启超认为:“大脑主悟性者也,小脑主记性者也。小脑一成而难变,大脑屡濬而愈深,故教童子者,导之以悟性甚易,强之以记性甚难……若不得兼,则与其强记,不如其善悟”[7],梁启超根据其所传递的脑学新说,而主张理解记忆优于死记硬背。这个观点可谓与章学诚的观点若合符节。
其二,遵循注意转移规律。《条训》第十三条:“童幼诵习经书,必须分别正闰。盖中人之性,多是厌故喜新,童幼初学诵习,则厌故喜新为尤甚也。假如学徒资性,每日能诵习三百言者,则使日诵本经止二百言,再授他经亦二百言,必能诵识无疑。是已不知不觉平添百字之功矣。盖一日之间,精神有数,少加变易,使之去故更新,则易于振作,大约可以增倍之差,理固当然。”[3]612如果长期读某一种内容的书,注意力往往容易分散,反而不易掌握。对此,章学诚提出“分别正闰”之法,也就是主张一日之内,几种内容穿插进行阅读。与章学诚基本处于同一时代的德国著名才子卡尔·威特,他出生后被认为是个有些痴呆的婴儿,但在他父亲后天的科学教育下,卡尔·威特成长为一名精通多国语言、通晓多门学科的才子。卡尔·威特的父亲总结出了八个重要的学习方法,其中一个便是交叉学习法。对此,《卡尔·威特的教育》中如是谈到:“交叉学习法,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根据情况不时地转换学习内容。这种学习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始终处于兴奋中。”[8]197所谓交叉学习法,其实与章学诚的“分别正闰”之法异曲同工。《卡尔·威特的教育》一书在问世近200年的时间内,培养出了近代像赛德兹、威纳·巴尔以及维尼夫雷特等无数世界级的通过早期教育成才的典范[8]。上述这些成功案例,从侧面佐证了章学诚“分别正闰”读书法的科学性。
3.4 从辩证而读——博观约取
如何看待博与约的关系,历来是中国古代学者文人讨论的焦点。有的学者偏重于博。比如章学诚的老师朱筠认为:“学者读书求通,当如都市逵路,四通八达,无施不可,非守偏隅一曲,便号通才。”[3]494意思是学者读书不能局限于一畛域,而应在各个畛域都有所涉猎。朱筠的观点体现了乾嘉时代的主流意识,当时学风贪多求全,一意以渊博来炫耀于人,甚至还有“一物不知,儒者所耻”的说法。而有的学者则偏重于约。比如明末清初文学家胡承诺在其所著《读书说》中便提到:“其始也专精一书,一书之指既为吾有,所得虽少,皆有实际,以此更历诸书,亦皆实际矣。”[9]在胡承诺看来,读书伊始宜专门钻研和精读一本书。章学诚取两家之长,认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尽之生而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而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3]338人生有限,书籍无穷,欲以有限的生命,穷尽浩如烟海的群籍,那便是自不量力。又说:“大抵学问文章,须成家数,博以聚之,约以收之,载籍浩博难穷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专精致力之处,则如钱之散积于地,不可绳以贯也。”[3]741若只是漫无边际的泛览,而无专精之处,则如钱散于地而不可拾也。章学诚认为应持辩证态度来看待博与约二者关系问题。他在《条训》第十七条明确指出:“博学守约,凡事皆然。即举业一道,博约二者,阙一不可。所谓守约,即揣摩之文,贵于简练,是矣。所谓博学,则泛阅之文,又不可不广也。”[3]614章学诚认为博与约阙一不可。
为了进一步说明博与约的相互关系,章学诚还在《文史通义》中写了《博约》上中下三篇、《博杂》一篇,加以论述。《博约》中:“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3]117章学诚阐明:博与约应是并行不悖的,不可仅执其一端。一方面,“博”要广泛阅读,“少或三数千篇,多至万有余篇”,在泛读中感受文章的气韵,“上下窥其风气,分晰辨其派别,错综通其变化。”[3]614另一方面,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认真揣摩其中的三五百篇佳作。章学诚还列举了十个视角以供揣摩:“命意,一也;立句,二也;行机,三也;遣调,四也;分比变化,五也;虚实相生,六也;反正开合,七也;顿挫层折,八也;琢句,九也;练字,十也。”[3]615这十个视角简言之即四个维度:一是立意,二是内容与结构,三是写作方法,四是语言。综上所述,章学诚提倡“博观约取”,并且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未停留在纯理论宣教层面,还进一步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具体方法。
3.5 勤札记而读——贵有簿记
《条训》第十九条:“阅文固贵有簿记矣,诵读经书一切学问中所有事,何者不当有簿记乎?”[3]615章学诚主张读书时勤做札记,他曾生动形象地说明札记的重要性:“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3]815这就是说,如不及时做笔记,读书时的体会、见解,随着日子的流逝,会无形中忘记,犹如雨落大海般,将无处可寻。其实,人们读书时,谈及这一点,难免不产生共鸣。宋代苏轼在其《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一诗中便写道:“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10]苏轼恐怕稍有延迟,所见清丽之景会从脑海中消失,再也难以描摹。
康熙朝理学名臣李光地曾在《摘韩子读书诀课子弟》中谈到:“凡书,目过口过,总不如手过。盖动手则心必随之,虽览诵二十遍,不如钞撮一次之功多也。”[11]手抄确能有助于记忆。但在章学诚看来,札记之功远非如此。首先,他认为:“札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3]741。札记不单是用来帮助记诵,积累知识,还是“读书练识”的一种重要手段。因为札记并不是简单机械的抄书,而是在读书过程中随时记下心得体会。它是锻炼思维能力,培养独立见解“练识”的重要途径。其次,章学诚又说:“读书服古,时有会心,方臆测而未及为文,即札记所见,以存于录,日有积焉,月有汇焉,久而久之,充满流动,然后发为文辞,浩乎沛然,将有不自识其所以者矣。此则文章家之所谓集义而养气也。《易》曰:‘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存记札录,藏往以蓄知也;词锋论议,知来以用神也。不有藏往,何以遂知来乎!”[3]587通过日积月累的做札记,久而久之,便能对已往心中了然,对未来有所预见。总之,通过“存记札录”,可积累知识,“读书练识”“藏往以蓄知”。这个过程,可谓知识在头脑中“发酵”的过程。
3.6 善发散而读——启悟于无方
章学诚一贯主张“读古人书,贵能知其意也”[3]515,对此,章学诚在《条训》第二十三条如是说:“学者株守尘册,终无进步,诚有卓尔之志,所贵启悟得于无方。昔蔡中郎渡江,得见《论衡》,北方人士,觉其谈说有异,此因文章而得于语言者也。叶石林读《史记·货殖传》,见陶朱公‘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之言,遂悟作文之法,此因语言而得于文章者也。担夫争道,草书何以入神?坏屋颓墙,绘画何以通妙?诚能即其性之所良,用其力之能赴,则半日读书,半日静体,游心淡漠,鬼神潜通。”[3]618至于“无方”,是思维路径的不确定,亦是思维方法的不确定。所谓“启悟于无方”,即不由通常的理解途径,不由常识的理解逻辑,透过现象看本质,同时用善于发现的眼睛去探寻似乎不相干之处的内在相通本质。换言之,读书时通过思考,不受文本本身所局限,而是从阅读文本入手,由此及彼、由浅及深,进而领悟其中深意,达到融会贯通之效。现代学人张弛在《写作构思的模型》一书首次提出:“阅读,可以分为封闭式阅读和开放式阅读两大类型”,前者“以把握文本的本义为目的”,后者则“以创造性地利用文本为目的”[12]。章学诚主张的这种发散性阅读观,实际上与今人所提开放式阅读内涵趋近。
总之,《条训》虽是章学诚担任清漳书院院长时,因“中道别去”而与诸生的竭诚留言。不可否认的是,清代书院多以举业训练为要务,章学诚作为书院举业之师,他在《条训》中整体行文围绕举业而展开,且强调以儒家典籍为阅读之本,这当然没有脱出时代窠臼。但难能可贵的是,《条训》中表达出章学诚尊经典而读、贵积累而读、循规律而读、从辩证而读、勤札记而读、善发散而读的读书观,表明他虽推崇阅读经史,但并非仅仅局限于举业之文,而更多的是向书院学生灌输读书向学要脚踏实地的理念,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探求义理,希望学生能从中获取真才实学,达到融会贯通之效。难怪梁启超如此强调章学诚思想解放的价值:“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13]48然而,在追求考据的乾嘉时代,这是另类的,梁启超曾这么评价章学诚:“学诚不屑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13]48,梁启超把章学诚看作是被清代汉学正统派掩盖了的异端。
4 章学诚读书观对当下阅读推广工作的启示
从章学诚所著《条训》,我们不难看出他作为书院师长对士子的知识期待。他主张涵咏经典,追本溯源,不走捷径;尊重身心发展规律,提出差异化读书策略;引导发散性阅读,不局限于阅读文本本身。他的系列读书观,时至今日,亦不无借鉴意义。
4.1 启迪经典阅读
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已经连续6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一方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全民阅读和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全民阅读对国家文化建设和提高国民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全民阅读活动的有序推进,全民阅读氛围日益浓厚。据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2018年中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80.8%,保持增长势头;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76.2%,也有所增长。然而不可忽视的是,2018年中国成年国民上网率为78.4%。其中,在网上活动行为中,以阅读新闻、社交和观看视频为主,娱乐化和碎片化特征明显,深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有15.9%的网民将“阅读网络书籍、报刊”作为主要网上活动之一[14]。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传统阅读模式已有所改变。如今我们身处浅阅读时代,阅读内容包罗万象,阅读活动也不再受时空所局限。然而,面对如此丰富的阅读内容以及便捷的阅读手段,不少人却陷入了迷惘与空虚。因此,在信息爆炸到让我们都有些无所适从的今天,章学诚“尊经典、贵积累”的读书观启迪我们要倡导经典阅读,不要急功近利,通过经典阅读的积累,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从而增强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4.2 倡导科学阅读
读书有法,自无疑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阅读方法的运用,在阅读过程中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章学诚提倡的“循规律、从辩证、勤札记”的读书观,提供了一套可借鉴的科学的阅读方法。首先,迎合记忆力发展曲线和注意转移规律,长期阅读时,平衡“记性”与“悟性”二者的关系;短期阅读时,注意不同内容的穿插阅读。其次,辩证的看待“博”与“约”的关系,以免在浩瀚的书海中迷失了方向。此外,阅读过程中采用科学的方法——札记,通过高质量的札记,达到掌握知识,提升认知能力的目的。总之,一套科学的阅读方法是相互联系的,它贯穿于阅读的全过程,只要能持之以恒,相信能提升阅读效率,取得良好的阅读效果。
4.3 引导思辨阅读
经典文本具有丰富、多元的内涵,故而能常读常新。然而,人们的认知是有限的,在阅读时难免会面临文本性固化、整体感虚化、批判性退化等问题的挑战,往往偏向于对阅读文本的一元解读,这好比“盲人摸象”,往往只能在特定的层面和角度去认知内在真理。若要跳出阅读定势,则需要引导思辨阅读。思辨性阅读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探究性、创造性的追求科学精神的历程,它对于引导阅读者知常达变,建构独立、自主、理性、思辨的阅读能力有重要价值。章学诚主张的“启悟于无方”的发散性读书观,就是通过引导思辨阅读,积极审思,培育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等素养,形成动态的思维学习过程,由此及彼,融会贯通,进而激发解决问题的潜能,达到思辨和科学精神同生共长的境界。
法国汉学家保尔·戴密微称章学诚“用其天才的思想火花,照亮了那个特别黑暗的世界”[15]。在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过程中,挖掘章学诚的读书观,探寻中国传统阅读精神,借鉴中国古代优秀的阅读传统和经验,将照亮着我们当下的阅读之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