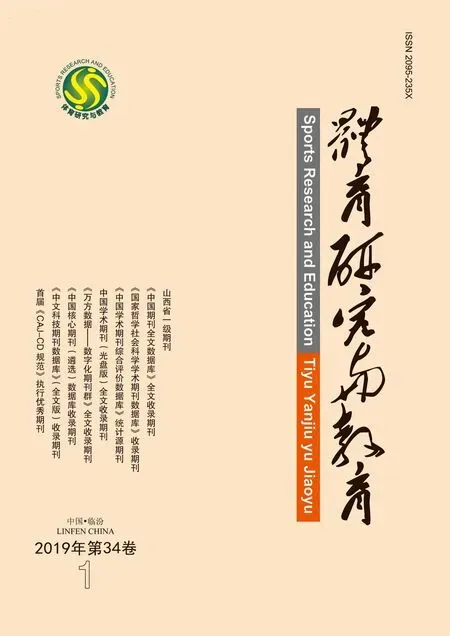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时期侠的形态与文化研究
侯天媛,郭玉成
1 魏晋南北朝时期侠的形态与文化兴起的历史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合称,始于汉献帝禅位给曹丕的黄初元年(220年),结束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历时共370年,前后经历了三十多个大小政权。“魏”是指三国时期的曹魏,“晋”是指司马氏建立的西晋和东晋,“南北朝”是指多个南北对峙的时期,其中包括南方的宋、齐、梁、陈和北方的北魏、东魏、本魏、北齐、北周。在魏晋南北朝期间,除了西晋时期经历了短暂的统一,大多数时间战乱四起、朝代更迭、自然灾难频发,民族冲突剧烈,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和混乱的时期。原本隐形的不稳定因素——侠,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也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加而重新活跃起来,并受到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变化的影响。
侠文化自先秦时期形成以来,就受到中国古代多元思想的影响,既融入了儒、墨、道等学说的思想,也受到先秦时期社会风气的影响。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侠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出现变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的思想大解放时期,此时佛教传入,玄学兴起,儒学和老庄哲学被重新定义,这些思想文化的变化自然会在传播中影响到侠文化的发展。同时,政权林立,朝廷腐败,战乱连年,文人们言论受限,于是多以咏侠来表达自己的壮志难酬之心,这些思想和情绪的变化在史书及诗歌中也都可觅其据。
史书中对侠的记载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中专门设有《游侠列传》篇以及《刺客列传》篇。太史公对游侠的评价很高,“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1]班固的《汉书》中仍列有《游侠篇》,但班固认为游侠虽“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但仍然“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罪已不容于诛”。[2]故继汉代以后史籍中鲜有侠的传记。
尽管正史不载,但有关侠的文字记载并没有消失,更多是以文学形式进入诗歌和辞赋中。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内容的极大丰富,加之当代的任侠风气和文人表达抱负的需要,以侠文化为主题的诗歌涌现出来。诗歌中侠的形象通过文学渲染的方式使其更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这种文体的转变也反映了当时从现实中的侠到精神上的侠的需求的转变。侠文化中侠的人格特质已成为文人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
2 三国时期侠的形态及文化
2.1 侠的涌现基于特定的时代环境
自三国烽烟燃起,儒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辉煌就已经开始消散。人的思想冲破桎梏,迎来了中国历史上自百家争鸣后的又一个文化繁荣时期。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移,封建教义的约束逐渐淡化,人开始追求自我的天性解放,人的思想从封建政治教化的牢笼里走向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化也从一枝独秀走向百花齐放,玄学兴起、道教勃兴、佛教传入以及波斯、希腊文化羼入都是在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虽有着与战国时期相类似的分崩离析、封建割据,但所不同的是随着胡人入主中原,中原本土文化首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并呈现出从保守到开放的转变。尤其在佛学兴起后,儒释道的纠缠在一次次碰撞中融合又对立,侠也从两汉时期的销声匿迹,逐渐重回人们的视野。但此时的侠与春秋战国时期无我无畏的古典性格相比有了新的特点,他们不再只远离官府,游历民间,而是愿意用自己的能力建功立业,开启仕途生涯。
东汉末年,为了安抚黄巾之乱,汉灵帝将权力下放,致使掌握了军权的州牧纷纷割据一方,很多游侠趁机借助世族的能力和声望从游离状态进入权力中心,执掌兵权。经过连年战乱,逐步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此间,群豪相争、英雄辈出,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侠义故事。
2.2 三国时期应运而生的古典豪侠
三国时期,风云激变,英雄迭出,无论是谋臣还是武将都有充分的机遇施展才华,正所谓“人才莫盛于三国”。其中,曹操唯才是举,又重权在握,“挟天子以令诸侯”,致使天下英才争相以赴,麾下人才济济。正如曹丕在《典略》中所述,“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然而,曹操帐中虽谋臣如雨,猛将如云,但鲜有高风亮节的侠士。典韦是其中为数不多令人景仰的豪侠之一,《三国志》中载典韦:“形貌魁梧,膂力过人,有志节任侠。”典韦的同乡刘氏与李永有仇,为给刘氏报仇,典韦驾着车,车上带着鸡和酒,假意等候,待“门开,怀匕首入杀永,并杀其妻”,而后,典韦带上刀戟,不慌不忙地离开。“永居近市,一市尽骇。追者数百,莫敢近。”[3]典韦为友报仇,有气节,有谋略,有胆识。为曹操效力后,数次杀敌有功。在与吕布的濮阳之战中,曹军本想夜袭濮阳,却遇吕布设防,幸好有典韦拼死冲杀,曹操才得以突围。后张绣军反叛,典韦为保护曹操力战身亡。曹操闻后痛哭流涕,派人取回典韦尸体,使典韦得享从祀于曹操庙庭。不同于荆轲的悲悯,不同于豫让的隐忍,不同于侯生的谦恭,典韦酣畅淋漓地将豪侠的勇猛、睿智、果敢、刚毅、忠诚践行至极致。
乱世之中,鸡鸣狗盗之人尤盛,且多为名利不为名节。因此鱼豢在《勇侠传》中提到三国时代的四位古典侠客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受到当时很多人的尊敬。
据记载,孙宾硕曾冒死收留隐姓埋名的逃犯赵岐。赵岐的侄儿赵息由于得罪宦官唐氏兄弟遭迫害而被满门抄斩,赵岐听闻后只好卖烧饼以掩饰逃亡。孙宾硕路遇赵岐,了解实情后和母亲共同商量把赵歧藏在了自家的复壁之中数年之久。祝公道是三国时期郭援的手下,郭援攻城成功后想杀掉魏国名臣贾逵,但因众人阻止,怕失了民心,才下令把贾逵关入狱中。祝公道认为贾逵是个义士,因此不惜冒生命危险闯入牢中解救出素昧平生的贾逵,却未向贾逵索要分文。杨阿若,字伯阳,喜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豪强黄昂为复仇击杀酒泉太守徐揖,杨阿若认为黄昂不义,欲为徐揖报仇,但又苦于自己势单力薄,便求助于武威太守张猛。张猛遂封杨阿若为都尉,命他讨伐豪强黄昂,却不给他一兵一卒,杨阿若无奈之下,只好凭借个人力量单骑突围,搬救兵诛杀黄昂,这件事轰动一时。鲍出是个守孝义的人,在遭到土匪劫掠时,只身救出被土匪劫走的老母和邻居老妪,后为躲避战乱与母亲逃至南阳,待战乱平定,其母思乡,便用竹筐背着母亲翻山越岭回到家乡。后人赋诗赞其曰,“救母险如履薄冰,越山肩负步兢兢;重重危难益坚忍,孝更绝伦足可矜”。
鱼豢曾言:“……今故远收孙、祝,而近录杨、鲍,既不欲其泯灭,且敦薄俗。至於鲍出,不染礼教,心痛意发,起於自然,迹虽在编户,与笃烈君子何以异乎?若夫杨阿若,少称任侠,长遂蹈义,自西徂东,摧讨逆节,可谓勇而有仁者也。”[3]汉魏四侠的出现,代表的是一种古时游侠之风的延续和复兴,是与战国时期相似的战争频仍的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相似形态的侠,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古时之侠的崇拜和渴望。
2.3 建安文学影响之下的侠风渐起
曹植的《白马篇》是一篇文采与豪情兼备的佳作:“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4]诗中描述了游侠骑马秉弓驰骋在沙漠中,遇到敌军时骁勇善战,身手矫捷的场景,生动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视死如归的少年游侠形象。
曹植对英雄少年歌颂,同时也是对自我理想的写照。他所赞扬的顾全大局、为国捐躯的侠义精神,正是他的个人理想。曹植在诗中将慷慨赴义的情怀与游侠的形象联系起来,体现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儒家思想与侠文化的融合,提升了侠的价值,扩充了侠的外延。
曹魏时期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大繁荣时期,出现了以建安文学为代表的文学观念的转变和文学价值的独立[5]。钱穆认为,中国纯文学独特价值之觉醒,正是在建安时代“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作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书写灵性,歌唱情感”[6]。即此时之文学在于“无意于施用”,而只纯粹表达个人情感的方式。时值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文人士大夫大都亲身经历过战乱,他们常常同情底层劳苦大众的悲惨际遇,同时又积极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因此侠拯救百姓家国的主题十分契合当时文人的心态,咏侠诗即文学之自觉和文人之自觉的体现。而文人对侠的咏赞,不仅表达了作者本人的侠义之心,也将侠的形象从两汉时期“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上升至心怀天下,为国捐躯的新高度。
汉魏之际,战乱蜂起,为有志之侠提供了诸多机遇和挑战。在思想解放、战乱频繁的背景下,此时的侠有了新的特点:首先,侠的社会功能有所扩充。他们不再只为乡邻朋友打抱不平,也不再只寄人篱下、靠出卖武力维持生计,而是有更多的机会能够领兵作战,驰骋沙场,为国效力。这样的侠士在三国时期也不在少数,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有才之士辈出,大浪淘沙,经过历史沉淀能够千载传唱的也只有那些真正心怀天下的侠士。其次,侠的地位有所提升。三国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各个军事集团之间利益与权势的分配不均衡而引起的社会动荡。而此时,有志报国的人不仅源于草莽之间,还有很多从小接受精英教育的文人士族也投笔从戎、征战疆场。他们走向底层,体验民间疾苦,用文学、音乐、书法等方式抒发自己所看所感,肯定侠的价值,弘扬侠的精神,赞颂侠的品质,对侠的形态和文化的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
3 两晋时期侠的形态及其表现
3.1 魏晋风骨坚守儒侠精神
学者刘诚龙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解放天性的时代,第一次出名士,第二次出怪人。其所谓的第一次就是魏晋时期,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超然脱俗的名士风度,又称为魏晋风骨。这是在当时特定社会背景下所形成的一种由士阶级兴起的审美潮流,逐渐蔓延开来影响到整个社会。唐代诗人杜牧也感叹道,“大抵南朝都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这种风流并非是彻底的放纵和放荡,而是不满于社会现状的一种无奈和对当朝者的反抗,是他们对于内心正义的坚守,魏晋风骨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是当时最具侠骨之人。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非“竹林七贤”莫属。嵇康居山阳,《晋书·嵇康传》载,“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时值司马氏篡位当权,曹魏集团的谋臣武将相继被杀,被牵连人数达五千之多,政治腐败,军阀混战,文人无法发声,他们虽悲愤难平但又无可奈何。竹林七贤每个人都才华横溢,但他们既不愿违背自己的意志而接受司马氏的示好,又担心公开拒绝会遭到残暴的司马集团的血腥杀戮。于是,七贤被迫采取消极态度,假装不问世事,躲在山里过着清贫的生活,终日纵酒狂饮,放浪形骸,以此排解烦恼,躲避灾难,以间接的表达他们宁愿隐居山林不愿同流合污的坚决态度。
嵇康虽为文士,但他心系家国,甚至企图募兵响应毋丘俭征讨司马的行动,为人心善、敢爱敢恨,与道不同的朋友划清界限,不攀附权贵,不屈尊强权,是一种广义上的侠。他的尚奇任侠与避地退隐,是一种矛盾,而恰恰是这种矛盾纠结的状态,使其能抓住机会坚持与黑暗权势进行斗争,同时又以避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嵇康之所以为人们所崇尚和追随,不仅仅是其所显现的魏晋风骨,更多是侠义的集中和体现,他的玄学主张和精神追求也为当时的任侠之风开辟了一种新的方式。嵇康虽为一代名士,他身上散发的侠者的精神和魄力,他行为里展现出的侠者的无畏和果敢,成为了后世侠者效仿的典范。
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张华学识渊博,胆识过人,受晋武帝重用,一生忠君爱国,政绩卓然。张华年轻时曾创作《游侠篇》:“翩翩四公子,浊世称贤明。……美哉游侠士,何以尚四卿。我则异于是,好古师老、彭,”[4]借战国时游侠和四君子的典故,赞赏他们的贤明,同时又表达了自己与他们所不同的志向,即更愿意追随老、彭。这种追求,是儒学衰微,老庄哲学取得主流地位的体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则是传统的侠文化中被赋予了更多的道家色彩。
3.2 士族门阀制下的勇侠世家
篡权夺位而来的政权始终难以服众。西晋经过短暂的统一后,很快又进入东晋十六国的分裂状态。中国北方陷入分裂混战,大量少数民族南迁中原,世族为了统一不得不率军北伐。祖逖就是其中北伐的代表人物。《晋书》记载,“逖性豁荡,不修仪检,年十四五犹未知书,……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散谷帛以周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祖逖长大后始才博览群书,见到他的人都称赞他的才华。“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7]后人便用“闻鸡起舞”比喻有志报国的人及时奋起。祖逖不仅心系百姓家国,而且更愿意用冲锋陷阵、建功立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报国志向。
公元313年,晋愍帝即位,司马睿手握军政大权,率兵赴洛阳勤王。于是祖逖进言司马睿,希望能够挥师北伐。因司马睿一心只想巩固江东政权,无心北伐,于是只象征性的拨给祖逖少许粮食作为北伐物资。但祖逖并没有放弃,他带着随他南下的部曲百余家北渡长江。祖逖等人自力更生,从起炉冶铁、铸造兵器,招兵买马起,经多年不懈努力,加之祖逖过人的军事谋略,终于成功收复中原地区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土地。祖逖不仅具有军事谋略,还礼贤下士、体恤民情。不仅对将士赏罚得当,同时劝督农桑、发展生产,还收葬枯骨,深得民心。晋元帝也对他的功绩十分肯定,下诏擢升他为镇西将军。唐代魏元忠评价说:“夫有志之士,在富贵之与贫贱,皆思立于功名,冀传芳于竹帛。故班超投笔而叹,祖逖击楫而誓,此皆有其才而申其用矣。”[8]“心系天下,侠之大者。”祖逖凭借个人力量招募大军,铸造兵器,挥师北伐,收复中原,保护一方百姓使其能够安居乐业,这对于连年征战的魏晋时期而言实属难得。
在晋朝,除了像嵇康、祖逖这样心怀大义的侠士之外,还有许多所谓的豪侠、游侠,其虽以侠之名,却趁社会动乱做抢劫盗窃之类的勾当。晋朝时期的糜烂腐化是自上而下的,当时的贵族生活乐趣在于近乎变态的享受,故有石崇和王恺斗富的现象,也产生了各种奇葩的纨绔子弟,整日无所事事,以行侠为由,实为攀比和消遣。
《晋书》记载,“戴若思,广陵人也,……若思有风仪,性闲爽,少好游侠,不拘操行。” 戴若思年少时性情豪爽,好行侠仗义,但也经常做一些抢劫之事。偶遇陆机赴洛,陆机见其抢劫船只,却仪态挺拔,气度不凡,指挥得当,知非常人,便对其进行劝解,“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剑就之”。[9]戴若思改邪归正之后,被人举荐至洛阳军中,由于才华出众,作战勇敢,表现突出,很快一路升迁至征西大将军,后在王敦之乱中遇害。晋朝时期,少年游侠多以武力劫掠为乐,如同戴若思这样最终能够为社会效力尽忠的真正侠士凤毛麟角。
3.3 国家危难时文侠的报国之思
东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频频入侵,不少豪强恃强凌弱,趁乱抢夺普通百姓的资产。这一时期,大多有志之侠都投身军队,报效国家,他们虽然最终沦为权利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他们对于和平安定和人民幸福和追求,并没有因此而磨灭。因此到了后期,文人士大夫通过赞颂他们的功绩表达了当时社会所追求的愿望,文人咏侠也成了一种潮流。据统计,这一时期咏荆轲的诗达十首之多,足见这一时期文人对于侠者精神的认可。诗歌中的人物形象经过艺术加工更加饱满生动,对于侠文化的传承和颂扬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陶渊明,东晋诗人、辞赋家,以淡泊名利,热爱田园而闻名。陶渊明也曾有过十三年的仕途生涯,但他最终还是由于对当时的政治和官场失去信心而决意归隐,他写过一首《咏荆轲诗》:“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4]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许多诗中,都曾表现过自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而恰恰这一首才是诗人的真情流露。诗人赞赏侠者荆轲的万丈豪情,愿为国难而慷慨捐躯,同时也暗含对晋朝灭亡的痛惜。陶渊明一直忠于晋朝,在晋灭亡后宁愿隐居山林过贫苦的生活,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出任官员。这首《咏荆轲》与其他田园诗的对比更真实地反映出陶渊明生不逢时、不能为国效力的遗憾,故而只好隐居山林,寄情于山水。
在两晋时期,侠的特点为:第一,文人名士为侠的群体和文化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西晋士族与皇权的斗争中,士族处境险恶,人生飘忽,儒学衰微,玄学兴起,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士族以寄情山水的方式表达自己不愿同流合污的政治理想,文人自觉追求的自由和自主被世人称作是任侠的典范,也向侠文化中融入了道教、玄学的思想。
第二,戍守边关的将领改变了侠的气质。东晋时期,皇权衰落,世族门阀崛起,甚至有的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权,上与皇权共治,下与庶族对立,并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10]的局面。寒门庶族虽不能进入上流,但他们征战沙场,豪情磊落,报效国家,既有侠的情怀,又有侠的气节,还赋予了侠除报恩复仇之外的更加骁勇绝人的气质。
第三,豪侠趁乱打劫也是两晋时社会混乱的恶果。士族制度之下,贵族子弟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把任侠作为一种消遣手段,而其任侠的方式无非欺压百姓、打家劫舍,并以此为乐。
第四,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咏侠风气渐浓。在民族分裂的社会背景下,“捐躯赴国难”的侠客成为人们的期待。文人对这些侠的美化和颂扬,是表达自我抱负的方式,也是社会尚武风气的体现。
4 南北朝时期的任侠风尚
4.1 胡汉文化融合形成尚武之风
相比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更为频繁,经济文化变革更为剧烈。在这种特殊历史阶段的复杂背景下,很难有个人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拯救黎民苍生,但随着汉化和胡化两种风气的融合,尚武任侠之风愈加受追捧,这一现象在南北朝的史料和诗歌中都能够清晰寻迹。
南北朝时期尚武风气浓厚。这一时期的史籍在评价一个人的性格时,往往从勇武任侠的角度加以评判:
《陈书》记载:“杜僧明,字弘照,广陵临泽人也。形貌眇小,而胆气过人,有勇力,善骑射。……子雄弟子略、子烈并雄豪任侠,家属在南江。”[11]“鲁悉达,字志通,扶风郿人也。……悉达虽仗气任侠,不以富贵骄人,雅好词赋,招礼才贤,与之赏会。”[12]“周炅,字文昭,汝南安城人也。祖强,齐太子舍人、梁州刺史。父灵起,梁通直散骑常侍、庐、桂二州刺史,保城县侯。炅少豪侠任气,有将帅才。”[13]
《梁书》记载:“邓元起,字仲居,南郡当阳人也。少有胆干,膂力过人。性任侠,好赈施,乡里年少多附之。起家州辟议曹从事史,转奉朝请。雍州刺史萧缅板为槐里令。迁弘农太守、平西军事。”[14]
《宋书》记载:“龙符,怀玉弟也。骁果有胆气,干力绝人。少好游侠,结客于闾里。早为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龙符为建武参军。江乘、罗落、覆舟三战,并有功。”[15]
这些史料中记载的人物,都被冠以侠以评判其人物的品性,足以说明在当时社会侠风尚武之盛,而这些人能够千古流传,和其侠性也有重要关系。
4.2 南北朝咏侠诗繁荣发展
如学者汪聚应所述,“中国侠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历史化现象,包含着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的丰富内涵,中国侠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侠的历史化变迁史、一部史家与文人的共建史、一部文人的心路历程史。”[16]
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繁荣之下有大量的诗歌传世,其内容也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社会的尚武之风也使得诗歌成为侠文化传承的载体。南朝士人普遍重文轻武,文人慕侠咏侠却只是抒情咏志,诗风多华丽轻艳。与南朝的诗歌相比,北朝的诗歌有更多关于尚武和战争的描写,反映了北朝人民豪迈尚武的特性,诗风也是大气磅礴,粗犷豪放。这种风格在后来也随着南北文化的交融而逐渐蔓延。
南朝诗人庾信的《结客少年场行》就是当时南朝诗歌的典型,充满了轻艳华靡的风气:
“结客少年场,春风满路香。歌撩李都尉,果掷潘河阳。隔花遥劝酒,就水更移床。”[17]诗的主题虽仍沿用咏侠乐府《结客少年场行》的古题,但其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柔艳的女人的脂粉香气,毫无游侠少年慷慨激昂之感。
北朝的《乐府诗集》中有很多关于民族尚武,以及战争残酷和爱国英雄的诗篇。其中《折杨柳歌辞其五》:“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跸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18]通过描写健儿纵马奔腾于原野之上的场景,将少数民族刚猛勇武的性格生动的展现出来,使人如同身临其境感受到健儿的恣意驰骋和昂扬姿态。
《木兰诗》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北朝乐府民歌,所讲述的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作为巾帼不让须眉的典范而千古流传:“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18]全诗节奏明快,酣畅淋漓,塑造了一个热爱家庭,热爱国家的勇敢女侠形象。诗中表现出的男女平等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方民族豪气开放的文化特点。中国传统的忠孝和北方平等的男女观的结合,正是当时南北方文化的融合的体现。
南北朝时期多元的文化基因极大丰富了咏侠诗的内容,情感和表现形式,使侠文化的表达方式更加丰富多彩,其精神特质和人格特点经诗意的渲染和提炼之后,更加的纯粹和精炼,使咏侠诗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同时也为唐朝咏侠诗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5 结语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其间的三百余年中,除西晋存在短暂的统一外,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分裂状态。而这种政权上的动荡和分裂,却催生出意识形态的解放和繁荣。所谓乱世出英雄,时局动乱为侠的再次兴起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思想上的解放又将侠从群体形态推向文化的新境,赋予其高尚的精神和不羁的人生态度,使侠成为文化载体和精神脊梁。这一时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为侠文化留存了一方滋养的土地,为后世侠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促使侠成为中国人心底里隐藏的品格和梦想。时至今日,侠的实体形态虽已消失,而侠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活跃于文学与影视作品中,成为大众所传颂赞扬的永恒话题。